一场斗争的描述.docx
《一场斗争的描述.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一场斗争的描述.docx(3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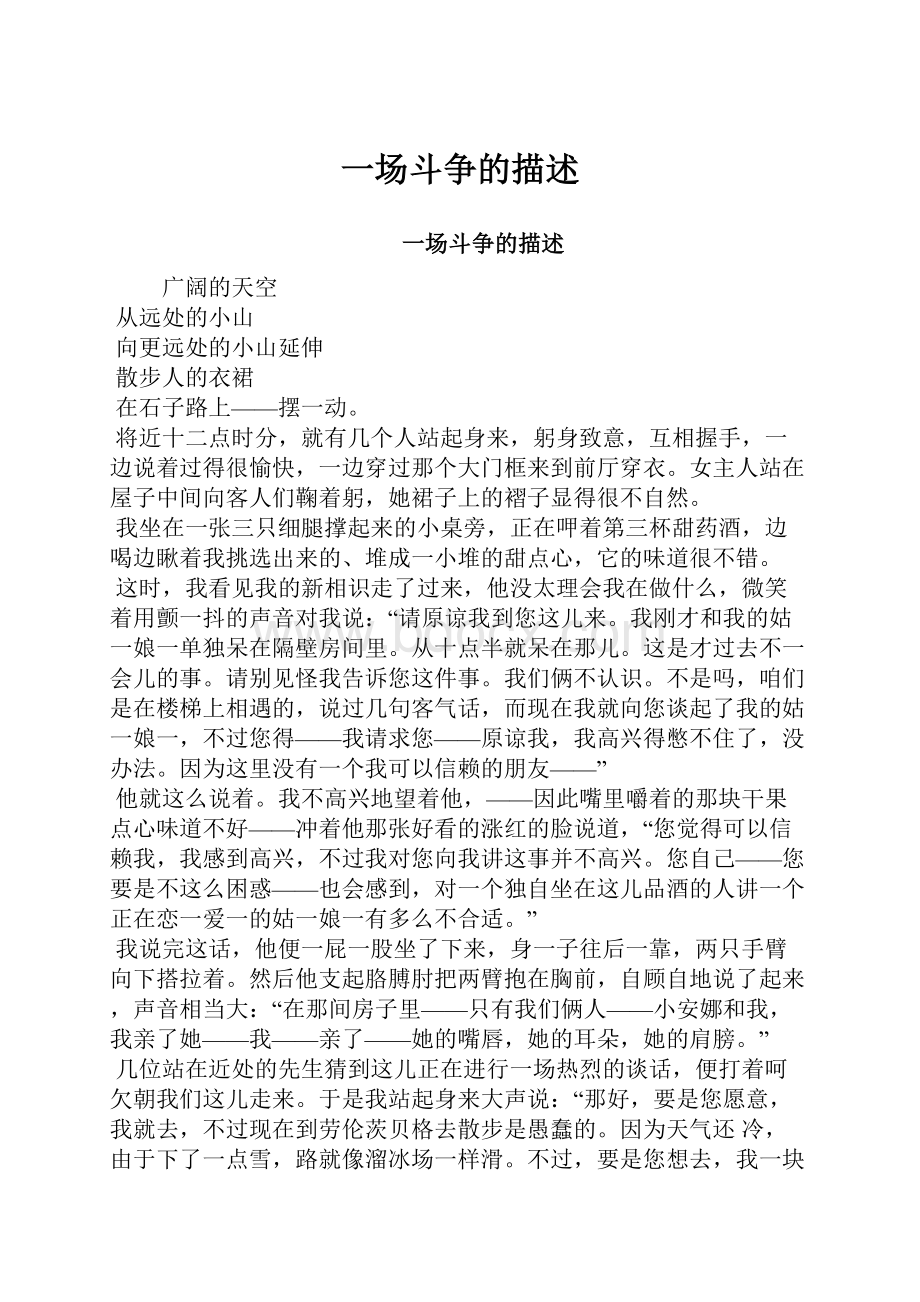
一场斗争的描述
一场斗争的描述
广阔的天空
从远处的小山
向更远处的小山延伸
散步人的衣裙
在石子路上——摆一动。
将近十二点时分,就有几个人站起身来,躬身致意,互相握手,一边说着过得很愉快,一边穿过那个大门框来到前厅穿衣。
女主人站在屋子中间向客人们鞠着躬,她裙子上的褶子显得很不自然。
我坐在一张三只细腿撑起来的小桌旁,正在呷着第三杯甜药酒,边喝边瞅着我挑选出来的、堆成一小堆的甜点心,它的味道很不错。
这时,我看见我的新相识走了过来,他没太理会我在做什么,微笑着用颤一抖的声音对我说:
“请原谅我到您这儿来。
我刚才和我的姑一娘一单独呆在隔壁房间里。
从十点半就呆在那儿。
这是才过去不一会儿的事。
请别见怪我告诉您这件事。
我们俩不认识。
不是吗,咱们是在楼梯上相遇的,说过几句客气话,而现在我就向您谈起了我的姑一娘一,不过您得——我请求您——原谅我,我高兴得憋不住了,没办法。
因为这里没有一个我可以信赖的朋友——”
他就这么说着。
我不高兴地望着他,——因此嘴里嚼着的那块干果点心味道不好——冲着他那张好看的涨红的脸说道,“您觉得可以信赖我,我感到高兴,不过我对您向我讲这事并不高兴。
您自己——您要是不这么困惑——也会感到,对一个独自坐在这儿品酒的人讲一个正在恋一爱一的姑一娘一有多么不合适。
”
我说完这话,他便一屁一股坐了下来,身一子往后一靠,两只手臂向下搭拉着。
然后他支起胳膊肘把两臂抱在胸前,自顾自地说了起来,声音相当大:
“在那间房子里——只有我们俩人——小安娜和我,我亲了她——我——亲了——她的嘴唇,她的耳朵,她的肩膀。
”
几位站在近处的先生猜到这儿正在进行一场热烈的谈话,便打着呵欠朝我们这儿走来。
于是我站起身来大声说:
“那好,要是您愿意,我就去,不过现在到劳伦茨贝格去散步是愚蠢的。
因为天气还冷,由于下了一点雪,路就像溜冰场一样滑。
不过,要是您想去,我一块去。
”
起初他惊奇地朝我望着,张着那张大而红的湿漉鹿的嘴。
后来,当他看见已离得很近的先生们时,便笑了,站起身来说:
“噢,不过冷点好,我们的衣服满是汗味和烟味,我也许有点醉了,虽然喝得并不多;好的,我们去道个别,然后就走。
”
于是我们走到女主人跟前,当他吻别她的手时,她说道:
“真的,您今天看上去这么幸福,我很高兴。
往日您的脸总是显得那么严肃,那么厌烦。
”这番好意的话语感动了他,于是他又吻了一次她的手;她笑了。
前厅站着一位侍女,我们这是第一次见到她。
她帮我们穿上外衣,然后拿上一只小手灯给我们照亮楼梯。
是的,这姑一娘一很美,她的颈子一裸一露着,只是在下巴处围着一条黑天鹅绒带,她衣带宽松,当她在我们前面提着手灯走下楼梯时,身一子好看地弯曲着。
因为刚喝了酒,她的面颊潮一红,嘴巴半张着。
在楼梯的下面,她把手提灯放到一级楼梯上,蹒跚地朝我的朋友走了一步,搂着他亲一吻,一直没松手。
直到我往她手上塞了一个硬币,她才磨磨蹭蹭地松开胳膊,慢吞吞地打开那扇小门,放我们走进黑夜。
天空上有些许云彩,因此显得更广袤,冷落的均匀地洒满月光的街道上罩着一轮大大的月亮。
地上有一片柔软的雪。
走路时很滑,因此只能迈着小步。
我们刚一来到外面,我的情绪便明显地异常兴奋。
我纵一情地抬起大一腿,让关节轻快地咯咯作响,我冲小巷喊着一个名字,好像有个朋友挣脱了我跑到拐角,我跳起一步把帽子扔高,然后大叫着把它接住。
我的朋友漫不经心地走在我身旁。
他低着头,也不吭声。
我感到奇怪,因为我以为,周围没有聚会的人会使他高兴万分。
我也不作声了。
我刚刚在他的背上打了一拳让他高兴高兴,又觉得不好意思,于是笨拙地把手收了回来。
我用不着这双手了,就把它塞到大衣口袋里。
我们就这么默不作声地走着。
我注意地听着我们的脚步声,不能理解为什么和我的朋友齐步走会使我难以忍受。
这使我有点不安。
月亮很亮,看东西很清楚。
有的地方有人倚在窗前望着我们。
当我们走进费迪南大街时,我发觉我的朋友哼起了一支曲子;声音很小,但我却听见了。
我觉得这是对我的侮辱。
他为什么不和我说话?
他要是不需要我,为什么不让我安静安静。
我恼火地想起了那些因为他才撂在桌子上的好吃的甜点心。
我也想起了甜酒,于是情绪好了一点,几乎可以说傲了起来。
我双手叉腰,就当我一个人在散步。
我刚才在和人聚会,替一个不知感恩的年轻人挽回了面子,现在又在月光下散步。
白天办公事,晚上会朋友,夜里串一胡一同,没做什么出格的事。
就其自然而言,也算是一种不受约束的生活方式吧!
可我的朋友还是走在后面,当他发觉拉后了时,甚至加快了步子,他装作这一切挺自然似的。
不过我倒是在考虑是不是该拐进一条街边小巷,因为我没有义务和别人一起散步。
我可以自己回家,谁也挡不住。
在房子里我会把放在桌子上铁支架里的灯点燃,坐到放在那张破了的东方地毯上的扶手椅上去。
想到这儿的时候,我忽然感到四肢无力。
我一想到又要回到房间里去,又要独自一人空对涂了色的四壁和地板——从后墙壁上挂着的镶金框的镜子里看,它显得歪歪斜斜的——度过几个钟头时,我总有四肢无力的感觉。
我的两条腿走累了,我已下定决心,无论如何得回家躺在一床一上,我犹豫着,在走开时是否该和我的朋友道个别。
可我胆子太小,不敢不打招呼就走开,又太软弱,不敢大声道别。
于是只得又站住,倚在一面洒满月光的墙上等着他。
我的朋友迈着轻快的步子走了过来,他也许有点担心。
他作了好一番准备,他眨眨眼,把手臂横着伸到空中,使劲地把他那戴着黑色硬礼帽的脑袋伸向我这边,他的这一切好像表示很懂得赞赏我为使他开心而在这儿开的玩笑。
我毫无办法,轻轻地说:
“今天晚上很有意思。
”我想笑没笑出来。
他回答说:
“是的,您看见那个侍女也怎样吻我了吗?
”我说不出话,因为我的喉头哽咽,为了不致于总是默不作声,我像一个邮车赶车人似的吹着号子,他起先竖着耳朵听,后来十分感激地握着我的右手。
他一定觉得我的手冰凉,因为他立刻就把它松开了。
他说:
“您的手真凉,那个侍女的嘴唇要暖和些,是的。
”我理智地点了点头。
我一边请求亲一爱一的上帝使我坚强,一边说:
“是的,您说得对,我们回家吧,时间不早了,明天早上我得上班。
您想,是可以在班上睡觉,可睡不好。
您说得对,我们该回家了。
”说着我把手伸给他告辞,好像事情到此就结束了。
可他笑着接着我的话说:
“是的,您说得对。
这样一个夜晚是不应该在一床一上度过的。
您想想,要是一个人孤零零地睡在一床一上,多少幸福的念头会在被窝里遭到扼杀,多少悲伤的梦境会在被窝里重一温一。
”他对自己的这个想法感到很高兴,使劲地抓住我外衣的前胸——再高他也够不着了——任一性一地摇晃着我;然后他眯起眼睛,神秘兮兮地对我说:
“您知道您是什么样的人吗?
您是个怪人。
”说完他又走了起来,我跟着他走,可自己并不觉得,因为我还想着他说的那句话。
起先我很高兴,因为看来这表明,我的朋友猜测我心有所想,虽然事情并非如此,但由于他的猜测,我已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种情况使我很高兴。
我对自己没有回家感到满意,对我来说,我的朋友很难得,他能在那些人面前抬举我,而不需要我自己去争取!
我极友一爱一地看着我的朋友,我头脑里想着要在危险时刻保护他,特别是要保护他不受情敌和一爱一吃醋的男人的伤害。
他的生命比我自己的生命更宝贵。
我觉得他的脸长得很美,我为他的艳福感到骄傲,我分享今晚两个姑一娘一给他的吻。
啊,今晚多快乐!
明天他会和安娜小一姐谈这事,开头当然要扯一扯平常的话题,然后他会突然说:
“昨天夜里我和一个人呆在一起来着,你,小安娜,肯定从没见过他。
他看上去——我该怎么描述他好呢——看上去就像一根不断晃动的棍子,上面不大适宜地长出一颗黄皮黑发的脑袋。
他的全身披着许多很小、很显眼的发黄的布块,把他裹得严严实实,因为夜里没有刮风,所以衣服很贴身。
他胆怯地走在我身边,你,我亲一爱一的、那么会亲一吻的小安娜,我知道你准会觉得有点可笑,有点害怕,可我,我的魂早就由于对你的一爱一而飞得无影无踪,我倒高兴有他作伴。
他也许不太高兴,所以默不作声,可走在他身边的人却兴奋不已。
我昨天为自己的幸运而心里美滋滋的,可我几乎忘了想你。
我觉得,好像随着他那扁平胸脯的呼吸起伏,繁星密布的天空那坚一硬的穹顶也在升起。
视野开扩了,火红的云彩下,山水风光一望无际,它也同样使我们快乐无边——我的天,我多一爱一你小安娜,我一爱一你的吻胜过一爱一美景。
我们别再说这个人了,我们彼此相一爱一。
当我们漫步走上码头时,我虽然羡慕我的朋友得到了亲一吻,但我也高兴地感到他在我面前,正如在他眼里我在他面前一样,也许会感到内心羞愧。
这就是我的想法。
但那时我的思绪混乱,因为莫尔多瓦河以及河对岸的城区都已笼罩在夜幕之中。
只有几盏灯亮着,和望着它们的眼睛捉迷藏。
我们站在栏杆边,我戴上手套,因为水上吹来阵阵凉风,我就像人们夜里站在一条河前可能做的那样,无缘无故地叹了口气,接着我想继续走。
可我的朋友望着河水一动不动。
后来他靠得离栏杆更近了,把胳膊肘支在铁栏杆上,把额头放进手掌。
我觉得这样子很蠢。
我身一子发冷,不得不把大衣领往上拉。
我的朋友伸伸身一子,把靠在胳膊的上身伸到栏杆外面。
为了不打呵欠,我不好意思地抢着说:
“是吧,的确奇怪,只有夜晚才能使我们完全陷入回忆之中。
比如现在我就能想起这么一件事。
一天晚上,我斜身坐在一条河岸的长椅上。
我的头搭在手臂里,手臂放在椅子的木质靠背上,我望着河对岸似云的群山,听见海滨酒店里有人轻柔地拉着提琴。
两岸时不时有吐着阵阵烟雾的火车隆隆而过。
”——我就这么说着,拼命地虚构一个个怪异的一爱一情故事;残暴野蛮和蹂一躏强xx当然也是少不了的情节。
我刚说出头几句话,我的朋友便漫不经心地转过头——我觉得他只不过对在这里还能见到我感到惊奇——说:
“您看,事情总是这样。
当我今天走下楼梯,打算在聚会前再作个晚间散步的时候,奇怪地发现我的两只发红的手在袖口里来回地晃动,晃得异常快活。
那时我就估计到会有艳一遇。
事情总是这样。
”他边走边说,并且只是对一种微不足道的小事观察着那样随便说说。
可这番话却使我很受感动,我非常抱歉的是,也许我的硕长身影会令他感到不快,他在我身边可能显得太矮。
虽然是在夜里,并且我们几乎也碰不到什么人,但这种情形仍使我感到如此痛苦,以至我不得不弓起腰走路,这样一来,我的两手就触到了自己的膝盖。
为了不让我的朋友看出我的意图,我只是缓慢地、小心翼翼地改变着自己的姿式,我让他看防护岛上的树木,让他看桥头上的灯光在水中的一交一相辉映,试图以此把他的注意力从我身上引开。
可他突然一转身,脸对着我宽厚地说:
“您怎么这样走路?
您整个人伛偻着,差不多和我一样矮!
”
他说这话是一番好心,所以我回答说:
“可能是这样。
不过我觉得这姿式很舒服。
您知道,我身一体不大好,挺一直身一子我觉得很难受。
这可不是小事,我走得很慢——”
他有点怀疑地说:
“这只不过是心情的关系。
我觉得您从前一直是挺一起身走路的;在和别人聚会时也还凑合。
您甚至还跳舞来着,对吗?
没有?
不过您是挺一直身一子走路的,现在您也能直起身一子。
”
我用手作了个拒绝的姿式,坚持说:
“行,行,我挺一直身一子走路。
不过您过低估计了我。
我知道什么是得体的举止,因此我才弓着腰走路。
”
可他觉得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他被自己的幸福冲昏了头,不能理解我这番话的意思,于是只得说:
“行,悉听尊便。
”他抬头看了看磨房钟楼顶上的钟,指针差不多指向了一点。
我对自己说:
“这人多没心肠!
他对我这番恭谦的话所抱的无所谓的态度多么典型,多么明显!
他很幸福,因而认为他们周围发生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这就是身在福中的人的样子。
他们幸福了,便把一切都看得那么美好。
要是我现在跳到水里,要是在他的面前,在桥拱下面的这条石子路上,痉一挛把我撕成碎片,我也得老老实实地适应他的幸福。
是的,要是他的火气一上来——一个身在福中的人是危险的,这毫无疑问——他会像一个拦路行凶者一样把我打个半死。
肯定会是这样,我胆子小,我会害怕得连喊叫的勇气都没有——天哪!
我害怕地四处张望。
在远处的一家镶着长方形黑玻璃的咖啡店前,一个警察在石子路上遛来遛去。
他的马刀有点碍事,他便把它拿在手里,这下走起路来就神气多了。
我和他之间还有一段距离时,我也听得见他发出的低低的欢呼声,这时我相信,要是我的朋友想打死我,这个警察也不会来搭救。
不过现在我也知道该怎样做,因为恰恰面临可怕的局面时,我便会有很大的决心。
我必须跑,这很容易。
就在现在,在往左拐进卡尔斯布吕克时,我可以往右一下子跑到卡尔一胡一同。
这条一胡一同有好多拐角,那儿有黑色的住户大门,有开着门的小酒馆,我用不着感到绝望。
当我们走到码头终点的桥拱下面时,我甩开膀子就往那条一胡一同跑;可正要跑进教堂的一扇小门时,我摔倒了,因为我没看到那儿有一级台阶。
啪嗒地响了一声。
最近的那盏路灯还离得好远,我倒在黑暗之中。
对面一家酒店里走出一个胖妇人,提着一盏烟雾腾腾的小灯,看看到底在一胡一同里出了什么事。
弹钢琴的声音停止了,一个男人把半开着的门完全打开了。
他往台阶上吐了一大口唾沫,紧紧挤住那女人的胸脯说,不管怎么说,这儿发生的事无关紧要。
然后他们俩转过身,门又关上了。
我试着站起来,又倒了下去。
“滑得厉害。
”我说,我感到膝盖一阵疼痛。
不过酒店里的人没有看见我,这使我很高兴,因此我觉得在这儿躺到天亮是最舒服不过的事情。
我的朋友可能是独自一人一直走到桥头都没有发觉我的不辞而别,因为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来到我跟前。
他同情地弯下一身一子,用柔软的手抚一摸一我时,感到很惊讶,我没有理他。
他来回抚一弄着我的面颊,然后把两只胖乎乎的手指放到我低低的额头上说:
“您摔疼了,是吧?
路滑得要命,得小心才是——头摔疼了吗?
没有?
喔,膝盖摔疼了。
是这么回事。
”他用一种唱歌的声调说话,好像在讲述一个故事,一个远在天边的膝盖摔痛的很有意思的故事。
他的胳膊也在动作着,但他根本没想把我扶起来。
我把头支在右手上,胳膊肘支在石子路上赶紧说——,免得一会就忘了这句话——:
“我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向右拐。
不过我在这教堂的树底下——我不知这树叫什么名字,啊,请原谅——看见一只猫在跑。
一只很小的猫,一毛一皮很亮,所以我看到了它——噢,不,不是,请原谅,不过白天时,人有足够的力量克制自己。
睡觉就是为了加强这种力量,可要是不睡觉,我们就少不了作出这种毫无意义的事情,不过要是我们的陪伴者对此大惊小怪就不太客气了。
”
我的朋友把手放在口袋里,望望空无一人的桥头,然后又望望天主教堂和晴朗的天空。
他没有听见我说的话,所以他担心地说:
“是呀,为什么您不说话,我的亲一爱一的;您觉得难受吗——是呀,您为什么不站起来——这儿很冷,您会冻着的,过一会我们还要去劳伦茨贝格。
”“当然,”我说着,“请原谅,”我自己站了起来,但是身上痛得要命。
我摇晃着身一子,不得不紧盯着卡尔四世的塑像,以便确保我站的位置。
但月光也照得不是地方,以至使卡尔四世也晃动起来。
我很惊奇,我担心,要是我站不稳,卡尔四世的塑像就会倒,所以我的腿一下子有力多了。
后来我的努力看来是白费了,因为当我忽然想起我被一个身着漂亮白裙的姑一娘一爱一着时,卡尔四世的塑像还是倒了下来。
我做了无用功,误了许多事。
这个关于姑一娘一的想法是多么美妙啊!
——月亮真好,它也照在我的身上,我看出月亮照耀着一切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于是出于谦让的心理准备站在吊桥悬索云柱的下面去。
因此我欣喜地伸展手臂尽情享受月光——这时我想起一段诗句:
我奔跑着穿过一胡一同
仿佛是个醉酒的步行人
踏着沉重的脚步穿行于空间
当我用懒散的双臂做着游泳的动作而不感到疼痛,毫不费力地前行时,我感到轻松。
我的头躺在冰冷的空气中,而白衣姑一娘一的一爱一使我有种忧郁的欣喜;因为我觉得好像游着泳离开了我的心上人,也离开了她那地方的那些似云似雾的群山——我记得曾经记恨过一个幸福的朋友,这人也许现在还走在我的身边,我的记一性一这么好,甚至记得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这使我感到高兴。
因为该记的东西很多。
比如,我虽然从没学过,却一下子记住了很多星星的名字。
是的,那是些稀奇古怪的名字,很难记,但它们的名字我都知道,并且知道得一清二楚。
我伸出食指,大声地一个个说出这些星星的名字——可我并没说出几个,因为我还得继续游,我不想潜得太深。
可为了使以后没有人会跟我说,在石子路上谁都可以游泳,根本不值得一谈,我便加快速度,跃上了栏杆并且绕着我遇到的每一个圣人塑像游去。
我绕着第五座塑像的时候——我正用察觉不到的击水动作在人行道上游——我的朋友抓住了我的手。
这时我又站在了石子路上,感到膝盖处的一阵疼痛。
我忘记了星星的名字,只记得那个可一爱一的姑一娘一穿着一件白裙,可我怎么也想不起有什么理由相信姑一娘一爱一上了我。
我内心升腾起一股对我记忆力的难以抑制的、有根有据的怒火,我担心失去那位姑一娘一,我费力地不停地说着“白裙,白裙”,以便至少用这种方式记住那位姑一娘一。
但这于事无补。
我的朋友说着话,离我越来越近,当我开始明白他说话的意思的时候,一道白光沿着桥栏杆轻轻地跳跃,掠过吊桥悬索支柱,然后又跃进了黑暗的一胡一同。
“我从前一直喜欢,”我的朋友指着圣人卢德米拉的塑像说,“左边这位天使的双手。
它柔一嫩无比,那张开的手指在颤一动。
但从今晚起,这双手对我来说已无关紧要,我可以这样说,因为我吻过一双手。
”——然后他搂着我,吻我的衣服,头挨着我的身一体。
我说:
“是的,是的。
我相信。
我毫不怀疑。
”边说边用他放松开来的我的指头掐他的小腿肚。
但他毫无感觉。
于是我便对自己说:
“你为什么要和这个人出去?
你不一爱一他,也不恨他,因为他的幸福只是在一个姑一娘一的身上,而她是否穿着一件白色的衣服都还说不定。
这么说,这个人对你来说无所谓——再说一遍——无所谓。
不过他也不危险,这已经得到了证明。
你虽然可以继续和他一起到劳伦茨贝格去散步,因为在这个美妙的夜晚,你已经走在这条路上,但你随他去说,照你自己的方式消遣吧,这样——我小声地说——你也可以最好地保护你自己。
”
开心或
无法生活的证明
1骑
我异常灵敏地纵身跃上我朋友的肩膀,用拳头一捅一他的背,使他轻步奔跑起来。
他不大情愿地踏着地,有时甚至停止不前,我就用靴子戳几下他的肚子,好让他更加一精一神。
我如愿以偿,于是我们很快地深入到一个大的,但还没有完工的地带的中心,天已黑下来了。
我骑着走的马路上石头很多,并且越来越陡,可这正合我意,我要它的石头再多些,路再陡些。
只要我的朋友绊个踉跄,我就拎住他的头发往上提,他一叹气,我就给他的脑袋几巴掌。
我感到,心情愉快地晚上出游多么有利于我的健康,为了使这次出游更为狂放,我让迎面吹来的劲风久久地吹着我们。
现在,在我朋友宽阔的肩膀上,我又加大了骑姿的跳跃动作,我用双手紧一抓住他的脖子,把头尽量往后靠,观察那多变的、比我还柔一弱的、慢腾腾地随风飘浮的云。
我笑了,为我的勇敢而战栗。
我的大衣伸展开来给我以力量。
我的两手紧紧地攥在一起,我装作好像不知道这样做会把我的朋友掐死似的。
我骑得浑身发一热,天空慢慢地被路边我让它长出来的树的弯枝遮掩了,我对着天空喊道:
“我还有其它的事情要作,没有功夫老听关于恋一爱一的闲扯。
为什么他,这个多嘴多舌的谈恋一爱一的家伙要找到我这儿来?
他们大家都很幸福,要是别人知道了他们的事,他们便特别幸福。
他们以为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因此值得为未来的生活感到高兴。
”
这时,我的朋友摔倒了,当我察看他时,发现他的膝头受了重伤。
因为他对我来说再没有什么用了,我便把他丢弃在石头上,吹着口哨从空中引来几只老鹰,它们带着尖嘴听话地朝他扑去,对他进行保护。
2散步
我无忧无虑地继续走着。
作为一个步行者,我害怕走山路的艰辛,所以我让道路越来越平坦,让它在远处的尽头通向一个山谷。
石头照我的意愿消失得无影无踪,风也停了,消失在夜晚之中。
我阔步前进,由于走的是下山的路,所以我抬着头,挺一直了身一子,把胳膊放在头后。
我喜一爱一杉树,所以我穿过杉树林,我一爱一默默地仰望繁星密布的天空,因此星星也都缓慢而平静地、按照它们自己的方式为我升上了开阔天空。
我只看见了些许延伸的云被一阵和云一样高的风吹着。
我的路对面,在相当远的地方,我让一座雄伟的高山拔地而起,我和山可以说是隔河相望,山上长满了灌木,与天相连。
我还能清楚地看见最高树杈上的小枝和枝杈的摆一动。
不管这是多么平常的景色,看到它,我竟高兴得像一只落在这遥远蓬乱的灌木枝条上晃动着身一子的小鸟,忘了让已躲在树后的月亮升起,也许它在为我的延误而生气。
而现在,山上洒满了月亮升起前的那道清冷的光。
突然,月亮自己在一束不平静的灌木丛中爬了上来。
可我这时正往另一个方向看,待到我往前看时,一下子发现月亮已经差不多滚一圆,它光芒四射,我站了下来,眼睛模糊了,因为看来我的那条陡峭的山路正是通向这个可怕的月亮的。
可是过了一会儿,我便一习一惯了月光,我仔细地观察,看月亮爬上山来是多么的不易,一直看到我和月亮面对面地走了好大一截路,最后感到困得睁不开眼睛为止,我觉得,这么困是白天太累的缘故,不过我也想不起白天究竟做了什么。
有一小段时间,我闭着眼睛走路,只用大声地、有规律地拍打两手的办法保持清醒状态。
可后来,当路险些要从脚下滑落,所有的一切都和我一样累得快要消失时,我便加快了步伐,用尽全力攀登路右边的山坡,以便及时到达那片高高的、令人迷惘的杉树林,我打算今晚在那儿睡个好觉。
快走还是必要的。
星星已经暗淡下来,天上的月亮就像在流动的水中一样缓缓下沉。
黑——群山已变成了黑夜的一部分,令人不安的是,公路在我转身下山的地方已到了尽头,树林中传来了越来越近的树木倒下的咔嚓声。
我本来可以倒在青苔上睡觉的,可我害怕蚂蚁,所以我两一腿攀在树干上,爬到一棵虽无风,但仍在摇曳的树上去,靠在一枝树杈上,头倚在树干上,很快地入睡了,而此时,我的情绪却起伏不定,犹如一只尾巴翘得老高的小松鼠,正坐在晃动的树枝顶端轻轻摇动。
我睡着了,没有作梦,睡得很沉。
月亮下山和太一陽一升起都未能把我唤醒。
即便我已醒了过来,我也安慰自己说:
“昨天你已很累了,所以睡你的觉吧。
”于是又睡着了。
虽然没有做梦,可我的觉也并非没有受到持续不断的轻微的打搅。
整个一一夜我都听见有人在我身旁说话。
除了个别的诸如“岸边的长椅”,“云山雾罩的山脉”,“突突冒着青烟的火车”以外,我几乎听不出说的是什么,听见的只是强调这些词的方式;我还记得,我在梦中高兴得直一搓一两手,因为我正睡着觉,不必去辨认每一个字词。
午夜以前,说话声很快活,不堪入耳。
我浑身发一抖,因为我觉得,有人正在下面锯我那棵早已摇曳不定的树木——午夜之后,说话声变得严肃了,也渐渐隐退了,在句子之间有了停顿,听起来,好像这声音在回答我并没有提出的问题。
这时我感到舒服些了,敢把四肢伸开了——将近黎明时分,说话声越来越和蔼了。
说话人的宿营地看来并不比我的更安全,因为我现在发觉,他就在我旁边的树枝上说着话。
我的胆子大了起来,把背对着他躺着。
这显然使他感到难过,因为他停止了说话,一直沉默不语,直到上午才用一声轻轻的叹息——因为我已完全不一习一惯他的说话声了——
把我唤醒。
我看到多云的天空不仅在我的头顶上方,而且甚至从四面将我包围起来。
云沉重得低低地掠过沼泽,撞上树木,被枝杈划得粉身碎骨。
有时些许云雾来到地面,或被树木裹挟其间,直到一阵狂风吹来把它们赶走。
大多数则夹一着冷杉球果、断枝折杈、滚滚青烟、倒毙的野兽、旗帜、风信鸡和其它许多叫不出名字的东西,飘飘扬扬地把它们带到远方。
我蜷伏一在我的树杈上,不得不想着怎样推开威胁着我的云,或者,要是云雾很宽时,就躲开它。
这对处于半醒半睡之中、又觉得常能听见叹息者的声音因而被搅得七上八下的我来说是个吃力的事儿。
不过我惊奇地发觉,我的处境越牢靠,天空也就越高越远,到最后,在我打了最后一个呵欠之后,夜晚正处于雨云之下的这块地方已清楚可见。
我的视野一下子变得如此之广令我恐惧。
我思索着究竟为何来到此地,这里的路我并不认得。
我觉得好像是在梦中糊里糊涂到了这里,到大梦初醒才意识到我处境的可怕。
幸好这时我听见一只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