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40年代成都城区方言简说二.docx
《上世纪40年代成都城区方言简说二.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上世纪40年代成都城区方言简说二.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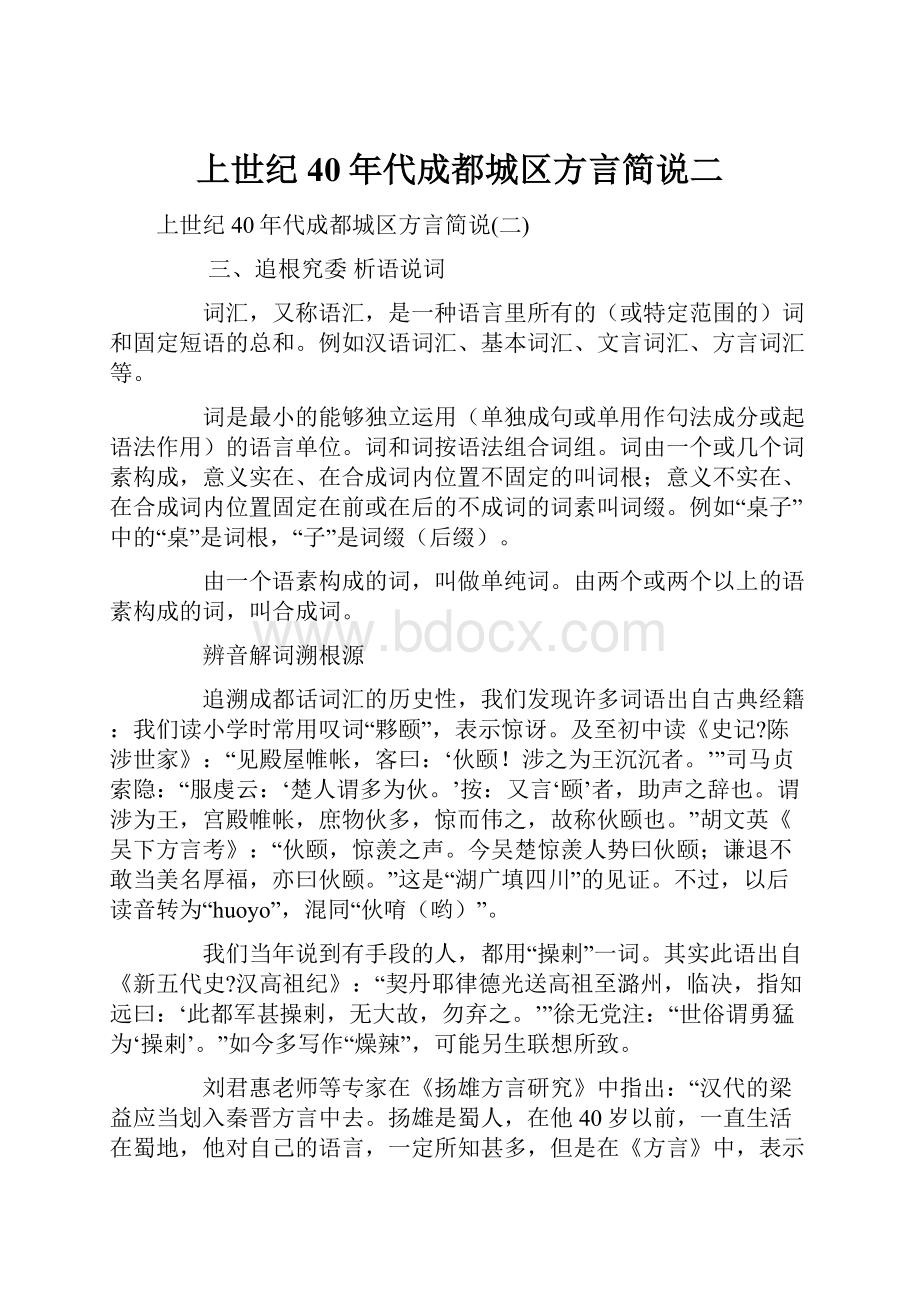
上世纪40年代成都城区方言简说二
上世纪40年代成都城区方言简说
(二)
三、追根究委析语说词
词汇,又称语汇,是一种语言里所有的(或特定范围的)词和固定短语的总和。
例如汉语词汇、基本词汇、文言词汇、方言词汇等。
词是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单独成句或单用作句法成分或起语法作用)的语言单位。
词和词按语法组合词组。
词由一个或几个词素构成,意义实在、在合成词内位置不固定的叫词根;意义不实在、在合成词内位置固定在前或在后的不成词的词素叫词缀。
例如“桌子”中的“桌”是词根,“子”是词缀(后缀)。
由一个语素构成的词,叫做单纯词。
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素构成的词,叫合成词。
辨音解词溯根源
追溯成都话词汇的历史性,我们发现许多词语出自古典经籍:
我们读小学时常用叹词“夥颐”,表示惊讶。
及至初中读《史记?
陈涉世家》:
“见殿屋帷帐,客曰:
‘伙颐!
涉之为王沉沉者。
’”司马贞索隐:
“服虔云:
‘楚人谓多为伙。
’按:
又言‘颐’者,助声之辞也。
谓涉为王,宫殿帷帐,庶物伙多,惊而伟之,故称伙颐也。
”胡文英《吴下方言考》:
“伙颐,惊羡之声。
今吴楚惊羡人势曰伙颐;谦退不敢当美名厚福,亦曰伙颐。
”这是“湖广填四川”的见证。
不过,以后读音转为“huoyo”,混同“伙唷(哟)”。
我们当年说到有手段的人,都用“操剌”一词。
其实此语出自《新五代史?
汉高祖纪》:
“契丹耶律德光送高祖至潞州,临决,指知远曰:
‘此都军甚操剌,无大故,勿弃之。
’”徐无党注:
“世俗谓勇猛为‘操剌’。
”如今多写作“燥辣”,可能另生联想所致。
刘君惠老师等专家在《扬雄方言研究》中指出:
“汉代的梁益应当划入秦晋方言中去。
扬雄是蜀人,在他40岁以前,一直生活在蜀地,他对自己的语言,一定所知甚多,但是在《方言》中,表示梁益地区的地名竟是如此之少,这只能解释为当时的梁益方言与秦晋方言非常接近。
”《方言》中有些字词是当时的“某地语”、“某地某地之间语”或“某地某地之间通语”,但是以后进入了巴蜀方言,现在如果不对照原书记载比较,简直无法说明它的来源。
例如――
芦菔:
“关之东西谓之芜菁,赵魏之郊谓之大芥……其紫华者谓之芦菔。
"郭璞注音:
“罗匐”。
清人王念孙注:
“芦菔音罗匐……今俗语通呼为罗匐,声转而为莱菔。
”成都人叫“萝?
N”(普通话叫“萝卜”,读音同样有变),写出来只比以前多加“草头”,标明植物。
中医药工作者就直接用“莱菔”了。
谁也不计较它是不是个外来词。
痨:
“凡饮药、傅药而毒,南楚之外谓之瘌;北燕、朝鲜之间谓之痨;东齐海岱之间谓之眠,或谓之眩;自关而西谓之毒。
”――瘌,音乖剌之剌,非刺,非癞,“痛也。
”汉代地处关西的巴蜀,照理是该叫“毒”的。
“痨”读阳平声,如劳。
后世一般指“痨瘵”(痨病,特指肺结核病,成都人呼作“痨病腔腔”);“饿痨”指容易饥饿的胃病,也形容贪食、没有好的吃相。
一般人不晓得它曾经被用来表示“中药毒”或“以药毒之”。
现在成都人都把毒药叫[lǎoyuo](或[nǎoyuo]),不就是“痨药”吗?
只不过成都话读成去声字罢了。
“痨、闹”同音,因此有人写作“闹药”。
“痨”当然可以作动词用的。
成都人中至今还使用《方言》中的有些字(其中也有省外通用者,如下例中加*者),例如:
披:
“器破曰披”――音胚,破裂。
“木匠凿子头头都打披了。
”
挡(?
?
)*:
“凡相推搏或曰?
?
”――推挡,招架。
“顺手一挡,没有挨到那一耳矢。
”
?
?
*:
“庸谓之?
?
”――读如松的阳平声,寒碜,窝囊。
“拖衣落食,没精打采,一副?
?
相。
”北方官话读音如熊。
筲:
“饭谓之筲”――音烧,竹编淘米、盛食物器。
“筲箕都装得水么?
”
菲*:
“菲,薄也”――音匪,少。
“这回花的钱,不菲啊!
”北方官话“菲薄”连用。
捞*:
“捞,取也”――捞取。
单用读阴平;捞钩,读如牢。
“这下着捞钩起来,脱不倒手。
”
淹*:
“水敝为淹”――音安,淹没。
“矮子过河――安(淹)了心的。
”
拌:
“挥弃物谓之拌”――掷弃。
“咋个办?
朝地下拌!
”
晒*:
“暴五谷之类”――晒。
“六月六,晒衣服。
”
筑里*:
“筑里,匹也。
”――妯娌。
“大嫂跟兄弟媳妇儿,两先后,也叫两筑里。
”
有趣的是“熬、、煎、?
q”几个字,泛言意思都是“火干也”;但是细细区分:
“凡以火而干五谷之类,自山而东,齐鲁以往,谓之熬”。
如今四川也说“熬锅肉、熬猪油”,这里的“熬”读阴平声;而“熬药、熬骨头汤”的那个“熬”却读阳平声。
“关西陇冀以往谓之”。
如今四川也说“蜈蚣虫焙干打面面”,改写成“焙”,音背。
“秦晋之间或谓之?
q”。
如今四川也说“小锅单炒”,写成“炒”,有写作“?
贰钡模?
音吵。
“凡有汁而干谓之煎”。
如今四川也说“煎二面黄,做家常豆腐。
”
《方言》:
“北燕、朝鲜、冽水之间谓伏鸡曰抱。
”黄仁寿老师在《蜀语校注》中引《说文解字》:
“孚,卵孚也”,说明“孚,古音同抱”,即“鸟伏卵”。
按,今四川人俗语有“抱鸡婆打摆子――又扑又颤”,指抱蛋鸡,即孵卵母鸡。
“抱”是从东北方言引进来的。
《方言》:
“鬼:
虔,儇,慧也……自关而东,赵魏之间谓之黠,或谓之鬼。
”清人卢文诏注:
“谓黠为鬼,今吴越语犹然。
”如今四川人评论人,特别是小孩子精灵,聪明,常说“鬼得很!
”就是从别的方言区域引进的外来词。
见于其他书籍的如《说文》有?
O――搏,打击、戴(头)――分物得增益、诖――误,今音拐、?
F――注视而谨畏、?
酢?
―寒也,如冰?
酰?
今音欠、凿――穿木,今指虫蛀、?
@――稻饼,糍粑。
《集韵》《广韵》有“?
――黑各切,螫也、――击,丑展切,今作产、槽――手搅,今作造、?
q――欺,徒河切、?
Q――足跌、豚――尾下窍,都木切、?
?
――以手散物,以赡切。
《蜀典》“犍为之俗谓江之?
?
水为浩”,《玉篇》“坝,必驾切,蜀人谓平川曰坝”。
有些则读音起了变化,如“”,《说文》:
“益州鄙言人盛(肥)讳其肥,谓之。
”《集韵》“,如阳切。
”如今成都人,特别是回民买肉,仍然沿袭旧说,用“”代肥,但读nàng,音如曩。
寻根究委,巴蜀方言中许多词语来自外地,如《南史》有“荆土方言谓父曰爹”,四川多呼父亲“爹爹”,也有变音如“diādiā,嗲嗲”者,如“dādā,哒哒”者;对义父通称“干爹”。
《说文》有“蜀谓母曰姐”,如今四川客家话保留此语,称母亲为“阿姐[jiè]”,呼姐姐则音如“阿甲[jiā]”。
《一切经音义》有“关西呼镰为,成都乡间呼带锯齿的镰刀为锯锯镰。
“吴楚之间资生杂具通谓之什(音十)物”,四川称为家什,如“锣鼓家什都请齐”。
《尔雅郭注》有“江东呼地高升者为敦”,四川呼为墩,音登(是dēn,而不是deng,不带鼻后声随)。
成都有五里墩。
《匡谬正俗》云:
“今痛而呻者,江南俗谓之呻唤。
"四川不说呻吟,说呻唤(cēn,音如抻。
还有扩展作“呻而打唤”的)。
《本草注》:
“莴苣,江东人谓之莴笋。
”今四川嘲讽人不仔细看,看不清,说“莴笋颠儿(尖儿,二字连读)吃多了,眼睛雾(瞀)"。
《通俗编》云:
“杭州人凡有所急问辄曰咋,盖以甚读舍,而又以做舍二字反切为咋也。
”四川普遍说“咋子[zuǎzi]”(咋不读zha。
做啥连读,如抓的去声),往往带有质询意味。
《辍耕录》云:
“江南于妇人贱之则曰婆娘。
”川西农村和市井一般喊妻子为婆娘(?
?
,读阴平声),俗语有“瞎子打婆?
?
――绺到不放”;对被自己轻视、鄙视的妇女呼婆?
?
。
《癸巳存稿》云:
“南人音亦转?
?
,苏湖言某老?
?
。
”四川喊老太婆为“老?
?
子”、“老?
?
儿”(?
?
,读阴平声。
?
?
儿连读,如nīr)则有失礼貌。
如果把妻子或“女朋友”也呼为“婆?
?
”、“老?
?
儿”,实为无知!
许多吴方言词语早已输入巴蜀方言。
诸书记载有:
《辍耕录》云:
“吴中呼女子之贱者曰丫头。
”四川人呼女婢为丫头,成都旧时叫“丫头儿[tēr]”(头儿连读),歌谣有“丫头子,蛮疙瘩,烧烟倒茶背娃娃。
”(头读阴平声,如偷)可见其劳累辛苦,过的非人生活。
《集韵》云:
“吴人谓鼻声为鼾。
”四川人说“吹扑打鼾”、“扑鼾扯得隔壁子都睡不着”)。
《广韵》云:
“髀,吴人云?
o,匹朗切。
”川戏唱“隔壁子杀鸡又炖?
o[pàng],邱大爷还在饿([māng]māng(读如莽,阴平声)”。
《通俗编》云:
“能个,吴语,犹云如何至此。
”川东如今仍然保留“恁个[nèngē]”作指示代词,可以看作“那样个”的合音。
《说文通训定声》云:
“今苏俗言物味辛曰辣。
又言虫螫曰瘌豁豁。
”四川人爱辣,语言文字离不开这个“辣”,清音唱词有“熟油辣子多放点儿,辣糊儿辣糊儿又辣糊儿。
”(四川读糊如符,糊儿连读,音fēr)。
“瘌豁豁”变读如“辣糊糊”(音如肤肤)。
《方言校正》云:
“今江淮人谓质弱力薄者为”,《华阳县志》:
“体质薄弱曰”。
四川曲艺作品写作“”,以会意字表示身材短小、体质虚弱,音如囊的阴平声。
俗语有“筋筋,瘦壳?
樱?
一顿要吃几钵钵”。
《蜀语》:
“釜溢曰鬻,音孛。
”《说文段注》云:
“今江苏俗谓火盛水溢出为铺出,鬻之转语也。
”四川话的pu,有写作瀑、?
?
的,与之同义,如俗语的“米汤瀑了!
”
《说文通训定声》云:
“今苏俗老而秃顶曰秀顶。
”四川人用以代替土话“光(去声,无毛,无物,无搭配)脑壳”。
《说文通训定声》云:
“今苏俗犹曰地窨子。
”《蜀语》记载呼地窨(音印)子,现在四川多呼“窖”,其音如告,保留古字古音(按,窖,从穴,告声),古味十足。
又云“苏俗谓熏篝曰烘篮”,四川除客家人呼“火囱”(音如佛葱)外,口语都加儿化称“烘笼儿”、“烘蓝儿”,或说“烘笼子”,旧日成都打更匠必喊:
“三更锣锣儿[lōr]响,烘篮儿[lēr]提下床!
小心火烛!
”
该书又云:
“今苏俗谓饭?
_曰筲箕。
”成都凡竹编器具呼为筲箕、撮箕、簸箕、鸳箕……还有“今苏俗谓履之判合者为帮。
”就是四川说的鞋帮。
“醪,汁滓酒,今苏俗语犹如此。
”就是四川农村家家户户都会酿制的醪糟。
店肆图简单,多以谐音写醪字作。
诸多例证说明成都话的变化虽然十分复杂,但仍然有规律可循,能够理清来龙去脉,区分其中的精华与糟粕,去粗取精,促进其健康发展,为便于交流思想服务。
异彩纷陈不简单
多年来,陕西商人大量长期在成都等商贸城市生活,成都方言当然受到影响,单音名词常常像陕西话那样重叠,如:
阴平声字重叠,后一字仍然读阴平声。
“缸缸”是缸子,是名词重叠;儿化,成gānggēr,表示茶缸子之类。
“窝窝”,普通话单说“窝”,儿化后特指笑窝、酒窝。
“扉扉”(单页纸,似由“柴扉、扉页”化来。
形容词一作“飞飞”,注重同音)可以儿化,音fēr。
“箍箍[kū]”由动词重叠构成,kūkūr是小箍圈。
“笆笆”(竹篾条、麦秆儿编制)、“粑粑”(米、面、玉麦粉蒸、炸之饼)、“疤疤”,补疤、疮疤,一般不儿化。
“抽抽”,即“抽屉[dǐ]”,可儿化,有时更指小的。
旧时民间讳言“撞鬼”,常把“闯到鬼”说成“碰到抽抽”,此义项不能儿化。
“瓜瓜”,说人是“傻瓜”,除开嘲讽,有时不带贬义,是“老实”的代词,也不儿化。
“锥锥”,有zūizūi、jūjū(音如居)两种读法,指物体上小而尖的突出部,也不儿化。
阳平声字重叠,后一字读阴平声的有:
“毛毛”,指细毛,不儿化。
“尘尘”,指灰尘,也不儿化。
“牛牛儿[nīr]”,儿童?
?
(以鞭子抽)的陀螺,必须儿化。
“坨坨”,团状物体,可儿化;同音的“驼驼儿[tūr]”,必须儿化,是对驼背者的不敬称呼。
“索索”,绳索,儿化suosūr;成都话则不大说“绳绳”,而直接说“绳绳儿”[sunsūr]。
成都人喊雀鸟,特别是麻雀,叫“雀雀儿[quoqǖr]”,必须儿化;社会允许大家逗小娃儿,常常说他的那话小“雀雀儿[quoqǖr]”咋个咋个,但是一般避讳这个容易联想阳物的词,又改说“麻雀子[quōz]嫁女――闹喳麻了!
”
阳平声字重叠,后一字也可读阳平声的有:
“钵钵”,儿化后指小件。
“脚脚”指沉淀物,不儿化。
“角角”指角落,常常组合成“?
?
?
?
[kaka]角角”使用,也不儿化。
“别别”,音pie,指门窗设置闭锁别件,由动词构成名词,或称“别别儿[piepir]”。
“缺缺”,缺口,可读阴、阳平声。
“塌塌[ta]”,指地方,“在啥子塌塌落脚?
”“?
]?
][jia]”(《蜀语》云“尘垢曰垢?
],音苟甲[gòujia]”)指身体的垢泥,长辈常常教训不爱洗脸的娃儿:
“不洗?
脸上?
]?
]结起壳壳,起(剥,揭)下来就是戏脸壳儿(面具)了。
”这些叠字都不兴儿化。
“钵、索、脚、角、别、缺、塌、?
]”之类都是古代入声字,四川话大都归入阳平声,所以往往有如此两种变音。
上声字重叠,后一字读阳平声,如“管管”儿化后特指细小管子。
“本本”儿化后特指小型本子。
“底底”指器皿或洞穴的底部,一般不儿化。
“嘎嘎[gàga]”,属于儿童语;“一身嘎嘎肉际际(记记)的”是说娃娃肥实。
形容词叠字作名词用,如“恍恍”,是说人不专心,不踏实。
“广广”则嘲笑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是城里人自高自傲的话。
“胴胴、打(光)胴胴”是赤膊,都不儿化。
去声字重叠,后一字读阴平声,如“罐罐”、“把把”是器物之柄(语有“把柄”),其小者可以儿化称呼。
“坝坝”,平地,特指院子里的空地,如果评论房舍可以说“小院坝儿”。
“凼凼”指低洼地或水坑,“谨防掉进人家的凼凼头”,就比喻陷阱了。
“棒棒”是说棍棒,儿化后指小棍;重庆人说“棒棒儿”,特指那些自备扁担、绳索,在街头待客担送物件的打工者。
动词叠用作名词用的“盖盖”或“盖盖儿”犹如普通话的“盖儿”。
“扫扫”、“扫扫儿”是小型扫除器具,与扫把略有区别。
“哨哨儿”,则是口吹的哨子,必须儿化,否则便是儿童词语。
成都话里名词后缀带“子”的很多,基本上与普通话名词带“儿”的相应,例如:
“枣子、带子、烟子、衫子”等。
普通话名词带“子”的如“架子、瓶子、肠子”等,成都话又说是“架架(架架儿则指穿的背心儿)、瓶瓶儿、肠肠儿”。
“杆”在成都话里组合出下列名词:
“手杆、腰杆(风趣说法是‘一杆’,谐音幺、腰)、腿杆、连二杆(胫)、脚杆”,普通话说“胳臂(胳膊)腰、腿、胫、小腿”。
成都话的方位词“头”[tou],基本上代替了“里”字,比如“桶头、碗头、屋头、坝坝头、圈圈里头”。
比较前后,则说成“前头[tōu]”、“后头[hǒutōu]”。
另外,“后头”读音变成hòutou,那么它就表示“里头”,比如“锅后头、碗后头、城后头、筒筒后头、圈圈后头”。
《蜀语》:
“重?
`?
`。
?
`,吐本反。
”引《方言》“?
`,重也。
”郭璞注“吐本反。
”今音重těntěn。
成都话的形容词带后缀,常常有增强感染力的效果,远比单说原形词可爱多了。
你听:
“薄菲菲[fēi](的衣服)”、“(周身上下)麻酥酥”、“瓜兮兮(的样子)”、“黑黢黢[qū]”、“黑黢黢[qüo]”、“黑奘奘[zàng]”,各有侧重,或形容天色、光线,或形容肤色、体质,或形容身体壮实,真可谓词材济济,待选无遗,写作者满可以挑肥拣瘦,酌情录用。
《蜀语》记录明代的四川口语,其中有些形容词是据音写字,或形容人,或形容物,不难区分。
例如:
“露牙曰龅,音报。
”今语有“龅牙齿[cī]”。
“谓人形短曰矮矬挫,七禾切,音搓。
”今语有之,音如撮[cuo]。
“老曰老革革。
《三国志》彭?
k骂先主‘老革荒悖’。
”今语有“啥子肉哦,老革革[gè]的!
”,也有“老疙兜”以状物。
“性傲曰戆,音刚去声。
”今语“性子直戆戆”,只是不弯环倒拐,并不一定骄傲。
“仔细谓之把稳。
”今语“穿钉鞋杵拐棍儿,把稳,又把稳。
”犹如“摸到石头过河。
”
“谓人朴讷曰木诎,诎音黜,词塞也。
”今语“木[mǔ]诎诎[cuo]的,站起不开腔。
”
“物朽而断曰音尊上声。
”今语“年辰久了,线子都[zèn]了。
”
“物之渐销曰?
`,音育。
”指出“遇”是俗字。
还说杨升庵告诉问者“牙牌磨?
`”,?
`字如此写。
“香气盛曰,音蓬去声。
”今四川音pěng。
“喷[pěng]香”、“香喷喷[pēng]”与普通话“喷喷香、香喷喷”读音不同。
“物臭曰?
t?
h。
?
t音滂;?
h,抽去声,在纣字韵。
”实为“?
t臭”[pāngcǒu]。
pāng臭与pěng香相对,pāng与pěng,疑是元音对转,表示相反意思。
今语有“绯红、漆[qū]黑、梆硬[gèng]、稀嫩、溜酸、蜜[mīn]甜、交咸[han]、刮[gua]苦、溜?
?
[pā]”。
由此证明钱玄同先生的说法有理:
“方言的本身,是一种独立的语言;方言文学的本身,是一种独立的文学,它们自己发达,它们永远存在。
”
作者:
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成都)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