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夜宴谣长钗坠发双蜻蜓翻译赏析.docx
《古诗夜宴谣长钗坠发双蜻蜓翻译赏析.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古诗夜宴谣长钗坠发双蜻蜓翻译赏析.docx(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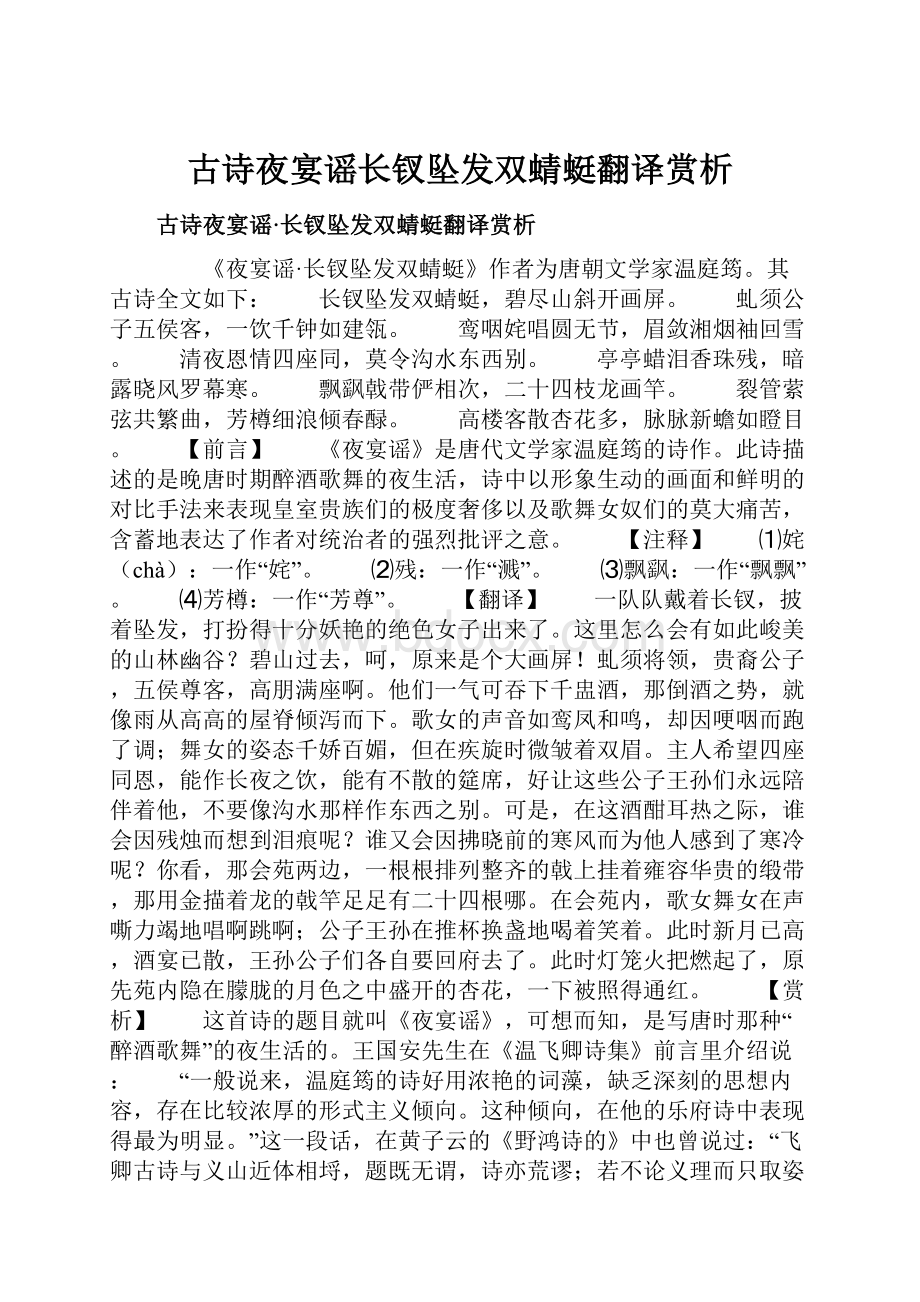
古诗夜宴谣长钗坠发双蜻蜓翻译赏析
古诗夜宴谣·长钗坠发双蜻蜓翻译赏析
《夜宴谣·长钗坠发双蜻蜓》作者为唐朝文学家温庭筠。
其古诗全文如下:
长钗坠发双蜻蜓,碧尽山斜开画屏。
虬须公子五侯客,一饮千钟如建瓴。
鸾咽姹唱圆无节,眉敛湘烟袖回雪。
清夜恩情四座同,莫令沟水东西别。
亭亭蜡泪香珠残,暗露晓风罗幕寒。
飘飖戟带俨相次,二十四枝龙画竿。
裂管萦弦共繁曲,芳樽细浪倾春醁。
高楼客散杏花多,脉脉新蟾如瞪目。
【前言】 《夜宴谣》是唐代文学家温庭筠的诗作。
此诗描述的是晚唐时期醉酒歌舞的夜生活,诗中以形象生动的画面和鲜明的对比手法来表现皇室贵族们的极度奢侈以及歌舞女奴们的莫大痛苦,含蓄地表达了作者对统治者的强烈批评之意。
【注释】 ⑴姹(chà):
一作“姹”。
⑵残:
一作“溅”。
⑶飘飖:
一作“飘飘”。
⑷芳樽:
一作“芳尊”。
【翻译】 一队队戴着长钗,披着坠发,打扮得十分妖艳的绝色女子出来了。
这里怎么会有如此峻美的山林幽谷?
碧山过去,呵,原来是个大画屏!
虬须将领,贵裔公子,五侯尊客,高朋满座啊。
他们一气可吞下千盅酒,那倒酒之势,就像雨从高高的屋脊倾泻而下。
歌女的声音如鸾凤和鸣,却因哽咽而跑了调;舞女的姿态千娇百媚,但在疾旋时微皱着双眉。
主人希望四座同恩,能作长夜之饮,能有不散的筵席,好让这些公子王孙们永远陪伴着他,不要像沟水那样作东西之别。
可是,在这酒酣耳热之际,谁会因残烛而想到泪痕呢?
谁又会因拂晓前的寒风而为他人感到了寒冷呢?
你看,那会苑两边,一根根排列整齐的戟上挂着雍容华贵的缎带,那用金描着龙的戟竿足足有二十四根哪。
在会苑内,歌女舞女在声嘶力竭地唱啊跳啊;公子王孙在推杯换盏地喝着笑着。
此时新月已高,酒宴已散,王孙公子们各自要回府去了。
此时灯笼火把燃起了,原先苑内隐在朦胧的月色之中盛开的杏花,一下被照得通红。
【赏析】 这首诗的题目就叫《夜宴谣》,可想而知,是写唐时那种“醉酒歌舞”的夜生活的。
王国安先生在《温飞卿诗集》前言里介绍说:
“一般说来,温庭筠的诗好用浓艳的词藻,缺乏深刻的思想内容,存在比较浓厚的形式主义倾向。
这种倾向,在他的乐府诗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这一段话,在黄子云的《野鸿诗的》中也曾说过:
“飞卿古诗与义山近体相埒,题既无谓,诗亦荒谬;若不论义理而只取姿态,则可矣。
”这样的论点,早成了正统的共识。
许多评论者大都是把温庭筠当作一个唯美派的形式主义者,而认为他作品的思想内容是不健康的,有的甚至说成是淫秽腐朽的。
王安国先生接着说:
“本来在中唐时期,由于白居易的倡导,诗人们‘缘事而发’,竞相创作新乐府,指摘时弊,反映现实,这种良好的风气,在晚唐作家中并未消失。
但是温庭筠的乐府诗,反映社会现实较少,而刻意追求的是形式的华美,描摹的是醉酒歌舞的奢靡生活,充满了珠光宝气、脂粉香泽。
他的一部分五七律中,也有这样的情况。
这种浮艳轻靡的诗风,是和他长期出入歌场舞榭的放荡生活分不开的。
” 很明显,在王国安先生看来,从新乐府来说,是晚唐不及中唐,而温庭筠又是晚唐中之最不济事者。
其实,这恐怕是误解,或者竟是偏见。
艺术上的繁复,是成熟的表现;不能以直白粗放为进步,而以艳丽多姿为堕落。
单瓣的原菊,当朴素的黄星洒满山峦的时候,也许是秋色宜人的,论野趣可;然于“花”,终少了几许姿色。
如果把这满山的黄花,尽换作后人在原菊的基础上用心血和智慧培育出来的、成百上千的名菊,如“主帅红旗”、“西施洗发”、“黄海秋月”、“碧水长天”,还有什么“绿牡丹”、“碧玉簪”等等,等等(仅此名目,就足令人心醉),则那整个大自然都将是充溢着美的发现,使人每见一枝,都大为惊叹,留连忘返,则是比单一的黄花,一目了然,有着更多的情趣和风韵。
诗,和所有的艺术一样,也应当如此。
就以王先生夸许的白居易的著名的新乐府而论,“满面灰尘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刻画一位烧炭老人,形象当然是鲜明的,诗人的“苦宫市”之情也是明白的。
然而,对于统治阶级的揭露,实事求是地说,绝像是一篇新闻报导,毕竟不耐读。
原因就在于欠了点韵味和深度。
这也难怪,因为正如他自己说的:
“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手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歌咏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
上以广宸聪,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而已。
他原本就是写给皇帝看的,所以他只能如此。
当然,作为一种写法,原也无可厚非。
但如果把它抬得太高,以为只此才是好诗,就未免有点以偏概全,不知“百花齐放”为何物了。
毛泽东在总结了唐宋诗的规律以后,指出来说:
“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可见用形象思维的诗人,也不能就说比散文化的诗人为低。
聪明的说法是:
都是时代的花朵,各有各的时代赋予他们的特色。
温庭筠这位艺术家的特色,也就是他倒霉的地方,就在于他的诗词,几乎是很少用散文式的语言的,绝少直抒胸臆。
他只习惯于用形象说话。
他的诗艺高超之处,可以这样说,他仿佛早在一千多年以前,就懂得了迟至今日才在电影美学里为电影大师们所掌握的蒙太奇。
他只是在逻辑思维的“经”上,去突出作为“纬”而显现的形象,让织出的艳丽的花纹把经掩盖起来,让这些看似跳跃性很大、甚至不大相关的景象,通过它们的分切组合,而显示出作品的意蕴。
这种手法即令当初在电影里,也曾经使人大惊小怪的,更何况他早在一千多年前的诗里就出现了。
所以说他是形式主义的,虽不合乎事实,但也就是可以谅解的了。
就以王先生认为“描摹的是醉酒歌舞的奢靡生活”的这首《夜宴谣》为例,读着它,让人仿佛感到在这丑恶的现实之中,有一颗能于别人的笑闹中见到泪光的伟大的心,正在因别人的痛苦而颤栗。
当然,这是要读者自己去体会,而不是他直接告诉读者的。
可见批评,固在衡人,其实也是在称量自己。
不能从华丽的外饰下区分出善良和丑恶、伟大和猥琐,而一概认为华丽即放荡,这样草率地断言别人为形式主义,恰好证明这个批评本身,倒真是形式主义的了。
《夜宴谣》不仅形式华美,思想内容也是深刻的。
只是它不像《卖炭翁》那样,将要表达的思想明摆在了外面,而就是要人从他的形式后面去细心地探求。
这大约是时代到了晚唐,走向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那种能容纳“补时阙”的胆略,也随之逐渐地衰落了之故。
是以这才产生了“温李”这样华丽而隐晦的作品。
学者们既在政治和经济上划分出中唐和晚唐,却要求这两个不同时代的作家风格一致,这本身就已违反了历史的逻辑。
其实晚唐的诗,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
此诗一开头:
“长钗坠发双蜻蜓,碧尽山斜开画屏。
”它确实不如“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那样好懂。
既然题目写的是“夜宴”,那当然,这儿写的“长钗”指的就是侍姬、歌妓、舞女。
当满堂都是“虬须公子五侯客”时,特别是下面点明了这是天子的私宴时,则这些歌舞妓也就绝对不止一个。
所以可以把这一句理解为这是一队队这样长钗、坠发,打扮得十分妖艳的绝色女子。
能蓄有这样多的技艺高超的绝色妖姬之宫庭,其富贵自是不待言的了。
所以胡仔说他善于写“富贵佳致”。
这不是主观的代诗人设想,而是内在逻辑的必然联系。
是以诗人在此只点到为止;这正是他的笔墨经济之处。
如果根据诗人特地圈定的这些景物,把它们串联起来,这就像是电影镜头,一开始从一队队歌舞妓摇了过去,接着,镜头摇到了碧山,只见奇峰叠翠,飞瀑流湍。
从脂粉的细腻,一下推到了丛山峻岭的雄奇。
读者或许会奇怪:
此处哪来如此峻美的山林幽谷?
碧山尽了,原来是此处的偌大的画屏。
画屏移开,这才出现了酒宴的情景。
至此,读者不能不惊喜作者的艺术手法之新奇。
在一开头的这一联里,居然悬念丛生,一波三折,遥遥写来,非常引人入胜。
没有新奇感,那是谈不上艺术的。
何况他这儿的新奇,原不是为了猎奇而节外生枝。
它原本就是这儿的典型环境,只不过在介绍时,作了点波折,遂显得别致而已。
第二联:
“虬须公子五侯客,一饮千钟如建瓴。
”诗人采用了避实就虚,虚实结合的写法。
前来赴宴的客人是要点明的,所以“虬须公子五侯客”,毫不含糊。
因为不点明就不知他们身份的高贵。
其实这宫廷的宴会,只不过是意在指出这就是上层社会的缩影。
但他用一“客”字,又躲闪了开去。
虬须,当是爱将;公子,是贵裔;而五侯,是借东汉的典故,借指专权的宦官。
晚唐之季,宦官之祸到了无比严重的地步。
《旧唐书·宦官传序》说:
“自贞元之后,威权日炽,兰锜将臣,率皆子畜;蕃方戎帅,必以贿成;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
”所以温庭筠这样写,绝不会是无所指的。
但他用“客”字推了开去,不露君臣的痕迹,以免剌激。
但用主客以写君臣,这实际又是最大的剌激。
虚虚实实,真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寻”。
至于客有多少,酒宴如何丰盛,主客们又是如何放浪形骸之外,这在诗里都不好写,于是他采取实物变形的手法,仅用了一句“一饮千钟如建瓴”以尽之。
钟,是圆形的大肚壶。
“一饮千钟”,正如“白发三千丈”一样,虽实犹虚。
因为既可以指他们豪兴方长,饮的酒多,一气可吞下千钟之酒。
但也可以是指宾客之众,济济一堂,大家举起杯子时,那数不清的杯子,简直需千钟才斟得满。
这儿的虚比实有更大的容量。
既然一饮千钟,那倒酒之势,是会像雨从高高的屋脊倾泻而下那样的。
这恰似现代电影中的主观镜头,他把倾下的千钟之酒,非常形象地化成了飞流直下的瀑布。
则这表象虽虚,却又非常的质实。
诗中深刻地写出了奢侈到了十分惊人的程度。
它所揭露的,将比任何叙述的语言都更为丰富得多的。
看来“虬须公子五侯客”并非是诗人所属意的主人,是以于他们只是虚晃一枪,接着就用非常细腻的笔触,写下了歌姬舞妓的姿容:
“鸾咽姹唱圆无节,眉敛湘烟袖回雪。
”鸾凤和鸣,古时用来形容声音的美妙。
姹,是美女。
唐时眉饰有一种含烟眉。
着一“湘”字,使人想到了屈原的“结桂枝兮延伫,羌愈思兮愁人”的神态。
美音和咽联系在一起,美容和愁联系在一起,使美而生愁,正如人们见着了西子捧心,那是非常容易动人恻隐的心弦。
这一联,艺术效果是非常强烈的。
当然,如果和白居易的新乐府《胡旋女》“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
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比起来,那以秾丽著称的温八叉,确实不及香山居士之风流酣畅。
当她“曲终再拜谢天子,天子为之微启齿”时,他这里的舞者和欣赏舞者,在感情上是很融洽的。
虽然白居易意在“数唱此歌悟明主”,但对那可怜旋转得“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的舞女,诗人只是欣赏,却全无半点怜悯与同情。
他的眼睛是向上看的。
他的“指摘时弊”只不过是如鲁迅先生说的,意在招呼他的主子不要把袍子烧了而已。
温庭筠这样的诗,看来他反映现实是较少的。
他不是新闻报导,是以他看到的不是舞女们的“斗妙争能”,不是“曲终再拜”,而是歌女因哽咽而跑了调,舞女在疾旋时微皱着双眉。
温庭筠是精通音律的,正如“曲有误,周郎顾”那样,她们细微的失误,都难逃他那敏锐的神经。
然而,这里与音乐的悟性无关,他是用良心在感觉,他是出于伟大的同情,这才能在别人看来是“香衫袖窄裁”、“金丝蹙雾红衫薄”连范文澜先生都说她们“故作媚态,尤为淫靡”的时候,温庭筠看到的却是痛苦的悲咽和愁容。
体贴,也是要有生活基础的,不是平日深谙她们的痛苦,或者竟是自己也有类似的经验,他不可能在欢乐的华林,偏偏有此悲凉之雾的感受。
温庭筠只不过写出侍姬们因失去了人格的尊严,过着心灵屈辱生活的痛苦,没有直接去指摘那个社会,指责这种奢靡的生活,如白居易那样,明白的说“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
——其实白居易在这儿把舞妓和安禄山、杨贵妃等同了起来,姑不论拟于不伦,说穿了也不过是女人是祸水的老调,为唐明皇开脱而已。
而温庭筠这里,虽只勾画了豪门夜宴中的这么两个细节,然而作家的进步倾向就寓于这细节之中了。
他就是要给这样美妙的生活戳上一个窟窿,而不是弥补它,粉饰它。
珠光宝气在他的笔下,无异是套在她们纯洁心灵上的枷锁,粉脂香泽,也不过是给尊严的人格涂上屈辱的标志。
他写的是另一种现实。
他是眼睛向下的。
是以他看到的,不是至高无上的皇帝的脸色,而是压迫在最底层的妓女们的痛楚。
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不仅写出了阶级的对立,甚至还写出了压迫的根源。
写出了皇王贵族的欢乐,就是建立在她们的痛苦之上的。
虽然他当年不可能懂得什么是阶级斗争的学说,但可以肯定地说:
他如果没有反对晚唐这种没落统治的进步思想,是绝对不会与这些“虬须公子五侯客”在感情上是如此绝然对立的。
仅这一点,他便远远胜过许多古人,也远远超过了白居易的乐府水平。
这样具有鲜明立场的诗,不能称之为现实主义的杰作,而硬要说成是什么“内容腐朽”,“无非是宫体的变形”,这是莫大的冤枉。
他虽参加了夜宴,但感情却不同,能有如此用心,根本谈不上什么“放荡”。
他不仅看到了这些女奴的痛苦,而且还有勇气在自己的乐府中为她们表达出来,根本不能说这是“形式主义”。
当然,正是他的这种立场和表现,是要被封建的士大夫们说为“无行”的;他若“有行”,也就是和他们一个样了。
然而对于今人,对于进步的评论家,由于立场的不同,不能和封建主义者同一个腔调。
是以跟着前人而不加分析地说温庭筠是什么“缺乏深刻的思想内容”,说他“描摹的是醉酒歌舞的奢靡生活”,是没有“反映现实”,没有“指摘时弊”,就未免有乏艺术的真知灼见了。
他正是出于对女奴的同情,因此对于她们的对立面——这里的主客们就不能不感到愤懑。
他表面上把主人写得何等的殷勤好客,然而,实际上却正是在揭露他们的贪得无厌。
“清夜恩情四座同,莫令沟水东西别。
”他要使四座同恩,要作长夜之饮,甚至奢望他们这样的日子地久天长,真格有不散的筵席,好让这些公子王孙们永远陪伴着他,莫要像沟水那样作东西之别。
主人的这种希望享尽人间富贵荣华的感情是非常强烈的。
但既然他们的欢乐是建立在歌舞侍姬们的痛苦之上的,则这一对矛盾的结果,那就必然是:
统治者愈长欢,她们的痛苦也就愈深沉。
这种对于公子王孙们的“恩情”,就是加在她们头上的罪孽。
统治者如此之尽情享乐,她们不得不歌喉裂,舞腰折,不可能如白居易说的那样“不知疲”。
在温庭筠的笔下,她们正是心力交瘁的。
他用了类似今天蒙太奇的隐喻手法,写出“亭亭蜡泪香珠残,暗露晓风罗幕寒。
”当酒酣耳热之际,谁会因残烛而想到泪痕呢?
谁又会因拂晓前的寒风而为他人感到了寒冷呢?
这绝不会是“一饮千钟如建瓴”的座上客,而只有那些侍姬们的心境才会如此。
所以这一联其实是写侍姬们的,但却是写诗人用心感觉到的。
同一舞妓,在别人看来是香艳肉感,而他却看到了泪珠和战栗。
这的确是巨大的思想差距。
世人一向以温庭筠同情妓女来鄙薄他,殊不知这恰恰使自己站在封建主的立场上去了。
这正如《红楼梦》中贾政说的:
这样演下去,“明日就要酿到弑君杀父”。
而在贾宝玉看来,却是“就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
”温庭筠正是如此。
态度之不同,原本就是立场的不同。
温庭筠在这儿反封建的立场是非常鲜明的。
诗人巧妙地利用时空穿插,在这里补叙出主人的身份:
“飘飘戟带俨相次,二十四枝龙画竿。
”据《典略》载:
“天子戟二十有四。
”那么温庭筠在这里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封建的最高统治者了。
他用典章制度形象地告诉了人们:
原来这儿的主人就是天子,无怪乎是如此之豪华。
这象征着天子之威仪的用金描着龙的戟竿,却滑稽地对着轻狂的醉汉;而那戟上显示雍容华贵的缎带,于歌舞妓的寒栗中飘动,构成了穆肃威严而又靡烂悲凉的意境。
这真是晚唐极其鲜明而又深刻的写照。
全诗共四绝,他的叙述是采取交叉方式进行的。
即在每一绝中,都是把歌舞妓和皇王贵戚们对比着写的,使人产生强烈的印象。
不知他是有意还是无意,在每一绝中,又总是先在上联写歌舞妓,后在下联再写皇王贵族。
这在封建社会等级森严的制度下,仅这失序就是大逆不道的。
所以温庭筠终至没没以终,那倒是与他这种耿介拔俗的气节分不开的。
他可以说是一个悲剧的性格。
不在封建的没落中找正直,而也随同封建之陈辞烂调以贬抑之,这不能不是当代学者的耻辱。
最后一绝更妙。
“裂管萦弦共繁曲,芳尊细浪倾春醁。
高楼客散杏花多,脉脉新蟾如瞪目。
”“裂管萦弦”,是歌舞者之悲辛;“芳尊细浪”见欢宴者之舒适。
诗到这里有点小的变化:
他用一联把妓女和主客的苦乐、既矛盾又相关的关系总在了一起,为夜宴作一小结。
不像上三绝分两联写,而是并到一联里。
但在写法上依然是先妓女而后皇王贵族,腾出下联来发感慨。
不过他的感慨也特别,依然是形象而不是议论。
是以末联最不好懂;然而也实在是深刻。
“高楼客散杏花多”,这里点明了时间,繁杏盛开,正是早春时候。
新月已高,说明夜已深沉。
所以身穿薄纱的歌舞妓们,要感到春寒料峭了。
然而要说“客散杏花多”,是因为酒宴已散,王孙公子们各自要回府去了,各府的执事之众,此时皆燃起了灯笼火把,只见一片火光,顿时把个皇宫内苑照得一片通明。
于是,原先苑内隐在蒙胧的月色之中的杏花,一下被照得分外的红了。
他在另一首诗《走马楼三更曲》中曾这样写过:
“玉皇夜入未央宫,长火千条照栖鸟。
”黑夜中树上本来看不见的栖鸟,一下就被千条长火照见了,可为此诗的注脚。
可见当时场面之大。
他的艺术之特色,就在于他不说车马填闉,而偏要说灯红熔杏。
这就既写出了客人的执事之多,排场之大,从而也突出了主人的庭院之闳美。
周必大《二老堂诗话》载:
“白乐天集第十五卷《宴散诗》云:
‘小宴追凉散,平桥步月迟。
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
残暑蝉催尽,新秋雁载来。
将何迎睡兴,临睡举残杯。
’此诗殊未睹富贵气象,第二联偶经晏文献公拈出,乃迥然不同。
”晏殊之拈出第二联有富贵气的,正是温庭筠这里的意思。
然而,白居易只不过直叙其事,而温庭筠则写出了光与人的视觉心理,更妙在他用漫画的笔法,勾勒出“脉脉新蟾如瞪目”,简洁地画上一个初出茅庐的月亮,见了这样豪华的场面,惊得目瞪口呆了。
以此作结,这也就足够了。
他没有说月亮瞪目是为了什么,仍然留给大家去想;但这样并不等于他没有说。
月亮惊大了眼睛,这形象就是很新奇而意义又非常含蓄隽永的。
比僧本真的“夸道客衙好灯火,不知浑尔点膏脂”浑成多了。
有意义的是:
嫦娥本来是为了长生不老才逃进月宫里去的,然而在诗人笔下,月亮的寿命居然只有三十天;从朔而望,从望而晦,一月一个新月亮。
是以刚见世面的“新”蟾,是那样的幼稚,乍一见到这个场面,竟傻了眼;则此处之富丽真足以羞月,使嫦娥也感到了月宫的寒酸。
神仙尚且如此,世人的惊讶当然更甚。
其实,写神仙的幼稚无知,正是写人间的腐败已到了人神共怒的地步。
他只是不用这样叙述的笔法,而采用形象的寓意罢了。
那么诗人在这极度的夸饰之中,也是寓有严于斧钺的批判的。
这就是温庭筠。
如果说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一幅色彩对比非常鲜明的油画,它以逼真见长,然而也就见画而止。
那么温庭筠的这个结尾,就是一幅更饶讽刺意味的漫画。
让月亮对着朱门宴散的情景而瞠目相向,这极其富于艺术的讽剌趣味。
如此清新幽默,则不是“宫体”所限制得了的。
---来源网络整理,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