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对宋学的现代诠释.docx
《钱穆对宋学的现代诠释.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钱穆对宋学的现代诠释.docx(3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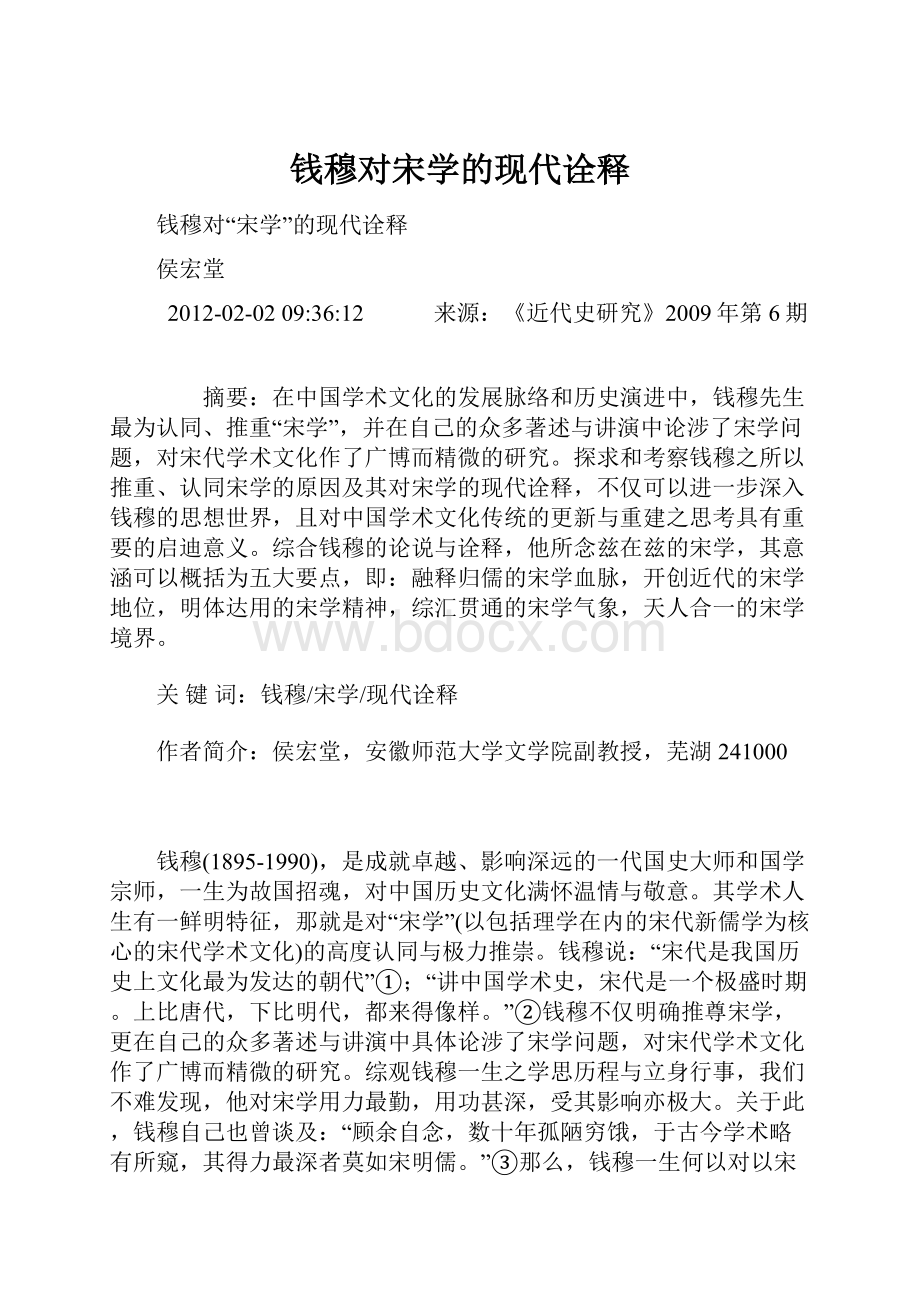
钱穆对宋学的现代诠释
钱穆对“宋学”的现代诠释
侯宏堂
2012-02-0209:
36:
12 来源:
《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
摘要:
在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脉络和历史演进中,钱穆先生最为认同、推重“宋学”,并在自己的众多著述与讲演中论涉了宋学问题,对宋代学术文化作了广博而精微的研究。
探求和考察钱穆之所以推重、认同宋学的原因及其对宋学的现代诠释,不仅可以进一步深入钱穆的思想世界,且对中国学术文化传统的更新与重建之思考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综合钱穆的论说与诠释,他所念兹在兹的宋学,其意涵可以概括为五大要点,即:
融释归儒的宋学血脉,开创近代的宋学地位,明体达用的宋学精神,综汇贯通的宋学气象,天人合一的宋学境界。
关键词:
钱穆/宋学/现代诠释
作者简介:
侯宏堂,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芜湖241000
钱穆(1895-1990),是成就卓越、影响深远的一代国史大师和国学宗师,一生为故国招魂,对中国历史文化满怀温情与敬意。
其学术人生有一鲜明特征,那就是对“宋学”(以包括理学在内的宋代新儒学为核心的宋代学术文化)的高度认同与极力推崇。
钱穆说:
“宋代是我国历史上文化最为发达的朝代”①;“讲中国学术史,宋代是一个极盛时期。
上比唐代,下比明代,都来得像样。
”②钱穆不仅明确推尊宋学,更在自己的众多著述与讲演中具体论涉了宋学问题,对宋代学术文化作了广博而精微的研究。
综观钱穆一生之学思历程与立身行事,我们不难发现,他对宋学用力最勤,用功甚深,受其影响亦极大。
关于此,钱穆自己也曾谈及:
“顾余自念,数十年孤陋穷饿,于古今学术略有所窥,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
”③那么,钱穆一生何以对以宋代新儒学为核心的宋代学术文化即宋学如此推尊呢?
他又是如何对宋学进行富于创造性的现代诠释的呢?
对这些问题的考察,不仅可以进一步深入钱穆的思想世界,深切感受他的学术理想与文化关怀,而且对中国学术文化传统的更新与重建之思考也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综合钱穆的论说与诠释,我认为,他所念兹在兹的宋学,其意涵可以概括为五大要点,即:
融释归儒的宋学血脉,开创近代的宋学地位,明体达用的宋学精神,综汇贯通的宋学气象,天人合一的宋学境界。
一、融释归儒的宋学血脉
1.“融释归儒”,此乃宋儒之“真血脉”、“大贡献”
宋代新儒学是宋学的核心,宋代新儒学之所以“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融化进了佛学。
钱穆在关于宋学的著述与讲演中尤其凸显和肯定了宋儒“融释归儒”的特殊功绩,认为这是宋儒的“大贡献”、宋学的“真血脉”。
钱穆说:
“禅宗冲淡了佛学的宗教精神,挽回到日常人生方面来。
但到底是佛学,到底在求清静,求涅槃。
宋明儒沿接禅宗,向人生界更进一步,回复到先秦儒身、家、国、天下的实际大群人生上来。
但仍须吸纳融化佛学上对心性研析的一切意见与成就。
宋明儒会通佛学来扩大儒家,正如《易传》、《中庸》会通庄老来扩大儒家一般。
宋明儒对中国思想史上的贡献,正在这一点,在其能把佛学全部融化了。
因此有了宋明儒,佛学才真走上衰运,而儒家则另有一番新生命与新气象。
”④又云:
“禅宗主张本分为人,已扭转了许多佛家的出世倾向,又主张自性自悟,自心自佛,早已从信外在之教转向到明内在之理。
宋明儒则由此更进一步,乃由佛转回儒,此乃宋明儒真血脉。
”⑤“融释归儒,是宋明儒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大贡献。
”⑥首先应当说明的是,钱穆虽将“宋明儒”合而言之,但综观钱穆的相关论述,我们不难发现,他是把“融释归儒”的功绩主要归功于“宋儒”的。
钱穆的这几段话极为重要,至少表明了他关于宋代儒释关系的两大观点:
其一,禅宗冲淡了佛学的宗教精神,把佛法挽向现实人生化,开启了宋代新儒学;其二,宋儒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大贡献是“融释归儒”,开出了儒家的新生命与新气象。
关于宋代新儒学之兴起,钱穆特别凸显了禅宗的作用,而反对流行的一般见解,即将宋代新儒学之开启归功于韩愈辟佛。
他说:
“禅宗时期,正是中国佛学的最盛时期,却被那辈祖师们都无情地毒骂痛打。
打醒了,打出山门,各各还去本分做人,遂开出此后宋代的新儒学。
后人却把宋学归功到韩愈辟佛,这不免又是一番糊涂,又是一番冤枉。
”⑦值得注意的是,钱穆同时又认为,宋学最初之姿态,要远溯到韩愈的提倡师道、辟佛卫道。
他说:
“宋学最先姿态,是偏重在教育的一种师道运动。
这一运动,应该远溯到唐代之韩愈。
”⑧“韩退之大声疾呼,斥佛排老,反对进士诗赋,尊儒术,唱古文,继孟子立师道。
在当时虽无多大影响,而宋学则远承韩氏而起。
”⑨钱穆同时兼持的这两种观点,看似自相矛盾,其实是一脉贯通的。
钱穆认为,宋代新儒学不等同于宋代理学,还应包括理学出现之前的北宋初期儒学⑩,宋代新儒学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北宋初期儒学(“初期宋学”)、北宋理学(“中期宋学”)和南宋理学(“南渡宋学”)。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钱穆上面所说的看似矛盾的两种观点了。
若整体综合地来看,钱穆其实是在强调:
禅宗开启了宋代理学,理学之兴起,实自禅宗启之,而不能归功到韩愈辟佛;韩愈影响了初期宋学之姿态,宋学“初期风气,颇多导源于韩愈”(11),而不是由禅宗开出。
在钱穆看来,无论是韩愈所影响的初期宋学,还是禅宗所开启的宋代理学,都对中国儒家思想文化之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他们“融释归儒”的功绩可以分别来看:
初期宋学外于释老而求发扬孔子之大道与儒学之正统,侧重于立儒归儒;理学则针对释老而求发扬孔子之大道与儒学之正统,侧重于辟释融释。
让我们先来看看初期宋学之立儒归儒。
钱穆在论及宋代新儒学之时,非常强调初期宋学重要的历史地位。
在《宋明理学概述》中,钱穆有言:
“北宋初期诸儒,其中有教育家,有大师,有政治家,有文学家,有诗人,有史学家,有经学家,有卫道的志士,有社会活动家,有策士,有道士,有居士,有各式各样的人物……但他们中间,有一共同趋向之目标,即为重整中国旧传统,再建立人文社会政治教育之理论中心,把私人生活和群众生活再纽合上一条线。
换言之,即是重兴儒学来代替佛教作为人生之指导。
这可说是远从南北朝隋唐以来学术思想史上一大变动。
至其对于唐末五代一段黑暗消沉,学绝道丧的长时期之振奋与挽救,那还是小事。
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一时期那些人物之多方面的努力与探究,才能了解此后宋学之真渊源与真精神。
”“后代所谓理学或道学先生们”,“这些人,其实还是从初期宋学中转来。
不了解宋学的初期,也将不了解他们。
”(12)在此,钱穆突出了两点:
其一,初期宋学多方面的活动与努力重整了儒学传统,扭转了魏晋以来儒学衰败的局面。
其二,初期宋学尊师重道,从学术和政治等方面正面重整儒家传统以代替佛教作为人生之指导,从而光大发扬了韩愈的道统说,直接影响到后起的理学。
在《朱子学提纲》中,钱穆在归纳简介了北宋初期儒学三个方面(一曰政事治平之学,一曰经史博古之学,一曰文章子集之学)的内容和成就之后,又总结道:
“宋儒为学……若衡量之以汉唐儒之旧绳尺,若不免于博杂。
又好创新说,竞标己见。
然其要则归于明儒道以尊孔,拨乱世以返治。
”(13)总之,钱穆认为,初期宋学“重整中国旧传统”,“明儒道以尊孔”,“重兴儒学来代替佛教作为人生之指导”,在发扬与回归孔子之大道与儒学之正统上作出了重大贡献。
再看宋代理学之辟释融释。
北宋初期诸儒虽然对发扬与回归儒学传统作出了不可磨灭之贡献,但由于他们毕竟外于释老而只是正面立说,所以,宋代重振儒学、辟禅辟佛之任务完成,主要还当归功于理学之兴起。
钱穆指出:
“宋儒可分先后两期。
胡瑗、孙复、石介、范仲淹开其先,大率从经学阐儒学,通经致用,近似汉儒轨辙。
周张二程承其后,始有所谓‘理学’。
理学家与前期诸儒异者,在其能入虎穴,得虎子,旁采老释,还以申阐儒义。
复以儒义纠弹老释,汇三派为一流,卓然成为一种新儒学。
”(14)又说:
“北宋诸儒,只重在阐孔子,扬儒学,比较似置老释于一旁,认为昌于此则息于彼……理学家之主要对象与其重大用意,则正在于辟禅辟佛,余锋及于老氏道家。
亦可谓北宋诸儒乃外于释老而求发扬孔子之大道与儒学之正统。
理学诸儒则在针对释老而求发扬孔子之大道与儒学之正统。
明得此一分辨,乃能进而略述理学家之所以为学,与其所谓为学之所在,亦即理学家之用心与其贡献之所在。
”(15)较之于北宋初期诸儒“从经学阐儒学”,理学家“针对释老而求发扬孔子之大道与儒学之正统”的任务更为艰巨、更为深细。
他说:
“禅宗的新宗教,不啻叫人回头,由真返俗。
而进士轻薄,终于担当不了天下大事。
在这情形下,须待北宋知识分子再来打开新风气,寻觅新生命。
书院讲学,由此酝酿。
他们要把和尚寺里的宗教精神,正式转移到现实社会。
要把清净寂灭究竟涅槃的最高出世观念,正式转变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中国传统人文中心的旧理想。
唐代禅宗诸祖师,只在佛教教理方面翻一身,先为宋人开路。
至于正式离开和尚寺,回头再走进政治社会现实人生的圈子,而仍须不放弃那一段对大群关切的宗教热忱,又须在理论上彻底破坏他们的,建立我们的,拔赵帜,立汉赤帜,那是宋儒当前第一工作。
那是一番够艰巨,够深细的工作呀!
”(16)
可见,在此一番艰巨而深细的工作中,理学与佛教禅宗的关系极为复杂:
一方面,禅宗把佛法挽向现实人生,开启了理学,理学要沿接禅宗进一步走向现实人生;另一方面,理学又要辟禅辟佛,在心性修养理论上从佛学那里夺回儒学的主导权,而理学在建立自己的理论时还须融会佛学心性理论的成就以扩大儒学。
也正是因为理学与佛教禅宗之间有着紧密而复杂的关系,“乃使后人有疑理学为禅学之化身者”(17)钱穆则强调:
理学家言性言理,融化佛学,尽管有近禅处,但就人文本位精神而言,则陆王确然为儒而非禅,“程朱决未失孔孟人文本位之大传统”(18);“要其宗旨血脉所在,则与夫老、释者不同也。
后世或专以迹涉老、释为理学家病,亦岂为知理学之真哉?
”(19)钱穆明确指出理学家与禅宗有着根本的差异:
“禅宗不脱佛学传统,以出世离尘为主,理学家则以淑人拯世为本。
因此禅宗推论宇宙,必归之于寂灭空虚,而理学家论宇宙,则不忽其悠久性与复杂性。
此乃双方之大异处。
”(20)“宋儒辟佛,是要在此心明觉之外提示一所觉之‘理’来……这是宋儒辟佛一最大根据。
儒言理,佛学则不言理。
后人称之为儒、佛疆界。
”(21)而理学家之所以要体贴出一个“理”来,“实别有一番苦心”(22),要由此而真正建立起自家的宇宙论与心性论,从而真正与佛禅抗衡。
钱穆之所以如此强调理学家确然未失孔孟人文本位之大传统以及儒释疆界,是因为“融释”最终必须“归儒”,如果融释而不能归儒,那么理学家就不得谓之为儒,理学对中国儒学之发展也就无所谓贡献了。
既“融释”而又“归儒”,才是理学对中国儒家思想文化发展之“大贡献”。
2.宋儒之“融释归儒”,体现了“更生之变”的文化理念
“融释归儒”,不只是宋儒对于中国儒学发展的客观贡献,同时也是他们自觉的主观努力,从中也明显体现了宋儒的文化理念:
“融释”,体现了宋儒融化佛禅以扩大儒学的开阔胸襟;“归儒”,体现了宋儒“严夷夏之防”的民族本位意识。
从文化理念的视角来看,宋儒之“融释归儒”,也最当钱穆所谓“更生之变”也。
钱穆对宋儒之“融释归儒”一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他说:
“以中国史比之西洋史,唐末五代,俨如罗马帝国之崩溃,而自宋以下,学术重兴,文化再起,迄于今千年以来,中国之为中国,依然如故,是惟宋儒之功。
”(23)“宋代国势积弱,虽未能全部扭转中、晚唐之颓运,但此后一千年,中国文化仍得传统勿辍,实胥赖于宋人。
”(24)“中国社会到了宋代,可说是纯净化了。
不像唐代,有新的外国宗教,有许多异血统、异民族,宋朝都把来纯化,学术领导是儒家,整个社会是中国传统。
”(25)从这几段话中,我们可以明显见出,钱穆对宋儒“严夷夏之防”的民族本位意识的认同与表彰。
钱穆又明确有言:
“宋代新儒学之主要目标,在于重新发扬古代儒家之人生理想,俾其再与政治理想通会一贯,把孔子教理来排斥释迦教理。
”(26)但应当强调的是,宋儒的排佛不是一味的对外来文化的拒斥,他们的“严夷夏之防”也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对佛教冲击的忧虑、对抗与回应,他们要为中国儒学争道统,其最终目的是复兴儒学,守持民族本位。
钱穆之所以推重宋儒之“融释归儒”,是和钱穆自己所持守的文化发展理念及其时代感受密切相关的。
钱穆所持守的文化发展理念即“更生之变”与宋儒之“融释归儒”的文化精神息息相通,钱穆所处之国家、民族和文化的现实情势也与宋儒所面临的国家危机、佛教挑战有很多相似之处。
钱穆认为,博古可以通今,鉴古可以知今,宋儒如何应付佛教的挑战,如何融会佛学而开出儒学之新生命,多少会留下一些历史的经验与教训。
钱穆说:
“中国儒学最大精神,正因其在衰乱之世而仍能守先待后,以开创下一时代,而显现其大用。
此乃中国文化与中国儒学之特殊伟大处,吾人应郑重认取。
”(27)
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和中国的变局,中国的文化传统究竟将何去何从?
这是钱穆心中最放不下的一个大问题,也是他的“终极关怀”。
钱穆毕生治学,分析到最后,可以说就是为了解答此一大问题。
(28)钱穆自己在晚年所著《师友杂忆》的一开始就明确有言:
“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
”(29)钱穆认为,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和中国的变局,中国文化自不能不进行调整和更新,但是调整和更新的动力必须来自中国文化系统的内部。
他称这种文化变化与更新为“更生之变”:
“所谓更生之变者,非徒于外面为涂饰模拟、矫揉造作之谓,乃国家民族内部自身一种新生命力之发舒与成长。
”(30)基于“更生之变”的文化发展理念,钱穆强调,中国文化传统之更新与发展,必须由己之旧而达于新,必须守持民族本位,必须充分抉发中国文化传统内部的生命精神。
钱穆坚决反对“打倒一切,赤地创新”的论说,主张“从历史中求变,从文化传统中求新,从民族本身求新生命”(31),强调“就中国人立场,当由中国之旧传统而现代化,不应废弃旧传统,而慕效为西方之现代化。
不当喜新厌旧,而当由己之旧而达于新。
”(32)钱穆所谓之“更生之变”,不仅内在地蕴涵着持守民族本位的文化理念,更强调要充分抉发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内部的生命精神。
他说:
“我民族国家之前途,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得其生机”(33);“我们的文化前途,要用我们自己内部的力量来补救”(34);“中国文化重在其内部生命力之一气贯通”(35);“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在其内里,实有一种一贯趋向的发展”(36)。
由上所述,宋儒之“融释归儒”最能体现钱穆“更生之变”的文化发展理念,宋儒“融释归儒”的文化态度依然富于现代启示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钱穆又进一步指出:
“到近代,另一套新的文化系统与思想体系,从西欧传入,中国知识界才又激起了一种新变动。
此一番新传入,较之以前佛教东来,远为丰富复杂,又兼带一种强力冲击,使中国人无法不接受,但又无法从容咀嚼消化,来作一番清明的、理智的调和与综合。
遂使中国思想界,走进一个前所未有的混乱情况中,而急切澄清稳定不下。
”(37)也正因如此,“一生为故国招魂”的钱穆,其承担是沉重的。
不过,对中国文化始终持有坚定信念的钱穆,还是对近代中国思想界之未来工作抱着乐观的态度。
他说:
“但就中国人以往的智慧来看,此下的中国思想界,应能运用他们以前那一套综合的、融和的心情与方法,来自找出路。
只要待以时日,中国人对于此项工作,应该是仍可乐观的。
”(38)而宋儒之“融释归儒”,正是“一套综合的、融和的心情与方法”,正是“中国人以往的智慧”。
二、开创近代的宋学地位
1.“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也”
钱穆治史之对象,虽为中国通史,但他更注重于历史上的大变动时代,尤其是注重宋代。
因为在他看来,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之大转折时代,“宋开创了近代”(39),宋学对近代之学术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早在1937年所著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钱穆就明确提出了关于宋代学术文化地位的两个重要论断:
一是“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也”;一是“不知宋学,则无以平汉宋之是非”。
(40)前一论断,侧重于文化地位,主要论说宋学对近代的影响;后一论断,侧重于学术影响,主要论说宋学与汉学的关系。
先看前一论断“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也”。
与此相关的论断,还屡屡见诸于钱穆后来之著述。
《理学与艺术》一文有言:
“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
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
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
”(41)《唐宋时代的中国文化》一文,强调唐宋时代是中国文化一个大变动的时代,安史之乱以前之唐代是一个样,五代后之宋另是一个样。
(42)《〈崔东壁遗书〉序》曰:
“天宝以往,内乱外忧纷起迭乘,陷极于五季,宛转于北宋,而乃有大谋所以振起之者,于是而为北宋中叶以下之学术……挽近世之学术、人才、政事,胥于是焉奠之基。
或者谓近世之中国乃程朱之中国,其言殆非尽诬。
”(43)《中国文化之成长与发展》讲演辞曰:
“今天的中国社会,实可以说是由宋代一路下来的,与汉唐各不同。
现在由我们的社会往上推,推到宋朝,是近代的中国。
”(44)《宋明理学概述》一书中更明确有言:
“中国历史,应该以战国至秦为一大变,战国结束了古代,秦汉开创了中世。
应该以唐末五代至宋为又一大变,唐末五代结束了中世,宋开创了近代……我们若要明白近代的中国,先须明白宋。
”(45)
钱穆“宋开创了近代”之观点,最集中最具体地体现于他对清学史的梳理与评介上。
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引论”中,钱穆说:
“治近代学术者当何自始?
曰:
必始于宋。
何以当始于宋?
曰:
近世揭橥汉学之名以与宋学敌,不知宋学,则无以平汉宋之是非。
且言汉学渊源者,必溯诸晚明诸遗老。
然其时如夏峰、梨洲、二曲、船山、桴亭、亭林、蒿庵、习斋,一世魁儒耆硕,靡不寝馈于宋学。
继此而降,如恕谷、望溪、穆堂、谢山乃至慎修诸人,皆于宋学有甚深契谐。
而于时已及乾隆,汉学之名,始稍稍起。
而汉学诸家之高下浅深,亦往往视其所得于宋学之高下浅深以为判。
道咸以下,则汉宋兼采之说渐盛,抑且多尊宋贬汉,对乾嘉为平反者。
故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也。
”(46)钱穆“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也”的命题,不只是着眼于学术思想之发展,而且内在地蕴涵了“不知宋学,则无以平汉宋之是非”的思想,强调由宋学至清代学术之间的连续性与继承性,体现了“每转益进”的学术观念(关于此,下文将专门述论);同时,还涵蕴着“鉴古知今”的史学思想和文化关怀。
在此,让我们先考察钱穆“鉴古知今”的史学思想和文化关怀。
在钱穆看来,宋代学术文化面临的佛学挑战之情势跟近代的西学东渐十分类似,博古可以通今,鉴古可以知今。
所以,钱穆明确指出,“治史不及宋,终是与下面少交涉也”(47)。
钱穆这些论说,旨在强调宋学研究对于当下现实有着特殊的启示、意义与价值。
关于宋儒在面临佛学挑战时所持守与实践的“融释归儒”之文化观念对于近代的启示,我们在上文已有所论略,此不赘析。
1986年端午节前夕,钱穆在告别杏坛的“最后一课”中,着重讲述了“有关王荆公、司马温公两人新旧党争的经过”。
钱穆之所以要讲论这样的历史问题与历史人物,是因为在他看来,“鉴”宋学之“古”可以“知”现实之“今”。
钱穆表面上是在“谈古”,实质上是要“诫今”。
面对现实情势中“惊心动魄”的“求新求变”和“早已西洋化了”的屈原纪念活动,钱穆感叹不已!
他通过“历史”的讲述,强调“新”、“旧”两字实在难加分辨,不能只听“新”与“旧”之名称,谆谆告诫“现在”的中国人:
当深思而明辨“我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可谓与欧西民族大相异”;“你们不要忘了自己是一中国人”!
(48)“鉴古知今”的史学思想与文化关怀,贯穿于钱穆一生之著述与讲演。
在《国史大纲》“引论”中,钱穆之所以强调国民要具有“历史智识”,强调“历史智识”与“历史材料”之不同,主要就是因为“历史智识,随时变迁,应与当身现代种种问题,有亲切之联络。
历史智识,贵能鉴古而知今。
”(49)
那么,钱穆何以如此重视和强调“鉴古知今”呢?
这是和他对历史和史学的看法密不可分的。
钱穆认为,“历史是一种经验,是一个生命。
更透澈一点讲,‘历史就是我们的生命’”,而“生命一定会‘从过去透过现在直达到未来’”。
(50)因此,“历史上之过去非过去,而历史上之未来非未来,历史学者当凝合过去、未来为一大现在,而后始克当历史研究之任务”(51)。
关于史学,钱穆指出:
“史学必以国家民族大群体长时期上下古今直及将来为其学问之对象”(52);“治古史本求通今,苟能于史乘有通识,始能对当身时务有贡献,如是乃为史学之真贡献”(53);“治平大道,则本源于人类以往之历史。
治乱兴亡,鉴古知今,此为史学。
”(54)在钱穆看来,“史学在中国,乃成为一种鉴往知来、经世致用之大学问”(55)。
2.“不知宋学,则无以平汉宋之是非”
再看“不知宋学,则无以平汉宋之是非”的论断。
与此一论断极其类似,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中,又明确有言:
“窃谓近代学者每分汉宋疆域,不知宋学,则亦不能知汉学,更无以平汉宋之是非。
”(56)钱穆的这一主张,主要包括两层意涵:
从纵向的学术演进来看,钱穆此一主张强调宋学在清代的延续性和清代学风对宋明的继承性,彰显了宋学对有清一代学术的深刻影响,体现了钱穆推尊宋学的衡评立场;从横向的学派关系来看,此一主张蕴涵着钱穆对宋学与汉学之关系的深刻思考,也流露出钱穆对“近代学者每分汉宋疆域”的门户之见的明显不满。
钱穆从宋学的立场来看清代学术的观点,迥异时流。
对于清代汉学的学术渊源及其与宋学的关系,近代学术界有一种流行的看法,即认为清代汉学是对宋明理学的全面反动。
此种“理学反动说”以梁启超为突出代表。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就提出了“清学之出发点,在对于宋明理学一大反动”(57)的主张。
钱穆则不赞同梁启超这一观点。
钱穆强调,学术思想发展有着明显的前后继承性,宋学的传统在清代并没有中断;不仅没有中断,而且对清代汉学仍然有很深的影响,就是在汉学盛行的乾嘉时期也是如此。
所谓:
“宋明以来相传八百年理学道统,其精光浩气,仍自不可掩,一时学人终亦不忍舍置而不道。
故当乾嘉考据极盛之际,而理学旧公案之讨究亦复起。
”(58)
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就明确强调宋学在清代的延续性和清代学风对宋明的继承性。
该书第一章“引论”即明确有言:
“今自乾、嘉上溯康、雍,以及于明末诸遗老;自诸遗老上溯东林以及于阳明,更自阳明上溯朱、陆以及北宋之诸儒,求其学术之迁变而考合之于世事,则承先启后,如绳秩然,自有条贯,可不如持门户道统之见者所云云也。
”(59)《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内容安排,更明显地体现了钱穆力主清学导源于宋学的思想。
钱著第八章以戴东原为题,而以江慎修(永)、惠定宇(栋)、程易畴(瑶田)附之。
江、戴、程三人皆歙人,以江、程附戴,目的在于厘清戴学的学术渊源,因为“徽歙乃朱子故里,流风未歇,学者故多守朱子圭臬也”(60)。
钱穆述东原之学源于徽歙,戴学源出朱子,其用意主要落在宋学对戴氏的影响上。
钱著第十章以焦里堂(循)、阮芸台(元)、凌次仲(廷堪)为题而附之以许周生(宗彦)、方植之(东树),也体现了这种安排。
焦循、阮元、凌廷堪学尊东原,为考据名家,但钱穆看重的并不是他们在考据学上的成就,而是把眼光投注到他们对汉学流弊的反思和批评上。
此章又以考据学风的批评者许宗彦附于三人之后,以攻击乾嘉汉学最烈的方东树殿尾,无非是要向人们表露这样一个信息:
乾嘉汉学发展到此时已流弊重重,逐渐失去了学术界的支持,路穷必变,此后的学术路向必然要向汉宋兼采的方向发展。
(61)钱穆强调指出:
“其实有清一代,承接宋明理学的,还成一伏流,虽不能与经学考据相抗衡,依然有其相当的流量与流力,始终没有断。
这又告诉了我们,宋明七百年理学,在清代仍有其生命。
”(62)
钱穆强调宋学在清代的延续性和清代学风对宋明的继承性,明显体现了他“每转益进”的学术发展观。
在《〈清儒学案〉序》中,钱穆明确指出:
“要之有清三百年学术大流,论其精神,仍自沿续宋明理学一派,不当与汉唐经学等量并拟,则昭昭无可疑者。
抑学术之事,每转而益进,途穷而必变。
”(63)钱穆之“每转益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