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标准大学生英语综合教程第一册全部课文翻译资料.docx
《新标准大学生英语综合教程第一册全部课文翻译资料.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新标准大学生英语综合教程第一册全部课文翻译资料.docx(1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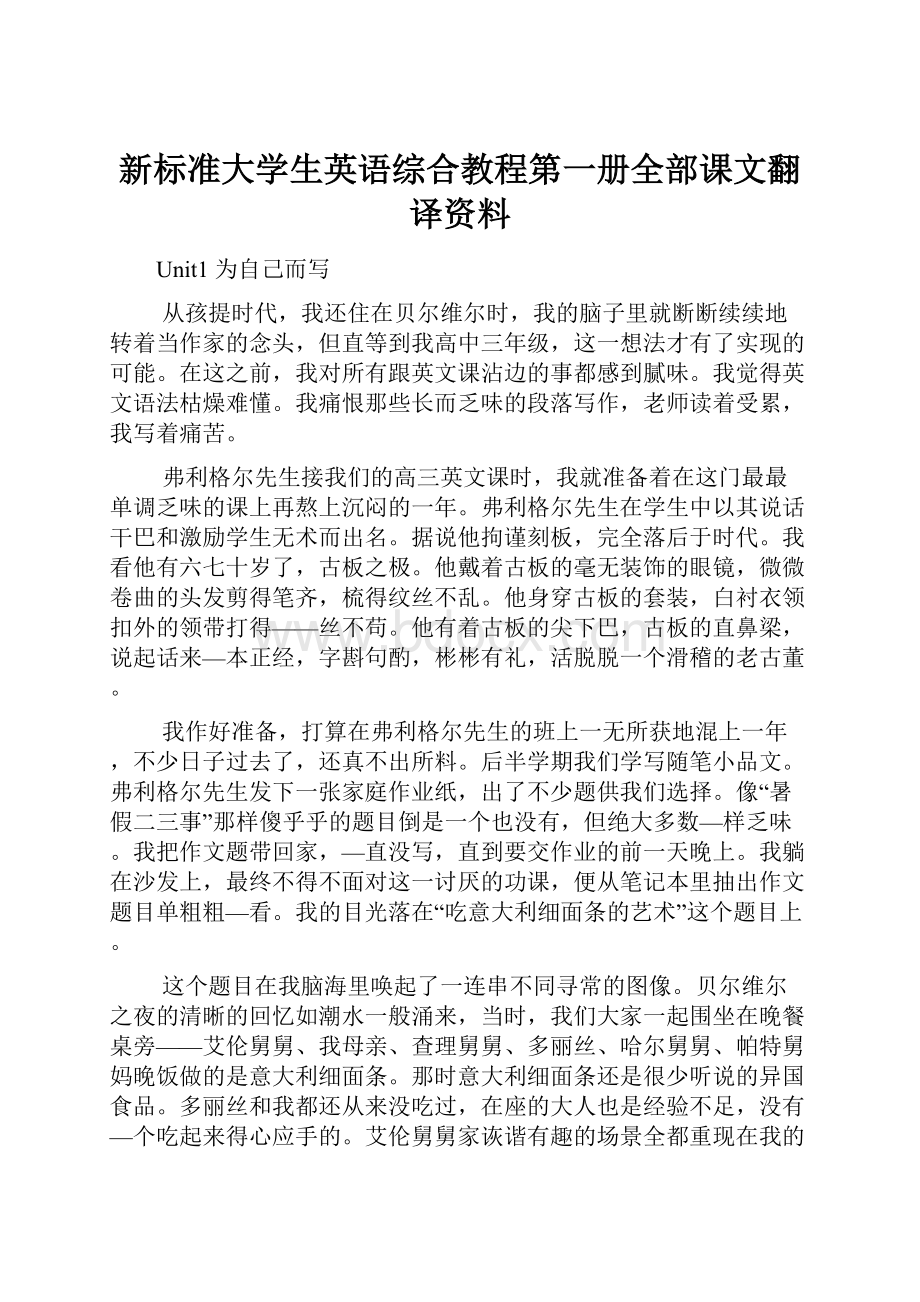
新标准大学生英语综合教程第一册全部课文翻译资料
Unit1为自己而写
从孩提时代,我还住在贝尔维尔时,我的脑子里就断断续续地转着当作家的念头,但直等到我高中三年级,这一想法才有了实现的可能。
在这之前,我对所有跟英文课沾边的事都感到腻味。
我觉得英文语法枯燥难懂。
我痛恨那些长而乏味的段落写作,老师读着受累,我写着痛苦。
弗利格尔先生接我们的高三英文课时,我就准备着在这门最最单调乏味的课上再熬上沉闷的一年。
弗利格尔先生在学生中以其说话干巴和激励学生无术而出名。
据说他拘谨刻板,完全落后于时代。
我看他有六七十岁了,古板之极。
他戴着古板的毫无装饰的眼镜,微微卷曲的头发剪得笔齐,梳得纹丝不乱。
他身穿古板的套装,白衬衣领扣外的领带打得——丝不苟。
他有着古板的尖下巴,古板的直鼻梁,说起话来—本正经,字斟句酌,彬彬有礼,活脱脱一个滑稽的老古董。
我作好准备,打算在弗利格尔先生的班上一无所获地混上一年,不少日子过去了,还真不出所料。
后半学期我们学写随笔小品文。
弗利格尔先生发下一张家庭作业纸,出了不少题供我们选择。
像“暑假二三事”那样傻乎乎的题目倒是一个也没有,但绝大多数—样乏味。
我把作文题带回家,—直没写,直到要交作业的前一天晚上。
我躺在沙发上,最终不得不面对这一讨厌的功课,便从笔记本里抽出作文题目单粗粗—看。
我的目光落在“吃意大利细面条的艺术”这个题目上。
这个题目在我脑海里唤起了一连串不同寻常的图像。
贝尔维尔之夜的清晰的回忆如潮水一般涌来,当时,我们大家一起围坐在晚餐桌旁——艾伦舅舅、我母亲、查理舅舅、多丽丝、哈尔舅舅、帕特舅妈晚饭做的是意大利细面条。
那时意大利细面条还是很少听说的异国食品。
多丽丝和我都还从来没吃过,在座的大人也是经验不足,没有—个吃起来得心应手的。
艾伦舅舅家诙谐有趣的场景全都重现在我的脑海中,我回想起来,当晚我们笑作—团,争论着该如何地把面条从盘子上送到嘴里才算合乎礼仪。
突然我就想描述那一切,描述当时那种温馨美好的气氛,但我把它写下来仅仅是想自得其乐,而不是为弗利格尔先生而写。
那是我想重新捕捉并珍藏在心中的一个时刻。
我想重温那个夜晚的愉快。
然而,照我希望的那样去写,就会违反我在学校里学的正式作文的种种法则,弗利格尔先生也肯定会打它一个不及格。
没关系。
等我为自己写好了之后,我可以再为弗利格尔先生写点什么别的东西。
等我写完时已是半夜时分,再没时间为弗利格尔先生写一篇循规蹈矩、像模像样的文章了。
第二天上午,我别无选择,只好把我为自己而写的贝尔维尔晚餐的故事交了上去。
两天后弗利格尔先生发还批改过的作文,他把别人的都发了,就是没有我的。
我正准备着遵命——放学就去弗利格尔先生那儿挨训,却看见他从桌上拿起我的作文,敲了敲桌子让大家注意听。
“好了,孩子们,”他说。
“我要给你们念一篇小品文。
文章的题目是:
吃意大利细面条的艺术。
”
于是他开始念了。
是我写的!
他给全班大声念我写的文章。
更不可思议的是,全班同学都在听着他念,而且听得很专心。
有人笑出声来,接着全班都笑了,不是轻蔑嘲弄,而是乐乎乎地开怀大笑。
就连弗利格尔先生也停顿了两三次,好抑制他那丝拘谨的微笑。
我尽力不流露出得意的心情,但是看到我写的文章竟然能使别人大笑,我真是心花怒放。
就在十一年级,可谓是最后的时刻,我找到了一个今生想做的事。
这是我整个求学生涯中最幸福的一刻。
弗利格尔先生念完后说道:
“瞧,孩子们,这就是小品文,懂了没有?
这才是——知道吗——这才是小品文的精髓,知道了没有!
祝贺你,贝克先生。
”他这番话使我沉浸在十全十美的幸福之中。
Unit2出租车司机拥有的就剩一封信
他准是完全沉浸在所读的东西里了,因为我不得不敲挡风玻璃来引起他的注意。
他总算抬头看我了。
“你出车吗?
”我问道。
他点点头,当我坐进后座时,他抱歉地说:
“对不起,我在读一封信。
”听上去他像是得了感冒什么的。
“我不着急,”我对他说。
“你接着把信读完吧。
”
他摇了摇头。
“我已经读了好几遍了。
我想我都能背出来了。
”
“家书抵万金啊,”我说。
“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因为我老是在外旅行。
”我估量他有六七十岁了,便猜测说:
“是孩子还是孙子写来的?
”
“不是家里人,”他回答说。
“不过,”他接着说,“想起来,也可以算是一家人了。
埃德老伙计是我最老的朋友了。
实际上,过去我俩总是以‘老朋友'相称的——就是说,当我俩相见时。
我这人就是不大会写东西。
”
“我看大家写信都不那么勤快,”我说。
“我自己笔头就很懒。
我看,你认识他挺久了吧?
”
“差不多认识了一辈子了。
我俩小时候就一起玩,所以我俩的友谊确实很长了。
”
“一起上的学?
”
“都一起上到高中呢。
事实上,我俩从小学到高中都在一个班里。
”
“保持这么长久友谊的人可真不多见啊,”我说。
“其实呢,”司机接着说,“近25到30年来,我跟他一年只见一两次面,因为我从原来住的老街坊搬了出来,联系自然就少了•,虽说你一直放在心上。
他在的时候可真是个大好人。
”
“你刚才说他‘在的时候'。
你是说——?
”
他点了点头。
“前两个星期过世啦。
”
“真遗憾,”我说。
“失去朋友真不是个滋味,失去个真正的老朋友更让人受不了。
”
他开着车,没有接话儿。
我们沉默了几分钟。
可我知道他还在想着老埃德。
他又开口时,与其说是跟我说话,还不如说是自言自语:
“我真该一直保持联系。
真的,”他重复道,“我真该一直保持联系。
”
“是啊,”我表示赞同,“我们都该与老朋友保持更多的联系。
不过总是有事情冒出来,好像就是抽不出空来。
”
他耸了耸肩。
“我们过去总能抽出空来,”他说。
“信里还提到呢。
”他把信递给我。
“你看看吧。
”
“谢谢你,”我说,“不过我不想读你的信。
这纯属私事。
”
司机耸一耸肩。
“老埃德人都死了。
没什么私事不私事了。
念吧,”他催促说。
信是用铅笔写的。
称呼写着“老朋友”,而开头第一句话让我想到自己。
“早就想写信了,可就是一拖再拖。
”信里接着写道,他常常回想从前两人住在一个街坊时的快乐时光。
信里提到些事,可能对司机很重要,比如“那次蒂姆•谢打破窗子,那年万圣节前夕,我们把老帕克先生的大门拴了起来,还有卡尔弗太太老是在放学后把咱俩留下训斥的那阵子”。
“你们俩准是在一起度过了不少时光,”我对他说。
“就跟信里写的那样,”他回答说,“我俩在那个时候能花的只有时间。
”他摇头叹道:
“时间啊。
”
信里接下来的那段我觉得有点凄凉:
“信的开头我写着‘老朋友',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们这对老朋友渐渐都老了。
我们这些人当中留下的也不多了。
”
“你要知道,”我对他说,“信里说我们这些人当中留下的不多了,说得一点不错。
比如说,每次我去参加老同学聚会,来的人总是越来越少。
”
“时间不饶人啊,”司机说。
“你们俩以前在一起工作吗?
”我问他。
“不,不过没成家时我俩总在一起闲荡。
后来,两人都成了家,就不时相互串门。
可最近这二三十年来,主要就是寄寄圣诞卡了。
当然,我俩都总在—卡上写几句——通常是关于各自家里的情况,不是吗,孩子们在干些什么,谁搬到哪儿,添了个小孙子,都是这类事——可一直都没正儿八经地写过信什么的。
”
“这—处写得好,”我说。
“这里写道:
‘你多年的友谊对我非常重要,远比我能说出来的重要得多,因为我不擅长说这样的话。
”'我颔首称是。
“这话准让你听着开心,是吧?
”
司机说了句什么,可我没听明白,因为他似乎哽噎得厉害。
于是我接着说:
“我也真想收到这样一封老朋友的来信。
”
我们快到目的地了,于是我跳到最后一段“因此我想你一定想知道我惦记着你。
”信末署名:
“老朋友汤姆”。
我们在我的旅店前停下,我把信递了回去。
很高兴能和你聊聊,”我将衣箱从车上提下时说。
汤姆?
信的署名是汤姆?
“我记得你朋友叫埃德,”我说。
“为什么他署名汤姆呢?
”
“这封信不是汤姆写给我的,”他解释说。
“我是汤姆。
这是我在得知他去世前写给他的信。
所以我—直没寄出。
”
他神情有点悲伤,似乎想看清远处什么东西。
“我想我真该早些写这封信。
”
我进了旅馆房间之后,没有马上打开箱包。
首先我得写封信——而且要寄出去。
Unit4托尼·特里韦索诺的美国梦
他来自意大利罗马以南某地一个满地石子的农庄。
他什么时候怎么到美国的,我不清楚。
不过,有天晚上,我看到他站在我家车库后面的车道上。
他身高五英尺七、八左右,人很瘦。
“我割你的草坪,”他说。
他那结结巴巴的英语很难听懂。
我问他叫什么名字。
“托尼·特里韦索诺,”他回答说。
“我割你的草坪。
”我对托尼讲,本人雇不起园丁。
“我割你的草坪,”他又说道,随后便走开了。
我走进屋子,心里有点不快。
没错,眼下这大萧条的日子是不好过,可我怎么能把一个上门求助的人就这么打发走呢?
等我第二天晚上下班回到家,草坪已修整过了,花园除了草,人行道也清扫过了。
我便问太太是怎么回事。
“有个人把割草机从车库里推出来就在院子里忙活起来,”她回答说。
“我还以为是你雇他来的。
”
我就把前晚的事跟她说了。
我俩都觉得奇怪,他怎么没提出要工钱。
接下来的两天挺忙,我把托尼的事给忘了。
我们在尽力重整业务,要让一部分工人回厂里来。
但在星期五,回家略微早了些,我又在汽车库后面看到了托尼。
我对他干的活夸奖了几句。
“我割你的草坪,”他说。
我设法凑了一小笔微薄的周薪,就这样托尼每天清扫院子,有什么零活,他都干了。
我太太说,但凡有重物要搬或有什么要修理的,他挺派得上用场。
夏去秋来,凉风阵阵。
“克罗先生,快下雪了,”有天晚上托尼跟我说。
“等冬天到了,你让我在厂里干扫雪的活。
”
啊,对这种执着与期盼,你又能怎样呢?
自然,托尼得到了厂里的那份活儿。
几个月过去了。
我让人事部门送上一份报告。
他们说托尼干得挺棒。
一天我在汽车库后面我们以前见面的地方看到了托尼。
“我想学徒,”他说。
我们有个挺不错的培训工人的徒工学校。
可我怀疑托尼是否有能力学会看图纸、用千分尺,是否胜任做精密加工工作。
尽管如此,可我怎么能拒绝他呢?
托尼减了薪水当了徒工。
几个月之后,我收到报告,他已从徒工学校毕业,成了熟练磨工。
他学会了在千分尺上辨识一百万分之一英寸,会用镶嵌着金刚石的工具制作砂轮。
我和太太都挺高兴,觉得他的事总算有了个令人满意的结局。
一两年过去了,我在托尼惯常等我的地方又看到了他。
我们聊起了他的工作,接着我问他有什么要求。
“克罗先生,”他说,“我想买房。
”在小镇边上,他看到有房出售,完全是座废墟。
我去见一位当银行家的朋友。
“人品贷款你干不干?
”我问。
“不干,”他说。
“我们承担不起。
没门。
”
“哎,等等,”我应道。
“有个人干活勤勉,人品端正,这一点我担保。
他有个好工作。
眼下,你从你那块地上—分钱也得不到。
那块地空在那儿要好多年呢。
至少他会付你利息嘛。
”
那位银行家勉强开了两干美金抵押贷款,没要托尼首付就把房子给了他。
托尼乐不可支。
从那以后,只要我家附近有什么被人扔弃的零星杂物,坏了的屏风啦,五金器具啦,包装纸板啦,托尼都要收起来拿回家,看他这个样子真是有意思。
约摸过了两年,我在我们见面的老地方又看到了托尼。
他身子似乎挺直了些,人也见胖了,样子挺自信。
“克罗先生,我卖房子!
”他得意地说。
“我得了八千美金。
”
我非常吃惊。
“可是,托尼,没了房子你住哪儿呢?
”
“克罗先生,我买农庄。
”
我们坐下聊了起来。
托尼告诉我说,拥有一个农庄是他的梦想。
他喜欢番茄,辣椒以及意大利菜肴中相当重要的其它各种蔬菜。
他把在意大利的妻子和儿子女儿都接来了。
他在小镇周边到处找,终于找到一处没人要的一小块地产,有一幢房,还有间小棚。
他正在把家搬到农庄去。
又过了一些时候,在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托尼来了,他穿戴得整整齐齐。
和他一起来的还有另一位意大利人。
他告诉我,他说服了儿时的伙伴前来美国。
托尼为他作经济担保。
他眼里露出顽皮的神情,对我说,他俩来到他经营的小农庄时,他的朋友惊奇地站住说,“托尼,你是个百万富翁啦!
”
后来,在战争期间,公司里传出了一个消息。
托尼去世了。
我让公司的人去他家看看,确保各项事宜都得到妥善安置。
他们看到农场上长着绿油油的蔬菜,小屋布置得舒适温馨,院子里有一辆拖拉机,还有一辆不错的汽车。
孩子受过教育,都工作了,托尼身前没有分文欠债。
托尼去世后,我一直想着他的经历。
他的形象在我心目中越来越高大。
最后,我觉得他就和美国那些最伟大的实业家一样高大、自豪。
他们都通过同样的途径,本着同样的价值观和原则获得了成功:
远见、执着、自制、乐观、自尊,以及最重要的,正直。
托尼不是从最低一级阶梯往上爬的,他是从地下室往上爬的。
托尼的事业很小,那些最大的实业家的事业很大。
但究其实两者的资产负债表完全一样。
惟一的不同是你把小数点点在什么地方。
托尼•特里韦索诺来到美国寻求美国梦。
但他没有找到什么美国梦——他为自己创造了个美国梦。
他的全部拥有是一天宝贵的二十四小时,而他—刻也没有浪费。
Unit5公司人
最终,他于星期天凌晨3点工作至死。
当然,讣告上没有这样写。
讣告上写的是死于冠状动脉血栓症,但他的好友和熟识的人都心知肚明。
他们互相握着手,摇头叹息地说他是一个追求完美的A型人,一个典型的工作狂,然后用几分钟时间来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
这位最终于星期天——他的休息日——凌晨三点整死于工作中的人是一位公司的副总裁,时年51岁。
他是公司六位副总之一,如果总裁去世或者退休的话,他也是最有望成为第一把手的三位人选之一。
菲尔清楚这一点。
他一周工作六天,其中五天工作到夜里八九点,他的公司里除了高级官员,其他人都已经开始四天工作制。
他工作起来像一个重要人物。
他没有其他的爱好。
当然,如果你认为每月打一次高尔夫球也算的话,对菲尔而言,高尔夫也是工作。
他总是在他的桌前吃着吃鸡蛋沙拉三明治,难免有点发福,超重了20-25磅。
他想这没什么关系,因为他从不抽烟。
星期六,菲尔换下西服,穿着运动衫去上班,因为这是周末。
他手下有大约60个人,大部分人多半时间都喜欢他。
其中三位紧盯着他的职位。
讣告上没有提及这些。
但是讣告颇为准确地列出了他的“遗属”。
他的妻子,海伦,一个48岁的好女人,没有什么适合市场需求的技能,结婚生子之前在一家办公室工作。
据她女儿说,很多年前,当孩子们还很小的时候,她就放弃了和丈夫的工作竞争了。
一个公司朋友说,“我知道你将会多么思念他”,她回答到,“我早就在思念他了。
”
“这么多年来一直思念着他。
”她一定是牺牲了自己的一部分,来尽力照顾这个男人。
以后她会得到“很好的照顾”。
他的“深爱的”孩子们中“深爱的”长子是南方某制造公司努力工作的经理。
在葬礼前的一天半里,他走访邻居询问邻居们,向他们打听自己的父亲是怎样一个人。
他们感到很尴尬。
他的第二个孩子是女儿,24岁了,刚刚结婚。
住在娘家附近,与母亲很亲密,但是每次跟父亲在一起,比如一起开车到什么地方去,彼此竟无话可说。
最小的孩子20岁,高中毕业生,像很多他的朋友一样,在过去几年里打了不少零工,挣的钱足够自己吃饱肚子吸大麻。
他是这个家里努力想抓住他的父亲,努力想让自己在父亲心目中显得重要,好让他留在家里的人。
他是他父亲最喜欢的儿子。
这两年来,菲尔常常彻夜不眠,为这个孩子担心。
他曾说过,“父亲和我只是在这里寄宿。
”
在葬礼上,60岁的总裁安慰48岁的遗孀说,这位51岁的死者对公司的贡献巨大,没有人可以替代他的位置。
这位遗孀没有直视他眼睛。
她害怕他会看出她的怨恨,毕竟,她需要他帮忙解决一些财政问题,比如优先认股权什么的。
菲尔超重、焦虑、工作强度太大。
如果他不在公司,就会担心公司的工作。
菲尔是一个A型行为者,先天易发心脏病。
在人群中,你可以一眼就把他认出来。
所以当他最终因工作死于星期天凌晨三点整,没人感到意外。
葬礼过后的下午5点,公司总裁已经开始询问接替菲尔的事,当然他做得很谨慎,小心而得体,四处打听:
三人中,“谁一向工作最卖力?
”
Unit6爱情故事
约翰·布兰查德从长凳上站起身来,整了整军装,留意着格兰德中央车站进出的人群。
他在寻找一位姑娘,一位佩带玫瑰的姑娘。
他知其心,但不知其貌。
十二个月前,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图书馆,他对她产生了兴趣。
他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很快便被吸引住了,不是被书的内容,而是被铅笔写的眉批。
柔和的笔迹显示出其人多思善虑的心灵和富有洞察力的头脑。
在书的前页,他找到了前一位拥有人的姓名,霍利斯·梅奈尔小姐。
他花了一番工夫和努力,找到了她的地址。
她住在纽约市。
他给她写了一封信介绍自己,并请她回复。
第二天他被运往海外,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接下来的一年当中,两人通过信件来往增进了了解。
每一封信都如—颗种子撒入肥沃的心灵之土。
浪漫的爱情之花就要绽开。
布兰查德提出要一张照片,可她拒绝了。
她解释道:
如果你对我的感情是真实的,是诚心诚意的,那我的相貌如何并不重要。
设想我美丽动人——我将会一直深感不安,惟恐你只是因为我的容貌就贸然与我相爱,而这种爱情令我憎恶。
设想本人相貌平平(你得承认,这种可能性更大)——那我一直会担心,你和我保持通信仅仅是出于孤独寂寞,无人交谈。
不,别索要照片。
等你到了纽约,你会见到我,到时你可再作定夺。
且记,见面后我俩都可以自由决定中止关系或继续交往——无论你怎么选择……”
他从欧洲回国的日子终于到了。
他们安排了两人的第一次见面——晚上七点,纽约格兰德中央车站。
“你会认出我的,”她写道,“我会在衣襟上戴一朵红玫瑰。
”于是,晚上七点,他候在车站,寻找一位过去一年里在自己生活中占据了如此特殊地位的姑娘,一位素未谋面,但其文字伴随着他、始终支撑着他精神的姑娘。
且让布兰查德先生告诉你接下来发生的事吧:
一位年轻的姑娘向我走来,她身材颀长纤细。
一头卷曲的金发披在秀美的耳后;眼睛碧蓝,如花似玉。
她的双唇和下颌线条柔和,却又柔中见刚,她身穿浅绿色套装,犹如春天一般生气盎然。
我朝她走去,完全忘了去看她有没有戴玫瑰花。
我走过去时,她双唇绽开撩人的微笑。
“和我同路吗,水兵?
”她小声问道。
我情不自禁,再向她走近一步。
可就在这时,我看到了霍利斯·梅奈尔。
她差不多就站在姑娘的正后面,早已年过四十,灰白的头发用卡子向上别着,头上带着一顶旧帽子。
她体态臃肿,粗圆的脚髁上套着一双低跟鞋。
穿着绿色套装的姑娘快步走开了。
我觉得自己好像被分成了两半,一方面热切地想去追赶她,但另一方面我又渴望那一位以其心灵真诚陪伴我并成为我的精神支柱的女人。
她站在那儿,苍白的圆脸显得温柔理智,灰色的眼睛透出热情善良。
我没有迟疑。
我手里紧握着那本小小的让她辨认我的蓝色羊皮面旧书。
这不会是爱情,但将是某种珍贵的、或许比爱情更美妙的东西,一种我曾经感激,并将永远感激的友情。
我挺胸站立,敬了个礼,并举起手中的书让那位女士看。
不过在我开口说话的时候,失望的痛苦几乎使我哽咽。
“我是约翰·布兰查德中尉,想必您就是梅奈尔小姐。
很高兴您来见我。
可否请您赏光吃饭?
”
妇女的脸上绽开了笑容。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孩子,”她回答说,“可是刚才走过去的那位穿绿色套装的姑娘,她央求我把这支玫瑰插在衣服上。
她还说,要是你请我吃饭的话;我就告诉你,她就在街对面那个大饭店里等你。
她说这是一种考验!
”
梅奈尔小姐的智慧不难理解,也令人称奇。
心灵的本质是从其对不美的事物的态度中反映出来的。
“告诉我你所爱者是谁,”何赛写道,“我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
Unit7动物到底想些什么
多年来,我写了大量关于动物智能实验、以及围绕这些实验所产生的争议的文章。
动物真的有思想,即我们所说的意识吗?
人们往往通过教动物人类手势语的实验来探索动物智能,我常考虑是否会有比这更好的方式,并悟出了现在看来是显而易见的一点:
如果动物能思维,它们的最佳思维发生在能为自己所用的时候,而不是在科学家让它们思考的时候。
于是我开始与兽医、动物研究人员以及动物园饲养员交谈。
他们大都不研究动物智能,但他们每天都碰到过动物智能与动物智能的欠缺。
他们讲述的故事开启了我相信是研究动物智能的一扇新的窗口:
即动物在对付樊笼生活和地球上的主宰物种——人类——时所表现的高超的思维技能。
让我们做笔交易
请考虑这一情况:
哥伦布动物园的一位动物保护主义者查伦·延德里觉察到一头叫做科洛的雌性大猩猩在玩弄一件可疑的物品。
延德里走过去,给了科洛一些花生,却被翻了个白眼。
意识到它是在讨价还价,延德里加大了筹码,又给了一片菠萝。
这时候,科洛一边望着延德里,一边摊开手,露出了一根钥匙链。
见不是危险或珍贵物品,延德里松了一口气,把菠萝给了考勒。
科洛真是个精明的还价者,它把钥匙链拉断,给了延德里一小段,或许在算计着,要是每一小段都能换片菠萝,我干嘛要给她全部?
如果动物能在以物换物中显示技能,又何尝不会在使用钱币中再露一手?
在田纳西大学人类学家琳·迈尔斯进行的一项手势语研究中,有头名叫夏特克的猩猩就这么做了。
夏特克悟出,如果它干些诸如清理房间的事,他就能挣些硬币,用来买好吃的,还可以坐迈尔斯的车外出兜风。
但这头猩猩对钱币的理解似乎远远超出了简单的交易。
迈尔斯一开始用塑料片充当硬币,而夏特克竟认定,它可以把塑料片拗成两片,以此扩大钱币供应量。
而当迈尔斯改用金属片时,夏特克找到了一些锡箔,试图复制。
迈尔斯还试图教会夏特克一些好习惯,诸如节俭和与人分享。
当我在它目前居住的亚特兰大动物园见到这头猩猩时,我果然见到它与人分享的一例,足以令任何人羡慕。
迈尔斯给了夏特克一些葡萄,要求它与人分享,它很快吃完了所有的葡萄。
随后,它似乎是想起了迈尔斯要它与人分享,便把梗儿递给了迈尔斯。
鲸鱼的故事
动物为什么会愿意与人合作?
行为主义者会说,动物认识到合作于已有利时就会这么做。
这没有错,但我觉得这一解释尚不充分。
动物行为顾问盖尔·劳尔说起过她了解的一头虎鲸奥基。
“在我照管过的动物当中,它是最聪明的,”她说。
“它会审时度势,再根据自己的判断采取行动。
”
比如有次它救了一个家族成员。
奥基的配偶科基生幼鲸时,那条幼鲸一开始情况不妙,饲养员把幼鲸用担架抬出水糟,实施紧急护理。
他们把幼鲸送回水槽时,出了事情。
当工人把担架停在高出水面几英尺处的时候,幼鲸开始呕吐。
饲养员担心它会窒息,但他们无法接近幼鲸提供帮助。
奥基显然看出了问题,它游到担架下,让其中一人站在它头上。
這是它从未被训练做过的事。
然后,奥基用尾部保持平衡,让饲养员接近,并松开了那条420磅重的幼鲸,以便让它获得帮助,滑入水中。
灵长目动物的骗术
有时动物的智能可以从欺骗的企图中得以证明。
西雅图伍德兰公园动物园饲养员海伦·休曼回忆道,一天她从喂食窗口给猩猩梅拉蒂扔了个桔子。
梅拉蒂没有移动身体去接,而是眼睛直视休曼,伸出手来。
休曼以为桔子准是滚到一边拿不到了,就又给了它一个。
可当梅拉蒂走开时,休曼却注意到原来那只桔子就藏在它另—只手里。
猩猩园的头领托温目睹了这个把戏。
第二天,这头雄猩猩也是眼睛盯着休曼,装作没有接到桔子。
“你肯定没拿到吗?
”休曼问道。
它仍直视着她,同时把手伸了出来。
她让步了,又给了它一个,随后却看见它把桔子藏在脚下。
智能究竟是什么?
如果生命关乎物种的生存——而智能是为生存服务——那么我们根本无法与大脑只有豌豆大的海龟相提并论,海龟早在人类出现很久之前便已存在,并经历了使恐龙灭绝的重大灾难而生存下来。
尽管如此,想到除了我们人类,尚有其它物种,即便它们的视野比我们还狭小,却也能退后一步,清醒地审视周围的世界,不由人深感宽慰。
Unit8关于懒散少年的语言故事(不考)
本杰明.斯坦
去年一个秋日,我文件夹用完了,便去杂货店买。
我拿了一大把文件夹搁在柜台上,问一个十几岁的售货员多少钱。
“不知道,”她回答说。
“反正单价12美分。
”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