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奇安《论撰史》.docx
《卢奇安《论撰史》.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卢奇安《论撰史》.docx(1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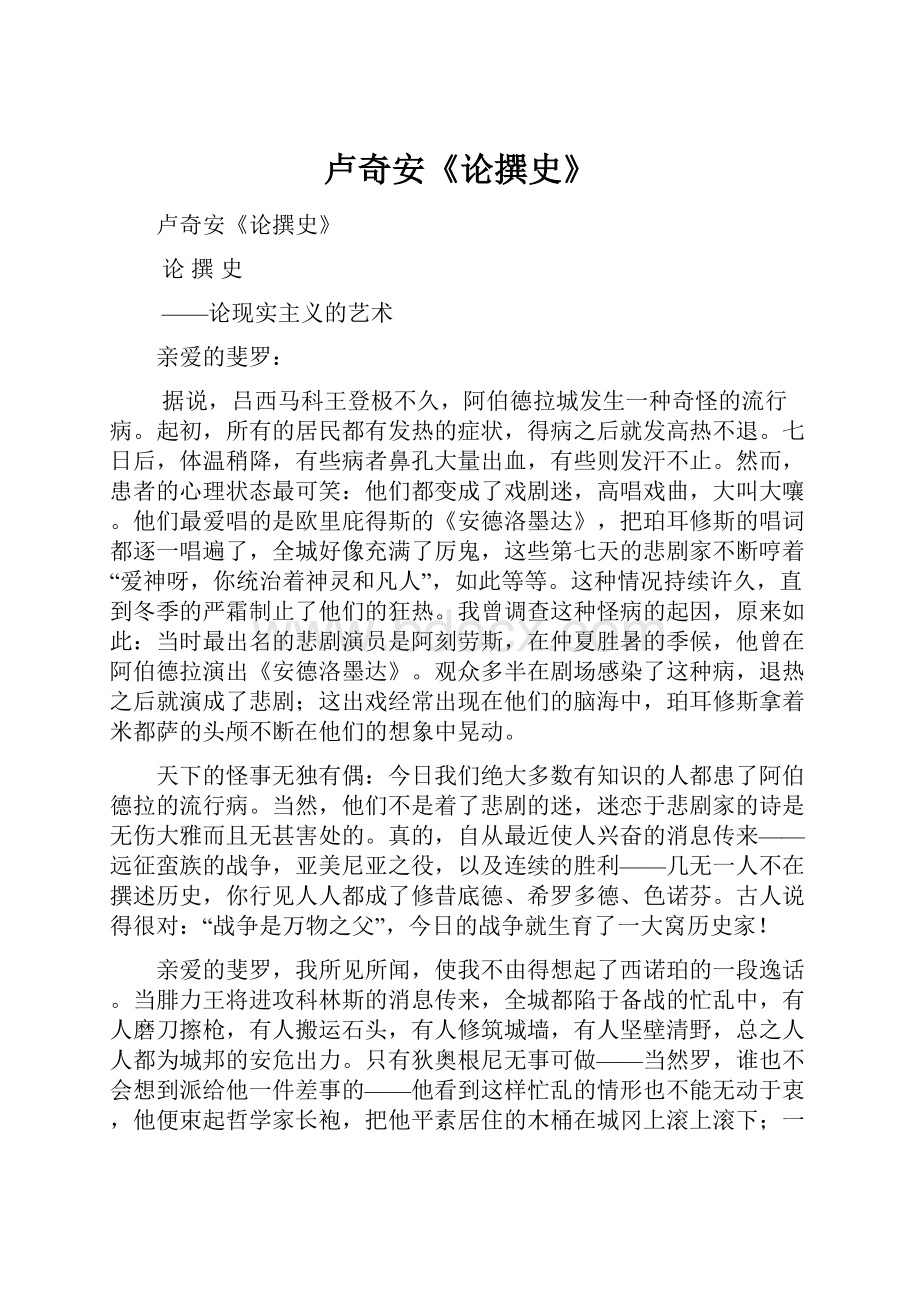
卢奇安《论撰史》
卢奇安《论撰史》
论撰史
——论现实主义的艺术
亲爱的斐罗:
据说,吕西马科王登极不久,阿伯德拉城发生一种奇怪的流行病。
起初,所有的居民都有发热的症状,得病之后就发高热不退。
七日后,体温稍降,有些病者鼻孔大量出血,有些则发汗不止。
然而,患者的心理状态最可笑:
他们都变成了戏剧迷,高唱戏曲,大叫大嚷。
他们最爱唱的是欧里庇得斯的《安德洛墨达》,把珀耳修斯的唱词都逐一唱遍了,全城好像充满了厉鬼,这些第七天的悲剧家不断哼着“爱神呀,你统治着神灵和凡人”,如此等等。
这种情况持续许久,直到冬季的严霜制止了他们的狂热。
我曾调查这种怪病的起因,原来如此:
当时最出名的悲剧演员是阿刻劳斯,在仲夏胜暑的季候,他曾在阿伯德拉演出《安德洛墨达》。
观众多半在剧场感染了这种病,退热之后就演成了悲剧;这出戏经常出现在他们的脑海中,珀耳修斯拿着米都萨的头颅不断在他们的想象中晃动。
天下的怪事无独有偶:
今日我们绝大多数有知识的人都患了阿伯德拉的流行病。
当然,他们不是着了悲剧的迷,迷恋于悲剧家的诗是无伤大雅而且无甚害处的。
真的,自从最近使人兴奋的消息传来——远征蛮族的战争,亚美尼亚之役,以及连续的胜利——几无一人不在撰述历史,你行见人人都成了修昔底德、希罗多德、色诺芬。
古人说得很对:
“战争是万物之父”,今日的战争就生育了一大窝历史家!
亲爱的斐罗,我所见所闻,使我不由得想起了西诺珀的一段逸话。
当腓力王将进攻科林斯的消息传来,全城都陷于备战的忙乱中,有人磨刀擦枪,有人搬运石头,有人修筑城墙,有人坚壁清野,总之人人都为城邦的安危出力。
只有狄奥根尼无事可做——当然罗,谁也不会想到派给他一件差事的——他看到这样忙乱的情形也不能无动于衷,他便束起哲学家长袍,把他平素居住的木桶在城冈上滚上滚下;一个朋友问他干甚么,他答道“人人都在忙碌,我不想别人说我是一条懒虫,所以我也要忙着滚木桶。
”
在这样热闹的时节,我也不甘寂莫。
我不想像一个“临时演员”在舞台上跑龙套,不说一句话,所以我也决心尽管滚我的木桶。
然而,我并不打算撰述历史或者创作小说,我没有这样的勇气,我倒有自知之明。
我知道任何东西在乱石中滚动都是危险的,尤其是像我那样不堪一击的破瓦瓮,万一猛撞在尖石上,我难免要粉身碎骨。
好吧,我告诉你我的想法:
我要“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避开战地,在安全地方安营下寨,那才是上策;但是我也要作出奇谋,定下战略,以便那些勇士们去冲锋陷阵。
这也就是说:
大厦落成了,我也出过一份力量,虽然我不策名于记功碑上,至少我的手指也曾沾染过污泥。
然而,也许大多数历史家不需要我的意见,他们认为:
“谈话有艺术,烹饪也有艺术,但是作史是最容易不过的事情,历史才能是一种普遍的品赋,你只需要有能力把所想到的写成文字,就可以了。
”然而,老友,你是聪明人,你知道事实上这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不,正像任何一种创作一样,撰史也要苦心经营,如果一个历史家想自己的作品能够像修昔底德所说的“永垂不朽”!
当然,我明明知道,许多历史家不会听取我的话,有些甚至会勃然大怒,他们已经完成大作,发表后还受到欢迎,他们的作品已成定稿,甚或已成国史的文献,难道还要他们改弦易辙吗?
虽然如此,我的话对于他们也不无益处。
今日我们大概不会再有外患了,我们已经击败了所有敌人,但是说不定将来会发生居尔特和哥特的战争,印度和巴克特里亚的战争,那时候历史家也许用得着我的新尺,当然我假定他们认为这把尺子准确,不然的话,就让他们用旧尺测量吧;如果讳病忌医,即使全阿伯德拉都吟诵《安德洛墨达》,医生也满不在乎!
我的意见有两方面:
一为选择,一为避免。
首先,让我们决定历史家应该避免甚么,必须清除甚么缺点,然后进而讨论他们应该采取甚么正路走上康庄大道。
后一点包括序文的做法,素材分配的程序,恰当的比例,慎重的保留,叙述的详简,史实的批判,文气的连贯等等问题。
然而,关于这些问题,容后再说。
现在,我们先讨论拙劣史家最容易犯的毛病。
至于各种文体所共有的毛病,例如措词、结构、字义以及一般浅薄的毛病,由于篇幅所限和不合目的,我姑且不谈。
然而,有一些错误是历史作品所特有的:
我经常参加作者的朗诵会就有此印象,你自己也会体会到的,只要你常常留心倾听,我随便从最近的历史著作中举几个实例吧。
首先,一种流行的严重错误是:
对史实不加以调查研究,而把大半篇幅用来歌颂帝皇将相,对我方的则极口赞扬,对敌方的则恣意贬抑。
他们忘记了历史与颂词之间有不可沟通的洪谷;用音乐术语来说,这两者是不同音阶的。
歌颂者的唯一任务是颂扬和取悦他的对象,只要能够达到目的,即使言过其实,也在所不计。
反之,历史则唯恐混淆是非歪曲真相:
历史有如气管,据医生说,气管不能容忍一点点食物落进去的。
其次,今日的历史家似乎不理解:
诗歌与历史不但各有其特质,而且各有其规律。
诗享有无限的自由权,诗只须遵守一条法律——诗人的想象。
诗人凭灵感创作,随诗与之所之。
假如诗人高兴驾着飞马的神车,驰骋于海洋或垄亩之上,谁也不能干预他的权利;他的宙斯可以用一条绳索把大地和海洋吊起,飘摇于空际,你也不用担心绳索会断,海陆会掉下来碎成微尘。
荷马歌颂阿伽门农的形象,说他双眼和头颅像宙斯的,胸膛像海神的,腰带像战神的,也没有人去反对他;其实,阿伽门农被写成为诸神的缩影,不论宙斯、海神或战神也不能单独构成他的十全十美。
然而,假如历史采取了这种雕虫小技,它就不过是无翼的诗罢了;历史将丧失崇高的格调,立刻露出无韵的伪装之真相了。
不能区别诗与史,确实是史家之大患:
以诗歌的奇谈、谀颂、夸饰给历史涂脂抹粉,可不是俗不可耐吗?
强使一个铜筋铁骨的壮士衣锦戴翠,粉颊朱唇,噫,何其污辱英雄如此!
但是,你不要以为我把歌颂完全排斥在历史之外;历史是可以歌颂的,但是歌颂要安于本分,要用得恰当,不要使读者讨厌。
我在下文将要讲到:
史家在歌颂的时候务必着眼于后世的读者。
真的,今日就有一派人把历史分为欣赏的历史和实用的历史两大类,认为历史可以采用歌颂的方法,因为这既可以欣赏,又使读者感到愉快。
然而,这种论调是最荒谬不过的了。
首先,这种分类就大错特错:
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真实。
历史中可欣赏的成分无疑是外加的东西,不是历史的本质,这正如美貌之于壮士;但是尼科斯特拉托年青力壮,无可匹敌,尽管相貌丑陋,也被誉为有赫拉克勒斯之勇,假使他的敌手是美貌绝伦的阿尔凯斯(据传说,阿尔凯斯之美足以使尼科斯特拉托爱上了他),他也不会败于这个美少年之手。
历史也是如此:
如果历史偶或加以修饰以供欣赏,它固然可以吸引一群爱者;但是历史必须努力尽它的本分——那就是写出真实——至于美不美,那是无关宏旨的。
还须指出:
历史如果是夸夸其谈,就连欣赏的价值也没有了,如果是歌功颂德的浮夸,就加倍地使人反感,因为它既是浮夸又是阿谀。
至少这种历史只能受庸俗的读者欢迎,而为有批判力的读者所不取,更不能逃过吹毛求疵的批评家的非难;这些批评家的眼睛像阿耳戈斯一样有一百双,而且比他的还要锐利,他们会称过你的每个字,像兑换银钱者称金币,当场挑出你的伪币,只接受够成分够重量的真金。
我们编撰历史,就要时刻把他们放在心上,而不必计较一般读者的品评,即使他们赞不绝口。
如果你忽视那些批评家,而沉湎于奇谈的美味和歌颂的诱饵,你的历史著作就将变成“赫拉克勒斯在吕底亚”了。
你大概看过这样一幅画吧?
它描写赫拉克勒斯做了奥姆法梨的奴仆,装扮得不伦不类,他的狮子皮和大铁棒交给了女主人,好像她才是真正的大力士似的,而他却穿起红袍紫褂,梳理着羊毛,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这真是羞人的丑态呵——宽袍大袖,坦胸露臂,堂堂大丈夫变成了女流!
俗人也许会喜欢这种历史,但是有识者(如果你不重视他们的判断力)就会从你的不伦不类支离破碎的劣品中取得无穷的笑料了。
凡物皆有其独特的美,但是取一物之美而用于另一范围,美也就化为丑。
更不用说,歌功颂德只能取悦于一人——被歌颂者——但徒然令他人作呕;而以时下流行的吹牛拍马的作品为尤甚,作者既然一心一意在取宠献媚,就不免要露出奴颜婢膝,他们又恬不知耻,绝不掩饰其媚态,但是虚造的谎言总会露出破绽。
结果,恐怕他们连眼前的目的也达不到;他们所称颂的对象,如果是刚直的人,定必厌恶他们的奉承,把他们抛弃,这是理所当然的。
昔日亚理斯托布鲁在他的历史著作中,插入一段描写亚历山大和波鲁斯决战的故事,他故意选出这一节给亚历山大朗诵,满以为最好的献媚机会是捏造大帝的英雄事迹,以此抬高大帝的丰功伟业。
当时,他们泛舟在海达泗披河上,亚历山大听了就把这部著作抛到水中,他说:
“此书作者理应受到同样的待遇,他竟敢捏造我的决斗,说我单人匹马射死几只大象。
”亚历山大的愤怒是合情合理的,正像他对待谄媚的建筑家那样,这建筑家提议把阿陀斯山凿成大帝的巨像,可是亚历山大认为他是媚臣,以后对他更不敢信任了。
事实上,阿谀之词绝无使人愉快之处,除非受者是一个蠢才,他才欣赏那些毫无根据不攻自破的夸赞。
当然,世间有一些丑人,尤其是丑妇人,她们要求画家尽可能把她们画得更美些,以为只要画家多施铅华,不惜丹青,她们就真的变成天姿国色了。
今日历史家之众多,其原因就在于此。
此等历史家鼠目寸光,只看到自己眼前的利益,企图以作品牟利;他们应该被人唾弃的,今人咒骂他们的露骨的无耻的谄媚,后人将咒骂他们的浮夸给史学带来污点。
如果历史家认为加上一些修饰是绝对必要的话,他应该只求风格本身之美;只有这种美是华而实,可惜今日的史家往往忽略了这种真实的美,却舍本求末,鱼目混珠,贩卖无中生有的浮词。
讲到这点,我想引证一些关于最近这次战争的记忆犹新的伊奥尼亚作品,呵,我想起了,还有近来发表的希腊作品。
你可以相信我的记载,皇天在上,我可以发誓那是千真万确的,如果纸上发誓无伤大雅!
一位作者一开始就请求诗神助他一臂之力。
多么风雅的序言呵!
多么恰当的历史精神呵!
多么合适的风格呵!
序言之后,他便把我们的皇帝比作阿喀琉斯,把帕提亚王比作忒西提斯;他倒忘记了,阿喀琉斯追杀忒耳西忒斯,胜之不武,假如对手是赫克托耳而不是忒耳西忒斯,假如一个伟大英雄在前面逃跑,“一个更伟大的英雄在后面追赶”,这才会更显出阿喀琉斯之骁勇!
临末,他歌颂他的故乡米利都,还说他比荷马更进一步,荷马就从未提及自己的故乡。
在序言的结尾,他信誓旦旦,表示他愿为祖国捐躯,请缨杀敌。
讲到历史的事实和战争的起因,他是这样开始的:
“可恶的伏罗格苏斯,这混账家伙,竟借口开战。
”
另一个摹仿修昔底德的作者,为了肖似他的典范,首先标榜自己的大名。
你看,古色古香的阿提刻风味:
“潘沛依古城克瑞珀琉斯·卡尔佩尼安纳氏著帕提亚罗马战争史,缕述战事之始末”!
序言如此,其余更不用说了。
他迂阔无边地先从亚美尼亚讲起,追溯科赛拉使节的事迹;他给尼细比斯降下大瘟疫(因为它不赞助罗马的要求),原封不动地从修昔底德的历史照样搬过来,只除了昔日希腊人避疫的地点和长城没有照抄,但是正像修昔底德所写的一样,“这次瘟疫起于爱西屋皮亚,蔓延到埃及”,以后便传入帕提亚王国,到此它就慎重地停止了。
他写道:
“在尼细比斯埋葬可怜的雅典人时,我就离开了,但是我深深知道,我走后它会怎样继续下去的。
”真的,今日有一种较为普遍的信仰:
认为只要你照抄他的原话,应改动的稍为改动,你的作品就是修昔底德笔法!
呵,我几乎忘记了指出一点:
这位作家讲到武器和军械时用了许多拉丁字,phossa指战壕,pons指桥梁,如此等等。
你试想多么庄严的史籍,试想多么和谐的修昔底德笔法呀——阿提刻风格衬上拉丁文字,正像罗马长袍系上希腊绶带!
又有一个作者把历史大事罗列成一笔流水账,枯燥乏味,平淡的像私人的、木匠或小贩的日记。
然而,这可怜虫的做法倒似乎有些道理:
他一开始就打着鲜明旗帜,拓开了荒地给更有史学才能的人去播种。
我对他唯一的指摘是:
每卷的冠冕堂皇的题词同贫乏可怜的内容不大相称:
“帕提亚史,枪兵第六排军医卡利谟夫斯著,卷几等等”。
是的,序言未免呜呼,末段说神医阿斯克勒甫斯是阿波罗之子,阿波罗是文艺女神的指挥和掌管文化的恩神,所以一个军医应当编写历史。
再则,他起首是用伊奥尼亚古文的,而稍后不知为甚么改用希腊口语,但仍然保留伊奥尼亚的拼字法,文笔像一般人的作品,未免太平凡了。
或许我应该把他同一个哲人历史家对照一下:
这位先生我姑讳其名,而仅仅指出他的态度,如他最近在科林斯发表的著作所表现的。
我对他的希望很大,可是毕竟令我失望了。
他从序言的第一句开始就强迫读者接受一种辩证法教条,他的原理具有高度的哲理,主张只有哲学家能撰写历史;这之后就是接二连三的层层逻辑推理,其实全篇序言是一大堆辩证法术语。
序言中谄媚的话真是“令人作呕”,庸俗的歌颂竟然达到滑天下之大稽,可是它并不缺少理论的装饰,而且往往是辩证法的教条。
他在序文中居然说,哲学家甘心记载帝皇的丰功伟绩,这是我们君主所特有的洪福;我想,这种庸俗的阿谀真是一个白发长须的哲人之耻:
如果他要献媚,他倒不如让读者自己作出结论呵!
若果我不提一提此人,那是不可饶恕的疏忽——这个史家是这样开篇的:
“予欲记载罗马与波斯之事迹”,接着就说“波斯人之受难,乃天意也,”又说“昔有奥斯洛斯者,希腊人称之为奥克斯洛斯”;他的风格多半是这样。
由此可见,他同上述的一个例子颇有相似之处,不过他是希罗多德第二,而后者却是修昔底德第二罢了。
此外,还有一位语言大师比修昔底德还有更多的修昔底德笔法:
在他自己看来,他把城市、山岳、原野、河流描写得最清楚最动人。
要是我希望我的死对头遭到再坏不过的命运,我一定希望他读一读这位大师的著作!
文笔冷淡无味吗?
恐怕里海的雪和北国的冰比它还要暖些。
整部书都描写不完皇帝的盾:
盾心刻着郭尔干的头颅,蓝的白的黑的眼睛闪闪有光,盾带是一条彩虹,盾边是盘曲蜿蜒的长蛇。
至于伏罗格苏斯的马裤和马缰,我的天呀,每一件东西的描写就占了几千行;他又浪费同样笔墨来描写奥斯洛斯泅渡底格里斯河时他的头发怎么样,他藏身的岩洞怎么样,常春藤、雁来红、月桂树密茂丛生,不见阳光。
你知道的,仿佛这些描写是历史著作必不可少的,没有写景,我们怎能了解历史的事件呢?
由于不能掌握真正的要点,或者由于不知道历史应该写的甚么,他们就不得不乞灵于绘声绘色的写景,风光景物,岩洞花草等等。
然而,当他们接触到一系列重要事件的时候,他们就好像一个家奴从主人继承了一笔财产,变成了富翁,可是他不懂得衣罗穿锦或者杀鸡烹兔,却匆匆忙忙跑入酒家,饱餐咸鱼豆羹,塞得肚皮快要胀破。
我所说的那位大师还写出最无稽最荒唐的死伤:
有一个人大脚趾受了伤便当场死去;普里斯卡斯将军大喝一声,二十七个敌人就应声倒毙。
至于死伤的数字,他就索性伪造虚报:
在欧罗巴斯一役敌方死者七万零二百三十六人,罗马死者二人,伤者仅七人!
一个稍有常识的人怎能容忍此种废话呢?
我真百思莫解。
还有一点值得大书特书的。
这位作家热爱纯粹的阿提刻语,要把语言净化到纤尘不染,所以他一概把拉丁名字改为希腊名字:
Saturninus改为Cronius,Fronto改为Phrontis,Titianus改为Titanius,光怪陆离,不胜枚举。
再则,讲到塞弗里安之死,他责备其他作家把他写成刎颈自杀是大错特错,他认为绝食饿死才是最不痛苦的方法;但是,事实上一个人饿死要七天,塞弗里安却饿了三天便死了;也许我们可以猜中作者的用意,奥斯洛斯怎能等待塞弗里安自杀的过程,等到七天之后才开始进攻呢?
那么,斐罗,这些沉湎诗句舞文弄墨的作家,我们应该把他们归入哪一类呢?
他们写道:
“弩石发兮山崩地裂”,“怒涛吼兮殷殷雷鸣”。
这种古色古香的历史著作写道:
“古城爱德萨,两军战城下,杀声干天魂,喧嚣动地魄”;或者说:
“将军苦筹划,铁城攻不下”。
然而,诗句之中却夹杂着贫乏可怜的平凡句子:
“司令官上本给皇帝陛下”,“于是军队获得了应用的东西”,“他们洗了个大澡,就穿得漂漂亮亮”,如此这般。
这就活像一个演员一只脚穿悲剧的高底靴,另一只脚穿喜剧的破拖鞋了。
你也会见到:
有些作家先写一篇辉煌响亮的序言,长得荒谬绝伦,留给你巨大的希望,你满以为下文将有惊人的宏篇出现了。
然而,下文只是短得可怜的附录——所谓“历史”。
那就活像一个小娃娃,譬如说,小爱神,戴着赫拉克勒斯或者提坦巨人的假面具,你大概看过这幅画吧?
当然罗,读者不禁要叫道:
“巨雷落细雨,大山生小鼠”。
这样的写法是不行的。
一部作品的结构必须安排得当,身首相称,轻重分明,决不能像头戴金盔,却身穿破皮烂布的胸甲,手执柳枝编成的盾牌,脚缠腐烂猪皮的护胫,那就太不像话了。
可是,不少作家却往往把罗德岛巨像的头放在侏儒的身上,或者相反,给你一个断头尸体,没头没脑叙述一大堆事件。
他们自称效法色诺芬的先例,色诺芬一开头就写道:
“大流士和巴里萨提斯有二子”,殊不知史家笔法有所谓“以事代序”,那不是人人可以做到的,但是关于这点以后再说吧。
然而,仅仅是表现方式或结构方面的欠妥还可以原谅,可是有些作家却凭想象乱写地理,地点的差误不是若干里而是若干日的路程,试问这有甚么古典的先例可依呢?
有一个作家完全不顾事实,我想,他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叙利亚人,甚或没有听过一些道听途说的情报,便这样描写欧罗巴斯:
“欧罗巴斯位于米索不达米亚,离幼发拉底河有两日路程,是以得萨的殖民地”。
然而,这位野心勃勃的作者还不知厌足,他在这部作品中竟然把我的故乡萨摩萨塔连同它的碉堡和城墙全部移到米索不达米亚去,又说它有两条河流为界,横贯全境,贴近城墙两旁。
我想,你定必笑我了,斐罗,如果我要再三对你声明我既不是帕提亚人也不是米索不达米亚人,可是这位胡思乱想的地理家却硬说我是。
顺便说,他讲及塞弗里安的故事是十分动人的,他发誓证明,那是从一个亲历其境的逃生者听来的。
据说,塞弗里安之死不是自刎,不是上吊,也不是服毒,他的自杀既悲壮又动人:
他有几个最名贵的玻璃酒杯,既已决心一死,便打破一个最大酒杯,用玻璃碎片割断喉咙,撒手尘世。
匕首或短戈虽然是英雄豪杰就义的最好工具,但是他当然不愿意死得这样平凡!
再则,因为修昔底德曾为古时波希战争的国殇创作过葬礼演讲,我们这位作家就觉得他也有义务为塞弗里安创作一篇;你看,今日的史家都想同修昔底德较量一下,虽则塞弗里安对于亚美尼亚的战祸不应负其咎。
所以,这位作家就在塞弗里安的葬礼上隆重地引进一个百人队长,名叫亚法拉尼乌斯·西罗,正如伯里克理斯那样,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说了一番不同凡响的话,这番话使得我不禁落泪,我的天,我笑得落泪呀,尤其是当这个能言之士亚法拉尼乌斯末了举杯奠酒的时候,他一边呜咽,一边呻吟,缕述着山珍海错的祭献。
然而,他在结束之时却扮演埃阿斯的角色!
他拔出剑来,真不愧为英雄亚法拉尼乌斯,当众在坟头自刎——天晓得,如果葬礼演讲可以做绝命之词,那真是自杀的最好时机呵!
这位历史家又讲到旁观的人们如何赞叹亚法拉尼乌斯的忠烈;至于我,我却大有理由要责备他,因为他这篇演讲不过是一张嘉肴美酒的菜单,他是为冷菜残羹流泪罢了,然而我想他的最大罪状是他没有先割断这个悲剧历史家的喉咙然后自杀!
我的朋友,我告诉你,我大可以扩大这些胡涂历史家的名单,但是再举一两个例子就够了,因为我还要履行我的任务的第二部分,提出改良的建议。
有些历史家完全不讲一切不可遗忘的重大事件,即使提及,也是草草了事。
他们是门外汉,不是艺术家,当然没有选材的能力,所以依依不舍,煞费苦心,连篇累牍来描写最琐屑无聊的事情;正如一个人游览奥林比亚大庙,却不去观赏宙斯像的壮丽之美,而只赏识石座的光滑和对称和石鞋的尺寸,只注意到那些微不足道的地方,便向他在家的朋友讲述并且推荐一番那样。
例如,我曾见过一个历史家用了不够七行的文字就写完了欧罗巴斯的战争,却费去二十小时冗长的篇幅来叙述一个沉闷的毫不相干的故事。
他讲到一个名叫毛萨卡斯的摩尔骑兵迷失了道路,走到山上寻水喝,遇到两个叙利亚庄稼汉在用午餐;初时他们很怕他,但是他们看出他没有恶意,便邀他一起吃饭,因为其中一个老乡曾经到过摩尔的乡下,他有一个兄弟在军中服役。
于是,这个老乡便喋喋不休地讲故事,说他怎样在摩尔打猎,见过一群大象出来觅食,说他险些儿给一只狮子吃掉,又讲到他在凯沙里亚买了一条鱼多么的大。
这样,这个怪癖的历史家就不管欧罗巴斯伏尸十万,流血漂橹,也不管罗马人追亡逐北,争城夺地,迫敌投降了,他却津津有味地叙述叙利亚人马尔奇安称赞那条大鱼价廉味美,一直拖延到日落西山的时候,要不是夜色降临得太快,我敢说他一定还要等到煮熟了大鱼和他一起饱吃一顿呢。
仿佛如果历史不把那些废话全都记录下来,我们对于历史就会无知得可怜!
仿佛如果这个摩尔骑兵找不到东西解渴,饿着肚皮回到军营,罗马人的损失就会无可挽救!
然而,我还是故意删去了无数更重要的细节呢:
例如,他讲及从邻村来了一个姑娘为他们吹笛,又讲及他们交换礼物,毛萨卡斯赠送长矛,马尔奇安报以胸针。
我说,此等作家从来不看蔷薇一眼,而只好奇地欣赏枝头芒刺,这决不是故甚其词!
还有一个有趣的作家:
他从未踏出科林斯境外一步,最远不外是到过科林斯港,当然谈不上见过叙利亚或亚美尼亚了,可是他一开首就写下我至今还记得的名言:
“目睹方为可信,所以我的记载尽是我目睹的,而不是我耳闻的”。
你看,他的观察多么细致,他就这样描写帕提亚的“龙”(我相信,帕提亚人用龙作为军旗的旗徽,代表一定的人数,一千人组成一个龙旗队):
他说,这些龙是活生生的猛兽,生长在意卑里亚对岸的波斯领土;帕提亚人先把龙绑在大木柱上,高高挂起,使得入境的军队一见就大惊失色;战争一开始,他们便把龙释放以进攻敌人;我方许多战士都被龙吞食或者被卷起压死。
他说,他亲眼看见这一切,因为他当时就躲在树顶安全地方来观察。
我的天!
幸亏他没有同龙交锋,要不然,我们将失掉一个优秀的历史家了,何况这位历史家曾亲手立过英勇的大功,因为他有过许多次冒险,在苏拉还受过伤呢(我想,他是从科林斯城冈顶到冈下散步的途中摔伤了吧)。
他曾把这篇宏文向科林斯听众朗诵过,听众定必猜到他连一幅战事画也没有见过的,因为他分不出各种武器,对于战略和军队的名词毫无概念:
他把前锋和侧翼,纵队和横队就混为一谈。
又有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居然把亚美尼亚、米索不达米亚、底格里斯、米太等地的几次战争自始至终的经过压缩在五百行的范围之内(严格地说,还不够五百行),完成了任务,便称之为历史。
然而,他的题目却差不多像这部著作这么长:
“罗马人最近在亚美尼亚、米索不达米亚、米太各地远征大战记事:
阿波罗神诞节比赛胜利者安提奥奇亚纳斯著”。
我想,他一定在长途赛跑中获得冠军。
我也见过一个作家写一部未来的历史:
他讲到罗马人攻陷伏罗格苏斯首都,把奥斯洛斯处死(把他抛给狮子吃掉),这样他就替我们取得了迟迟未实现的胜利。
他用这种未卜先知的口吻匆匆写完这部著作,可是他还有时间来讲述罗马人在米索不达米亚建立一个城市,这是巨大城市中之最大者,美丽城市中之最美者,不过他还未能决定这城市应该叫甚么名字:
“胜利城”,“协和城”,还是“和平城”。
所以,在目前我们只好让它无名吧,可是这城市已经是人口稠密,楼阁林立了——当然是“乌有居民”和“空中楼阁”!
这位作家又曾许诺下要写印度的未来大事和环游大西洋的航程。
真的,他的诺言已经实现了一半:
“印度大事记”的首篇已经写完,他讲到罗马第三军团、居尔特军分遣队、摩尔军一师,在加西阿斯率领下,已经浩浩荡荡渡过印度河了;不久这位最有独创能力的历史家将从迢迢千里的东方古国来书告诉我们罗马大军的丰功伟绩,例如,他们如何“迎击大象”。
这些不学无术的作家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他们对显著的事情是没有眼睛的,即使有眼睛,也没有表现的才能;捏造事实就是他们的作品内容,道听途说就是他们的风格;他们以连篇累帙的著作自豪,尤其是以冠冕堂皇的书名自诩,这些书名也是荒谬绝伦的,例如“某某著帕提亚大战胜利志,帕提亚志卷一,帕提亚志卷二,帕提亚志卷三……”,这大概是效法古代史籍“阿提刻志”吧?
另一部作品(我曾读过此书)的书名更简洁:
“某某著帕提亚史记”。
我不是想嘲笑那些寂寂无闻的历史著作,我的目的在于提供实用的参考而已。
凡是能避免类似这些错误的史家,去成功之道不远矣,不,他已经成功了;因为,按照逻辑的公理,在矛盾的两方,否定其一就是肯定其余。
或许你会对我说:
“好了,现在你已经有了空旷的地盘:
藤萝荆棘已经斩除,断瓦颓垣已经搬去,崎岖地面已经铲平,那么,请你自己来建设,表示你不但能破而且能立,做出一个无可非议的榜样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