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语文教学论文 水流云在风过无痕沈从文小说诗学观.docx
《高中语文教学论文 水流云在风过无痕沈从文小说诗学观.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高中语文教学论文 水流云在风过无痕沈从文小说诗学观.docx(1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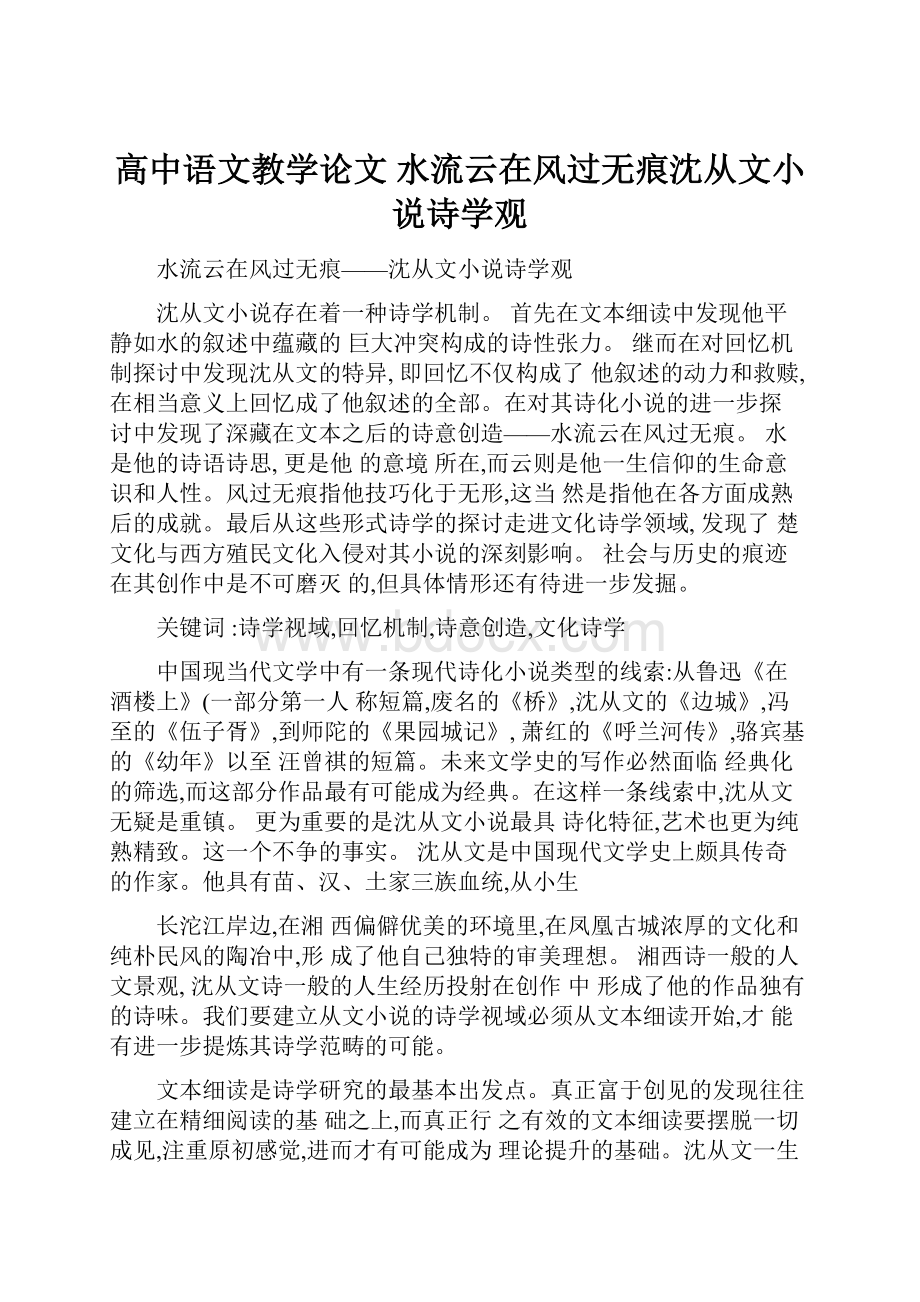
高中语文教学论文水流云在风过无痕沈从文小说诗学观
水流云在风过无痕——沈从文小说诗学观
沈从文小说存在着一种诗学机制。
首先在文本细读中发现他平静如水的叙述中蕴藏的巨大冲突构成的诗性张力。
继而在对回忆机制探讨中发现沈从文的特异,即回忆不仅构成了他叙述的动力和救赎,在相当意义上回忆成了他叙述的全部。
在对其诗化小说的进一步探讨中发现了深藏在文本之后的诗意创造——水流云在风过无痕。
水是他的诗语诗思,更是他的意境所在,而云则是他一生信仰的生命意识和人性。
风过无痕指他技巧化于无形,这当然是指他在各方面成熟后的成就。
最后从这些形式诗学的探讨走进文化诗学领域,发现了楚文化与西方殖民文化入侵对其小说的深刻影响。
社会与历史的痕迹在其创作中是不可磨灭的,但具体情形还有待进一步发掘。
关键词:
诗学视域,回忆机制,诗意创造,文化诗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有一条现代诗化小说类型的线索:
从鲁迅《在酒楼上》(一部分第一人称短篇,废名的《桥》,沈从文的《边城》,冯至的《伍子胥》,到师陀的《果园城记》,萧红的《呼兰河传》,骆宾基的《幼年》以至汪曾祺的短篇。
未来文学史的写作必然面临经典化的筛选,而这部分作品最有可能成为经典。
在这样一条线索中,沈从文无疑是重镇。
更为重要的是沈从文小说最具诗化特征,艺术也更为纯熟精致。
这一个不争的事实。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颇具传奇的作家。
他具有苗、汉、土家三族血统,从小生
长沱江岸边,在湘西偏僻优美的环境里,在凤凰古城浓厚的文化和纯朴民风的陶冶中,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审美理想。
湘西诗一般的人文景观,沈从文诗一般的人生经历投射在创作中形成了他的作品独有的诗味。
我们要建立从文小说的诗学视域必须从文本细读开始,才能有进一步提炼其诗学范畴的可能。
文本细读是诗学研究的最基本出发点。
真正富于创见的发现往往建立在精细阅读的基础之上,而真正行之有效的文本细读要摆脱一切成见,注重原初感觉,进而才有可能成为理论提升的基础。
沈从文一生笔耕不辍著作颇丰,《边城》、《萧萧》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纵观沈从文小说研究,这两部作品也是最受人们关注的因而对其细读也更具挑战性。
一、细读《边城》与《萧萧》
1933年创作的中篇小说《边城》无疑在沈从文的艺术生涯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以往提到《边城》总是囿于田园牧歌风情,认为翠翠作为作家心目中完美的女性形象代表沈从文的审美理想,即纯朴健康没有污染的永恒人性。
全篇21节,每一节都充满了诗意、洋溢着牧歌气息,是“一部田园牧歌式的杰作”,是“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
①当我们抛弃所谓的经典解读,真正细读文本从最初的感觉生发出自我想象,从文本清理中进行理论提升就会发掘沈从文小说真正具有诗性张力的潜质。
《边城》的诗情画意是历来被学术界所公认的。
这诗情画意不只来自于美丽的湘西绿水青山和醇厚的民风民俗,更主要来自于作家的爱与情感以及叙事的态度。
《边城》的整个故事是围绕翠翠的爱情纠葛展开的。
这爱情受着别人的关心,也受着误解,得到的却只是忧郁而略带凄凉的悲剧。
而正是这关心与误解形成一种诗性张力:
老船夫,摆渡撑船忠于职守五十年。
端阳龙舟令人神往,但他出于责任不离渡船。
老人的热诚负责让过渡人感动,许多人会抓把钱掷在船板上,老人照例不收,但有时盛情难却留下作了过渡人的茶水钱。
如此善良的老船夫心灵深处有种隐忧。
这便是翠翠,他唯一的亲人。
翠翠父母在小说中是缺席的,但我们却可以察觉他们的存在。
祖父对翠翠的娇惯,一方面是所有亲情的叠加,另一方面我们是否可以看作祖父对女儿犯下的错误在孙女身上的补偿?
边城里的人几乎个个都是豪爽的,唯独作为边城老叟的祖父有些局促,譬如他去打听二老订婚的事,支支吾吾费尽周折,受到船总冷遇回来后就大病一场。
可以想象,女儿的悲剧多少会与他有关。
总之,老人时刻牵挂翠翠的将来,在安静恬淡的生活布景之后祖父的心中升起某种说不出的忧郁——他害怕女儿的悲剧会在翠翠色身上重演,而自己又充当伤害她的祸首。
祖父把对女儿的爱加倍地转移到翠翠身上,他知道翠翠总有一天会走。
翠翠走了,留下老人更加孤单,又或许老人先走向另外的世界,留下孤雏他更加难以瞑目。
祖父留意着翠翠的心,可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怎么会明白一个少女的心。
他所关注的并不是爱情,而是把翠翠交给一个可靠的人。
如此一来,祖父对翠翠的婚姻,毋宁说是关心,更是谨慎行事。
不幸的是,老人自以为了解翠翠就如同当初以为了解女儿,她要翠翠为自己作主,内心却看好大老天保。
戏剧化的是翠翠真正爱上的却是二老傩送。
祖父为此弄出了一系列的误解误会,客观上增加了翠翠爱情的曲折,也最终重演了这场悲剧。
翠翠是《边城》中最能感动人的形象,在祖父呵护下翠翠一出现便是一个美丽自然的山野少女: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
„„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
”她既有少女的羞怯又有大自然的生气是青春的化身。
《边城》写少女思春是独到的诗化的。
翠翠年龄渐长,心理生理情绪开始滋长一种说不出的东西:
“无意中提到什么是,会红脸了。
时间在成长她,似乎真催促她,使她在另外一件事情上负点儿责。
她欢喜看扑粉满脸的新嫁娘,欢喜述说关于新娘的故事,欢喜把野花戴到头上去,还欢喜听任唱歌。
茶峒人的歌声,缠绵处她已领略得出。
”翠翠天真未凿情窦初开,在无忧无虑不知人间烦恼为何物的年纪,邂逅二老傩送竟然“沉默了一个晚上”。
当翠翠爱上二老,最了解自己的爷爷也爱莫能助了。
她烦恼忧愁却不忘在爷爷面前撒娇,当知道二老惦记自己,却用矜持让二老看成是冷落。
一切的关心与误会在交织,只有到了老船夫遽然离世,翠翠才明白了部分真相当然不会是全部。
原先不明白的全明白了,翠翠哭了一夜。
傩送因为哥哥的死和父亲的逼迫远走,心里还带着些许
的哀愁,在心里始终分不清翠翠是不是爱自己。
而翠翠却在痛苦中撑起渡船等待着那个把自己的生命都带走的傩送。
尽管“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
正是在这种诗性的张力中,我们领略到沈从文的诗学魅力。
犹如穆旦的诗歌,在冲突分裂与绝望中发现美的极致。
这种诗学张力,不独在《边城》中,在沈从文的大部分小说,甚至散文中都可以看到。
过去我们一直把沈从文放在对古典主义和原始生活的纬度上,是很有见地的,但我们相当程度大大地的忽视了他在小说诗学以及叙事技巧上的特异。
最令人惊喜的是沈从文的小说中无论是诗学的还是叙事的技巧甚至各种形式的尝试都围绕着一个中心展开即他一生都为之经营的“人性”。
在他著名的《〈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写道:
“我只想造希腊小庙。
选山地作地基,用坚硬的石头堆砌它。
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弱,是我理想的建筑。
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
②在理论上,沈从文一直主张,文学只有表现人性,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人心与人心的沟通与连接,原始以来文学的。
人性的种种纠纷,于人生向上的憧憬,原可依赖文学来诠释启发的,“一个伟大的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
——对于当前社会黑暗的否认,以及未来光明的向往。
”③《边城》在这样一种诗性张力中全然没有穆旦式的残缺的自我与分裂,甚至连翠翠祖父在内的所有善良人的悲剧都带有一种美尽管凄凉,留在我们心上的却只是淡淡的哀伤。
这就是沈从文最独特的创造,即节制的诗学原则,宽容的叙述态度,以及对人事的脉脉温情。
正如他在《<边城>题记》中写道“对于农人与兵士。
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随处可以看出。
我从不隐讳这点感情。
”④
在《萧萧》中,这种诗性张力与温爱更能表达纯真与自然的力量。
在旧中国贫困地区“童养媳”风俗是源远流长的。
小说里的萧萧是个孤儿,十二岁嫁到农家时,丈夫三岁,还在吃奶。
依地方规矩,“过了门,她喊他弟弟。
她每天应作的事是抱弟弟到村前柳树下玩,饿了,喂东西吃,哭了,就哄他。
”到十四岁时,萧萧已然发育的相当成熟,帮工花狗靠山歌和花言巧语骗了她。
几个月后萧萧肚皮渐大,花狗逃了,将一个残酷的命运交给了她。
萧萧到庙里许愿,吃大把香灰,又常常到溪里喝冷水,都没有用。
腹中的孩子一天天长大,她选择逃跑却被发现关进柴房。
于是婆婆家的祖父就请了萧萧的伯父来,商量着依老规矩沉潭或变卖。
伯父不忍让萧萧沉潭,只好让她住在丈夫家中,直到主顾看人再走。
等到十二月还没来人。
萧萧次年二月间,坐草生了一个儿子,圆头大眼,声音宏壮。
生下的既是儿子萧萧不必另嫁别处,儿子十二岁娶亲,她又在唢呐声中迎接另一个“萧萧”的来临。
“蒙昧”之于萧萧绝不是某种缺憾,正如小鹿般浑然无知的状态对于翠翠丝毫不减她的美丽一样。
《三三》中的三三,《边城》中的翠翠,《萧萧》中的萧萧都是纯洁无邪,事事对人信任,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完全可以组成一个人物谱系。
纯真与自然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常是人性的主要方面。
惟其纯真让人怜悯,惟其自然让人可亲。
她们无不具有金子般的心肠,小鹿般的温顺,她们健康自然却又无一例外的成为悲剧。
一种悲剧被另外一种悲剧所掩盖,这正是沈从文“言不尽意”的诗学观的体现。
他永远都不会把话说尽,实际上也不可能说尽。
就如同海明威的“冰山理论”,我们所能看到的甚至连八分之一也未必有。
沈从文在其习作中探索出了中国现代小说诗化的路子,当然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功劳都记在沈老的名下。
但客观上讲,诗化小说无疑是在沈从文的努力下成为一种别具一格的文体。
二、回忆机制下的诗学关照
在诗化小说这一类型中,回忆的诗学机制往往是最常用的,诗化小说之所以感人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回忆。
我们知道人的感情常常是无从把握无从捉摸的,可是无论任何人在回忆往事时总会萦绕着一种温馨或伤感在。
而回忆中的悲伤与爱就常常是诗化小说惯用的材料。
鲁迅的某些第一人称的小说《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等,回忆构成了小说叙事的出发点,回忆同时也构成了小说叙事得以进行的动力。
《在酒楼上》这部小说中,对于从记忆中获得心理慰藉和归宿的吕纬甫来说,回忆是现实中的吕纬甫的自我救赎的方式,回忆的姿态从根本上说标志了现实中吕纬甫的缺失,因为对往昔记忆的追寻总是与弥补现实的缺失联系在一起的。
如果说“回忆”在《在酒楼上》中更多带有动机性和象征性的功能的话,那么,回忆在《呼兰河传》、《幼年》等小说中则是结构情节的方式,即小说是叙事者“我”的回忆的产物,叙事者是通过回忆来结构整部小说的,回忆因此成为小说主导的叙事方式。
这一切,使我们对回忆的探讨有可能上升到普泛的诗学层面,提升出关于“回忆的诗学”的范畴。
事实上,在沈从文绝大部分的小说中也都有一种回忆的机制,回忆与怀旧的姿态在某些篇章中甚至不仅是情绪和氛围,很大程度上成为小说叙述的全部。
这主要与其对回忆或过去的温爱有关。
“若能温习过去,变硬了的心也会柔软的!
到处地方都有个秋风吹上人心的时候,有个不太亮的时候,有个想从‘过去’伸手,若有所攀援,希望因此得到一点助力,似乎方能够生活得下去时候。
我或那些偶然,难道不需要向过去伸手„„”⑤从《水云》的这段话很能表达他对过去的温爱和对回忆的钟情。
于是到了沈从文的笔下,回忆往往只是带来温馨或悲凉的情绪记忆。
在他关于故乡人事的回忆中,故事如水一般静静的流淌。
他不会在现实与回忆中穿梭也不会故意卖弄技巧,一切是那么自然。
回忆成了他全部情绪的触发点,一旦与回忆接轨,剩下的事情往往就不是他所能左右的了。
譬如《夫妇》乡下来的年轻夫妇在野地里亲热被人们抓起来,在近乎一场闹剧中结局竟如此波澜不惊。
然而看过后并不觉得平淡,反而有种真实的美感。
《新与旧》中刽子手在蒙昧中杀掉两个共产党员,像以往一样提着人头到庙里“受审”却被当作疯子看待。
最后刽子手死了,可湘西愚昧的旧俗还在;忏悔的机会没了,人心早已不再朴素。
至于《柏子》、《丈夫》、《七个野人和最后一个迎春节》、《黔小景》、《贵生》莫不是在回忆中完成一种宿命。
然而,回忆在沈从文这里不是动机或是结构而是全部包括情节。
在阅读了沈从文大部分作品后,才发现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有一种回忆的调子,即使是像《龙朱》、《月下小景》之类的取自传说的也有一种温馨或感伤的回忆姿态。
回忆在沈从文的小说里,又更多成为叙述的情感或姿态。
当然,回忆的模式的归纳并不意味着“回忆”已完全缝合了小说的全部叙述,相反,看看小说中的哪些部分或那些小说无法被纳入“回忆”框架,是更有意味的诗学问题。
譬如《灯》,在这部小说中回忆只是叙述者获得女性好感和注意的手段,而且回忆的内容有多少是杜撰连叙述者也不知道。
《灯》从某种意义上消解了沈从文对回忆机制的严肃信仰。
这种“反回忆”的形式即由小说中的人物讲故事又反过来说明故事的虚构性。
到底故事是不是虚构留下一个永远难以解开的谜。
这种叙事技巧竟然与八十年代先锋派有着惊人的相似。
这不在笔者论述之内,存疑。
在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中,几乎所有人都有孩子一般的心,单纯善良淳朴。
翠翠的无知,萧萧的蒙昧,老马兵的古道热肠,顺顺的仗义,三三的单纯,傩送的使气,祖父的尽忠职守总是伴随着一点青春的懵懂。
湘西世界是美丽的,不仅因为山水的秀美,更在于这些人身上有着人类童年的原始情绪。
不过不能简单地归纳为儿童视角。
毕竟在叙述中并没有一个儿童形象在,更遑论儿童视角了。
然而不可否认,沈从文叙事视角的独异性。
在全知叙事中又有限制叙事,而且一切处理得更像一场梦,就如同翠翠连续几夜做的梦,摘虎耳草。
这种朦胧多义性几乎存在于他的大部分小说中。
尽管沈老多次表示反感别人把他的小说作为寓言,但还是可以体会到某种象征的幽微。
三、水流云在与风过无痕:
沈从文小说的诗意创造
“我还有另外一种幻想,即从个人工作上证实个人希望所能达到的传奇。
我准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粘附的诗。
情感上积压下来的东西,家庭生活并不能完全中和它,销蚀它。
我需要一点传奇,一种出于不巧的痛苦经验,一份从我‘过去’负责所必然发生的悲剧。
换言之,即爱情生活并不能调整我的生命,还要用一种温柔的笔调来写各式各样的爱情,写那种和我目前生活完全相反,然而与我过去情感又十分相近的牧歌。
”⑥从沈老的这段话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小说散文创作从一开始就是创造一点纯粹的诗。
而事实上,沈老从1924年开始到解放前被迫封笔,近三十年的耕耘中形成了自己的诗学创造,即水流云在与风过无痕。
这不是随意的总结,我们可以从出入诗思、诗语、意境等等体悟出。
沈从文在文章中提到“我的生活同一条辰河无从离开„„从汤汤流水上,我明白了多少人事,学会了多少知识,见过多少世界!
我的想象是在这条河水上扩大的。
我把过去生活加以温习,或对未来生活有何安排时,必依赖这一条河水。
这条河水有多少次差一点儿把我攫去,又幸亏他在流动,帮助我作着那种横海扬帆的远梦,方使我能够依然好好的在人世中活着。
”⑦很明显,水的流动与灵性给了沈从文莫大的启示。
沈从文的诗思就是水样的。
老子曾云上善若水,水没有固定的形状故能容于一切空间也能容纳一切。
这就像沈老的为人,总是和为贵极少与人纠纷。
他的性格表现在创作上就如同梦魂牵绕的辰河汤汤流过没有刻意的雕琢一切自然流畅。
在他的诗思中没有一刻凝滞,因为对所写的一切太熟了那就如同自己的一部分了。
思维的流动异常活跃但有一点东西他的一生中绝没有忘记,后来到解放之后他的文学信仰与执着已经不合时代,于是他宁可封笔也不写逢迎之作。
这点东西就是“人性”。
“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我的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
„„若处置题材表现人物一切都无问题,那么,这种世界虽消灭了,自然还能够生存在我那故事中。
这种世界即或根本没有,也无碍于故事的真实。
„„我本来就只求效果,不问名义;效果得到,我的事就完了。
”⑧水流云在,水样的诗思流过,永恒的人性关怀不变。
沈老总是称自己的小说是习作,其实并不是出于谦虚或者为自己的某些不成熟辩白。
他的许多作品是在教授写作时作为范本的,当然不会是标准,他只是用自己的尝试告诉学生写作原是可以不拘一格的。
正是由于沈老尝试各种文体实验被称为“文体家”。
无庸置疑沈从文小说的技巧常常是高超的,
而实验的先锋姿态也是可以与鲁迅媲美的。
然而,读他的小说除非刻意地提炼否则很难发现其技巧在。
此谓风过无痕。
最值得关注的还是沈从文小说的语言,即诗语。
如水一般清新明丽,水一般舒缓自如。
沈从文的语言是经过历史淘洗的湘西土语、古文精华、楚巫文化与现代生活奇妙的融合。
在“五蛮溪”的水土上尽管有残暴和污秽,但到了沈从文的语言中都成了美。
美不因风光而静止,生命也不会因风光而凝滞。
所以,无论是是风光还是人事在沈从文的语言中都是流动的,就像水。
沈从文的语言没有悲愤更没有过火的词句,迥异于同时代左翼作家的诟骂恫吓。
无论是兴奋还是悲哀都是淡淡的轻轻的叙述。
仿佛久经沧桑的老者在讲历史传说。
一切在潺潺的流水中逝去,然而有一种氛围是不变的,那就是沈从文的悲悯。
对于人事的哀乐,对于世事的变迁,如果沉潜到他语言的内核总会发现,那平静的语言下面是一颗多么火热的心。
在《<长河>题记》中,他为故乡变化中的堕落而痛心,“农村社会所保留的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
在引文中“几几乎”三个字显示了痛心,尽管节制仍是表露无余。
这绝非技巧,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他的语言是有技巧的。
否则,单是一些简单词句的罗列就可以,那太不足取了。
他的技巧是什么?
粉条缕析地排列出却未必是事实。
若非要找出一条的话,当是真诚,对人事的虔诚,对人性的信仰或许也有楚巫文化的因子在里面。
然而最大的技巧莫过于无技巧,正如古人“不射之射”。
此谓风过无痕。
沈从文小说最令人折服的还是意境的美,这当然是就其描写“湘西世界”的作品而言。
湘西辰沅风景已足以让人留恋,而湘西人事的纯真更是让人迷恋。
在湘西世界里一切都浸在水里。
这是一方世外桃源,尽管有死亡也有不幸但比起中国其他的地方,这里的生活是自然的。
一切不幸和苦难也是自然的决不是政治染指的罪恶。
意象是构成意境的元素。
在沈从文的小说中,以意象的独特性是众所周知的。
譬如《夫妇》中一圈野花,《柏子》中唱歌的毛腿,《静》中小尼姑院里的桃花,《萧萧》中的花狗和毛虫,《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中石洞里的蓝色野菊花。
《夫妇》中女人头上那圈野菊花就像D.H.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中,保罗和克拉拉第一次热恋时的石竹花,撒在他们调情的地上表现了一种生命的力量。
小说中的村民代表了一种宗法的准则封建伦理的自然反射。
璜则代表了一种道德心。
尽管夫妇受尽村民的折磨侮辱,但他们并没有反抗。
最后女人走时还捏着那支恶作剧的花。
最后结局出人意料,璜说到:
“慢点走,慢点走,把你们那一把花丢在地下,给了我。
”作为生命力量象征的花,正是摆脱城市的璜所渴求的。
如果说《夫妇》中的野花还只某种幽微的象征,在《静》中小尼姑院里的桃花则成了一种反讽。
在流亡的死亡世界中桃花无疑是自然
的象征,自然的美更加昭示了现实的罪恶。
女孩岳珉不知所谓的笑要面对的却是父亲坟上的纸旗。
这挽歌式小说,留给我们内心的沉重远远超过文字的唯美。
不过,在沈老的小说中最有代表性的还是《边城》。
虎耳草葱绿之于翠翠青涩的爱情,白塔的坍塌之于祖父的死去,渡船之于清苦,磨坊之于富贵总有某种生命的联系。
在种种意象组成的意境就是湘西独特的生活景象,纯真和谐美丽。
在这样一个世界里,连妓女也永远浑厚。
他们的生活是凝固在艺术中的,所以边城的生命就如同水一样流过,而边城里素朴的人性永恒。
水流而云在,一切合乎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
从这意义上边城成了沈老人性的希腊小庙,虽小然而结实。
沈从文小说的意境美,是在回忆中自然叙述,毫无雕琢的痕迹。
然而真的没有吗?
未必。
此谓风过无痕。
水流云在风过无痕,这种诗学品质无疑是沈老最为独特的创造。
这与沈老严谨的创作态度以及湘西水的侵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当然我们也需意识到这种诗学品质是他步入成熟以后的创造。
阅读他的早期作品,就会发现他的早期的语言还是文言化色彩浓厚而且语法语态语气语感都处于探索期,这种成熟化的诗学还不存在。
然而,在诗思、诗语、意境等方面,沈从文从一开始创作就初步显示了他的独特,正如鲁迅先生的创作一开始便是成熟的一样。
不过,鲁迅的创作是中年写作,一开始的便成熟是合乎逻辑的。
而沈从文一落笔便显示了他的年少老成,这自然与他在湘西书吏从戎的生涯相关。
惟其老成,我们可以发现这种诗意创造是一个逐渐累积的过程,而水样的情思只不过客观上缝合了他所有的记忆。
沈从文在经历了早期的探索之后,他的笔锋终于落到梦回牵绕的湘西。
于是远在北方的沈从文只能用回忆的姿态和温爱关照故土,而回忆几乎也成了他作品中全部的情感和思绪的触发点。
正式回忆机制的发现使得沈老的诗意创造不再是猜测,而有了切切实实的技术支撑。
然而,纵观沈从文的小说创作,我们又有理由相信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之所以具有诗性,除了文本探索的勇气之外还会有其文化与社会历史等外部动力。
自然而然地,我们目光落在了文化诗学的视域中。
从形式诗学的分析探讨走进文化诗学的理论提升,是当今文学研究的常规。
然而,笔者不仅仅旨在重复这样一条路向。
在我看来,从形式诗学走进文化诗也是沈从文小说乃至散文创作的努力方向。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他的抒情品质之一。
而沈从文小说这种抒情品质是长时期被人们忽略的,即使现在还存在着对沈从文小说的误读。
我们应该认真清理一下以往的研究思路,开拓出新的研究境界。
四、从形式诗学走向文化诗学:
沈从文小说的抒情品质
沈从文的小说大都有一种动人的抒情品质,沈从文小说的诗意冲动和审美想象促使了诗化小说中的抒情性得以生成。
但除此以外还有没有文本之外的文化动力?
在探讨这些问题时必然要走出形式诗学走向更为广阔的文化诗学领域。
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社会产品在文化系统中由作者、文本、读者的相互交织的话语组成。
为了揭示文本的意义,必然要考察三种要素:
作者的生活;文本中发现的社会规则;文本呈现的对文本产生的历史形势的反映。
薛毅先生指出,诗化小说可能从根本上涉及了一个后发国家的文学抒情性问题。
相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国是一个后发展的民族国家,它的文学也因此带有后发国家普遍具有的双重的文化和美学特征:
一方面是现代性的焦虑,其中交织着对现代性的既追求又疑虑的困惑;另一方面则是在现代性的强大冲击下,面临本土的传统美感日渐丧失所带来的怅惘体验和挽歌情怀。
诗化小说总体上的美感和诗意正生成于这种挽歌式的意绪。
在挽歌中蕴涵着天然的抒情性和诗意品质。
这种形式和情感内容在沈从文的小说中是常见的。
在诗化小说家那里,“太初”与“最初的幸福”正是本土的固有经验,是为乡土之根立传的冲动。
诗化小说的文化动力便来自于小说家对本土经验的眷恋和回归的渴望,这在《在酒楼上》、《呼兰河传》、《桥》、《边城》、《果园城记》、《幼年》等小说中都有突出的体现。
而沈从文则以其自我宣称的人性的希腊小庙为他具有少数民族孤独感的地缘政治意义上偏僻的乡土“边城”立传,其中隐含了百年孤独式的主题。
在这些小说家的乡土情结中,沈从文无疑是最独特的。
这不仅来自于其苗汉土的三族血缘认同,更来自他对湘西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