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俄罗斯国家政治制度的演变.docx
《论近代俄罗斯国家政治制度的演变.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论近代俄罗斯国家政治制度的演变.docx(14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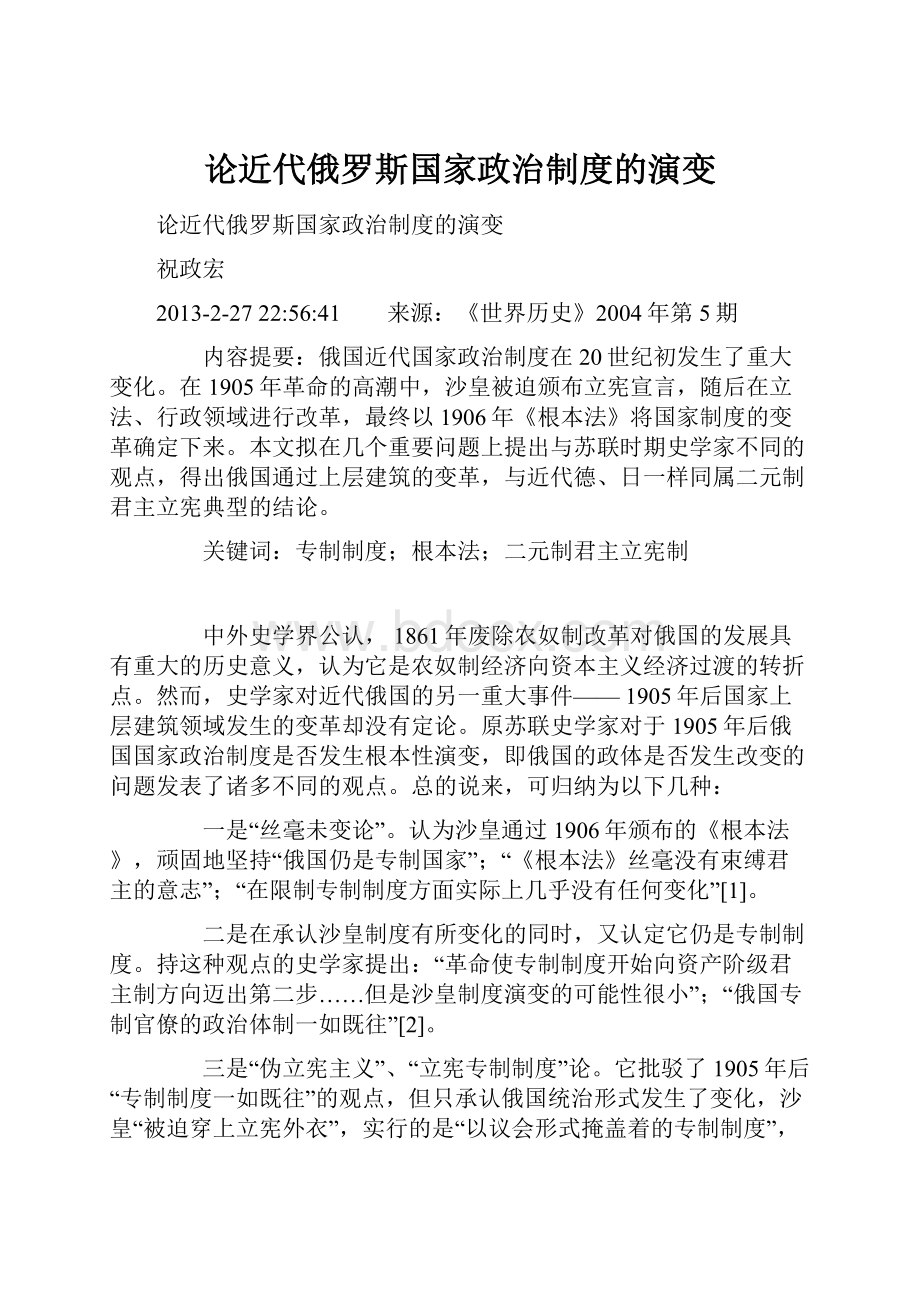
论近代俄罗斯国家政治制度的演变
论近代俄罗斯国家政治制度的演变
祝政宏
2013-2-2722:
56:
41 来源:
《世界历史》2004年第5期
内容提要:
俄国近代国家政治制度在20世纪初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1905年革命的高潮中,沙皇被迫颁布立宪宣言,随后在立法、行政领域进行改革,最终以1906年《根本法》将国家制度的变革确定下来。
本文拟在几个重要问题上提出与苏联时期史学家不同的观点,得出俄国通过上层建筑的变革,与近代德、日一样同属二元制君主立宪典型的结论。
关键词:
专制制度;根本法;二元制君主立宪制
中外史学界公认,1861年废除农奴制改革对俄国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认为它是农奴制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过渡的转折点。
然而,史学家对近代俄国的另一重大事件——1905年后国家上层建筑领域发生的变革却没有定论。
原苏联史学家对于1905年后俄国国家政治制度是否发生根本性演变,即俄国的政体是否发生改变的问题发表了诸多不同的观点。
总的说来,可归纳为以下几种:
一是“丝毫未变论”。
认为沙皇通过1906年颁布的《根本法》,顽固地坚持“俄国仍是专制国家”;“《根本法》丝毫没有束缚君主的意志”;“在限制专制制度方面实际上几乎没有任何变化”[1]。
二是在承认沙皇制度有所变化的同时,又认定它仍是专制制度。
持这种观点的史学家提出:
“革命使专制制度开始向资产阶级君主制方向迈出第二步……但是沙皇制度演变的可能性很小”;“俄国专制官僚的政治体制一如既往”[2]。
三是“伪立宪主义”、“立宪专制制度”论。
它批驳了1905年后“专制制度一如既往”的观点,但只承认俄国统治形式发生了变化,沙皇“被迫穿上立宪外衣”,实行的是“以议会形式掩盖着的专制制度”,并认为在《根本法》颁布后对沙皇制度是否发生变化的准确用语,应是与君主立宪制相对立的“立宪专制制度”[3]。
此外,还有一种不定论观点,即在肯定“立宪的虚伪性质”的同时,不确切地回答1905年后俄国政治制度的性质,或认为国家制度变化甚大,但在确定其统治形式时模棱两可。
如认为“10月17日宣言宣布了俄国统治形式由专制制度向立宪君主制的演变,当然,同时并没有任何可以使之实现的保障”[4]。
实际上,在近代俄国政治制度发生演变的问题上,原苏联学者所持的观点,在国内近年来出版的历史论著中也不难见到。
因此,笔者以为,有必要就这个问题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有关学者专家。
一
沙皇俄国的政治制度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嬗变,到18世纪基本确立了专制君主制,之后直至1905年前,逐渐发展为以沙皇为核心的无限专制制度。
1892年颁布的《国家根本法》规定:
“全俄罗斯皇帝是专制的、无限的君主。
上帝嘱咐服从他的至上权威不仅是出于畏惧,而且是出于至诚。
”[5]由此可以看出,俄罗斯皇帝是集国家行政、立法、司法、军事、外交大权于一身的至高无上的统治者。
事实也是如此。
1905年前,俄国不仅没有代表国民的机关,甚至不存在名符其实的政府,国家的某些最高管理机构都是听命于沙皇的高级咨询机关,没有任何实际权力。
只有沙皇享有完全、无限的权力,他在立法、行政等领域不受丝毫的限制。
20世纪初,俄国面临着严重的社会矛盾和政治危机:
以“解放同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以“立宪主义”为武器,持续地掀起抨击沙皇政府的运动,争取到了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人的拥护;沙皇阵营内的某些重臣也受到这一社会思潮的影响,迎合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政治主张,形成了一个“自由派官僚”阶层,进而渗入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工农革命运动日益高涨,随时有爆发推翻沙皇王朝革命的可能。
显然,当时的俄国在政治领域已出现了政府、自由派和革命派三大阵营。
然而,专制制度的观念仍然囿于某些“死硬派”代表的“哲学构思”中,末代君主尼古拉二世就是死守专制制度最后防线的总代表。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俄国在战场上连连失利,更加剧了原有的社会矛盾。
在内外交困中,沙皇被迫考虑进行某些政治改革问题。
1904年,沙皇颁布了12月12日诏令,应允进行一些次要的社会改革以缓和国内局势。
1905年“流血星期日”之后,沙皇被迫颁布了2月18日诏令,答应召开由选举产生的国民代表会议。
8月6日沙皇颁布关于《设立布里根杜马》的宣言以及《国家杜马章程》、《国家杜马选举法》。
由于这些文件没有明确赋予国家杜马以立法权,进一步激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强烈不满。
在“十月政治总罢工”的惊涛骇浪中,以大臣委员会主席维特为代表的“自由派官僚”主张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较为彻底的改革,以防止革命的进一步发展。
维特拟定了一份奏章,提出全面改革上层建筑的计划,又按沙皇的指令草拟了一份宣言。
在无法实行军事独裁、镇压革命的情况下,沙皇终于在10月17日颁布了维特起草的宣言。
宣言除许诺赋予公民各种自由外,最重要的一点是“规定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即任何法律不经国家杜马同意不得生效”。
与此同时,沙皇还批准发表了维特的奏章,并赋予其同等的法律效力。
10月17日宣言及维特的奏章实际上宣布了立宪的原则。
接着,10月19日沙皇发布改革大臣会议的敕令,以后又废除了大臣委员会。
12月11日,沙皇再次颁布了经过修改的《国家杜马选举法》,扩大了选民的范围。
1906年2月20日颁布了重新审定的《国家杜马章程》和《国务会议章程》。
4月颁布了新版《国家根本法》并召开了第一届国家杜马。
至此,俄国国家政治改革告一段落。
从这几份宪法性文件可以看出,俄国国家机构已发生了深刻变革。
立法方面。
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已具有议会的基本组织形式,拥有议会的基本权力,构成了相互制衡的立法两院。
国家杜马是按1905年8月6日和10月17日宣言设立的新机构,国务会议则是按新章程进行改革的原机构。
设计国务会议改革蓝图的仍是维特,他是在参考了西方议会结构的基础上,确定国务会议与国家杜马为俄国议会上下两院的格局的。
按照以上两个《章程》,国家杜马成员全部由选举产生,国务会议的一半成员由君主任命,另一半则由选举产生。
关于立法权的总原则,在1906年的新版《根本法》中有明确规定,“皇帝与国务会议、国家杜马共同行使立法权”,“任何新法未经国务会议和国家杜马的赞同不得产生,未经皇帝批准不得生效”。
“在立法事务方面,国务会议和国家杜马享有同等权力”(第7、86、106条)[6]。
《国家杜马章程》规定杜马的职权范围是有关“颁布、修改、补充、停止实施、废除法律和编制的事宜”,“国家杜马可以提出废除或修改现行法、颁布新法的建议”,但《根本法》除外(第31、32条)。
关于立法程序则规定,由大臣、杜马下设机构、国务会议创议的法案提交国家杜马,国家杜马通过的法案转交给国务会议审核,国务会议有权否决;国务会议创议并通过的法案转交国家杜马;未被国家杜马或国务会议通过的法案则视为已被否决(第34、48、49、50条);经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通过的法案由国务会议主席呈交沙皇批准,若未被沙皇批准,则不能在此会期再次提出(第52、53条)。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国务会议和国家杜马都享有一定的立法权,即对法律有创议、修改、补充、停止实施、废除的权力,而且彼此间相互监督,相互制约,形成议会制下的上下两院。
除了立法权,这两个机构还拥有两项重要权力:
审核批准国家预算,向政府各部大臣提出质询(第31、33条)[7]。
这样,按照新章程设立的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具备了一般国家议会的基本特征,它们与君主构成了三位一体的立法体系。
行政方面。
改革后的大臣会议虽然保持了原来的名称,但它已是新的机构,具有类似于现代内阁制的几大特征:
第一,大臣会议主席由沙皇从大臣中任命,沙皇不再自任主席。
大臣会议主席直接对沙皇负责。
第二,大臣会议主席获得高于其他成员的权力,他有权就各部门的事务出席国务会议和国家杜马会议,可代替大臣向沙皇呈递奏章,有权要求各部门主管人向他提供必要的情况和解释。
第三,大臣会议成员的行动必须协调一致,禁止各部门自行其是,禁止各部大臣擅自向沙皇呈交奏折。
第四,大臣会议的成员是固定的,它是由大臣和与之平权的部门主管人组成,从而初步形成了现代内阁的结构,即内阁由若干名重臣组成,某些大臣、副大臣不一定是内阁成员。
第五,大臣会议成为常设的行政机构,定期召开会议,并依法行政。
大臣会议主席的设立具有决定性意义:
由主席统一整个大臣会议的行动,其职能已接近于现代内阁的首席大臣(首相、总理大臣)。
正因为如此,旧俄的学者曾认为大臣会议主席一职的设立是“1905年10月19日改革的关键”[8]。
可以说,经过改革的大臣会议已具备了现代内阁的基本条件,成为常设的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即中央政府。
由国家杜马、国务会议组成两院的立法机关,以及由大臣会议形成的中央政府,是1905年后俄国国家机构发生的重大变革。
然而这些变革是否引起了俄国政治制度的变化呢?
二
可以肯定地说,1905年后随着俄国国家机构的变革,其政治制度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这主要表现在沙皇在立法、预算、行政领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沙皇在立法领域受到限制是显而易见的。
1905年后沙皇已不可能随心所欲地颁布、修改、废除法律。
因为“皇帝与国务会议、国家杜马共同行使立法权”,“任何新法不经国务会议和国家杜马赞同不得产生,不经沙皇批准不得生效”的总原则,从根本上打破了过去沙皇总揽立法权的局面。
尽管沙皇享有最终立法权,但任何法律不首先经过立法两院的审议、通过就不能产生,这无疑是对沙皇在立法方面的限制。
原苏联的一些史学家也曾正确指出,从1906年4月第一届国家杜马开幕时起,“俄国的立法职能已不是由一个机构——君主来实现,而是由三个机构——国家杜马、国务会议和君主来行使”。
“在1906年4月以前,沙皇大笔一挥就可以修改、废除任何法律”,而在此之后沙皇就“丧失了独自决定立法的权力和按自己的裁夺支配国家预算的权力”[9]。
然而,原苏联及国内的另一些学者则常以《根本法》第87条来否定国家杜马拥有立法权,证明沙皇在立法方面没有受到丝毫限制。
“第87条”是俄国参照普鲁士、德意志宪法的规定而制定出来的,的确是对国家杜马立法权的限制,但它不可能完全剥夺杜马的立法权。
其一,该条款允许的是,政府在国家杜马休会期间的“非常情况下”,直接经沙皇批准通过法案,而这种“非常情况”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可以经常使用。
其二,该条款本身还规定了一个追认的程序,即大臣在国家杜马复会后的两个月内如不向杜马提交此法案,或杜马、国务会议不批准此法案,则停止实施此项法案,这就决定了政府各部不能毫无顾忌地甩开立法机关而自行立法。
其三,国家杜马每年都有一个月以上的会期,集中从事立法事项,这就保证了有相当数量的法案是经过立法两院渠道产生的。
诚然,在此种情况下,沙皇在立法领域中仍占优势,立法两院特别是国家杜马的立法权有时并不稳固,但沙皇在1905年后毕竟丧失了立法的垄断权,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与立法权相关联,沙皇在预算方面的权利受到限制也是毫无疑问的。
过去,给哪个部门拨款,拨多少款,主要由沙皇一人定夺,而在1905年后,这些权力一部分便转到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手中了。
沙皇在行政领域所受的限制要弱一些,但这些限制仍对他构成了一定的牵制。
从《根本法》的规定来看,沙皇受到的限制分为两种。
一种是直接限制,如第84条规定,“俄罗斯国家管理的坚实基础是按规定程序颁布的法律”,沙皇下达的诏令、法令也必须“与法律相符”。
这就强调了包括君主在内的所有人的行为都应以法律为惟一准绳,尽管沙皇享有发布各种诏令、法令的权力,但他在拟定这些文件时,却不能全然像过去那样为所欲为,毫无顾忌。
因为造成大量与现行法律相抵触的事实将使他威信大减,这是他需要竭力避免的。
《根本法》第24条也直接限制了沙皇的行政权:
沙皇颁布的诏令、法令必须“经大臣会议主席和有关大臣、部门主管人的副署”方可生效[10]。
“副署”的规定打破了君主单独发布诏令、法令的有效性,因为从理论上说,这一规定隐含着某些大臣有拒绝“副署”的可能,也就存在着君主的诏令、法令不能生效的可能。
这一规定实际是君主面对代议机关被迫自我羁縻的表现,无怪乎维特曾称,副署“好比是议会制的影子,大臣不单是向皇上一人负责了”[11]。
间接限制主要表现为,作为最高行政机关的大臣会议的行为也要受到法律的约束。
《根本法》第122条规定,“大臣会议、大臣、部门主管人及法律授权的机关发布的行政决定、指令和命令,都不得与法律相抵触”[12]。
监督此项条款落实的是立法两院,因为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享有监督政府行为是否合法,有向政府成员质询的权力。
这就决定了政府在发布任何行政决定时,必须认真考虑现行法律的规定。
一旦由于不慎而作出与现行法律相冲突的决定,就有受到议会两院质询的可能。
虽然大臣会议(即“沙皇政府”)是直接对沙皇负责,但它所颁布的行政决定及其行为却要受到立法两院的一定监督,无疑,这自然也使沙皇的行动受到间接的限制。
实际上,沙皇权力受到限制的问题,在重新审定《根本法》时已明显地提出来了。
当时为修改旧版中沙皇是“无限的、专制的君主”一句,曾在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最后,沙皇经过异常痛苦的考虑终于被迫同意删去“无限的”一词。
“无限的”(Неограниченный)一词在俄语中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无止境、无穷的;二是指无限制、不受限制的。
这里显然用的是后一层意思。
删除了“无限的”三字,无疑表明沙皇的权力今后将受到限制,因为“无限的”即不受限制的对立面是受到限制。
尽管这一句中仍保留了“专制”一词,但正如维特所解释的,“专制”一词是回到很久以前俄罗斯君主古代称号的最初含义,它只是表示君主和国家对外的独立性,而非指18世纪以后的君主专制[13]。
三
《10月17日宣言》、《国家杜马章程》、《国务会议章程》如同英国历史上的《权利法案》、《王位继承法》一样,都属于宪法性文件,这是没有疑问的,而俄国1906年新版《根本法》究竟是不是宪法的问题,在原苏联史学界、法学界长期没有解决。
大多数苏联学者不是回避这个问题,就是称之为宪法性文件,很少有人径直称之为“宪法”。
实际上,这是个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
即使按苏联对“宪法”一词的权威性解释,1906年《根本法》也是名符其实的宪法。
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对宪法的定义为“拥有最高法律效力并规定一国政治、法律、经济制度的根本法”[14]。
可见,1906年新版《根本法》首先在名称上与宪法相吻合。
不仅如此,1918年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苏联1924年和1936年宪法的本名都是“根本法”。
显然,“根本法”是苏俄历来对宪法的另一称呼。
历史上和当今世界还有一些国家也以“根本法”或“基本法”来代替对宪法的称呼。
更重要的是内容。
1906年《根本法》对俄国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有明确规定,如皇权的最高权利(第4—24条),王位继承顺序(第25—39条),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大臣会议、国务会议、国家杜马、枢密院等)的职权范围、组织和活动原则(第98—124条),法律、法律效力和立法程序(包括非常时期的立法程序,第84—97条),国家预算(第114—118条)。
另外,它还规定了帝国领土的范围(第1、2条)、国语(第3条)、国徽(第61条)。
在新增加的有关臣民权利和义务一章中,它又确认了带有资产阶级民主、自由色彩的原则,如臣民有选择职业、迁徙、得到财产的权利(第76条),臣民住宅和私有权不容侵犯(第75、77条),臣民有言论、出版、结社、集会和信仰自由(第79—81条),未经法律程序臣民不受监禁和判处(第72、73条)[15]。
《根本法》还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大臣会议、大臣、部门主管人及法律授权机构颁布的行政决定、指令、命令均不得与法律相抵触”。
这里说的“法律”系指《根本法》。
此外,对《根本法》的修改要经过特别的立法程序:
只有沙皇创议,才能经国家杜马、国务会议进行修改。
由此可见,1906年《根本法》的内容及法律效力和立法程序也符合宪法的一般要求。
说1906年《根本法》是一部宪法还有一个佐证,即它完全是按当时一些君主立宪制国家的宪法为蓝本制定的。
维特主持了这项工作,他曾责成大臣会议办公厅主任诺尔德男爵从普鲁士、奥地利、日本、英国等“保守性宪法”中借用一些有关的原则和条款。
在审定《根本法》草案时,维特利用了诺尔德的研究成果。
他特别对普鲁士1850年宪法、德意志帝国1871年宪法、日本1889年宪法中的一些条文十分赞赏,有些针对俄国的情况稍加改动,有些就索性照抄。
因此,俄国1906年《根本法》中很多原则和规定与这些宪法十分相似,如君主神圣不可侵犯;君主是全国陆海军的最高统帅;议会由上下两院组成并享有一定立法权;君主有权提前解散议会;政府成员由君主任免,只对君主一人负责;非常时期的立法程序等。
维特在回忆录中曾经明确称,1906年《根本法》是一部宪法,是“保守性的宪法,不实行议会制的宪法”[16]。
他说得完全准确。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肯定地说,1906年《根本法》是俄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性质且予以实施的成文宪法。
遗憾的是,这点长期没有得到原苏联史学界和法学界的肯定。
这些学者之所以没有称1906年《根本法》为宪法的原因在于,苏联长期在政治思想、文化学术领域实行禁锢政策,使这一问题变成了禁区,触及它便有可能与“政治立场”相联系而遭到厄运。
因为苏联政治界一直只认定十月革命后的1918年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为俄国的第一部宪法,而否认沙皇时代即君主制时代也曾制定过一部宪法——《根本法》,因而苏联学者也不得不对此小心翼翼,不敢直接称《根本法》为宪法。
既然1906年《根本法》是一部名符其实的宪法,而沙皇在立法、行政等方面又受到这部宪法的一定限制,因而得出俄国1905年后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制政体的结论就是顺理成章的。
某些原苏联学者持“伪立宪制度”观点的主要根据是,沙皇在革命风暴中为了自保而被迫发布欺骗舆论的法律文件,此后在形势有利时他就夺回丧失的一切。
总之,他们认为,法律文件是一回事,执行法律则是另一回事。
笔者并不否认沙皇的这一企图,他为了维持封建专制王朝存在下去,被迫颁布有关政治改革的法律文件,但是这些法律文件一旦颁布,就会自然构成对沙皇自身的束缚,造成改行君主立宪的既成事实。
这也是不以沙皇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例如在立法领域,仅在第三届杜马的5年内,被称为“磨坊”的国家杜马就“磨”出了2197项最终成为法律的法案[17]。
此外,直到1914年右派报刊还认为国家杜马与国务会议、沙皇陛下一样各享有1/3[18]。
在编制国家预算和借款方面,沙皇政府也必须依靠国家杜马,没有杜马的批准,政府各部就不能得到拨款。
财政大臣科克夫佐夫曾多次抱怨,他任大臣会议主席时,感到自己的经济纲领的实施受到了杜马一定程度的监督和限制;在1907年曾请求杜马尽快审核批准国家预算,因为只有依靠杜马的威信才能搞到国外贷款[19]。
尽管在1905年后沙皇并未忘记复辟旧秩序的念头,极右派势力也在推波助澜。
然而由于受到各种政治因素的钳制,沙皇又不得不打消恢复旧制度的企图,仍然在以10月17日宣言和1906年《根本法》为基础的立宪制的轨道上行进。
此外,笔者不否认沙皇曾践踏过法律,但这种情况只是少数,违反法律的也只是其中的个别条文。
而事实是,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沙皇并未彻底推翻上述宪法性的法律文件。
因此,那种视《根本法》为“伪立宪制度”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四
原苏联史学界关于1905年后实行何种政治制度的问题尽管众说纷纭,观点各异,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否认1905年后俄国改行为君主立宪制。
即使是在研究专制制度演变方面卓有成效的某些学者在基本肯定国务会议、国家杜马为议会上下两院,明确肯定1906年《根本法》为宪法之后,也否认俄国实行了君主立宪制,而是采用了“立宪专制制度”这一术语。
笔者一直迷惑不解,为什么苏联时期的历史学家在承认沙皇权力受到宪法和宪法性文件一定限制的同时,却否认俄国实行了君主立宪制呢?
在查阅了有关资料后,笔者才恍然明白了其中的缘由。
除了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之外,原来,苏联与我国对“君主立宪制”这一政治概念的标准不一。
我国政治、历史学科将“君主立宪制”概括为某些国家君主权力受到宪法限制的君主制,将它分为议会制和二元制。
在议会制的君主立宪制下,君主不直接支配国家政权,内阁掌握行政权并对议会负责,如英国。
在二元制的君主立宪制下,君主任命对他负责的内阁,直接掌握行政权;立法权归议会行使,但君主有否决权,如1871—1818年的德意志帝国即属此例[20]。
我国学者称俄国实行君主立宪制,正是指这种二元制下的君主立宪。
而在苏联则不同。
1960年出版的《苏联历史百科全书》没有“君主立宪制”的词条,在“君主制”的词条中写道:
“在一些国家(如俄、德)君主制的特征是封建专制君主制缓慢地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但这个转变没有最终完成,如革命前的俄国”。
1970年以后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虽有“君主立宪制”的词目,却无内容,只注明参看“君主制”词条。
这一词条在列举了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君主制后写到,“在资产阶级君主制的国家中,君主制通常表现为受到限制的君主立宪制,它的形成是资产阶级和贵族妥协的结果。
在现代资产阶级君主制国家中,君主的权力受到宪法的限制,也就是立法职能转给议会,行政权转给政府”。
接着该词条又详细地介绍了君主如何“统而不治”的内容[21]。
很清楚,苏联学者认为的“君主立宪制”只是我国所说的“议会制的君主立宪”,并没有把“二元制的君主立宪”划入君主立宪制的范畴之中。
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具备了英国式的“议会制”条件才算是实行了君主立宪制,即通常所说的“资产阶级君主制”。
难怪一些对近代俄国政治制度演变研究到一定程度的苏联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总是踌躇徘徊,不敢径直称1905年后俄国实行了君主立宪制,只能以各种术语取而代之。
将君主立宪制分为两种类型无疑是科学的,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因为我们不能否认世界历史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时期存在过二元制的君主立宪。
自英国“光荣革命”确立了君主立宪后,世界各国先后形成了两种形式的君主立宪制。
最常见的是英国式的议会制,但在那些封建势力较为强大、资产阶级相对弱小的国家往往确立的是二元制,例如1850年后的普鲁士王国、1871年后的德意志帝国、1889年后的日本帝国等。
二元制的君主立宪制是一种较为复杂的政体,它实际上是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出现的一种君主制。
在这种制度下,君主的权力虽然十分强大,但它与专制君主制存在着重大区别,这就是国内存在着一部宪法,从一定程度上说,它是该国民主化和不同阶级力量对比的产物。
原苏联的某些学者总是强调俄国的独特性,即封建势力的强大和资产阶级力量的弱小。
殊不知德国、日本也有自己的特殊之处,例如1871年后的德国,议会权力相当微弱,不仅皇帝可以解散下院(帝国议会),而且上院(联邦议会)在得到皇帝批准后也可以解散下院。
再如1889年后的日本,封建势力也很强大,“万世一系”的天皇大权在握,帝国议会的两院只有“协赞”天皇的权力,其权力还不如俄国的国家杜马。
然而,这三个国家仍有共同之处,那就是君主在保持着强大权力的同时,或多或少地受到宪法的限制。
研究历史应该根据各国基本的共同点来确定各国的政体,而不应该过多地受某种政治因素的影响。
否定二元制君主立宪制的概念极不可取,这会给政治、法律、历史学带来混乱。
如果否定这个概念,我们连上述几个国家的政体都无法准确地判定,又如何确定1973年前的阿富汗王国、1974年前的埃塞俄比亚王国、1979年前的伊朗王国以及当今的尼泊尔、约旦、摩洛哥、科威特等王国的政体呢?
笼统地称它们为君主制国家和专制君主制国家显然都是不适当的。
因此,二元制君主立宪制这个概念是绝不能否定的。
倒是旧俄时代的某些学者和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少数苏联历史学家的结论较为接近二元制君主立宪这一科学的表述,这多少反映了政治环境与学术观点存在某些联系。
如原苏联学者Ф.塔拉诺夫斯基就认为,俄国在1905年后建立了“二元立宪主义体系”。
他说:
“建立在政府和国民代表机关这种二元制基础之上的君主立宪制的特征是,国民代表机关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