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争光《驴队来到奉先畤》中篇小说.docx
《杨争光《驴队来到奉先畤》中篇小说.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杨争光《驴队来到奉先畤》中篇小说.docx(3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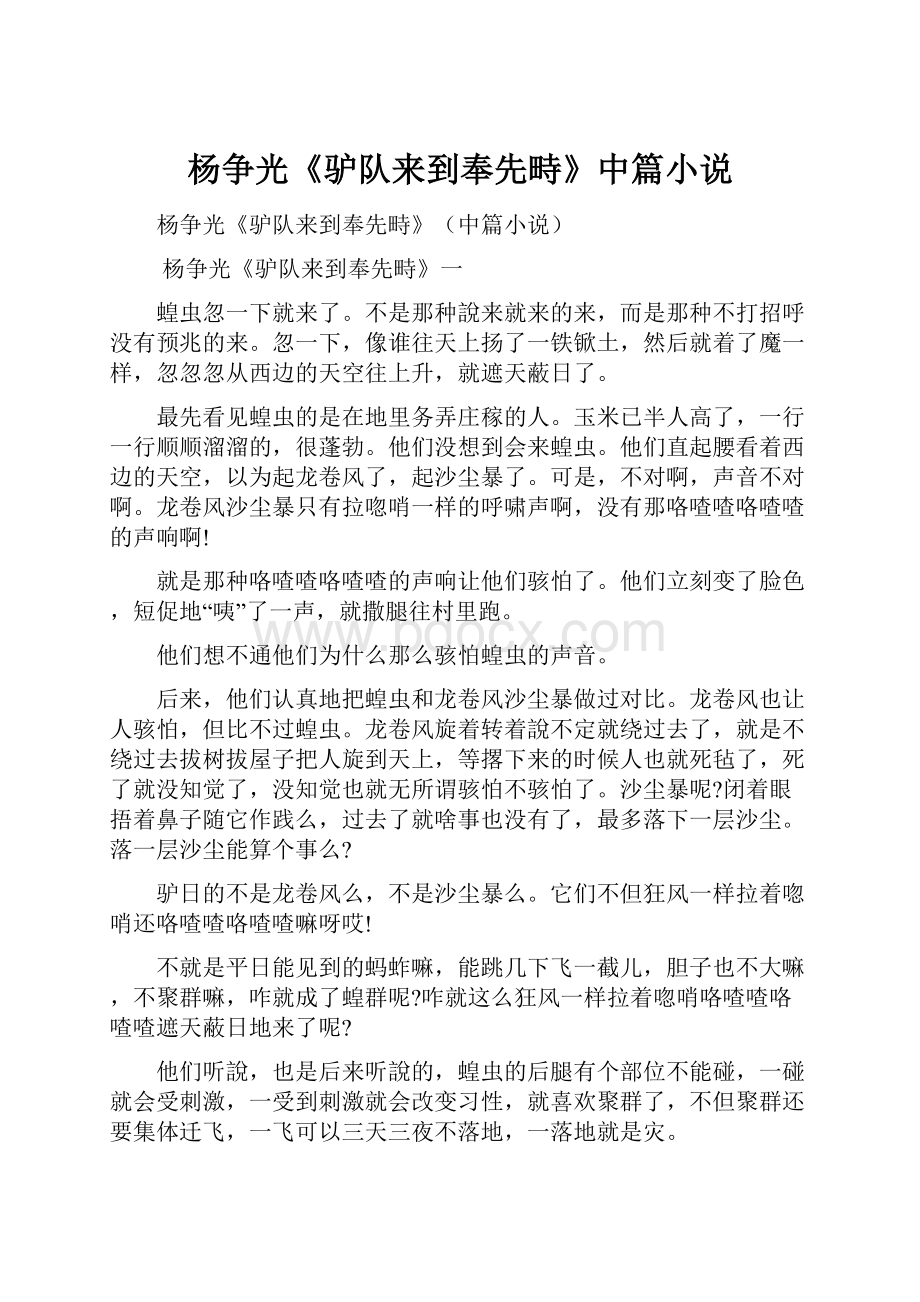
杨争光《驴队来到奉先畤》中篇小说
杨争光《驴队来到奉先畤》(中篇小说)
杨争光《驴队来到奉先畤》一
蝗虫忽一下就来了。
不是那种說来就来的来,而是那种不打招呼没有预兆的来。
忽一下,像谁往天上扬了一铁锨土,然后就着了魔一样,忽忽忽从西边的天空往上升,就遮天蔽日了。
最先看见蝗虫的是在地里务弄庄稼的人。
玉米已半人高了,一行一行顺顺溜溜的,很蓬勃。
他们没想到会来蝗虫。
他们直起腰看着西边的天空,以为起龙卷风了,起沙尘暴了。
可是,不对啊,声音不对啊。
龙卷风沙尘暴只有拉唿哨一样的呼啸声啊,没有那咯喳喳咯喳喳的声响啊!
就是那种咯喳喳咯喳喳的声响让他们骇怕了。
他们立刻变了脸色,短促地“咦”了一声,就撒腿往村里跑。
他们想不通他们为什么那么骇怕蝗虫的声音。
后来,他们认真地把蝗虫和龙卷风沙尘暴做过对比。
龙卷风也让人骇怕,但比不过蝗虫。
龙卷风旋着转着說不定就绕过去了,就是不绕过去拔树拔屋子把人旋到天上,等撂下来的时候人也就死毡了,死了就没知觉了,没知觉也就无所谓骇怕不骇怕了。
沙尘暴呢?
闭着眼捂着鼻子随它作践么,过去了就啥事也没有了,最多落下一层沙尘。
落一层沙尘能算个事么?
驴日的不是龙卷风么,不是沙尘暴么。
它们不但狂风一样拉着唿哨还咯喳喳咯喳喳嘛呀哎!
不就是平日能见到的蚂蚱嘛,能跳几下飞一截儿,胆子也不大嘛,不聚群嘛,咋就成了蝗群呢?
咋就这么狂风一样拉着唿哨咯喳喳咯喳喳遮天蔽日地来了呢?
他们听說,也是后来听說的,蝗虫的后腿有个部位不能碰,一碰就会受刺激,一受到刺激就会改变习性,就喜欢聚群了,不但聚群还要集体迁飞,一飞可以三天三夜不落地,一落地就是灾。
谁个驴日的闲毬没事干为啥要碰人家的后腿嘛!
驴日的你要飞就一直飞一直飞死你个驴日的再落地不行吗呀哎!
村庄里所有的人都从屋里院里跑到村街上了,都梗着脖子,都直愣着眼,把眼睛直愣成了眼窝,看着西边的天空,都“咦”了一声。
“咦!
”
就一声。
每个人只“咦”了一声,蝗虫就到他们的头顶上了。
他们被震慑住了,没法“咦”第二声。
他们的心立刻收缩成了一块肉疙瘩,肉管子一样的喉咙也挤严实了,没一点缝隙了,没法出声。
人在恐惧骇怕的时候叫唤几声会好受一些的,但他们确实只“咦”了一声。
就算他们的喉管没挤严实,还能“咦”,也听不见的。
蝗虫不但遮住了太阳糊住了天空,还狂风一样拉着唿哨咯喳喳咯喳喳要搅昏天地呢!
把全村人排成演唱队伍让谁指挥着一起“咦”,也听不见。
他们“咦”不过蝗虫。
他们抱着头,跑回各自的家,紧紧地关上了门。
为什么要抱头呢?
蝗虫又不是飞来的砖头。
他们抱头抱得有些自作多情了。
就算蝗虫是砖头,也不是冲着他们来的。
为什么要跑回屋关上门呢?
他们太把他们的屋子当回事了,以为把他们关在屋里就安全了。
事实不是这样的。
后来,他们也认真地把屋子和蝗虫和安全关联在一起思量过。
屋子是用来遮风挡雨的,遮挡邻人的目光的,当然也能遮挡仇人撇过来的砖头。
但蝗虫不是风雨,也没想偷看他们的隐私,也没和他们结怨结仇,用不着把自己变成解冤消仇的砖头。
蝗虫只是蝗虫。
蝗虫对他们的头和他们的屋子都没兴趣。
蝗虫感兴趣的是他们在地里种出来的田禾,具体到眼下,就是已长到半人高的玉米。
他们到底还是思量明白了,真正能给他们安全的,实在不是他们费心使力建造起来的以为可以一劳永逸的屋子,屋子没有这么大的能耐。
真正能给他们安全的,也正是蝗虫感兴趣的东西——地里的田禾么。
狂风一样拉着唿哨的声音没有了,只剩下那种咯喳喳咯喳喳的声响。
他们知道蝗虫已经落地,正在啃嚼着他们的田禾。
全村的人都直直地坐在他们的屋子里听蝗虫的声音。
他们没睡没躺,直直地坐着,直愣着眼窝,听得很仔细,很耐心,一直听了三天三夜。
也有人听得不耐心了,不服气了。
再說它们也只是蝗虫啊!
再說咱们是人啊!
难道就这么一声不吭地让虫虫治咱们人么?
他们拉开门,跑出村,就看到了蝗虫啃嚼田禾的情景。
他们太多太多了,没法說清他们的数目。
它们咯喳喳咯喳喳地拥着铺排在田地里,看不到边沿。
它们啃嚼得多认真啊,多细心啊,多从容啊,多有章法啊。
玉米不是半人高了么?
它们就互相摞在一起搭成架子从上往下啃。
它们咯喳喳咯喳喳啃完一片,就挪到另一片地里,挨个儿往过啃。
踢它们驴日的!
可是,你的脚有多大的能耐呢?
把脚踢断也踢不散它们。
踩它们驴日的!
一脚下去,能踩出一个蝗虫肉饼。
可是,腿脚上的力气是很有限的,你能踩多少下?
对整个蝗虫队伍来說,你踩多少下也没有知觉的,和没踩一样,它们依然啃嚼得很从容,很细心,不乱章法,啃嚼完一片再挪移到另一片里继续啃,结果只能是,你踩得没了一丝力气,一屁股坐下去,眼睁睁地看着它们啃嚼,咯喳喳咯喳喳,你服气不?
不服气也没办法啊。
想哭不?
想哭也哭不出声的,没力气哭了嘛。
这就叫绝望。
如果不带意气不带情感的话,你就会佩服蝗虫的。
三天三夜之后,它们忽一下又走了,和来的时候一样,不打招呼,没有预兆。
村庄里没有一个人看见它们是怎么走的。
服不?
还有,它们啃嚼得多开心啊!
不光是玉米,还有各种草,还有树叶,方圆多少里连个碎渣渣都找不到的。
所有的田地都一个成色了,连成一片了,光秃秃一丝不挂,平展展裸袒着,让太阳照着,好像遭了劫掠连衣服也被扒得净光的人,在用它们的裸体给所有围观的人說:
别看了没啥看的了,它们搞得很彻底。
驴日的把咱弄净光了嘛。
没冤没仇啊!
驴日的你还不如冲着人来呢,哪怕把人弄死呢!
驴日的你不弄人弄田禾!
既然你不弄人让人活着为啥要断人的活路嘛你个驴日的。
这就叫自然灾害,没冤没仇给你弄个灾,害你么。
你說的意思就是天灾嘛,非要說成个自然灾害好像你念过书一样。
不不不,龙卷风沙尘暴是天灾。
地震也是。
上半年的大旱也是。
这是蝗虫么。
那叫虫灾!
你看你看,咱犟这嘴有啥意思嘛又犟不来口粮。
就是没口粮才犟嘴呢嘛,有口粮吃饱肚子我就上我女人的肚子去了,哪有心思和工夫和你磨这号闲牙!
那些天,村庄里时常有人在一起磨这样的闲牙。
其实那些天他们还是有口粮的。
說蝗虫走了以后什么都没留下也不符合实情。
实情是,蝗虫走的时候留下了许多死蝗虫。
他们用脚踩出的蝗虫肉饼算是被动留下的,更多的是它们主动留下的尸体。
谁也弄不清楚它们是怎么死的,是咀嚼的时候拥着挤着互相踩踏死的,还是搭架子从玉米顶头往下啃的时候压死的,还是吃得太饱撑死的?
一连吃了三天三夜,难道没有撑死的?
没有人细究这个问题,反正它们被留下了,就成了人的口粮。
他们提着草笼子背着背篓,用扫帚在地里抢着扫拾那些死蝗虫。
也有人用的是装粮食的麻布袋子,装满了摇一阵压一阵继续装,装得很实在。
也有人为抢拾发生过口角,甚至恶言相向,到了要动手脚的地步。
多亏蝗虫的尸体是有限的,很快就抢拾完了。
咋吃呢?
蝗虫挺肥的,身体上不但有肉也有油,在锅里一炒,又酥又香。
他们过了几天好日子。
但很快就有了不良的后果,许多人屙不下来了,要用手抠,抠出来的全是蝗虫皮。
这时候,他们才知道,蝗虫的尸体可以当口粮,却实在不是真正的口粮。
可以当口粮的蝗虫嚼断了他们获取真口粮的路。
这时候,他们也知道了,在很多情况下,虫虫是可以把人治住的,尤其像蝗虫这样的虫虫,不但能把人治住,还要往绝路上治呢!
他们一年种两料田禾。
上半年的田禾因为一场大旱全死了,田禾变成了柴禾,土地不但没有给他们一粒口粮,还龇着牙咧着嘴给他们示威一样。
他们也龇牙咧嘴了。
他们龇着牙咧着嘴用他们的力气和汗水把龇牙咧嘴的土地抚弄平顺了,松软了,种上了第二料田禾,眼看着半人高了,忽一下,蝗虫来了。
驴日的明年来也成啊,让咱收一料庄稼有点口粮就能对付了咋拣这时候来嘛哎哎!
驴日的就是干旱了才碰后腿才聚成群胡飞哩要不就不是驴日的蝗虫了。
如果听到这一类的对谈,五十九岁的吴思成就会一脸轻蔑地给对谈者撂过去两个字:
扯蛋。
村上已经有饿死的人了,许多人已经撂下了他们的屋子院子推车挑担逃难去了。
他不屑于这样的对谈。
在他看来,这时候还說这样的话,就不是拉闲话也不是犟嘴了,而是纯粹的扯蛋。
扯蛋就是虽有动作却无所作为的意思。
然后是驴队。
二
驴队比蝗虫简单。
是啊,不能光扯蛋啊,肚子也不悦意啊。
哪怕逃难呢!
哪怕去远地方伸手讨要呢!
哪怕做三只手当贼娃子呢……
“不行。
要有所作为,但不能下贱。
”
这是吴思成撂出来的另一句话。
他们老中青一共十二个人,聚合在村外的一个草庵子里,都是没离开村庄想有所作为都不知道怎么才能有所作为的人。
他们要在这里商量出一个有所作为的办法来。
他们都同意吴思成“要有所作为但不能下贱”的观点。
在他们中间,吴思成年龄最长,也是十二个人里唯一没有被饥饿捏弄得面露凶相的人。
他高而干瘦,像麻秆,有一对老鼠一样贼亮的小眼睛,三十多岁的时候娶过一房女人,没等到生养儿女,女人病死了。
他一直单身,和村上一个寡妇好,隔三差五到寡妇炕上放松一次。
逃难的人里就有那个寡妇。
他没留她,也没跟她走。
他不愿逃难,原因就是他說的:
不能下贱。
现在,吴思成站着,小眼睛一下也不眨。
他的小眼睛只在兴奋的时候才会眨的。
他在给蹲坐在地上的十一个人說话。
他說:
“咱不投亲靠友不伸手讨要不做三只手,也不能等着饿死。
”
瓦罐打断了吴思成的话:
别說饿啊!
你一說饿我就会想把蝗虫当口粮的那些天贪吃屙不下,现在连吃了屙不下的东西也没了你还說饿!
瓦罐本不叫瓦罐,因为头越长越像瓦罐,就叫他瓦罐了。
瓦罐的表情和声调都很痛苦。
他不让吴思成话里带饿字。
他在十二个人里年龄最小。
吴思成一丝同情也没有:
扯蛋。
瓦罐急了,站起来了:
没有啊我的手在屁股上你看么。
瓦罐把屁股摆给吴思成看。
瓦罐的手确实在屁股那里。
瓦罐說他那些天抠得太过火了还没好彻底。
吴思成說:
扯蛋!
瓦罐蹲下了:
好吧,就算我扯蛋了。
吴思成继续說他要說的话了。
他說:
“人拿天没办法,拿虫虫也没办法,人拿人呢?
那就看怎么办了。
咱不想把咱活成贱人,就只能当强人。
强人就是明着抢人的人,也是不怕死不得已也敢杀人的人。
把你们家的驴拉出来,再掂一样家伙,最好是带铁的,注意,镢头锄头镰刀不行,这些家伙虽然带铁,一看就是种地的家伙。
最好是榔头、砍刀。
有了驴和家伙,咱就是队伍了。
”
有人问:
女人和娃咋办?
吴思成說:
留着守村子,守家。
咱有吃有喝就由咱了,要么接他们出去,要么咱再回来,继续种地。
瓦罐又起身了:
我媳妇娶进门还不到一年啊叔哎!
吴思成說:
扯蛋。
成队伍就没有叔了。
队伍要有个头儿,注意,我年岁大了,当不了头儿,咱弄一个头儿。
咋弄?
你们往外边看——
草庵外边放着两只木桶,凉水满得要溢出来了。
吴思成說:
谁有能耐往肚子里灌进去一桶,谁就是咱的头儿。
十一个人都看着那两只木桶。
吴思成看着看木桶的十一个人。
瓦罐咽了一口唾沫,把目光从木桶上移开,看吴思成了。
吴思成說:
想试试,得是?
瓦罐說:
我没想试。
吴思成說:
没想试就别看我。
瓦罐說:
别刺激我啊。
吴思成說:
凭你那么一点肚子也装不下的。
瓦罐說:
你刺激我了!
吴思成不理他了。
瓦罐說:
你又刺激我了!
吴思成还是不理他。
瓦罐站起来了。
瓦罐问:
一桶还是两桶?
吴思成說:
一桶。
瓦罐低头看了一下自己的肚子,走到吴思成跟前,又问了一个问题:
当头儿能带媳妇不?
吴思成說不能。
瓦罐又看了一下自己的肚子,想了一下,又问:
当了头儿說话算数不?
吴思成說那得看說什么话,还有军师呢。
瓦罐间军师是谁?
吴思成說:
我么。
瓦罐又想了一下,說好吧那就再问一句,头儿大还是军师大?
吴思成說头儿大。
瓦罐說我真受刺激了,蝗虫受刺激就聚群了我受刺激就想喝那桶凉水了。
吴思成說这时候說再多的话都是扯蛋往木桶跟前去才是有所作为你往木桶跟前去。
瓦罐真朝木桶走过去了,走到木桶跟前了。
他歪过头又问了吴思成一个问题:
头儿和军师的话顶牛了听谁的?
吴思成說:
听头儿的。
瓦罐冲着草庵里的人說:
你们可都听见了啊!
瓦罐一脸悲壮,跪在木桶跟前了。
他看着桶里的凉水,一只手在肚子上来回摸着,看摸了好长时间。
这时候他才知道,他要把满满一桶凉水全灌进肚子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甚至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吴思成說:
你看摸的时间太长了,再看凉水不会变少再摸肚子也不会变大的。
瓦罐扭过头要哭了一样,对吴思成說:
你又刺激我了!
吴思成說:
你又扯蛋了。
瓦罐說好吧我不扯蛋了我喝。
他把嘴伸进木桶,开始喝了。
咕咚一口。
咕咚一口。
除了吴思成,没有人看瓦罐。
他们在听。
咕咚。
咕咚。
该有小半桶了吧。
咕咚……咕咚……
咕咚声的间隔越来越长了,响动也越来越小了。
快要变成一口一口往进吸的声音了。
吴思成說:
满满一桶凉水是喝不完的,要抱着桶往下灌。
瓦罐把头从木桶里抽出来了。
他没看吴思成,他的脸对着桶里的凉水:
你管我喝还是灌呢!
喝和灌都要进肚子呢!
他把头又埋进了木桶里。
他已经咕咚得很艰难了。
听声音就能知道,他咕咚得有多么艰难。
他不像在喝凉水,像在受刑,快受不下去了。
咕……咚。
他把嘴从凉水里抽离出来,头脸依然埋在木桶里,好像要歇会气。
他說:
我不叫你叔要叫你吴思成了!
他說:
虫把人没整死你拿凉水把人往死里整啊!
吴思成好像没听见一样。
其他人也是。
他们都阴着脸,一直阴着脸。
瓦罐又把嘴塞进凉水里了。
吴思成皱眉头了,他听见瓦罐喝凉水的声音好像变化了,不再咕咚了。
他走到瓦罐跟前看了一会儿,然后就叫了起来:
“瓦罐你个驴日的喝一口吐一口等于没喝啊难怪不咕咚了!
”
又给草庵里的人說:
他驴日的喝进去一口啵儿一声又吐出来了不往肚子里咽了!
这一回。
瓦罐很快速地把头脸从木桶里抽出来了,直直地对着吴思成。
瓦罐不但满脸是水,眼里也有水了。
說话的声音也不如前了:
“我早喝到喉咙眼了,一口也下不去了,再下去一口喝到肚子里的凉水就会全吐出来的不吐就会死的你信不信嘛啊唔唔……”
瓦罐哭了。
他跪着,两只手在木桶沿上把着。
“我想我要喝下去这桶凉水头一样事就是另换个军师肚子不给力么你为啥不让带媳妇嘛啊唔唔唔……”
瓦罐的眼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木桶里掉着。
九娃几步就到了瓦罐跟前。
九娃的脚大而厚重,落地稳而有力。
他走得很快,最后一脚没落地,反而抬高了,一脚就踏在了瓦罐的屁股上。
瓦罐没想到会有人踢他。
他哼了一声想拧过头看一眼踏他的是谁,身子却朝前扑去了,扑在了木桶上,和木桶一起倒了。
他翻了个身,就仰着肚子躺在他没喝完的那大半桶水里了。
他像打嗝一样,嗝一声嘴里就会冒出一口凉水。
他不哭了,也没心情看踏他的是谁了。
他大张着嘴在冒水。
九娃抱起了另一只木桶。
九娃往喉咙里灌凉水的声响很清晰。
麻秆吴思成快速地眨了一阵小眼睛,给草庵里的人說:
拉你们的驴去。
他们都起身了。
他们没人追究九娃到底能不能把那桶凉水全灌到他的肚子里去。
吴思成没忘记躺在泥水里的瓦罐:
听见我的话了么?
瓦罐还在冒水,一边冒着水一边给吴思成点着头。
三
驴队是朝着东南方向走的。
他们认为东南方向雨水多,好长庄稼。
驴队有一条纪律:
走到任何地方见了任何人,都要把面目摆弄成一副凶狠的样子。
这不难,蝗虫已经让他们一脸凶相了。
但吴思成想得比较远:
有吃有喝了就不一定老这么一脸凶相了,所以,一定要有这么一条纪律。
三个月以后,他们换了装备,把从家里带出来的榔头砍刀换成了清一色的鬼头刀。
吴思成嫌鬼头刀不好听,就另起了个名字,叫护胆夺命刀,给自个儿壮胆,必要时夺他人性命的意思。
半年以后,他们接收了一个打兔的。
他有一杆土枪。
他们私下叫他打兔的,公开场合叫他土枪手。
他们不但有了铁器,也有了火器,真成队伍了。
驴队就是驴队,最好不往里边掺杂其它牲口,所以他们给打兔的也弄到了一头驴。
这时候的他们要弄到一头驴已经不算什么事了,顺带着就能办到。
驴队上路没多少天,九娃就给瓦罐分配了一样特别的差事,要他把一路上走过的村住过的店记下来,不但要记住村名店名还要记住方位和线路。
瓦罐问为啥?
九娃說不为啥让你记你就记少问多做。
瓦罐說走村过店大家一起的大家都记嘛为啥要我记?
九娃說你年龄最小脑子最好使。
瓦罐說脑子好使就应该管账。
九娃說管账有吴思成呢!
你就给咱记村名店名。
瓦罐說好吧你是头你說钉子就是铁我记。
九娃說可不能记乱啊。
瓦罐說不会乱的不过我得问清楚,你說的是经过的村还是进过的村?
九娃說进过的经过的都记。
瓦罐說咱经过的村比进过的可就多了去了,不过那也不会乱的,你不是說我脑子好使么我也承认。
每天晚上临睡前,瓦罐都会把他们走过的村住过的店在脑子里过滤一遍。
不难么。
不但不难,而且还很享受么,很刺激么。
因为过滤的时候会顺带着过滤出一些情景来的,过滤到进某个村要吃要喝要钱款很顺利的情景,他就觉得很享受,过滤到那些逢凶化吉化险为夷的情景,他就觉得很刺激。
这实在是一件出乎意料的好差事么,不但能锻炼记性,还能品咂经世活人的滋味么。
但很快就过滤不出享受和刺激了。
走过的村住过的店越来越多,瓦罐过滤不过来了。
不光是村名店名啊,还有方位啊,还有线路啊,那么多村名店名加上方位线路在脑子里快要搅成一锅粥了。
真搅成一锅粥就没法给九娃交待了。
他给九娃說:
我脑子不听使唤了我受不下心里也不平衡了。
他說:
每天晚上我都要在脑子里演皮影戏一样走村过店你们睡得和猪一样。
他說:
再这么折磨几个晚上我脑子就残废了。
他让九娃另找个人。
他說我不是怕脑子残废是怕误你的事。
九娃问吴思成咋办?
吴思成笑着說瓦罐:
你驴日的肚子不行脑子也不行么。
瓦罐說你别给我笑你人瘦脸瘦咋笑都看着不厚道,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啊。
吴思成說你脑子不行就找个东西代替脑子嘛。
瓦罐說你可真能說话脑子不行还能想出个东西代替脑子啊?
吴思成說你找张牛皮纸往上画嘛。
瓦罐在自己的额颅上拍了一巴掌,說:
是啊,咋就想不到牛皮纸呢!
可是,光有牛皮纸也不行啊还得有笔有墨才能往上画啊。
也不行,总不能因为一张牛皮纸还要揣上笔和砚台吧?
砚台是石头啊!
吴思成說哪个村都有识文断字的人都能找到笔墨你只揣一张牛皮纸就成。
瓦罐又在额颅上拍了一巴掌,說:
服你了服你了我找牛皮纸。
他找到了一张牛皮纸。
从此,每过一个村庄住一个店吃了喝了以后,瓦罐就到处找笔墨,在牛皮纸上画记号,写村名店名,不会写的字就问吴思成。
他把牛皮纸画成了一张地图。
瓦罐的牛皮纸快画满了,驴队还在往前走。
但九娃說了,走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就想办法试着落脚。
瓦罐說:
再不落脚我就得另换一张牛皮纸了。
九娃說:
你再画小一点就能多画一阵子。
瓦罐說:
不再往上画了多好,你的话真让我绝望。
瓦罐质问过吴思成:
你說有吃有喝了就咋就咋你說过没?
吴思成說:
說过,咋啦?
瓦罐說:
我以为你忘了。
吴思成說:
我没忘。
瓦罐說:
那我再问你,咱现在算不算有吃有喝了?
吴思成没回答瓦罐的问题,他說你问九娃去。
瓦罐没问九娃。
瓦罐避开吴思成,私下给九娃說了一番话。
他說:
“吴思成說等咱有吃有喝了要么把女人接出来要么咱回去,依我看吴思成压根就没想这么做。
他钻了多年的那个寡妇撂下他连影子都没了他接谁去?
他光毬一个人和咱一边当强人一边逛世界他跑回去做啥?
种地啊?
在外边有吃有喝他为啥要回去种地?
他和咱情况不一样心思也不会一样的。
咱有女人啊,你还有娃儿呢!
咱抢人劫人这么长时间总有些积攒了吧?
你一路上只让劫财不准劫色硬憋着熬着不就是还想看咱自个儿女人么?
我不信你晚上不想女人。
吴思成去年五十九今年过六十了还說饱暖思淫欲呢!
他年岁大了过个嘴瘾能行,咱血气正旺說不想就能不想么?
实话给你說,我天天晚上都想!
你是头儿,你可不能忘了咱拉驴出来时說的话。
要不你就把规定放宽一些,实在憋不住了也劫点色。
”
九娃给瓦罐的回答是:
你个驴日的敢动这心思敢动哪个地方的女人我让土枪手把枪里的火药和铁砂全打到你驴日的脸上,让你到阎王那里动女鬼去。
然后,又替吴思成說了几句话:
你别把人家吴思成想恶了。
我也实话给你說,劫财不劫色就是吴思成的主意。
财是身外之物,女人不是。
咱走了一路劫了一路没死一个人没伤一个人就是因为咱只劫财不劫色。
你以为我不想?
不想就不是人了。
敢劫么?
有人会和咱拚命的。
就算不拚命,咱劫着劫着会乱心性的。
你听好了,驴日的你老实憋着,憋死你个驴日的也不能坏规矩。
生锈?
你驴日的真能想也能說出口啊。
你那东西不是铁多长时间不用也不会生锈,只要不割下来就不会坏不会变成一吊子烂肉!
咱现在还不算有吃有喝,咱还没有积攒。
咱还没走到合适的地方还得继续走,你好好给牛皮纸上画记号去!
瓦罐在自己的嘴上扇了一巴掌,說:
明白了我嘴上爱說淡屁没味的话你别生气你赶紧看土枪手正瞄呢要放枪了——
驴队要停下来了。
他们骑在驴背上,看着土枪手。
土枪手也在驴背上,他正在瞄准。
他拿枪瞄准的姿势很特别,不是两手一前一后端着枪朝前瞄,而是两只胳膊直伸出去,横握着,枪口朝着旁边。
这实在不能叫瞄准,应该叫对准。
他不用眼睛用的是感觉。
他感觉对准了就等于瞄准了。
然后,右手食指一勾,砰——他不会打偏的。
九娃喜欢看土枪手这么瞄准这么放枪。
这么拿枪不是本事。
这么拿枪每一次都能打准都不会失手才是本事。
土枪手就有这样的本事。
土枪手說他的这手本事是让兔逼出来的。
兔不会卧在你前边让你瞄着打它嘛。
你看见兔的时候它也不一定正在你前边嘛,它在你旁边咋办?
你转身还没瞄它就跑了。
它胡乱跑不给你瞄的时间嘛。
你要瞄你的身子你的枪就得跟着它胡转,转几下兔跑了你晕了。
你晕乎乎端着一杆土枪你会是个啥感觉?
你让兔把你当猴耍了嘛。
“所以,”土枪手說,“我不胡转,我不动身子只动枪。
”
现在,驴背上的土枪手就那么直伸着两只胳膊,横握着那杆土枪。
不光九娃,整个驴队都喜欢看土枪手这么瞄准这么放枪。
他们顺着那杆土枪看过去,不远处有一道土台,长着许多杂草,草丛里好像有一只黄羊。
他们提紧缰绳,不让他们的驴挪动蹄脚。
万一惊扰了黄羊呢?
“砰——”
看不见黄羊了。
瓦罐拍了一下驴屁股,紧跑了几步,第一个跑上土台,这才看见土台上不是长乱草的地方,土台上边只长着一溜杂草。
土台是个打麦场。
铺在场子中间的麦秸秆已碾压过无数遍,成麦草了。
一头拉碌碡的驴戴着笼嘴在麦草上站着,很安静,也很孤独。
它不用拉着碌碡在麦草上无休止地转圈了,因为赶它转圈的人中了土枪,栽倒在土台边上的那一溜杂草里了。
它竟然没有受到土枪的惊吓。
驴队全上了土台,围在那个误挨了土枪的碾场人跟前了。
瓦罐给九娃說:
不是黄羊。
骑在驴背上的九娃没有吭声,脸上的茬茬胡子里满是灰土。
他们都没有吭声,都一脸灰土,都骑在驴背上。
驴到底是不省人事的牲畜,有几头不但打了几声响鼻,还轻松地挪了几下蹄脚,引得麦场上的那一头也刨了几下前蹄,表示它和它们是一类的。
瓦罐跳下驴背,把蜷拱成一团的碾场人摆弄平顺了。
是个老头,光着屁股,裤腰在腿弯处。
然后,瓦罐又看见了一泡人粪尿。
瓦罐明白了,给土枪手說:
人家正蹶着屁股屙屎呢,你看成黄羊了。
又說:
屁股稀烂稀烂了,成马蜂窝了。
又惊讶地叫了一声,說:
不会吧?
脸咋也稀烂了?
噢噢明白了全明白了,你瞄他的时候他也蹶着屁股瞄你呢,屁股和脸都给你了。
又发表了几句看法:
他不瞄你也许还死不了。
屁股打得再稀烂也不会致命,头脸可是致命的地方。
他不知道要挨土枪么,要知道肯定不会蹶着屁股往后看的。
土枪手很尴尬,给九娃說:
我看走眼了。
九娃好像没听见土枪手在给他說话。
他扭着头朝周围看着。
到处都能看到碾完场收完粮食以后摞起来的麦草垛。
土枪手說:
肯定是坡底下那个村里的。
咋办?
九娃和吴思成商量了一阵子,就有了断语。
九娃說:
命该如此。
吴思成說:
我同意。
九娃:
这地方有好收成了。
吴思成說:
我看见那些草垛了。
九娃說:
还是个出细粮的地方。
吴思成說:
全是麦草垛。
九娃和吴思成又商量了一阵,就定了主意。
九娃给瓦罐說:
你去把那头驴卸了。
又给其他几个說:
把死人搭到驴背上,驴认识路,会驮着死人进村的。
他们问:
咱们呢?
九娃說:
驴进村一袋烟的工夫,咱也进。
他特别叮咛要让死人的屁股朝上,看见的人首先看到的是他马蜂窝一样钻满铁砂的屁股。
他们立刻紧张起来了。
土枪手也很紧张。
九娃拍了一下土枪手的肩膀,說:
别紧张,你给咱往土枪里装火药装铁砂,我看着你装。
他真蹲在了土枪手跟前。
他說:
你得把打兔的姿势改一下了,要改成直瞄。
一阵锣鼓唢呐声从坡底下的村子里传了过来。
瓦罐拍了一下驮着尸体的那头驴。
它挪动蹄脚,下了土台。
九娃他们也骑上了他们的驴背,模样都变成了驴队纪律要求的那种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