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军工体系崩盘地原因.docx
《前苏联军工体系崩盘地原因.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前苏联军工体系崩盘地原因.docx(1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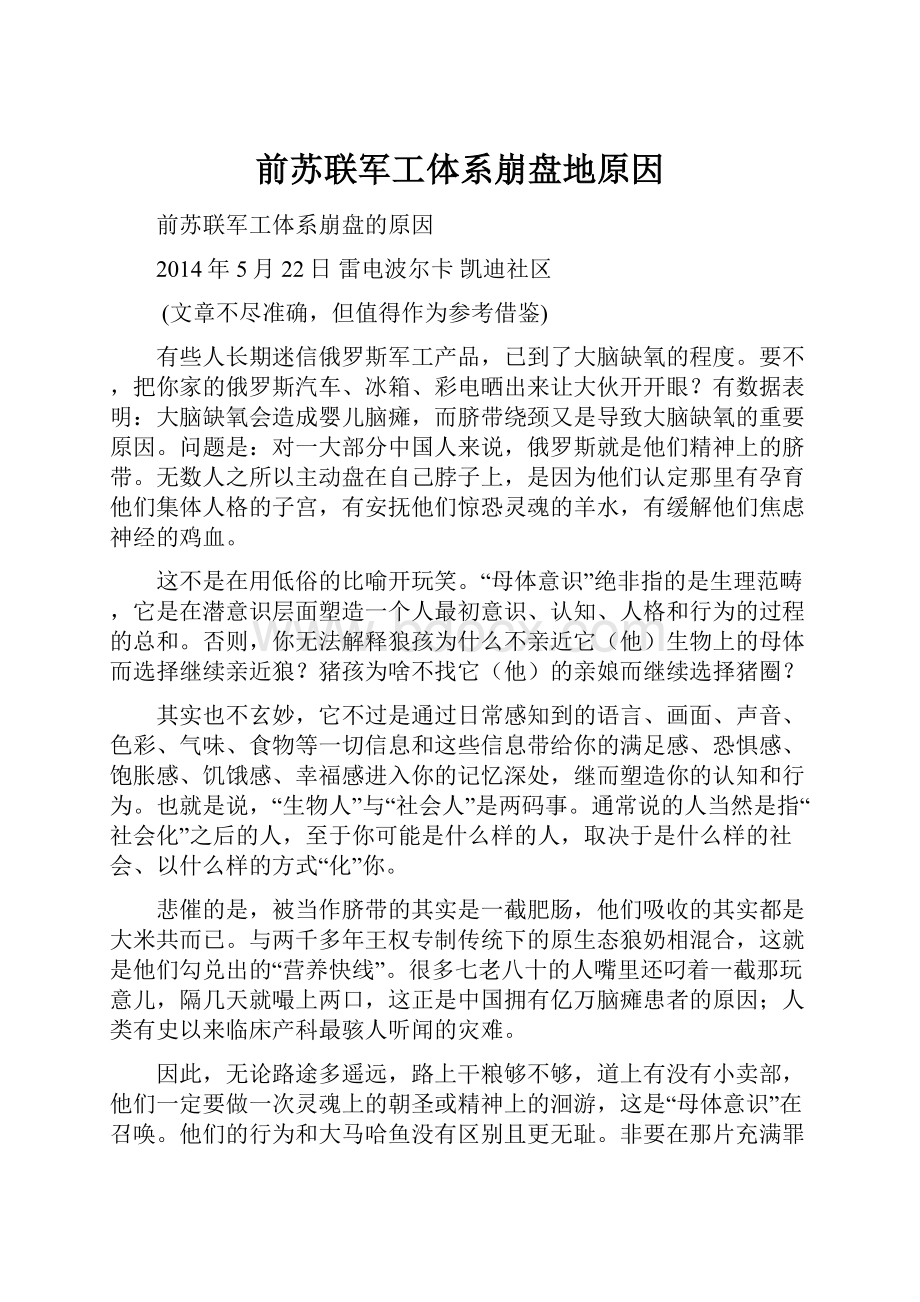
前苏联军工体系崩盘地原因
前苏联军工体系崩盘的原因
2014年5月22日雷电波尔卡凯迪社区
(文章不尽准确,但值得作为参考借鉴)
有些人长期迷信俄罗斯军工产品,已到了大脑缺氧的程度。
要不,把你家的俄罗斯汽车、冰箱、彩电晒出来让大伙开开眼?
有数据表明:
大脑缺氧会造成婴儿脑瘫,而脐带绕颈又是导致大脑缺氧的重要原因。
问题是:
对一大部分中国人来说,俄罗斯就是他们精神上的脐带。
无数人之所以主动盘在自己脖子上,是因为他们认定那里有孕育他们集体人格的子宫,有安抚他们惊恐灵魂的羊水,有缓解他们焦虑神经的鸡血。
这不是在用低俗的比喻开玩笑。
“母体意识”绝非指的是生理范畴,它是在潜意识层面塑造一个人最初意识、认知、人格和行为的过程的总和。
否则,你无法解释狼孩为什么不亲近它(他)生物上的母体而选择继续亲近狼?
猪孩为啥不找它(他)的亲娘而继续选择猪圈?
其实也不玄妙,它不过是通过日常感知到的语言、画面、声音、色彩、气味、食物等一切信息和这些信息带给你的满足感、恐惧感、饱胀感、饥饿感、幸福感进入你的记忆深处,继而塑造你的认知和行为。
也就是说,“生物人”与“社会人”是两码事。
通常说的人当然是指“社会化”之后的人,至于你可能是什么样的人,取决于是什么样的社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化”你。
悲催的是,被当作脐带的其实是一截肥肠,他们吸收的其实都是大米共而已。
与两千多年王权专制传统下的原生态狼奶相混合,这就是他们勾兑出的“营养快线”。
很多七老八十的人嘴里还叼着一截那玩意儿,隔几天就嘬上两口,这正是中国拥有亿万脑瘫患者的原因;人类有史以来临床产科最骇人听闻的灾难。
因此,无论路途多遥远,路上干粮够不够,道上有没有小卖部,他们一定要做一次灵魂上的朝圣或精神上的洄游,这是“母体意识”在召唤。
他们的行为和大马哈鱼没有区别且更无耻。
非要在那片充满罪恶的大地上着床不可,哪怕是宫外孕都在所不惜!
这大概是“下贱胚子”这个词的来历。
所以,郭沫若声称斯大林胜过亲爷爷,绝对是一件符合科学的事情,因此郭老才能当科学院院长。
请不要取笑科学,也不要取笑郭老。
过去的苏联到底发生了什么?
2009年新华网援引一片长文,题目是“俄罗斯军工科研面临毁灭性现状,苏联遗产已耗完”。
2012年俄罗斯《报纸报》报道:
以生产AK-47突击步枪扬名的“伊热夫斯克机械制造厂”宣布破产。
该报指出:
“如果不找到问题的症结,俄罗斯军事工业的彻底崩盘或将为期不远。
”俄另一份杂志却道出了残酷的真相:
“导致俄军工企业集体没落的根源并不在外部,从苏联时代延续至今的深层次体制问题才是关键。
”
结论好下,但未必人人能体会到“从苏联时代延续至今的深层次体制问题”究竟是什么。
概括说,从宏观经济体系到微观的企业治理结构、管理体制、运营效率、发展潜力等等方面,没有一样是做对的。
为此,不得不加入大量碎片化的历史细节、案例和数据来尝试回答这些追问:
前苏联制造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庞大的战争机器
“前苏联与军事有关的设施总面积有4200万公顷,约占整个国土面积的2%”。
这个面积略低于瑞典或伊拉克的面积,大于日本或德国的国土面积。
苏联的军工企业分别隶属于国防、航空、机械、通信、无线电、造船、电力、核动力8大部(有的又称为9大部门),上级机关是国家军事工业委员会。
“到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共有134个武器总装配厂、3000余个部件和分系统生产厂,能生产150余种重要的武器系统。
民用工业部门中,约有60%的民品工厂从事军品生产。
有50个主要的武器设计局,民用科研所中有近1/2从事与国防有关的应用研究或基础研究。
”
1988年,《真理报》载文指出:
“苏联国防工业从业人员达1300万,每年生产的作战飞机相当于美国空军全部飞机的总和,平均7小时造出1枚导弹,坦克年产量2000辆以上…”
这是一组怎样的天文数字?
正如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说:
全国只有两三个人可以接触军工综合体的数据资料,“我们都明白不堪重负的军费开支对经济的影响是多么严重,但只是在当了总书记之后,我才了解了国家军国主义化的真正规模。
原来,军费开支所占国家预算的比例并非16%,而是40%!
250个亿的科研总经费中,将近200个亿都用于军事设备的研制。
”
人类从未象苏联一样生产出如此规模的武器。
它完全配得上另一个新国名:
苏维埃“军国主义”联盟。
“世界革命”军工厂的一本烂帐:
前苏联建立了如此庞大的军工集群,当然不止是自用。
它一开始就是彻头彻尾的“世界革命”军工厂。
从战前的西班牙、东亚某国,到战后的东德、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古巴、尼加拉瓜、格林纳达;从北非到南亚和中北美洲,统统接受过苏联的巨额军事援助,从人员到图纸,从零件到成品•••
上世纪三十年代起到解体的60多年中,前苏联到底对外输出了多少军事物资?
其供应链到底有多长?
早就是一本烂帐。
所有供应链加在一起会不会到达月球?
你就展开想象的翅膀猜去吧。
对苏联来说,军火本身更是推行政治和外交的手段和工具,至于能获取怎样的经济回报,是能收回工钱、料钱还是本钱?
那更是一笔烂帐了。
物质财富的总量毕竟是有限的,一方面超额了另一方面势必匮乏,不难想象的是,如此长时间跨越了3-4代人,普通国民过得是一种怎样艰辛困顿的生活?
国民财富全固化到军火里去了,每人手里都是一堆铁疙瘩,但谁手里也没有面包。
被誉为“四流作战能力、一流逃命能力”的米格-25,为改善发动机性能,需要在进气口喷水和乙醇的混合溶液以增加进气密度,米格-25机组经常贪污水箱里的乙醇兑酒喝。
米格-25机组比一般战斗机机组还要昂贵,可见苦逼、匮乏到什么程度。
顽疾难治:
永远尿不在一壶
看看俄罗斯自己的权威说法:
2008年,俄罗斯在研究航空工业整合过程中有一个这样的结论:
“在固定翼飞机领域,苏霍伊、米高扬、伊留申、图波列夫等设计局都已形成自己设计、试验和生产的独特方向和经验,这些设计局都在争夺联合飞机制造集团(OAK)内部的技术和行政领导权,以至于集团的核心领导层至今没有确定”。
听着一本正经、文质彬彬的哈?
沿着这条线再往前捋:
从1999年开始,北方造船厂和波罗的海造船厂为中国的两艘改进型“现代级”驱逐舰订单争得你死我活,最终单子落到北方造船厂,直接导致倾向于波罗的海造船厂的俄副总理克列巴诺夫去职。
扯来扯去2002年终于开工。
全俄1800多家军工企业参与了这两艘新舰的建造。
直到2005年12月才交付,这就是东海舰队的“泰州”号和“宁波”号。
为争夺联合企业的领导权,各军工厂大打出手,甚至闹出人命:
“2003年,‘金刚石-安泰’防空联合体刚成立不久便爆出丑闻,新任CEO的热门人选克里莫夫在自家门前遭枪击身亡,案件至今仍是悬案。
这些被硬‘捏’到一起的联合企业,内部矛盾重重而难有作为,被俄军寄予厚望的S-500防空系统,历经10年研发,至今难见踪影。
”
和别人尿不在一壶也就罢了,自己和自己还尿不在一壶:
即使在苏-27/30出口高峰期的上世纪90年代,苏霍伊内部也为了抢订单而自相残杀:
“传统上专业于双座教练型的伊尔库茨克推出了单座型苏-30MKI;而传统专业于单座型的阿穆尔共青城却造出了双座型苏-30MKK。
”一个系统内部之混乱和饥不择食可见一斑。
尿不在一壶的根源是什么?
上一贴说了苏联航空工业领军人物的狗血命运,这一切显然不是孤立存在的,也不仅仅是“上行下效”那么简单。
在相互撕咬与恶斗方面,他们绝对属于“久经考验”!
个个“作风优良”,确实是长期斗争积累下的“宝贵财富”。
《苏联的心灵》在描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时就有这样的记录:
“革命的狂热分子发现,革命意欲创建的那个新的世界不知何故并没有实现,于是开始寻求解释、追查罪魁祸首、寻找替罪羊,把它归罪为这群或那群执行者或支持者的懦弱和背叛,断言革命处于生死关头,并开始‘猎巫’,如今则发展成一种恐怖运动,在这个过程中,形形色色的革命团体不断进行相互残杀,整个社会处于一种丧失起码的社会黏合剂的危险之中。
”
以至于“全体人民就好像永远都在疲于奔命,而且左左右右、步履维艰,个人能否保全自己取决于他是否准确地感觉到中央权力机关何时会下达前进或后退的命令,以及他是否能够迅速调整自己转向新方向,时间的把握至关重要。
”看来,要诀也是盯死、关注、紧跟!
《苏联的心灵》中,帕斯捷尔纳克讲了一个故事:
“一个人跑来要他在一封声讨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的公开信上签名,帕斯捷尔纳克拒绝了并解释了拒绝的原因,那人听后失声痛哭,说诗人是他见过的最高尚最神圣的人,还热烈拥抱了他;但随即他便径直去找秘密警察告发他。
”
假如告发仅能带来利益却不能带来危害,也未必会这么做;但如果不这样做可能带来巨大的危险:
有人“告发”他“没有告发”,他就有了大麻烦。
不行动你就没有“组织性、纪律性”,至于行动的方式是撕咬还是恶斗,是造假还是撒谎,悉听尊便。
也不论对内还是对外。
就像作家们讨论的结果:
“任何扇西方资产阶级文化‘耳光’的行动,无论何种形式:
只有是抨击西方体制、打击它的士气、瓦解它的道德和美学基础,本质上都是一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表现,新的文化监控者就不加干涉”。
假如你不行动,就意味着“组织”本身非常危险,你当然就是“组织的敌人”。
曾经的一号人物马林科夫说:
“如果你不把别人踩死,别人就会把你踩死并让你永世也不得翻身。
”这是曾经一号人物说的话!
尽管如此,也不能笼统将其概括为俄国人的“本性”如此,这也是一种非常糊涂的看法,这和人的真实“本性”毫无关系:
如果把所有种族、国家的新生婴儿放在一起,你还能断言哪个有哪样的“本性”吗?
假如把这些婴儿交叉互换呢?
所以,区别在各回各家之后发生。
显然,这一切都是由组织行为和组织逻辑决定的。
它是“组织”的“本性”而非“人”的“本性”。
所有人的行为都是被组织塑造的结果。
与长年累月的血雨腥风相比,七八十年后的俄罗斯军工系统发生这么点小摩擦,简直是风和日丽的下午:
令人心旷神怡。
什么是传说中的“体制僵化”?
媒体报道说:
“最惨的1996年,俄陆军只有5辆坦克入役;即便是如此可怜的产量,也需要几百家工厂同时开工来凑那几辆坦克。
仅有的一点资金犹如撒胡椒面,根本不够确保生产线运转,而后者一旦关闭,重启的费用更加昂贵。
2006年,俄打算向东亚某国出售伊尔-76运输机和伊尔-78加油机,谈判结束后,惊觉多个生产工厂已经瘫痪,合同总价还不够恢复产能,这笔交易只能打了水漂。
”
“计划经济体制下,各军工厂分工非常细致,以T-72坦克为例,合作生产单位就有700多家。
”这已经不能说僵化了,简直就是僵尸。
奇葩的“设计局-工厂”联合体模式
苏联独有的“联合体”模式只能让人愤怒。
这种让一部分人只设计而不参与生产的制度安排,比让一个母亲只生育孩子而剥夺其抚养权还要罪恶。
工业的起码常识是设计、生产、服务、反馈是一个闭环的完整逻辑。
设计是一部分怎么能独立在体系之外存在呢?
就像我们不能想象:
技艺精湛的传统手工大师如烧瓷、制陶、漆器等,让他只关注设计而不参与生产,其荒谬性一眼便知;而苏联则生生把一条完整的链条剁成几截。
美其名曰“计划经济”。
专权下的经济与奴隶社会有分别吗?
以此造成的恶果是,苏联生产的任何工业品,你看不出有什么灵魂,军品民品无一例外,令人作呕的远不止其设计之粗暴、工艺之粗糙,最让人愤怒的是你分明看出设计者对其没有任何感情!
完全没有!
网上有过一个帖子:
“卡式直升机做工之粗糙工艺之简陋令人发指”,这还是现在,其实完全可以追溯到七八十年前,这都是一脉相承的:
米格-1的发动机是水冷V12发动机,散热器就在座舱之下,飞行员坐在这个火盆上面十分痛苦,酷热难耐倒在其次,万一泄露或被击中,飞行员会被活活烫死!
“尽管水冷系统修改了17次,润滑油系统重新设计了14次,直到衍生型的米格-3停产,这个问题仍没解决”。
还是米格-1,座舱盖是侧面翻开的,令飞行员恐怖的是:
如果卡住的话,需要地面人员从外面打开,飞行员索性拆了座舱盖,宁可牺牲气动特性也得保命。
它的前身I-16也是如此,起落架设计缺陷经常打不开,没有液压驱动而需要飞行员手摇收放,没有一把子力气根本放不下来。
有时需要在空中做高G点机动,用惯性把起落架甩出来!
王牌试飞员契卡洛夫就被卡住过,飞机因机腹迫降而损害严重,所幸人没事;
苏系列就更搞笑了,从苏-7开始,双座教练型的设计“仅仅是把机身拉长,在原有座位后面再塞进一个教练席”,问题是后座视野大受影响,在起飞和降落时两眼一抹黑,于是设计者粗暴地给后座舱盖上装了一个潜望镜,为方便后座教官观察,这办法一直沿用到苏-25,连米格-29的双座教练机都装有潜望镜!
潜望镜还不算,米格-21PF还有后视镜呢,不知道是并线使还是移库使。
设计者也有话说呀:
嫌麻烦别开嘛!
96个开关排在一个面板上确实有点乱,但你多练就熟悉了,嫌苦别当苏联红军!
烫死就烫死呗,战争哪有不死人的?
不烫能叫发动机吗?
卡住就卡住呗,反正那又不是我,再说我设计的是战斗机,又不是游戏机!
怎么就你那么娇贵呢,看不清?
你要特别忠诚特别有责任,就不会觉得两眼一抹黑了。
二战期间,贝尔飞机公司有一款战斗机P-39“飞蛇”,美军对这种飞机评价甚低:
空间狭小,操作不便,逃生困难等等毛病一大堆,美国飞行员根本不愿意飞。
编成歌唱“不要给我39”。
援助给苏联后反而大受欢迎。
在苏联人眼里P-39的缺点根本就不是缺点!
设计是工业的源头,设计体系糟糕成酱紫,后面的结果就可想而知。
把“设计”和“生产”切开,最大的问题是责任和利益的丢失。
把本该是一个循环的整体,切成各自循环的子系统,各自向“人民委员”负责,而真正符合经济内在规律的链条却被切断了:
设计与用户的互动、设计与生产的互动、生产与消费的互动全部断裂;有用的信息全都处于丢失状态,关键是责任与利益之间的关联关系也被切断了。
再往下延伸到企业内部的部门设置,把本已切断的链条再次剁成碎末!
短时间还可以靠“建设热情”和“阶级觉悟”来粘合,时间一长,每个环节都无法尽责、尽力、尽利;全体怨声载道且理由充足,每个环节都声称自己不可或缺,都说自己付出太多而所得太少,尿不在一壶的制度性裂痕早已出现。
生产者对产品也没有感情
从生产角度看,这种指定工厂永远只生产一种或一类产品的“计划经济”,比指定一个人出生即为奴隶还要罪恶。
它不止是扼杀人的创造性,是把一个人的潜能在未激发出之前就阉割掉了,而且把制度性的“激发机制”也作为“无用组织”摘除了,把人的创造本能从肉身抽离出去,犹如摘除了心脏和大脑,只留下肉身,罪大恶极者非此莫属。
当然,对于他们来说这么做是对的!
因为他们压根就不希望你有创造性,他们连你思考的能力都不希望有,这是他们的组织行为背后的根本动机,所有“统一思想”的根本用意就在于此。
100年前,福特说过一句颇具幽默的名言:
“我只需要一双手,结果却来了一个人”。
这话被左棍和文痞们揪住不放,说资本家如何黑心:
将人异化为工具;其实哪里是那么回事?
这是人类第一次面对大工业生产时的管理困惑。
这个困惑当然是有积极意义的,因此福特在自传中详细描述了如何教“农民工”(原文说的就是农民工)怎样在工厂中学习技能,无数遍进行技术和管理优化,如何改善流水线,让流水线适应不同技能、不同身高的工人,甚至左撇子、右撇子都要区分。
你看,他确实仅需要一双手,但为适应“手”的主人“人”,工厂做了无数工作,其实福特明白一个道理:
你不把手的“主人”伺候好了,你得不到你期望的那双手!
接着优化岗位来招聘不同的残疾人,为让残疾人取得和正常人一样的工资待遇;然后探讨如何在农村就近建厂,以便让农民工在田间和工厂之间自由转换角色:
100年前的美国农民工,已经可以使用两种工具在自己的农田和工厂转换角色:
农闲时开着福特车上班、农忙时开着“福特森”拖拉机耕作。
也许还会追问:
这样下去活人不还是工具吗?
错!
福特在100年前就已经做到了:
任何岗位和工种,只要你做腻了,任由工人自由调换,你提出申请,就会根据你的特点安排培训,直到你能在新的岗位合格上岗;每人入厂时都要填“专长卡”。
“有一次我们需要一位瑞士钟表修理工,轻易地从专长卡里找到了这个人:
他在另一个车间开钻床”。
这倒要说说了,斯大林的工厂,一辈子基本上就在一个岗位上,与有选择权尝试不同的岗位相比,哪里的工人更像工具呢?
咱别抬杠中不?
与此相反,斯大林的工厂恰恰是:
来了一个人,却只留下了一双手。
分享:
分享到新浪微博分享到腾讯微博分享给朋友凯迪社区APP下载
延伸阅读|最新热帖
希特勒的,设计生产党卫军制服的HugoBoss[找神仙去05]
已获打赏(0)
还没有人打赏此帖,觉得帖文写的好,点击右边的按钮打赏。
打赏
赞(3)|踩|回复|引用|举报
回帖人:
雷电波尔卡手机绑定用户凯迪会员|只看此人|不看此人|2014-5-2023:
52:
45凯迪推出“云情报”新站点沙发
接上
整整100年前的1914年,福特因率先给工人大规模提升工资而轰动世界:
“日工资5美元起,工时从9小时调整为8小时”。
有个岗位只干一个程序:
用钢钩把零件放进一种油里摇一摇然后放在一个篮子里。
这个岗位不需要任何力气、技能和思考,有个工人在这里工作了8年,工头多次询问他愿不愿意换一个工作?
他固执地拒绝了。
“他工作了8年,用赚来的薪水继续投资,8年攒了4万美元。
”
老话说的好:
千金难买我乐意。
“乐意”即自主意志的自由表达,就不是强迫的。
一个人乐意去干一件事情,没有干不好的。
而所有被称为“安心本职工作”的,不但粗暴垄断了“工作”的标准和定义,而且分明要切除你自主意志的表达意愿,因此,“安心本职工作”的另一面是“安心为奴”。
很多人理解工业就是工人只负责生产即可。
不知道这种混账看法是从什么时候有的?
传染了多少人?
仅这一点认识误区就足以造就数亿脑残。
第一次工业革命之所以能在英国产生,除了英国工人普遍高工资、能源价格低廉等诸多社会背景以外,不止有几位大发明家这么简单,很重要的原因是“英国出现了一大批二流乃至三流的发明家”。
此观点也是当今西方史学界的广泛共识。
而二流、三流发明家发挥才能的场所,恰恰就是车间,他们在工厂里本就是技艺精湛的高级技师。
在工业领域尤其是重工业领域,天才的设计师和新入厂的学徒工都不重要,主力是40-50岁的高级工程师和高级技师:
再好的奇思妙想也需要他们一张图一张图去实现,再好的材料也要他们一炉一炉炼出来,然后一刀一刀车出来。
没有好的工艺和材料,一切都是零。
其实,真正牛叉的工业品,用不着最后造出来,高级技师们一看图纸心里就有数了:
是不是好东西心里有数,能不能按设计要求干出来心里也有数,而后者更加重要!
在这一点上,设计师也无能为力。
亨利•罗伊斯14岁就当学徒工,19岁就是利物浦一家工厂的总工。
21岁时和朋友凑了70英镑搞了个工厂。
很快远近闻名。
主要产品是电动机及工程机械。
直到约1902年,已近不惑之年的罗伊斯买了一台法国二手车,拆开发动机一看:
我靠!
这活儿比我和我的工人差远了!
查尔斯•罗尔斯第一次试驾罗伊斯的两缸车时误以为这是一部四缸车,激动地深夜跑去助手家:
“我找到了世界上最好的工程师”!
1906年,两人创办了那家举世闻名的企业。
而1300万苏联产业工人,生产的汽车是个什么样子呢?
正如前面的例子:
一辆坦克需要700家厂商配套,除了自己那份别的干不了。
现在觉得麻烦了?
那怪谁呢?
几十年的习惯下来,那份热情、那份功能早就做了绝育了。
高级技师和熟练工人搞发明,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本能。
这有什么好质疑的吗?
这就像高级厨师进了后厨,看见新鲜的肉类、翠绿的蔬菜和活蹦乱跳的鱼一样,他不可能不想贡献手艺,你让他一天到晚土豆丝、土豆丝;一日三餐揉馒头、揉馒头,他能不疯吗?
讽刺的是,高尔基也描写过沙俄时代的面包师:
如何诅咒这个工作,汗水都揉进了面里;社会主义了之后又如何有了积极性云云,高老师除了为舔菊而写出那些垃圾以外,哪里知道工业运行的本质呢?
苏联工人参与创造的可能性,从制度安排上就被切割出去了。
反而经年累月生产一种与他们的想法和生活毫无关系的产品,他们怎么可能对这该死的、万恶的、狗娘养的东西有感情呢!
?
再说,工人投入感情去生产、去改进工艺、去发明,能从用户那里取得回报吗?
思想产业链在细微处都处于扭曲和断裂的状态,任何人的思想都没有变现的方式和通道。
这一条,就是工业发达国家与其他国家的根本区别。
创作于二战前后,通篇都是与俄罗斯作家、诗人访谈的《苏联的心灵》,居然寥寥几笔记录了俄罗斯作家对工业的看法,看得我都快哭了,但人家是这么说的:
“技术官僚大行其道,以至于那里人满为患,相互内耗,产品中垃圾居多,有价值的创造不足百分之二十,转化为生产力的不足百分之一。
”
可持续落后的工业体系已经建成
“联合体”不“联合”,这就是苏联工业企业组织结构的真相。
两大环节和最终用户全部处于离散状态,一个“可持续落后”的工业体系就算建成了。
这种结构性的错误,注定苏联的工业将长期处于落后且越来越大,这可不是哪个部门、哪个行业或哪家企业就能改变得了的。
所以,米格-15出现在朝鲜半岛时,苏美在一个起跑线上,都是刚进入喷气时代,美国的F-80、F-84还处于弱势地位,北美公司推出F-86后才取得平衡。
从此一路拉开距离。
1976年,一个令敌对双方都意外的机会突然降临:
一架米格-25P叛逃到日本北海道函馆民用机场。
看来,天上确实能掉下馅儿饼!
当天即被大卸八块装进C-5A运输机运往千岁基地,一路高规格接待。
结果令兴冲冲地美国人大失所望:
他们被米格-25“让人匪夷所思的落后”震惊了,研究了67天,从里到外翻腾了一溜够:
结构、发动机、电子系统、雷达系统没有一样是先进的。
索然无味的美国人把米格-25散件“装了30大箱子还给了苏联”。
至今,俄美之间军机落后30年,民机落后40年的总体差距已经形成。
“军转民”转到晕头转向
1992年,俄政府出台了《国防工业军转民法》,“试图让军工企业自己养活自己。
然而习惯了吃大锅饭的俄军工企业既不懂得市场经济,又没有民品的技术储备,更缺少转型的启动资金。
没过两年,80%的军工企业转产失败,它们生产的冰箱、洗衣机、煤气炉工艺粗糙、外型笨拙,根本找不到销路,反倒丧失了最后的资金储备,落到连水电费都交不起的地步。
”
媒体的观点是:
“企业陷入了订单不足导致产能不足,又因产能不足导致没有订单的死循环。
军工产业成了喂不饱的‘吞金怪兽’,先拖垮了苏联,现在又将拖垮它自己。
”
这就对了!
一切都对了,因果的齿轮咬合上了:
丝毫不差!
这一切都不是凭空发生的,这两头不靠的僵死机制,早就决定了苏联工业整体的垂死命运,无可更改。
飞机和文章都是集体创作的产物
把“设计-生产”的链条切断后,设计人员就有充足自由度了?
妄想!
上一贴已说过:
苏式飞机在设计中“片面强调单项性能的极端化设计思想其实和各个设计局无关,原因来自对国民的极端压制和强力塑造”。
飞机强调单一性能,没有“均衡”的概念,统统是长官意志的产物:
说高速就高速,其他要素不管;只要完成要求的指标,就能“报喜”。
米格-25号称3马赫,但实际限制在2.8马赫以下,要求平时飞行不超过2.5;飞一次3马赫发动机就报废了;机动性也非常糟糕,过载被限制在4.5g,满载时只有2.2g,只能是“如履薄冰一样小心翼翼地飞直线”;片面强调速度油耗却增加了,“虽然米格-25起飞总重量40%是燃油,但作战半径仅为300公里”;或者是以牺牲载油量换取轻巧和高性能,米格-29即如此。
水货不止出自水里。
设计师也知道这样的思路是有缺陷的,但这是一个集体在承担上面的任务。
给上面说的是3,给飞行员交代是不要超过2.5,欺上瞒下,共同沉浸在谁也不能戳破的肥皂泡里,还是那个逻辑:
谁先戳破谁是大家共同的敌人!
因此,你说和不说都没有用:
一切会按组织行为的逻辑一步步演进下去。
飞一趟3发动机报废?
报废就报废呗,发动机不是有的是嘛!
制造了一堆极为昂贵的废物!
与苏联作协养活的那堆废物一样,他们认为:
“艺术作品必须是团队集体创作的,艺术批评、评论、随笔也是由一班评论家共同完成的,他们集体为作品承担责任,每一位成员只是整个社会无名的一分子。
他们认为,共产主义意味着坚信通过集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