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狸与刺猬.docx
《狐狸与刺猬.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狐狸与刺猬.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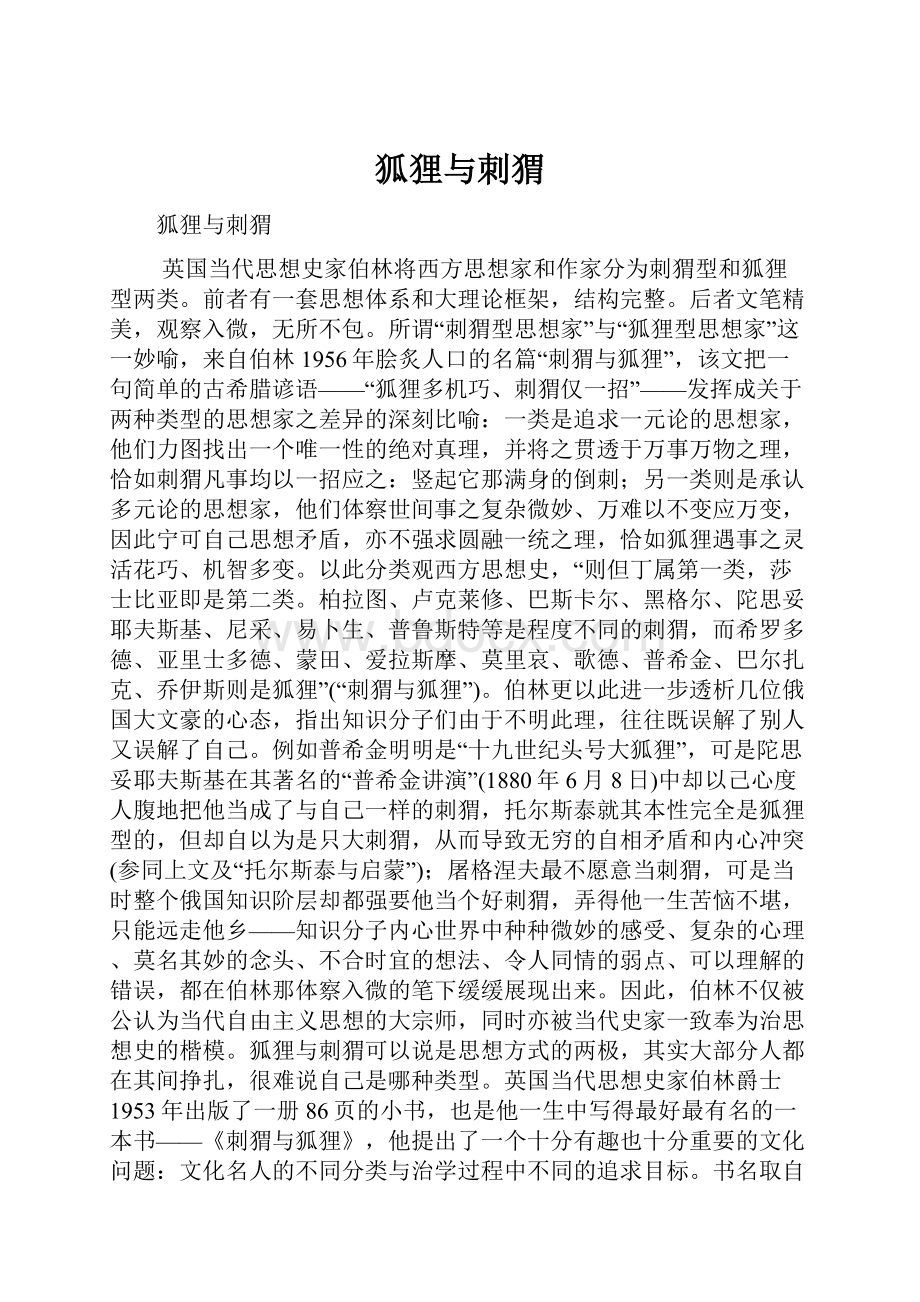
狐狸与刺猬
狐狸与刺猬
英国当代思想史家伯林将西方思想家和作家分为刺猬型和狐狸型两类。
前者有一套思想体系和大理论框架,结构完整。
后者文笔精美,观察入微,无所不包。
所谓“刺猬型思想家”与“狐狸型思想家”这一妙喻,来自伯林1956年脍炙人口的名篇“刺猬与狐狸”,该文把一句简单的古希腊谚语——“狐狸多机巧、刺猬仅一招”——发挥成关于两种类型的思想家之差异的深刻比喻:
一类是追求一元论的思想家,他们力图找出一个唯一性的绝对真理,并将之贯透于万事万物之理,恰如刺猬凡事均以一招应之:
竖起它那满身的倒刺;另一类则是承认多元论的思想家,他们体察世间事之复杂微妙、万难以不变应万变,因此宁可自己思想矛盾,亦不强求圆融一统之理,恰如狐狸遇事之灵活花巧、机智多变。
以此分类观西方思想史,“则但丁属第一类,莎士比亚即是第二类。
柏拉图、卢克莱修、巴斯卡尔、黑格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易卜生、普鲁斯特等是程度不同的刺猬,而希罗多德、亚里士多德、蒙田、爱拉斯摩、莫里哀、歌德、普希金、巴尔扎克、乔伊斯则是狐狸”(“刺猬与狐狸”)。
伯林更以此进一步透析几位俄国大文豪的心态,指出知识分子们由于不明此理,往往既误解了别人又误解了自己。
例如普希金明明是“十九世纪头号大狐狸”,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著名的“普希金讲演”(1880年6月8日)中却以己心度人腹地把他当成了与自己一样的刺猬,托尔斯泰就其本性完全是狐狸型的,但却自以为是只大刺猬,从而导致无穷的自相矛盾和内心冲突(参同上文及“托尔斯泰与启蒙”);屠格涅夫最不愿意当刺猬,可是当时整个俄国知识阶层却都强要他当个好刺猬,弄得他一生苦恼不堪,只能远走他乡——知识分子内心世界中种种微妙的感受、复杂的心理、莫名其妙的念头、不合时宜的想法、令人同情的弱点、可以理解的错误,都在伯林那体察入微的笔下缓缓展现出来。
因此,伯林不仅被公认为当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大宗师,同时亦被当代史家一致奉为治思想史的楷模。
狐狸与刺猬可以说是思想方式的两极,其实大部分人都在其间挣扎,很难说自己是哪种类型。
英国当代思想史家伯林爵士1953年出版了一册86页的小书,也是他一生中写得最好最有名的一本书——《刺猬与狐狸》,他提出了一个十分有趣也十分重要的文化问题:
文化名人的不同分类与治学过程中不同的追求目标。
书名取自古希腊诗人阿寄洛克思之语——“狐狸知道很多的事,刺猬则知道一件大事”,意思是狐狸机巧百出通晓百科,然不及刺猬一计防御与见解深刻。
伯林借此语将西方思想家与作家分作两大类型:
狐狸型与刺猬型。
狐狸型为百科全书型,无所不知无所不包,观察入微机巧四迸,然思想散漫缺乏深度,属于艺术型;刺猬型则有一中心主轴,建有一整套思想体系,有自己的理论框架,绵厚精深,属于思想型。
刺猬分泌原创性思想,总结归纳人类每一阶段经验的精华,编织全新的思想构架,提供解释世界的基础支撑点。
狐狸则辛勤地消化刺猬的思想成果,化高雅为通俗,适当补充刺猬原创体系中的不足,乃为“快乐的搬运工”。
狐狸型人物有:
亚里士多德、但丁、伏尔泰、莎士比亚、黑格尔、歌德、普希金、巴尔扎克、屠格涅夫、陀思妥也夫斯基、尼采、易卜生、托尔斯泰、乔伊斯;刺猬型人物有:
柏拉图、马克思。
伯林说托尔斯泰乃天生狐狸,却一心想做刺猬,到头还是一只狐狸。
此后,哈佛大学文学教授李欧梵写有“‘刺猬’”与“‘狐狸’”;威斯康辛大学史学教授林毓生写有“学术工作者的两个类型”;钱钟书在《管锥编》中也谈到刺猬与狐狸。
李欧梵说鲁迅是一只大“狐狸”,说他的文学技巧及反讽手法都是“狐狸性”的,虽然鲁迅的思想较一般作家深刻得多,但没有一套体系。
反之,李欧梵认为茅盾倒是一只“刺猬”,虽然文字与技巧不如鲁迅,但他每部作品都有一个大构架,如《子夜》浓缩了1930年代中国资本主义社会,体现了作者完整的宏观构思。
李欧梵认为中国古今作家中兼具刺猬与狐狸优点的只有一位曹雪芹。
为钱钟书作传的高晏先生认为钱钟书与托尔斯泰一样,是一只天生的大狐狸,但又一心想做刺猬。
成为狐狸还是刺猬,决定性因素恐怕还是天赋禀性。
性格奔放、兴趣广泛、指望“短平快”出成果者,怀揣“出名要早呀”的急迫,最终难逾狐狸之限。
能够升华进入刺猬级的,必得器局宏大,志趣高远,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甚至准备吃冷猪肉(身后受祭)。
当然,也有“刺猬”羡慕“狐狸”的。
哈耶克说如果自己是“困惑型”学人,与知道许多事情的“狐狸型”学人相比,他不愿只做“一个只知道一件大事的刺猬”。
其实,据笔者个人生活经历,在我们这个乾嘉学风余绪犹存的国度,敢于思考宏大课题,实在不易得很。
文学研究界向有如此“排序”:
一流学者搞古代,二流学者搞现代,三流学者搞当代,四流学者搞港台,五流学者搞海外,末流学者搞理论。
可见走向刺猬的第一步就阻力重重呢。
像李泽厚这样的当代一流学者,当年也曾遭到讥评:
“不扎实”。
他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后记中说:
“我也羡慕别人考证出几条材料,成为‘绝对真理’,或集校某部典籍,永远为人引用……据说这才是所谓‘真学问’。
大概这样便可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了。
但我却很难产生这种‘不朽’打算……这倒使我终于自暴自弃也自觉自愿地选择了写这种大而无当的、我称之为‘野狐禅’的空疏之作。
”从李泽厚的遭遇中,不难看出宽容的重要性。
说到底,不成“刺猬”,终究还可以成“狐狸”,若尽朝着“狐狸”努力,也许就没有一只“刺猬”了。
以赛亚·伯林与“狐狸和刺猬”说2012年09月16日16:
43
字号:
T|T0人参与0条评论打印转发犹太观念史家以赛亚·伯林(IsaiahBerlin,1909-1997年)近些年来在中国思想界与读书圈中,可谓名声卓着。
伯林的重要着作,除《马克思传》之外,已基本引进国内。
作为一个俄裔思想家,伯林的诸多论述,其论题都与俄国相关。
尤有代表性的文集,是《俄国思想家》。
该书最为经典性的篇章《刺猬与狐狸》,就是通过对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观念差异的论述,区分了两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及其对待世界的态度。
伯林讲,思想家分刺猬与狐狸两种:
刺猬之道,一以贯之(一元主义);狐狸狡诈,却性喜多方(多元主义)。
这就是伯林着名的刺猬与狐狸论。
这不是说伯林没有偏爱。
他有偏爱。
伯林爱的是狐狸。
所以,伯林常讲的,不是“刺猬型”的卢梭、黑格尔、谢林、马克思,而是冷门的“狐狸”们,如维科、赫尔德、赫尔岑等等。
在他看来,这些在当代世界早已被遗弃的思想家,才是多元自由主义、消极自由的最好实践者,是对抗按照一元主义方案设计的极权社会的最好良药。
伯林擅谈,关于两种自由的讨论,基本上隐藏在两个话题之中,其一为犹太人的身份与国家问题;另一个就是俄国知识分子的内在冲突与国家问题。
终其一生,念兹在兹。
我想,这两者,都和伯林的身份有一定关系。
俄国是伯林的故国,怎么理解故国兴亡?
如何看待“老大哥”的兴衰?
这是观念史家伯林最关切的,也是我们关切的。
伯林1909年出生于当日俄国的里加,后移居彼得堡,1920年举家移居英国。
对于彼得堡这座城市,伯林再熟悉不过了。
这座城市,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上四度更名,第一个叫圣·彼得堡,此名译自德语(SanktPeterburg),为彼得大帝钦定;1914年一战爆发,俄罗斯与德国鏖战东线,为了避嫌,彼得堡遂改成俄国名,成了彼得格勒;1924年,列宁逝世,彼得格勒又更名为列宁格勒,1991年,苏联崩塌,列宁格勒又改为彼得堡。
20世纪俄罗斯的历史,犹如伯林故国旧首彼得堡的名字一般,城头变幻大王旗,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恰好,高寿的伯林,全看见了。
怎么理解这个复杂的20世纪,需要从历史深处去寻找。
观念史家的办法,往往是从思想根源上来探讨问题的根源。
由此,不难理解伯林在《俄国思想家》中,一再阐发俄罗斯思想与文化界所谓“黄金时代”的人物(1840-1860年代),他将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作为生平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有此用意。
为什么伯林要去追溯遥远的十九世纪的黄金时代?
很清楚,伯林的心目中,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存在某种对立关系。
我的问题,不在于追究伯林的消极自由与赫尔岑贵族保守主义之间有什么样的渊源,我更乐意认为,按师承或问题排列的思想史追溯,未必是有效的。
赫尔岑晚年,关注农村公社问题甚于其他,显然伯林显然不会醉心于此。
伯林与赫尔岑,唯一吻合的一段时光,或许是1859年左右,赫尔岑沉醉在改革沙皇的美好想象时期。
综观伯林着述中关于俄罗斯的论题,一个有趣的现象值得注意。
伯林更关注的,是俄罗斯沙皇1905年改革前思想史与苏联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文艺思想界状况。
这中间,明显缺少一个连贯一致的环节,即1905年至1928年,俄罗斯思想界究竟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这是在是个很意外的缺失。
这个时期有一半的时间,恰恰是伯林在俄国的时间,通常来说,最初的知识与印象世界,是会给予人极深的印象。
不过,奇怪的是,伯林很少谈及,也没有专文论述这一段历史,或是或隐或显地讲了,但总是一笔带过。
一个思想家对其生平中发生重要影响的事件,取回避正面讨论态度,这是相当令人遗憾的。
但这不能不说,伯林对俄国革命没有“态度”。
伯林很有“态度”,对俄国大革命,一言以蔽之,是全盘否定。
按照伯林的论断,1917年大革命,是开启现代世界积极自由变成政治实践的“潘多拉魔盒”。
尽管“因”早就种植在了一系列欧洲思想家中了,但这个“果”,却结在了1917年。
那么,伯林的俄国论述的中心是什么?
显然,是一连串思想家及其圆点。
这个圆点,就是伯林回避正面迎击的1905至1928年俄国大革命。
假如,历史不是线性的,而是圆形的。
那么,或前或后,俄罗斯两个世纪的历史,都在围绕这个以革命为中心点展开。
今年是苏联解体二十年,自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历史学界似乎也陷入了一种讨论怪圈,或者选择1917年二月,或者选择1905年冬,但无论如何,都不是1917年10月。
尽管关于俄国大革命的历史讨论,已经基本上进入非实证性历史工作,而是政治化的辩论,关键问题仍然存在,俄罗斯不能回避这两个世纪的中心点,世界史也不能回避这个关节点。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关于十月革命前后,俄国诸多文学思想流派的作家的着述有较大规模的引介,其中不乏着述对大革命有所论断。
各家观点,不尽一致。
本文无意于概括各方论点,只从伯林的论述出发,讨论为什么伯林缺失了这一段思想史的观察,以及伯林对于俄国革命,究竟是什么样的态度。
刺猬与狐狸之争伯林对于俄罗斯兴衰的入题方式,同样是观念史研究。
在伯林看来,正是俄国知识分子对于一元政治观念不屈不挠的实践,才构成了俄国二十世纪的一系列政治悲剧,而二十世纪俄国的政治-文化实践本身,又以一元取消多元的方式展开,这就是伯林两本着作《俄国思想家》与《苏联的心灵》的主题。
观念的承担者,是知识分子;观念史,也就是18知识分子史。
《俄国思想家》,讲的是“刺猬”对“狐狸”的战争、俄国知识分子与帝国的冲突;《苏联的心灵》,讲的是国家对知识分子的压制。
我想,如果不是伯林在1990年代身体状况不允许,他必定还要写一本书,关于革命年代俄罗斯的新政治与及知识分子的烦恼。
可惜,这三部曲少了一部。
正是因为这或许缺失的最后一部,让人无法观测伯林对于俄国革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无论在访谈中,还是在着述中,伯林多次强调“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这个名词的特殊性,这是他理解俄罗斯思想与政治的切入口。
今天,知识分子大致是指受过高等教育的文职人员与技术人员,没有政治指向,很中性化。
不过在1917年之前的帝俄时代,这个词的意思就大相径庭了。
帝俄时代所谓的知识分子,前期是指受了教育,为人民福祉呐喊的人。
别尔嘉耶夫说,当十八世纪末期的着名反对派拉吉舍夫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中说,“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便诞生了。
别尔嘉耶夫的说法,倾向于贵族精英知识分子,甚至于带点宗教人道主义意味。
从真正的实践角度来说,十八世纪围绕沙皇周围持启蒙态度的“改革派”,能不能说是俄罗斯第一批知识分子,是可持疑义的。
或者说,别尔嘉耶夫的论断,缺乏社会学意义上的支持。
那么,关于俄罗斯知识分子诞生这个工作,伯林就做的完整的多了。
伯林在《俄国思想家》中,考证了知识分子一词的词源,正式产生于1870年代,具有很浓烈的道德诉求。
1860-1890年代,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19马克思主义各种流派相继涌入俄罗斯,基于不同的政治诉求,各流派之间不断搏杀。
“知识分子”这个定义,也就成了政治竞赛的词语工具,越革命,越“知识分子”。
到帝俄晚期,“知识分子”就和职业革命家划了等号,无论博学鸿儒,还是贩夫走卒,只要干革命,都是“知识分子”。
由此,知识分子这个词的意思,在俄国,从一开就不是简单的专业化术语,而是处在不断下降化、社会功能化的过程中,其涵义,随着时间变化越来越靠近“革命”。
但由此,知识分子这个词,在帝俄时代得面目不清,往往给人误解,知识分子似乎跟“文化”不沾边。
其实不然,帝俄时代,干革命的,多数还真属于“有文化”的:
无政府主义的主要成员,是贵族革命家;民粹派的主力,是平民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者,是新一代平民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有文化”,就享有“革命的文化领导权”。
按照伯林在《俄国思想家》中一再表述的意见,俄国社会是这样一个金字塔结构社会,上有沙皇--贵族地主小集团,有文化有权力,下有大批农奴--城市平民,没文化没权力。
这个金字塔帝国,没有英国式的有部分文化有部分权力的“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中间阶层作为缓冲地带。
所以帝俄的命运,只有两种,一种是农奴-市民被改革(1861年大改革、1905年大改革),另一种是沙皇-贵族地主被革命(1917年大革命)。
贵族地主的改革搞不好,就只有等人们来革沙皇-贵族地主的命了。
奇妙的是,恰恰是风云激荡的19世纪,沙皇放开了教育政策,稍稍有些社会地位的小市民,也能上大学,这就导向了1860年代平民知识分子阶层的崛起,帝俄主动培养了一个奇怪的中间阶层,即“有文化领导权没政治权力”的知识分子。
帝俄知识分子要闹革命,闹的不是文化领导权,而是政治领导权。
恰恰罗曼诺夫家族对政治领导权吝啬到无以复加,这是他的禁脔,他人不得染指,哪怕稍稍分享一点,也不行。
1905年,彼得堡知识分子领导市民卑躬屈膝向沙皇请愿,希望开民权开议会,其结果却是机枪扫射。
这是帝俄历史上的“黑色星期天”,1000多无辜市民殉难。
1905年之后,有文化的知识分子,无论是民粹派(社会革命党),还是马克思主义派(社会民主党),彻底明白了,和沙皇请愿请不到“政治领导权”,只有发动民众来夺取领导权。
在对知识分子词源的考订与历史语境的解释中,伯林讲清楚了他的苏联难题。
苏联怎么来的?
是这批革命知识分子不断实践的结果。
或隐或现,我们看到了伯林的结论:
“狐狸”都被沙皇逼成了革命党或者多愁善感的遁世主义者,所以解决问题,只能靠“刺猬”们了。
刺猬按照他们的办法,用“积极自由”的实践方法,创制“一元主义”的苏联。
刺猬当道,狐狸遁迹,这是十九世纪走向二十世纪俄罗斯知识界的趋势,其背后隐含的,是革命走向问题,有复杂的历史语境。
思想史的发展,往往并不按照一二高明哲人的指点前行。
对于1905年后的俄罗斯思想史,伯林同情俄国知识界的狐狸们的尴尬,批评刺猬们的高蹈。
伯林愿意谈米哈伊洛夫斯基、普列汉诺夫乃至于列宁这些“帝俄公敌”的失策,却不太愿意讲俄罗斯1905年给狐狸们出的难题,这是他的政治立场给他带来的理论盲区,同时也是其政治立场所无法解释的误区。
实际上,1905年之后,俄罗斯思想界的对抗性政治,进一步加剧。
与此相配合的,是知识分子的政治空间日益被压缩。
斯托雷平出任俄国首相的时代,是政治上高度集权的时代。
在明的压制与暗的对抗之中,1905年之后的历史走向,已不难猜测。
历史不能采取一种单纯的道德谴责来加以批判,如果真存在“刺猬”按照“一元主义”构建苏联这一事实的话,那么,沙皇的“一元主义”显然更为残酷与苛刻。
关于俄罗斯大革命及其问题,并非三言两语就能得出,这也正是我接下去讨论的问题
文化与革命党国家化1917年,按照伯林的说法,是“刺猬”们赢得了革命。
但革命的影响力,显然不至于苏联,非但如此,1917年俄国革命还激荡起中欧的革命浪潮,甚至于给一战后一代西欧知识分子以极大冲击。
怎么回应这场法国大革命之后欧亚大陆上最猛烈的革命浪潮,给深具保守主义传统的英国知识界出了道难题。
18世纪英国保守主义对于法国大革命的文化批判,是在这样的前提上展开的,即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预设的启蒙前景,看起来固然美好,而其事事仰仗理性的设计,却违背历史、自然乃至于人性,根本上来说,理性设计最大的弊端就是不懂历史、不通人性的“没文化”表现。
伯林深谙保守主义,其“消极自由”观,显见是受了保守主义的启发。
苏联有没有“文化”建设成就,对伯林来说,不是单纯的“文化问题”,而是“政治成败”问题。
1945年,伯林得到一个以外交部人员造访苏联的机会。
能近距离观察苏联,对此,伯林深感欣慰。
伯林没有辜负此行,他带回来革命后俄国知识界的报告(《斯大林统治下的俄罗斯艺术》)、帕斯捷尔纳克与阿赫玛托娃的近距离观察以及对阿克梅派诗人命运的思考(《一位伟大的诗人》、《与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的交谈》、《鲍里斯?
帕斯捷尔纳克》),这就是《苏联的心灵》的主要内容,也是该书副标题所揭示的--“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伯林在《斯大林统治下的俄罗斯艺术》一文里说,1928年斯大林上台之前,苏联文艺界还是掀起了一股实验主义的高潮,甚至于给世界艺术创作以持久性的影响。
1928年,形势就急转之下了,渡过了叶若夫(内务人民委员,大清洗执行人)恐怖时代的俄国文化界在1939年的状态,“就像一个被战争摧毁的地区。
只有一些宏伟的建筑仍然相对完好,孤独地矗立在一片片废墟和荒野之上”,俄国知识界的精英,不是自戕或大清洗,就是卑躬屈膝苟延残喘。
还剩下“宏伟建筑”帕斯捷尔纳克,神经质,讲话前言不搭后语,生活在对国家既爱又恨的矛盾之中;而阿赫玛托娃,依然骄傲,却连发表诗歌的权力也没有,日丹诺夫诬蔑其为“圣女加婊子”。
据伯林的观察,阿赫玛托娃就像是“悲剧中的女王”。
1928年,就是伯林对于苏联能不能“有文化”加以辨析的分界线。
1917年的革命在经历十年的战争、内部权力斗争之后,执政党从党派路线斗争的工具,转化为国家机器。
党-国一体化的要求,不仅要取消敌视的反对派,而且要取消自身的反对派。
在这场取消运动中,文艺界的反对派,如阿克梅派,首当其冲。
其次是取消自身的反对派,如对于拉普的打击、1928年之后建作协等等体制化运动、大清洗等等。
在这场数十年的取消运动中,不仅在沙皇时代不得不转向多愁善感的“狐狸型”诗人被打击,连刺猬们,也难以幸免。
按照刺猬理念建立起来的苏联,在集权化的过程中,同样反对刺猬。
表面上看,不合情理。
《苏俄文化》一文中,伯林慎重地谈了这个问题,伯林说,“思想争论会激发出人们的批评精神,所以对于那些陷入权力斗争的政权来说,思想争论要比信仰各种独裁主义更危险”,苏联的党-国一体化,就要取消所有意识形态的辩论,刺猬与狐狸,殊途同归。
斯大林的取消政治辩论以及文艺辩论的最佳手法,是树典型。
典型就是典范,不可置疑,比如马雅可夫斯基的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方法。
在伯林看来,通过讨论苏联的“文化建设”的失败,已经说明他的政治判断了。
整个苏联的历史,确实越来越朝向“没文化”的轨迹上行进。
伯林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
但伯林的质疑仍是单向度的,他把问题抛给了苏联,却没有自省。
1970年代,索尔仁尼琴被“没文化”的政权驱逐出国后,面对西方世界的前来听他演讲的朝圣者,说出了他的感受,资本主义的复制世界腐烂至死,美国民主是“荒唐胡闹”,科学技术是“罪恶之源”,跟苏联一样的“没文化”。
也就是说,在索尔仁尼琴看来,现代社会及其政治,都处在衰败之中,非仅苏联。
1990年,欧东剧变,伯林写了篇短文,题为《不死的俄国知识阶层》,是为《苏联的心灵》的最后一篇。
伯林说,他很高兴,他又看见俄国1815-1830年代的贵族俄国知识阶层在俄国又复活了。
1990年代,索尔仁尼琴归国,对俄国现状大为不满,撰文说,俄罗斯坍塌了。
言下之意是,非但“文化”没了,连“国家”都塌了。
伯林主张回到贵族知识阶层的传统,求得“消极自由”的大智慧。
索尔仁尼琴却说,不仅苏联要清算,连彼得以来所有的西方传统和西方本身,都要清算,只有尼康大主教(1652年出任大主教)以前的传统,才是好的。
尼康大主教以前的传统是什么传统?
是东正教传统的神权政治。
伯林讲的,还是启蒙的政治,是启蒙政治中的右翼观点。
在索尔仁尼琴看来,启蒙的政治理念,无论是贵族的,还是平民的,都是一丘之貉,是现代“没文化”政治。
所以,他就沿着斯拉夫主义的路线,干脆就讲信仰的政治。
伯林要的,是不革命,是1840-1860年代。
而索尔仁尼琴所求的,与站在革命两翼的现代性全然无关。
两位讲“文化”的苏联反对派,两位都带点保守主义意味的作家,现都已作古,想必身前死后,都很难握手言和。
(转:
本文原名为《伯林和俄国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