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话之输入与日本早期自撰诗话.docx
《中国诗话之输入与日本早期自撰诗话.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国诗话之输入与日本早期自撰诗话.docx(1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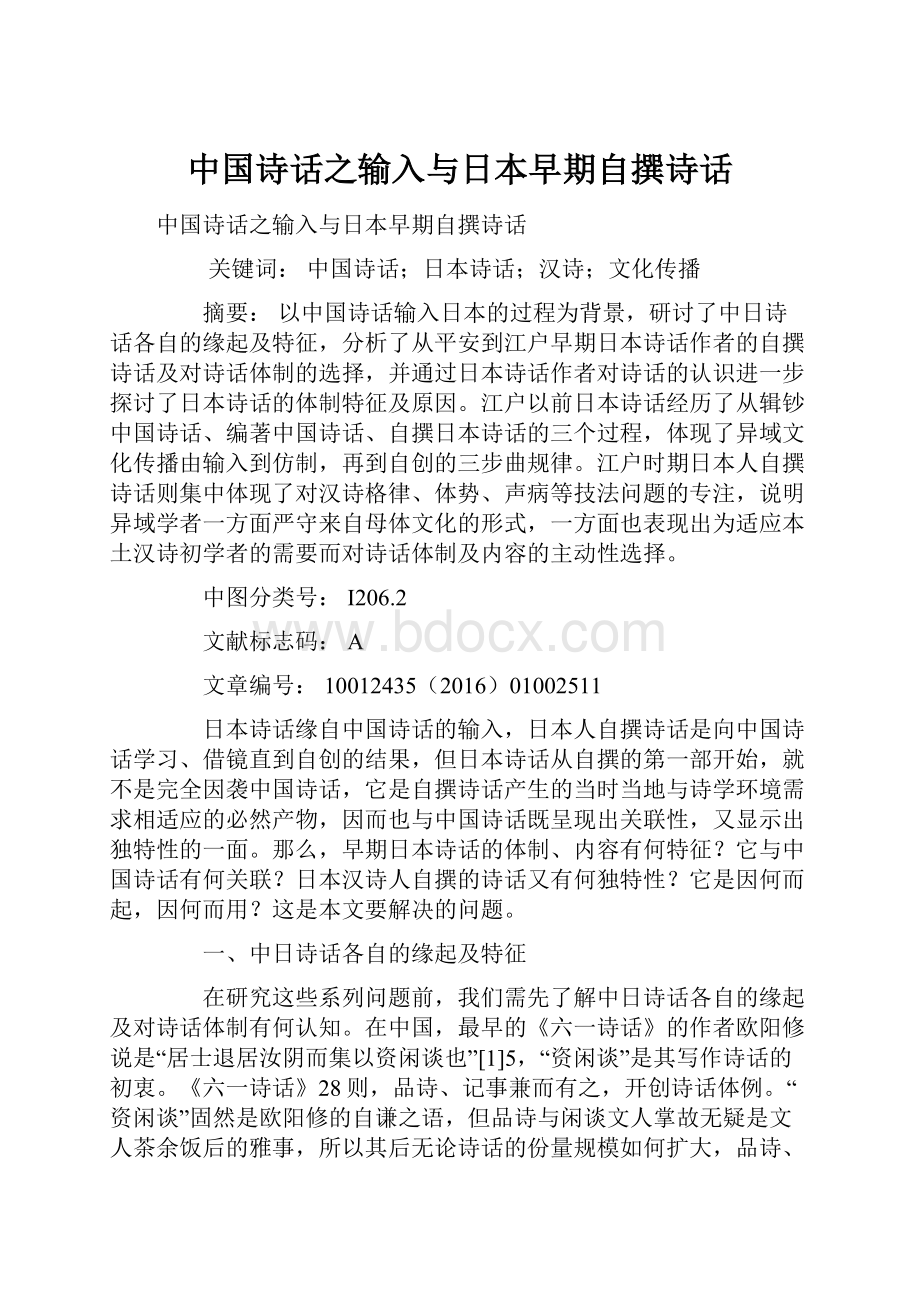
中国诗话之输入与日本早期自撰诗话
中国诗话之输入与日本早期自撰诗话
关键词:
中国诗话;日本诗话;汉诗;文化传播
摘要:
以中国诗话输入日本的过程为背景,研讨了中日诗话各自的缘起及特征,分析了从平安到江户早期日本诗话作者的自撰诗话及对诗话体制的选择,并通过日本诗话作者对诗话的认识进一步探讨了日本诗话的体制特征及原因。
江户以前日本诗话经历了从辑钞中国诗话、编著中国诗话、自撰日本诗话的三个过程,体现了异域文化传播由输入到仿制,再到自创的三步曲规律。
江户时期日本人自撰诗话则集中体现了对汉诗格律、体势、声病等技法问题的专注,说明异域学者一方面严守来自母体文化的形式,一方面也表现出为适应本土汉诗初学者的需要而对诗话体制及内容的主动性选择。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6)01002511
日本诗话缘自中国诗话的输入,日本人自撰诗话是向中国诗话学习、借镜直到自创的结果,但日本诗话从自撰的第一部开始,就不是完全因袭中国诗话,它是自撰诗话产生的当时当地与诗学环境需求相适应的必然产物,因而也与中国诗话既呈现出关联性,又显示出独特性的一面。
那么,早期日本诗话的体制、内容有何特征?
它与中国诗话有何关联?
日本汉诗人自撰的诗话又有何独特性?
它是因何而起,因何而用?
这是本文要解决的问题。
一、中日诗话各自的缘起及特征
在研究这些系列问题前,我们需先了解中日诗话各自的缘起及对诗话体制有何认知。
在中国,最早的《六一诗话》的作者欧阳修说是“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1]5,“资闲谈”是其写作诗话的初衷。
《六一诗话》28则,品诗、记事兼而有之,开创诗话体例。
“资闲谈”固然是欧阳修的自谦之语,但品诗与闲谈文人掌故无疑是文人茶余饭后的雅事,所以其后无论诗话的份量规模如何扩大,品诗、记事一直是诗话之体的应有之义。
比如张戒《岁寒堂诗话》、严羽《沧浪诗话》增加了阐述诗理的成分,但品评诗艺、记录文坛掌故的内容依然存在。
说明诗话之体“论诗及辞”与“论诗及事”(章学诚语)为一物之两面,不可缺一,这是我们判定诗话的产生及体制的基础,也是讨论诗话缘起的前提。
讲到中国诗话的起源,章学诚将之推原到钟嵘《诗品》,谓其有论诗及辞者,又推原至唐人孟?
さ摹侗臼率?
》,谓其有论诗及事者[2]559。
及至何文焕编《历代诗话》、丁福保编纂《历代诗话续编》,亦在起首相继编入钟嵘《诗品》、释皎然《诗式》、孟?
ぁ侗臼率?
》等著。
但何、丁之编及章氏之说,更应看作是推究诗话之源头,非定论南朝至唐代,诗话已然成体。
诗话之成体,从名实二者而言,无疑仍以欧阳修《六一诗话》为标的,这在郭绍虞《宋诗话辑佚》序中,已有详细论述。
由于本文所论以中日诗话为核心,不能不考虑产自中土,又在日本产生广泛影响的诗格、诗法一类的著作。
从南朝以至晚唐五代,虽无狭义之诗话,却有数量不小的诗格、诗法一类的诗学著作产生。
它的繁盛期有明显的阶段性,约而言之,南朝、初唐、中唐、晚唐五代及元代,是诗格、诗法类著作集中出现的时期。
起初这类著作是一个独立的系列,以研究及规定各种诗律声病及诗体诗格为主要目的,并不宜归属在诗话之列。
但明以后在诗家及历代目录学家眼中,渐与狭义诗话合流,成为广义诗话的一部分。
事实上,自何文焕编辑《历代诗话》总集起,后来的多种诗话集均收录诗格、诗法类著作。
日本凤出版社的《日本诗话丛书》中也有大量的此类诗话,说明将诗格、诗法类著作归属于诗话是一个虽不科学却有广泛共识的现象。
因此,我们在讨论诗话问题时,会涉及到狭义诗话和广义诗话的不同情况。
关于中国诗话输入日本的问题较为复杂,如从广义的诗学方面而言,输入时间甚早。
由于孔子在《论语》中多有对《诗经》的评论,所以说中国诗学之输入,从弥生时代《论语》被引入日本时就开始了。
其后从奈良到平安早期,随着《毛诗》《文选》的输入,中国的诗学理论(如《毛诗序》《文赋》)就开始为日本人所熟悉,编辑于公元8世纪中期的《怀风藻》里有一篇序言,其中说:
“调风化俗,莫尚于文;润德光身,孰先于学?
”[3]60这样的文字与理论显然来源于两汉魏晋以来中国的诗学思想。
至于诗话的输入,最早的一部是为大家熟知的释空海的《文镜秘府论》,它大约在弘仁七年(817)就已编辑摘钞成书,“输入”日本,其所提及的中国诗论,除了引述中国南朝以来沈约、王斌、刘善经、刘滔、皎然、元兢、王昌龄等人论述诗文声病、体势的诗格诗式类著作以外,还有孔子《论语》、《毛诗》、陆机《文赋》、挚虞《文章志》、沈约《宋书?
谢灵运传论》、萧子显《南齐书?
文学传论》、《魏书?
文苑序》、梁太子《昭明文选》、钟嵘《诗品》、殷?
[《河岳英灵集》等多种也被其称引过,另从该书序言看,他还应读过《文心雕龙》。
可见日本汉诗界自平安时期以来就广泛接触了众多的中国诗学著作,尤其是被后世归入诗话类的诗格诗法型书籍。
我们拟以成书于日本最早的三部诗话为例进行讨论。
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三部诗话间隔均在一、两百年以上,体例各不相同,一部为丛撮重编中国诗律学著作的《文镜秘府论》,一部为日本人自撰的第一部以汉诗诗律为主要内容的诗格类诗话《作文大体》,一部是日本人自撰的第一部以论中国诗为主体的《济北诗话》。
三部诗话均有典型意义,也非常符合异域文化传播由输入到仿制,再到自创的三步曲规律。
《文镜秘府论》是一部既不被中国人视为中国诗学的著作,又不被日本人视为日本诗学的著作。
盖因其书是由日本人所编辑,成书于日本,但其内容又来自于中国。
受当时中国类书形式的影响,空海将带回日本的中国多种诗学著作重新编排,分为天、地、东、南、西、北六卷。
此书虽是辑录性质,但对日本汉诗界具有非凡的意义,日本人(尽管是少数)首次可以集中在一部书中了解汉诗格式、韵律、体势、技法等。
此著另一个具标志性的意义,即显示了日本人在面对诸多中国诗学著作时,更倾向于了解汉诗的格式、韵律及声病等方面的问题,对诗格诗律方面的著述更感兴趣。
这当然与日本人虽然早已接受中国文化影响,但对汉字读音及声律毕竟较为隔膜有关。
同时,它也成为此后日本自撰诗话的一个明显的走向。
虽说《文镜秘府论》昭示了日本诗话此后的走向及特质,但空海此著对日本汉诗界所发生的影响是渐进的,历时也很长。
《文镜秘府论》之后的百余年间,未见日人自撰诗话。
据现存文献,仅有大江朝纲、藤原宗忠等编于天庆二年(939)的《作文大体》或可称为广义诗话著作《群书类从》文笔部另收有《童蒙颂韵》一书,但此类蒙学之书似不宜归入专门诗学著作,故不论。
,此书有《群书类从》本及观智院本等,是迄今可见最早的日本汉诗诗律学专书。
全书可分唐诗与日本汉诗两部分,第一部分分论唐代近体诗含五七绝、五七律近体的字数、句数、对仗、平仄(按:
大江以“他声”指仄声)、韵律、声病等体格声律方面的问题,并引诗为证。
第二部分据说由藤原宗忠所著,内容系以日本汉诗来复核唐人近体格律。
虽说此书的体例与《文镜秘府论》相异,且由大江、藤原等自编,但从书中内容看,编者参考过白居易的《白氏文集》、元兢的《诗髓脑》、王?
钡摹吨遂弊邮?
格》等著,对中国唐代诗律非常熟悉,且能运用这些诗律校准此前日本的汉诗人如庆宝胤、纪纳言长谷雄、菅文时等人的近体律绝,可见《作文大体》所总结的唐人近体格律至少在平安时代中期已经为日本诗人所知悉并能熟炼运用。
大江朝纲在该书序中说:
“夫学问之道,作文为先,若只诵经书,不习诗赋,则所谓书橱子,而如无益矣。
辩四声详其义,嘲风月昧其理,莫不起自此焉。
备绝句联平声,总廿八韵,号曰倭注切韵。
”《作文大体序》,见?
U保己一、太田藤四郎等编《群书类从》卷第137之《文笔部》第16,东京,续群书类从完成会,昭和三十四年版。
疑《作文大体》原为大江朝纲与藤原宗忠所撰的独立的两部小册子,后经人合为一书。
从其序言看,编者不仅重视诗赋,而且对汉诗声律相当熟悉,并总结出日本汉诗的28韵,号为“倭注切韵”。
大江朝纲等撰《作文大体》晚《文镜秘府论》122年始出,从文中引用的中国典籍来看,不排除其中诸如《诗髓脑》等文献来自《文镜秘府论》,但除此之外,从著书体例到其他内容,找不到更多证据说明大江此书受到了《文镜秘府论》的影响,二者更像是长江、黄河,各有源头。
至于《文镜秘府论》为何没有对此后两、三百年的诗学著作产生影响,主要在于此著编辑完成后,限于钞本形式,流传不便,长时间内仅在寺院留存,为寺人及声韵学者阅读。
到了江户时期的宽文年间,此书有刻本出现,才开始在文人中流传。
小西甚一在《文镜秘府论考》的序说部分考证空海大约在弘仁七年(817)编成此书,直至江户后期,提及《文镜秘府论》的著作共有34种,其中仅有6种属于诗学著作,其他均为韵学书,说明在悠久的历史上,《文镜秘府论》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对诗学产生过重要影响。
这6种诗学著作,多为诗律、诗格、诗法一类的书。
最早的是观智院本的《作文大体》,写于平安末期,约在公元939年左右。
其次是僧印融的《文笔问答钞》,编写于室町时期的文明年代(约1469-1478)。
其他4种均写于江户时期,如明和七年(1770)的《淇园诗话》、天明六年(1786)的《诗辙》、生活在江户中期而生卒年不详的长山贯所著《诗格集成》及天保五年(1834)赤泽一堂的《诗律》。
这几种书,只是部分提及或引用了《文镜秘府论》的文字,据小西甚一观察,现存观智院本的《作文大体》也仅在卷尾部分手抄了一点,而其他版本中未见,并猜测这仅有的文字也是后人添加的。
因此小西甚一在文中认为:
“总之,平安时代《文镜秘府论》还没有广泛流传。
”[4]小西甚一的结论,当然有其道理,尤其是在《文镜秘府论》仅有抄本而无刻本的江户以前,由于流传不广的原因,未能对汉诗界产生影响,是可信的。
但作者仅以后世著述中有无引述《文镜秘府论》的原文作为其影响力的唯一论据,则失之于偏狭。
尤其江户以来,《文镜秘府论》有了刻本,相信有更多的人阅读了此书,其中相当的汉诗人他们只作诗,不写诗学著作,当然也就无从考察他们是否受到过《文镜秘府论》的影响。
此外,室町以来,日本人西游中土更为方便,中国的书籍东渡日本也有了更多的渠道,即便对中国诗律的了解学习不从《文镜秘府论》获得,也可从众多的其他来自于中国的诗学著作中取汲。
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大江朝纲的《作文大体》虽说未见更多的《文镜秘府论》的内容,却也同样能较熟练地运用中国诗律学。
《作文大体》面世两百余年后的镰仓时期,僧人虎关师炼(1278-1346)用汉语写成《诗话》(后称《济北诗话》或《虎关诗话》),这成为日本人自撰狭义诗话的第一部,也成为日本诗话史中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我们前面考察了两部输入型诗话及自撰诗格型诗话,它们主要的关注点在于中国诗的声律、格式问题,而虎关的《济北诗话》在体例和内容上,更接近于宋以后由欧阳修所奠定的诗话类型,即以“论诗及辞”与“论诗及事”为主要特征,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超越《六一诗话》,具有南宋以后中国诗话析理论事的特点。
《文镜秘府论》及《作文大体》的编者目的主要还是为了方便日本人了解并学习汉诗,两位编者均以唐诗作为汉诗的标杆来崇仰,尚未有胆量和“资格”对产自异域又是自己文化母国的汉诗评头论足。
到了《济北诗话》,这一局面发生了变化。
它既是日本人自撰的诗话,同时也是日本人首次在诗话中对汉诗及汉诗人进行褒贬品评,同样具有重要的标志性。
虎关生活的年代相当于中国南宋末祥兴元年至元朝的至正六年,在日本相当于镰仓后期到南北朝的前期。
在书中,虎关没有谈及他撰写这部诗话的动机,但从背景而言,两宋以来,大量中国诗话传入日本,他阅读过不少这类著作,在《济北诗话》引述的文字中及被直接提及的中国诗话著作有《六一诗话》《古今诗话》《庚溪诗话》《苕溪渔隐丛话》《?
q斋闲览》等数种。
但显然,仅仅这一背景并不能说明这就是他写作这部诗话的动机。
在《日本诗话丛书》该书的解题中,或能看出一些他的思想背景。
该题解记载,虎关曾对宋代以来大量日本人渡海西行中国甚为不满,称其行为是日本人的耻辱[5]。
这样一种想法,当然体现出虎关强烈的民族自立意识。
宋元时期,中日文化的对比,仍以中国文化占主导优势。
但随着留学制度的改变,日本学人开始更多更方便地接触中国文化。
我们知道,自平安时代前期(895)日本政府就废除了已实行260多年的遣唐使制度,至此以后,接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人员构成发生了变化,即由原来的遣唐使变成了僧侣和个别游学之人。
当时,僧侣流行到中国寺庙学习,据日本《本朝高僧传》载,镰仓、室町两朝的高僧111人,除本身就是宋元归化僧以外,剩余的五分之一以上的高僧都有留学中国的经历,其中少则两三年,多的甚至达到二三十年。
这些人在中国与中国诗人交往学习,并通过他们将中国当时最好的诗人诗作快捷地传入东土,而东土的日本汉诗人对中国诗坛的认识和中国诗人也是基本同步的。
这促进了日本汉诗人渐渐升起的自信心,吉川幸次郎曾说:
他们的著述,采用与当时的中国,即元、明文化人完全相同的体裁。
其本身即表明,日本人欲与中国人在同一竞技场上比赛,并且也具备了这种能力。
[6]
联系到虎关此前对大量日本人西渡中土的不满,恰可以说明镰仓后期至室町时代,日本文化自立的倾向开始出现。
当然,这种自立倾向欲转化为一种自立的成果,必有待于具大魄力人物的出现,而虎关师炼就恰恰是这样的人。
《济北诗话》的形式虽然完全沿袭中国诗话,但是其采用像空海大师那样辑录中国诗话的形式,还是采取自撰的方式,却显示了不一样的胆识。
它说明在经过长时期的输入消化之后,日本也有具魄力的学者能够用文化输入国的著作形式撰写同类型的著作。
对其意义更具敏感性的无疑是其本国的学者,吉川幸次?
?
的上述评论,无疑有一种为本民族文化自立的自豪感。
事实上,《济北诗话》作为第一本日本人自撰的诗话,虽然形式与中国诗话相同,但仍具有不同寻常的标杆意义。
而且,这部诗话在内容上也有不少值得称道的地方,一是有其基本的诗论系统,超出了欧阳修《六一诗话》“资闲谈”的格局。
在中国诗话中,除了少数几种理论性较强的诗话外,多数诗话中作为“资闲谈”的各种文人轶事、文坛掌故占了很大份量,论述诗理的内容往往是吉光片羽。
而《济北诗话》则很少“闲谈”方面的内容,它似乎更加“严肃”。
构成这部诗话的基本内容大概就是三部分,或论述诗理,或品评诗人诗作,或考证诗文悬疑。
就其理论主张而言,也有一些新的提法。
比如他主张诗要“适理”,讲求诗的“性情之正”与“醇美”,提出“童子之心”,这一话语系统虽然来自于中国,但对诗的主张并非完全因袭当时在中国流行的理论,他提出的诗应有“童子之心”,远比明代李卓吾的“童心说”来得要早,而且之前日本汉诗界基本没有自己的诗论体系,所有一切都来自中国,虎关的用语虽然仍是中国式的,但其理论却在揉合了理学家的思想基础上,有自己独立的诗学主张。
二是他重点讨论的诗人,包括陶渊明、杜甫、李白、王安石等,都有他自己的看法,最突出的是对陶渊明的评价,与北宋以来陶渊明在中国诗坛地位上升的情况不同,虎关很尖锐地指出陶渊明人格的缺陷,显示出他独出机杼的批评意识。
三是他对杜甫的推介,被誉为日本杜诗研究的开山之祖,扭转了平安朝以来独尊白居易的风气。
这些都表现出虎关在接受中国诗学的同时,力图与中国诗学“角力”,有新的创获和独自的评价。
而这些理论、评价,又直接影响甚至是开创了五山文学的新局面。
这一点,在学界是有共识的。
它反映出中国诗学在向日本输入的同时,日本汉诗界力图将之本土化的努力,也是外域文化长期输入以后出现“自创”的一种质变的开始,在日本诗话史上是一部标志性的著作。
二、江户早期诗话体制的选择
到了江户时期,在相隔三百年后,又一本日本人自撰的诗话出现,这就是林?
馑?
编撰的《史馆茗话》,但这部篇制短小的诗话实际上是无心自得,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林?
獾母盖资强砦哪昙涞闹?
名学者林鹅峰,因此林?
庾孕∮辛己玫暮貉?
修养。
这部诗话其实是林氏父子二人协力的成果,也是一个偶然的情况所造成。
当时林鹅峰正在编《本朝通鉴》,林?
庑?
助他父亲做些资料搜编的工作,搜编资料之余,林?
庖擦粢馐占?
有关中国诗方面的材料。
当时共辑出42条,可惜他英年早逝。
在他过世后的第一年即1667年,时值康熙六年,他的父亲林鹅峰补58条凑足百则行世,使林?
獬晌?
继虎关师炼后,江户时期第一位自撰诗话的学者。
这部书与《济北诗话》最大的不同有二,一是如其书名,以茗话闲谈为主;二是主论日本汉诗而非中国诗。
林鹅峰在这本书的跋中说:
本朝中叶以来,缙绅之徒,唯游倭歌之林,不窥唐诗之苑。
故世人不知中叶以前不乏才子,其蔽至以诗文为禅林之业,可以痛恨也。
[7]
作者批评了江户以来日本汉诗界的两种弊端,一是近代文人写作汉诗只在日人的圈子钻研,不知研习唐诗;二是不了解江户以前本土诗人中已有相当杰出者,而误以为五山僧侣才会写诗。
所以,林氏父子在书中摘录了不少嵯峨天皇至平安朝菅原道真、大江朝纲、桔直干等日本汉诗人的名句,记载了诸多日本汉诗人的趣闻轶事,还有历史上日本诗人、僧人与中国文人的交往并受到中国人赞赏的事例等。
意在说明自嵯峨天皇以来,汉诗人阅读了大量唐诗选本,精心揣摩中国诗人的做诗技法,使得日本诗人也写出过不亚于中国的汉诗。
该书体例秉承欧阳修《六一诗话》,以轻松闲谈的方式记录嵯峨天皇以来历代日本汉诗人的优秀诗作及轶闻趣事,虽说理论上没有太多建树,但对江户以前日本汉诗界优秀诗作的品评讨论,以及指出这些优秀诗作与唐诗的关系,客观上起到了倡导学习唐诗纠正镰仓、室町以来五山诗僧独占诗林风气的效果。
因此,该书的编撰虽无直接、强烈的主观意图,但结合林鹅峰跋语,可以看出它仍有应对现实的客观需要。
《史馆茗话》在日本诗话编撰史上跟《济北诗话》一样具有标志性意义,它在日本诗话史上系第一部专论日本汉诗人的诗话著作,而后者虽属第一部日本人自撰的诗话,但内容上仍以中国诗人为评述对象。
在《史馆茗话》中,林氏父子在叙述中日诗人诗学交往时,常常表现出大和汉诗人可与中土诗人角力的自立意识,与《济北诗话》一脉相承。
其开创性在于用诗话之体来论述本土诗人,同样表现了日本早期诗话在经过输入、仿制以后,自主创作本土新诗话的努力。
《史馆茗话》之后未几,相继出现了几部专论诗格诗法的诗话。
如果说《史馆茗话》的出现有些偶然的话,后几部诗格类诗话的编撰发行,却有一定的必然性。
这个必然性,即指此类诗话面向的是汉诗初学者,满足的是这个时期大批涌现的汉诗习作者的需求。
首先是《诗法正义》,由石川凹(丈山)用日文撰写,它见著于1684年,晚于《史馆茗话》(1667)发行,但考虑到石川丈山卒于1672年,此书的编撰年代应该更早。
石川这部书的份量不大,中文与日文参半,特别有意思的是在同一段文字中也会出现中日文各半的情况,这是否反映了日本汉诗人在接受中国诗话过程中所出现的奇特现象呢?
又该书的性质与贝原益轩的《初学诗法》类似,先论作诗大要,次举律体平仄格式,再谈作诗之法,并泛举前人论诗之语。
这部书虽然篇幅不大,但其内容及汉日文参半的体例形式,无疑亦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我揣摩,编者之所以掺入日文,是为了方便汉语水平低的读者学习汉诗。
其后,这类书籍渐渐多了起来,编写及出版时间也变得密集起来。
比如梅室云洞的《诗律初学钞》,出版于1678年,也是一部谈诗律格式声病的书,从内容看,它受晚唐五代及元代诗法诗格类书的影响很大,每种体式均论其意格、句法上虚实的起承转合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部完全用日文写成的诗话,从石川的汉日兼半到全由日文写成,似乎完成了诗话由中转日的脱胎换骨。
而且内容多系梅室云洞自撰,从体制到内容,都受了晚唐五代以来诗法诗格一类著作的影响。
一年后,贝原益轩作于1679年的《初学诗法》也出版了,从这本诗话的书名我们即可知道,也是一部面向初学者的书,从内容上看,同上述两种诗话相类,也是专论诗法诗格。
贝原益轩是一个儒学者,与名儒木下顺庵、伊藤仁斋等人同时。
此书除个别段落为贝原自撰外,多数内容系辑录中国诗话的论诗之语,面向的读者也是汉诗的初学者,虽没有太多个人的创见,但该书在辑录中国历代论诗之语时,所涉及的语料既有宋元以来各种诗话,还有大量的史籍、笔记、文集序跋、文人书信。
作为日本人所编写的诗话,这是江户时期第一部较全面论作诗纲领、诗体格式、作诗技法的书。
其意义在于全面开启了日本汉诗人撰写有关诗格诗法类型诗话的大门,奠定了日本本土诗话多以诗法诗格为主要内容的基本特色。
这以后,江户汉诗人撰写了十数部有关诗法方面的著作,对象亦以汉诗的初学者为主。
如果说在平安后期大江朝纲编撰以诗律声病为主的《作文大体》尚具偶然性的话,江户早期百年间陆续面世数种诗法、格律类的诗话就有一定的必然性。
首先从宏观方面考察,“关原之战”德川家康取胜后,实施幕藩体制,对外锁国,对内实行身分制度。
这些铁腕政策,获得了较长时间的政治稳定,经济也有了较大发展。
原本处于社会底层从事商业活动的“町人阶级”渐渐富裕起来,形成了所谓的“町人文学”,社会中的多数人摆脱文盲状态,具备了基本的写作能力,使得其中不少人有了从事汉诗写作的环境及条件。
从文化方面来看,江户早期已开始有新的气象,随着德川家康执政理念的实行,改变织田、丰臣两代马上得天下而无暇于文化的局面,形成江村绶在《日本诗史》中所说的“广募遗书以润色鸿业”的文化盛世出现,儒学尤其是朱子学开始兴盛,诗文、小说、绘画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在印刷出版界,虽然早在16世纪传教士已将印刷机械引入日本,丰臣秀吉又从朝鲜带回活字印刷技术,但这些设备技术的真正光大还是从德川时代嵯峨版、骏河版的印刷发行开始的。
大量和刻本书籍的印行,对著作人的诱惑巨大,对促进此期学者著书不能不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
进入江户以来,相继出现数种诗法诗格类著作,是因为社会文化下移,能识字读书的人多了,学习写诗的人多了,因此有了阅读诗法诗格书籍的需要,另外也跟出版技术的飞跃发展不无关系。
再从这几部诗话作者的经历来看,多有一段较长的隐居并专业汉诗的时间。
这几位诗话作者本身就是日本汉诗史上有名的人物,如编写《诗法正义》的石川丈山人称“日东李杜”,他本属德川家康部下的谱谍之家,亦武亦文,后因战中轻举妄动而失去官位成为浪人。
自1641年失职至1672年去世,长达30余年石川均在京都一乘寺过着隐居的生活,日以汉诗为娱,并与过往名士谈论唱和。
他编写《诗法正义》,除了与友人交流外,给习诗者提供读本也当是目的之一。
《初学诗法》的编写者贝原益轩与石川一样为儒学者,先习朱子学,后改换门庭。
哲学外,擅植物学、地理学、诗学。
贝原长寿,早年游历各地,70岁时隐居京都,直至过世,隐居长达14年。
江村绶《日本诗史》称“其所撰,不为名高,勤益后人”[8]221。
江村所称能勤益后人者,当也包括教人作诗的《初学诗法》一书。
从这些历史的和诗话作者个人的情形看,此期诗话偏于诗格、诗法类形式,无疑有其内在的必然性。
从以上我们选择的江户早期日本诗话来看,在文化的输入与选择接受中,它们各具特色。
《史馆茗话》最大的特点在于它论述的对象是日本汉诗。
从《济北诗话》的用汉语论汉诗,到《史馆茗话》的用汉语论日本汉诗,体现了一种飞跃。
而这两部诗话,都体现了日本诗话的自立倾向。
《诗法正义》的出现,显示出日本诗学者不再满足于通过阅读中国唐五代以来的诗法、诗格类的著作来学习汉诗,而是自编一本更适合日本人需要的同类型著作。
为此,编撰者在形式上也予以创新,就是采用了日汉兼半的语言形式,其目的也是为了适合文化水准低,汉语能力差的日本普通读者的需要。
稍后一年梅室云洞的《诗律初学钞》,更是完全由日文撰写,说明这已成为较普遍的市场需求。
因此,日本自撰诗话,一方面脱胎于中国诗话,从早期的《文镜秘府论》到镰仓晚期的《济北诗话》,再到《史馆茗话》《诗法正义》《诗律初学钞》《初学诗法》,从内容到形式,一方面有与中国诗格类诗话同质化的色彩。
另一方面,如果细细考察,日本诗话在接受中国诗话的同时,也在一步步地图谋自立和更新。
这在上述诗话的演进当中,有比较清晰的轨迹。
三、日本诗话家对诗话的认知
日本早期自撰诗话多为诗格类,有其必然性。
为了探讨这一必然性背后的原因,我们还可以通过日本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