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docx
《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docx(1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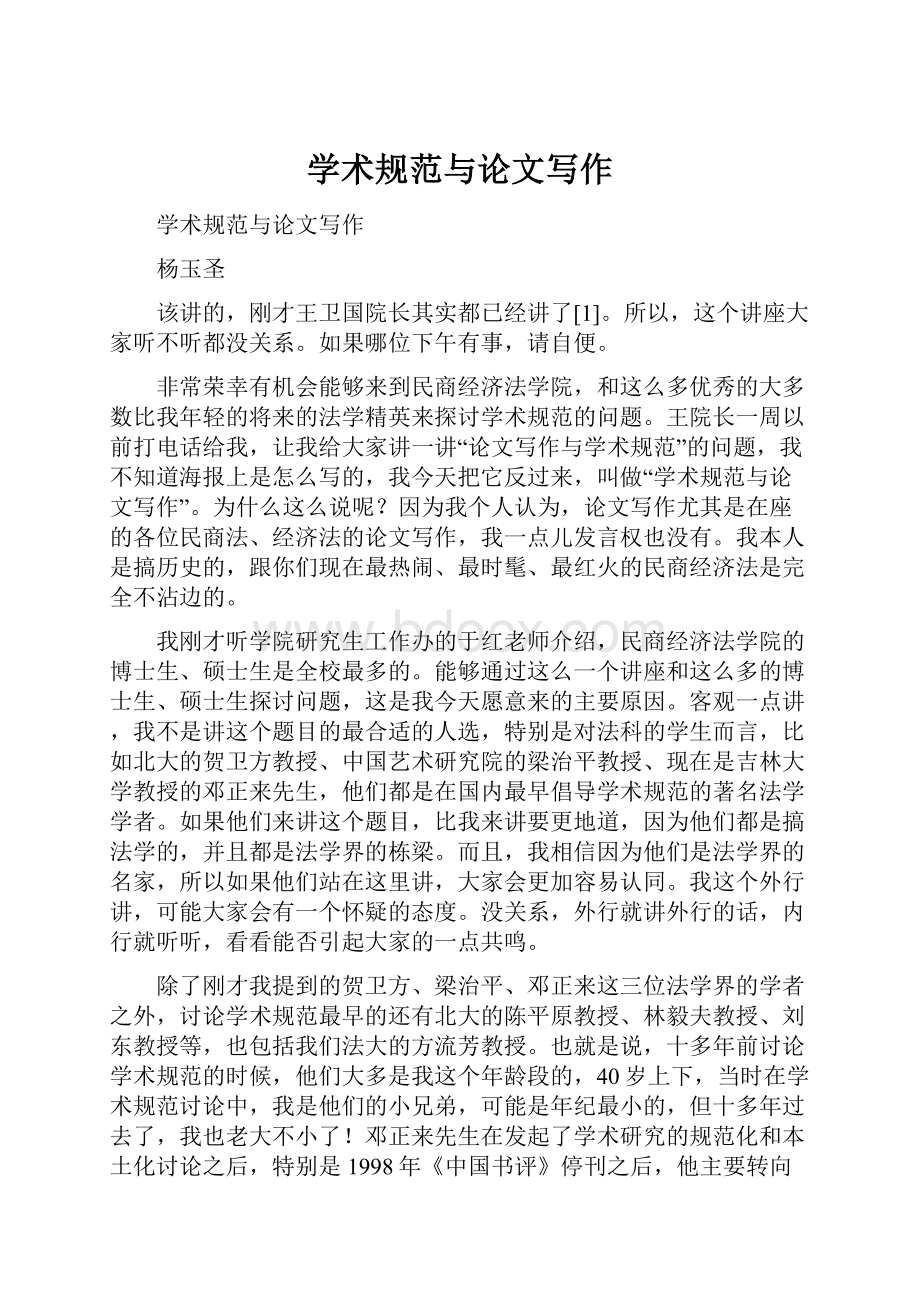
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
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
杨玉圣
该讲的,刚才王卫国院长其实都已经讲了[1]。
所以,这个讲座大家听不听都没关系。
如果哪位下午有事,请自便。
非常荣幸有机会能够来到民商经济法学院,和这么多优秀的大多数比我年轻的将来的法学精英来探讨学术规范的问题。
王院长一周以前打电话给我,让我给大家讲一讲“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的问题,我不知道海报上是怎么写的,我今天把它反过来,叫做“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个人认为,论文写作尤其是在座的各位民商法、经济法的论文写作,我一点儿发言权也没有。
我本人是搞历史的,跟你们现在最热闹、最时髦、最红火的民商经济法是完全不沾边的。
我刚才听学院研究生工作办的于红老师介绍,民商经济法学院的博士生、硕士生是全校最多的。
能够通过这么一个讲座和这么多的博士生、硕士生探讨问题,这是我今天愿意来的主要原因。
客观一点讲,我不是讲这个题目的最合适的人选,特别是对法科的学生而言,比如北大的贺卫方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梁治平教授、现在是吉林大学教授的邓正来先生,他们都是在国内最早倡导学术规范的著名法学学者。
如果他们来讲这个题目,比我来讲要更地道,因为他们都是搞法学的,并且都是法学界的栋梁。
而且,我相信因为他们是法学界的名家,所以如果他们站在这里讲,大家会更加容易认同。
我这个外行讲,可能大家会有一个怀疑的态度。
没关系,外行就讲外行的话,内行就听听,看看能否引起大家的一点共鸣。
除了刚才我提到的贺卫方、梁治平、邓正来这三位法学界的学者之外,讨论学术规范最早的还有北大的陈平原教授、林毅夫教授、刘东教授等,也包括我们法大的方流芳教授。
也就是说,十多年前讨论学术规范的时候,他们大多是我这个年龄段的,40岁上下,当时在学术规范讨论中,我是他们的小兄弟,可能是年纪最小的,但十多年过去了,我也老大不小了!
邓正来先生在发起了学术研究的规范化和本土化讨论之后,特别是1998年《中国书评》停刊之后,他主要转向了哈耶克的翻译和研究,陈平原教授主要转向学术史研究,梁治平教授主要转向法制史研究,卫方教授转向了司法制度改革的研究,而我呢?
傻人有傻福,一直坚持下来。
除了和张保生先生共同主编《学术规范读本》和《学术规范导论》外,还参与起草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并发起筹办了“首都中青年学者学术规范论坛”,草拟了《关于恪守学术规范的十点倡议》。
论年龄,我感到自己确实是老大不少了,比在座的大多数都要大十多岁,但还保持“童言无忌”的特点,是优点,更是缺点。
有些话,他们那些功成名就的人不便于说,那就由我来说,因为总得有人当主角,有人当配角,还得有人扮丑角——比如本人。
今天,我主要是围绕学术规范的基本问题跟大家做一个交流。
我讲五个问题:
第一,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谈学术规范,也就是为卫国院长讲的学术规范是学术的生命线做个注解;第二,从学术积累、学术交流和学术创新的角度来谈谈这个问题;第三,讲讲学术荣誉、学术责任和学术义务的内在关系;第四,简单谈一下如何把学术规范落到实处;最后,就学位论文写作做最简单的说明。
讲座的时间大概是一个多小时。
一为什么要讲学术规范
“学术规范”这四个字,通过2004年学者们的努力,还有教育部的推动,作为一个概念、一个名词,大家应该不陌生了。
原因就在于报纸、刊物、网络等作为主题讨论了很长时间,通过XX也好、google也好,搜索一下“学术规范”,会发现有几万条,当然这里面有很多重叠,还有很多只是涉及到这几个字的。
但不管怎么样,在十多年以前的时候,学术规范还只是极少数的中青年学人的边缘话题(大概二三十个人在那里说),但现在不同了,你说我说他说,众声喧哗,异口同声。
大家都知道,在中国,一件事情要想让大家知道、认同,并且转化为自觉的行动,需要经过相当漫长的曲折历程。
中国这么一个大国,人这么多,情况这么复杂,在别的国家容易办到的事,在我们国家往往是难上加难,难乎其难。
不过,就学术规范这个话题来讲,比我当初想像得要好,至少学界内外对学术规范的认同的时间要比当初预想的要快得多。
就像卫国院长讲的,学术规范是学术的生命线,是我们这些学者的生命线,为什么?
因为它是学术之所以能成其为学术、学者之所以是学者的基本前提条件之一。
我们有句话叫“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这是我们的古话,早就有人说了,而且我们大都耳熟能详。
这个“规矩”,放到学术语境里,就是学术规范。
现在我们在城市里面都知道有交通规则,学术规范说它深奥,它很深奥,说它简单,其实也不复杂,它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学术研究中的红绿灯。
不过,大家也知道,尽管红绿灯已经在中国有百年历史了,但无论是行人还是司机,闯红灯还是司空见怪的。
在座的,包括我在内,大概没有一个没闯过红灯的。
为什么?
因为大家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包括步行,包括骑自行车,包括开车,似乎都可以闯;许多司机还知道哪里有摄像头,有的话,就停下来,没有就闯过去,红绿灯形同虚设。
这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体验。
其实,学术研究也是这样,大家都知道有红绿灯,都知道有不少最基本的规范,但总是有一种侥幸心理,似乎能闯红灯就闯,而且闯了也白闯。
刚才,我听于老师讲,去年民商经济法学院有一个博士生没有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连百分之一都不到。
据我了解,北大的历史学系、中文系的博士论文答辩,要先预答辩,再正式答辩,预答辩可能要刷下五分之一左右甚至更多,有的博士生感到惶惶不可终日。
他们觉得很亏,因为在别的学校拿个学位很容易,而在北大中文系、历史学系现在却变得越来越难。
我跟这些朋友讲,表面上是吃亏,但实际上是获益,因为你获得的将是名副其实的博士学位!
就像卫国院长讲的,一个名牌大学培养的博士学位获得者、硕士学位获得者,能不能是“信得过”产品、能不能是“免检”产品?
我觉得这将是判定一个大学是否真正是名牌大学的主要标准,也是判断某一个专业是否是王牌专业的主要标准。
现在的情况还是以数量取胜,比如政法大学,不管怎么扩招,也不可能跟那些巨无霸式的大学相比,比如华中科技大学有6万人,而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浙江大学在数量规模上更是望尘莫及;再如,像我们这个大学,无论怎么盖大楼,也盖不过清华、北大,因为国家为这两个大学每年多开十多个亿的小灶。
但是,我相信单纯靠规模而不顾效益、强调数量而忽视质量的情况,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在中国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人才市场和学术市场,即将实现从规模到效益、从数量到质量的转型。
哪个大学在这个转型中把握住了机遇,也就在就业市场和学术市场中占据了发展的先机。
以法科为例,比如民商法、刑事诉讼法,我们政法大学能否培养出品学兼优的学术新秀?
我们的博士和硕士学位获得者能否成为政法大学名副其实的“拳头产品”和“免检”产品?
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卫国院长提的问题,可谓切中时弊,决非无病呻吟。
十年前,硕士学位获得者找一份体面的工作还是不难的,包括在北京。
十年后的今天,硕士学位甚至博士学位获得者,包括学法学的,想找到一份比较理想的工作已经不容易了。
这里的原因当然很多,但十年来硕士生和博士生急剧扩招的结果,确实是泥沙俱下,大家都有硕士、博士学位,都要找工作。
北京本地的找,外地的也来北京找,就造成了这种硕士毕业难就业、博士毕业就业难的“人才过剩”的形势。
我想,再过五年八年,单纯有个高级学位已经不灵了,而是要看是哪个大学毕业的、是哪个系科毕业的、导师是谁,这三个因素的作用可能会更重要了。
为什么?
就像我们的许多产品不过关一样,我们培养的有高级学位的人才,事实证明,也有不少不是放心产品。
我举一个例子。
十年前,在一批学界前辈的指导和支持下,我编了一套《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选的是1981-1994年的博士、硕士论文,共200篇。
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担心过这些论文会有抄袭剽窃的问题,而事实也证明这200篇论文在学术上基本上是信得过的名牌产品。
这套书在1998年初版,浙江教育出版社第二年就重印了,反映不错,于是他们就请我负责编辑该书的续编,主要是选收1994年到2000年的优秀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也选一部分1994年以前的),在专家推荐、作者投稿等多种方式初选的基础上,我最后选了150篇,当时我面临的最大的难题就是低水平重复和抄袭剽窃的问题。
大家知道,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特别是名牌大学的学位论文,从道理上讲,应该是免检的,为什么?
因为这些学位论文,既有导师的指导,又有作者至少一年多的时间所作的呕心沥血的努力,还有外部的专家评议、内部的专家答辩,校学位委员会把关,最后还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把关授予学位,按说学术质量应该是放心的。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比如,本来我准备收录一篇中国人民大学获得2000年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选的“百篇优秀博士论文”的经济学博士论文,作者也同意授权,并把论文电子文本传给了我,但我在编辑加工的过程中却发现了一个问题——注释问题。
这位作者采用的是芝加哥注释模式,比如说,他在行文中注明是“弗里德曼1959:
98”,但是,在后面的参考文献中却死活找不到对应的相关文献,我估计这可能是张冠李戴了,也可能是把转引变成直引了,并且还不止一处。
后来我就对作者说必须修改,否则体例这一关就过不了,但作者说当时正在搬家,没有时间改,那我就说对不起,抽掉了。
《文库》(续编)已经在最近出版了,但到现在我还如履薄冰,因为从1994年到2000年的时候,学风问题已经越来越不好,2000年之后就更加严重。
在座的,除了原来是政法大学的学生外,可能还有不少来自其他兄弟院校,包括北大、清华等名牌大学,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讲,包括北大在内,没有一个高校的教师没有发生过抄袭剽窃的问题的,没有一个高校的学生不存在抄袭剽窃的情况的。
有人问:
你为什么总是跟抄袭剽窃过不去啊?
大家都是学法律的,一定都知道知识产权,知识产权保护的就是智力劳动成果。
最基本的一点,就是不能抄袭剽窃别人的劳动成果,但就是人民大学的一篇研究知识产权的博士论文,恰恰被证明是抄袭剽窃的,这位老兄后来到北大做博士后,因为东窗事发,只好把他除名了。
学术剽窃现象的严重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像。
我本人是2003年到政法大学来的。
上学期第一次开课,叫“美国历史与文化”,有78位学生选了这门课。
对此,我很知足。
政法大学的本科生的生源是非常好的,学生热情也很高,从大一到大三,各个学院都有。
我从一开始就强调:
这门课推荐18本参考书,随便读其中的一本所获得的知识和信息量都要比听我一学期的课收获多,那么,我怎么知道你读过这本书了呢?
于是,我要求每个人写一篇读书报告。
这份读书报告的水平可高可低,但无论如何不能抄袭别人的。
但是,结果却有20%以上都是原封不动从网上当下来的。
对于这种情况,第一,我感到很吃惊;第二,我觉得自己非常失败。
大家可能对我不是很了解,我从1981年起读本科学的就是历史,1988年起在北师大教美国史,在这个“稀饭大学”教了十五年书,但从来没有遇到过学生在我的课上大量抄袭的情况。
我在师大教书时,开始时是最受欢迎的教师之一,选我的课的人相当多,到后来越来越少,因为学生们口口相传哪个老师要求高、哪个老师要求低,他们都知道我要求不能抄,结果到后来只剩下了三四十个人。
那么,为什么我觉得自己第一次在法大开课是失败了呢?
因为我反复讲不能抄袭别人的,但还是有很多人抄袭,并且不少是大三的学生,而且还是在我的课堂上抄!
事后我给徐显明校长写了一封信:
我说我很不理解,为什么政法大学有这么好的生源的学校,而且是法科大学,学生居然这么肆无忌惮地抄?
徐校长在和和我谈这个问题时,问我有什么危害。
我说,第一,那些抄袭的学生肯定看不起我这个当老师的,因为他抄的往往是好的文章,如果老师发现不了抄袭事实的话,肯定会给高分,那么这个学生就会从内心里鄙视老师,会说你什么破水平啊?
我明明是抄的,你照样给高分嘛!
第二,对学生不好,会造成学生的投机心理。
如果一个学生能在我这么一个口口声声要搞学术规范的老师的手里都逃过去了,其他老师就更不用说了。
第三,对学校的学术形象不好,因为如果学生是靠抄袭完成大学学业的话,这个大学的学术声望一定是成问题的。
选我的课的还有三个留学生,让中国的学生代抄。
因此,如果抄袭问题解决不了的话,这对于中国的研究生与学位教育的国际地位也会产生消极后果。
我们知道,中国的留学生要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名牌大学拿一个博士学位是非常难的,要过生死关头,但如果外国人到中国拿一个学位易如反掌的话,那么他们从骨子里面就看不起中国的大学和中国的学位。
为什么我们中国这么多大学的学位在外国得不到承认,首先是我们自己的学位还不值钱,另外就是外国人到中国拿学位实在是太容易了。
我跟徐校长讲:
我的课的学生的读书报告抄袭的有20%-30%,那么马克思主义概论等公共课估计有80%-90%是抄的,法学的课估计40%是抄的。
为什么呢?
民商法一上就是上千人的课,交上来上千份作业,老师都不知道是从哪儿抄的。
在这个问题上,徐校长非常诚恳,他说恐怕不止40%,应该在60%以上。
朋友们想想看:
政法大学的学生是以法科为主的,都学过知识产权法,居然如此!
其他高校和其他专业就可想而知了。
在很多高校,包括最好的大学在内,大家对写文章、写书、编字典已经不当成一回事了。
像儿戏一样,如同有的老师说的那样,几天就攒出一篇论文来,已经稀松平常了。
除了网上公开卖论文的外,许多学生常常从网上攒一篇出来就把老师糊弄了。
而且,已经不止一次发现博士论文作者在送审的时候正好送到了他所抄袭的那个学者的手中。
所以,我们有的非常有名的大学的外号叫“复印大学”,还有的著名大学被称作“抄袭大本营”。
去年12月,我们政法大学对门的石油大学请我去给他们的教授培训班讲学术道德问题。
我当时先问在座的有没有南京大学的校友?
没有一个吱声的,我把南大的追求排名、热衷量化以及抄袭问题数落了一通,当场有个教授抗议说:
杨教授,你怎么能这样说我们南大!
我说,你们南大的问题还不止这些,比如要求研究生必须发论文,要求博士生在国外发论文,都是从南大开的恶例。
这个风现在刮遍全国,恶贯满盈。
我说:
南大和复旦争一争二就不得了了,怎么能争过北大、清华?
但是,前些年它楞是说自己所谓的SCI排名第一。
去年南大发生了一个丑闻:
一个本科生在国外的SCI期刊上发了八篇文章,被美国的数所大学录取,被南大树为“标兵”,但事实上这个本科生既没有实验室,又没有科研经费,也没有写作什么论文,都是他那在北师大物理系当教授的老爸写的,但儿子署名第一作者。
这叫“上阵父子兵”。
我觉得不光是南大,其他高校特别是“211工程”、“985工程”国家重点投资建设的高校,都应该反思。
为什么现在的论文越来越多、书越来越厚,学术质量却越来越差?
据说,北京某高校有一个搞刑法的教授,平均每周都要发一篇论文。
可是,这样一来,论文还能叫论文吗?
现在关于教授,有种种不怎么中听的说法,比如,“博士不如狗,教授满街走。
”再如,有一本《所谓教授》的小说,其中的主人公说:
“所谓教授就是白天是教授,晚上是禽兽!
”我在两年以前一直特同意这些说法,因为本人那时一直是副教授。
现在我也是教授了,但也不反感这些说法,因为这确实是个问题。
学术抄袭的问题不解决,所谓的学术创新就无从谈起。
大家知道,我们中国的文科,包括法学,基本上跟国际主流学术界是不接轨的。
不过,自然科学因为没有意识形态的因素,学者们又常常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成果,应该说在主流上还是接轨的。
但即便是自然科学,也不妙。
这里有一个统计数字:
据《光明日报》2004年7月9日报道,在1993年到2003年这十年中,在国际科学引文检索排名中,各学科被引证最多的前20篇论文中,没有一篇是中国科学家的论文;在前100篇中,只有两篇;前1000篇中,只有四篇。
所以,邹承鲁院士呼吁:
“现在是从对量的重视转而对质的提高提出明确要求的时候了!
”他说,“我们应该大力刹住浮躁之风,彻底改变急功近利的观念”。
应该说,这些德高望重的老院士已经给我们树立了好的榜样,在学风建设上是功德无量的,因为他们地位高,名气大,登高一呼,即可产生积极效应。
另一个问题就是粗制滥造。
说到粗制滥造,大家一定知道大名鼎鼎的王同亿先生,他编了很多词典,最有名的叫《语言大典》,有15斤重,在人民大会堂搞首发式,被吹得天花乱坠、神乎其神。
但就是这本《语言大典》,不仅大量抄袭《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海》,而且还有大量的胡编乱造。
在座的肯定有穿牛仔裤的,在这本词典中,王先生对“二流子”这个词的解释就是:
“没有牛仔经历而穿牛仔裤的人”;对“鬼使神差”的解释是:
“由神和鬼派的使者”;什么叫“不破不立”呢?
他的解释是:
“公安机关受理的刑事案件,能破案的就立案,不能破案的就不立案”。
《语言大典》里还有一个词——“牛鞭”,他说这是“用公牛阴茎制成的鞭”。
这个王先生真是“可乐”,跟我们开了不知多少令人哭笑不得的“玩笑”!
王先生十年内编了25部词典、1.7亿字,平均每年1700万字。
王先生是湖南人,有的湖南人很魁梧(像毛主席),也有的个子不怎么高,王同亿先生1.6米左右,他请新华社的一位记者为他拍了一张照片,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标题就叫“著作等身”,因为他编的书摞起来同他一般高。
和编词典一样,现在编教材也是形同儿戏。
我们的教授、副教授,很少没有不编教材的。
所以,我估计中国的大学教授、副教授大概90%是教材教授、教材副教授,也就是靠编教材而评上的高级学术职称。
像《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的教材大概有500种左右,最新的统计数据讲,《中国文学史》的教材已经有1600部,我估计法理学、民商法的教材也得上百种了。
那么,为什么大家把编教材当成评职称的捷径呢?
因为在中国有一个怪现象,即编教材变成你抄我的,我抄你的,互相抄来抄去,最后究竟是谁抄谁的,用刘宗绪教授的话说,考证不清楚了。
几年前,《中华读书报》的一个记者就这个问题作采访,其中有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政法大学的副教授就说:
什么主编、副主编、新编、合编,他说还不如叫“主骗、副主骗、新骗、合骗”呢!
可是,有讽刺意味的是,包括在座的在内,我们差不多都是上过这些“主骗、副主骗、新骗、合骗”的当的。
学术界确实也有一个沙尘暴侵蚀和危害的问题,也有一个怎样保护学术生态的问题。
现在我们已经感到环境保护不了,社会和经济无法可持续健康发展,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更不可能。
学术界也开始认识到:
我们大家都是学术共同体的一员,在这个共同体中,应该有大致认同的价值取向、有大致相似的学术激励与惩处机制,还应该有大致认同的游戏规则。
这些就是“学术规范”。
离开了学术规范,学术共同体就不复存在了。
我赞成卫国教授的观点,即政法大学应该有条件成为遵守学术规范的模范大学。
因为我们是一个以法科为主的大学,而在法科人的心目中没有一个不懂得知识产权,也不应该不尊重知识产权,所以我们应该努力去做。
二学术积累、学术交流与学术创新
有一句老话:
“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江河不择细流,故能成其深。
”这用学术语言来讲,就是学术规范体系中的学术积累与学术交流以及学术创新的辨证关系。
我们这些年来,作品越来越多,教授越来越多,但像狗熊掰棒子一样,掰一个扔一个,低水平重复。
这当然有很多复杂的因素。
比方说,校方规定的硕士生、博士生必须发表论文才能毕业的要求,就属于逼良为娼的制度性因素。
还有的是学生不晓得什么叫合理借鉴、什么叫合理引用、怎样构成抄袭剽窃?
真理往前多迈了一步,可能就犯规、甚至栽跟头了。
我觉得主观上应该检讨,我们这些做老师的、做导师的都有重大的学术责任。
导师,并非意味着在每一个专业领域都站在最前沿,但他应该让学生明白做学问的最基本的底线伦理,比如学术研究中不能闯红灯,这是做老师的应该教给学生的。
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讲,有很多老师一辈子也没有写出一篇像样的论文,也没有写出一本像样的书,但照样带着一大批硕士生、博士生,因此他只能“放羊”。
这差不多就是误人子弟,而且这种情况也包括中国最好的大学在内,因为就是在中国最好的大学,事实证明也有一些博士生导师是抄袭剽窃的主角。
北大的李零教授在2003年讨论北大改革的时候提出一个非常有名的观点,他说:
“大学不是养鸡场。
”现在为了提高产蛋的数量,养鸡场采取了各种办法,特别是现代化的大型养鸡场,为了多产蛋,无所不用其极,比方说一天24小时在养鸡场里开着灯,让鸡总认为是白天,鸡本来也是要睡觉的,但它不像我们人这么聪明,一看开着灯就误以为是白天,所以就不怎么睡觉了,饿了就吃食,吃多了就下蛋。
所以现在的蛋黄不黄了,那就是因为这些蛋和放养的鸡下的蛋不一样,它不是自然生产的,而是人为催生的。
总而言之,只是让鸡多下蛋,越多越好,而不管蛋的质量如何。
李零教授说,大学不是养鸡场,我非常赞同。
如果大学也逼着这些教授、副教授、讲师像鸡一样,不打盹儿,一个劲地下蛋;甚至还逼着这些小鸡——博士生、硕士生一个劲地下蛋(尽管这些小鸡还不到下蛋的时候),那么就像蛋黄不黄了一样,我们的学术论文也就不再像是学术论文、学术专著不再像是学术专著、学位论文不再像是学位论文了。
这也还是刚才讲过的道理,再也不能单纯搞什么量化比赛了。
讲到学术交流,我们古人还有一句话非常好:
“君子以文会友”;又说: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
就像没有学术积累一样,我们现在也都不怎么重视学术交流,拿起笔来就写,而且下笔千言万言,既有“又臭又长”的,也有“又短又臭”的。
有一个叫陈国生的,原来是西南师范大学的教授,现在是湖南一个学院的教授,搞历史地理的,经常对学生夸海口,说他每天不写七八千字就不爽!
人们常说“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就像孔乙己先生说的“窃书不能算偷”一样,算是我们中国读书人的一个传统,但按照现在的知识产权、学术规范和学术伦理,抄袭就是窃取别人的学术成果。
既然连小朋友都知道不能偷别人的橡皮、铅笔,为什么我们这些学者还要去窃取别人的学术成果、并且振振有词呢?
学术交流,一定是在欣赏别人和尊重别人的基础上,借鉴已有的成果,并通过注释等形式,明确区分清楚哪些是别人的,哪些是自己的,人己有别,先后有别。
可是,我们的许多论文,特别是法科的论文,上万字的论文,往往没有几个注释。
我记得朱苏力教授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批评这种情况。
我们搞史学的,比较迂腐,讲究“无一句无来历”。
搞法科的,再聪明,也不能每一句都无来历吧!
我觉得苏力教授的批评还是相当中肯的。
正是因为没有学术积累,没有学术交流,所以我们看到的很多学术论文,包括博士论文、硕士论文往往是各说各话,自言自语,闭门造车。
所以,清华大学的李强教授批评说:
现在许多学者写论文,就像给别人讲课一样,没有学术对话;中国社科院的蒋寅教授说:
别说与国际接轨,就是“开会坐在一起也没法对话。
因为大陆学者通常是自说自话,并不管别人说什么,罗罗嗦嗦一堆毫无信息量的废话,”而且拿起话筒来就不放下,滔滔不绝,也不管别人愿不愿意听。
现在的学术著作很多,到北京的大书店逛一圈,累得慌,因为新书太多了,眼花缭乱,但要找一本名副其实的好书,非常困难,所以我不想逛大书店,因为粗制滥造的太多。
学术研究并非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否则,只能是无效劳动,并且浪费自己的和社会的学术资源。
为此,《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规定:
学术成果“应注重学术质量,反对粗制滥造和低水平重复,避免片面追求数量的倾向。
”
现在总是谈学术创新,似乎博士论文要创新,硕士论文也要创新,我们学者发表的书、论文也常常夸口是创新。
中国现在有30万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如果真的是每个人都创新的话,那么每年至少有30万个创新点,这怎么可能呢?
我们还有2000万的在校大学生、数百万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如果“学术创新”是这般模样的话,那就不叫创新了。
科学巨匠爱因斯坦有一个说法非常好,他说:
“从我自己痛苦的探索中,我了解前面有许多死胡同,要朝着理解真正有重大意义的事物迈出有把握的一步,即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