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只冠冠雀.docx
《我是一只冠冠雀.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我是一只冠冠雀.docx(6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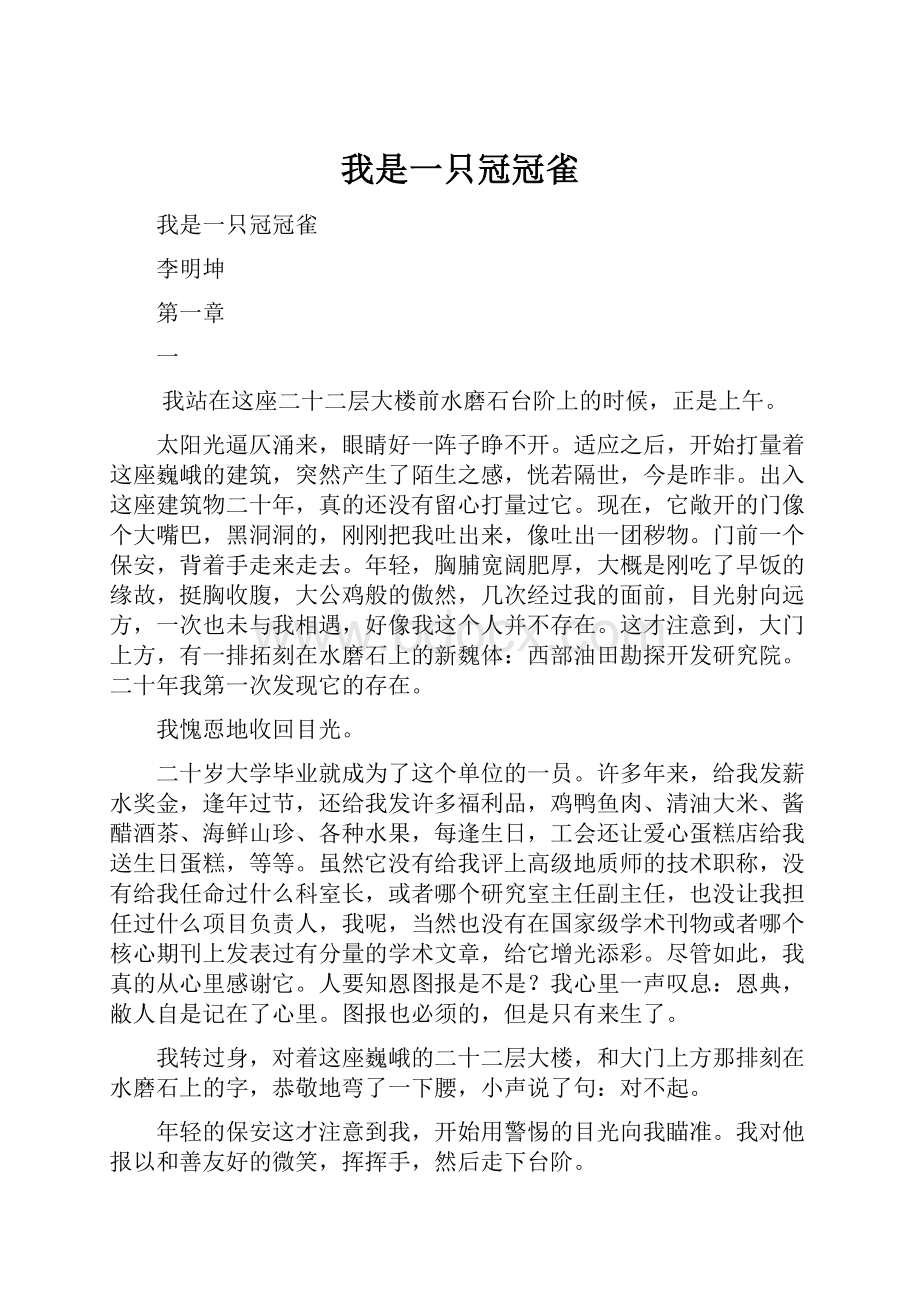
我是一只冠冠雀
我是一只冠冠雀
李明坤
第一章
一
我站在这座二十二层大楼前水磨石台阶上的时候,正是上午。
太阳光逼仄涌来,眼睛好一阵子睁不开。
适应之后,开始打量着这座巍峨的建筑,突然产生了陌生之感,恍若隔世,今是昨非。
出入这座建筑物二十年,真的还没有留心打量过它。
现在,它敞开的门像个大嘴巴,黑洞洞的,刚刚把我吐出来,像吐出一团秽物。
门前一个保安,背着手走来走去。
年轻,胸脯宽阔肥厚,大概是刚吃了早饭的缘故,挺胸收腹,大公鸡般的傲然,几次经过我的面前,目光射向远方,一次也未与我相遇,好像我这个人并不存在。
这才注意到,大门上方,有一排拓刻在水磨石上的新魏体:
西部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
二十年我第一次发现它的存在。
我愧恧地收回目光。
二十岁大学毕业就成为了这个单位的一员。
许多年来,给我发薪水奖金,逢年过节,还给我发许多福利品,鸡鸭鱼肉、清油大米、酱醋酒茶、海鲜山珍、各种水果,每逢生日,工会还让爱心蛋糕店给我送生日蛋糕,等等。
虽然它没有给我评上高级地质师的技术职称,没有给我任命过什么科室长,或者哪个研究室主任副主任,也没让我担任过什么项目负责人,我呢,当然也没有在国家级学术刊物或者哪个核心期刊上发表过有分量的学术文章,给它增光添彩。
尽管如此,我真的从心里感谢它。
人要知恩图报是不是?
我心里一声叹息:
恩典,敝人自是记在了心里。
图报也必须的,但是只有来生了。
我转过身,对着这座巍峨的二十二层大楼,和大门上方那排刻在水磨石上的字,恭敬地弯了一下腰,小声说了句:
对不起。
年轻的保安这才注意到我,开始用警惕的目光向我瞄准。
我对他报以和善友好的微笑,挥挥手,然后走下台阶。
二
我这年四十五岁。
内退之后,我有了充足的由自己支配的时间。
从前不大喜欢上班,从星期一开始,就盼着周末的到来。
在属于自己支配的日子里,骑上自行车,去古河滩捡玉石,或者去湖畔垂钓。
一个人走在古河滩上或是坐在湖畔,一天的时光很快就过去。
我是一个时代的落伍者。
不喜欢看电视,对电脑也不感兴趣,没有手机,也没有银行卡(好在结婚以来家庭财务一直由妻子管着)。
每天太阳不出就出发,在早餐店买几两个干馕,两块钱一个,装进布袋里,袋子里还有几根大葱,一袋榨菜,和一大壶水。
骑着自行车走在戈壁上,小路崎岖,自行车颠簸出如同秋天里的铃铛刺丛被大风吹过的声音。
到了古河滩,把自行车放倒在一簇红柳旁,将大水壶(装一公斤半水)斜挎在身上,头上戴着麦秸草帽。
直到太阳落下去,才骑上自行车返回。
几日之后又去湖畔钓鱼。
湖很大,水面生长着芦苇和蒲草,看上去湖对岸显得遥远。
鱼很多,有时会杆杆不空,为了多在湖边安静呆上些时辰,我会像姜太公那样垂钓。
这样的日子没有多久,我好像对古河滩和湖畔厌倦了。
开始怀念起上班的日子,人真是很怪的动物。
上班不可能了,只好整日蛰居在住所里。
在黎明和黄昏之后,偶尔到门前的河边走一走。
三
我过起离群索居的生活。
太阳落下去之后,一人躺在黑天鹅绒般的黑暗里,被河水的喧闹搅扰得难以入眠。
卧床在临河窗户一侧,一扇窗不知何时悄然打开,夜风拂动厚重的帘布,流水的喧闹像只翩翩飞舞的蝴蝶进入居所。
起身关闭了窗户,帘布安静下来,抹去河岸照耀的灯光,也使喧闹声远去。
我依旧躺在黑夜中,睡眠却像只迷途的羔羊,不知在何处徘徊。
河水在低声的絮语,像一个人在我耳边讲述一段往事。
一个多月前,我被医生检查出患上了不治之症。
我并不感到吃惊和恐慌,很平静地问医生我还能活多久。
医生告诉我大概还有半年时间。
我拒绝了医生要我住院治疗的建议,回到自己的居所。
之所以把栖身之地叫居所,而不称之为家,是因为很长时间里只有我一人,我对它既不怎么眷恋也不深怀厌恶,而且一直想离开它,像一个人在夜到来之时与影子的告别,只是没想好去往何处。
从医院回到居所,平静地重复着每个日子。
早晨睁开眼,上半身离开床铺,坐一会儿,想一想曾做过什么梦。
失眠使我的睡眠像块被老鼠偷食的蛋糕,本来已千疮百孔,却又被梦占去了很多。
近一段时间以来,做些奇怪的梦。
看见自己又背上书包,去县城中学读书,或者又回到了大学的校园。
同学们还是那样年轻,穿的衣服还是记忆里的样子。
只有我是如今这副猥琐的小老头儿模样。
醒来久久望着黑暗,弄不清自己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
带着困惑离开了床,趿着拖鞋走进盥洗室,打开水龙头,撩起水轻轻敷到脸上,会瞥见镜子里那个憔悴的脸孔偷偷打量我。
开始刷牙,白色的泡沫越来越多堆在镜中的嘴唇上。
刮去胡须前小心地往脸上涂抹刮胡膏。
疾病和岁月使这张脸日渐消瘦和衰老,眼神模糊不清,像仓储室里被遗弃多年的一页信纸,颊上红晕似乎还在,却变成铁板上的红锈。
用刀具刮胡子,刮得小心翼翼。
皮肤正在失去昔日的弹性,摸上去像橡胶,如我的神经一样开始脆弱,稍不小心就会被刮破。
这一切做完之后带上门,楼梯间开始响起我的脚步声,很轻,怕惊动了谁。
我去食堂用早餐。
时候尚早,年轻人还在睡眠中,空旷的厅堂里回荡我一人的筷子碰到菜碟的响声。
离开食堂返回居所。
早晨的阳光将桔红色铺在弯曲的小道上,浓荫里没有晨风的吹拂,仿佛比居所还安静。
一天中坐在居所中那张黑皮椅子上,翻看一本本老旧的杂志,它们曾尘封在地下室的一只木箱里。
更多时候我对着某本摊开的杂志发呆,上面刊有一篇小说,是我制造出来的,可是我对它们充满陌生感。
只有到了太阳坠下地平线之后,夜的长翼完全覆盖了居所前的河流和岸上的树丛,我才走出居所到河岸边沿河行走。
一年多以前,妻子突然中止了与我的争吵。
她去了遥远的新西兰,给女儿带孩子,并且一去不复返。
她曾给我打来过电话,异国他乡的生活使她的心情有了很大的改变,她说做梦都没想到她这辈子还能过上如此美满如意的生活,她为后半生的好命运而欣慰,建议我是否也这样做。
“不过,”她在电话里自顾自地叹息:
“也许我的感觉不适用于你,你这人总是与众不同。
”说完这句话,沉默了十几秒钟,没有听到我的回答之后,她悄然挂了电话。
妻子是石油人的第二代,来自大山深处的一个老油田。
她的父辈们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在深山里开发石油。
在认识我之前,她一直没有走出那片大山褶皱中深掩的石板屋群落,初中毕业后当了油田采油工,经人介绍我们认识。
和妻子的相识,真的是偶然而又偶然。
单位上让我去那个老油田取油样,用于和新区一口探井的原油做对比。
我坐了一辆212吉普车去了。
取完了油样,配合我工作的老地质工程师,要给我介绍对象,他很热情,让我有点盛情难却,就和后来成为我妻子的姑娘见面了。
第一次见面给我留下的印象不错,我想自己也该结婚了。
她愿意嫁给我,很大程度上因为我是大学生,大学生在当时是稀缺品。
不久之后,在这条河边一间平房里我们住在了一起。
不多久,她发现了我很多缺点,最令她不能容忍的是我的不求上进且游手好闲。
没有被评为过先进,哪怕是班组一级的,既不主动做家务也不读业务书。
我们经常吵架。
妻子像个领导那样质问我:
“大家都在努力大干四化,只有你整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像个寄生虫!
”妻子认为我与她及周围的人格格不入。
一段岁月里,周围的人都在复习功课,去读职大、电大,妻子也加入这个行列,自学拿到大专文凭。
在单位上她成了为数不多的女党员,还被选为车间工会的女工委员,差不多每年都会被评为先进个人。
一次,妻子无意中发现我有一笔数目不菲的存款,她毅然决定从银行取出来,以她的名字存入另一家银行。
女儿大学毕业后,她用这笔钱将女儿送去国外留学,并以命令口吻让女儿学成之后不要再回来。
她的努力获得成功。
那天中午,我们回到家,几乎同时向对方报告了被内部退养的消息。
妻子坐在沙发上大哭,接下来是绵长的且哭且诉,数叨我过往的劣迹,像一部已经翻阅过半的书,忽而又从头阅读。
第二天,我一大早就逃出了家门,骑上自行车去了古河滩。
去古河滩捡玉石或去湖畔垂钓,很大成分是逃避。
一段时间彼此沉默之后,妻子对我彻底绝望了。
她重新振作起来,每天打扫房子,认真打扮自己,去跳广场舞,或者去谁家打麻将。
当然,我的那点工资她还管着,每月初将三百块钱塞我枕头底下,算我一个月的生活费。
有时夜半时分,客厅的电话突然响了,妻子像一直醒着在等这个电话似的,敏捷地从卧室跑出来,经过我的卧室门前时,看见她迅速移动的腿,将睡衣下摆扇得飘起来。
她进客厅时随手将门带上了。
妻子并不掩饰这一点,她有了我所不知道的秘密。
一天,妻开始打理行装,并且告诉我去新西兰给女儿带孩子的事。
即将启程的前夕,我们有过简短的对话。
我说:
“祖国四化尚未实现,你这位大半辈子都在大干四化的人却要走了。
”妻子停下来,抬起那张岁月沧桑的脸,几分黯然神伤:
“我倒想努力工作,可是组织上不是让内退了吗?
一个靠组织养活的人,去哪儿还重要吗?
”我知道,她其实对这片生活了四十多年的土地充满眷恋,还有对远在万里之外新西兰的恐惧,她不知道后半生交给新西兰的一个小镇会有怎样的面对。
她在人过中年竟然生出奋然一搏的勇气,是缘自对我这个男人的失望和绝望。
四
那笔数目不菲的存款是爷爷去世前留给我的。
爷爷对我说,这笔钱你存着,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去动它,或许在你的将来会遇上人生过不去的坎,它能救你。
我记得爷爷看我的目光充满着复杂的情感。
爷爷生前多次对我说,我是我们家从天津来到西部第四代人,而且是唯一的男丁。
我们家祖上是天津的大商户,爷爷的父亲那辈起把生意做到了西部。
一百多年前,出了嘉峪关往西戈壁千里,黄沙连着天涯,是囚徒流放的去处,但是对于商人,他们看见了遥远西部的金钱。
我出生的时候,爷爷的家住在大雪山下的一座小县城。
父母大学毕业去了军垦农场,将我放在爷爷身边。
我游手好闲的习性是爷爷培养起来的。
爷爷经常对我说,人自身是最重要的,身之外的所有东西与之相比都不重要。
比如钱财,我年轻时候为了挣钱,向东去过天津、北平、上海和香港,向西去过中亚的许多地方,甚至到印度的孟买,挣来的钱可以堆满这个小院子。
现在这些钱哪里去了?
像群鸽子飞走了,飞去了哪里连我也不知道。
爷爷年轻时从他父亲手里接管在省城的商铺,他很快把商铺开到了西部很多县城。
这座小县城商贸公司的前身就归爷爷所有。
解放不久,爷爷的商业帝国被公私合营,国家给了他一大笔钱,存在银行里,每年拿利息,过了几年利息又被冻结了。
爷爷到了这座小县城做起商贸公司的顾问。
爷爷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对我进行启蒙教育。
他把我抱在怀里,吟哦唐诗、宋词,稍长之后又给我讲陶渊明的诗,教我背诵《西厢记》、《牡丹亭》中的佳句。
爷爷是个大商人,但从不教我如何谋取金钱。
爷爷给我讲过许多话,很认真的交谈只有两次,一次在我十六岁那年,我考入了省城大学,即将离开爷爷。
一次是大学毕业那年,志愿去遥远的石油勘探新区。
这两次爷爷都给了我关乎人一生命运的忠告,偏偏都被我忽视了。
有人说,祖上高寿的人,后人一般说来也会长寿,这是基因的遗传。
我在三十岁前与一位叫李晓刚的写小说的人成了朋友,他曾在一座小县城里埋头研究《易经》,还看些《周公解梦》、《麻衣相》之类的民间秘籍。
那天晚上,天下着鹅毛大雪,鸡们都睡熟了。
李晓刚和我在养鸡场一间平房里吃完一只煮得烂熟的鸡,喝光十二瓶啤酒,外面大风呼号,大雪下得很猛,突然停电,窗外漆黑如墨,风声凄厉,一支蜡烛在我俩中间,烛光像团鬼火在飘摇,气氛诡异。
相坐谈起易经八卦。
李晓刚说,但凡祖上高寿的人,后代可能会短寿,因为他的寿命被祖上提前享用了。
那个深夜李晓刚讲了不少离奇古怪的事,我却对他这句话记忆深刻。
爷爷活了九十岁,他生命最后一段岁月是在敬老院度过的,去探望他老人家时他坐在轮椅上,见到我的时候眼眶里放射出奇异的光来,像一盏燃烧太久的灯结了灯花,突然被拨去,然而不久目光又暗淡下去。
爷爷的神智一会儿清醒一会儿混浊。
我相信,我不会活到爷爷这样的岁数,爷爷把许多钱花在我身上,用它们买走了我的一部分寿命。
我甚至为自己不会活到爷爷这样久而庆幸。
所以,我从医生那里知道了我将不久于人世,并不感到吃惊。
爷爷供养了我一生,并惠及我的女儿。
他老人家应该享用我一部分寿命。
这段日子,我在梦中时常回到半个世纪前爷爷居住的那座县城。
县城很小,井字形的街道将全城的小巷连接起来,城南是大片果园,一直铺到山脚下,山里有煤矿,所以有条路从山里延伸出来,穿过果园进入县城。
到了秋天,一车车煤运进城里,让居民们迎接严冬。
城西有条源自雪山的大河,傍城而过,绕城半周流向北方的荒野。
城北是一片苇湖,春天,那些鲜嫩欲滴的芦叶伸出碧绿的水面,水禽成群穿行其间。
远远望去葱笼一片,不见尽头,大河把苇湖和县城分开,河上有道大桥。
每个星期的第一天,邮电局出来一辆骡子拉的胶轮车,满载装着邮件的口袋,穿一身绿色邮政制服的哈萨克小伙子哈比罕,斜坐车辕边,扬起短鞭,胶轮车经过爷爷家前的街道,向北跑去,上了街尽头那道大桥,消失在无边的绿色中。
爷爷曾告诉过我,邮车穿过那片苇湖后,给军垦农场送邮件,每个农场要走半天,一直走到沙漠边缘,邮车返回县城是星期六的晚上。
一个黄昏,我真的看到邮车归来。
邮车上的口袋同样是满满的,一身紫红的骡子通体冒汗,仍劲头十足地跑过爷爷家门前。
爷爷家的邻居玛哈古丽风姿绰约地站在一株老榆树下,在邮车跑过的时候会扬起戴着银手镯的手臂:
嘿,哈比罕!
哈萨克邮递员会咧开被黑胡子包围的嘴唇,露出洁白牙齿:
嘿,玛哈古丽!
年轻美丽的玛哈古丽,经常这样站在老榆树下,看见认识的人会热情打招呼。
小的时候我曾被玛哈古丽领进她的家。
院子里有座很大的葡萄架,下面是盘大炕,夏天时他们一家人坐炕上吃饭。
墙角还拴了几只小羊羔和一头小牛,那儿有道木栅门,推开它才知道玛哈古丽家后面有片更大的天地。
一头大奶牛和几十只绵羊在槽上吃草,好几株苹果树,沙枣树枝夹成的院墙上还爬着葫芦瓜秧,那里有道后门,出去进入一片树林,林间小路一直通往城南的果园。
玛哈古丽一家人都在果林场工作。
我在襁褓中的时候,爷爷便和玛哈古丽家商量好了,每天向他们买一铝水壶鲜奶。
我喝着玛哈古丽家的牛奶长大,他们家后院里那头大花奶牛是我的奶妈。
一开始我以为玛哈古丽在榆树下守望的可能是哈萨克邮递员哈比罕,希望他有一天上门提亲。
后来我发现玛哈古丽对很多她认识的人都热情打招呼,包括从外面回家来的爷爷。
玛哈古丽是我所见过的最迷人的大美人,她有一双覆盖着浓密睫毛的大眼睛,洁白的皮肤像每天用牛奶洗浴过一样,扎着各种颜色的绸巾,头发不是梳成辫子而是慵懒地散披下来,随着她说话时的搔首弄姿而在肩头滑来滑去。
连衣裙也是绸缎的,每件都不一样,轻薄的料子使她妙曼身材若隐若现。
爷爷在玛哈古丽和他热情打招呼时,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从怀里掏出一件礼物。
后来我怀疑玛哈古丽的那些头巾、连衣裙以及手镯都是爷爷送的。
爷爷送了玛哈古丽一件礼物后,会站在老榆树下和她说一会儿话。
他俩之间用另一种语言交谈,我听不懂,玛哈古丽还会被爷爷的某一句话逗得哈哈大笑,分别时玛哈古丽会热情地亲吻一下爷爷脸颊。
我把这一发现告诉了奶奶。
奶奶寻常足不出户,在家里忙这忙那。
谁知奶奶竟宽和地笑了:
“你爷爷年轻时就喜欢长得好看的女人。
他经常给我说,女人是水做的骨肉。
你看玛哈古丽多漂亮,人又年轻,不光男人看了喜欢,连我这个老太婆都喜欢呢。
你说,我们邻居家怎么养育出这么个大美人呢?
”
后来,玛哈古丽跟着一位骑马的哈萨克汉子走了。
据说,那个脸膛黑红的汉子英俊无比,骑一匹通身火红的骏马昂然走过街道。
他突然勒住马,被榆树下美丽的玛哈古丽吸引住了。
他牵着马走向玛哈古丽,那双覆盖着浓密睫毛的眼睛闪烁着让男人无法摆脱的魅力。
他俩说了一会儿话,汉子突然抱住玛哈古丽,把她扛到肩头,放到马背上,汉子左手挽住马缰绳,脚塞进马镫的同时策动了马鞭,玛哈古丽似乎尖叫了一声,很快便温顺地搂住汉子的腰,脸儿贴到汉子坚实的后脊上。
马蹄敲击坚硬的街道,迅速远去。
骑马汉子带着玛哈古丽去了伊犁。
那个傍晚,玛哈古丽的母亲走进爷爷的家门,这位胖老太太平时像奶奶一样足不出户,每天为一大家子人的生活而忙碌。
胖老太太对女儿突然离去很伤心,说要是早早把玛哈古丽嫁出去就好了。
他们一家早年从伊犁迁过来,在伊犁还有很多亲戚,打算让儿子骑马去打听一下。
胖老太太流着眼泪说:
“玛哈古丽让我娇惯得什么也不会做,去给放牧人家当媳妇,那日子她能受得了吗?
”
爷爷到了人生暮年,神志清醒时,还对我提起玛哈古丽。
他声音喑哑地说:
“玛哈古丽真是大美人,曹雪芹看到了会写进书里的。
你今后去那座小城看看。
如果她家门前那个老榆树下站着一个年轻姑娘,那一定是她的女儿,如果坐着一个胖老太太纳凉,那一定是玛哈古丽本人了。
”爷爷指着一个箱子让我打开,里面有个精致的盒子,盛着当年年轻姑娘喜爱的花头巾、裙子之类的。
我猜想,如果当年玛哈古丽依然站在那棵老榆树下,她会陆续得到它们。
爷爷羞涩地笑了。
“女人是水做的骨肉。
钱算什么呢?
看见玛哈古丽纯洁的笑脸,我真是很开心。
”爷爷让我带上它:
“如果见到玛哈古丽,交给她。
在我心里,玛哈古丽一直那么年轻漂亮。
”
那个精致的盒子我一直带在身边,此生能否再见到玛哈古丽,只有苍天说了算。
……在梦中,我又回到爷爷的那个小院。
茂密的树叶在阳光下摇曳,把很大的浓荫投落在爷爷家的庭院里。
这是一棵胡杨树,因为得到充沛的水和肥料,它生长得挺拔而枝叶繁茂。
我沿着记忆的河道溯流而上,看见它的源头的胡杨树下坐着的小男孩。
半赤裸的身子,屁股下坐着羊毛绒缝成的垫子,小男孩子张开小树丫般的手,手脖上的银镯咣啷咣啷响,他看见一个细长的影子小溪一样流淌进树荫里,目光顺着影子,于是出现了穿老黑布鞋的长脚,裤角堆在脚面上。
他仰起脸,看见自己所熟悉的眼睛朝他笑,小男孩欢快地用小手拍打身子,喊:
“牙牙,牙牙。
”身子挪动,竟颤微微站了起来。
爷爷慌忙弯下身子迎接正艰难向他走来的小男孩,对一旁正洗衣服的奶奶大声说:
“看,孙子自己站了起来,开始学走路了!
”这是我关于爷爷的最初记忆。
从此我与爷爷形影不离一直长到十六岁。
爷爷经常带我上街,走过工农兵饭店、大众理发馆、红星照相馆、红旗商店,也会带我去他上班的县商贸公司。
走过红旗商店,他一手伸进怀里,从一个很长的内衣口袋里掏出钱来,买我喜欢的各种东西。
我觉得他那内衣长口袋里,钱永远也掏不完。
在学校听到同学议论怎样吃不饱肚子,衣服要穿哥哥姐姐换下来的,总是很奇怪,他们为什么不向爷爷要?
我在同学们中很孤立,没有人愿意和我交朋友,放了学我飞快跑回家。
一九七七年我十六岁,高中毕业,国家在这一年恢复了高考。
我打算参加高考。
我把这个打算告诉了爷爷。
爷爷却表现出从未有过的慌乱。
他很认真地对我说:
“读大学其实没有什么用的。
真的,像过去的科举。
古时候很多人埋头苦读,把头发熬白了,就是为了入科考试,金榜题名,做个朝廷命官,一生为那几斗米折腰。
你爸爸不是这样么?
念了四年农学院,毕业去了军垦农场。
现如今过了四十岁刚提拔为副场长。
副场长,相当于副县级,在前清充其量是个七品官……”
奶奶从来不和爷爷争吵,凡事总是附和,但只要说到爸爸什么不好,她会勇敢站出来,维护她儿子的声誉:
“考大学有什么不好?
现在全城多少人家在抢购鸡蛋、借肉票,都是为了自己孩子复习考大学。
只有你说读大学没用。
你难道能养孙子一辈子吗?
真像他爸爸说的,你要把孙子养成一只冠冠雀?
”
奶奶端着一只箩筐,且说且往屋子里走。
这是她不愿同爷爷吵下去的表示,主动脱离战场。
爷爷和我相对无言站在院子里。
胡杨树叶里隐藏的冠冠雀们一齐鸣叫起来,它们的声音很像芦笛。
刚才它们被争吵惊吓住了。
冠冠雀是栖息于荒野的一种鸟,与麻雀差不多大小,羽毛颜色也相近,头上长了一撮毛,由此得名。
冠冠雀是一种极聪明的鸟,它们知道人不是善类,凡人类居住的地方均不见它们的踪影,而且从不筑巢做窝,栖息在腐朽的树洞里,或荒原鼠遗弃的家园中。
冠冠雀繁衍后代的本领高强,春和日丽的日子里,一对对配偶在天空上下翻飞,调情做爱且乐此不疲,但它们从不承担父母的义务和责任,而是将蛋下到别的鸟类巢中,让其孵化且抚养。
爷爷一次骑马走过荒野,一对雌雄冠冠雀上下翻飞调情太过于忘我,倏地钻进他老人家宽大的袖子里。
爷爷买了只大鸟笼,把一对情人放进去,好吃好喝伺候着。
起初这对情侣望着笼外天空发呆,一段日子后它们经受不住强烈情欲的折磨,在鸟笼里开始了调情做爱。
爷爷每天把产下的蛋取出来,放到栖息在屋檐下和胡杨树上的麻雀窝里。
不久之后,一只只冠冠雀在院子里吹响芦笛。
爷爷在院墙上掏出一个个洞给它们做家。
爷爷家满树的冠冠雀,是小城的一道独特的风景。
爷爷年轻时候似乎有些像冠冠雀。
爸爸和几个姑姑出生时候,爷爷正值盛年,事业亦如日中天,他对儿女的关注,如同每日从他商铺里关注门外那条汩汩流淌的小河,天天看见却无动于衷,不知道它从哪儿来,也不想知道它流向何方,简单地将他们的一切交给奶奶和学校。
他的儿女长大成人后,无一例外地选择了离开他。
解放后,爷爷头上戴了顶“资本家”的帽子,这顶帽子像团阴影跟随他儿女后面。
爸爸大学毕业毫不犹豫去了军垦农场,几位姑姑嫁给现役军人或国营企业的工人,但他们永远面对一个事实:
他们是资本家的儿女。
爷爷当然明白。
他被时代尘封后,感到了儿女远离的悲凉。
爸爸妈妈结婚前夕,礼节性地来到爷爷家。
父子相对无言。
爷爷向他儿子,也是他们家这一代唯一的男丁提出一个要求,那就是在我出生后,留在爷爷奶奶身边。
爷爷忿忿地说:
“你们不是说老子是剥削阶级吗,贪婪地喝人民的血吗,老子就像树上的冠冠雀吗?
好,你们的孩子送来我养,不要你们一分钱抚养费,让你们当冠冠雀总成吧!
”
十六年中,我慢慢变成了爷爷心中的老儿子。
当然,爷爷最终没有阻拦我去参加高考。
我被省城大学录取后,他和奶奶一同送我去汽车站。
爷爷知道他养的一只冠冠雀飞走了,它可能不再回来,选择永远留在他身边,临别时还是很认真地说:
“想把你永远留在我身边,可能是我很多错误想法中的一个。
但人在一生中,要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不要随波逐流,像粒砂子那样被水流卷着走。
”我离开小城时,看见爷爷站在汽车站台上,他没有像奶奶那样流着泪,不停地用袖口擦拭,而是像平时那样,松闲地袖着手,瘦长的脸永远不变似的覆盖着淡淡的笑容,春天的阳光没有多少温暖,投射到那张脸上,却洋溢着光润和安祥。
我清晰记得,那一天,空中有淡淡的薄雾,正把几片雪花抛撒下来。
第二章
一
一九七八年三月一日。
有位年轻人在北湖农场的旷野上行走。
冬雪开始融化的时光,天气很寒冷。
他没戴帽子,光秃秃的白杨林带里吹来的风把耳朵咬得通红,颊骨、下巴和鼻子也红了,嘴里哈出一缕一缕白汽。
他走上总干渠大桥时,身后一辆骡子拉的胶轮车跑上桥来,骡子浑身蒸着汗汽,毛卷成一小撮小撮的,鬃毛和唇边染着白霜,咚咚咚地贴他身边跑过,下了桥远去。
几天前,这辆邮车给他送来了省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他下了桥往东走。
前方这条路在冬天第一场雪后,好像再没人走过,他身后每个脚印都像踩塌一只荒原鼠洞。
前头那个连队被一片光秃秃的树笼罩,一群麻雀飞了起来,黑压压像片云在灰色天幕上飘移,又像秋天飘零的树叶原落回树上。
他走到村口,走上进村的小路。
这路像躺在雪地上的藤蔓,伸出的一支小岔引领他走向一间地窝子。
葵花秆夹成的小院子,推开红柳枝条夹成的门,门像散了架似地歪向一边。
他看见院子边堆着不多的苞谷秆,一人弯腰抱起一些来。
他这么默默站了一会儿,沙哑地叫了声:
“妈。
”
那人转过头,头巾包裹得很严实,眼睛里僵直着惊愕:
“来——来喜,你回来了……”
他跟她身后走进地窝子,身后的寒气变成白雾。
两个同母异父的妹妹围坐在火墙边,炉子里没有火,她们把小手贴在火墙上,眼睛怯怯地望着这个哥哥。
这个哥哥不大回来,而每次回来总会给这个家搅起不小的波澜。
他曾在院子里和继父打架,一拳将继父击倒在地,血从继父鼻子里流出来,又被继父细长苍白的手涂得满脸都是。
继父一瘸一拐逃出村去,像只被打折了一条腿的流浪狗那样哀叫着。
这个哥哥离开家之后,要过好几天,她们的爸爸才回来,夜里哼哼唧唧躺在床上,院子里有什么响动,就会惊悸地坐起来……
他原打算第二天出发去省城,现在改变了。
他要用三天时间让院子里生长出一个柴垛。
他踏着没膝的雪走向荒野,一直到了那片梭梭林。
梭梭是取暖最好的柴禾,燃烧的火苗玉米般的金黄,边缘镶着蓝色。
两米多高的梭梭生长在荒野上,抱住摇晃几下就倒下了。
三天里他起早贪黑,让院子里出现一座高大的梭梭柴堆。
走的时候,他把多年积攒的六百元钱交给妈妈,让妈妈每个月寄给他十元钱。
大学四年他有四百多元钱就够了。
第四天,他在凌晨五点钟搭乘一辆去省城的油罐车。
天亮的时候到了小县城。
他以前去山里煤矿上拉煤,在井字街第二个路口,会把拖拉机停下来,到工农兵饭店吃饭,坐靠窗的桌旁可以看见街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