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说序跋中的文学真实论.docx
《明清小说序跋中的文学真实论.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明清小说序跋中的文学真实论.docx(1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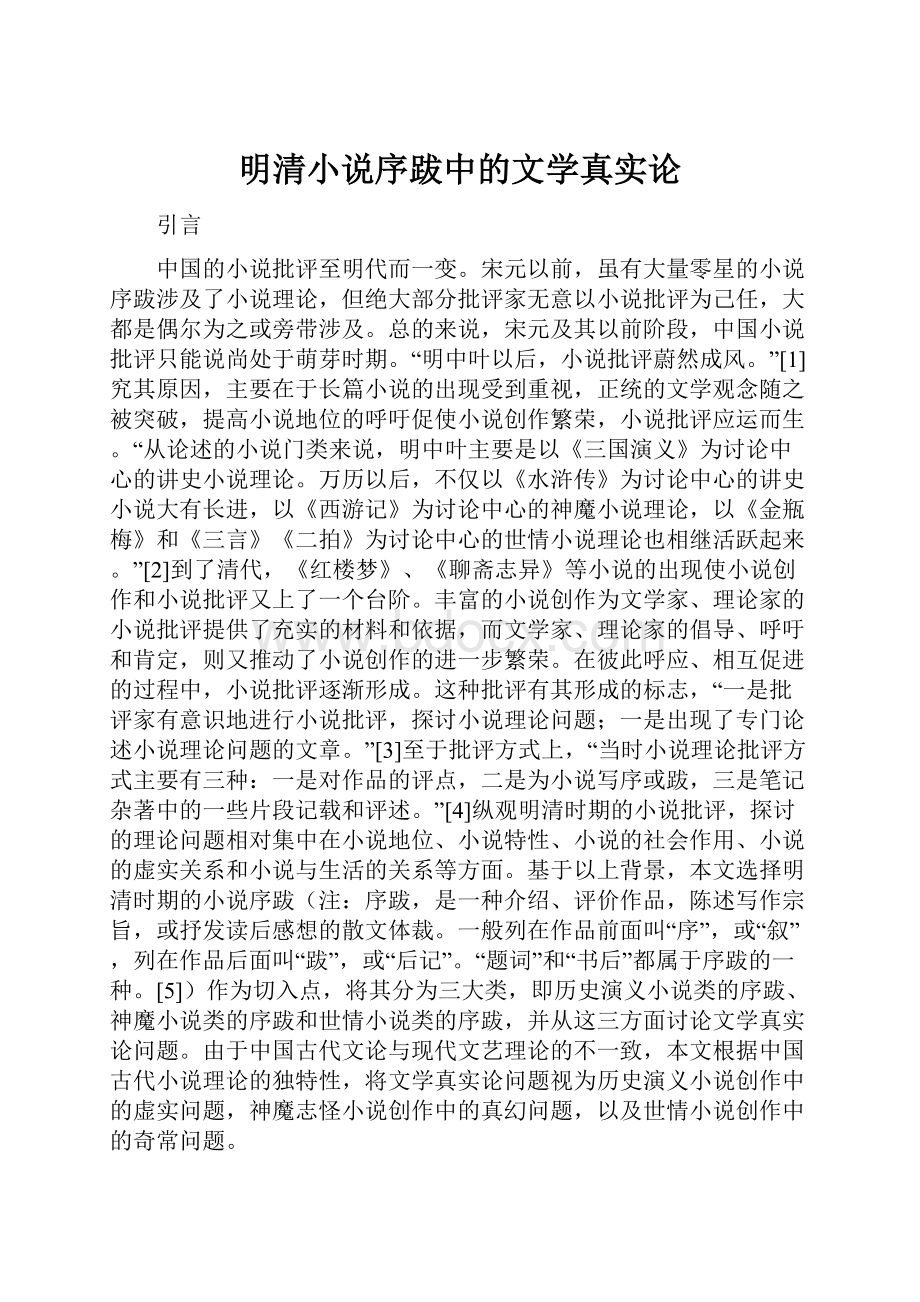
明清小说序跋中的文学真实论
引言
中国的小说批评至明代而一变。
宋元以前,虽有大量零星的小说序跋涉及了小说理论,但绝大部分批评家无意以小说批评为己任,大都是偶尔为之或旁带涉及。
总的来说,宋元及其以前阶段,中国小说批评只能说尚处于萌芽时期。
“明中叶以后,小说批评蔚然成风。
”[1]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长篇小说的出现受到重视,正统的文学观念随之被突破,提高小说地位的呼吁促使小说创作繁荣,小说批评应运而生。
“从论述的小说门类来说,明中叶主要是以《三国演义》为讨论中心的讲史小说理论。
万历以后,不仅以《水浒传》为讨论中心的讲史小说大有长进,以《西游记》为讨论中心的神魔小说理论,以《金瓶梅》和《三言》《二拍》为讨论中心的世情小说理论也相继活跃起来。
”[2]到了清代,《红楼梦》、《聊斋志异》等小说的出现使小说创作和小说批评又上了一个台阶。
丰富的小说创作为文学家、理论家的小说批评提供了充实的材料和依据,而文学家、理论家的倡导、呼吁和肯定,则又推动了小说创作的进一步繁荣。
在彼此呼应、相互促进的过程中,小说批评逐渐形成。
这种批评有其形成的标志,“一是批评家有意识地进行小说批评,探讨小说理论问题;一是出现了专门论述小说理论问题的文章。
”[3]至于批评方式上,“当时小说理论批评方式主要有三种:
一是对作品的评点,二是为小说写序或跋,三是笔记杂著中的一些片段记载和评述。
”[4]纵观明清时期的小说批评,探讨的理论问题相对集中在小说地位、小说特性、小说的社会作用、小说的虚实关系和小说与生活的关系等方面。
基于以上背景,本文选择明清时期的小说序跋(注:
序跋,是一种介绍、评价作品,陈述写作宗旨,或抒发读后感想的散文体裁。
一般列在作品前面叫“序”,或“叙”,列在作品后面叫“跋”,或“后记”。
“题词”和“书后”都属于序跋的一种。
[5])作为切入点,将其分为三大类,即历史演义小说类的序跋、神魔小说类的序跋和世情小说类的序跋,并从这三方面讨论文学真实论问题。
由于中国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艺理论的不一致,本文根据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独特性,将文学真实论问题视为历史演义小说创作中的虚实问题,神魔志怪小说创作中的真幻问题,以及世情小说创作中的奇常问题。
一、实中有虚——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倾向
(一)历史演义小说与正史的区分
对于“历史演义小说”,《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是这么定义的:
“历史演义小说:
明清长篇小说创作题材。
源于历史。
宋人说话四科,讲史居其首。
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概括此类小说特点时说:
‘是讲历史上底事情,及名人传记等;就是后来历史小说的起源。
’……《三国演义》成书后,在明、清两代形成了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高潮,不下数十种,蔚为大观,甚至出现了总揽全史的《二十四史通俗演义》。
”[6]“历史演义”是一种我国古典文学中特有的文体。
李汉秋、胡益民认为,“按照现代的小说观念,小说乃是一种虚构艺术(在英语中,‘虚构’与‘小说’本就是一个名词fiction)。
我们考察它的真实性,是考察它如何艺术地反映了生活的真实,即虚构得是否合情合理,而不是问它是否‘于史有据’,中国古典小说由于它脱胎于历史的史实,一开始就形成了与现代迥然不同的小说意识。
”[7]具体说来,宋元及其以前的小说家、批评家,对于小说与史、小说与文的区别,认识上比较模糊,他们努力把小说归属于史类或文类,认为小说与史、与文难以分割,借以肯定小说的价值。
如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载云:
“尹师鲁初见范文正《岳阳楼记》,曰:
传奇体尔。
然文体随时,要之理胜为贵。
文正岂可与传奇同日语哉?
盖一时戏笑之谈尔。
”[8]其实,尹师鲁说《岳阳楼记》乃传奇体,并非只是“戏笑之谈”,言而无据。
宋赵彦卫《云麓漫钞》云:
唐代传奇“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
[9]这说明当时人们普遍视传奇为文之一体;而《岳阳楼记》融诗笔、议论、描写于一体,在形式上确乎与传奇有相近之处,尹师鲁正是据此而论的。
陈振孙不以为然,但他认为传奇与文的区别在于“理胜为贵”,却又并未划清两者界限。
严格说来,尹、陈二人以及他们以前的批评家都还未确立小说观。
小说的特性与史难以截然区别,小说有史的实录性质,能够拾正史之所遗,详正史之未赅,补正史之不足,因而小说可与正史参行。
努力把小说附骥于正式的批评,其出发点当然是为了肯定小说,但在理论上未能解释小说的特性。
只是到了明代,批评家们才开始有意识地探讨小说本身的特性,并力图把小说与史区别开来,“这既是对上一时期理论的突破,又是这一时期小说得以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
[10]
署名“庸愚子”的蒋大器,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率先发唱,试图区别演义小说与史书的不同。
由于论述的对象是演义小说,因而蒋大器不可能截然斩断演义小说与正史的关系,但又不同于以往批评家把小说归于史类,他根据正史“理微义奥”和演义小说“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特点来区别两者的不同,把演义小说和正史视为两类不同的文体。
[11]陈继儒则更进一步,在《唐书演义序》中,他落笔便给演义小说下了定义:
“往自前后汉魏吴蜀唐宋咸有正史,其事文载之不啻详矣,后市则有演义。
演义,以通俗为义者也。
故今流俗节目不挂司马班陈一字,然皆能道赤帝,诧铜马,悲伏龙,凭曹瞒者,则演义之为耳。
演义固喻俗书哉,意义远矣!
”[12]陈继儒的看法显然与蒋大器的“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不同。
他认为演义是“以通俗为义”,演义“固喻俗书”,并不一定“言辞鄙谬”而是“意义远矣”。
他还认为,演义小说的另一特点是比正史记载更为详细,这就不只是指出两者语言上的不同,而且指出了两者在内容和撰写方式上的不同,从而进一步区别了演义小说与正史各属一体的不同特点。
其后,袁宏道的《东西汉演义序》和甄伟的《西汉通俗演义序》,分别从欣赏、客观效果和创造方式的角度区别了小说与史的不同。
不难看出,从蒋大器到甄伟,批评家对于演义小说和正史的界分的认识渐趋明确。
而这种认识的明确,使得小说的作者和批评者们逐渐意识到,为区别正史与小说,在历史演义类的小说创作中是可以允许虚构的。
必要的虚构才是小说之所以为小说的原因所在。
(二)虚实论争——徘徊于虚实之间
虚、实有很多意思,这里所谓的“虚”和“实”,在文学批评理论里确切指什么呢?
虚,为虚假、不真实的意思,《三国志·魏书·荀彧传》有言:
“推诚心,不为虚美。
”[13]实,则取“实际”、“事实”的意思,如《国语·晋语》云:
“吾有卿之名而无其实。
”[14]小说尚虚还是尚实,自有小说批评家以来就一直争论不休;这种争论在脱胎于史实的历史演义小说出现后达到了顶峰。
明代以前,除了洪迈等极个别的批评家认为小说内容可以是虚幻的(注:
洪迈,南宋名臣,在其笔记小说集《夷志坚》自序中就志怪小说的“虚”与“实”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些故事的来源尽管是“耳目相接”,似“皆表表有依据”,但实质上是虚的,只能“往见乌有先生而问之”。
[15]),一般批评家都主张小说必须实录。
直到到了明代,这种一边倒的情况才发生了转变。
林瀚在《隋唐志传通俗演义序》中提出“以是编(注:
这里的“是编”指通俗演义之类。
)为正史之补”[16]后,明代历史小说论者逐渐形成了两种流派:
一派是强调崇实翼史,另一派则提倡虚实相混。
张尚德就是强调历史演义必须忠于历史事实的最初代表之一。
署名“修髯子”的张尚德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中明确提出了“羽翼信史”说。
[17]他理解的历史演义,是“以俗近语,檃栝(注:
檃栝,矫正曲木的工具;引申为动词含义,约束,规范。
[18])成编”,不允许有作家的艺术虚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羽翼信史而不违”。
张尚德的这种观点反映了当时社会上一批人的看法,反过来也影响着以后历史演义的创作和批评。
陈继儒、余象斗、可观道人等基本上接受和发展了他的观点,逐渐形成了要求历史小说严格依傍历史记载的“羽翼信史”派。
前文已提到陈继儒给“通俗演义”下了定义,但毕竟只是从语言、情节上着眼,而默认了演义小说对史实的依附。
此外,在中国的历史演义小说中,《列国志》是一部倾向于“信史”的代表作品,许多信史派的小说批评家愿意通过它来表述自己的小说创作主张。
余象斗在为重刊余邵鱼编写的《春秋列国志传》所作的序中说《列国志》“旁搜列国之事实,载阅诸家之笔记”,是“诸史之司南,吊古者之鵔鸃(注:
鵔鸃,神俊之鸟,这里是特出的意思。
)也”,由此表明他对历史小说的主要要求也就是要忠于史实。
[19]可观道人继承了张尚德、余象斗等人的观点,通过《新列国志叙》进一步阐述了这类历史小说的创作主张。
他认为《列国志》“本诸《左》、《史》,旁及诸书,考核甚详,搜罗极富,虽敷演不无增添,形容不无润色,而大要不敢尽违其实”[20],可以看出他对《列国志》的这种特点是持肯定态度的。
必须指出的是,“《叙》中所述主张过分强调了依傍正史,这种主张的实施,往往使得一些历史演义小说近乎历史通俗读物,其中的一些部分几乎是正史材料的联缀和解释。
《新列国志》也不免于此。
”[21]
当明代一部分批评家仍然坚持小说实录时,另一部分批评家则开始突破实录观念,提出了新的看法。
明代演义小说家熊大木就在《心坎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序》中首先提出小说不必事事苟同正史。
他说:
“或谓小说不可紊之以正史,余深服其论。
然而稗官野史实记正史之未备,若使的以事迹显然不泯者得录,则是书难以成野史之余意矣。
如西子事昔人文辞往往及之,而其说不一。
《吴越春秋》云吴亡西子被杀,则西子之在当时固已死矣。
唐宋之问诗云:
‘一朝还旧都,靓妆寻若耶。
鸟惊入松网,鱼畏沈荷花。
’则西子尝复还会稽矣。
杜牧之诗云:
‘西子下姑苏,一舸遂鸱夷。
’是西子甘心于随蠡矣。
及东坡《题范蠡》诗云:
‘谁遣姑苏有麋鹿,更怜夫子得西施。
’则又以为蠡窃西子,而随蠡者或非其本心也。
质是而论之,则史书小说有不同者,无足怪矣。
”他以西施的事迹为例,说明文学家创作作品并不一定要与史书保持一致。
文学作品所表现的人物事迹,本来就是多样并存的,以此推而论之,小说内容与史书的记载有出入有不同“无足怪矣”,“小说与本传有同异者,两存之以备参考”。
显然,熊大木认为演义小说须以人物本传行状之实迹为据,但不必事事加以对照,小说可以“用广发挥”,多记与正史有异的事迹,这才体现出小说的特点。
熊大木突破了实录观念,它的理论实际上提出了历史小说可以有一定的虚构的主张,这是他的杰出贡献。
[22]熊大木的理论得到了李大年的赞同,他在《唐书演义序》中对与史书有出入而作虚构的演义小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李大年认为,虽然《唐书演义》“似有紊乱《通鉴纲目》之非”、“出其一臆之见”,但是仍然与《三国志》《水浒传》相仿,有可取之处,而且其中“诗词檄书颇具文理,使俗人骚客披之自亦得诸欢慕”,因此,“不能以全谬忽之”。
这就承认了作为文学作品的历史演义小说虚构的合理性。
[23]
前面所述熊大木、李大年的理论已经说明明代小说批评家已经涉及到了小说创作的虚构理论,但是,直接讨论虚实命题的还是汪道昆。
他在署名“天都外臣”的《水浒传叙》中谈到和正史有关记载的关系时说:
“《史》与《宣和遗事》俱不载所终,《夷志坚》乃有张叔夜杀降之说。
叔夜儒将,余不之信。
《史》又言淮南,不言山东;言三十六人,不言一百八人。
此其虚构,不必深辨,要自可喜。
”显然,这段话表明汪道昆认为进行小说创作时是不必深辨“虚实”的,只要“要自可喜”,即为好书。
[24]汪道昆的观点,在“酉阳野史”的文章中得到了更为明确的阐释和发挥。
酉阳野史编撰的《续编三国志》,实非严格根据史实。
他搞创作的指导思想是小说与国史正纲有别;小说家创作只为了“泄万世苍生之大愤”和“取快千载”;而读者“无过消遣于长夜永昼,或解闷于烦剧忧愁,以豁一时之情怀耳”。
因此,小说无须一一皈依正史,读者亦不必事事究其根源。
他在《新刻续编三国志引》中为自己虚构创作辩护说:
“客或有言曰:
‘书固可快一时,但事迹欠实,不无虚诳渺茫之议乎?
’予曰:
‘世不见传奇戏剧乎?
人间日演而不厌,内百无一真,何人悦而众艳也?
但不过取悦一时,结尾有成,终始有就尔。
诚所谓乌有先生之乌有者哉!
大抵观是书者,宜作小说而览,毋执正史而观,虽不能比翼奇书,亦有感追踪前传,以解颐世间一时之通畅,并豁人世之感怀君子云’。
”酉阳野史承认自己的小说“事迹欠实”、“虚诳渺茫”,但他觉得这样创作是合理的。
他以传奇戏剧为例说明自己的小说内容“内百无一真”、“诚所谓乌有先生之乌有者”,与正史确有区别,但却能使读者“解颐”、“通畅”,而收到“人悦而众艳”的艺术效果。
他强调人们读他的作品,“宜作小说而览”,言下之意就是说小说有它自身的特点和价值。
酉阳野史没有明确使用“虚构”一词,但他从作家创作的动机和小说的艺术效果两方面说明了小说虚构的特点,肯定了小说创作虚构的合理性。
[25]
在明代,小说实录的理论受到了批评,相当一部分批评家已在不同程度上冲破了实录观念。
本来这种实录观念应该继续抨击进而得到全面否定才是,然而事实却非如此。
到了清代,一部分批评家仍然坚持忠于史实的实录观念。
这是因为中国小说理论的发展并不是直线登梯似的步步高,而是波浪式地向前推进;每一理论突破总会出现某种回旋,然后才会推进一步。
清代小说批评中的实录理论,便是这种回旋的表现。
同时,实录理论的回旋与清代文网森严相关。
在清代统治阶级的高压政治下,文人不敢随意发表见解,更不敢虚构荒诞小说,小说批评家同样患有这种思想恐惧症。
除此之外,嘉乾时代考据风行,讲究考实的学风同样影响小说批评家的思想,这也是清代实录理论得以继续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清代历史演义小说的批评中,崇尚实录的倾向十分明显,这可以以毛宗岗、蔡元放为代表。
[26]
“毛宗岗假托金圣叹之名作《三国志演义序》,阐述了他的实录观点。
”[27]他主张演义小说以实录为本,旨在不违反历史史实,与正史合拍。
他在《序》中开宗明义:
“近又取《三国志》读之,见其据实指陈,非属臆造,堪与经史相表里,由是观之,奇又莫奇于《三国》矣。
”又说:
“作演义者,以文章之奇而传其事之奇,而且无所事于穿凿,第贯穿其事实,错综其始末,而已无之不奇。
”[28]意思是他认为《三国志》最“奇”、最值得称道的地方是翼史而作,并非虚构;“作演义者”最好能像《三国志》学习,事实贯穿始终。
毛宗岗以演义小说必须实录为批评原则,过分强调了演义小说的历史真实性。
事实上,任何一部演义小说都不可能事事依据正史而无丝毫出入。
毛宗岗的实录理论与可观道人提出的“大要不敢尽违其实”相比,实际上是一种倒退。
然而却有不少批评家效法毛氏学说,张扬实录。
如黄淑瑛《第一才子书三国志·序》云:
“《西厢》晦淫,《水浒》导乱,且属子虚乌有,何如演义一书,其人其事,章章史传,经文纬武,竟幅锦机。
”[29]而从蔡元放在《东周列国志序》中发表的看法,更是不难看出他对历史演义小说创作的态度。
他重申“稗官固亦史之支流,特更演绎其词耳”,又说“盖稗官不过纪事而已”,[30]这就说明他坚持历史演义小说创作必须严格实录的主张。
当然,有固守就有突破。
“纵观有清一代的小说批评,批评家对小说虚实关系的认识较之明代批评家更为深入,阐述也更为具体。
”[31]如明末清初的吟啸主人在《平虏传序》中说道:
“传成,或曰:
风闻得真假参半乎?
予曰:
苟有补于人心世道者,即微讹何妨,有坏于人心世道者,虽真亦置。
”[32]也就是说他认为为了作品的主题需要和创作目的,可以而且应该对事实进行剪裁和必要的艺术虚构。
署名“吉衣主人”的袁于令在《隋史遗文序》里强调正史是传信,要“贵真”,而小说是传奇,要“贵幻”;创作历史小说时,主要不依据史书,所谓“什之七皆史所未备者”,而主要是“凭己”,根据作者个人的创作意图,“可仍则仍,可削则削,宜增者大为增之”。
[33]袁于令的这些观点,可以说完全跳出了史学家的框框。
康熙年间的金丰更进一步,肯定了小说可以虚构、应该虚构,指出了虚构的必要性和虚与实之间的关系。
金丰与钱彩合作整理了《新镌精忠演义说本岳王全传》,他在卷前《序》中说:
“从来创说者不宜尽出于虚,而亦不必尽由于实,苟事事皆虚则过于诞妄,而无以服考古之心;事事皆实则失于平庸,而无以动一时之听。
……实者虚之,虚者实之,娓娓乎有令人听之而忘倦矣。
”[34]可以说金丰在这篇序中总结了历史演义小说的丰富创作经验,针对贵“虚”、重“实”两种倾向,提出了这类小说应该“不宜尽出于虚,而亦不必尽由于实”的主张。
清末的洪兴全就是这一主张的忠实跟随者,他在所作的《中东大战演义》自序中就金丰的原话进行了一番拓展,再次肯定了“虚实相半”。
[35]值得一提的是,金丰在序中还提到了一些幻化描写,因此所说的“虚”与写实小说创作的“虚构”概念尚有差别,表明他还并未辨明生活真实和事理真实的区别,把它们混为了一谈。
而这两种真实都会在后文中提到。
总的来说,从明至清,创作历史演义小说时是要完全“羽翼信史”还是可以“虚实相半”,还是一个众人争论不休的问题;但可以看出,适当的虚构已逐渐为人们所接受。
。
二、幻中求真——神魔小说的创作目的
(一)神魔乃幻,情理为真
神魔小说是明清长篇小说创作题材的一种。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六篇至第十八篇专门论述了明代的神魔小说。
他认为,历来儒、释、道三教之争,“都无解决,互相忍受,乃曰:
‘同源’,所谓义利邪正善恶真非妄诸端,皆混而又折之,统于二无,虽无专名,谓之神魔,盖可赅括矣。
”神魔小说以《西游记》的艺术成就最高,嗣后又有记而成集的《四游记》、《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封神演义》亦为其代表作。
在鲁迅看来,明代嘉靖前后,小说创作形成了两大主潮,神魔小说即为其一。
[36]
真与幻,是在神魔小说创作中体现得特别突出一对对立而又统一的命题。
到明代后期,人们一般已经不再把妖魔鬼怪视为实有之物,神魔小说中的角色内容基本上已被人们认为是想象之物。
由此看来,志怪神魔小说中的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关系问题,与历史小说中的这个问题具有不同的内容。
这里,所写之事纯属虚幻,但虚幻之中亦含真实——人情事理的真实。
这就是真与幻的问题。
(二)真与幻的关系:
互为表里
上文已提到,真与幻是对立而又统一的,对于这种奇特的关系,明清时期的文论家们自有各自的理解。
优秀的志怪神魔小说,要做到以妖魔鬼怪之幻显人情事理之真。
首先表现出这种思想的,就是《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
吴承恩没有留下关于《西游记》的论述,但有一篇《禹鼎志序》(注:
《禹鼎志》是吴承恩创作的一部志怪小说集,今已亡佚,仅留此自序一篇)约略反映了他的志怪小说的创作思想。
序中称:
“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名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
昔禹受贡金,写形魑魅,欲使民违弗若。
读兹编者,傥玃然易虑者,庶几哉有夏氏之遗乎?
”[37]禹铸九鼎,是为了备百物之形,,使民知神奸,意义极其重大。
把创作志怪小说喻为禹铸九鼎,说明志异物之怪并不是出于好奇,恰恰是为了寄寓对现实世界的深刻认识。
这里虽没有直接讲到幻与真的关系,但所谓真幻问题的实际内容即是如此。
许多小说批评家提倡神魔志怪小说应当“幻极”。
前文提到的袁于令就对“幻”作了极高的评价。
号“幔亭过客”的袁于令在《西游记题辞》中说:
“文不幻不文,幻不极不幻。
是知天下极幻之事,乃极真之事;极幻之理,乃极真之理。
故言真不如言幻,言佛不如言魔。
”又说:
“今日雕空凿影,画脂镂冰,呕心沥血,断数茎髭而不得惊人只字者,何如此书驾虚游刃,洋洋纚纚数百万言,而不复一境,不离本宗;日见闻之,厌饫不起;日诵读之,颖悟自开也!
”[38]本文在评价《西游记》时,高度得评价了艺术的虚构和和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认为只有“幻”,才能“文”,“极幻”当中包含着“极真”。
这从《西游记》来看,当然并不过分,且也道出了浪漫主义的一些基本特征。
但假如过分强调了“幻”,从而笼统地认为“言真不如言幻”,这就显得片面了。
一名署名“杜陵男子”的批评者更是只追求“幻”和“诞”。
杜陵男子在《蟫史序》(注:
《蟫史》二十卷,屠绅作。
《蟫史》一书作于嘉庆初年,系文言长篇小说,情节离奇,文词古涩,主要叙述桑蠋生、甘鼎等平定妖乱,功成身退的故事。
[39])中谈到:
“盖有可为无,无可为有者,人心之幻也。
有不尽有,无不尽无者,文辞之诞也。
幻故不测事,孰察其端倪?
诞故不穷言,孰究其涯际?
蜃楼海市,景现须臾,牛鬼蛇神,情生万变,讵可据史载之实录,例野乘之纪闻乎!
”“幻”就是虚构,即所谓“有可为无,无可为有”。
通过“幻”,达到“穷物之变”,就显得“诞”。
“诞”就是“怪怪奇奇,形形色色”。
作品的“幻”和“诞”,就能“耸人之闻”,以“餍好奇之心而供多闻之助”。
这是道出了神魔志怪小说的某些特点。
从这些特点的表面情况看来,似乎神魔志怪小说与“据史载之实录”风马牛不相及,其实则不然。
故还有个署名“小停道人”的序《蟫史》时进一步提到了“驱牛鬼蛇神于实录中”的观点,希望通过怪诞的描写,最后达到“世道人心之一助”。
这也就是说,神魔志怪小说还是根植于现实的,还是要为现实服务的。
这就比较全面了。
[40]
在真与幻的问题上,也有一些折衷之论,提倡“兼真幻之长”。
张无咎的《批评北宋三遂新平妖传叙》就是这样。
叙云:
“小说家以真为正,以幻为奇。
然语有之:
‘画鬼易,画人难。
’《西游》幻极矣,所以不逮《水浒》者,人鬼之分也。
鬼而不人,第可资齿牙,不可动肝肺。
《三国志》,人矣,描写亦工;所不足者幻耳。
……兹刻回数倍前,盖吾友龙子犹所补也。
始终结构,有原有委,备人鬼之态,兼真幻之长。
”[41]然而,这种论调看起来很全面,且似论高一筹,其实,张氏根本不明白真与幻这个问题的含义,以为写人即真、写鬼即幻。
他也根本不理解《西游记》等文学作品的含义,“第可资齿牙”同王世贞批评《拜月记》“无风情”一样,属无稽之谈。
而他所推崇的《平妖传》,写的是实有之事,又杂之以神鬼妖术,思想上迷信荒诞,艺术上不伦不类,更无“至理”、“真气”可言。
以此下乘小说为“备人鬼之态,兼真幻之长”的上品,由此张无咎所谓“兼真幻之长”为何物,也就可想而知了。
一味求幻当然会走上荒诞无稽的邪路,但这需要以强调“幻”正是为了表现“真”来纠正,而不应该像张无咎这样,提倡真事与妖术的混杂。
[42]
这里,本文用对《聊斋志异》的评论为例对真幻关系做一个具体分析。
《聊斋志异》,是清代杰出小说家蒲松龄以二十年左右时间写成的文言短篇小说集。
《聊斋》实际上也是一部志怪小说,它在创作上所取得的空前成就,为志怪小说理论批评的提高创造了一定条件。
《聊斋》是以大量的花狐妖魅为题材的,但绝不是单纯的志怪传奇,而是有所依托的。
其寄托堪与韩非的《孤愤》相比:
“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
”这就直截了当地说明了作者的创作思想:
将一腔不平之气寄寓于谈狐说鬼之中,通过设幻的故事,尖锐地揭露和抨击了当时社会政治的黑暗与不平,抒发了自己的社会理想。
这也就达到了以“幻”表现“真”的艺术要求。
蒲松龄在广泛采集民间传说的基础上,“雅爱搜神”,“喜人谈鬼”,用这种特殊的写作手法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显示出如屈原赋骚、李贺作诗式的浪漫主义色彩。
[43]
蒲立德是蒲松龄的爱孙,因此对《聊斋》的成败得失能较深入地理解。
他的《聊斋志异跋》文字不多,却将《聊斋》的思想内容、写作特点、以及它与作为“源”的生活、作为“流”的古代文学作品的关系,概括地勾勒了出来,从而丰富了我国志怪小说的理论。
《跋》中这样总结《聊斋》:
“而于耳目所睹记,里巷所流传,同人之籍录,又随笔撰次而为此书,其事多涉于神怪;其体仿历代志传;其论赞或触时感事,而以劝以惩;其文往往刻镂物情,曲尽世态,冥会幽探,思入风云;其义足以动天地,泣鬼神,俾畸人滞魄,山魈野魅,各出其形状而无所遁隐。
此《山经》、《博物》之遗,《远游》、《天问》之意,非第如干宝《搜神》已也。
”[44]“多涉于神怪”,表明其内容上是“幻”的;“刻镂物情,曲尽世态”,说明小说反应了社会的“真”;“冥会幽探,思入风云”道出了小说作者的想象之飞驰;“各出其形状二无所遁隐”称赞小说所刻画的形象的生动性。
总之,蒲松龄将人情事理的真实完美地融入到了奇幻的人物形象与荒诞的故事情节中。
不论从哪一方面说,《聊斋志异》都体现了一部优秀的神魔志怪小说的创作要求,并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另一篇值得重视的评论是清乾隆年间的余集所作的《聊斋志异序》。
本文围绕着《聊斋》“恍惚幻妄,光怪陆离”的艺术特色,形象地渲染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和分析了作家的创作意图及其艺术成就。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