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爱与美.docx
《关于爱与美.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关于爱与美.docx(12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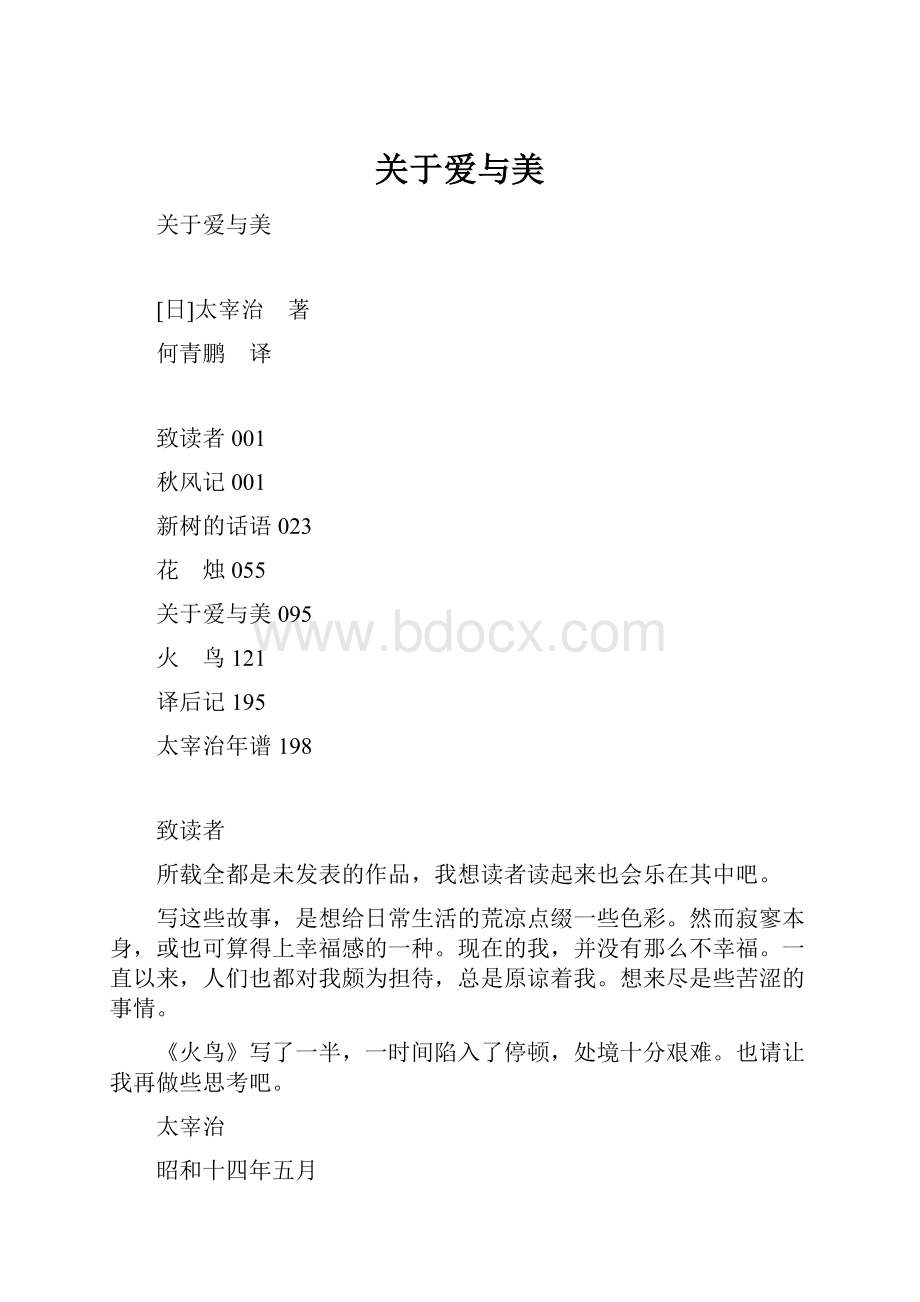
关于爱与美
关于爱与美
[日]太宰治 著
何青鹏 译
致读者001
秋风记001
新树的话语023
花 烛055
关于爱与美095
火 鸟121
译后记195
太宰治年谱198
致读者
所载全都是未发表的作品,我想读者读起来也会乐在其中吧。
写这些故事,是想给日常生活的荒凉点缀一些色彩。
然而寂寥本身,或也可算得上幸福感的一种。
现在的我,并没有那么不幸福。
一直以来,人们也都对我颇为担待,总是原谅着我。
想来尽是些苦涩的事情。
《火鸟》写了一半,一时间陷入了停顿,处境十分艰难。
也请让我再做些思考吧。
太宰治
昭和十四年五月
秋风记
唉,我啊,究竟该写一部怎样的小说呢?
我被淹没在故事的汪洋之中。
我要是个演员该多好啊!
我连自己睡觉的样子都能描画出来。
即使我死了,也会有人为我死去的脸描上美丽的妆容,也会有人为我而悲伤。
K,她大概就会为我这样做。
K,是个比我大两岁的女人,今年三十二岁。
那就说说K吧。
K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血缘关系,但从小就常与我家往来,因此与亲人也没什么分别了。
而现在,K和我一样,也觉得“若从未活过该有多好”。
生而为人,不过十年光阴,便已见过这世上最美的事物。
此后无论何时死去,也都不会后悔。
可K却依然活着。
为了孩子活着,也为了我活着。
“K,你恨我,对吧?
”
“嗯,”K严肃地点点头,“有时候,甚至想让你去死。
”
亲人大都已经亡故。
最年长的大姐,二十六岁时去世了。
父亲,五十三岁去世。
最小的弟弟,十六岁去世。
三哥,二十七岁去世。
今年年初,二姐紧随其后,三十四岁去世。
侄子,享年二十五岁。
堂弟,享年二十一岁。
都是与我非常亲近的人,结果到了今年,一个个都相继亡故了。
若是有什么必须赴死的缘由,就请敞开胸怀对我说吧。
虽然也帮不上什么忙,但两个人还是可以好好谈谈。
一天只说一句也行,就这么说上一两个月也可以。
和我一起出去游玩吧。
若是那样也寻不到活下去的意义,不,即便那样也不能让你一个人去死。
到了那时,就让我们一起去死吧。
留在世上的那个人太可怜了。
你呀,知道的吧,断念之人的爱有多么深。
就这样,K活着。
今年晚秋时节,我戴着一顶格纹鸭舌帽,把帽檐压得低低的,前去找K。
吹了三声口哨,K才悄悄地打开屋后的栅栏门。
“要多少?
”
“没钱了。
”
K盯着我的脸,问:
“想去死?
”
“嗯。
”
K轻轻地咬着下嘴唇,说:
“好像每年一到这个时候,你就熬不下去了啊。
冷吗?
还扛得住吗?
有没有外套?
啊呀,还光着脚。
”
“这叫时髦。
”
“跟谁学的啊?
”
我叹了口气道:
“没跟谁学。
”
K也小声叹了口气,说:
“肯定不是什么好人。
”
我报以微笑:
“想和K两个人一起去旅行……”
K认真地点了点头。
我知道,大家都知道。
K会带我去旅行,她不会让这个孩子死掉。
那天午夜,我们乘上了火车。
火车开动之后,K和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小说怎么样?
”
“写不出来。
”
黑暗之中,只有火车的声音。
哆啦嗒嗒,哆啦嗒嗒,哆啦嗒嗒。
“抽烟吗?
”
K从手提包里一个接一个地拿出三种外国香烟。
有一次,我写过一部这样的小说:
决意寻死的主人公在临终之时,吸了一口醇香浓郁的外国香烟。
在隐秘而模糊的愉悦之中,他打消了寻死的念头。
这部小说,K也是知道的。
我脸红了,可依旧还放不下端着的架子。
一支接着一支,若无其事地把三种国外香烟都抽了。
火车到了横滨,K买了些三明治。
“吃点儿吗?
”
K有意做出一副狼吞虎咽的吃相给我看。
我也放下心来,大口吃了起来。
有点儿咸。
“我感觉自己哪怕只是说句什么话,都会让大家痛苦,无端的痛苦。
倒不如就闭上嘴微笑还好一点儿。
可我却是个作家,是个不说点儿什么就没法生活下去的作家。
真是够难为人了。
就连一朵花我也没办法好好爱护。
只是闻一闻那朦胧的花香,这我忍不住。
我总会像狂风一样折下这朵花,放在手心里,揪下花瓣,揉成一团。
眼泪就这样不听控制地流下来,把花塞进嘴里,一点点嚼烂,再吐出来,踩在木屐下碾碎。
就这样,我拿自己一点儿办法都没有。
我想杀了自己。
我可能不是个人吧。
我这段时间真是这么想的。
我莫不是撒旦?
杀生石?
毒蘑菇?
什么?
可不要说吉田御殿
①,我毕竟是个男人。
”
“谁知道呢?
”K绷住了脸。
“K是恨我的。
恨我的八面玲珑。
啊,我明白了。
K相信我的坚强,高估我的才华。
因此,对于我的努力,对于我光鲜背后那些愚蠢的努力都一无所知。
就好像一个猴子剥藠头,剥呀剥呀,剥到最里面什么都没有。
可还是坚信,那里边一定有点儿什么东西。
于是便接着剥另一个,剥呀剥呀,剥到最后还是什么都没有。
这猴子的悲哀,又有谁能懂呢?
所谓的见一个爱一个,其实就是谁都不爱吧。
”
K拽了拽我的袖子。
我说话的声音很大,在乘客里很是突兀。
我笑了。
“我的宿命就在此处了。
”
在汤河原下了车。
“说是什么都没有,那都是骗人的。
”K一边换上旅馆的棉袍,一边说,“这棉袍的青色花纹,真漂亮啊,是不是?
”
“嗯。
”我带着倦意回答,“你是说刚才关于剥藠头的那番话?
”
“嗯,”K换完衣服,紧挨着我悄悄地坐下,“你不相信现在,那你能不能相信当下的这一刹那呢?
”
K像个少女那样天真地笑了,她伸着脖子,盯着我的脸。
“刹那不是任何人的罪过,也不是任何人的责任。
这我是知道的。
”我像个当家的那样双手环抱胸前,端坐在垫子上,“但对我而言,刹那也不能构成生命的喜悦。
我只相信死亡之时那一刹那的纯粹。
然而,这世上那些喜悦的刹那——”
“是害怕紧随喜悦之后的责任吗?
”
K有点起劲儿了,小声地问道。
“实在没法收场啊。
烟火只有一瞬,可肉体即便死去,却依然要以丑陋的形态残存在世上,还不知道要残存到什么时候。
若是在看见美丽极光的那一刹那,肉体就随之一同燃尽,那该多好。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
“真没志气。
”
“啊,对于语言,我已经感到厌倦了。
随你怎么说吧。
有关刹那的事情,就去问那些刹那主义者吧。
他们会挽着你的手一点一点教你的。
为人生添汁加味,每个人都对自己的那套烹调方法信心十足。
活在过去也好,委身刹那也罢,再不然就是寄希望于未来。
笨蛋与聪明人之间的分别,大约就在此处了吧。
”
“那你呢?
是个笨蛋吗?
”
“你可饶了我吧,K。
我们既不是笨蛋,也并非聪明人。
我们要糟糕得多。
”
“快说!
”
“布尔乔亚。
”
而且是落魄的布尔乔亚,仅仅背负着罪的记忆而活着。
两人意兴阑珊,便匆匆忙忙站了起来,拿了毛巾向楼下的浴场去了。
过去明日皆不可语。
只在这一刻,只在这情感满溢的一刻,于沉默中立下坚定的誓约,我也好,K也好,一同踏上旅程。
家中的琐事不可说,身上的痛苦不可说。
对于明日的恐惧不可说,对于为人的困惑不可说,对于昨日的耻辱不可说。
只有这一刻,至少在这一刻,能够得到安宁。
我们一边在心中祈祷,一边悄悄地洗刷身体。
“K,你看我肚子这里,有个伤疤对不对?
这是盲肠手术的时候留下来的。
”
K像母亲一样,温柔地笑了。
“K的腿很长,可你看,我的腿要更长对不对?
一般的裤子都穿不了。
还真是个麻烦的男人啊。
”
K凝视着昏暗的窗户,问道:
“你说,有没有善的恶行?
”
“善的恶行?
”我也出了神,嘴里喃喃着。
“下雨了?
”K忽然竖起耳朵听了起来。
“是山间的溪流,就从这下边流过。
早上的时候,浴场窗外满是红叶。
高耸的山峰就立在眼前,简直要让人惊讶得叫出声来。
”
“你时常来这儿吗?
”
“没有,就来过一次。
”
“为了寻死吗?
“
“对。
”
“那会儿有没有在附近走走?
”
“没有。
”
“今晚怎么样?
”K若无其事地问。
我笑了,道:
“什么呀,这就是K说的善的恶行吗?
哎呀,我还没——”
“什么?
”
我终于下定了决心,道:
“我想你会不会和我一同去寻死。
”
“啊,”这一次K笑了,“这有一种说法,叫作恶的善行。
”
我们慢悠悠地,一级一级地走上浴场长长的楼梯。
每登上一级,就念一次:
“善的恶行,恶的善行,善的恶行,恶的善行,善的恶行,恶的善行……”
我们叫了一个艺伎。
“我们两个人待着,有殉情的危险。
因此只好请你今晚看着我们不要睡觉。
要是死神来了,就把它赶跑。
”K一本正经地说。
“明白了,如有万一,我们就三个人一同殉情而死吧。
”艺伎回答。
我们点燃了纸捻儿,做起了游戏。
要在纸捻儿上的火灭掉之前,说出规定的事物,并把纸捻儿传递给下一个人。
毫无用处的东西,好,开始!
“裂了一只的木屐。
”
“不能跑的马。
”
“坏掉的三味线。
”
“照不了相的照相机。
”
“不亮的电灯泡。
”
“不能飞的飞机。
”
“那还有什么?
”
“快点儿快点儿。
”
“真相。
”
“啊?
”
“真相。
”
“什么蠢话,那么,忍耐。
”
“好难啊,那我说,辛劳。
”
“上进心。
”
“颓废。
”
“前天的天气。
”
“我。
”K说。
“我。
”
“那,那,那我也说——我。
”火灭了,艺伎输了。
“我都说了嘛,太难了。
”艺伎马上放松下来。
“都是玩笑话吧?
K,说什么真相啊,上进心啊,还有K自己都是没用的东西,都是玩笑话。
即使是我这样的男人,只要活着,就会尽可能地过得体面一点。
K呀,真是个笨蛋。
”
“那您还是请回吧。
”K也变得严肃起来,“就那么想在大家面前显摆自己的严肃和自己那严肃的痛苦吗?
”
艺伎的调子也不动听了。
“那我走,我回东京去。
给我钱,我走。
”我站了起来,把棉袍也脱了。
K抬头看着我的脸,哭了。
脸上还残留着些许笑容,哭了。
我不想回去,可没有一个人阻止我。
好,那就去死,去死。
我换了衣服,穿上袜子。
出了旅馆,我跑了起来。
站在桥上,凝望着桥下白色的山间溪流。
觉得自己是个笨蛋。
笨蛋,笨蛋,真的觉得自己是个笨蛋。
“对不起。
”不知何时,K已经悄悄地站在我的身后。
“可怜……可怜别人这种事,还请适可而止吧。
”我的眼泪淌了出来。
回到旅馆,两床褥子已经铺好。
我吃下一剂巴比妥,便立即装出睡着的样子。
没过多久,K也悄悄爬起来,吃了一剂同样的药。
第二天,在床上迷迷糊糊直到午后才醒。
K先起来了,打开走廊上的一扇窗。
下雨了。
我也起来了,没有和K说话,独自一人下楼去浴场了。
昨晚的事是昨晚的事,昨晚的事是昨晚的事——我一边勉强着说服自己,一边在宽敞的浴缸里轻轻游了起来。
从浴缸里出来,打开窗,便看见蜿蜒曲折的白色山溪从下面流过。
一只手突然冷冷地放在我的背上。
回过身来,是K。
她赤身裸体地站在那里。
“鹡鸰。
”K指着山溪岸边岩石上那只蹦跶着的小鸟,说,“真是过分,竟然有诗人会说鹡鸰像手杖。
鹡鸰其实更严肃,也更勇敢,根本不把人类放在眼里。
”
我心里也这么想。
K把身体滑进浴缸。
“红叶啊,真是漂亮的花。
”
“昨晚——”我欲言又止。
“睡得好吗?
”K天真地问,她的眼睛像湖水一样澄澈。
我扑通一下跳进浴缸。
“只要K活着,我就不会死,对不对?
”
“布尔乔亚,不好吗?
”
“我觉得不好。
寂寞也好,苦恼也好,感激也好,全都成了趣味。
自以为是地活着罢了。
”
“那么在意别人的风言风语,”K哗啦一下走出浴缸,快速地擦拭身体,“我觉得其实是因为有自己的肉体在那里吧。
”
“富人上天堂——”玩笑开了一半,脸上就像啪地挨了一鞭,“寻常人的幸福,似乎很难拥有啊。
”
K在沙龙里喝着红茶。
大约是下雨的缘故,沙龙里很热闹。
“要是这次旅行一路平安,”我和K肩并肩坐在能看见远山的窗边椅子上,“完事之后我应该送给K一件什么礼物呢?
”
“十字架。
”K小声说。
她的脖颈细细的,看起来十分纤弱。
“啊,要一杯牛奶。
”我吩咐完女服务生,接着说,“K,你果然还在生我的气。
我昨晚说的那些胡言乱语,要回去之类的话,都是演戏呢。
我啊——可能是得了舞台魔障吧。
一天里总要有这么一次装腔作势,不然就浑身不舒服,简直要活不下去。
即使现在坐在这里,我也在拼命装腔作势呢。
”
“那恋情呢?
”
“也有啊。
有一天晚上就因为过分在意自己袜子上的破洞而失恋了。
”
“喂,你觉得我的脸怎么样?
”K认真地把自己的脸伸了过来。
“怎么样?
怎么说呢?
”我皱起眉头。
“好看吗?
”感觉像个不认识的人,“看着年轻吗?
”
我想要痛打她一顿。
“K,你就那么寂寞吗?
K,你好好记着,你是贤妻良母,而我是不良少年,人中渣滓。
”
“只有你是。
”话音未落,女服务生端着牛奶来了。
“啊,谢谢。
”
“令人苦恼的东西,是自由。
”我啜饮着热乎乎的牛奶,“令人开心的东西,也是那个自由。
”
“可我却不是自由的,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不是。
”
我深深地叹了口气。
“K,后边有五六个男人,你觉得哪个好?
”
四个年轻人看上去像是在旅馆工作的人,正在打麻将。
另外两个中年男人正一边喝着威士忌,一边看报。
“最中间那个。
”K望着擦拭过远山面庞的那股流动的云雾,慢慢地说。
回头一看,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有一个青年站在沙龙的正中了。
他双手揣在兜里,正看着入口右边角落里的菊花插花。
“菊花很难插啊。
”K似乎在插花界的某一流派里很有地位。
“好像很久前见过。
啊,他的侧脸不是和晶助哥一模一样吗?
哈姆雷特。
”这位兄长,二十七岁时死了,很擅长雕刻。
“所以嘛,我也不怎么认识其他的男人啊。
”K似乎有点害羞。
“号外。
”
女服务生一边跑一边将报纸一张一张发给我们。
事变之后的第八十九天
我军已经全面包围上海。
敌军溃乱全线撤退。
①
K瞥了一眼:
“你呢?
”
“丙种。
”
“我是甲种。
”K大声笑了起来,几乎吓人一跳。
“我其实没有在看山,我其实是在看眼前房檐上垂落下来的雨滴的形状。
每一滴都有自己的个性。
有的像煞有介事似的,啪嗒一下落下来;有的则着急得很,瘦瘦小小地就落下来了;有的装模作样得很,落下来啪的一下,发出很大声响;有的就很无聊,哗地一下就被风吹下来了——”
K和我都已经疲惫不堪。
那天我们从汤河原出发,抵达热海的时候,街市正被暮霭所笼罩。
家家户户都点亮了灯火,模模糊糊的,让人颇为不安。
到达旅馆,想在晚饭之前散散步。
向店里借了两把伞,去了海边。
雨天的大海,无精打采地翻腾着,溅起冰冷的飞沫。
给人一种冷漠、敷衍之感。
回头看看街市,只是一些零星四散的灯光。
“小的时候,”K停下脚步,说起话来,“我曾用针在明信片上扑哧扑哧地扎小洞,再透过灯光去看。
那明信片上的洋楼啊森林啊军舰啊,都裹上了一层漂亮的霓虹——还记不记得?
”
“这样的风景,”我故意做出反应迟钝的样子,“我在幻灯片里见过,朦朦胧胧的,大家都看不太清楚。
”
我们沿着海岸大街安静而缓慢地走着。
“好冷啊,泡个温泉再出来就好了。
”
“我们已经别无所求了。
”
“嗯,父亲已经给了我一切。
”
“你那种想死的心境——”K蹲下擦着赤脚上的泥,“我明白。
”
“我们啊,”我像个十二三岁的少年那样天真地说,“为什么就不能靠自己活下去呢?
哪怕去打打鱼也好啊。
”
“谁都不会让我们这样做。
好像是故意的一样,每个人都把我们视为掌上明珠。
”
“对啊,K。
即使我故意做些顽劣不堪的事情,大家也只是笑笑——”一个钓鱼人的身影,进入了我的视线,“干脆啊,这一辈子就钓钓鱼,像个傻子一样活着就好了。
”
“那可不行哟,鱼的心思,你懂得太多啦。
”
两个人都笑了。
“你大概知道的吧?
我就是所谓的撒旦。
我爱上的人,全都被我毁掉了。
”
“我不觉得。
谁也不恨你呀。
你就喜欢装坏人。
”
“是不是很天真?
”
“啊,这个好像是神社的石碑。
”路边立着一个金色夜叉的石碑。
“我想说说最单纯的东西,K,我是真的,可以吗?
我——”
“够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
“真的?
”
“我什么都知道。
我还知道自己是父亲的情妇所生。
”
“K,我们——”
“啊,危险!
”K挡在我的身前。
K的伞被巴士的车轮碾过,发出嘎啦嘎啦的声音。
K的身体也像游泳潜水一样,嗖的一下就化成了一道白色的直线,紧跟着雨伞一起被拽进了滴溜滴溜转着的车轮下面。
“停车!
停车!
”
我仿佛遭了当头一棒,愤怒不已。
使劲踹着好不容易才停下来的巴士的侧面。
K趴在巴士的下面,像一朵被雨打湿的桔梗花一样美。
这个女人,是个不幸的人。
“谁都不许碰她!
”
我抱起神志不清的K,放声大哭。
我背着K一直走到附近的医院。
K一边哭一边用微弱的声音说着:
“好疼,好疼。
”
K在医院待了两天,便同驱车赶来的家人一道坐车回去了。
我一个人坐火车回去了。
K的伤似乎并不严重,身体日渐好转。
三天前,我有事去了一趟新桥。
回来的时候去银座走了走,忽然瞧见一家店的展示橱窗里有一个银十字架,便走进了那家店,没有买银十字架,而是买了架子上的一枚青铜戒指。
那天晚上,我兜里刚好有一点钱,是从杂志社那里刚刚领来的。
那枚青铜戒指上,镶着一块黄色石头雕成的水仙花。
我把这枚戒指寄给了K。
作为回礼,K给我寄了一张明信片,上面是她三岁的大女儿的照片。
今天早上,我收到了明信片,看到了那张照片。
新树的话语
甲府是盆地,四面环山。
小学的时候学地理,刚刚接触盆地这个词,老师就为我们做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和说明。
可无论如何,我都难以想象盆地的实景。
来到甲府之后,我才第一次点点头,感叹道:
原来是这个样子。
排干这片巨型沼泽里的水,在沼泽的底部开垦田地,建设家园:
这就是盆地。
不过,要造出像甲府这么大的一块盆地来,只怕是要排干周围五六十里的湖水才能办得到。
沼泽的底部,说起来有点儿不可思议。
我本以为甲府是个多多少少有那么点儿阴郁的城市。
事实上,甲府却是个漂亮活泼的小城。
有很多人说甲府是“研钵底子”,这话并没有说到点子上。
甲府其实要洋气得多。
把高筒礼帽倒放过来,在帽子的底部,立着一座小小的旗帜。
要这么形容甲府,才算得上准确。
甲府,是一座浸染着美好文化的城市。
今年早春时节,我曾在此工作过一小段时间。
住得离公共澡堂很近,下雨天里,也不撑伞,就径直去了。
路上,同披着雨斗篷的邮递员打了个照面。
“啊,正巧碰见你。
”邮递员小声叫住了我。
我倒也并不十分惊讶,心想着应该是有寄给我的邮件。
笑也没顾上,一句话也没说,就直接把手向他伸了过去。
“不是,今天没有你的邮件。
”邮递员微笑着说道,鼻尖的雨滴闪着光。
是个年纪在二十二三岁的红脸青年。
脸上的表情十分可爱:
“您是青木大藏先生,对吧?
”
“嗯,是我。
”这个青木大藏,是我原来的户籍名字。
“很像啊。
”
“什么?
”我心里有点慌张。
邮递员眯起眼睛笑了。
被雨打湿的两个人,就这么在路上面对面站着,这会儿谁也没有说话。
有点奇怪。
“那知道幸吉吗?
”他以一种近乎讨厌的亲昵语调问道,口气还似乎带着些许嘲弄,“内藤幸吉啊,您知道吗?
”
“是内藤幸吉吗?
”
“对对,就是他。
”邮递员好像已经认定我认识这个人,满脸自信地点着头。
我又想了想,说:
“不认识。
”
“是吗?
”这次,邮递员严肃地把头一歪,“您老家是津轻的吧?
”
总不能这么一直站在这里被雨淋,于是我便溜到豆腐店的屋檐下躲雨。
“请来这边说话,雨越下越大了。
”
“好。
”他也大大咧咧走了过来,同我肩并肩在豆腐店的屋檐下躲雨,“是津轻的吧?
”
“嗯。
”我的语气十分不愉快,自己听了都吓一跳。
但凡提到我的老家,哪怕只是只言片语,我也会感到万分的沮丧和痛苦。
“那就对了。
”邮递员笑了,桃花般的脸上露出了酒窝,“那您就是幸吉的哥哥了。
”
不知为何,我的心跳加快了,一阵厌恶感油然而生。
“您说的这话可真奇怪。
”
“不,这回错不了了。
”他一个人欢欣鼓舞起来,“真像啊。
幸吉一定会很高兴吧。
”
他像只燕子似的,轻巧地跳进了雨中的街道。
“那我先走了。
”他跑了几步,又回过头来,“我现在就去告诉幸吉。
”
豆腐店的屋檐下就剩我一个人了,好似做了一场梦,白日梦。
就是这种感觉,一点儿也不真实。
真是荒唐透顶。
也没管那么多,又继续往澡堂走了。
等到身体已经泡在浴缸里时,开始慢慢思量起来,便又觉得十分不愉快。
不知怎的,就是让人不舒服。
就好像我正舒舒服服睡着午觉呢,谁也没得罪,就突然飞来一只蜜蜂,在我脸上叮了一下。
就是这种感觉,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为了避开东京的诸多恐怖,我悄悄来到甲府,住址也没敢让任何人知道。
就这么安安稳稳地,一点一点儿地推进自己那点儿微薄的工作。
这段时间好不容易弄出了点儿眉目,心情稍微好一点儿了。
现在又来了,真是无妄之灾。
那些莫名其妙的家伙,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在眼前,对我笑,同我搭讪。
我被这些妖怪团团围住,别说招呼寒暄了,光是想想这些家伙在我面前走来走去,就让人十分难受。
也不是因为工作或者其他的什么事情,只是这样不负责任地过来挠我一把,然后扔下一句“啊,对不起,认错人了”,就跑掉了。
一定是这样。
内藤幸吉。
想来想去,我也不认识这么一个家伙。
而且还说是我的什么兄弟,也真是一通蠢话。
一定是认错人了,就是这样。
下次再碰见,一定得跟他把事情说清楚了。
可尽管如此,心中的这般不快,究竟因何而起呢?
就是因为这通蠢话!
开什么玩笑!
一个全不相识的人竟开口对我说:
“哥呀,真的好久不见啊。
”真是令人作呕,一股子温温热热,黏黏糊糊的作态,连喜剧都算不上,是愚蠢,廉价。
我感到自己受到了无法忍受的侮辱,心中憋屈不过,便从浴缸里爬了出来。
站在更衣室的镜子前,看着镜子里自己的脸,竟然异常地凶恶。
我感到不安。
我又回忆起过去的那些悲惨:
今天这件意料之外的事情,岂不是要再次逆转我的生活,重新将我重重地摔入谷底?
这突如其来的难题,真是个难题啊。
我拿这个只是荒唐却一点儿也不可笑的难题完全没有办法。
到头来,心情也变得阴郁惨淡。
回到了旅馆,也只是毫无目的地撕着那些还没写完的稿纸。
而这时,为这场灾难所滋养浇灌的劣根性也抬起头来。
“如此不爽,还工作个屁。
”好像给自己找理由一样,我一边咕哝,一边从壁橱里拿出一瓶一升装的甲州产白葡萄酒,倒进茶杯里,咕嘟咕嘟地喝了。
喝醉后把被子拉上来盖了就睡了。
同别人一样,这大概也是个愚蠢至极的家伙。
我被旅馆的女侍叫醒了。
“您好,有客人来了。
”
“来了!
”我猛地跳了起来,“请带他进来。
”
灯还亮着。
纸拉门是浅黄色的。
大概六点吧。
我赶紧把被子塞进榻榻米的壁橱里,收拾了一下房间,披上和服外套,绑好扣子,然后在桌旁坐好,摆出一副正襟危坐的架势。
异样的紧张。
这般奇妙的经历,即使于我来说,此生也恐怕不会再有第二次。
客人只有一位,穿着一身久留米碎纹布的衣服。
女侍带他进来之后,他一声不响地在我面前坐下,恭恭敬敬地给我鞠了长长的一躬。
我当即慌张起来,手忙脚乱地,也没给他回礼。
“认错人了。
实在对不住,可真的是认错人了。
真是件荒唐事。
”
“不。
”他低声说,身体却依旧保持着鞠躬的姿势。
抬起来的那张脸是一副端正面孔。
眼睛太大了些,反倒给人一种虚弱和奇怪的感觉。
可除此之外的额头、鼻子、嘴唇和下巴都好似雕刻一样棱角分明。
跟我一点儿也不像。
“阿鹤的孩子,您忘了吗?
母亲曾给您当过奶妈。
”
经他这么一番开门见山的说明,我才恍然大悟,简直激动得要跳起来。
“啊,对了,对了,对了。
”我大声笑了起来,声音大得连我自己都觉着不像话,“啊,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你吗?
”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话说了。
“嗯。
”幸吉也爽朗地笑了,露出洁白的牙齿,“一直都想着什么时候能跟您见上一面呢。
”
好小伙子。
真是个好小伙子。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我高兴极了,是那种简直要高呼万岁的高兴,高兴得身体仿佛都不听使唤了。
真是莫大的喜悦,所谓高兴得近乎于苦涩,就是这种喜悦。
我刚出生不久,就被托付给奶妈照顾了。
具体的原因不太清楚,大约母亲的身体虚弱吧。
奶妈的名字叫鹤,是津轻半岛一个渔村里来的。
人还年轻,丈夫和孩子都相继死去,只有她一个人生活,被我家里瞧见了,就雇了来。
这个奶妈,从始至终都坚定地支持我,还告诉我,一定要成为这世界上最伟大的人。
阿鹤一门心思全都扑在我的教育上。
我五六岁的时候,她十分担心我被别的女佣娇惯。
便一本正经地坐下一点一点给我讲大人的道德:
哪个女佣好,哪个女佣坏,为什么她好,为什么她坏。
这些事情,直到现在我都未忘记。
她念各种各样的书给我听,攥着我的手,片刻都不放。
六岁的时候,阿鹤带我来到村里的小学。
我记得很清楚,是三年级教室的后面,有一个空桌子。
阿鹤就让我坐在那听课。
阅读没什么问题,可到了算术课,我就哭了。
什么都不懂,一点儿都不会。
阿鹤也一定感到很抱歉吧。
可那个时候,我就是想让阿鹤难堪,于是便大张旗鼓地哭了起来。
那时,我把阿鹤当成妈妈。
而第一次知道自己真正的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