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docx
《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docx(3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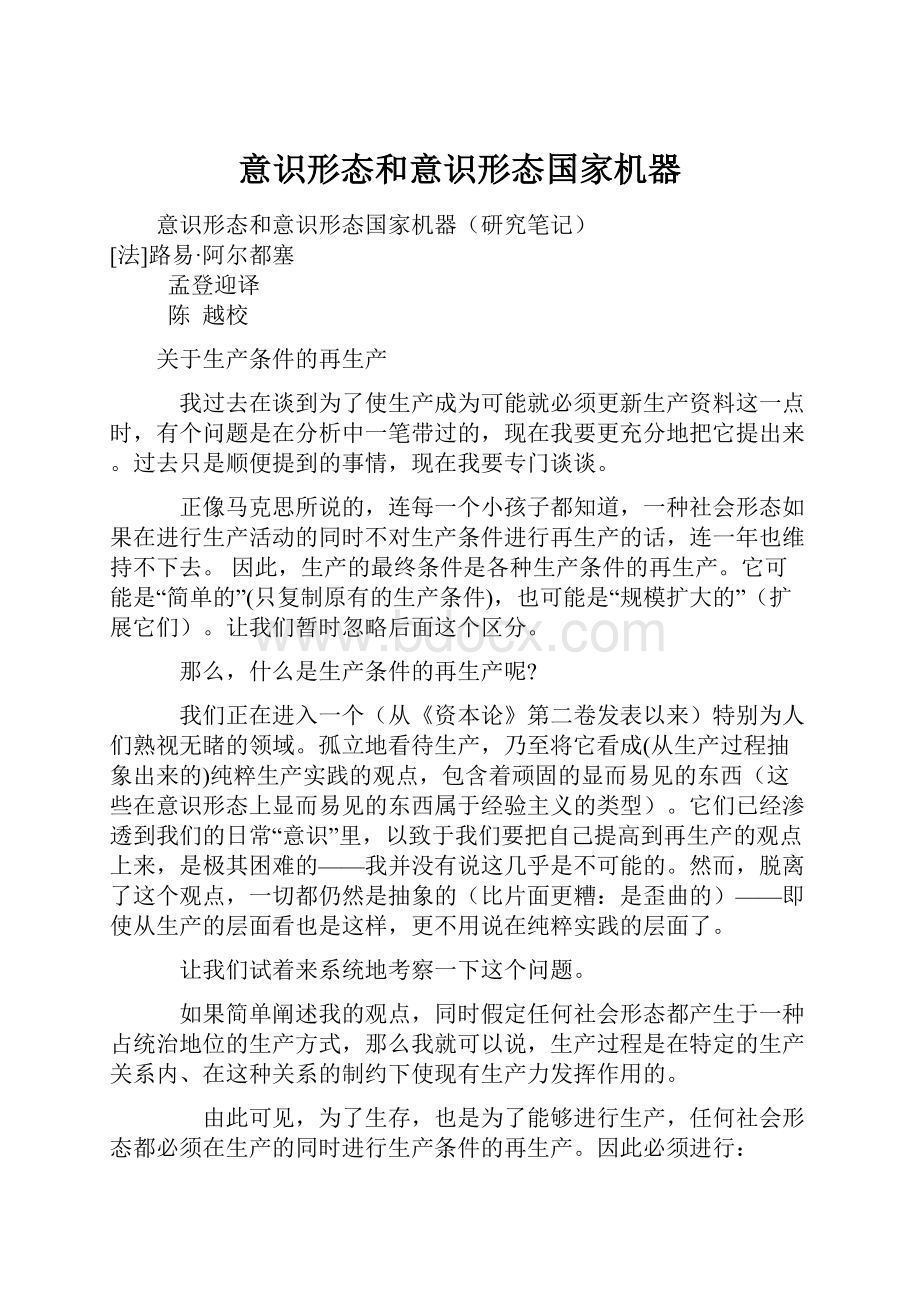
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笔记)
[法]路易·阿尔都塞
孟登迎译
陈 越校
关于生产条件的再生产
我过去在谈到为了使生产成为可能就必须更新生产资料这一点时,有个问题是在分析中一笔带过的,现在我要更充分地把它提出来。
过去只是顺便提到的事情,现在我要专门谈谈。
正像马克思所说的,连每一个小孩子都知道,一种社会形态如果在进行生产活动的同时不对生产条件进行再生产的话,连一年也维持不下去。
因此,生产的最终条件是各种生产条件的再生产。
它可能是“简单的”(只复制原有的生产条件),也可能是“规模扩大的”(扩展它们)。
让我们暂时忽略后面这个区分。
那么,什么是生产条件的再生产呢?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从《资本论》第二卷发表以来)特别为人们熟视无睹的领域。
孤立地看待生产,乃至将它看成(从生产过程抽象出来的)纯粹生产实践的观点,包含着顽固的显而易见的东西(这些在意识形态上显而易见的东西属于经验主义的类型)。
它们已经渗透到我们的日常“意识”里,以致于我们要把自己提高到再生产的观点上来,是极其困难的——我并没有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脱离了这个观点,一切都仍然是抽象的(比片面更糟:
是歪曲的)——即使从生产的层面看也是这样,更不用说在纯粹实践的层面了。
让我们试着来系统地考察一下这个问题。
如果简单阐述我的观点,同时假定任何社会形态都产生于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那么我就可以说,生产过程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内、在这种关系的制约下使现有生产力发挥作用的。
由此可见,为了生存,也是为了能够进行生产,任何社会形态都必须在生产的同时进行生产条件的再生产。
因此必须进行:
1.生产力的再生产,
2.现存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生产资料的再生产
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做出了强有力的证明,所以,现在所有的人(包括那些从事国民经济核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家”)都认识到,任何生产都不可能不考虑生产的物质条件的再生产,即生产资料的再生产。
一般的经济学家都知道,每一年都必须预见需要用什么东西来替补那些在生产中被消耗或损耗掉的东西:
原料、固定设备(厂房)、生产工具(机器)等等。
在这一点上,他们和一般的资本家没有什么差别。
我说一般的经济学家=一般的资本家,是因为他们都表达了企业的观点,都仅仅满足于对企业财务核算的实践进行讨论。
多亏天才的魁奈首先提出了这个“刺眼的”难题,也多亏天才的马克思解答了这个难题。
于是我们懂得,不能在企业的水平上思考生产的物质条件的再生产,因为在这个水平上,这种再生产并没有获得它存在的实在条件。
在企业水平上所发生的只是一种后果,它只能给人一个关于再生产必要性的观念,但绝对不能让人考虑到再生产本身的条件和机制。
片刻的反省就足以确信这一点:
一个开纱厂生产羊毛线的资本家X先生,必须“再生产”他的原料、他的机器等等。
但他本人并不为了自己的生产来生产这些东西——别的资本家为他生产:
比如澳大利亚的牧场主Y先生、生产机床的重型机械商Z先生,等等,等等。
有了他们的产品,才有了X先生的生产条件再生产本身的条件,而Y先生和Z先生为了生产这些产品,也必须进行自己的生产条件的再生产,以此类推,直至无穷——从国内到世界市场,整个都照此进行,从而对(用于再生产的)生产资料的需求都可以通过供给来满足。
这种机制造成了一根“无穷无尽的链条”;要思考它,就必须追随马克思所说的“全球”进程,特别要研究《资本论》第二、三卷讨论的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和第二部类(消费资料的生产)之间的资本流通关系、以及剩余价值的实现。
我们不打算深入分析这个问题。
关于生产的物质条件的再生产,我们只要指出它的必要性的存在就足够了。
劳动力的再生产
然而,读者不会没有注意到一件事。
我们刚才讨论的是生产资料的再生产,而不是生产力的再生产。
因此我们漏掉了把生产力和生产资料区别开来的那个劳动力的再生产。
通过观察在企业中发生的事情,特别是通过考察对分期偿还和投资进行预测的财务核算实践,我们能够获得关于再生产的物质过程存在的粗略观念。
但对于我们现在要进入的这个领域来说,只观察在企业中发生的事情,即便不是完全盲目,至少也是近乎如此了。
原因很简单:
因为劳动力的再生产从根本上说是在企业之外进行的。
劳动力的再生产是如何得到保障的呢?
劳动力的再生产是通过付给劳动力用于自身再生产的物质资料——即通过工资来得到保障的。
工资在每个企业的核算中都举足轻重,但那只是作为“工资资本” ,根本不是作为劳动力物质再生产的条件。
然而,这实际上就是工资“起作用”的方式,因为它只代表劳动力消耗所产生的价值的一部分,也就是劳动力再生产所必不可少的那部分价值,也就是恢复雇佣劳动者的劳动力所必不可少的那部分价值(为了支付衣、食、住,简言之,为了让雇佣劳动者在第二天——以及上帝让他多活的每一天——再次出现在工厂门口所需要的费用)。
我们还应该补充说:
这部分价值也是抚养和教育子女所必不可少的,无产者也在子女的繁衍中(以 n=0,1,2,……的任意数模式)进行着自身劳动力的再生产。
请记住,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这个价值量(工资),不单单取决于对“生物学的”最低保障金的需要,而且还取决于历史的最低限度的需要(马克思特别提到,英国工人需要啤酒,而法国无产者需要葡萄酒),即一种随历史变动的最低限度的需要。
我还想指出,这个最低限度在两方面是历史性的,因为它不是由资本家阶级能够“承认”的工人阶级的历史需要所规定的,而是由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两方面的阶级斗争:
反对延长工作日和反对降低工资)能够强加进来的历史需要所规定的。
然而,仅仅保障劳动力再生产的物质条件并不足以进行劳动力本身的再生产。
我说过,有效的劳动力必须是“合格的”,即适合在生产过程的复杂体系内从事工作。
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特定历史阶段由生产力构成的统一体类型,都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劳动力必须拥有(各种各样的)的技能,并以这种方式获得再生产。
而各种各样的技能是根据社会技术分工及其不同“工作”、“岗位”的要求来划分的。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力(多样化)技能的再生产是怎样获得的呢?
在这里,与奴隶制或农奴制特点的社会形态不同的是,劳动力技能的再生产(作为大趋势)倾向于越来越少地(通过生产内部的学徒期)“当场”获得,而是越来越多地在生产之外,通过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以及其它场合和机构来完成。
孩子们在学校里学到了什么呢?
他们在学业上会有各种各样的差距,但至少学会了读、写、算之类的许多技法,同时也学到了许多别的东西,包括“科学”或“文学教养”的要素(它们可能是初步的,也可能正好相反,是深入的)。
这些教养直接有助于在生产中从事不同的工作(有的学校培养体力劳动者,有的培养技术人员,有的培养工程师,还有的培养高层管理人员,等等)。
就这样,他们学到了“本领”。
但在学习这些技法和知识的同时,孩子们在学校还要另外学习良好的行为“规范”,即每个当事人在分工中根据他们“被指定”要从事的工作所应遵守的姿态:
道德规范、公民良知和职业良知;实际上就是关于尊重社会技术分工的规范,说到底,就是由阶级统治建立起来的秩序的规范。
他们还要学会“讲体面的法语”,学会正确地“管理”工人,即实际上(作为未来的资本家及其雇员)学会恰当地“使唤他们”,也即(在理想情况下)学会用正当的方式“对他们讲话”,等等。
更科学的说法就是,劳动力的再生产不仅要求再生产出劳动力的技能,同时还要求再生产出劳动力对现存秩序的各种规范的服从,即一方面为工人们再生产出对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服从,另一方面为从事剥削和镇压的当事人再生产出正确运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能力,以便他们也能“用词句”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做准备。
换言之,学校(还有像教会这样的其它国家机构,像军队这样的其它机器)给人传授“本领”,无非是以保障人们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臣服或者保障他们掌握这种“实践”的形式进行的。
所有那些从事生产、剥削和镇压的当事人,更不用说那些“意识形态专家”(马克思语),为了要“凭良心”克尽职守——被剥削者(无产者)、剥削者(资本家)、剥削者的助手(管理者)或者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权威(它的“官员”)等等各自的职守——都必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浸染”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当中。
由此可见,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不仅要再生产出劳动力的“技能”,而且要再生产出它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臣服或这种意识形态本身的“实践”。
甚至只说“不仅……而且……”都是不够的,因为很明显,只有在意识形态臣服的形式下并受到这种形式的制约,才能为劳动力技能的再生产做好准备。
但是,这就要承认一种新的现实——意识形态——的实际存在。
在这里我要做两点说明。
第一点旨在完成我对再生产的分析。
我刚刚迅速浏览了生产力再生产的两种形式,其一是生产资料的再生产,其二是劳动力的再生产。
但是,我还没有触及到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的问题。
对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来说,这是一个决定性的问题。
放过这个问题将是一个理论失误——说得再坏点,就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
所以,我准备讨论这个问题。
但是为了获得讨论它的手段,我还不得不再兜一个大圈子。
第二点说明是,为了兜这个圈子,我必须重提我的老问题:
什么是社会?
基础和上层建筑
在许多场合 ,我都强调过马克思主义“社会整体”观念的革命性,在这方面它跟黑格尔的“总体”是截然不同的。
我说过(而这个论点只是对历史唯物主义著名命题的重复),马克思把任何社会的结构都设想成是由不同的“层面”或“诉求”所构成的,这些“层面”和“诉求”又被一种独特的决定作用连接在一起:
基础或经济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和上层建筑。
上层建筑又包括两个“层面”或“诉求”:
一个是政治-法律的(法律和国家),另一个是意识形态(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
宗教的、伦理的、法律的、政治的,等等)。
这种表述除了有理论教学上的好处 (揭示了马克思和黑格尔的不同)之外,还有这样一种决定性的理论优势:
它使我们有可能把我所说的这些基本概念各自的有效性指数纳入这些概念的理论体系。
这是什么意思呢?
很容易看出,这个表述把任何社会结构都说成是一座大厦,它有一个地基(基础),上面竖立着两“层”上层建筑,这是一个隐喻,更准确地说,是一个空间的隐喻,一个地形学的隐喻 。
像任何隐喻那样,它暗示着某件事情,让这件事情可以被人看到。
什么事情呢?
那便是:
上层如果不是明确地坐落在它们的基础上,是不会独自“矗立”(在空中)的。
因此,大厦这个隐喻的目的首先是要表述经济基础“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
这个空间隐喻的作用就是赋予基础一种有效性指数,这种指数可以通过那些著名的说法来了解:
在那些上“层”(属于上层建筑)中所发生的事情归根到底是由在经济基础中所发生的事情决定的。
从这种“归根到底”的有效性指数出发,上层建筑的各“层”显然都被赋予了不同的有效性指数。
是些什么样的指数呢?
人们可以说,上层建筑的各层不具有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它们都是由基础的有效性所决定的;假如它们也以各自的(至今还没有得到明确规定的)方式具有某种决定作用,那也只有在被基础决定的范围内才是可能的。
它们的有效性指数(或决定作用)是由基础的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所决定的,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则是从两个方面来考虑的:
(1)上层建筑对基础有“相对独立性”;
(2)上层建筑对基础有“反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地形学即关于大厦(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空间隐喻有着巨大的理论优势,它既揭示出决定作用(或有效性指数)是问题的关键,又揭示出正是基础归根到底决定了整个大厦;结果是,它使我们不得不提出关于上层建筑特有的那些“派生的”有效性类型的理论难题,也就是说,它使我们不得不思考马克思主义传统一并称之为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和上层建筑对基础的反作用的问题。
用大厦的空间隐喻来表述任何社会结构,最大的缺点显然在于:
这种表述实际上是隐喻性的,即它仍然是描述性的。
现在在我看来,有可能也有必要用另外的方式来表述这些事情。
注意:
我这样说的意思,不是要抛弃这个经典的隐喻,因为是这个隐喻本身要求我们去超越它。
而我现在超越它并不是想要把它当旧货扔掉。
我只是试图在思考,它以这种描述的方式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
我相信,我们可以而且必须从再生产出发去思考上层建筑的存在和性质的本质特征。
一旦采取了再生产的观点,由大厦的空间隐喻所指出、却又不能用概念来解答的许多问题,都会豁然开朗了。
我的基本论点是:
如果不采取再生产的观点,我们就不可能提出(并解答)这些问题。
我将从这一观点出发,对法律、国家和意识形态做出简要的分析。
我将表明,从实践和生产的观点出发和从再生产的观点出发,分别会发生什么情况。
国 家
马克思主义传统在这里是很严格的:
在《共产党宣言》和《雾月十八日》中(以及在后来所有的经典文本中,尤其是在马克思有关巴黎公社的作品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国家都被直截了当地说成是一套镇压性的机器。
国家是一种镇压的“机关”,它使得统治阶级(在19世纪是资产者阶级和大土地所有者“阶级”)能够确保他们对工人阶级的统治,使得统治阶级能够利用这种机关去强迫工人阶级服从于对剩余价值的榨取过程(即服从于资本主义剥削)。
因此,国家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称作的国家机器。
这个说法的含义,不仅指那些专门化的(狭义上的)机器,即警察、法庭和监狱——我曾经联系法律实践的需要说明了它们的存在和必要性;还指军队,当警察及其专门化辅助队伍“无法控制事态”时,它归根到底会作为追加的镇压力量直接干预进来(无产阶级为这一经验付出过血的代价);而且还指在这个一切之上的国家元首、政府和行政机关。
以这种形式提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理论”真正指明了事情的本质,任何时候没有任何疑问可以否认这确实就是事情的本质。
国家机器把国家定义为在资产阶级及其同盟者所展开的反对无产阶级的斗争中,“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实施的镇压和干预的力量;这样的国家机器才是真正的国家,才真正定义了它的基本“功能”。
从描述性的理论到理论本身
然而,在这里也像我关于大厦的隐喻(基础和上层建筑)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对国家性质的表述也仍然带有几分描述性。
由于我以后还要经常使用这个形容词(“描述性的”),为了避免语义含混,有必要做些解释。
在提到大厦隐喻或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时,我说这些都是对对象的描述性的观念或表述,其实我这么说并没有任何隐蔽的批评动机。
相反,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伟大的科学发现都不得不经过我要称之为“描述性的‘理论’”的这个阶段。
这是所有理论的第一个阶段,至少我们所关心的领域(关于社会形态的科学的领域)是这样。
如此说来,人们也可以——依我看就是必须——把这个阶段看成是理论发展必要的过渡阶段。
在我的表达方式(“描述性的理论”)里,就已经暗示了这种过渡性,因为它在词语的组合中显示出带有几分“矛盾”的对应关系。
事实上,理论这个说法在某种程度上与我加在它前面的“描述性的”这个形容词是“相抵触的”。
这恰好意味着:
(1)“描述性的理论”确实是理论的不可改变的开端,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
(2)理论表现出“描述性的”形式,这个“矛盾”的后果恰恰要求理论的发展去超越“描述”的形式本身。
让我回到我们目前讨论的对象——国家——上来,进一步阐明这个观念。
当我说我们现在可以运用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仍然带有几分“描述性”的时候,首先是指这种描述性的“理论”毫无疑问正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开端;这个开端为我们说明了事情的本质,即决定这一理论今后一切发展的原则。
我甚至可以说这种描述性的国家理论是正确的,因为在它所关心的这个领域里出现的绝大多数事实,完全可以符合它给自己对象所下的定义。
例如,把国家定义为存在于镇压性国家机器中的阶级国家,能够洞若观火地说明我们在任何领域的不同层面的镇压中可以观察到的所有事实:
从1848年6月、巴黎公社、1905年5月的彼得格勒“流血星期日”、抵抗运动、夏龙等等发生的历次大屠杀,到“审查”制度单纯的(相对和缓的)干预,例如对狄德罗的《修女》或加蒂(Armand Gatti)关于佛朗哥的戏剧的查禁;它能够说明所有直接或间接的剥削形式和灭绝人民大众的形式(帝国主义战争);它能够说明那种微妙的日常统治,我们可以在这种统治底下,比如在各种政治民主形式中,窥见列宁遵循马克思的观点称之为资产阶级专政的东西。
然而,描述性的国家理论仅仅代表了理论构成过程本身需要“替代”掉的一个阶段。
因为很清楚,这个定义把压迫的事实与国家联系在一起,把国家看作镇压性的国家机器,如果说这个定义的确能给我们提供辨别和认识这些事实的手段,那么,这种“相互关系”就会变成一件特别显而易见的事情(这一点我马上就要加以说明):
“是的,就是这么回事,真是这样的!
” 在国家的定义内部,事实的积累会使例证成倍地增加,却不会真正地促进对国家的定义(即科学的国家理论)。
因此,任何描述性的理论都冒着“阻碍”理论发展的风险,而发展才是根本。
因此我认为,为了把这种描述性的理论发展成为理论本身,即为了进一步理解国家发挥功能的机制,就必须在把国家规定为国家机器的这个经典定义上再做些补充。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要点
让我先来澄清很重要的一点:
如果不把国家(及其在国家机器中的存在)看作国家政权的功能,它就没有任何意义。
全部政治性的阶级斗争都是围绕着国家展开的。
我的意思是指,它是围绕着由某个阶级、由阶级或阶级的某些部分之间的联盟占有(即夺取并保持)国家政权的过程展开的。
首先做出的这点澄清使我不得不把作为政治性阶级斗争目标的国家政权(保持政权或夺取政权)与国家机器区分开来。
我们知道,国家机器是可以长期存在下去的,就像十九世纪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1830、1848)、政变(12月2日和1958年5月)、国家的崩溃(1870年帝国的垮台、1940年第三共和的垮台)、小资产阶级的上台(1890—1895年的法国)等等所证明的那样,它们都没有触动或改变国家机器;国家机器在经历了影响国家政权归属的政治事件之后,仍然可以存在下去。
甚至在像1917年那样的社会革命之后,在无产阶级和小农的联盟夺取了国家政权之后,大部分国家机器仍然保存了下来。
列宁一再重申了这个事实。
可以说,国家政权和国家机器之间的这种区分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组成部分,从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和《法兰西的阶级斗争》以后就明确地存在着这个区分。
从这一点上来概括“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我们就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主张:
(1)国家是镇压性的国家机器;
(2)必须对国家政权和国家机器加以区分;(3)阶级斗争的目标在于国家政权,因此在于利用国家机器——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以及阶级或阶级的某些部分之间的联盟)可以利用国家机器的功能来实现他们阶级的目标;(4)无产阶级必须夺取国家政权,以便打碎现存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在第一阶段代之以完全不同的无产阶级国家机器,接着在随后的阶段,进入一个彻底的过程,即国家消亡(国家政权的终结、一切国家机器的终结)的过程。
由此看来,我原打算给“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补充的东西是早已明确存在了的。
可在我看来,即使补上了这一点,这个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描述性的;虽说它现在的确包含了一些复杂的和差异的要素,但要理解这些要素发挥功能的方式和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补充理论的发展。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Appareils Idéologiques ďEtat)
因此,必须给“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补充别的东西。
在这里,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踏进一个领域。
其实在我们之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进入这个领域了,只是他们没有用理论的形式,把他们的经验和做法中隐含的明确前提系统地提出来。
他们的经验和做法也确实主要限于政治实践的领域。
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实践中,他们所看待的国家是一个比“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对国家的定义更为复杂的现实——即使这个定义已经像我刚才提议的那样做了补充。
他们在实践中认识到了这种复杂性,却没有用相应的理论来表达它。
我想试着为这个相应的理论做出一个非常图式化的概括。
为此,我提出以下论点。
为了推进国家理论,不仅必须考虑到国家政权与国家机器的区分,而且还必须考虑到另一种现实——它显然是和(镇压性)国家机器并立的,但一定不能与后者混为一谈。
我用一个概念把这种现实叫做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什么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AIE)呢?
一定不能把它们与(镇压性)国家机器混为一谈。
别忘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家机器(AE)包括政府、行政机关、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等,它们构成了我今后要称作镇压性国家机器的东西。
“镇压性”意味着上述国家机器是“通过暴力发挥功能”的——至少最终会是这样(因为镇压也可以采取非肉体的形式,比如行政压制)。
我所说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这样一些现实,它们以一些各具特点的、专门化机构的形式呈现在临近的观察者面前。
我给这些现实开出了一个经验性的清单,它显然还必需接受仔细的考察、检验、修改和重组。
尽管有这种需要包含着的所有保留意见,我们暂时还是可以把下列机构看成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我列举的顺序没有任何特殊的含义):
——宗教的AIE(由不同教会构成的制度),
——教育的AIE(由不同公立和私立“学校”构成的制度),
——家庭AIE,
——法律的AIE,
——政治的AIE(政治制度,包括不同党派),
——工会AIE,
——传播AIE(出版、广播、电视等等),
——文化的AIE(文学、艺术、体育等等)。
我说过,AIE不能与(镇压性)国家机器混为一谈。
那么,是什么构成了它们的区别呢?
第一点,很明显,(镇压性)国家机器只有一个,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却有许多。
即使我们假定存在着一个由许多AIE构成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也不是直接可以看到的。
第二点,很明显,统一的(镇压性)国家机器完全属于公共领域;与之相反,绝大部分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它们显然是分散的)是私人领域的组成部分。
教会、党派、工会、家庭、某些学校、大多数报纸、各种文化投机事业等等,都是私人性的。
我们可以暂时不管第一点。
但一定会有人对第二点提出疑问,问我凭什么把大部分不具有公共地位而完全只是私人性质的那些机构看成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呢?
作为一个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早已用一句话堵住了这种反对意见。
公私之分是资产阶级法律内部的区分,在资产阶级法律行使“权威”的(从属)领域 是有效的。
而国家领域避开了这种区别,因为国家“高于法律”:
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国家,既不是公共的,也不是私人的;相反,国家是公共与私人之间一切区分的前提。
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出发,我们也可以这样说。
它们在“公共”机构还是“私人”机构中得到实现,这并不重要,问题在于它们如何发挥功能。
私人机构完全可以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发挥功能”。
对任何一种AIE进行彻底的理性分析,都能证明这一点。
现在谈一下什么是根本的东西。
区分开AIE与(镇压性)国家机器的基本差别是:
镇压性国家机器“运用暴力”发挥功能,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则“运用意识形态”发挥功能。
我可以修改一下这个区分,把问题说清楚。
我应该说,任何国家机器,无论是镇压性的,还是意识形态的,都既运用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