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佑天历间雅正诗风及其形成.docx
《延佑天历间雅正诗风及其形成.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延佑天历间雅正诗风及其形成.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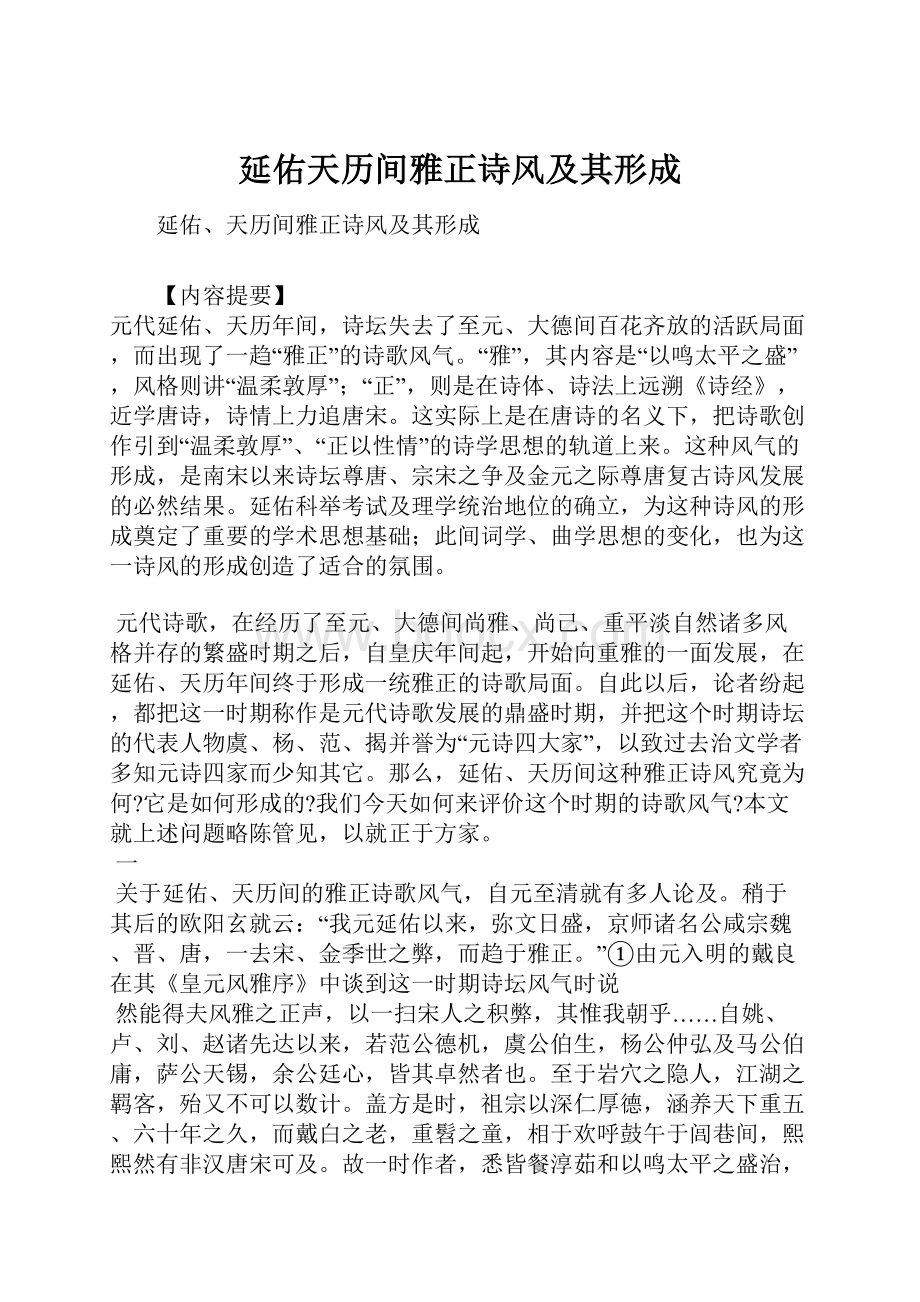
延佑天历间雅正诗风及其形成
延佑、天历间雅正诗风及其形成
【内容提要】
元代延佑、天历年间,诗坛失去了至元、大德间百花齐放的活跃局面,而出现了一趋“雅正”的诗歌风气。
“雅”,其内容是“以鸣太平之盛”,风格则讲“温柔敦厚”;“正”,则是在诗体、诗法上远溯《诗经》,近学唐诗,诗情上力追唐宋。
这实际上是在唐诗的名义下,把诗歌创作引到“温柔敦厚”、“正以性情”的诗学思想的轨道上来。
这种风气的形成,是南宋以来诗坛尊唐、宗宋之争及金元之际尊唐复古诗风发展的必然结果。
延佑科举考试及理学统治地位的确立,为这种诗风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学术思想基础;此间词学、曲学思想的变化,也为这一诗风的形成创造了适合的氛围。
元代诗歌,在经历了至元、大德间尚雅、尚己、重平淡自然诸多风格并存的繁盛时期之后,自皇庆年间起,开始向重雅的一面发展,在延佑、天历年间终于形成一统雅正的诗歌局面。
自此以后,论者纷起,都把这一时期称作是元代诗歌发展的鼎盛时期,并把这个时期诗坛的代表人物虞、杨、范、揭并誉为“元诗四大家”,以致过去治文学者多知元诗四家而少知其它。
那么,延佑、天历间这种雅正诗风究竟为何?
它是如何形成的?
我们今天如何来评价这个时期的诗歌风气?
本文就上述问题略陈管见,以就正于方家。
一
关于延佑、天历间的雅正诗歌风气,自元至清就有多人论及。
稍于其后的欧阳玄就云:
“我元延佑以来,弥文日盛,京师诸名公咸宗魏、晋、唐,一去宋、金季世之弊,而趋于雅正。
”①由元入明的戴良在其《皇元风雅序》中谈到这一时期诗坛风气时说
然能得夫风雅之正声,以一扫宋人之积弊,其惟我朝乎……自姚、卢、刘、赵诸先达以来,若范公德机,虞公伯生,杨公仲弘及马公伯庸,萨公天锡,余公廷心,皆其卓然者也。
至于岩穴之隐人,江湖之羁客,殆又不可以数计。
盖方是时,祖宗以深仁厚德,涵养天下重五、六十年之久,而戴白之老,重髫之童,相于欢呼鼓午于闾巷间,熙熙然有非汉唐宋可及。
故一时作者,悉皆餐淳茹和以鸣太平之盛治,……盖至是本朝之盛极矣。
他们在谈到延佑、天历间诗风时,均以“雅正”名之。
诗讲“雅正”,本来是传统儒家诗学思想的重要命题。
但延佑、天历诗坛所讲的雅正,并非传统“雅正”诗歌思想的照搬。
那么此间的雅正诗风,其内涵究竟怎样呢?
关于雅,延佑、天历间诗人多有人论之,范德机《诗法源流》中云:
“雅之作,如后世之五、七言古诗,作于公卿大夫,而用之朝会燕飨者也,其言主于述先德,通下情。
”袁桷云:
“雅也者,朝廷宗庙之宜用。
仪文日兴,歌金石,迭奏合响。
”②他们所言的“雅”,是就诗之体而发,即作于公卿大夫、用于朝廷宗庙的一种诗。
虞集论雅诗云,“其公卿大夫,朝廷宗庙,宾客军旅,学校稼樯,田猎宴享,更唱迭和,以鸣太平之盛,则谓之雅”③,这是从诗之作用来论雅的。
当时还有人从诗之气象论诗之雅,如柳贯《赢海集序》云“气和而声应,言短而意舒,台是大雅之风”;范德机《诗法正论》中论《诗三百》之气象,“皆温厚平易老成。
所谓温厚者,和而不流,怨而不怒;平易者所言皆眼前事;老成者,忧深思远,达于人情事物之变,皆有理寓于其间”。
当然,也有从诗之风格来论诗之雅的,怀悦刊本《诗家一指》中,有《当代名公雅论》载虞集云雅诗之风格有“典雅、抛掷、出尘、浏亮、缜密、渊雅、温蔚、宏博、纯粹、莹净”十种④,虞集把此称为“诗之十美”。
延佑、天历间诗人所推崇的诗之“雅”,乃是承《诗经》雅诗之传统,以“鸣太平之盛”,为元朝中叶的盛世大唱赞歌的诗。
尽管这种诗风格多样,但终不离温厚、平易、老成的温柔敦厚之旨。
关于《诗经》雅诗之传统,此间诗人每每论及。
范德机《诗法正论》历数《诗经》、《骚》诗之后诗歌流变时云:
“自汉以来,由《骚》之变而为赋。
以当时去古未远,故犹有《三百篇》之遗意。
”魏晋以来,天下分裂,“而诗声遂不复振尔”,“其间独渊明诗,淡泊渊永,出流俗”。
到了唐代,“海宇一而文运兴”,“太白天才放逸,故其诗自为一体,子美学优才赡,故其诗兼备众体,而述纲常,系风教之作为多。
《三百篇》以后之诗,子美又其大成也。
昌黎后出,厌晚唐流连光景之弊,其诗人自为一体”。
宋代诗人,欧、苏、王、黄、后山、简斋、放翁、晦翁、诚斋,均是足以名世之人,特别是晦翁诗“如《蒸民》、《懿威》诸作,不害其为《二雅》之正”,但是宋诗与唐诗比,“唐人以诗为诗,宋人以文为诗。
唐诗主於达性情,故于《三百篇》为近,宋诗主於立议论,故于《三百篇》为远”。
类似论述,虞集《易南甫诗序》、《庐陵刘桂隐存稿序》、欧阳玄《潜溪后集序》等也有之。
他们均认为,只有唐诗才直接继承了《诗经》之精髓。
这一点,释来复《蜕庵诗原序》讲的尤为明确
鸣呼,诗岂易言也哉,大雅希声,宫徵相应,与三光五岳之气并行天地间,……然自删
后,至于两汉,正音犹完,建安以来,尚绮丽,而诗道微矣。
魏晋作者虽优,不能兼备众体,其铿轩昂,上追风雅,所谓集大成者,惟唐以后有之,降是无足采焉。
于是,延佑、天历间诗人在倡雅诗之时,上溯《诗经》,下学唐诗,以盛唐诗为雅诗之典范,以致形成了延佑、天历间一以唐为宗的诗歌风尚。
此间诗人,咸宗唐诗,虞集诗宗杜甫,人谓深得少陵家法;杨载五古效法李白,范德机“以清拔之才,卓异之识,始专师李杜”⑤。
揭斯云“学诗宜以唐人为宗”⑥,萨都刺歌行学习晚唐。
马祖常古体诗学汉魏,近体诗入盛唐。
吴师道五言古诗与唐人陈子昂的诗气韵相通。
延佑、天历诗坛在提倡雅道的同时,也提出“正”的范畴,认为“雅”要合于“正”,是为“雅正”。
这一时期,诗坛所讲的“正”,其含意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曰诗体之正关于诗之体,杨载《诗法家数》云:
“诗之六义,而实则三体,风、雅、颂者,诗之体”,扩而大之,“诗之为体有六,曰雄浑,曰悲壮,曰平淡,曰苍古,曰沉着痛快,曰优游不迫”,作诗“命意修辞,不可径情真叙,不可粉泽膏脂。
意刻则拘,文癖则怪,字巧则生。
故欲简淡则恐失於枯,欲典重则恐伤于窒,欲雄健则恐过于刚,欲微婉则恐流于腐,欲富丽则恐陷于娇,欲飘逸则恐流于放,欲平易则恐失于浅,欲奇险则恐入于怪,欲细腻则恐过于精,欲清新则恐过于巧。
大抵作诗体制最难,然要而论之,亦不过自然便好”⑦。
对于如何做到诗体之正,他们首先提出了正之以“三百篇”的诗体标准:
“或感古怀今,或怀人伤己,或潇洒闲适。
写景要雅淡,推人心之至情,写感慨之微意,悲怀含蓄而不伤,美刺婉曲而不露,要有《三百篇》之遗意方是”⑧。
针对不同题材的诗,他们提出了具体的“正”的标准。
如荣遇之诗要“富贵尊严,典雅温厚。
写意宜闲雅,美丽清细”;讽刺之诗,要“感事陈辞,忠厚恳侧。
讽谕甚切,而不失情性之正”;征行之诗,要“发出凄凉之意,哀而不伤,怨而不乱,要发兴以感其事,而不失情性之正”;赠别之诗,“当写不忍之情,方见襟怀之厚”;咏物之诗,“要托物以伸意”;赞美之诗,“贵乎典雅浑厚,用事宜的当亲切”;哭挽之诗,要“情真事实”⑨。
元佚名《诗家模范》也云:
“大凡台阁之作,气象要光明正大;山林之作,要古淡闲雅;江湖之作,要豪放沉着;风月之作,要蕴藉秀丽;方外之作,要夷旷清楚;征戍之作,要奋迅凄凉;怀古之作,要慷慨悲惋;宫壶闺房之作,要不淫不怨;民俗歌谣之作,要切而不怒,微而婉。
虽寓情写景不同,而止于忠爱则一”。
要而言之,诗体之正,就是要正之于《诗经》之三体,正之于温柔敦厚之诗旨。
和论“雅”一样,延佑、天历诗人论诗体之正,也是远溯《诗经》,近学唐人的,揭斯《诗法正宗》在谈及古今诗体变迁时就讲
三百篇末流为楚辞、乐府,为《古诗十九首》,为苏、李五言,为建安、黄初,此诗之祖也。
《文选》、刘琨、阮籍、潘、陆、左、郭、鲍、谢诸诗、渊明全集,此诗之宗也。
齐、梁、《玉台》,体制卑弱。
……唐陈子昂《感遇》诸篇,高古简远,出人意表;李太白《古风》、韦苏州、王摩诘、柳子厚、储光羲等古体,皆平谈萧散,近体亦无拘挛之态,嘲哲之音,此诗之嫡派也。
杜少陵古律各集大成,渐趋浩荡,正如颜鲁古书一出,而书法尽废,言其浑然天成,略无斧凿,乃诗家运斤成风手也,是以独步千古,莫能继之。
其他唐人宋贤,奇作大集。
因当遍参博采,难以遍学。
元佚名氏撰《诗家模范》也云“正者,盛治之音,皆安乐和平,如开元、天宝前之诗是也。
非正者,元和以后诗是也”。
不难看出,他们把唐诗,特别是盛唐诗看作是与风、雅、颂三体一脉相承的诗之正体。
因此,诗体之正,实际上就是要正之以唐诗,尤其是盛唐之诗。
二曰诗法之正与唐宋人喜谈诗法一样,延佑、天历间诗人也重论诗法,其讲诗法,亦是远学《诗经》,近学唐人作诗之法。
范德机门人集录范氏论诗之《总论》云:
“作诗之法,大抵尽于《三百篇》,后人直学不得”,而《诗》作诗之法,即为赋、为比、为兴。
杨仲弘《诗法家数》云:
“赋比兴者,诗之制作法也。
”诗法之正,首先以赋、比、兴为准,但赋比兴之用,要“随其笔意所至,当赋则赋,当比则比。
古诗兴多而赋少,律诗则比兴少而赋多,况律诗言景物,虽有似兴而实赋者,云有似比而实兴者,亦有比而兼兴、兴而兼比者。
皆非
出于安排布置也”⑩。
延佑、天历间人尤重诗之起、承、转、合,也就是诗之“格”,云“作诗成法,有起、承、转、合四字”,“大抵起处要平直,承处要舂容,转处要变化,合处要渊永。
起处戒陡顿,承处戒迫促,转处戒落魄,合处戒断送。
起处必欲突兀,则承处必不优柔,转处必至窘束,则合处必至匮竭”11。
此间诗人认为,唐诗最切起、承、转、合之法。
因此,他们云:
“学诗宜以唐人为宗”,“欲学诗,且须宗唐诸名家,诸名家又当以杜为正宗。
”12杨载《诗法家数》论《律诗要法》一章,尽取唐诗作例,其《诗解》所载五言律九首,七言律四十三首,标立生意格、柳杨格等三十三格,全用杜诗为例予以剖析。
范德机《木天禁语》“以篇法、句法、字法、气数、家教、音节谓之六关,每类又系子目,各引唐人一诗以实之”13。
揭斯《诗宗正法眼藏》自谓“且如看杜诗,自有正法眼藏,勿为傍门邪论所惑,今于杜集中取其铺叙正,波澜阔,用意深,琢句雅,使事当,下字切五七言律十五首,学者不可草草看过”,分明是以杜诗作为诗之正法。
宋人也讲诗法,但宋人是以魏晋以前的诗歌范式作为楷模的。
朱熹《答巩仲至第书》中云:
“古今之诗凡三变,盖自书传所记,虞夏以来,下及魏晋,自为一等,自晋宋间颜、谢以后,下及唐初,自为一等。
自沈、宋以后,定着律诗,下及今日,又为一等。
然自唐初以后,其为诗者固有高下,而法犹未变。
至律诗出,而后诗之与法,始皆大变,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无复古人之风矣。
”可见其是如何看重魏晋以前之诗而以唐诗为轻的。
宋人学杜,是因为杜诗超脱声色货利欲望之真情正好与他们“吟咏性情之正”的诗歌主张相契合。
而延佑、天历间所讲的诗法,恰恰是唐诗的艺术范式即格与调,这与宋人讲的诗之法度有着极大的不同。
三曰情性之正延佑、天历间诗人视性情之正为雅正之根本,“作诗之法,只是自己性情中流出”14。
性情正,诗法、诗体自然正。
“诗,言当正其心,心正则道德仁义之语,高雅温厚之气,自具于言辞之表”15。
前云山林、台阁诸体,“虽寓情写景不同,而止于忠爱则一”,就是讲诗体之正,要以情性之正为之本源。
这一点,此间诗人论述颇多,揭斯《诗法正宗》云:
“咏吟本出情性,古人各有风致。
学诗者,必先调燮性灵,砥砺风义,必优游敦厚,必风流酝藉,必人品清高,必神情简逸,则出辞吐气,自然与古人相似。
”范德机《诗家一指》也云:
“诗者情性也……盖其温柔敦厚,抱道而居,与时乖违,于物悲喜。
情有不堪,因发于呻吟调笑之声,比律吕而歌,列干羽而舞,是诗之正也。
”他们所云诗之情性之正,均指合于《诗经》温柔敦厚的诗教。
范德机《诗法正论》云:
“《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之始,《文王》为《大雅》始,《情庙》为《颂》始,皆周公所定之乐歌也。
未当教化纯被之余,文明极盛之运,作者之情性,既极其正矣。
”而能继承《诗经》情性之正者,远有楚、汉、魏、晋,近则为唐。
“诗,情性也,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所以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
水中之月,镜中之像,万折东流,千灯一空,言有尽而意无穷,由思惟而非思惟者也。
近代之作奇特解会,往往以才学文字议论为之,夫岂不工,而于古人情性愈觉远矣”16。
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数语,本出自严羽《沧浪诗话?
诗辨》,是严氏对盛唐诗之气象而言。
范氏所云,正是指盛唐诗之情性合于《诗经》情性之正,而以议论、才学、文字为诗的宋诗则离古诗之情性较远。
值得提出的是,延佑、天历诗人在肯定唐诗达于古之情性时,并未完全弃掷宋诗。
他们肯定唐诗情性之正,是基于唐诗合于风雅之正,而宋诗虽未直承《诗经》之旨,但不背离风雅之义。
范德机《诗法正论》云:
“唐诗主于达性情,故于《三百篇》为近,宋诗主于立议论,故于《三百篇》为远。
然达性情者,国风之余,立议论者,国风之变。
因未易以优劣也”,“变风、变雅皆因正风、正雅而附见焉”,其不弃宋诗之意已十分明显。
实际上,“吟咏性情之正”的说法,宋人就已提出。
朱熹《诗集传》云:
“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
”他在《建宁府建阳县学藏书记》中公开提出“诗以道性情之正”。
宋人提出“性情之正”,既不违背诗人抒发人之常情,又将情纳入“道”、“理”的规范。
它直承“发情止义”的诗教,但又与不同。
“发情止义”是外向的,要求诗情的抒发要合于外在之“礼”;“吟咏性情之正”是对内的要求,朱熹云:
“性者心之理,情者性之动,心者性情之主。
”17“正性情”的内涵即是要“正心”、“诚意”、“思无邪”,这是在理学出现之后对诗情要合
于封建伦理规范之“理”所提出的新的命题。
要而言之,延佑、天历诗坛出现的“雅正”诗风,是要求诗的内容要“鸣太平之盛”,要尊重诗之“吟咏情性”的艺术规律,在诗体、诗法即诗之格、调诸方面向唐诗学习。
但诗歌之情性的抒发,一定要合于理学之“理”,其实质是在以学习唐诗为主的旗帜之下,把诗歌创作重新引到温柔敦厚、正以性情、关乎政教风化的诗学思想的轨道上来。
宋人也讲温柔敦厚,讲诗言志,但宋诗强调的重点不在诗之美刺及政教风化的政治功利意义,而是在涵养性情之一面。
可见,延佑、天历诗风既吸收了传统儒家诗学之思,又融合了宋诗“正以性情”之旨。
其后戴良《皇元风雅序》所云元延佑、天历之间诗人“皆餐淳茹和以鸣太平之盛,治其格调固拟诸汉唐,理趣固资诸宋氏,至于陈政之大,施教之远,则能优入乎周德之未衰”,正是道出了此一时期诗风的这一特征。
二
延佑、天历间雅正诗风的出现,是南宋以来诗坛出现的唐诗与宋诗之争以及金元之际尊唐复古风气发展的必然结果。
宋诗自江西诗派出,最终形成了其以理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基本格调,并长期统治着宋代诗坛。
到南宋杨万里、陆游等,他们的诗才唱出了与宋诗稍有不同的异响。
至南宋后期,学习唐诗的风气较为盛行,明人徐象梅《赵师秀传》云:
“至潘柽出,始倡为唐音”,四灵诗派出现后,“唐体盛行,其诗清新圆美”。
南宋末的时候,江湖诗派继四灵之后,把学唐诗之风气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刘克庄自云学诗经历:
先学陆游、杨万里,兼取江西,上及于唐人,大小家数,手抄口诵。
戴复古面对风雨飘摇的动荡时局,发出了“飘零忧国杜陵老,感遇伤时陈子昂”的感叹18,时人即云“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作,一时自谓之唐音”19。
当时的严羽,首次倡学盛唐,云“予不自量度,辄定诗之宗旨,且借禅以为喻,推原汉魏以来,而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
《沧浪诗话》中指出“诗有别裁,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从理论上提出了反对“以理为诗、以才学为诗”为特征的宋诗的观点。
元灭南宋之后,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又一次大规模的南北文化交流的局面,加之当时朱陆合流的学术思潮的影响以及诗歌自身的发展,在至元、大德年间出现了元代诗歌创作的一次繁荣。
这个诗歌创作的高峰,以风格多样、调和唐诗、宋诗为其主要特征。
当时由南方入元的诗人,在纠正四灵、江湖诗派诗风的弊端中,分为两途,戴表元、袁桷、仇远、白铤、赵孟等人借复古以尊唐,方回、吴澄、刘埙、赵文、刘将孙、胡炳文等人则力主宗宋。
主张学习唐诗的诗人,反对宋诗“以理为诗”,主张诗歌创作要有韵味,如袁桷认为“理学兴而文艺绝”20,“夫以理为诗,文常患于不工”21。
提出“今一以理为言,遗其音韵,失其体制,其得谓之诗欤”22。
因此,他们打出“尊唐得古”的旗号,主张有情之诗,提倡一种振荡凌厉、清整雅洁的诗歌风格。
赵孟“为律诗则专守唐法”23,释弘道说赵诗“波澜有唐句,潇洒晋贤风”24,戴表元称道那些“奔驹纵鹘,搴拔俊耸,飞舟幻宾,闪烁风发”的诗是诗人之情之所致25。
至元、大德间尊唐的诗人以清整雅洁之诗代替四灵、江湖诗派的孱弱纤细,以情真意切的韵味代替宋诗的理趣,把诗歌创作重视诗的艺术的一面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而此间宗宋的诗人,紧步江西诗派之后尘,提出“一祖三宗”之说,方回《瀛奎律髓?
陈与义清明批》中云:
“古今诗人,当以老杜、山谷、后山、简斋四家为一祖三宗,余可预配飨者有数焉”,认为“学诗不以杜、黄为宗,岂所谓识其大者。
”26他们崇尚理趣,张之翰《陈菊圃尚书以诗相饯依韵为别》中说:
“文不本乎理,岂得文之真;诗不由乎义,岂得义之灵。
”当时诗坛出现的崇尚平淡自然诗风的倾向,实际上是由宋入元的一部分诗人接受宋诗以淡为美的审美情趣的必然结果。
而表现出来的重视作家个人精神风格的倾向,则是理学主张内心冥悟的哲学思理在诗学思想上的折射。
但至元、大德间尊唐、宗宋的倾向并未表现出壁垒森严的局面,而是呈现出一种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状况。
尊唐诗人并不完全排斥宋诗,他们往往把唐、宋诗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如云:
“唐之元和,宋之庆历,斯近矣。
”27而宗宋的诗人也不完全拘于宋诗的理趣,他们中不少人也看到“以理为诗”是宋诗之不
足,认为“皆理义策论之有韵者”最道着宋诗之病28。
至元、大德年间这种诗分唐宋、调和唐宋的诗歌风气,是宋诗之后诗歌向重艺术、重兴味方向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为延佑、天历间诗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至元、大德年间毕竟是元刚刚混一南北的时期,在位之臣,多有攻城野战之功。
而那些“守志厉操之士,高蹈深隐于其乡”29,因而这一时期诗人,除少数台阁诗人外,多为在野文人,正是他们,造就了这一时期诗坛风格各异的崭新局面。
随着时运日益承平,加之朝廷以显爵延致山林隐人,至元、大德后诗人群体,成份发生了较大变化,台阁诗人渐渐占据主要地位。
诗风的变化也就在所难免。
姚遂《跋雪堂雅集后》记至大三年京城文人雅集之盛况,正是延佑、天历诗风变化的前奏
雪雅堂集…去者去其繁,复得二十有七人,副枢商士讳挺,中书则平章张九思,右丞马绍燕公南,左丞杨镇,参政张思立,翰林承旨则麓庵王公讳磐、董文用、徐勃、李谦、闫复,翰林王构,学士则东轩徐公讳世隆、李磐、王恽,集贤学士则苦斋雷君膺、周砥、宋渤、张孔孙,赵孟,御史中丞王博文、刘宣,吏曹、尚书则谷之秀、刘好,礼部郎中张之翰,太子宾客宋道,提刑使胡祗,廉访使崔,皆咏歌其所志。
余阙《待制集序》中说“当是时,士大夫之尚,论学则尊道德而卑文艺,论文则崇本实而去浮华,盖久而至于至大、延佑之间,文运方启,士大夫始稍稍切磨为辞章”。
余氏所云,是就建元以来台阁诗人的情况而言的,但他毕竟客观地指出了至大、延佑文风变化这一历史事实。
延佑、天历间的雅正诗风,也是金元之际诗坛尊唐复古风气发展的必然结果。
金承北宋,在诗歌创作和诗歌批评方面深受北宋的影响。
和南宋诗坛一样,金代诗坛也出现了批评宋诗、提倡唐诗的复古倾向。
赵秉文于《答李天英书》中提出作诗当学“《三百篇》、《离骚》、《文选》、《古诗十九首》,下及李、杜”,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中云:
“百年才觉古风回,元佑诸人次第来。
讳学金陵犹有说,竟将何罪废欧、梅。
”他倡导唐诗,认为唐诗“知本”,在《杨叔能小亨集引》中他云:
“唐人之诗知其本乎?
何温柔敦厚蔼然仁义之言多也。
”他是从传统儒家的诗学观念出发来衡量唐诗的。
元好问主于风雅正体的思想,正好与元代初期保存汉民族传统文化及回归儒学的社会心态相适应。
金元之际尊唐复古的主张,主要是恢复传统儒家的诗学思想,这一点,对延佑、天历间雅正诗风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
延佑之后,元王朝进入其前所未有的和平盛世,当时,文人士大夫“涵煦乎承平,歌舞乎雍熙,出其所长,与世驰骋,黼黻皇猷,铺张人文”30,完全是一派歌舞升平的气象。
时代风尚的变化要求一种思虑安静,辞气平和的盛世之音与之相适应。
生活于延佑、天历间的诗人开始对此时的诗歌创作进行深刻的反思,范德机于《咏古》诗中感叹“正声始微茫,与世狎隆”、“雅道日以晦,六义谁折衰”;虞集在《庐陵则桂隐有程序》中感慨南方新附之后,“执笔者,肤浅则无所明于理,蹇涩则无所昌其辞,徇流俗者,不知去其陈腐,强自高者,唯旁窃于异端”,呼吁要“激清风于古道,发大雅于儒林”31。
他们提倡的理想诗歌,即:
“为诗与为政同,心欲其平也,气欲其和也,情欲其真也,思欲其深也,纪纲欲其明,法度欲其齐,而温柔敦厚之教常行其中也”32。
而至元、大德间宗唐诸公所提出的“宗唐得古”的主张以及金元之际的诗风,恰恰为此间“鸣太平之盛”的雅正诗风的形成准备了充分的前提条件。
文学自身发展所要求的对诗歌艺术规律的重视和对盛世之音的追求,使延佑、天历间诗人很自然地在格调上把唐诗作为理想的诗歌范式,以致形成“天历之际,作者中兴,上探诗书礼乐之源,下咏秦汉唐宋之澜,摆落凡近,宪章往哲,缉熙皇坟,光并日月,登歌清庙,气陵骚雅,由是和平之音大振,忠厚之璞复还”的局面33。
值得提出的是,延佑、天历时期是“理学”成为“国是”的时期,程朱理学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使此间雅诗的创作必然受到理学思想的浸染,理学思想影响下的“吟咏性情之正”的诗思,使此间诗坛在学习唐诗的同时很自然地被纳入到符合理学之“理”的轨道,从而使传统儒家的“雅正”之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了新的内涵。
三
延佑科举考试的重新恢复和理学统治地位的确立,以及延佑、天历间词学思想和曲学思想的变化,对延佑、天历间雅正诗风的形成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皇庆二年,元仁宗听从中书省的建议,下诏开科取士。
《元史?
选举志》云这次科考:
“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
皇庆科诏所定考试程式,汰除浮华,重古注疏和古赋,突出强调了经术和实用,尊定了程、朱理学的“国是”地位。
欧阳玄《李宏谟诗序》在谈到这一点时云:
“宋讫科举废,士多学诗,而前五十年所传士大夫诗多未脱时文故习。
圣元科诏颁,士亦未尝废诗学,而诗皆趋于雅正。
”那么,延佑科考是如何刺激了之后雅正诗风的形成呢?
延佑科举之制带来的社会风气的变化,对延佑、天历间雅正诗风的形成具有重大的影响。
自戊戍选试以来,由于科举考试长期停止,除少数知识分子混迹于官场之外,不少文人或为工、为农、为商、为吏。
延佑科考无疑给知识分子带来了走上仕途的希望,也促使了知识分子奔竞科考,尊祟理学,餐淳茹和,吟咏太平的风气。
他们有感于皇帝开科取士之恩,在诗歌创作上侧重于咏歌太平之盛。
黄《彭史绍诗序》云当时士风,云“为士者,唯知涵煦德泽而与咏歌太平之盛,欲访百年之遗事”,其欢欣鼓舞之情,申然可见。
所谓:
“朝廷方贵士,经术足谋身”,“云霄开大道,溟涨接通津”34,正是当时知识分子雀跃欢呼的鲜明写照。
当时鸿生硕儒,为文皆雄深浑厚,而无靡丽之习。
如蒲道源“以性理至学,施于台阁之文,譬如良金美玉,不假锻炼雕琢,而光铄自不可掩”35。
黄“诸论着一本乎六艺,而以羽翼圣道为先务”36,以致世风时和气清,文风辞平和而意深长,“淳古醇厚之风立,异人间出,文物灿然,是古昔可以加焉”37。
这种文风的形成,无疑给诗坛创作咏歌太平之盛的雅诗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延佑科诏提出以程朱理学家的注疏作为准绳,这就使兴于宋代的理学在元代第一次被抬高到至尊的地位。
苏天爵《伊洛渊源录序》云:
“仁宗临御,肇兴科举,网罗俊彦。
其程式之法,表章六经,至于《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专以周、程、朱子之说为主,定为国是,而曲学异说,悉罢黜之。
”科举程式的鲜明导向,使延佑、天历间学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欧阳玄《文正许先生道碑》云“皇庆、延佑之设科……一洗唐以来声律之陋,致使海内外之士非程朱之书不读”,从而成就了延佑前后非程朱即罢而黜之的学术风尚。
吴师道“于经术颇深”,为文“多阐明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