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科技史中的事实与价值.docx
《口述科技史中的事实与价值.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口述科技史中的事实与价值.docx(14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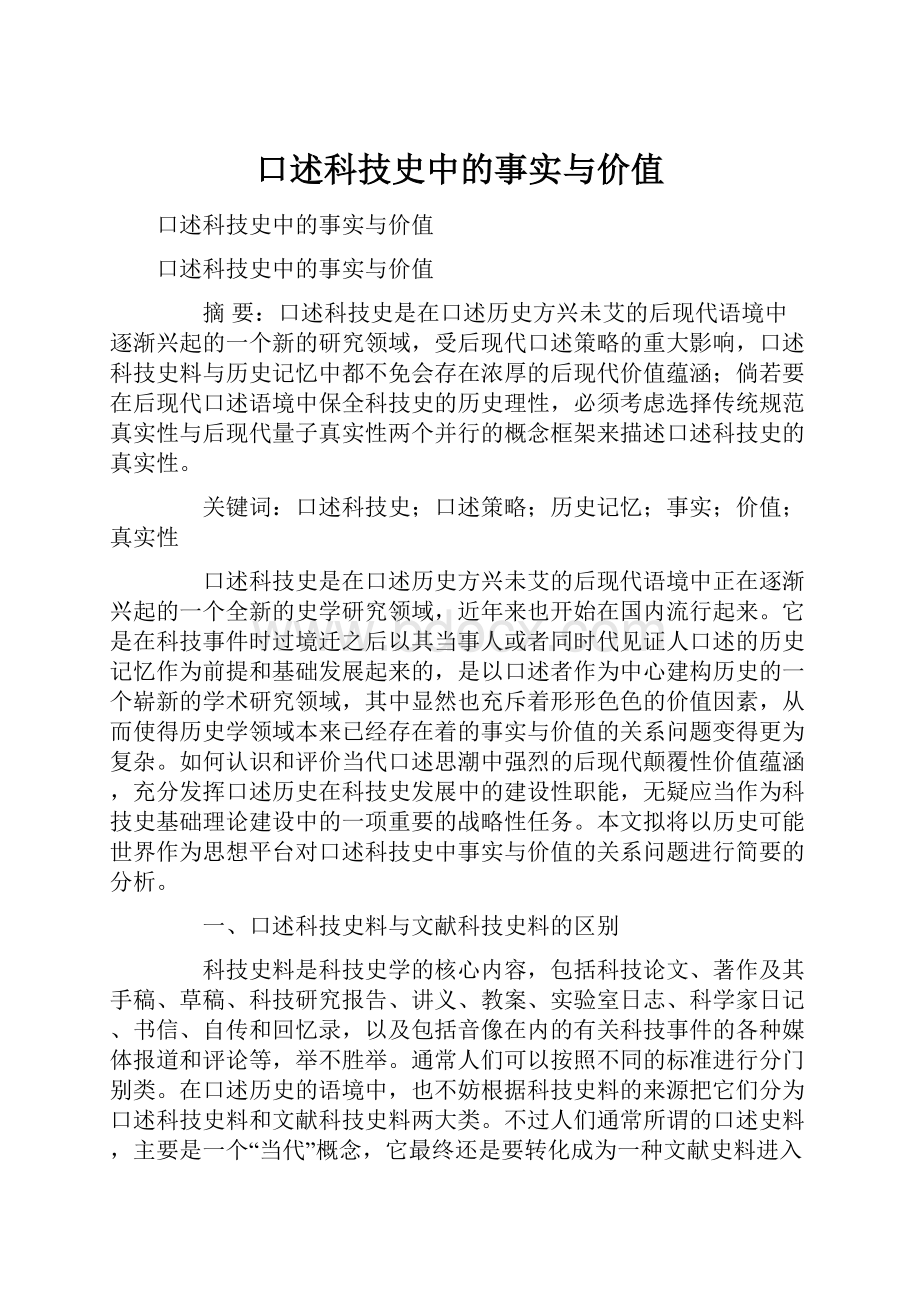
口述科技史中的事实与价值
口述科技史中的事实与价值
口述科技史中的事实与价值
摘要:
口述科技史是在口述历史方兴未艾的后现代语境中逐渐兴起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受后现代口述策略的重大影响,口述科技史料与历史记忆中都不免会存在浓厚的后现代价值蕴涵;倘若要在后现代口述语境中保全科技史的历史理性,必须考虑选择传统规范真实性与后现代量子真实性两个并行的概念框架来描述口述科技史的真实性。
关键词:
口述科技史;口述策略;历史记忆;事实;价值;真实性
口述科技史是在口述历史方兴未艾的后现代语境中正在逐渐兴起的一个全新的史学研究领域,近年来也开始在国内流行起来。
它是在科技事件时过境迁之后以其当事人或者同时代见证人口述的历史记忆作为前提和基础发展起来的,是以口述者作为中心建构历史的一个崭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其中显然也充斥着形形色色的价值因素,从而使得历史学领域本来已经存在着的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如何认识和评价当代口述思潮中强烈的后现代颠覆性价值蕴涵,充分发挥口述历史在科技史发展中的建设性职能,无疑应当作为科技史基础理论建设中的一项重要的战略性任务。
本文拟将以历史可能世界作为思想平台对口述科技史中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进行简要的分析。
一、口述科技史料与文献科技史料的区别
科技史料是科技史学的核心内容,包括科技论文、著作及其手稿、草稿、科技研究报告、讲义、教案、实验室日志、科学家日记、书信、自传和回忆录,以及包括音像在内的有关科技事件的各种媒体报道和评论等,举不胜举。
通常人们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分门别类。
在口述历史的语境中,也不妨根据科技史料的来源把它们分为口述科技史料和文献科技史料两大类。
不过人们通常所谓的口述史料,主要是一个“当代”概念,它最终还是要转化成为一种文献史料进入历史的。
所以,从历史上看,二者之间的界限从来也不是绝对的。
然而,从哲学上看,口述科技史料与文献科技史料毕竟是两种性质全然不同的科技史料,它们之间无疑是存在着一些本质上的或原则上的区别的。
第一,文献科技史料,从原则上讲,应当是一种原始的、或者说本原的科技史料,它是同科技事件一体两面、同步产生的,也大都是作为科技事件的标志存在的。
因为科技事件总是不可避免地以科技文献作为载体的,作为科技事件标志的科技文献本身就是它自己的史料。
例如,爱因斯坦的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也标志着狭义相对论诞生这一事件。
从这一事件出发,科技史料的来源可以进一步伸向科技事件的当事人及其他所生活的社会这样两个不同的维度。
具体说来,科技史料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向内返回爱因斯坦本人,包括同他的这篇论文有关的手稿、草稿、日记、书信、讲义和教案等;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向外走向爱因斯坦所生活的社会,包括当时的各种媒体报道和社会评价等。
这样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一个狭义相对论的时代。
广义相对论产生之后,狭义相对论成为历史,然而爱因斯坦及其同时代人犹在,这就为口述科技史料的产生提供了广阔的可能性空间。
比较而言,这里口述科技史料显然是历时的和追加的,或者说派生的,所谓时过境迁就是这个意思,它包含着时代和语境的变化。
例如,爱因斯坦晚年关于狭义相对论的回忆录及其同时代人关于狭义相对论那个年代的各种历史记忆等。
口述科技史料总是关于已经逝去了的那个时代的历史记忆。
第二,文献科技史料同科技事件一体两面、同步产生的总体特征也决定了它必然是自然历史地形成的。
一般说来,在忽略预谋作弊这样一种极端的小概率事件之后①,越是接近于科技事件发生的那个年代和语境,科技史料的可靠性和真实性程度也就越大;反之,则是越小。
从这样一种意义上讲,口述科技史料的可靠性和真实性是非常可疑的,因为它是在时过境迁的不同时代和不同语境中产生的,而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所产生的口述科技史料,显然都不可避免地是由人工来策划和制造的。
口述科技史料的口述目的和动机,问题的设置与提问的方式,以及口述者相应的回答,都直接隶属和服从于口述策划者与口述者所生活的那个业已变化了的时代和语境。
通常科技史料的储量同科技事件在当时所产生的学术影响与社会影响直接相关。
具体说来,越是普通的科技事件,遗留下来的科技史料越是片面、稀少和残缺,口述科技史料的建设性职能也越大,尽管它未必能够因此提高其自身的可靠性和真实性;反之,越是重大的科技事件,遗留下来的科技史料越是全面、丰富和完整,口述科技史料生存和发展的可靠性与真实性空间也越小,相应地,其颠覆性价值蕴涵也就越大。
第三,文献科技史料是客观指向的,它的原始性和自然历史性进一步规定了它的客观性。
它是以科技事件为核心形成的,事件的当事人及其同时代评论人在第一时间关注的首先是内容和事实而不是价值。
无论科技文献关于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过程的各种描述,还是科技史文献关于科技事件与科技文献的各种记录、描述和评论,都同样是客观性追求的产物。
客观性是科技文献和科技史文献共同的学术规范。
比较而言,口述策划者考虑的首先是价值,而且口述者几乎不可能遵循这样一种以客观性为职守的行业规范,即使那些经历过这种严格规范化职业训练的科学家本人的回忆录,也大都是其晚年的一种历史记忆,其中不可避免地渗透了他们在新的时代和语境中对于其科技思想的合理化与合法化修饰。
口述科技史料的历时性和人工性特点也天然地决定了其中不能不具有浓厚的无法剔除的主观意向性。
即使一个无偏见的口述者,他所描述的科技事件也只能是口述者历史记忆中的科技事件,而不是事件的当事人及其同时代人利用文字现场记录下来的科技事件。
所以,主观意向性显然是以口述者而不是科技事件为中心建构起来的口述科技史料所固有的一种本质特征。
第四,文献科技史料是抽象的,它是以语言文字、数学公式和图表数据为表述形式生成的一种常见和基本的史料类型,是科技史料的主体。
一般说来,这种抽象性根源于语言文字自身的局限性及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使用规范。
它使得本来具体、完整和统一的科技事件不得不以一种破缺和离散的抽象形式保存下来。
比较而言,口述科技史料则是具体形象的。
它是以口语、体态和音像作为表述形式而生成的一种虽说年轻而事实上却又非常古老的史料类型,只不过它在科技史中很少使用。
这种史料即使从音像转换到语言文字中,也仍然保留着口述者口语中的语气、语态和语调等极为丰富的现场情景信息。
这样的信息是人们完整和具体地把握那些一去不复返了的科技事件原貌不可多得的宝贵的历史资料,尽管它们所还原的那个历史事件未必是真实可靠的,然而这些感性和具体的信息对读者或观众的感染力和控制力却是无法估量的。
这或许就是后现代史学家所以热衷于文学史学的根本原因,也是后现代社会的人们所以把口述历史纳入话语权争夺策略的原因所在。
二、口述科技史与口述科技史料的区别
口述科技史与口述科技史料也是两个全然不同的概念,尤其不能够把它们混为一谈,尽管人们尚未来得及仔细加以区分。
一般说来,口述科技史料指称科技史料获取和存储的一种类型,隶属于历史学中的史料学范畴;而口述科技史则是指称人们表述科技史的一种特殊方式,在这种意义上讲,它可以同比较科技史学、计量科技史学和心理科技史学等学科相提并论,隶属于科技史学方法范畴。
具体说来,口述科技史是系统地运用口述科技史料再现科技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或某一方面的一种表述科技发展历史的形式,是人类阐释科技史的一种独特方式。
应当说,没有口述科技史料就没有口述科技史。
口述科技史与口述科技史料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联。
然而绝不能因此把它简单地等同于口述科技史料;反过来也是同样的,绝不能够把口述科技史料直接地等同于口述科技史。
第一,同口述科技史料相比,口述科技史应当是能够较为全面、系统和完整地再现科技事件的历史面貌的。
口述科技史料是零散而又灵活的,一部科学家回忆录、一次科学家访谈、甚至是一种有关科技事件的传闻、一个笑话等,都可以作为一种口述科技史料,它们可以作为独立的结构单元在不同的口述科技史中反复地使用。
然而,即使这些具体的口述科技史料是客观的和真实的,它们也只能是作为这一科技事件的一个侧面而已。
口述科技史还必须尽可能地从全方位、多角度广泛地收集关于科技事件各个不同侧面的口述科技史料相互印证、互相补充,以建构一种关于科技事件的立体全景,以具体、明晰和丰富人们关于科技事件的历史认识。
例如,要想具体地再现爱因斯坦在中国这一科技史上的片段,不仅需要采集爱因斯坦本人的口述,而且还需要采集爱因斯坦在此期间的陪同、接待和服务人员的口述;要想再现原子弹在中国的历史,则不仅应当广泛地采集来自决策层面的各种口述,而且还必须广泛地采集来自研制、生产和测试等各个环节与各类人员的口述。
第二,同口述科技史料相比,口述科技史应当始终不渝地坚持客观性原则和真实性原则,这是科学研究和史学研究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则。
口述科技史料可以真伪并存,主观性和失真性并不能够影响它的史料价值;口述科技史则必须真实可靠。
尽管同口述社会史料相比,无论作为口述策划者的科技史工作者,还是作为绝大多数口述者的科技工作者,都曾不同程度地经历过科学精神的洗礼,应当说,口述科技史料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程度相对说来还是比较高的,然而就具体的口述科技史料来讲,要达到绝对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还是不大可能的。
这是由口述这样一种特殊的形式先天决定的。
即使能够完全排除口述者阶级利益、文化修养和道德品质等方面各种差异的干扰和影响,口述科技史料的历时性特点也已经决定了历史记忆的选择性和模糊性,从而漏记与错记的现象也注定是不可避免的,更何况这里还有亲历和耳闻等其它方面的差别。
然而,口述科技史则必须准确地使用经过严格考证的口述科技史料再现历史,它必须保证它所使用的口述科技史料的真实可靠。
一时还无法鉴别真伪的口述科技史料可以存疑悬置,但是绝不允许随便拿来直接使用。
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第三,同口述科技史料相比,口述科技史必须具有逻辑上的统一性和条理性,它必须根据科技事件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首先在思想上建构一个合理自洽的框架结构,使得科技史的客观内容与其口述表达形式能够在其中获得一种尽可能完美的统一。
口述科技史料可以是没有规则的,在具体的采访过程中,为了能够让口述者在自然轻松的气氛中完全彻底地敞开自己的历史记忆,口述策划者被口述者牵着鼻子走的现象是在所难免的。
口述者的叙述可以是不连贯的,甚至是语无伦次、时序颠倒、前后矛盾的。
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对口述科技史料的进一步考证、甄别和分析得到纠正。
然而,口述科技史则必须根据一定的规则展开自己的叙述,它必须按照时间的流逝顺序严格遵循科技事件演化的内在逻辑循序渐进地展开叙述。
当然,这就要求撰写口述科技史的学者必须具备一定的逻辑思维训练。
从这种意义上讲,并非利用口述科技史料撰写的作品就一定能够称为口述科技史。
口述科技史应当提供一种关于科技事件的科学解释,而不应当写成一种道听图说的科技传闻大荟萃。
三、口述策略中的颠覆性
如果说第一部分中还可以在口述科技史料与文献科技史料之间作出明确的事实判断的话,第二部分中所谓口述科技史与口述科技史料之间的区别则仅仅是一种可能的事实判断,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价值规范。
它是传统文献科技史所追求的价值规范在口述科技史领域的移植。
因为迄今为止似乎还未曾出现过可供得出这一结论的口述科技史作品。
事实上,在充满价值蕴涵的口述科技史料基础上撰写一部真实可靠的口述科技史非常艰难。
然而,后现代口述史学期待的正是这一点。
他们认为这种价值规范并没有合法性,它体现的实际上是国家对民间、精英对草根的话语霸权。
他们要反其道而行之,追求一种来自民间草根的或许更为真实可靠的口述历史。
这就是极具颠覆性色彩的后现代口述策略,它必然造成科技史中的绝对价值相对化、边缘价值中心化、传统价值现代化。
第一,重新阐释口述的性质是后现代口述史学开始其一系列颠覆性活动的总体策略。
口述历史源远流长,它是人类在史前时期已经广泛采用的一种极为古老的历史表述方式;文字产生以后,它作为文献历史的一种史料来源和必要补充,也仍然发挥着自己的独特作用。
人们通常总是在口述和文献相统一的框架中把口述作为文献的一个重要补充来理解的。
然而,后现代口述史学却别出心裁。
它们声称揭示了口述与书写之间的二元对立,认为文字和书写已经变成了一种国家权力,文字及其掌握文字的精英长期占领了历史叙述的话语权,而那些不识字的“文盲”则始终被作为没有文化的人排斥在历史叙述之外。
口述历史的目的就是要彻底解构这样一种不具有合法性的叙事霸权。
按照英国著名口述历史学家汤普森的说法:
“口述历史是围绕人民所建构的历史。
……,它不仅允许英雄来自领袖,而且还允许英雄来自大多数不被人知晓的平民”,[1]“口述历史通过曾经创造过和经历过历史的人们自己的语言,重新赋予他们在历史中的中心地位”。
[2]同传统历史学家把口述历史当作全面展示历史细节的口碑史料全然不同,后现代口述历史学家把口述历史当作一种新的更加真实的历史记忆加以建构。
这样一来,“口述”这样一种起源于史前神话故事中的古老的叙事方式和人类学中的特殊研究方法便在后现代语境中获得了一种新的更加普遍和广泛的意义,并且从后台走向前台、从边缘走向中心,它旨在全面挖掘那些被主流社会完全淹没了的边缘人物、或者始终被排斥在传统文献历史之外的历史记忆,使人类历史从此以后从国家的“精英史”全面彻底地走向“大众史”。
第二,以边缘来消解中心是后现代口述史学颠覆历史的基本策略。
后现代口述策略是以口述者作为中心建构历史的,也就是说,历史其实仅仅是口述者的历史。
这里显然已经不仅是口述的性质问题,而是更进一步地触及到了历史的客观性问题。
口述者作为历史主体始终是处于价值评判中心,它不可避免地为口述史料以至口述历史的价值蕴涵大开了方便之门。
根据这样一种口述策略,当代口述历史的见证人都是来自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而非来自社会上层的文化精英。
美国著名口述历史学家保罗·布尔在介绍其口述历史著作《马克思主义在美国:
重新标示美国左翼历史》一书时曾经非常明确地讲:
“我的朋友都不是名人。
他们不会出现在历史书中。
在采访中,他们以及其他几百名不同辈份、出自不同激进派别的人和我进行了沟通”。
[3]英国左翼历史学家更加注重口述历史的价值属性,他们尤其善于利用西方传统的民主政治这样一种思想价值体系和社会组织制度为工人阶级的现实利益服务。
女性主义历史学家讲的还要更加露骨:
“历史不可避免地关系到政治,而我们的研究就反映了我们的政治”[4]。
当代所谓公众理解科学运动也在功利主义框架中赤裸裸地宣扬一种公众立场。
科技史是以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作为主线的,口述科技史原则上也应当是围绕这样一条主线深化和发展。
然而同科技史不同的是,口述科技史的口述者并不是科技史工作者,甚至也未必一定是科技工作者,而科技史中的书写人则通常都是科技史家。
一般说来,以科技事件为核心,从中心到边缘,科技活动可能涉及的人物包括这样几个不同层次:
其一是科学家和发明家本人;其二则是科学家和发明家所隶属的科研团队,包括其他科研人员和科研管理人员;其三是科学家和发明家的亲朋好友,也包括曾经为他们进行科学启蒙的各级学校教师;其四是科学家和发明家同时代的其他各色人等。
所有这些不同层次的社会成员,都将可能成为口述科技史的口述者。
这就为后现代口述史学的边缘化策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由于不同的社会成员对于科技发展的贡献及其在科技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他们对于科技事件的理解和评价也截然不同,从而科技史也将因此失去其客观的和普遍的属性而成为口述者视野中的“一种”科技史。
虽说口述科技史事实上未必都能够具有如此明确的价值蕴涵,然而它显然也不可能完全超脱这样一种正在广泛流行的社会思潮的各种影响。
第三,重新阐释中心是后现代口述史学颠覆历史的又一项基本策略。
除了以边缘来消解中心外,后现代口述史学还特别善于在解释学的框架中重新阐释中心。
随着库恩和费耶阿本德等后现代科学哲学的泛滥,科学与玄学、事实与价值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现代科学也在科技一体化的功利主义牵引下丧失其普遍的精神追求而蜕化为一种技术性知识,这就为形形色色地方性知识的复兴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传统本质主义框架中,科学家和发明家的科技创造活动作为科技史表述中天然和绝对不可移易的核心,既是可能的,也是现实的,所有口述者只能围绕科技事件和作为当事人的科学家和发明家挖掘自己的历史记忆,口述科技史工作者也是在史料学的框架中诠释口述科技史的。
在这里,科学主义是口述科技史活动的缺省配置,口述科技史只是为了抢救科技史料,丰富科技史细节,保存历史的真实。
然而,口述科技史毕竟是在真理缺席的后现代价值场中出现的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
尽管迄今为止科技史领域的绝大多数科技史家并没有接受后现代主义泛滥的实质性影响,但是毕竟还是有一部分科技史家已经从宏观走向微观,从内史走向外史,从书斋走向田野,从科学走向文化,而口述科技史关注的焦点也已经“不再是科学思想的观念史,或是伟大科学家的传记”,它“更触及了日常生活中的文化议题与科技的关系”。
[5]这一点可以从当代德国科技史家傅玛瑞“从席地到座椅——技术人类学视角中的热炕”一文中窥见一斑。
在绝大多数新新历史学家眼里,科学正在演变为博物学,口述科技史的内容也正在相应地从现代科学走向后现代所谓的地方性知识。
四、历史记忆中的价值蕴涵
后现代口述史学苦心孤诣地以口述颠覆文献,然而口述是以人的记忆作为前提和基础的,人的记忆真的能够比文献更加可靠吗?
事实上,倘若把后现代思想贯彻到底,则记忆也同样是不可信的。
后现代历史学家多米尼克·拉卡普拉曾经专门分析了历史与记忆的关系,得出的正是这样一个结论。
他认为记忆不仅仅是对过去的回忆,而且掺杂了现在的观点,甚至未来的想法。
用他本人的话来说,“记忆不但是过去时的,而且也是现在时的和将来时的”[6]。
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发现历史记忆具有明显的价值关联,它同后现代口述史学在社会学的反本质主义框架中抹煞事实与价值的界限倒也是一脉相承的。
因为他们本来就不相信、也不需要真实可靠。
他们所追求的仅仅是政治上的正确。
第一,选择性是历史记忆中普遍存在的一个显著特征,它不仅广泛存在于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之中,而且也存在于历史记忆的再现和表述之中。
事实上,任何记忆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各自的盲点。
它不可能像照相机那样把观察对象的全部细节都一览无余地、机械地纪录下来的,而是按照观察中所渗透的特定理论选择焦点进行观察和记录的。
例如,爱因斯坦关于麦克尔逊─莫雷实验在相对论中的作用问题曾经说过一些前后矛盾的话,科学史界还因此产生一些争议。
然而我们显然没有必要怀疑爱因斯坦1954年的这样一种说法:
“在我本人的发展中,麦克尔逊的结果并没有重要影响,我甚至不记得在我写关于这个问题的第一篇论文时(1905年)是否知道它。
解释就是,出于一般原因,我坚信不存在绝对运动,而且我的问题只是这一点怎样才能符合我们的电动力学知识。
”[7]事实上,爱因斯坦对于麦克尔逊─莫雷实验的理解是与其狭义相对论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在相对论尚处在襁褓之中时他不可能对于麦克尔逊─莫雷实验有很深的印象。
只要我们充分理解了爱因斯坦是一个具有浓厚唯理论倾向的物理学家,这一点就不难理解。
因此,R.S.向克兰1950年对爱因斯坦的访谈中说“当我问他是怎样知道麦克尔逊─莫雷实验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是通过H.A.洛仑兹的作品知道的,不过只是1905年以后才引起了他的注意!
”[8]显然也应当是可信的。
一般说来,个体记忆的内容通常取决于个体成长经历、生活经验、思想信念及其价值取向。
集体记忆的内容取决于特定社会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基本理论及其思维方式,以及正在方兴未艾的社会思潮,以至于特定历史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等。
历史记忆的解释、叙述和再现也同样的取决于这样一些因素。
所以,爱因斯坦1922年在日本京都大学演讲中所说的这段话,“在学生时代,我就知道了麦克尔逊的奇妙结果。
不久我就有了我们关于地球相对于以太运动的想法不正确的结论,如果我们承认麦克尔逊的零结果是一个事实的话。
这就是把我引向狭义相对论的第一条小路。
”[9]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爱因斯坦理论的创造史,而只能把它理解为相对论产生以后爱因斯坦对于理论内在逻辑的一种梳理。
第二,想象性是历史记忆中无法排除的一种重要成分,是历史记忆中价值渗透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显然构成了历史记忆的一个重要特征。
这一点后现代史学家尤其情有独钟,他们总是乐于从正面肯定并大肆渲染。
罗伯特·布朗在一篇为后现代历史想象辩护的文章中引用了纳粹“种族大屠杀”一位犹太幸存者和作家的话:
“这一种族大屠杀是如此难以理解和错综复杂。
也许只有借助于美学的想象,我们才能对它获得一个现实主义的理解。
”[10]后现代史学出于其颠覆性目的的需要,总是喜欢撇开历史记忆中的硬事实而在各种逸闻趣事中展开自己的历史想象,而口述历史的巨大诱惑是,像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等这样一些历史记忆中的硬事实,在时过境迁之后的口述中也居然会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例如,道尔顿关于原子论的形成就留下了一些众说纷纭的口述资料。
原子论捍卫者托马斯·汤姆森1825年披露,早在1804年8月,道尔顿就曾告诉他,原子论的产生同其关于气体(甲烷、乙烷)组成的研究有关。
然而道尔顿留下的笔记本却显示,直到1804年他才开始研究甲烷和乙烷,而直接表达原子论的原子量表则早在道尔顿1803年的记录中就已经出现了。
亨利父子分别口述了他们1824年和1830年两次同道尔顿的谈话,道尔顿曾明确表示,他受到里希特化学当量表的启发提出了关于化合物的倍比定律。
但是汤姆森在1845年却表示,早在1804年他见到道尔顿的时候,他和道尔顿两个人都还不知道里希特的工作,正是他后来才把里希特的工作告诉道尔顿的。
而道尔顿在1810年的一次演讲中则是非常详细地叙述了他是在阅读牛顿的著作和思考气体粒子的不同大小与重量后得到倍比定律的。
可见,道尔顿关于其原子论的形成在不同时期具有截然不同的说法,以至于科学史家梅尔德伦认为道尔顿关于原子论的起源“没有说过值得一丁点儿信任的话”[11],这种极端的说法虽然不必当真,却也让我们初步见识了历史记忆中的随处可见的历史想象。
第三,语境性是历史记忆中不容回避的一个基本特征,它贯穿于全部历史记忆的始终。
无论是历史记忆的个体存储,还是大面积地集体提取,都难以摆脱语境的制约和影响。
个体记忆的选择是由理论决定的,而理论的选择归根到底是由语境决定的。
然而语境本身却又是在社会共同体成员的相互作用中流动和变化着的。
事实上,狭义相对论和原子论固然是由爱因斯坦和道尔顿分别创立的,但是狭义相对论和原子论的语境却是在爱因斯坦和道尔顿与其所生活时代的科学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相互交流过程中共同建构的。
爱因斯坦和道尔顿本人对于自己的理论的理解也是伴随着各自语境的形成而逐渐深化、清晰和明确的。
在此之前,科学家的记忆完全取决于特定的情景。
在特定情景中存储的历史记忆只有在相应的情景中才能够准确地提取出来。
这就是许多科学家关于自己科学创造过程的说法常常不能够前后一贯的根本原因。
至于历史记忆中的叙述和解释就更是无法摆脱语境的制约和影响。
还是以爱因斯坦相对论与麦克尔逊─莫雷实验的关系为例,1931年,爱因斯坦在美国帕萨迪纳的一次物理学会议上唯一一次见到了当时已经79岁的麦克尔逊先生。
爱因斯坦发表了一番热情洋溢的演讲恭维麦克尔逊说:
“您,我尊敬的麦克尔逊博士,当我还是一个几乎只有三英尺高的孩童时,就开始了这项工作。
正是您,把物理学家们带到了新的小路上,并且通过您那绝妙的实验工作为相对论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您揭示了光的以太理论那时所隐含的缺点,并且激发了洛仑兹和菲茨·杰拉尔德的思想,狭义相对论由此发展起来,而这些又转而带上了去广义相对论和引力理论的大路。
没有您的工作,这个理论今天就不过是一个有趣的推测而已。
”[12]当时负责这次演讲报道的伯纳德·贾菲正是以此作为众所周知的证据而得出结论说:
“就在麦克尔逊去世前的1931年,爱因斯坦公开把他的理论归因于麦克尔逊的实验”[13]。
实际上,这完全是语境中的一种应酬。
事实正如科学史家霍尔顿先生所说的,“这种场所和这种期待完全是为爱因斯坦的回应安排的”[14],因为在此之前,麦克尔逊本人和其他一些科学家都已经在公众场合这样讲过了。
所以,爱因斯坦在这里显然是不能公开地损毁老麦克尔逊先生一生的名望所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