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白与中国佛教考古.docx
《宿白与中国佛教考古.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宿白与中国佛教考古.docx(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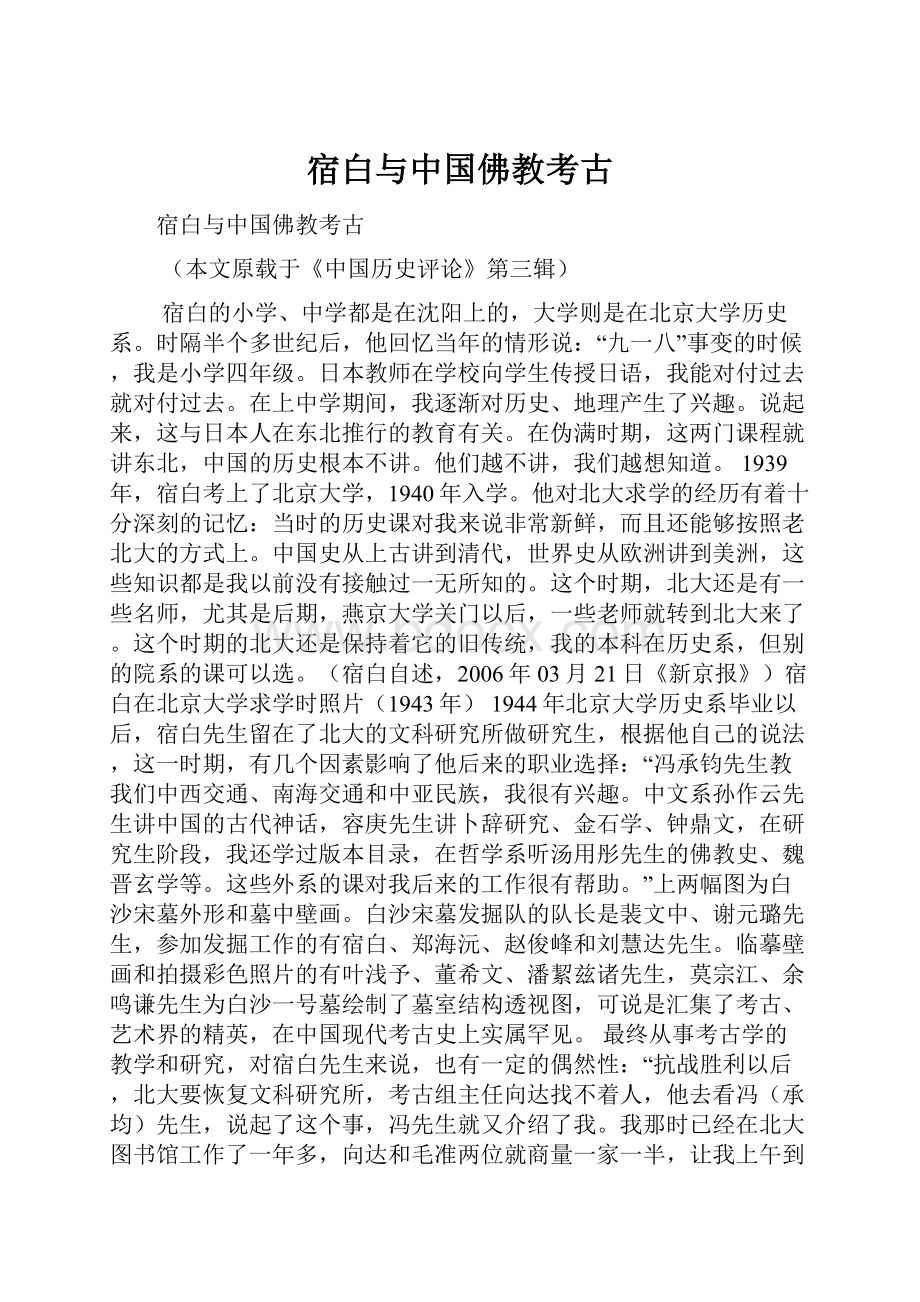
宿白与中国佛教考古
宿白与中国佛教考古
(本文原载于《中国历史评论》第三辑)
宿白的小学、中学都是在沈阳上的,大学则是在北京大学历史系。
时隔半个多世纪后,他回忆当年的情形说:
“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我是小学四年级。
日本教师在学校向学生传授日语,我能对付过去就对付过去。
在上中学期间,我逐渐对历史、地理产生了兴趣。
说起来,这与日本人在东北推行的教育有关。
在伪满时期,这两门课程就讲东北,中国的历史根本不讲。
他们越不讲,我们越想知道。
1939年,宿白考上了北京大学,1940年入学。
他对北大求学的经历有着十分深刻的记忆:
当时的历史课对我来说非常新鲜,而且还能够按照老北大的方式上。
中国史从上古讲到清代,世界史从欧洲讲到美洲,这些知识都是我以前没有接触过一无所知的。
这个时期,北大还是有一些名师,尤其是后期,燕京大学关门以后,一些老师就转到北大来了。
这个时期的北大还是保持着它的旧传统,我的本科在历史系,但别的院系的课可以选。
(宿白自述,2006年03月21日《新京报》)宿白在北京大学求学时照片(1943年)1944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以后,宿白先生留在了北大的文科研究所做研究生,根据他自己的说法,这一时期,有几个因素影响了他后来的职业选择:
“冯承钧先生教我们中西交通、南海交通和中亚民族,我很有兴趣。
中文系孙作云先生讲中国的古代神话,容庚先生讲卜辞研究、金石学、钟鼎文,在研究生阶段,我还学过版本目录,在哲学系听汤用彤先生的佛教史、魏晋玄学等。
这些外系的课对我后来的工作很有帮助。
”上两幅图为白沙宋墓外形和墓中壁画。
白沙宋墓发掘队的队长是裴文中、谢元璐先生,参加发掘工作的有宿白、郑海沅、赵俊峰和刘慧达先生。
临摹壁画和拍摄彩色照片的有叶浅予、董希文、潘絜兹诸先生,莫宗江、余鸣谦先生为白沙一号墓绘制了墓室结构透视图,可说是汇集了考古、艺术界的精英,在中国现代考古史上实属罕见。
最终从事考古学的教学和研究,对宿白先生来说,也有一定的偶然性:
“抗战胜利以后,北大要恢复文科研究所,考古组主任向达找不着人,他去看冯(承均)先生,说起了这个事,冯先生就又介绍了我。
我那时已经在北大图书馆工作了一年多,向达和毛准两位就商量一家一半,让我上午到文科研究所考古组,下午到图书馆。
一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北大从城里搬到城外,我这才离开了图书馆,正式来到北大历史系。
”正是在这段时间,即1951年12月至1952年1月,宿白先生参与发掘了河南禹县白沙镇的三座宋墓。
1957年9月,宿白先生撰著的《白沙宋墓》一书由刚刚创立的文物出版社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出版的考古报告之一。
该书出版后,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半个世纪以来多次再版,是公认的考古学和历史文献学相结合的学术经典。
考古发掘与历史文献的注释、参证并重,是《白沙宋墓》广受推崇的重要原因。
“四五十年前宿先生在《白沙宋墓》注释中所论证的事物和专题,经过这些年新的考古材料的验证,他当初的推测和结论,几乎都是正确的。
如果没有深厚的学力,是做不到这么恰如其分的。
(徐苹方:
《重读<白沙宋墓>》,《文物》2002年第8期)也是在这一时期,宿白先生开始了对中国佛教石窟、寺庙考古学的集中研究。
而研究的开端,则同样缘起于他深厚的历史文献学根基。
1947年宿白先生在参加整理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籍时,偶于缪荃孙抄自《永乐大典》“顺天府志”条所引《析津志》文中,发现了一则云冈石窟研究史上从不为人知的文献资料——元人熊自得抄录的《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碑文,文中记录了大同云冈石窟(原名武州山石窟)在历史上的重修情况。
在此基础上,宿白先生于1951年完成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初稿,这是宿先生将古代文献引入石窟寺研究,并取得突破性成果的重要标志。
李力的《从云冈出发——记宿白先生》一文,曾细致描述了宿白先生的这段学术经历和学术意义:
先生在《校注》中指出,(碑文)“记述详细,征引宏博。
所述自唐迄金一段云冈的兴修、设置,正好弥补了云冈历史的空白页,而引用现已佚名的北魏铭刻和文献记录考订云冈石窟的时代,也正给今天研究云冈各个石窟开凿先后的问题提供了绝好的参考材料。
”《校注》肯定了碑文的重要史料价值。
通过对碑文提供的新资料,主要是所述云冈十寺等内容的研究,结合当时国内外已对云冈石窟所做的考古调查、清理和挖掘,排列出云冈第二阶段洞窟开凿的先后次序以及第三阶段终止的年代。
此文经先生长达五年的修订,终于1956年第1期《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发表,引起国内外特别是日本中国石窟研究者的注意。
原来,自20世纪初年起,日本学者就开始了对云冈石窟的考察和研究。
到20世纪30年代以前,已有包括伊东忠太、大村西崖、关野贞、常盘大定和小野玄妙等在内的十多位日本学者发表了关于云冈石窟的研究文章,出版了有关图录。
30年代以后,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京都大学水野清一、长广敏雄在1938-1945年,对云冈石窟进行了连续八年的全面调查、记录和实测,还对部分窟前遗址作了小规模的发掘。
1951、1956年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以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报告的形式,陆续出版了十六卷三十二册大型《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的考古学调查报告》。
这套书卷帙浩大,代表了当时日本学者研究云冈石窟的最高水平。
“宿白先生《校注》一文发表时,作者(先生当时尚不到35岁)和文章所披露的《金碑》资料都是日本学者不知道的。
但是,他们不太相信这份文献,可能也不屑与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理论。
”(李力:
《从云冈出发——记宿白先生》)
宿白先生一直主张自己动手画线图,说只有自己画图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发现问题。
这是宿白先生手绘云冈石窟部分线图。
1950年,宿白先生参加雁北文物考察团时曾到大同云冈考察,而此后主持全国考古人员训练班和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实习,则几乎每年都到云冈。
如,1951年与清华大学建筑系赵正之先生勘察了敦煌莫高窟;1957年带领北大考古专业学生到河北响堂山石窟实习,作考古调查和勘测。
1978年,宿白先生发表《云冈石窟分期试论》一文(《考古学报》1978年1期)。
宿白先生的这一系列新的研究结论终于使日本学者感到了压力,并做出回应。
1980到1981年,长广敏雄先后在日本《东方学》第60辑发表《驳宿白氏的云冈分期论》,在《佛教艺术》第134号发表《云冈石窟之谜》,对先生的研究予以极不客气的反驳,甚至公开质疑《析津志》所载《金碑》及其碑文的真实性。
(李力:
《从云冈出发——记宿白先生》)
宿白先生一直主张自己动手画线图,说只有自己画图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发现问题。
这是宿白先生手绘云冈石窟部分线图。
1982年,宿白先生发表《(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与日本长广敏雄教授讨论有关云冈石窟的某些问题》一文(《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2期),论证了《金碑》的可靠性和熊自得所录文字无窜补的事实。
1989年,宿白先生又在日本平凡社和中国文物出版社合作出版的大型十七卷本《中国石窟》之《云冈石窟
(一)》(日文版)上,发表《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一文,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1990年,长广敏雄于《中国石窟》之《云冈石窟
(二)》(日文版)中著《云冈石窟第九、十双窟的特征》,在该文的最末一个“注”中,终于承认:
“从文献学角度出发,宿白教授的推论当无误,因而分期论也是符合逻辑的。
作为‘宿白说’,我现在承认这种分期论。
”虽然有些扭捏,却是部分同意了先生的观点。
这在日本学者,已属不易。
这是先生学术生涯中得益于古文献并将其成功运用于考古学研究的最精彩的一笔。
(李力《从云岗出发——记宿白先生》)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徐苹芳先生在《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创建历程——读宿白先生<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1998年第2期)中对此也有一个精辟总结:
宿白先生和长广教授是代表了上两个不同时期研究中国石窟寺的学者。
学术的发展和进步,与历史的发展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它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落花流水春去也”,长广教授所代表的中国石窟寺研究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以宿白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历史考古学家所创立的中国石窟寺考古学已经建立。
这是中国考古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学术成果。
宿白先生在敦煌莫高窟(1962年)(1952年)我到历史系考古专业后,开始上课并带学生实习。
考古不能脱离田野工作,实际上,从1950年开始,我就一直做田野调查和发掘工作,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停止。
从1952年到1964年,我教的主要课程是汉以后的考古学和古代建筑。
从1964年到1974年,我们什么事都干不了,我的书都被封了。
后来回想,幸亏封了,不然也保不住。
所幸我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所以还算清白,没受到太大冲击。
——宿白自述,2006年03月21日《新京报》1961—1962年宿白先生带学生在敦煌实习,选择典型石窟进行考古实测、记录,并举办了成果展。
在敦煌期间,宿白先生在敦煌文物研究所作了七次学术专题讲演,这就是著名的《敦煌七讲》。
演讲以敦煌为例,对中国石窟寺考古学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
据徐苹芳先生介绍,七讲题目分别是:
1.敦煌两千年;2.石窟寺考古学简介;3.石窟寺研究的业务基础知识;4.有关敦煌石窟的几个问题(其中包括:
索靖题壁间题,从乐傅、法良所联想到的问题,试论敦煌魏隋窟的性质,唐窟性质的逐渐变化,密宗遗迹及其它);5.敦煌研究简介;6.石窟记录与排年;7.佛像的实测与《造像量度经》。
这七讲被学术界公认为是先生建立中国石窟寺考古学体系的开篇之讲。
1979年,宿白先生带学生在新疆克孜尔石窟考察两个月,期间为石窟保管所业务人员讲授了如何以考古学方法记录石窟寺,并亲自参加绘图和记录工作。
克孜尔文物保管所所长说:
先生除经常到清理现场(指窟前遗址的清理现场)指导外,又于11月2日晚专门给大家讲了怎样记录的问题……除讲授一些记录方法和注意事项外,还一再强调,要使劲看,看明白了再记录。
在勾线图时,先生叮嘱大家要认真,不能有任何遗漏,哪怕是菱格图案内的一朵小白花,都要如实地勾画出来以使画面准确、完整。
宿白先生自己则回忆说:
“文革”末期,北大恢复招生。
1979年9月,我带领北京大学研究石窟的学生到新疆克孜尔石窟实习。
其间还有一次历险的经历。
那里的98窟是由僧房窟主室改建的中心柱窟,原先的门道便单独成为一个长条形小窟,后来不知是谁为上下窟方便,又将它们之间封闭的门重新打开,串通起来,而长条形小窟一直未安窟门,与99窟前室敞口侧壁相隔仅有1米多。
这样,往来于98、99窟,除走梯子外,还可攀岩,直接从长条形小窟进出。
这看起来便捷多了,但若是手扒不住岩壁,或是脚踩不稳,都有可能跌入沟底。
我那天也是从99窟直接攀到98窟,我先用右手抓住99窟侧壁,转过身,迈出右脚,蹬到一块突出的地方,再翻身伸左手拽住长条形小窟侧壁,将整个身体紧贴住崖壁。
因为上了年纪,我没能快速跨出右脚,借势进窟,结果用左脚试着找落脚点找了好多次,幸好最后还是平安跨过了。
后来有人告诉我,当地文管所曾经有一位年轻同志,就在跨越这个地方的时候一脚踩空,不幸坠崖身亡。
1996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石窟寺研究》,是宿白先生在创立中国石窟寺考古学方面的杰出理论建树。
该书共收录宿白先生自1951年至1996年间陆续写作和发表的23篇论文。
徐苹芳先生认为:
“它记录了中国历史考古学的一分支——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全部创建历程,是当代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一项丰硕学术成果,也是近年中国考古学的重要著作。
”该书出版后获得多项国内重要奖励,先后获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奖以及美国史密森学院和日本京都大都会远东艺术中心联合设立并颁发的“岛田著作奖”。
徐苹芳先生说:
中国石窟寺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20世纪50年代以前为一个阶段,50年代以后为另一个阶段。
这两个阶段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以考古学的方法来调查记录和研究中国石窟寺遗迹。
中国石窟寺是中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佛教遗迹。
对遗迹的清理和研究必须按考古学的方法来进行,这是现代考古学诞生后发展起来的唯一科学方法。
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石窟寺的研究,不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基本上都是从美术史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石窟寺遗迹的,只能记录(主要是照相和测量)现状,临摹壁画。
历史遗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有变化的,这种变化是历史发展实况的记录,考古学便是研究和揭示这些历史遗迹变化的学科。
因此,把中国石窟寺是否纳入考古学的范畴,便成了现代中国石窟寺研究是否符合科学的唯一标准。
宿白先生在建立中国石窟寺考古学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它关系到中国历史考古学研究的目的和方法,是中国考古学上的大事。
(徐苹芳:
《中国石窟寺考古的创建历程——读宿白先生的<中国石窟寺研究>》)
宿白先生手绘佛寺局部速描图西藏佛教考古,是宿白先生佛教考古研究的又一重要领域,其重要代表作就是《藏传佛教寺院考古》。
宿白先生自己回忆说:
1959年,我去了一趟西藏,在那里呆了5个月。
当时国家文物局要公布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西藏还没有。
文物局组织人到西藏调查佛教遗迹,我就去了。
好在我身体健康,没什么高原反应,吃住和行动都能适应。
解放军把寺庙的钥匙给我们,用专车拉着我们到处跑,愿意上哪儿就上哪儿,所以工作效率很高。
当时我把调查的材料交给文物局以后,就没继续管这事情。
1988年,西藏文管会庆祝一个节日,邀请我去参加。
我发现,很多寺庙在“文革”被毁掉了。
回来后,我就开始整理当年的那些材料,其中好多插图都是我那时自己画的,现在正好可以做复原的参考。
1996年,《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出版了,这离我当初去西藏调查已经隔了三十多年。
《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所涉及的佛教考古以前还没人做过。
自公元7世纪中叶到上世纪50年代,西藏长期处于政教合一的社会状态,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等历史,都在佛寺遗迹中有所反映。
因此,对于西藏佛教寺院的研究,其意义和价值就绝不限于寺庙建筑领域本身,也关涉到西藏历史诸多方面。
例如,我通过对拉萨大昭寺第二阶段建筑遗存剖析,发现了11世纪中国内地斗拱的典型样式,认为当时的雪域高原有可能有内地工匠活动,这些内容任何文字史书都没有记录。
(宿白自述,2006年03月21日《新京报》)《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文物出版社,1996年)获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罗炤认为,该书是西藏考古学研究的奠基之作。
他说:
中国近代意义的西藏考古工作,最早是由欧洲人开始的。
自1929年至1948年,意大利学者朱塞佩·杜齐(GiuseppeTucci)曾经8次进入西藏调查,出版了多种著作。
但是,他们的做法局限于对地上文物的随机调查与搜集,虽网罗周遍,但门类庞杂,缺乏系统、深入的专业性研究。
近40年来,中国学者在西藏考古领域做了许多工作,获得多项重要成果,全面超越了欧洲学者在西藏考古领域里所做的工作,为西藏考古学的发展建立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但在题材和内容上多是局部性的、甚或是孤立的,尚未形成综合的系统,普查资料也多属对遗迹遗物的客观记录,研究深度远远不够。
凭藉这些成绩,我们还不能说西藏考古学已经坚实地确立起来了。
宿白先生的《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使得有文字记载之后的西藏历史考古学,终于有了一部奠基之作。
该书由按地域划分的三部分内容组成:
第一部分是西藏域内寺院,第二部分是甘、青、内蒙古藏传佛教寺院遗迹,第三部分是内地蒙元时期的藏传佛教寺院遗迹。
其中第一部分的调查和研究涵盖了西藏拉萨、山南、日喀则和阿里地区的几乎所有主要寺院,是全书论证的核心和主体,也是作者在全书中用力最勤的部分。
我们之所以说《藏寺考古》是西藏历史考古学的奠基之作,就是因为自公元7世纪中叶迄本世纪50年代的1000多年时间里,西藏长期处于政教合一的社会状态,且教权甚至高于政权。
因此,作为西藏佛教遗迹遗物的集中代表和载体—寺院,便成为西藏历史考古学的主要对象。
西藏地区千余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等历史,几乎无一不在佛寺遗迹中得以反映,许多西藏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均与佛教寺院发生关联。
因此,对于西藏佛教寺院的研究,其意义和价值也就决不限于寺庙建筑领域本身,而关涉到西藏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美术、音乐、服饰等诸多方面。
宿白先生在西藏历史考古学领域中的筚路蓝缕之功,值得钦佩和讴歌,他献身于中国考古事业的忠诚与奋勉,更让人崇敬。
(罗炤:
《西藏历史考古学的奠基之作——读宿白先生<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文物》1998年第7期)半个多世纪以来,辛勤耕耘于执中国考古学教学与科研之牛耳的北大讲坛上的宿白先生,在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和石窟寺考古学的教学与科研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享誉海内外。
宿白先生著述颇丰,最能体现其学术造诣的考古研究成果如:
《中国石窟寺研究》、《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以及《中国历史考古论集》,《白沙宋墓》、《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等。
此外,宿白先生还有《敦煌七讲》、《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隋唐考古》、《中西文化交流考古》、《中国佛教考古》、《古代建筑》、《汉文佛籍目录》、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等多部专题讲义没有出版。
其中有的讲义曾在学生中辗转手抄或复印流传。
以上著作之所以久不出版的原因,还是源自宿白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
李力说:
我们曾与先生讨论结集和出版之事,先生说,我还要一篇一篇校订,修改,要有时间,哪能原封不动地拿出去。
宿白先生对出书一直态度谨慎。
他多次说“文章哪有不改的,活着就要不断修改,死了才出书,这就是盖棺论定的本意”,先生的习惯是文章写完了放进抽屉里,隔些时候拿出来再看,再改,再放回去。
就是送到编辑部,到了印刷厂,只要有问题,有新发现新体会,仍要照改不误。
我做编辑对此深有感触。
先生的稿子常常改到三校样、核红样,还是有得改。
先生的第一部研究专著——《中国石窟寺研究》,迟至1996年才正式出版。
其实,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学术著作的出版,特别是有些名气的学者出书已不是太困难的事。
先生的好几位学生就都早于先生出版了学术专著,有的还出了不止一本。
先生之所以在从事研究教学近半个世纪后才出版第一部个人专著,除了文革等因素外,主要是对专著的出版极为审慎。
半个多世纪以来,宿白先生培养了国内外众多的从事佛教考古研究的优秀学生,他的研究生们,也无不以能成为先生的入室弟子而自豪,正如李力所言:
“当今国内研究佛教石窟寺的著名学者,几乎都出自宿白先生门下。
”
宿白先生带领学生在新疆克孜尔石窟考察(197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