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四心四端与四德的真实逻辑.docx
《《孟子》四心四端与四德的真实逻辑.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孟子》四心四端与四德的真实逻辑.docx(2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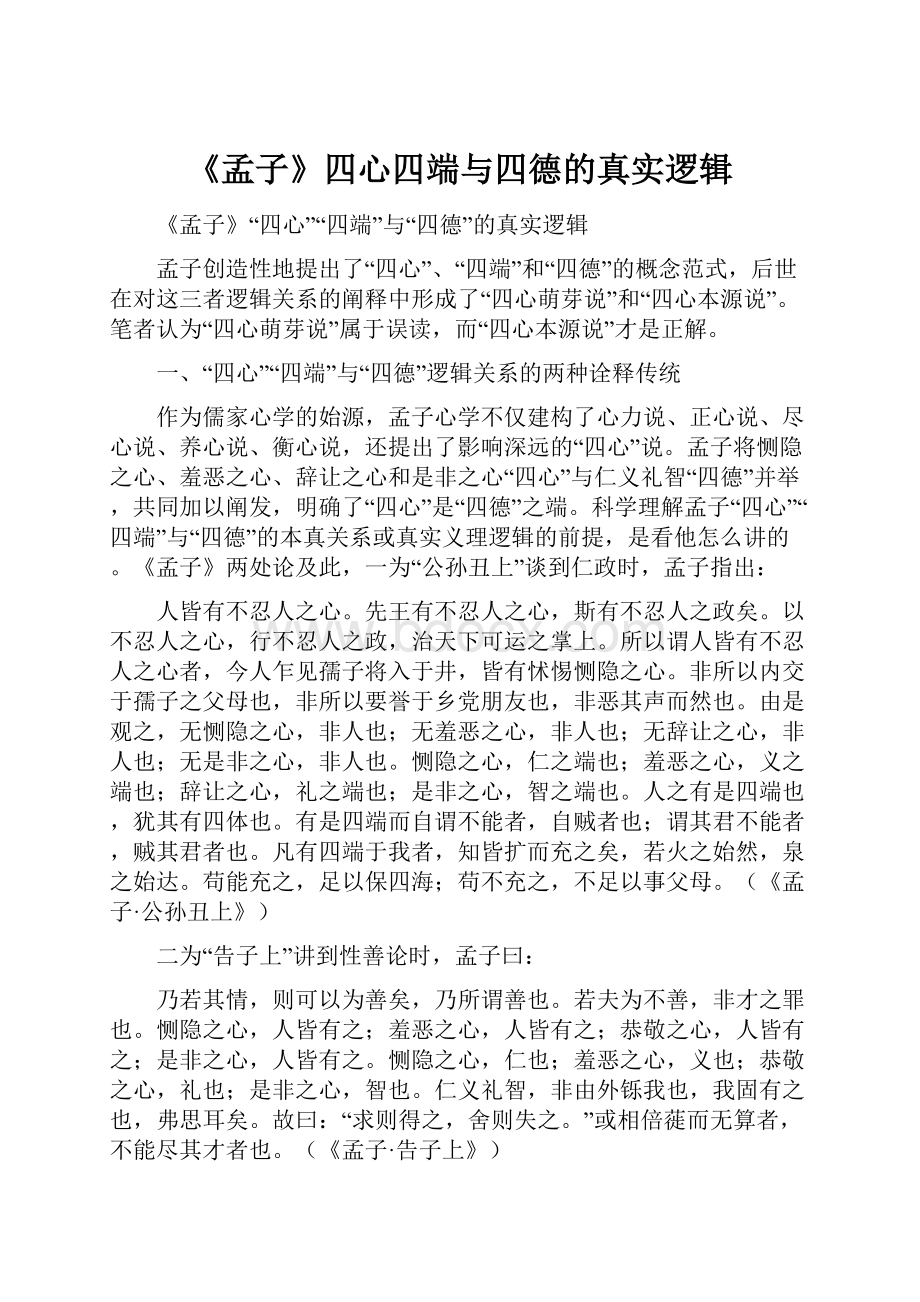
《孟子》四心四端与四德的真实逻辑
《孟子》“四心”“四端”与“四德”的真实逻辑
孟子创造性地提出了“四心”、“四端”和“四德”的概念范式,后世在对这三者逻辑关系的阐释中形成了“四心萌芽说”和“四心本源说”。
笔者认为“四心萌芽说”属于误读,而“四心本源说”才是正解。
一、“四心”“四端”与“四德”逻辑关系的两种诠释传统
作为儒家心学的始源,孟子心学不仅建构了心力说、正心说、尽心说、养心说、衡心说,还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四心”说。
孟子将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四心”与仁义礼智“四德”并举,共同加以阐发,明确了“四心”是“四德”之端。
科学理解孟子“四心”“四端”与“四德”的本真关系或真实义理逻辑的前提,是看他怎么讲的。
《孟子》两处论及此,一为“公孙丑上”谈到仁政时,孟子指出: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
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
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
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公孙丑上》)
二为“告子上”讲到性善论时,孟子曰:
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
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
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故曰:
“求则得之,舍则失之。
”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
(《孟子·告子上》)
对上述孟子的“即心言性”“即心言德”论说,自古以来存在多种多样的训释,其中争议最大的莫过于关于“四心”“四端”与“四德”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
要正确理解孟子“四心”“四端”与“四德”三者之间的真实逻辑,把握“四心”如何为“四德”奠基,最关键的是如何理解“四心”与“四德”的关系:
是“四心”在前“四德”在后,“四心”构成了“四德”形成发展的基础,还是“四德”在前“四心”在后,“四德”构成了“四心”形成发展的基础?
要准确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需要我们分析一下“四心”“四端”与“四德”的内涵和特性。
一是先天性。
在孟子心目中,“四心”是人天生具有的。
首先,人生来就有“不忍人之心”的道德本能,正因如此,人才能一看见小孩掉到井里就自然而然地动了恻隐之心去给予施救,而没有任何功利考虑;其次,“四心”是人与生俱来的才质、才性,是人赖以为善的心理基础,为人行善提供可能性前提,假如行动作恶,并不是人的才情有什么过错。
当然,人的“四心”有一个由潜在向显在、由不成熟向成熟的转化过程,它需要后天的培育、教化——不能设想一个心智不健全的人会对落水儿童产生“不忍人之心”,同时它也需要特定道德境遇、事件的触发、刺激(乍见)。
二是内在性。
孟子指出,人的“四端”是“在我者”而非“在外者”,它如同《论语》所言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论语·微子》)中的“四体”(四肢)一样,是人所固有的;“四端”是人自有的道德潜能,有了它却说自己不能,那就是自我残害,是自暴自弃;反之,如果赋有“四端”又知道加以扩充,就完全可以“保四海”和“事父母”。
三是普遍性。
孟子基于人性的普同性视角强调所有人不论圣凡都具有“不忍人之心”,具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
这“四心”本质上就是仁义礼智“四德”。
只要注意思索且用心追求,就可以获得它,否则就可能失去。
如果没有“四心”,那就根本不是人了。
人的行为表现之所以差异那么大,原因在于是否尽到了自身的才质。
两千多年来,对孟子言说的“四心”“四端”与“四德”的诠释,大致形成了两条路线。
一种是“四德”为体“四心”为用,“四德”为根基“四心”为生发,不妨将之概括为“四心萌芽说”。
朱熹训解道:
“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
仁义礼智,性也。
心,统性情者也。
端,绪也。
因其情之发,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见,犹有物在中而绪见于外也。
”[1](P221)这里,朱熹从心、性、情三者关系角度诠释“四心”与“四德”,认为“四心”是情、是发,“四德”是性、是本,它们共同由总体的心加以统摄。
程朱理学上升到道德本体论高度对孟子的仁义礼智信“五常道”和仁义礼智“四德”做了诠释。
朱熹认为性理合一,仁义礼智“四德”为性中所含之理,是性之未发本体,它们发之于外即是“四心”。
他承继了程颐在《程氏易传》中提出的“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
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的思想,指出,狭义上仁与礼、义、智各自对应“四心”,分别表达了温和慈爱、断制裁割、恭敬撙节和分别是非的道理;广义上是“理一分殊”,仁为一体、一元,它包含仁义礼智,融贯在“四德”之中:
“仁者,仁之本体;礼者,仁之节文;义者,仁之裁制;智者,仁之明辨。
”
这里不难发现,孟子明明讲的是“四心”为“四德之端”,可是朱熹在《朱子语类》《答陈器之问〈玉山讲义〉》等文献中未能紧密结合《孟子》文本而倾向于把“四德”等同于“四端”,没有严格分清“四德为端”和“四德之端”的界限。
他的以“仁包四德”为核心的仁说尽管有力地推动了儒家的仁学本体论,拓展了孟子“四心”与“四德”学说的内涵,但也轻视了“四心”的本源意义,形成了“四心”为用的思想传统,以致包括冯友兰在内的后世许多学者沿袭了这一错漏。
即使力主“心理合一”的心本体论和良知(良心)本体论的王阳明,也认为性主于身就是心,而仁、义、知是性之性;虽然他也承认“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3](P7),但这也可以理解为恻隐之心是仁的发用而不是本源;他甚至从性与气的关系角度将“四心”下降为体现善端的气:
“然性善之端须在气上始见得,若无气亦无可见矣。
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即是气。
”[3](P68-69)
在朝鲜儒学发展史上,从14、15世纪的权近、柳崇祖到16世纪的郑之云、李退溪、奇大胜、栗谷,再到18世纪的丁若镛,皆立足于朱熹的理气论,这些性理学家围绕“四端”“七情”的同异性展开过广泛讨论。
虽然观点歧异,虽然深化了对儒家“四端”“七情”关系的理解,但不足的是,他们共同把“四端”理解为由人的善性生发出来的形而下层面的情感。
当代中国哲学史界有极少数学者如王其俊认为,这三者是相互独立的人性善的三个层次[4](P177),绝大多数人则主张“四端”不是不同于“四心”或“四德”的独立形态,它或是指“四心”,或是指“四德”①。
其实,“四端”不过是对“四心”的描述和定位,其本身并不构成独立的心灵形态。
国内儒学界绝大多数人继承了宋明理学“四心萌芽说”的诠释传统,认为“四心”是“四德”的萌芽、发用或体现。
杨泽波指出:
“孟子认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分别为仁义礼智的初生、开始。
”[7](P318)陈来的观点更具代表性,他引用《孟子·告子上》的话后分析说,“孟子从仁者爱人出发,把仁规定为人的本性,把恻隐规定为仁之本性的发用,提出了著名的‘四端’‘四心’说”[8](P108);他还讲:
“恻隐之心是仁的开始和基点,故称端。
把恻隐之心加以扩充,便是仁的完成。
这也说明,仅仅有恻隐之心,对仁的德行来说还并不就是充分的。
”[8](P109)显而易见,陈来把“四心”确定为“四德”的萌发,然而问题是,这与他的“恻隐之心是仁的开始和基点”提法存在一定的冲突——要知道,基点与开始是事物相反的两个节点,它是开展某种活动的基础之处,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始基。
另一种是“四心”为体、“四德”为用,“四心”为根基、“四德”为生发,不妨将之概括为“四心本源说”。
国内学者蒙培元、杨国荣等对此做了一定的阐发。
杨国荣指出,孟子所言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含有情感之义,它们是内在于主体的、自然的、人之所以为人的本然之心;“人心所蕴含的恻隐、羞恶等情感,主要为仁义等道德意识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潜在的可能(端)惟有通过一个扩而充之的过程,才能达到自觉形态的道德意识”[9](P46)。
遗憾的是,大概没有摆脱朱子的影响,杨国荣机械地把仁义礼智“四德”规定为人性,把“四心”划定为人心,忽视了孟子也讲过“四德”也是人心的重要形态——如孟子说“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孟子·告子上》),也没有区分孟子说的总体心和具体心,以至于在论证过程中把孟子说的总体心等同于具体的“四心”。
当然,最为重要的是他未就“四心”何以为“四德”提供可能性基础展开充分的阐释。
二、“四心”“四端”与“四德”义理逻辑的正解
笔者认同“四心本源说”,认为仁义礼智既是德性,也是德心,还是人应当履行的责任伦理(德行)。
“四心”并非“四德”的萌芽、体现,它不但与“四德”相互作用、相互依存、互为条件,而且“四心”构成“四德”的心理本源,为“四德”奠定情感根基。
虽然“四德”是“四心”赖以形成发展的重要条件,但不是其本源、本体,“四心萌芽说”是对孟子“四心”、“四端”和“四德”逻辑关系的误读,其理由如下。
第一,“端”具有始基、原因的义项。
自古至今许多学者持“四心”萌芽论说却没有做充分的学理论证,多受性体情用思维模式的影响,并从文字学上强调“端”本作“耑”,并引《说文解字》“耑,物初生之题也,上像生形,下像生根也”,解释“端”具有发端、萌芽、始见等含义,由此得出结论说:
“四心”是“四德”的发端、萌芽,仁义礼智“四德”是通过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四心”而体现出来的。
从文字学来说,“端”本义为“轮廓线和缓起伏的山头”,引申义为“圆弧形山头”,“立”与“山而”联起来表示“站立于圆弧形山头上”,因此,“端”本义就是指在圆弧形山头上站得中正。
此外,“端”也具有用手平拿着、规矩、直、东西的一头或事情的开头方面以及开端、萌芽等多种多样的含义。
然而,焦循在《孟子正义》中注疏道:
“端者,首也。
”[10](P234)这说明“四心”是“四德”的始发地或出发点。
而且,“端”也有原因、起因等意涵。
持“四心萌芽说”者大多仅取“端”的开端、端绪、萌芽含义,据此认定“四德”是“四心”萌发的本体论基础,是“四心”的精神基因;“四心”则是“四德”的外在展现或表现形式,是“四德”与对象化事物相互作用的产物。
假如“端”确实有始基、原因的义项,那么据此就完全可以断定人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分别是仁义礼智“四德”得以产生、依托的重要心理根源和精神基因。
第二,孟子肯定了“四心”与“四德”是人的才质。
上引孟子关于“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一段话中,孟子首先明确指出人的先天性情是可以为善的,有人为不善不是人的才性、秉赋的过错;接着他把“四心”与“四德”视为完全同一性的东西,指出“四德”是人所固有的,必须求取,人与人之间后天之所以存在那么大的差距,正是由于没有充分发挥天生的资质。
表面上,后面的论述指认了“四德”是人的才质,但是,孟子在此并没有明确地说“四德”是“四心”的才质,只不过论证了人要为善必须发挥才质。
实际上,由于孟子在这里把“四心”与“四德”看成同质性的事物,因而他也肯定了“四心”是人为善得以依托的才质。
第三,“四心”为“四德”奠定情感基础。
犹如朱熹所言,孟子心中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是道德化情感,虽然是非之心体现了一种知善知恶的道德认识,但也包含着好恶的情感成分。
就仁义礼智“四德”而言,它们呈现出多种面向,既可以像孟子本人那样称之为德,也可以像朱熹那样称之为“性”,还可以将之理解为践仁、行义、循礼、明智这样的“德行”。
孟子本人好像从来没有明确称仁义礼智为“性”,即便能够称为“性”,就一定要说它们决定“四心”的本性、本体吗?
尽管荀子、董仲舒、二程、朱熹等儒家常常分“性”与“情”为二,但在儒家性情学说中,情包括四个层面:
一是人的心性内在化和外在化的某种事实状态,相当于情况、情状等;二是由喜、怒、哀、惧(或乐)、爱、恶、欲等组成的普通感性情感;三是由孟子阐发的“四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之类的道德化情感;四是社会化的用于人际交往的特殊化的人伦情感[11](P59)。
孟子的心性之学区别于后世儒家“情生于性”“性本情用”的性情体用思维,往往性情合一,它包含的“四心”之情作为不同于喜、怒、哀、惧、爱、恶、欲等感性情感的情理合一的高级道德情感,并不是如同宋明理学释读的那样是“用”,而同样是人与生俱来的本体、本性,某种意义上同样与“四德”一般可以称为“性”,故而它也有资格为“四德”和“五常之性”奠定情感基础。
毋庸置疑,如同程朱所言,仁可以包“四德”或统“四德”,为此可以像程明道创建“仁体”概念范式一样建构仁本体论或仁学本体论,但这并不表示一定要肯定仁与义、礼、智一起是“四心”的本体、本源。
要知道,本体可以具有多种不同层次、指向(天体、性体、心体、情体、道体及宇宙本体、历史本体、社会本体等),“四心”作为道德化的情感,同样能够成为“四德”的本体、本源。
正因如此,李泽厚才提出了情本体论或情感本体论,蒙培元才认为孟子说的“四端”是具有内在性、普遍性的“天理人情”[12](P6)。
第四,孟子虽然承认“四心”和“四德”是内在的,并凸显仁义内在的一面,但是他有时也肯定“四德”的外在性。
一般说来,作为人的深层情感结构,孟子讲的“四心”虽然要随感而发、触物而动,虽然它是人类道德长期进化积淀和社会化的结晶,但它们作为人类道德与心理机能相融合的精神样态,当其未发时也可以潜藏在人的内心深处,本质上还是属于人精神世界的内在道德意识和道德情感。
朱熹从内与外、未发与已发视角指出:
“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虽无形,而端的之发最可验。
故有其恻隐所以必知其有仁,有其羞恶所以必知其有义,有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礼,有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
使其本无是理于内,则何以有是端于外?
由其有是端于外,所以必知有是理于内而不可诬也。
”[13](P2779)这显然是对孟子“四端”说的误读。
对孟子来讲,“四德”无疑也具有内在性,他除了强调仁义内在外,尤其注重阐发“仁”这一“四德”中的总体性德目的内在特质。
孟子把“仁”称之为“安宅”:
“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
”(《孟子·公孙丑上》)并从民本角度把“仁”规定为人心的特殊类型:
“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孟子·离娄上》)“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
”(《孟子·告子上》)甚至直接断定“仁”就是一种人心:
“仁,人心也;义,人路也。
”(《孟子·告子上》)然而,孟子也不否定“四德”中义、礼、智的外在性。
他不仅讲“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
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孟子·离娄上》)还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义路礼门观念:
“夫义,路也;礼,门也。
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
”(《孟子·万章下》)尽管义路礼门说使用的是比喻手法,尽管它与孟子的仁义内在说具有一定的冲突,但毕竟体现了义和礼相对于仁的外在性。
在对“四德”的实质揭示中,孟子更是彰显了它的外在性:
“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
”(《孟子·离娄上》)无论是事亲、从兄还是节制,都是外在化的行为(德行),均是“四德”外在性的表证。
既然“四心”主要是内在的,而“四德”作为儒家伦理的主要德目既有内在性又有外在性,那么,依照孟子一贯的由内在决定外在的思维逻辑,把“四心”理解为“四德”的心理根源就更具有合理性。
第五,最重要的是,孟子明确指明过“四心”是“四德”的根源。
一方面,孟子立足君子人格维度提出了“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命题。
孟子所说的“心”,有时从总体普遍而言,如尽心、存心、动心、不动心、用心、吾心、心之官则思等;有时从具体特殊而言的,如仁心、仁义之心、恒心等。
主张“四心萌芽说”的人也许会说,“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意味着仁义礼智根源于人的总体心,而不是指“四德”根源于具体的“四心”。
笔者认为,既然孟子断定“四心”是“四德”之端,既然“四心”是心的重要内容和类型,既然孟子常常将“四心”与“四德”连用,为什么不能把“仁义礼智根于心”解释为“四心”是“四德”的根源、端始呢?
即便像朱熹那样把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规定为“情”,把仁义礼智界定为“性”,所谓“心统性情”也只是意味着总体的“心”具有对具体的性情的统摄、控制作用。
另一方面,孟子指出过“四心”是种、“四德”是果。
他论述仁学时说:
“五谷者,种之美者也;苟为不熟,不如荑稗。
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孟子·告子上》)这段话清楚的是孟子强调“仁”必须使之不断地生发、成长,以使它成熟完善;不太清楚的是孟子到底是把“仁”比喻为“五谷”抑或比喻为“种子”,如果联系他的“四端”说,把“仁”比喻为“五谷”,它是由“四心”孕育、生发开来而发展成熟的结果,也不失为一种合理的诠释选择。
第六,把“四心”理解为成就“四德”提供心性基础更能彰显孟子对儒学的创造性贡献。
孔子虽阐释了仁义礼智等德目,但未就其基础做过多叙说。
孟子对孔学乃至整个儒学的原创性贡献之一体现在,他着眼于人内在的心性,把“四心”看作产生仁义礼智“四德”的端始、基础——虽然它们本身具有善的属性,讲述了“四心”是致善的主体条件、根本原因,将“四心”之类天生的道德情感看作是仁义礼智之类现实善的端始,认定它们构成了性善和人善的根基,为人行善提供了主观可能性。
虽然笔者不同意蒙培元把“四心”与仁义礼智归结为情与性、情感与理性的做法——因为“四心”本身是伦理理性与人伦情感合一的四种典型人心形态,但赞同他的如下说法:
“仁义礼智四种道德范畴,孔子早就提出来了,只是除了仁、知之外,孔子并没有一般地从心理情感上说明‘四德’是如何可能的。
”[14](P175)“孟子的重要贡献,就在于将孔子提出来的仁义礼智这些道德范畴统统归结为情感问题,以情感为其内在的心理基础。
”[14](P175)与孔子凸显“德政”有所不同,孟子在儒学史上创构了鲜明的“仁政”学说,并为此对人心做了深刻思考。
如果说“四德”说构成了仁政说的直接道德基础理论支撑的话,那么,“四心”说或“四端”说则构成了仁政说的根本心理依据、思想基石,孟子的王道政治理想正是建立在深厚的“四心”基础之上。
围绕孟子“四端”、“四心”与“四德”关系的诠释,除上述“四心”本根说和“四心萌芽说”两种解释路线外,也有极少数人在这两者之间摇摆。
譬如,刘宗贤时而说“‘四心’是以‘四德’为内容描绘出的人的主观心理状态,是‘四德’的具体化”[15](P15),时而又说“孟子认为‘四德’寓于‘四心’之中,完满的‘四德’是由‘四心’发展而来,说明道德意识是以心理活动为基础的”[15](P15)。
关于“四心”与“四德”关系的诠释,要么持“四心”本根说,要么持“四心萌芽说”,二者必居其一,刘宗贤出现如此摇摆只能使自己陷入矛盾境地。
而且,大概没有摆脱心学的束缚,刘宗贤和所有“四心萌芽说”者一样,把“四德”主观化、内在化,归结为一种道德意识或道德观念形态,完全忽视了它的外在性、社会性——礼更是一种社会建制。
应当承认,孟子所言的心,既广大又深邃,既有总体心又有具体心,不过“四心”作为心的具象形态,只是“四德”的必要情感基础,而非充分必要条件,“四德”的孕育、发展当有其他心性因素和社会环境。
孟子本人虽然强调恻隐之心为仁的根源,甚至将二者等同,可他经常单独使用“仁心”和“仁义之心”用以说明道德现象、王道政治的心性根基。
三、恻隐之心与人的仁德
上面笔者从普遍性角度就“四心”“四端”与“四德”的义理逻辑做了总体诠解,为了更加充分揭示这三者之间的真实逻辑,以下试图围绕恻隐之心与人的仁德、羞恶之心与人的义德、辞让之心与人的礼德、是非之心与人的智德四个层面,依次具体展开讨论孟子阐发的“四心”“四端”与“四德”的义理逻辑。
孟子只是说“四心”为“四德”之端,甚至直言“四心”就是“四德”,可惜他未能就其理由展开论述。
好在他有一些相关论述可以借鉴,尤其是后世儒家就此做了阐发,为进一步梳理“四心”何以能够为“四德”奠基提供了参考。
孟子把“恻隐之心”与仁爱对置起来,试图为人的仁爱提供道德根据。
那么,到底什么是恻隐之心?
它的性质、功能何在?
上述引文中孟子不仅强调只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就可以“治天下可运之掌上”,表达了不忍人之心是推行仁政的精神支撑观点,而且指出: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
”(《孟子·公孙丑上》)显然,孟子视“不忍人之心”和“怵惕恻隐之心”为同一性概念。
什么是“不忍人之心”?
《广雅·释言》曰:
“忍,耐也。
”[16](P774)忍耐实质即人控制或克制自己。
孟子讲到人的艰难成长过程时言及“动心忍性”(《孟子·公孙丑上》),这说明对他来说,人性系统之中不光有善性、善端,也有味、色、臭、声、安佚等自然欲望,有可善可恶的气性甚至是纯粹的恶性。
正因如此,才需要人控制自己的人性。
与“忍性”意义相反,“忍心”是指把感情按住不让表现,即为狠心,意味心的残酷。
不忍心是指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也就是不狠心、心不狠,它值得大力提倡。
仔细分析,“不忍之心”包含“不忍人之心”和“不忍物之心”,也就是“不忍人痛苦之心”和“不忍物痛苦之心”——用孟子的话说就是“不忍其觳觫”,它们不仅指无伤人害物之心,也指助人爱物之心。
就“不忍人之心”一句,《孟子注疏》断为“先圣王推不忍害人之心,以推不忍伤民之政”[17](P93)。
这只是看到了“不忍人之心”消极的不去伤害他人之心的一面,实则它还有不愿看到民众(他人)自身痛苦的意思。
什么是“怵惕恻隐之心”?
朱熹训解道:
“怵惕,惊动貌。
恻,伤之切也。
隐,痛之深也。
此即所谓不忍人之心也。
”[1](P221)怵惕意为恐惧警惕,用通俗点的话说就是害怕,恻隐意为悲伤、隐痛,于是“怵惕恻隐之心”就是指因某种东西产生的害怕、悲痛。
概括起来,“不忍人之心”和“怵惕恻隐之心”体现出共同的内涵,这就是见到遭受灾祸或不幸的人或事生成或表示同情之心。
孟子较为重视“忍”,不仅阐述了“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的君子人格理想,还利用“不忍人之心”去诠释仁政学说,提出了“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的政治理念,并依据“忍”解说仁。
他之所以断定齐宣王具备“不忍之心”,就在于齐宣王不愿意看到牛被伤害——“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体现了对动物的同情之心,因而表现出了一种“仁术”。
孟子还讲:
“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孟子·尽心下》)。
历来所有注家注解这一章句为:
每个人都有不忍心干的事,把这种不忍心推及到忍心干的事上,就是仁。
如此解读虽然不错,却不够周延。
正如上述,孟子既讲“不忍”也讲“忍”,他倡导的“不忍”就是“不忍心”,就是不狠心,包含“不忍人痛苦之心”和“不忍物(动植物)痛苦之心”,不仅指无伤人害物之心(不忍死、不忍食肉,这是底线伦理),也指向上向善的助人爱物之心。
孟子这里说的“达之于其所忍”的“忍”,是指控制不了自己的坏心恶意做坏事(忍心),这时需要人发挥“不忍心”(善心)精神加以制止。
也许持“四心萌芽说”者会辩护说由“不忍”到“忍”的推恩,不过是内在的仁心本源的外在体现,并不是对仁的缘起的界定。
这也许不失为一种合理的解释。
但是,把孟子这句话理解为将普遍的“不忍人之心”加以扩充,以扬善抑恶,是达成仁德的重要门径和动因,又何尝不是恰当的创造性诠释呢?
应当说这同样也是可以成立的。
把“不忍人之心”或“怵惕恻隐之心”视为仁德的心理根源和情感原因与西方思想家用同情去规定爱本质上是相通的。
同情是指对他人、他物遭受的不幸、苦难产生的关怀、理解等情感,它以移情作用(感同身受)为心理基础,严格意义上的同情主要是指同情者本身针对弱者、不幸者表示关心、关爱的情感体验,它的近义词有哀怜、可怜、怜惜、怜悯、仁慈等。
西方许多学者对同情在仁爱、慈爱中的功能表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