罂粟之家.docx
《罂粟之家.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罂粟之家.docx(1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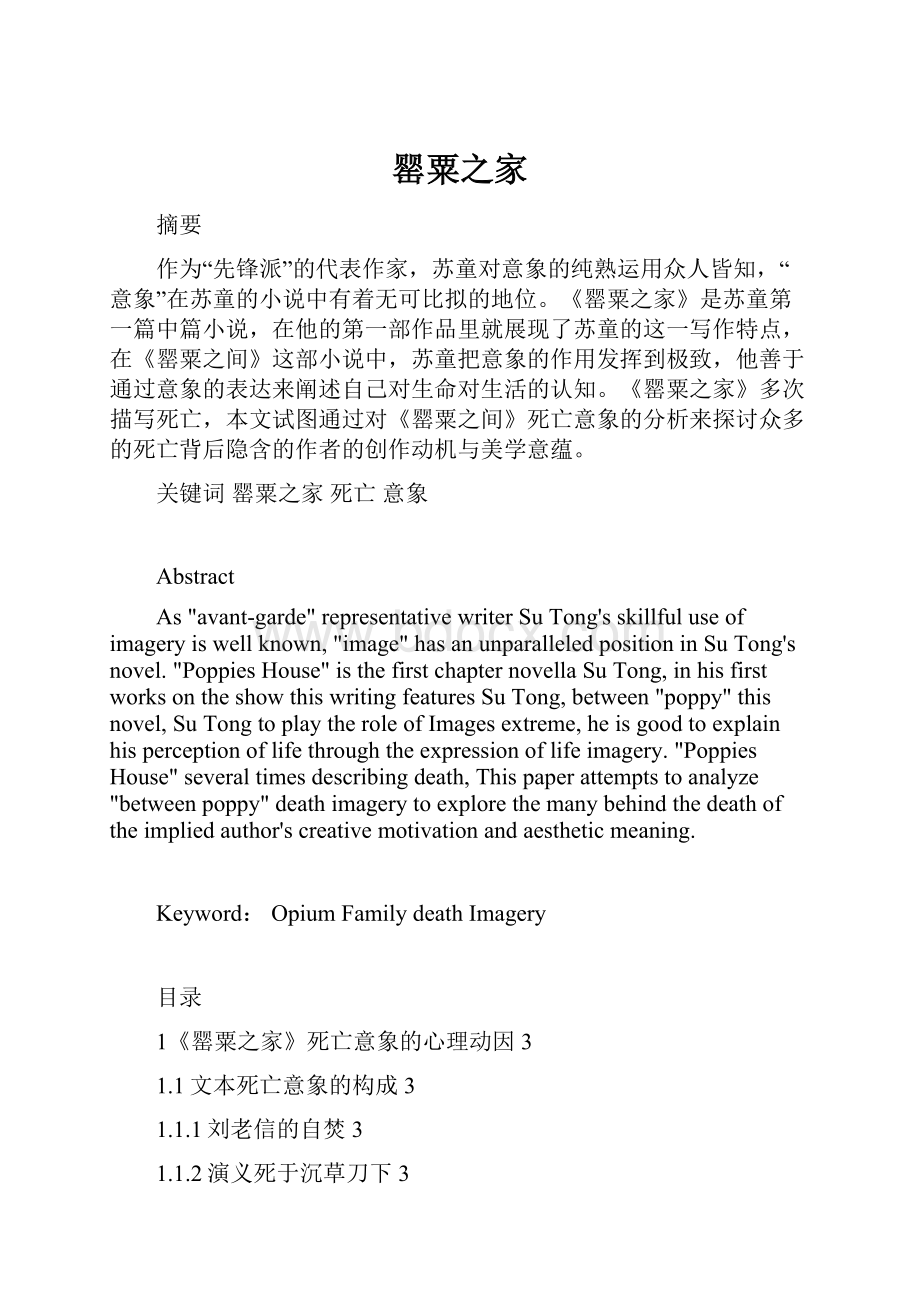
罂粟之家
摘要
作为“先锋派”的代表作家,苏童对意象的纯熟运用众人皆知,“意象”在苏童的小说中有着无可比拟的地位。
《罂粟之家》是苏童第一篇中篇小说,在他的第一部作品里就展现了苏童的这一写作特点,在《罂粟之间》这部小说中,苏童把意象的作用发挥到极致,他善于通过意象的表达来阐述自己对生命对生活的认知。
《罂粟之家》多次描写死亡,本文试图通过对《罂粟之间》死亡意象的分析来探讨众多的死亡背后隐含的作者的创作动机与美学意蕴。
关键词罂粟之家死亡意象
Abstract
As"avant-garde"representativewriterSuTong'sskillfuluseofimageryiswellknown,"image"hasanunparalleledpositioninSuTong'snovel."PoppiesHouse"isthefirstchapternovellaSuTong,inhisfirstworksontheshowthiswritingfeaturesSuTong,between"poppy"thisnovel,SuTongtoplaytheroleofImagesextreme,heisgoodtoexplainhisperceptionoflifethroughtheexpressionoflifeimagery."PoppiesHouse"severaltimesdescribingdeath,Thispaperattemptstoanalyze"betweenpoppy"deathimagerytoexplorethemanybehindthedeathoftheimpliedauthor'screativemotivationandaestheticmeaning.
Keyword:
OpiumFamilydeathImagery
目录
1《罂粟之家》死亡意象的心理动因3
1.1文本死亡意象的构成3
1.1.1刘老信的自焚3
1.1.2演义死于沉草刀下3
1.1.3陈茂被沉草打死3
1.1.4刘老信、翠花花、刘素子死在衰草亭3
1.1.5沉草死于罂粟缸4
1.2对父权的颠覆4
1.2.1刘老侠与子女的关系4
1.2.2沉草与陈茂的关系5
1.3童年的死亡意识5
2.死亡意象的审美内涵6
2.1死亡意象的历史化6
2.1.1欲望与历史的颓败6
2.1.2革命与暴力的表达6
2.1.3历史的困惑与沉思7
2.2生存的悲剧与死亡的超越7
2.2.1人性之困7
2.2.2寓于死亡之中的永恒之美与悲悯情怀8
3.《罂粟之家》与余华作品《兄弟》中死亡叙述的比较8
3.1两种死亡给读者带来的别忘感受8
3.2两部作品中死亡意象叙述差异的原因9
3.3苏童小说死亡意象的美学情韵9
参考文献11
1《罂粟之家》死亡意象的心理动因
1.1文本死亡意象的构成
纵观《罂粟之家》全文,罂粟之家——刘家,几乎所有人都走向了死亡。
全文的死亡意象也在刘家人一个接一个的死亡过程中不断演变、深化。
笔者将按照文本人物死亡的时间顺序解构《罂粟之家》的死亡意象。
1.1.1刘老信的自焚
在目前关于苏通及其小说的研究文章中,对于《罂粟之家》刘老信这个人物的讨论非常罕见。
其实,刘老信对于整个故事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正是因为他,给刘老侠带来了罂粟生意,使得“刘家由两支变为一支”,也带来了翠花花,那个日后成为故事关键冲突的女人,因为他的死亡,白痴演义失去了唯一可以对话的人。
值得注意的是,刘老信和刘老侠处于竞争地位,刘老信的自焚宣告着刘老侠的彻底胜利,象征着他统治地位的确立。
刘老信死亡之时,是刘老侠实力最盛,对枫杨树乡村拥有绝对霸权的时刻。
1.1.2演义死于沉草刀下
演义这一人物,是愚笨的是原始的,演义虽然是刘老侠的儿子,但是他却无时无刻都充满了饥饿感,一直叫着“给我馍!
给我馍!
”这象征着被地主阶级和封建势力压迫下一个普通人的原始诉求。
演义同时又是一个反抗者,他叫嚣着“我饿,我要杀了你。
”“不给我馍我就杀了你”但是他一直被父亲禁足,反抗得到了无情压迫。
最终,他拿起砍刀去砍杀沉草的性命,但是却被沉草连砍五刀,凄惨死去。
他的死由沉草完成,地主阶级接班人凶狠的完成了父辈的期许——连砍五刀。
演义的死亡标志着反抗者的失败。
1.1.3陈茂被沉草打死
陈茂的死非常悲惨。
先是被自己的亲儿子用枪打中眼睛和裤裆而死,后来又被刘老侠转移到衰草亭作为陪葬和牲祭品。
他虽然出走、反抗,但是最终还是像狗一样死去。
陈茂的死似乎也暗示着反抗的失败,他参加革命看似获得重生,但是像革命者说的一样,“我们可以改变他的身份,但是改变不了他身体里流的血”做了革命者,最想的是把刘老侠的女儿刘素子睡了,最后一面见到沉草,称呼的还是“少爷”。
这样看来,陈茂本性未改,参加革命看似是反抗的胜利和复活,但是本性却注定了他的覆灭,他在心理上一直没有战胜对“狗”这个身份的认同,奴性并未消除。
所以说,陈茂的死,象征了广大愚昧无知的人的宿命,虽可获得自由身,但却丢不掉血液里流淌的“奴性”,解放和革命,也只会加剧他们的毁灭。
1.1.4刘老信、翠花花、刘素子死在衰草亭
翠花花和刘素子是本部小说中仅有的两位女性,他们一直作为陪衬存在,自醒自强的意识微薄。
翠花花本来的身份是妓女,被强迫带到刘家,刘老侠没有生育能力,她又被强迫和陈茂交合诞下沉草,最终可能心存不甘,但是和刘老侠死在了一起。
刘素子,这个身体冰冷,一生大部分时间与猫相伴的女人,也是被重重利用,先是被父亲当做筹码换取800亩田地,后来又被父亲推走当做平息土匪闹事的条件,最终也和翠花花一样,不能选择的死在父亲身边。
两位女性虽有反抗,但是摆脱不了陪衬的命运,他们是整个家族巨变当中迷茫的旁观者,也是社会变革中被地主阶级残害的受害者。
山雨飘摇的时代,谁都不能置之事外,她们的死,是凄凉的,也是无辜的。
1.1.5沉草死于罂粟缸
“诞生于故事开首的婴儿一旦长大将成为核心人物,这在家族史中是不言而喻的”小说开头是他的出生,结尾是他的死亡。
起初穿着蓝色制服的少年队封建的“罂粟之家”是不了解的、甚至是排斥的,他走在田野中,闻着罂粟的花香,感到晕颤。
但是遭遇革命之后,他自己吸食了罂粟,比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最终也在罪恶之花、死亡之花的花粉下结束生命。
沉草最终死在罂粟缸之中,颇具象征意味——罂粟将沉草埋葬。
毫无疑问,罂粟是罪恶之源是死亡之手,是罂粟将沉草毒害,但是画本无罪,是人的罪,是整个封建制度的罪恶,是千百年来地主阶级自己种下的恶果。
沉草,既是无辜被害的少年,又是地主阶级、封建势力竭力培养的新生力量。
他的死,既意味着地主和封建势力对人的残害,也同时昭示着封建势力的解体、地主阶级的垮台。
1.2对父权的颠覆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纲常里面,父权永远是高高在上的、不可抗辩的、拥有绝对权威的。
在《罂粟之家》这部小说里面,刘老侠虽然也带有上述特点。
但是更多了一些复杂性,从亲情角度出发,他们之间存在的有别于真正亲情的令人寒心的关系是特别的,其中父子或父女之间充斥着权利、地位、利益、血缘、生存、报复等多种元素的复杂关系。
这种关系背后,是这部小说流露出的对传统父权权威的颠覆。
主要表现在刘老侠和子女的关系和沉草与陈茂的关系上。
1.2.1刘老侠与子女的关系
刘老侠与子女的关系是对立的,同时也是互相依靠、利用的。
演义是刘老侠的儿子,但是在文中读者能够感受到刘老侠对这个儿子深深的恨意。
这种恨意超越了传统意义的“恨铁不成钢”,是真正的敌人,仿佛刘老侠对演义这个儿子唯一的爱就是允许他还活着。
“虎毒不食子”的警语在刘老侠这里被颠覆,当沉草将演义砍死,刘老侠没有表现出一丝的悔意,没有对沉草有一丝的责骂。
父与子,是纯粹的对立,这种对立本身就是对传统父权纲常的颠覆。
刘素子是刘老侠的女儿,被反复利用。
先是用她来换取良田百亩,后来又将女儿推入火坑,用做阻止土匪入侵的挡箭牌。
“没有永远的亲情与血缘,只有永远的利益”这句话在刘老侠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刘素子的幸运在于她不像演义那般“痴傻”,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反抗者,与父亲的关系存在着看似可以缓和的灰色地带。
有一个大胆的比喻,刘素子不像是刘老侠唯一的女儿,而更像是从哪里捡来随手可以抛弃的小姨太。
沉草与刘老侠的关系要微妙的多。
首先明确,沉草并不是刘老侠的亲生儿子,借“种”生子。
这种私生子在传统的父权社会里是极大的罪恶,沉草本应该是极低贱的地位。
但是在《罂粟之家》中,沉草的身份是合法的,是被刘老侠接受并且视若珍宝的。
沉草有如此地位的原因是:
刘老侠唯一的儿子演义痴痴傻傻,不能作为家业的继承人,他希望沉草这个“儿子”能够继承土地,接过那把“有月晕光泽,散发着田野植物各种气息”的白金钥匙。
沉草离不开刘老侠,离不开刘家暗黑的大院,离不开种满罂粟花充斥着罪恶的枫杨树村。
沉草只有在刘老侠的庇佑下,他才是少爷,才是被众人尊敬的合法地主接班人。
没有刘老侠,沉草只是被人唾弃的私生子,什么也没有。
“鸟儿的翅膀被刷上了金漆,便再也不能飞翔了”,于沉草来说,刘老侠是他的庇护伞,是他地位和名誉的源泉,他依赖刘老侠。
反观刘老侠,能够理解他对沉草的复杂感情,一方面他深知眼前的少年不是自己的“种儿”在替别人养儿子,但是另一方面,他要依靠沉草将家业传承下去,维继刘家的香火,他要沉草发誓“你接过刘家的土地和财产,你要用这把钥匙打开土地大门,你起誓刘家产业在你这一辈更加兴旺发达!
”
为了活着为了活的有尊严,沉草离不开刘老侠;为了家业,为了不断血脉,刘老侠依赖沉草。
表面父与子的关系却隐藏着互相依靠、利用的暗流。
总体来说,刘老侠与子女的关系是非亲情的,非传统的,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依赖利益而不是父权的基础标志——血缘。
所以,刘老侠与子女的关系标志着《罂粟之家》对父权的颠覆。
1.2.2沉草与陈茂的关系
沉草与陈茂的关系满足了“俄狄浦斯情节”的两个元素之一的“弑父”情节——最终沉草举枪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杀死了自己的生父。
并且比遥远的俄狄浦斯弑父情节更加悲剧的是沉草在结束自己生父时选取的方式——在眼睛和裤裆各打一枪,极具复仇意味,并且饱含诅咒。
陈茂地位素来低贱,他在刘家被刘老侠当做一条狗,并且刘老侠还要变态的强迫陈茂承认自己是条狗,强迫“儿子”沉草叫陈茂为“狗”。
滑稽的是,这种变态的叫法植根于沉草和陈茂的内心之中,少爷认同了这种叫法,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陈茂也表示了对这种叫法的接受。
事实上,最后经历革命的陈茂虽然不再答应被叫做“狗”但是身上的奴性依旧没有消除,面对来讨命的沉草,他卑躬屈膝的叫着“少爷”。
陈茂身上的奴性致使他在内心深处接受了儿子被抢夺的既定事实,小说自始至终没有表现出陈茂对自己儿子的挽回或者怜爱,他只是很规矩的很正常的叫着少爷。
沉草和陈茂之间本来没有直接的矛盾,但是作为刘老侠的接班人,他必须要为自己身后的罂粟地背书,沉草已经完全融入了封建地主阶级,他必须要为了自己所代表的利益斗争,是陈茂和陈茂带领的人毁坏了他锦衣富食的生活,他虽然听说过甚至也可能怀疑过陈茂就是自己的生身父亲,但是它还是毅然决然的拿起枪向陈茂身上打去。
沉草弑父结束了一切的矛盾。
这一部分也作为小说的高潮结束,严格来说,沉草与陈茂的矛盾并不是个人之间的矛盾,而是他们各自所占的阶级的矛盾,已然没落的地主阶级和并不成熟的革命者的对垒。
至此,具有血缘关系的父子在枪响中彻底崩溃,小说亦完成了对父权的完全颠覆。
1.3童年的死亡意识
童年的死亡意识主要是指沉草在童年时期经历的死亡事件——亲手将哥哥演义打死。
“沉草从来不行新演义是自己的哥哥”,演义身上带有“某种低贱的痛苦”那是一代枫杨树人所共有的气质,粗蛮、贪婪、痛苦…….这些特质与沉草格格不入,他被宠爱着长大,受过学校教育,远离贫穷、肮脏,他没想过也不相信自己有这样一个哥哥。
本来想要和演义打球,但是最终却把演义杀了。
经过这个事情,父亲没有责备沉草,反而告诉他不要害怕,那是演义的命,是他要杀你你才杀他的。
演义的死除了给沉草带来惊吓以外,更从父亲那里学到了两个词语:
命数和报复。
“王侯将相有种乎!
”压迫阶级制造的宿命论在演义的心里埋下了种子,维护自己利益不惜牺牲别人生命的念头也在沉草心里生根发芽。
这次事件带给沉草的死亡意识使得他更进一步的向刘老侠所处的地主阶级封建势力靠近,是日后沉草拿枪杀死陈茂,守护家产的动力诱因。
2.死亡意象的审美内涵
2.1死亡意象的历史化
苏童写作《罂粟之家》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一反中国现当代家族小说的叙事传统,以人性欲望取代阶级矛盾,以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精神和血缘联系取代两个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对立冲枫杨树世界植物的颓败、生存空间的潮湿霉烂与人的精神堕落异形同构地交织在一起。
2.1.1欲望与历史的颓败
《罂粟之家》这本小说中,欲望是骚动的,不安分的,犹如火苗,闪烁跳跃,试图僭越。
翠花花本来是刘老信从城里妓院带来献给父亲的礼物,但是这一“礼物”并不是被存藏的物品,她的到来引起了轩然大波,猫眼女人的死亡极可能与她有莫大的关系,不得不说这个城里来的女人燃烧着欲望之火。
这把“火”可能是猫眼女人死亡的原因,翠花花的欲望是非法的,不符宗法的。
后来刘老侠掌握了家族的实际控制权,他的欲望蔓延到翠花花的身上,这种欲望的僭越是伦理上的。
土匪姜戎在抢夺刘家大院的时候,宁愿放弃粮食–这一对土匪的生存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物质。
转而要求带走刘素子,姜戎对刘素子的欲望跨越了基础需求,超越了理性思考。
陈茂在枫杨树村有着“金枪不倒”的称号,但是陈茂却不甘于在普通的村民女子中挥洒欲望,书中前半部分可以看到他与翠花花的偷情,并且在刘老侠的默许下生下沉草。
后半段陈茂参加革命,回到家乡第一个想睡的女人是地主的女儿——刘素子。
陈茂是个不折不扣的普通百姓,但是他的欲望一直朝向地主阶级的女人不断散发。
这种欲望的僭越是阶级上的。
《罂粟之家》里面的每个人物都深陷在欲望的沼泽中不能自拔。
刘老侠因为日日和女人在衰草亭野合,终究因为血旺而乱,乱不能生正常的小孩儿,刘老侠的欲望使得自己无法拥有一个健康正常的孩子,面临着“无后”的不孝罪名,并且,刘老侠对于财富的欲望是造成刘老信悲惨死去的直接原因,因为欲望,手足相残,刘老侠也背负着不仁的罪过。
因为陈茂对翠花花不合常理的欲望,他们的孩子沉草一生下来就带着不符宗法不合礼数不被法律社会承认的“原罪”。
这是沉草悲剧一生的出发点。
土匪姜戎本来打算抢劫刘宅,但是因为对刘素子的欲望,他放弃抢劫,转而将刘素子带走当做压寨夫人。
陈茂对翠花花的欲望使他陷入了被当做狗的境遇中,对刘素子的欲望又使他丢掉了农会主席的职位。
《罂粟之家》描述的所有欲望,无论是追求女人或者追求爱情亦或者是推翻地主压迫的欲望,这些欲望都是非理性的、突发的,他们是简单的爱恨相加,无法上升到历史的自觉意识。
做不到自觉的维护阶级利益,所以罂粟之家的欲望是骚乱躁动的,由于欲望所引起的巨变并不是真正的历史进程,而是带着原始爱恨的历史颓败。
2.1.2革命与暴力的表达
每一部小说都不是凭空捏造的,都有一定的创作背景。
苏童的《罂粟之家》,故事发生背景在中国解放前后,土改期间。
面对那片历史,大多数人习惯的书写方式是站在历史进步的观点,以新的视角来描述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土改是历史的必然。
但是苏童在肯定土改的必然性和认同历史进步的同时,他选择站在更少的视角去写作。
他以被历史抛弃的群体的视角描绘了这场大运动,他的描写充满了神秘感,以一种绝望的立场看待一场必将到来的历史事件,在这里看到的不是“敢叫天地换新颜”的壮烈激昂步调,相反会被历史颓败的气息笼罩。
小说中几乎没有多少笔墨去表现直接的阶级压迫。
刘老侠对陈茂几乎谈不上是阶级压迫,陈茂与翠花花通奸本身就是对阶级压迫的一种颠覆。
它显然不是阶级反抗的一种方式,而是阶级错位的一种形式。
因而土改的到来一直在一种宿命感中被注定,土改不过加速了本来就要灭亡的地阶级的死亡而己。
在苏童的书写中,土改实际上寄生于欲望的错位结构中。
苏童对土改的叙述弥漫着强烈的反讽情绪,它把土改的场面描写和阶级冲突重新植入欲望的结构中。
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仇恨远没有大到足以推翻一个阶级力量。
就个人来说,农民的
不满也很容易被改良主义所抹平。
沉草把土地租给农民,只收一半的租子,农民就给沉草下跪。
二民的革命并没有多少自主性,庐方启发陈茂革命,陈茂始终搞不清楚土地改革的实质,对于他来说,他当上农会主席,手中有枪意味着他有权力,而这种权力被他简单地等同于性权力。
他还是以他的惯性回到原来翻墙的那种生存方式,他终于把刘子干了,这是他的阶级报复还是他由来己久的欲望梦想。
土改斗争的场面也被苏童戏谑化了。
1950年春天,三千枫杨树人参加了地主刘老侠的斗争会,这个场面演变为又哭又闹的喜剧场面。
最荒谬的
在于翠花花冲进会场与陈茂撕扯在一起,这个斗争的现场被欲望的关系给嘲弄了。
随后哄抢账本的场面,不过是这个最荒谬的现场的补充。
这是在末日发生的革命,这样的历史暴力如期而至,就像不速之客,本来地主阶级己经颓败,己经走向灭亡,这样的历史变故就显得是趁火打劫,这样的暴力就显得更加残酷。
地主阶级陷入这样的境地就几乎是加速死亡。
沉草坐在婴粟面上,大把吃罂粟,已经濒临疯狂,那疯狂,带着绝望的气息。
所以,作者关于革命与暴力的表达是残酷的、冰冷的、甚至是戏谑的、略带讽刺的。
2.1.3历史的困惑与沉思
“祖父”津津乐道的“历史”回忆,无疑造成了“孙子”思维上的困惑不解:
“大约有一千名枫杨树人给地主刘老侠种植水稻与婴粟”的刘氏家族,却仍旧同“枫杨树”的普通农民一样天天“喝稀粥”,并让其子嗣“饿得面黄肌瘦”“整天哇哇乱叫”,乍一听去简直
是有点天方夜谭,但作者却告诉我们这就是一种“历史”文本的真实记载,是“枫杨树”人历来引以为自豪的人文传统。
阅读《婴粟之家》我们的确对于“历史”倍感迷茫—长工是种地的“农民”,地主是收租的“农民”,除去物资方面的财富差别,他们“农民”的本质却并无两样—他们勤奋,他们节俭,他们务实,他们守旧—每天喊“饿”的“演义”到“死”也没有吃饱过肚子,可“演义睡了棺材。
枫杨树老人告诉‘我’,演义的棺材里堆满了雪白雪白的馒头,那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殉葬,他们说白痴演义应该螟目了,他的摸再也吃不光了”。
我真想对于这种无与伦比的反讽叙事。
“历史”不可言说而只能感知,这是《婴粟之家》告诉读者的客观“真理”“因为‘历史’是山曾经发生在‘过去’的所有事情组成”,它由“人”所造就并由“人”来书写;因此文化修养与意识形态完全不同之“人”,也就会对“历史”产生完全不同的自我理解。
无论苏童个人的“历史观”正确与否,但他却道出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历史”文本恰如“小说”文本一样,它们都是由“人”来完成的一种书写实践;而“人”在认识上的思想局限性,又直接导致了“历史”书写的思想局限性—故“历史”总是“残缺”的而不是“完整”的民族记忆!
2.2生存的悲剧与死亡的超越
2.2.1人性之困
小说的中心人物当然是沉草,他是所有的矛盾的聚集体,他就是轴心,是起源,也是结果。
正如小说的开头就是他的出生一样,小说的结尾也是他的死亡。
这是他的完整一生的故事。
他建立起一张关系图谱,那是变异、倒错、嫁接和暴力完成的拼贴。
沉草最终的悲剧收场体现了小说展现的人性之困。
陈茂抑制不住人性的欲望,他和翠花花偷情并且生下了沉草,刘老侠恐惧陈茂的存在,人性的阴暗使得他不断奴役陈茂,责骂陈茂为“狗”。
沉草与土改组组长是同窗好友,但是为了阶级和个人利益,沉草毅然选择了斗争到底…….诸如此类,《罂粟之家》集中展现了小说里人物的人性黑暗一面,困顿其中,不得解救。
2.2.2寓于死亡之中的永恒之美与悲悯情怀
在《罂粟之家》中,苏童使笔下的人物重新找到了人性的最本真状态,使人性中长期被遮蔽的欲望挣脱沉重的镣铐,浮出历史地表。
人的欲望不再龟缩在道德伦理的重负中急迫地呼吸,欲望成为颠覆阶级力量对比,推动历史前进的神秘动力。
这里,苏童摈弃了自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的“宏大叙事”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系统,创造了一种伦理关系和阶级(层)关系的新的叙事范式。
“我的创作目标,就是无限利用‘人’和人性的力量,无限夸张人和人性力量,打开人生与心灵世界的皱折,轻轻拂去皱折上的灰尘,看清人性自身的面目,来营造一个小说世界。
川引’苏童总是小心翼翼地将人性从社会和时代的标签中剥里出来,直面人性的残缺,不露声色地不做任何价值评判地,将人性的幽暗之处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也许它是丑陋的阴暗的罪恶的,但只因为它是真实的。
这就是苏童式的人性关怀,深刻而特别。
3.《罂粟之家》与余华作品《兄弟》中死亡叙述的比较
3.1两种死亡给读者带来的别忘感受
《兄弟》中4次描写到死亡,8岁时李光头和宋钢到处寻找父亲,见到的却是暴尸街头的宋凡平,出生不好的人的死亡在“文革”年月是没有任何人敢同情的,母子三人不敢哭泣,直到空无一人的夏天的田野里只剩下家人和躺在棺材里的宋凡平时,他们才敢痛快响亮地哭泣,那如同阵阵爆炸声的哭泣里充满了对离去亲人的依恋。
如果说8岁时父亲的死让童年的李光头和宋钢感到一种未知和茫然的话,巧岁时母亲的死让少年的李光头和宋钢感到的则是一种责任和已知的绝望。
饱受折磨的李兰在宋凡平死后7年未曾洗头,在预感到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死亡对她而言没有痛楚,有的只是能够见到宋凡平的渴望,她平静地向兄弟俩交待后事并催促兄弟俩回家睡觉,凌晨1点兄弟俩回到家里,等天亮来到医院时母亲已经去世,“宋钢跪在水泥床前的地上哭得浑身哆嗦,李光头站在水泥床前哭得像风中的小树那样抖个不停。
李光头和宋钢一起哭,一起叫着妈妈。
李光头是在这一刻真正感到自己是这个世界上的孤儿了,他只剩下了宋钢,宋钢也只剩下了他。
”当他们拉着棺材走在7年前的那条路上时,“两个人没有了哭声,他们弯着腰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一个拉着一个推着,他们的身体弯得比板车上那具棺材还要低,远远看去不像是两个人,像是那辆板车多出来了一个车头和一个车尾。
”李兰去世以后,宋钢伴随着风烛残年的爷爷老地主,当宋钢知道背上的老地主已经自然地老去时,没有眼泪,独自料理了爷爷的后事,死亡对于此时的宋钢则是一种漠然与接纳。
当李光头知道宋钢去世的消息时,他惊呆了,赤裸裸像个傻子一样站在那里,像失去知觉一样一动不动,面对宋钢的死,李光头感到一种悲凉,寒自心底的悲凉。
余华就是这样借助他人曾在的死亡表达了死亡始终是一种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的发生又有着不确
定性,在走向不确定的已知的死亡的时候,主人公迅速地走向成熟。
《兄弟》里以死亡来见证亲情的脆弱和本能欲望才是人性的主体。
李光头的父亲因偷窥女厕而掉进粪坑淹死,宋钢的死则不过是导致李光头性无能,而林红彻底堕入到风花雪月的色情场所。
生的脆弱和死的无意义(包括宋钢的父亲的死和“文革”中被打死的人),彰显苦难在人类生活中不可挥去的悲悯气息。
在本文第一章节提到《罂粟之家》的几个死亡意象,刘老信的自焚、演义死于沉草刀下、
陈茂被沉草打死、刘老信、翠花花、刘素子死在衰草亭、沉草死于罂粟缸。
作者的笔锋冷峻,像是从高空俯视的角度来观察生死沧桑,作者用死亡的阴影雕刻出欲望的本质和亲情的脆弱。
3.2两部作品中死亡意象叙述差异的原因
同样作为先锋小说,仔细看起来《兄弟》的死亡描写比《罂粟之家》更具现实性,兄弟对死亡的描写也大多是具体可感的。
这是因为在余华的写作当中,总是充斥着生与死的辩证思考,死亡是伴随着出生就已经注定了的事情,在“生”的过程中,你不会知道死亡是什么时候发生,一个人活着的时候永远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余华的小说写作总是在把主人公放在一个极其矛盾的位置,但就是在这样略显荒诞的境地下,小说的主人公实现了成长。
在这种创作背景下描写的死亡会让读者感同身受,在“兄弟”的故事里看到自己生活里面的悲苦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