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徒生童话故事第《波尔格龙的主教和他的亲族》中英文版.docx
《安徒生童话故事第《波尔格龙的主教和他的亲族》中英文版.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安徒生童话故事第《波尔格龙的主教和他的亲族》中英文版.docx(1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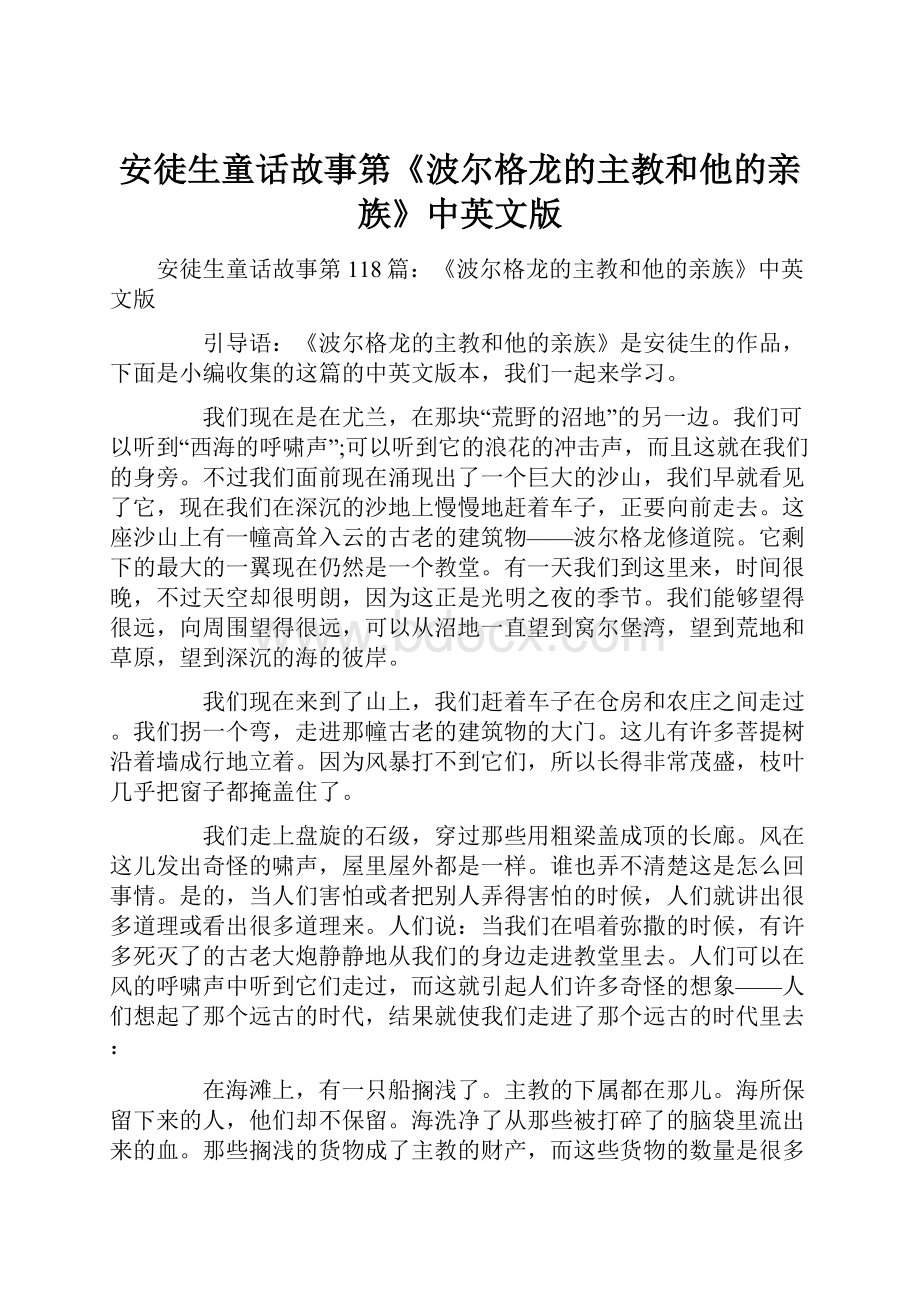
安徒生童话故事第《波尔格龙的主教和他的亲族》中英文版
安徒生童话故事第118篇:
《波尔格龙的主教和他的亲族》中英文版
引导语:
《波尔格龙的主教和他的亲族》是安徒生的作品,下面是小编收集的这篇的中英文版本,我们一起来学习。
我们现在是在尤兰,在那块“荒野的沼地”的另一边。
我们可以听到“西海的呼啸声”;可以听到它的浪花的冲击声,而且这就在我们的身旁。
不过我们面前现在涌现出了一个巨大的沙山,我们早就看见了它,现在我们在深沉的沙地上慢慢地赶着车子,正要向前走去。
这座沙山上有一幢高耸入云的古老的建筑物——波尔格龙修道院。
它剩下的最大的一翼现在仍然是一个教堂。
有一天我们到这里来,时间很晚,不过天空却很明朗,因为这正是光明之夜的季节。
我们能够望得很远,向周围望得很远,可以从沼地一直望到窝尔堡湾,望到荒地和草原,望到深沉的海的彼岸。
我们现在来到了山上,我们赶着车子在仓房和农庄之间走过。
我们拐一个弯,走进那幢古老的建筑物的大门。
这儿有许多菩提树沿着墙成行地立着。
因为风暴打不到它们,所以长得非常茂盛,枝叶几乎把窗子都掩盖住了。
我们走上盘旋的石级,穿过那些用粗梁盖成顶的长廊。
风在这儿发出奇怪的啸声,屋里屋外都是一样。
谁也弄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情。
是的,当人们害怕或者把别人弄得害怕的时候,人们就讲出很多道理或看出很多道理来。
人们说:
当我们在唱着弥撒的时候,有许多死灭了的古老大炮静静地从我们的身边走进教堂里去。
人们可以在风的呼啸声中听到它们走过,而这就引起人们许多奇怪的想象——人们想起了那个远古的时代,结果就使我们走进了那个远古的时代里去:
在海滩上,有一只船搁浅了。
主教的下属都在那儿。
海所保留下来的人,他们却不保留。
海洗净了从那些被打碎了的脑袋里流出来的血。
那些搁浅的货物成了主教的财产,而这些货物的数量是很多的。
海浦来许多整桶的贵重的酒,来充实这个修道院的酒窖;而这个酒窖里已经储藏了不少啤酒和蜜酒。
厨房里的储藏量也是非常丰富的;有许多宰好了的牛羊、香肠和火腿。
外面的水池里则有许多肥大的鲫鱼和鲜美的鲤鱼。
波尔格龙的主教是一位非常有权势的人,他拥有广大的土地,但是仍然希望扩大他占有的面积。
所有的人必须在这位奥拉夫·格洛布面前低下头来。
他的一位住在蒂兰的富有的亲族死了。
“亲族总是互相嫉恨的”;死者的未亡人现在可要体会这句话的真意了。
除了教会的产业以外,她的丈夫统治着整个土地。
她的儿子在外国:
他小时候就被送出去研究异国风俗,因为这是他的志愿。
他许多年来一直没有消息,可能已经躺在坟墓里,永远不会回来接替他母亲的统治了。
“怎么,让一个女人来统治吗?
”主教说。
他召见她,然后让法庭把她传去。
不过他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她从来没有触犯过法体,她有十足的理由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波尔格龙的主教奥拉夫,你的意图是什么呢?
你在那张光滑的羊皮纸上写下的是什么呢?
你盖上印,用带子把它扎好,叫骑士带一个仆人把它送到国外,送到那辽远的教皇城里去,为的是什么呢?
现在是落叶和船只搁浅的季节,冰冻的冬天马上就要来。
他已经这样做了两次,最后他的骑士和仆人在欢迎声中回来了,从罗马带回教皇的训令——一封指责敢于违抗这位虔诚的主教的寡妇的训令:
“她和她所有的一切应该受到上帝的诅咒。
她应该从教会和教徒中驱逐出去。
谁也不应该给她帮助。
让她所有的朋友和亲戚避开她,像避开瘟疫和麻风病一样!
”
“凡是不屈服的人必须粉碎他,”波尔格龙的主教说。
所有的人都避开这个寡妇。
但是她却不避开她的上帝。
他是她的保护者和帮助者。
只有一个佣人——一个老女仆——仍然对她忠心。
这位寡妇带着她亲自下田去耕作。
粮食生长起来了,虽然土地受过了教皇和主教的诅咒。
“你这个地狱里的孩子!
我的意志必须实现!
”波尔格龙的主教说。
“现在我要用教皇的手压在你的头上,叫你走进法庭和灭亡!
”
于是寡妇把她最后的两头牛驾在一辆车子上。
她带着女仆人爬上车子,走过那荒地,离开了丹麦的国境。
她作为一个异国人到异国人的中间去。
人们讲着异国的语言,保持着异国的风俗。
她一程一程地走远了,走到一些青山发展成为峻岭的地方①——一些长满了葡萄的地方。
旅行商人在旁边走过。
他们不安地看守着满载货物的车子,害怕骑马大盗的部下来袭击。
这两个可怜的女人,坐在那辆由两头黑牛拉着的破车里,安全地在这崎岖不平的路上。
在阴暗的森林里向前走。
她们来到了法国。
她在这儿遇见了一位“豪强骑士”带着一打全副武装的随从。
他停了一会儿,把这部奇怪的车子看了一眼,便问这两个女人为了什么目的而旅行,从什么国家来的。
年纪较小的这个女人提起丹麦的蒂兰这个名字,倾吐出她的悲哀和痛苦——而这些悲愁马上就要告一终结,因为这是上帝的意旨。
原来这个陌生的骑士就是她的儿子!
他握着她的手,拥抱着她。
母亲哭起来了。
她许多年来没有哭过,而只是把牙齿紧咬着嘴唇,直到嘴唇流出热血来。
现在是落叶和船只搁浅的季节。
海上的浪涛把满桶的酒卷到岸上来,充实主教的酒窖和厨房。
烤叉上穿着野味在火上烤着。
冬天到来了,但屋子里是舒适的。
这时主教听到了一个消息:
蒂兰的演斯·格洛布和他的母亲一道回来了;演斯·格洛布要设法庭,要在神圣的法庭和国家的法律面前来控告主教。
“那对他没有什么用,”主教说。
“骑士演斯,你最好放弃这场争吵吧!
”
这是第二年:
又是落叶和船只搁浅的季节。
冰冻的冬天又来了;“白色的蜜蜂”又在四处纷飞,刺着行人的脸,一直到它们融化。
人们从门外走进来的时候说:
“今天的天气真是冷得厉害啦!
”
演斯·格洛布沉思地站着,火燎到了他的长衫上,几乎要烧出一个小洞来。
“你,波尔格龙的主教!
我是来制服你的!
你在教皇的包庇下,法律拿你没有办法。
但是演斯·格洛布对你有办法!
”
于是他写了一封信给他住在萨林的妹夫奥拉夫·哈塞,请求他在圣诞节的前夕,在卫得堡的教堂做晨祷的时候来会面。
主教本人要念弥撤,因此他得从波尔格龙旅行到蒂兰来。
演斯·格洛布知道这件事情。
草原和沼地现在全盖上了冰和雪。
马和骑士,全副人马,主教和他的神父以及仆从都在那上面走过。
他们在容易折断的芦苇丛中选一条捷径通过,风在那儿凄惨地呼号。
穿着狐狸皮衣的号手,请你吹起你的黄铜号吧!
号声在晴朗的空中响着。
他们在荒地和沼泽地上这样驰骋着——在炎暑的夏天出现海市蜃楼的原野上驰骋着,一直向卫得堡的教堂驰去。
风也吹起它的号角来,越吹越厉害,它吹起一阵暴风雨,一阵可怕的暴风雨,越来越大的暴风雨。
在上帝的暴风雨中,他们向上帝的屋子驰去。
上帝的屋子屹立不动,但是上帝的暴风雨却在田野上和沼泽地上,在陆地上和大海上呼啸。
波尔格龙的主教到达了教堂;但是奥拉夫·哈塞,不管怎样飞驰,还是离得很远。
他和他的武士们在海湾的另一边前进,为的是要来帮助演斯·格洛布,因为现在主教要在最高的审判席前出现了。
上帝的屋子就是审判厅,祭坛就是审判席。
蜡烛在那个巨大的黄铜烛台上明亮地燃着。
风暴念出控诉和判词;它的声音在沼泽地和荒地上,在波涛汹涌的海上回响着。
在这样的天气中,任何渡船都渡不过这个海峡。
奥拉夫·哈塞在俄特松得停了一下。
他在这儿辞退了他的勇士,给了他们马和马具,同时准许他们回家去,和他们的妻子团聚。
他打算在这呼啸的海上单独一个人去冒生命的危险。
不过他们得作他的见证;那就是说:
如果演斯·格洛布在卫得堡的教堂里是孤立无援的话,那并不是他的过错。
他的忠实的勇士们不愿意离开他,而却跟着他走下深沉的水里面去。
他们之中有十个人被水卷走了,但是奥拉夫·哈塞和两个年轻的人到达了海的彼岸。
他们还有五十多里路要走。
这已经是半夜过后了。
这正是圣诞节之夜。
风已经停了。
教堂里照得很亮;闪耀着的光焰透过窗玻璃,射到草原和荒地上面。
晨祷已经做完了;上帝的屋子里是一片静寂,人们简直可以听到融蜡滴到地上的声音。
这时奥拉夫·哈塞到来了。
演斯·格洛布在大门口和他会见。
“!
我刚才已经和主教达成了协议。
”
“你真的这样办了吗?
”奥拉夫·哈塞说。
“那么你或主教就不能活着离开这个教堂了。
”剑从他的剑鞘里跳出来了,奥拉夫·哈塞向演斯·格洛布刚才急忙关上的那扇教堂的门捅了一剑,把它劈成两半。
“请住手,亲爱的兄弟!
请先听听我所达成的协议吧!
我已经把主教和他的武士都刺死了。
他们在这问题上再也没有什么话可说了。
我也不再谈我母亲所受的冤屈了。
”
祭台上的烛芯正亮得发红,不过地上亮得更红。
被砍碎了脑袋的主教,以及他的一群武士都躺在自己的血泊里。
这个神圣的圣诞之夜非常安静,现在没有一点声音。
四天以后,波尔格龙的修道院敲起了丧钟。
那位被害的主教和被刺死的武士们,被陈列在一个黑色的华盖下面,周围是用黑纱裹着的烛台。
死者曾经一度是一个威武的主人,现在则穿着银丝绣的衣服躺着;他的手握着十字杖,已经没有丝毫权力了。
香烟在维绕着;僧众们在唱着歌。
歌声像哭诉——像忿怒和定罪的判同。
风托着它,风唱着它,向全国飞去,让大家都能听见。
歌声有时沉静一会儿,但是它却永远不会消失。
它总会再升起来,唱着它的歌,一直唱到我们的这个时代,唱着关于波尔格龙的主教和他的厉害的亲族的故事。
惊恐的庄稼汉,在黑夜中赶着车子走过波尔格龙修道院旁边沉重的沙路时,听到了这个声音。
躺在波尔格龙那些厚墙围着的房间里的失眠的人也听到了这个声音,因为它老是在通向那个教堂的、发出回音的长廊里盘旋。
教堂的门是早已用砖封闭了,但是在迷信者的眼中它是没有封闭的。
在他们看来,它仍然在那儿,而且仍然是开着的,亮光仍然在那些黄铜的'烛台上燃着,香烟仍然在盘旋,教堂仍然在射出古时的光彩,僧众仍然在对那位被人刺死的主教念着弥撒,主教穿着银丝绣的黑衣,用失去了威权的手拿着十字杖。
他那惨白和骄傲的前额上的一块赤红的伤痕,像火似地射出光来——光上面燃着一颗世俗的心和罪恶的欲望……
你,可怕的古时的幻影!
坠到坟墓里去吧,坠到黑夜和遗忘中去吧!
请听在那波涛汹涌的海上呼啸着的狂暴的风吧!
外边有一阵暴风雨,正要吞噬人的生命!
海在这个新的时代里没有改变它的思想。
这个黑夜无非是一个吞噬生命的血口。
至于明天呢,它也许是一颗能够照出一切的明亮的镜子——也像在我们已经埋葬了的那个远古的时代里一样。
甜蜜地睡去吧,如果你能睡的话!
现在是早晨了。
新的时代把太阳光送进房间里来。
风仍然在猛烈地吹着。
有一条船触礁的消息传来了——像在那个远古的时代里一样。
在这天夜里,在洛根附近,在那个有红屋顶的小渔村里,我们从窗子里可以看见一条搁了浅的船。
它触到了礁,不过一架放射器射出一条绳子到这船上来,形成一座联结这只破船和陆地的桥梁。
所有在船上的人都被救出来了,而且到达了陆地,在床上得到休息;今天他们被请到波尔格龙修道院里来。
他们在舒适的房间里受到了殷勤的招待,看到了和善的面孔。
大家用他们的民族语言向他们致敬。
钢琴上奏出他们祖国的曲子。
在这一切还没结束以前,另外一根弦震动起来了;它没有声音,但是非常洪亮和充满了信心。
思想的波②传到了遭难者的故国,报道他们的遇救。
于是他们所有的忧虑就都消逝了,他们在这天晚上,在波尔格龙大厅里的舞会中参加跳舞。
他们跳着华尔兹舞和波兰舞的步子。
同时唱着关于丹麦和新时代的“英勇的步兵”的歌。
祝福你,新的时代!
请你骑着夏天的熏风飞进城里来吧!
把你的太阳光带进我们的心里和思想里来吧!
在你光明的画面上,让那些过去的、野蛮的、黑暗的时代的故事被擦掉吧。
①这是指阿尔卑斯山脉。
丹麦没有山;从丹麦向法国和意大利去的路程,是一段由平原走向高山的路程。
②此处原文意义不明,疑是指电报。
《波尔格龙的主教和他的亲族》英文版:
TheBishopofBorglumandHisWarriors
OURsceneislaidinNorthernJutland,intheso-called“wildmoor.”Wehearwhatiscalledthe“Wester-wow-wow”—thepeculiarroaroftheNorthSeaasitbreaksagainstthewesterncoastofJutland.Itrollsandthunderswithasoundthatpenetratesformilesintotheland;andwearequiteneartheroaring.Beforeusrisesagreatmoundofsand—amountainwehavelongseen,andtowardswhichwearewendingourway,drivingslowlyalongthroughthedeepsand.Onthismountainofsandisaloftyoldbuilding—theconventofB?
rglum.Inoneofitswings(thelargerone)thereisstillachurch.Andatthisconventwenowarriveinthelateeveninghour;buttheweatherisclearinthebrightJunenightaroundus,andtheeyecanrangefar,faroverfieldandmoortotheBayofAalborg,overheathandmeadow,andfaracrossthedeepbluesea.
Nowwearethere,androllpastbetweenbarnsandotherfarmbuildings;andattheleftofthegateweturnasidetotheOldCastleFarm,wherethelimetreesstandinlinesalongthewalls,and,shelteredfromthewindandweather,growsoluxuriantlythattheirtwigsandleavesalmostconcealthewindows.
Wemountthewindingstaircaseofstone,andmarchthroughthelongpassagesundertheheavyroof-beams.Thewindmoansverystrangelyhere,bothwithinandwithout.Itishardlyknownhow,butthepeoplesay—yes,peoplesayagreatmanythingswhentheyarefrightenedorwanttofrightenothers—theysaythattheolddeadchoir-menglidesilentlypastusintothechurch,wheremassissung.Theycanbeheardintherushingofthestorm,andtheirsingingbringsupstrangethoughtsinthehearers—thoughtsoftheoldtimesintowhichwearecarriedback.
Onthecoastashipisstranded;andthebishop’swarriorsarethere,andsparenotthosewhomtheseahasspared.Theseawashesawaythebloodthathasflowedfromtheclovenskulls.Thestrandedgoodsbelongtothebishop,andthereisastoreofgoodshere.Theseacastsuptubsandbarrelsfilledwithcostlywinefortheconventcellar,andintheconventisalreadygoodstoreofbeerandmead.Thereisplentyinthekitchen—deadgameandpoultry,hamsandsausages;andfatfishswiminthepondswithout.
TheBishopofB?
rglumisamightylord.Hehasgreatpossessions,butstillhelongsformore—everythingmustbowbeforethemightyOlafGlob.HisrichcousinatThylandisdead,andhiswidowistohavetherichinheritance.Buthowcomesitthatonerelationisalwayshardertowardsanotherthanevenstrangerswouldbe?
Thewidow’shusbandhadpossessedallThyland,withtheexceptionofthechurchproperty.Hersonwasnotathome.Inhisboyhoodhehadalreadystartedonajourney,forhisdesirewastoseeforeignlandsandstrangepeople.Foryearstherehadbeennonewsofhim.Perhapshehadbeenlonglaidinthegrave,andwouldnevercomebacktohishome,torulewherehismotherthenruled.
“Whathasawomantodowithrule?
”saidthebishop.
Hesummonedthewidowbeforealawcourt;butwhatdidhegainthereby?
Thewidowhadneverbeendisobedienttothelaw,andwasstronginherjustrights.
BishopOlafofB?
rglum,whatdostthoupurpose?
Whatwritestthouonyondersmoothparchment,sealingitwiththyseal,andintrustingittothehorsemenandservants,whorideaway,faraway,tothecityofthePope?
Itisthetimeoffallingleavesandofstrandedships,andsoonicywinterwillcome.
Twicehadicywinterreturnedbeforethebishopwelcomedthehorsemenandservantsbacktotheirhome.TheycamefromRomewithapapaldecree—aban,orbull,againstthewidowwhohaddaredtooffendthepiousbishop.“Cursedbesheandallthatbelongstoher.LetherbeexpelledfromthecongregationandtheChurch.Letnomanstretchforthahelpinghandtoher,andletfriendsandrelationsavoidherasaplagueandapestilence!
”
“Whatwillnotbendmustbreak,”saidtheBishopofB?
rglum.
Andallforsakethewidow;butsheholdsfasttoherGod.Heisherhelperanddefender.
Oneservantonly—anoldmaid—remainedfaithfultoher;andwiththeoldservant,thewidowherselffollowedtheplough;andthecropgrew,althoughthelandhadbeencursedbythePopeandbythebishop.
“Thouchildofperdition,Iwillyetcarryoutmypurpose!
”criedtheBishopofB?
rglum.“NowwillIlaythehandofthePopeuponthee,tosummontheebeforethetribunalthatshallcondemnthee!
”
Thendidthewidowyokethelasttwooxenthatremainedtohertoawagon,andmounteduponthewagon,withheroldservant,andtravelledawayacrosstheheathoutoftheDanishland.Asastrangershecameintoaforeigncountry,whereastrangetonguewasspokenandwherenewcustomsprevailed.Fartherandfarthershejourneyed,towheregreenhillsriseintomountains,andthevineclothestheirsides.Strangemerchantsdrivebyher,andtheylookanxiouslyaftertheirwagonsladenwithmerchandise.Theyfearanattackfromthearmedfollowersoftherobber-knights.Thetwopoorwomen,intheirhumblevehicledr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