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与政治的相关性研究.docx
《农村土地与政治的相关性研究.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农村土地与政治的相关性研究.docx(1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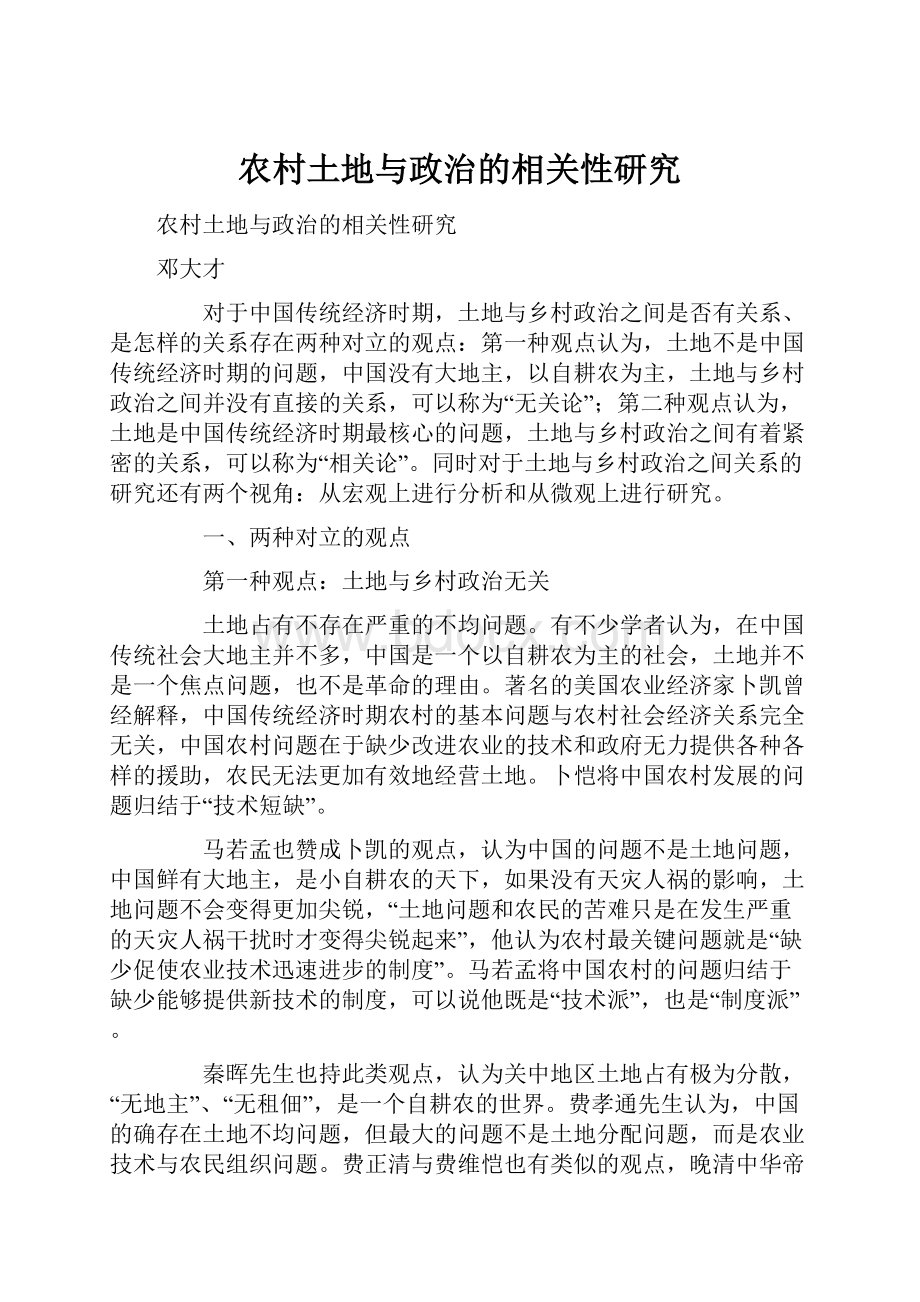
农村土地与政治的相关性研究
农村土地与政治的相关性研究
邓大才
对于中国传统经济时期,土地与乡村政治之间是否有关系、是怎样的关系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土地不是中国传统经济时期的问题,中国没有大地主,以自耕农为主,土地与乡村政治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可以称为“无关论”;第二种观点认为,土地是中国传统经济时期最核心的问题,土地与乡村政治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可以称为“相关论”。
同时对于土地与乡村政治之间关系的研究还有两个视角:
从宏观上进行分析和从微观上进行研究。
一、两种对立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
土地与乡村政治无关
土地占有不存在严重的不均问题。
有不少学者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大地主并不多,中国是一个以自耕农为主的社会,土地并不是一个焦点问题,也不是革命的理由。
著名的美国农业经济家卜凯曾经解释,中国传统经济时期农村的基本问题与农村社会经济关系完全无关,中国农村问题在于缺少改进农业的技术和政府无力提供各种各样的援助,农民无法更加有效地经营土地。
卜恺将中国农村发展的问题归结于“技术短缺”。
马若孟也赞成卜凯的观点,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土地问题,中国鲜有大地主,是小自耕农的天下,如果没有天灾人祸的影响,土地问题不会变得更加尖锐,“土地问题和农民的苦难只是在发生严重的天灾人祸干扰时才变得尖锐起来”,他认为农村最关键问题就是“缺少促使农业技术迅速进步的制度”。
马若孟将中国农村的问题归结于缺少能够提供新技术的制度,可以说他既是“技术派”,也是“制度派”。
秦晖先生也持此类观点,认为关中地区土地占有极为分散,“无地主”、“无租佃”,是一个自耕农的世界。
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的确存在土地不均问题,但最大的问题不是土地分配问题,而是农业技术与农民组织问题。
费正清与费维恺也有类似的观点,晚清中华帝国“大地产的罕见、小块的家庭农田以及典型的土地小型化,都是传统继承习惯造成的部分结果。
”这些学者认为,传统中国根本不存在土地问题,土地占有也并非严重不均,甚至认为传统中国根本不存在大地产、大地主。
学者们否认传统中国是一个地主制经济社会,地主制经济不是传统中国的经济基础。
土地占有与乡村政治没有必然的关系。
许多学者认为,传统中国不仅不存在大地主、大地产,而且农民占有土地的数量与其在村庄的地位和权力也没有必然的关系。
张仲礼认为,绅士管理乡村的职责与其私人土地的占有及所在地点无关。
绅士对土地的占有,是他们在社会上拥有权力的结果,而不是先决条件。
弗兰兹?
迈克尔在为张仲礼的《中国绅士研究》作序时说,绅士对中国社会的管理,包括经济方面的管理,并不是依赖于其对土地的占有。
他认为,中国绅士在职责上也并不像英国乡绅那样与土地联系在一起,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绅士并不是“地主绅士”。
在弗兰兹?
迈克尔为张著再版作序时,仍然强调这一观点,“中国绅士的地位不是来自地产,而是出自对教育的垄断。
由功名作为凭证的教育使绅士有资格向国家和社会提供重要的服务”。
黄宗智先生则从自耕农的角度说明了村庄内向性治理的形成,华北地区的农村商品化程度低、自耕农比重大,村庄与外部交往少,所以国家政权对村庄的影响大,国家通过税赋渗透进村庄,而村庄阶级没有分化,没有显赫的人物和组织抵抗国家政权,因此加剧了村庄的内向性。
李怀印则从生态环境角度说明了优越的生态环境、集体利益是形成乡村自治的原因,土地因素与村庄结构并没有明显的关系,士绅的治理主要依靠声望。
士绅的权力和权威来源于社会身份和地位。
按照张仲礼与弗兰兹?
迈克尔的观点,传统士绅对乡村的支配或者影响不是因为他们占有土地,而是因为他们拥有社会权利,对绅士而言是对教育的垄断和身份资格,尔后才获得土地。
对于宗族头人而言,因为是宗族头人,尔后才有拥有土地。
也就是说,士绅和宗族头人对村庄的支配和权力的拥有是社会因素,不是经济因素,更不可能是土地因素。
土地占有并不是士绅和宗族头人拥有村庄权力的原因,而是拥有权力的结果。
瞿同祖也持类似的观点,“尽管大多数士绅成员确实拥有财产,特别是土地,但人们却忽视了一点,即许多士绅像《儒林外史》所述,是在取得士绅身份后才获得土地的。
”“中国士绅的特权地位并不纯粹取决于经济基础。
士绅的成员身份,并不像有些学者推测的那样来自财富或土地拥有。
”瞿同祖的观点是,士绅先有身份,然后再获得土地,土地与士绅身份有一定的关系,但土地与士绅拥有村庄权力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因果关系。
李怀印则认为士绅治理村庄是根据声望,但是其声望究竟如何来则没有做具体的分析。
“无关论”者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土地不是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技术、制度和工业才是关键;中国是一个以自耕农为主的社会,大地主、大地产并不占主导;农民拥有土地数量与村庄政治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素关系;士绅依靠身份和功名等社会因素治理村庄。
第二种观点:
土地与乡村政治相关
土地与乡村政治相关关系,又可以分为三类:
土地与乡村政治相关论、部分因果论、直接因果论。
土地是传统中国最重要的问题。
这一观点认为,传统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是土地分配不均的问题,土地分配问题构成了中国农村政治和革命的根源。
李景汉在河北定县调查时说,“中国农村经济的难点在于土地短缺”。
陈翰笙通过调查得出结论:
农村诸问题的中心“集中在土地之占有与利用”,“土地所有与土地使用间的矛盾,正是现代中国土地问题的核心”陈翰笙认为土地分配问题是中国的核心问题,同时他引用意大利学者托尼的话,证明土地与社会、政治之间的紧密关系:
每当权利失去均等,土地转移到少数人手中的时候,社会与政治,必起绝大的变异。
陈翰笙只是说明了土地是中国的核心问题,土地不均会带来重大的政治和社会效应,但是他没有明确说明土地占有与村庄权力的关系。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李景汉、陈翰笙这一学派被称为土地“分配派”,即通过解决土地的分配问题而拯救中国。
土地与乡村政治:
相关论。
这一观点认为,土地重要但并非最重要的问题。
费孝通先生指出: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土是乡下人的命根子”,“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
费孝通认为,“农业和牧业不同,它是直接取于土地的。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
常态的生活是终老还乡”。
费孝通先生上述论述表明了土地对农民的重要性,农民离不开土地,不能没有土地。
费先生并也没有直接论述土地占有与政治和村庄权力之间的关系,只是在《乡土重建》中表明了土地占有与政治的相关性,他认为分配是从所有权上说的,中国土地分配不平均是事实。
分配问题远没有技术及组织更为重要。
分配问题在民生上有极严重的影响。
费孝通先生的观点也代表了20世纪30年代“技术派”观点,包括当时的美国学者卜凯等都持此类观点,他们认为通过农村技术革新可以为中国的现代化找到一条道路。
土地与乡村政治:
部分因果论。
土地与政治之间有关联,土地占有的数量会影响农民对政治的态度和盟友的选择。
亨廷顿在论述土地政治时说:
没有哪一个社会集团会比拥有土地的农民更加保守,也没有哪一个社会集团会比田地甚少或者交纳过高地租的农民更为革命。
亨廷顿因此得出一个结论,农村的作用是一个变数:
它不是稳定的根源,就是革命的根源。
亨廷顿只是表明了土地与政治有关系,但土地与村庄之间的关系如何成为政治的变数,则没有明确提出。
费正清在分析中国社会的本质时说,“在农民大众眼里,士绅还包括大地主,这是统治阶级的经济基础”。
“士绅家族之所以能不断主宰农民,不仅依靠其拥有土地,而且由于这样一个事实:
士绅中间主要产生出将来可以被选拔为官吏的土地士大夫阶级”。
“士绅家族的最好保障并不只是靠田地,而是靠田地与官府特权的结合”,士绅能够凌驾于农民经济之上主要依赖于置田产和当官。
费正清认为决定村庄权力的不仅是土地,还有当官,土地是士绅及其家族主宰农民的重要工具,土地占有与政治之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但是土地占有与村庄权力只有一定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土地并不完全是村庄权力的来源,还有其他因素影响着村庄权力。
土地与乡村政治:
直接因果关系。
这一观点认为,土地占有数量决定着村庄的地位和拥有的权力。
黄宗智先生主张,“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相互交迭”,他引用西德尼?
甘布尔的研究证实自己的观点:
在众多村庄中,财产是获得村中长老身份的一项资格。
有时不限定数量,由最富裕的村户的家长充任。
有时则规定要有一定数额的土地才可担任长老……穷人绝对不会被任命,部分原因是土地太少。
黄宗智得出一个结论:
村庄政治领导权的延续和变化,反映了社会经济地位特别是土地数量的持续和流动。
黄宗智先生明确地提出了土地与村庄权力之间的因果关系,土地占有数量与权力大小、土地占有的时间长短与权力持久之间的关系,土地决定村庄权力,土地占有数量决定权力的大小。
黄宗智先生用个案比较明确地说明了土地占有与村庄权力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而且说明了土地占有是村庄政治的经济基础。
“分配派”是从农民角度来研究土地占有与变动对中国政治的影响,相关派、部分因果派及直接因果派都是从士绅占有土地角度探讨土地与乡村政治的关系。
虽然研究的对象和视角不同,但是他们得出的结论有一个共同点:
土地与乡村政治有关系,至于这种关系是相关,还是部分因果或者直接因果则有一定的差异。
第一种观点否定土地与乡村政治有关系,第二种观点主张土地与乡村政治之间有一定的关系,土地占有数量决定村庄权力的大小,士绅能够不断地主宰农民、治理村庄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拥有土地。
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小农的土地是封建经济的基础,小块土地是政府的物质条件,小块土地是官僚立足的基础,小农与国家和村庄的关系都是通过土地而形成。
同理也可以说,小块土地是乡村士绅治理村庄的基础,即小农的小块土地构成了村庄权力的“经济基础”,构成了传统村庄治理的基础,小块土地是村庄治理的“物质条件”,还是村庄得以施展权力的“生活来源”。
笔者认为,农民的小块土地对村庄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政治传统都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两者之间有着因果或者相关关系,小块土地构成了乡村政治的经济基础。
二、两种分析视角
在确定土地与乡村政治具有相关关系后,我们就要具体探讨土地与乡村政治之间影响机制或者连接机制。
对于土地与乡村政治之间的互动影响机制,学界一般有两个视角或者两个传统,一个是从宏观的角度、整体的角度分析土地占有与乡村政治之间的关系;另一个是从微观的视角分析土地占有与乡村政治之间的关系。
第一种视角:
宏观分析
宏观分析视角是指从宏观层面、理论层面分析小块土地与政治或者乡村政治之间的关系的研究,马克思、沃尔夫、费正清等是主要代表。
马克思曾经从三个方面对此问题进行分析:
第一,小块土地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生产关系。
小块土地的生产属于生产方式范畴,小块土地的生产方式决定村庄的生产关系:
农民与土地、农民与农民、农民与地主之间关系。
“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
“在所有以自然分工为基础的社会里,产品支配着生产因而在某种程度上,生产资料至少在某些场合也支配着生产者:
在中世纪,土地支配着农民,农民只是土地的附属物。
”在马克思看来,小块土地的所有制形式、生产形式决定着小农、地主的社会地位和他们在村庄中的作用,同时小块土地影响着农民和地主,它成为农民的主宰,成为了地主的工具。
第二,小块土地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设,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
小块土地所有制“是使法国封建农民成为小块土地的所有主,而使拿破仑成为皇帝的物质条件”。
小块土地的生产方式变成了法国皇帝的物质条件,生产方式决定上层建筑。
小块土地“是行政权力整个机构的生活源泉。
强有力的政府和繁重的赋税是同一概念。
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本性说来是全能的和无数官僚立足的基地”。
小块土地不仅是皇帝的物质基础,还是政府和官僚的立足基础,生产方式是政府和官僚的基础。
农民“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静静地看着整个帝国的崩溃、各种难形容的残暴行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杀,就像观看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衷”。
“随着小块土地所有制日益加剧的解体,建立在它上面的国家建筑物将倒塌下去”。
虽然小块土地所有制是皇帝和政府的基础,但是有时农民只关注自己的小块土地,并不太关注政治,小块土地所有制的解体,以它为基础的上层建筑也必将随之倒塌。
小块土地的经济基础不仅支撑上层建筑,而且也决定上层建筑的兴衰、消长。
第三,小块土地与宏观政治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曾指出:
“自耕农的这种自由小块土地所有制形式,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正常形式,一方面,在古典古代的极盛时期,形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在现代各国,我们又发现它是封建土地所有制解体所产生的各种形式之一”也就是说马克思坚持自耕农的小块土地是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又是封建制度解体后的一种形式。
他认为,“小块土地所有制的经济发展根本改变了农民对社会其他阶级的关系”,“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
”前一句话说明了小土地所有制经济决定农民与其他阶级的关系,即小土地所有制决定乡村的生产关系。
后一句话说明,小土地所有者或者传统小农总是被行政权力所支配,变成了行政权力的俘虏。
另外,马克思在论述俄罗斯、印度、中国的小农时,明确提出小农是东方政治制度的经济基础。
“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
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首创精神。
……他们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
”同时,马克思也认为小农是东方政治制度的自然基础。
他认为,俄罗斯的小块土地的公社“就是东方专制制度的自然基础”。
马克思研究要么很微观,要么很宏观,从微观层面来看,马克思只是说明了小块土地在村庄的社会影响,并没从社会影响上升到村庄政治。
也就是说,马克思只是从小块土地的生产力上升到生产关系(小农的社会影响和地位),但是没有将生产关系展开到村庄政治层面,即马克思并没有将小块土地与村庄政治之间的关系理出来,显然既使是微观入手,其实目标仍然是宏观的。
从宏观层面来看,因为农民只有小块土地而且与外地隔膜,小农只将注意力放在仅有的土地上,只会听任其他阶级和权力的调摆。
这个特征构成了东方专制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和自然基础。
马克思的理论关怀是小块土地的小农与国家的关系、与政权的关系,他并没有直接涉及到小块土地的小农与村庄权力的关系。
对于前者,马克思非常明确的提出了小块土地的小农与政治、政权有着紧密的因果关系,前者决定后者,后者与前者表现为一种“支配关系”,即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或者经营者变成了行政权力的支配对象。
中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土地占有与村庄权力的关系分析得比较多,他们坚持“租佃关系决定论”,这一理论将传统农村视为由土地租佃关系决定的地主—佃农两极社会。
土地集中、主佃对立被视为农村一切社会关系乃至农村社会与国家之关系的基础,……“土地兼并——农民战争”的叙述模式被用来解释历史上的各种政治事件。
秦晖先生这段话只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有关土地与政治关系的描述,其实中国官方正统的解释就是地主—佃农两极对立导致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切问题。
其实这种分析也只是将地主与佃农作为一个微观基础,但是其论证逻辑的跳跃性比较大,佃农与地主之间的对立与矛盾一下子上升到阶级对立,从而引发斗争、造反和动乱,即从主佃对立这个微观基础跳跃到宏观政治。
这种观点也只是说明土地占有与国家政治有关系,但是并不能说明主佃对立与村庄治理的关系,更没有讨论主佃对立对村庄治理的影响机制。
费正清在《美国和中国》中曾经说到:
“中国家庭是自成一体的小天地,是个微型的邦国。
社会单位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家庭才是当地政治生活中负责的成分。
”费正清认为小农家庭构成了当地政治生活的基本单位,即小农家庭既是社会单位,也是政治单位。
李根蟠也间接谈到小块土地的小农与政治的关系:
“规模狭小、极度分散的状态,铸就了小农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弱势地位,许多问题即由此而生。
中国传统社会最大的群体,何以长期处于经济上和政治上受剥削受欺圧的弱势地位?
根本原因就是小农经济的细小、分散和缺乏组织性。
”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小块土地与村庄权力之间的关系,其他学者也做过探讨。
毛泽东也提出了与马克思类似的观点:
农民那“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
”不管是马克思、毛泽东,还是费正清、李根蟠都没有将小块土地与村庄权力的关系说清,即小块土地如何影响村庄权力,其机制是什么?
小块土地的生产方式如何决定村庄权力关系。
第二种视角,微观分析
微观分析主要是从村庄层面探讨小块土地与村庄权力之间的关系,人类学家沃尔夫曾经对此做过分析,“乡民的政治经济将社会关系和统治的网络连结于土地——乡民的福利和家庭地位的决定因素。
乡民的土地代表人际关系的地图,而非西方观点中不带私情的地块。
这个社会关系的网络是以社会控制的阶层制度加以组织。
”人类学家谢林还总结到,“土地总是独具声望和影响力,不能以纯粹的经济观点解释。
土地就是权力,而权力就是土地和地主所拥有的地位。
”沃尔夫、谢林对乡小块土地与乡村政治的关系论述是从微观角度的分析,但是他们在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时并不比宏观分析学者更加明晰、更加具体。
黄宗智先生是将小块土地与村庄权力之间的关系论述完整的第一人。
黄宗智先生从实证的角度,利用日本满铁的调查资料,通过对冷水沟、沙井、侯家营三个村庄的数据,证明了凡是村庄的首事都是有土地的农户,没有土地的农民几乎没有当首事的,而且当了首事后土地基本没有增加,相反还有一定比例的首事卸任后,土地有所减少。
他用调查数据证伪了张仲礼、瞿同祖等人的观点——先有身份后有土地,土地并不影响村庄政治。
同时他也用河北、山东6村的数据证实了宗族头人能够主导支配村庄,也与土地分不开的。
同时他利用这些数据证明了自耕农不仅是村庄治理的基础,而且本身就是治理的中坚。
黄宗智先生的逻辑是:
小块土地——农民分散——与外界隔绝——国家通过赋税影响村庄——没有显赫人物——国家在农民心中有较高的地位——但是国家财力不足——赋税通过士绅和头人征收或者代垫——从而士绅与头人成为村庄权力的核心——也成为沟通国家与农民之间的桥梁。
由于自然村的闭塞性和内向集聚性,从而形成了士绅、地主和宗族头人主导、自耕农参与和支持的村庄政治权力结构。
黄宗智还引用萧公权文中的一句话说明了村庄权力的形成机制:
当时中国村庄的头头,多是该村公认的自生的领袖,一般来自村中最有势力的家庭。
“公认”是自耕农的公认,“自生的领袖”说明不是政权委派的,也不是竞争产生的,而是本身就具有影响力的人自然而然形成,或者小农拥护而形成。
小块土地与村庄治理之间的关系很少有直接的因果论证,要么如马克思从宏观层面、一般层面论述,要么为证论村庄与国家关系而间接涉及到小块土地与村庄治理之间的关系。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研究格局呢?
原因有两个方面:
一是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都以村庄为研究单位,经济学以农民、农户为研究单位,但是不考察政治问题,因此小块土地与村庄治理之间的关系不在考察之列;二是学者们大多论述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联性,解释小农受到外部冲击的集体行动——革命、运动、造反、起义等现象,很少有人关注小块土地与村庄治理之间的微观机制。
这就导致了小块土地的生产方式与村庄治理之间关系研究的裹足不前,即使有学者意识到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只会借用马克思的观点或者不加实证的联想:
小农与传统村治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并没有具体的经验材料和逻辑实证。
三、小块土地与乡村治理的基础
小块土地对乡村治理的影响有两个方面:
一是小块土地直接对乡村治理的影响,这是直接影响;二是小块土地对乡村社会的影响,从而乡村社会再影响乡村治理,这是间接影响。
(一)小块土地的社会效应
小块土地不仅仅对经济层面的影响,对乡村社会特别小农的心理、小农动机、小农行为都产生深远而重要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五种性格”。
内向性,小农只有一块能够养家糊口的土地,土地是家庭生存的基础,也是就业的载体,为了生存小农必须将所有的精力都花在小块土地上,甚至不惜“内卷化”。
刘创楚、杨庆堃,“乡土束缚,就是指种田的人,被土地所束缚,一切农村社会,均有此限制。
……乡土地束缚从何而来呢?
很简单,在土地耕作的人,衣食等直接依赖土地。
土地是直接维持生命的工具。
因此人们就不能离开土地。
这是农村社会的第一个特征。
”为了就业,小农必须与土地绑在一起,同样土地与小农的家庭绑在一起,小农只将眼光盯在土地上,盯在土地上面的庄稼。
对村庄的其他事务、对国家都比较冷漠。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小农可以看着帝国倒塌,可以看着皇帝被赶下台。
中国有句俗话能够说明小农对社会和政治的冷漠:
各人自扫门前雪,那管他人瓦上霜。
关注土地使小农眼光向内,只关注自己家里的事情,不关注社会和国家的事情,形成了内向性、内聚性的性格,所以小农的这种特点使乡村社会很难组织,很难实现跨区域的合作。
保守性,小块土地使小农时刻面临着生存安全和社会风险,小农经营小块土地时,不是考虑能够获取最大化利润,也不是考虑获取长期利润,首先考虑的是家庭生存,小块土地提供的不是最大化利润而是最大化产量。
因为要保证生存安全,小农不敢冒险,不敢创新,守旧是小农的最大特点。
小块土地使小农应对风险的能力比较低,小农经不起折腾,因此小农最相信的是自己的经验,根据传统经验来经营。
小块土地的小农以经验来经营小块土地,长期对经验的依赖,加剧了其保守的性格,害怕外来新生事务。
马克思“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
”费孝通说过:
“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地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
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先的经验。
”
依附性。
不管是佃农,还是中农都对支配、影响其生产的士绅与地主有依附性。
马克思认为,“如果说小土地所有制创造出了一个未开化的阶级,它半处于社会之外,并且兼有原始社会形态的一切粗野性以及文明国家的一切痛苦和穷困”虽然小农经营小块土地没有问题,也不需要求助社会和市场。
但是小农的小块土地也决定了小农的能力,许多问题无法依靠自己解决,如水利灌溉问题,小农自己不能解决,需要依靠村庄或宗族;小农的资金融通,也只能依靠村庄的富裕农户或者宗族。
在国家缺位的情况下,小农只能依靠村庄或者宗族提供生产方面的服务,小农需要村庄或宗族为其提供必要的安全庇护,因此这就使小农对宗族、村庄形成了一定依赖性,从而降低其自主性。
另外,小农生产就像大海中的小船一样,有随时覆灭的危险,其危险来临时又加剧了对士绅和地主支配村庄和宗族头人控制宗族的依赖性。
不流动性。
“自给自足的乡土社会的人口是不需要流动的,家族这个社群包含着地域的涵义”小农将精力放在小块土地上,没有时间、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外出务工经商,而且小农回避风险,尽量避免与市场打交道,而且只有极少部分的产品在市场销售。
前者使小农不能走出村庄,后者使小农不愿意与市场打交道。
更为重要的是小农相信经验、守旧的心态使其自锁在村庄,自闭于社会。
小农自锁和自闭的心理和行为使小农交往范围较小,交往能力差。
所以传统小农的小块土地决定了小农的流动性低,小农的社会化程度低。
胆小怕事。
小块土地及其生产方式也改变和影响着小农的社会心理。
一是胆小,小块土地使小农的经济社会地位比较低,而且小块土地决定了小农的收入很低,能够支配的资源比较小,所以小农做事交往的胆子比较小,中国农村有句俗话,“口袋无钱胆子小”。
二是不惹事,小农一般不会主动惹事,一则没有能力惹事,二则没有必要惹事,三则没有机会惹事。
三是怕事,小农不仅不惹事,而且怕事,见到事情都要躲,中国农村也有句俗话,“树叶落下来打破脑壳”,农民最怕惹事上身,最怕麻烦。
这种性格决定了农民不会主动参与社会,主动参与村庄政治。
农民的不参与、怕麻烦又为士绅地主治理村庄、主导村庄提供了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