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海龙解构动产公示公信原则Word文件下载.docx
《纪海龙解构动产公示公信原则Word文件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纪海龙解构动产公示公信原则Word文件下载.docx(1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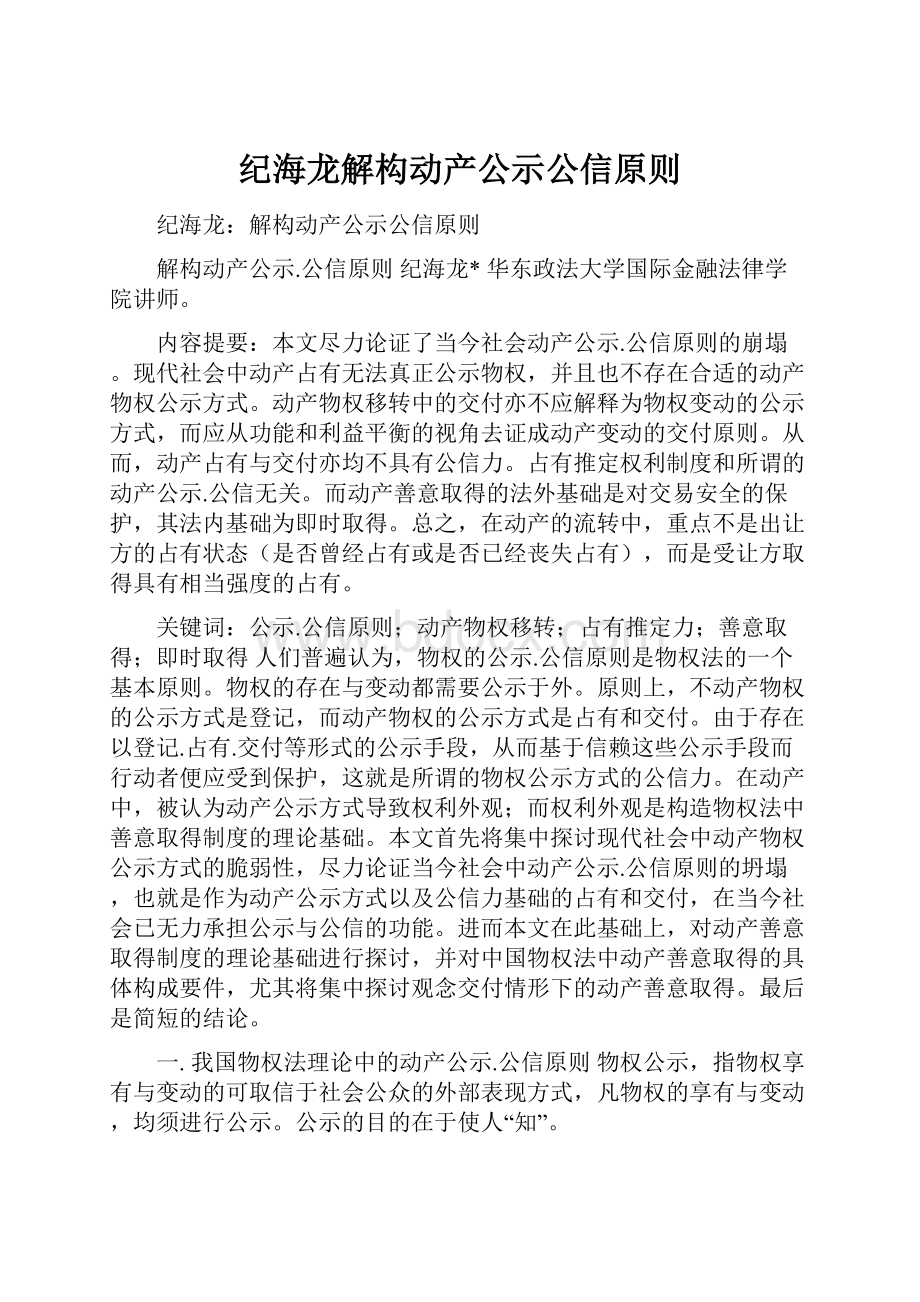
一.我国物权法理论中的动产公示.公信原则物权公示,指物权享有与变动的可取信于社会公众的外部表现方式,凡物权的享有与变动,均须进行公示。
公示的目的在于使人“知”。
[[]梁慧星.陈华彬:
《物权法》,法律出版社xx年版,第85页;
王利明:
《物权法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xx年版,第172页。
]从而所谓公示,指的是公之于众,以示众人的意思。
所谓公信原则,按照通常的理解,指物权的存在以登记或占有作为其表征,则信赖该表征而有所作为者,即使其表征与实质的权利不符,对于信赖该表征的人也无影响。
公信原则,其目的在于使人“信”。
[[]前引[1]梁慧星.陈华彬书,第96页。
]承认物权公示.公信原则的一个重要理由为,作为绝对权和具有排他效力的物权,不仅牵涉直接当事人,也潜在地对所有民事主体发生影响,因此对于物权,法律必须规定一定的公示方式。
[[]前引[1]梁慧星.陈华彬书,第85-86页。
]根据物权公示到底指向何种对象,学者对物权公示的对象进行了概括,区分了几种说法:
一.公示指向权利的存在;
二.公示指向权利的变动;
三.公示指向权利的享有与变动;
四.公示指向物权的享有.变动与消灭;
五.公示指向的是物权的享有与消灭。
[[]江平.李永军主编:
《物权法》,法律出版社xx年版,第75-76页。
]由于权利消灭可以被理解为广义的权利变动范畴,总结上述几种说法,物权的公示要么指向权利存在,要么指向权利变动。
在动产中,学者普遍认为占有这种公示方式指向权利存在,而交付这种公示方式指向权利的变动。
[[]叶金强先生将指向权利存在的公示称作“物权的表征方式”,而将指向权利变动的公示称作“物权变动的公示”。
参见叶金强:
《公信力的法律构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第16页;
叶金强:
《物权法第106条解释论之基础》,《法学研究》xx年第6期,第56页。
]这里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公示究竟针对何人?
传统说法认为,公示针对的是不特定公众。
传统观点从物权的绝对权属性出发来论证公示原则,即认为作为绝对权的物权之享有和变动涉及社会不特定的人,所以其享有和变动需要公示。
下文将首先对占有和交付是否能够承担起针对不特定公众的公示功能进行分析。
不过究而言之,尽管物权是针对不特定世人的绝对权,但只有在与物发生法律上关系的人,才可能受到物权公示及公信力的影响。
从而,公示方式所针对的人,具有法律意义的主要是可能与物发生具有法律上联系的人。
而与物发生或可能发生法律上联系的人,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在物的流转中的交易对手,如物权移转的受让人.设定质权中的质权人;
另一类是因物的保护而发生争议的人,如主张物权请求权(如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之人,因所有权被侵犯而主张侵权责任之人。
第一类物的流转情形,依照处分人是有权处分还是无权处分,又可进一步划分为自有权处分人处受让物权与自无权处分人处受让物权。
具体牵涉到公示原则,自有权处分人处受让物权涉及物的变动公示,在动产中即为交付原则;
自无权处分人处受让物权涉及公信原则,在动产中为占有的权利外观及与之联系的动产善意取得制度;
在第二类因物的保护而发生争议之时,涉及占有的权利推定效力。
从而,本文下文的结构如下:
首先论证占有无法作为针对不特定公众的物权享有公示方式(本文第二部分);
其次论证交付无法作为针对不特定公众的物权变动公示方式(本文第三部分);
紧接着讨论在有权处分动产物权变动的场合,交付原则并非起到公示功能,而是法律设置的平衡处分人和受让人利益关系的恰当手段(本文第四部分);
然后讨论占有的权利推定效力与占有的公示.公信无关(本文第五部分);
最后对动产的公信力(权利外观)进行探讨,探讨动产善意取得的法理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对物权法中善意取得相关规定的解释提出建议(本文第六部分)。
二.占有无法作为动产物权存在的“公示”方式物权的公示方式,必然是一个可以观察到的物理现象。
否则,所谓“公示”将为无根之木,无所凭据。
认为占有为动产物权存在的公示方式,所基于的理由是,主体对物的事实管领力(物理现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与主体享有物权重合。
但本文认为,对物的事实管领力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与本权重合的说法,在当今社会已不能成立;
另外,对物的事实管领力也并不必然意味着直接占有,亦即对物具有事实管领力的人,并不一定是占有人,从而该事实状态也不能表征该人享有物权。
首先,间接占有无法承担动产物权公示的功能。
当今社会中,动产所有权和占有状态之间经常性的分离,导致占有无法作为适格的所有权表征。
当今社会,租赁.融资租赁.保管.所有权保留等法律制度极大便利了物的利用,但也导致了占有与所有的分离。
虽然在占有与所有分离的情况下,所有权人一般享有间接占有[[]中国物权立法并没有规定间接占有。
理论上大多承认间接占有,参见庄家园:
《间接占有与占有改定下的所有权变动》,《中外法学》xx年第2期,注10。
],但间接占有实际上是通过法律上的占有媒介关系构成。
也就是,构成间接占有的是法律上的媒介关系,而非属于物理现象的事实控制。
而由于法律上的媒介关系并不表露于外,从而它也就无法承担公示物权.表征物权的作用。
其次,当今社会中,通过占有辅助人进行占有是直接占有的常态。
所谓占有辅助人的辅助占有,是指占有人对于物的占有,并非亲自为之,而是借助特定从属关系中受自己支配之人进行事实上的管领,例如,企业的雇员.家政服务中的保姆。
尽管他们为企业或雇主实际管领某物,但他们只是占有辅助人,而真正的直接占有人为企业或雇主。
在当今社会,鉴于绝大多数动产属于工商企业,所以实际上,社会中绝大多数的动产是由占有辅助人进行事实上管领,法律上的直接占有人实际是通过占有辅助关系而“直接”占有某物。
与间接占有中的占有媒介关系同理,法律上的占有辅助关系也并不具有物理上的可观察性。
从而外在物理表象无法显示出谁是法律上真正的占有人,便更谈不上直接占有的权利表征作用了。
德国学者鲍尔和施蒂尔纳即认为,在占有辅助关系欠缺外部可认识性时,此有害于交易,且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公示思想。
[[]
[德]鲍尔/施蒂尔纳,《德国物权法》上册,张双根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七章边码67。
]另外,直接占有本身也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从而在某些场合无法对外显露到底谁是直接占有人。
直接占有要求占有人与被占有物具有物理上的管控关系。
但此物理上的管控关系,常常无法显露于外。
现代社会所谓的直接占有,多为将动产存放于某个闭锁空间中,而占有人掌握进入这个闭锁空间的渠道,例如钥匙。
在房屋租赁的情形,如果出租人公开地保留一份进入租赁房屋的钥匙,则德国主流观点认为,此时除了承租人外,出租人也对房屋及屋内动产具有直接占有。
[[]BGHNJW1979,715,转引自JensThomasFü
ller,Eigentä
ndigesSachenrecht?
xx,S.278.]但如果出租人偷偷地保留一份进入租赁房屋的钥匙,对此则观点不一。
可见,同样是拥有钥匙进入空间(对于公众而言相同的物理现象),出租人公开亦或秘密保留一份钥匙,可能会影响对出租人是否为直接占有人的认定。
从而事实上的管领力(公开的物理现象)并不等同于直接占有。
对于是否是直接占有,在特定场合还需要(不具有公开性的)法律上的评价。
另外一个例子是银行保险箱服务。
于此场合,德国主流观点认为拥有保险箱钥匙的人(银行客户)对保险箱内物品具有唯一的直接占有。
[[]Palandt/Bassenge,68.Aufl.,
xx,§
866,Rn.2;
Mü
nchKomm/Joost,
4.Aufl.,2004,§
866,Rn.4;
鲍尔/施蒂尔纳,《德国物权法》下册,申卫星.王洪亮译,法律出版社xx年版,第55章边码17。
]但不可否认,在此场合客户对保险箱并不具有直接的事实上的管领力,因为未经银行同意,客户无法获得保险箱中之物。
[[]参见前引[8]Fü
ller书,S.279.]这个例子也说明了直接占有与事实上的管领力并不完全相同。
具有事实上的管领力,不见得具有直接占有,也就更加不能从事实的管领力中“公示”出物的所有权了。
基于上述理由,尤其是基于在当今社会中占有与本权经常分离的现象,当前德国有相当部分民法学者认为占有无法作为物权存在的公示手段。
[[]参见JohannKindl,Gutglä
ubigerMobillarerwerbundErlangungmittelbarenBesitzes,AcP201(2001),S.392-393;
BerndRebe,ZurAusgleichsfunktionvon§
935BGBzwischenVertrauenschutzundEigentü
merinteressenbeimgutglä
ubigenMobiliarerwerb,AcP,173(1973),S.194-195;
WolfgangBrehm,Rezesionzu„Eigenstä
“vonJensThomasFü
ller,AcP207(xx),S.273.详细的论述见前引[8]Fü
ller书,S.272-296;
Westermann/Gursky/Eickmann,Sachenrecht,
8.Aufl.,
45Rn.
6.]一种观点认为,不能基于动产所有和占有状态经常分离这个经验事实,来否认占有可以作为动产权利表征方式。
这种观点的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物权表征方式的确立,逻辑上必然以表征方式标示的物权信息有发生错误之可能为前提。
如果绝对不会出错,则无需法律确定表征方式。
其次,确立物权表征方式乃旨在打造法定的物权信息传递渠道,节省物权信息成本,经验事实并非决定性因素。
在必须确立表征方式的前提下,对于动产也没有比占有更好的选择。
[[]前引[5]叶金强文,第58页。
]该观点初看很有道理,但尚经不起如下的仔细推敲:
首先,占有和所有可能不一致,自然是确立动产权利表征方式的前提,但也只是一个前提。
亦即在逻辑上,占有与所有可能不一致只是应该确立动产权利表征方式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占有与所有可能不一致这个前提,引申出的逻辑结果至少有如下几种:
1)从应然角度讲需要确立动产权利表征方式,并且在实然层面上也存在合适的权利表征方式;
或者2)从应然角度讲需要确定动产权利表征方式,但实然层面上不存在合适的权利表征方式;
或者3)从应然层面讲不需要确立动产权利表征方式。
上述观点显然认为从应然角度讲需要确立动产权利表征方式,亦即不认可3);
并在此基础上进而承认在实然层面上也存在占有这种合适的权利表征方式,亦即认可1);
但并没有对占有的确是合适的权利表征方式进行有力的论证,也就是尚未排除2)。
而本文所持观点恰恰为2)。
就占有是否为合适的动产权利表征方式而言,上述观点认为,“在必须确立表征方式的前提下,对于动产不存在比占有更好的选择。
”这个说法类似于矮子群中找高个子,占有是个子最高的那个;
或者从手段-目的的角度讲,与其它众多待选择的手段相比,占有是最优的手段,因此上述观点确认占有作为权利表征方式。
但矮子群中个子最高的那个,不见得就足够高;
与其他待选手段相比最优的手段,也不见得就是的确能够实现目的的恰当手段。
进而言之,不存在比占有更好的选择,并不意味着占有就是恰当而合适的动产权利表征方式。
正如上文的论述显示,在占有与本权经常分离的当今社会,单纯占有已不足以表征动产权利。
尽管从理想和应然的角度讲,作为具有对世性和排他性的动产物权,最好存在相应的权利表征以公示于外。
但在对于动产无法构建登记制度的当今社会(并不排除未来社会可能实现这一点),在占有无法表征动产物权的当今社会(而在过去的静态社会占有或许可以表征动产物权),遗憾的是并不存在合适的动产物权表征方式。
三.交付无法作为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方式对于物权变动的公示,学者普遍认为,“交付是动产物权变动(动态)的公示方式”[[]前引[1]梁慧星.陈华彬书,第93页。
],并认为交付的形态,除了作为交付常态的现实交付外,亦包括观念交付,亦即简易交付.返还请求权让与与占有改定。
[[]前引[1]梁慧星.陈华彬书,第94-95页。
]德国学者亦认为,“为法律交往的安全起见,绝对权的移转应自外部可查知。
对此,在不动产处由土地登记簿承担此任务,而在动产处则由占有承担此任务,虽然占有承担此任务,但对此占有却些许力有不逮”[[]Schwab/Prü
tting,Sachenrecht,30.Aufl.,2002,Rn.37
1.类似论述亦参见Mü
nchKomm/Quack,
929,Rn.
3.]。
如果如学者普遍理解那样,对于公示原则在公之于众.使众人“知”的含义上进行理解,则对于动产交付是公示原则的表现,至少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进行质疑:
一是交付能够公示什么?
也即是交付能够承担起使动产变动公之于众的功能吗?
二是实际生活中的动产物权变动在多大程度上遵循号称具有公示性的变动方式,也就是,实际生活中的动产物权变动还是以交付为常态吗?
对于这两个问题,下文的回答是,交付本身无法将动产物权的变动公示于外;
且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现实中,对于动产物权的变动,交付原则都没有被彻底贯彻。
首先,若公众观察到某一动产自一主体交付于另一主体,则于交付这一物理现象中,公众可查知何事呢?
回答是,一般而言公众只能查知占有转移这一物理现象,而对于该物理现象背后所蕴含的法律效果,公众无从得知。
因为交付行为作为物理现象,在法律上为无色的,能引起何种法律效果,需要结合当事人的意思。
也就是,当事人交付某物,可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如租赁.转让.保管.出质.出资.信托等等,而物权移转只是一种可能的目的。
在所有权保留场合,即便动产已经交付,但所有权尚未转移。
而到底交付是出于何种意思,公众作为外人无法查知。
在这一点上,交付与不动产的登记完全不同。
交付并不付诸于公开性的文字记录,而登记则有文字向外表达登记的具体意思。
从而登记作为物权变动的公示方式,自无疑问;
而交付可否将物权的变动公示于外,则大有问题。
这种不同,也就可以解释为何在德国物权法中,登记被普遍认可具有“公信力(Ö
ffentlicheGlaube)”,而无人言及动产的交付具有“公信力”。
其次,公众观察到某一动产被交付于某人,即便是在物权变动的交付场合,也未必能够知道该动产物权转移给何人。
于买卖合同中,货交第一承运人即为交付完成,从而货物所有权即转移给买受人(合同法第141条第2款情形1结合第133条)。
但外部公众如何知悉该货物的所有权是转移给何人呢?
另外,在现实生活中,交付在绝大多数情形下通过占有辅助人完成,也就是,由出让人的占有辅助人将货物交付给受让人的占有辅助人,占有辅助关系是一种法律上的关系,并不具有公开性。
在认定占有辅助关系时,外部是否可以查知,在所不问。
[[]参见前引[1]梁慧星.陈华彬书,第394页;
王泽鉴:
《用益物权·
占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2页;
前引[7]鲍尔/施蒂尔纳书,第七章边码67。
]那么,在基于占有辅助人进行交付的情形,公众如何知悉动产所有权自何人转移给何人呢?
再次,在现代远程链条式动产交易中,亦即德国学理中所谓的指令取得(Geheisserweib)情形,交付亦不具有公示功能。
所谓指令取得,例如甲与乙签订买卖货物的合同,乙将同一批货物卖给丙,并指示甲直接将货物交付给丙。
在此情形下,丙并非直接从甲处取得所有权,应该认为乙先自甲获得所有权,而于法律的瞬间货物所有权转移于丙。
[[]参见前引[16]王泽鉴书,第261页;
前引[9]鲍尔/施蒂尔纳书,第51章边码17。
]乙虽然在法律的瞬间获得所有权,但乙对货物即未曾直接占有,也未曾间接占有,何谈占有移转(交付)的公示作用?
最后,如学者普遍承认的[[]Mü
929,Rn.3;
Wieling,Sachenrecht,
3.Aufl.,1997,§
1III3b);
前引[9]鲍尔/施蒂尔纳,第51章边码3。
崔建远教授援引日本我妻荣教授的著作,也认为占有作为动产物权的表征越来越不充分,并认为对于无法构想出如证券或账簿等其他公示方法的动产,不必执着于必须贯彻公示的原则,而仅止于透过公信原则来保护交易安全,参见崔建远:
《物权:
规范与学说以中国物权法的解释论为中心》,清华大学出版社xx年版,第173页。
],在动产所有权移转的情形,交付原则并未被彻底贯彻。
除了现实交付外,尚存在交付的替代,也就是简易交付(物权法第25条).返还请求权的让与(物权法第26条),占有改定(物权法第27条)。
而所谓交付的替代,并非交付。
在交付替代的场合,动产所有权的移转,根本不具有对外的移转占有行为,何谈外在的公示呢!
[[]对此德国法上详细的论证,参见前引[8]Fü
ller书,S.297-322.]由此可见,动产移转中,并未严格遵守公示原则。
首先是动产所有权的移转并不必然以交付为前提,而是存在大量交付替代的情形,而这些情形并无公示作用;
其次,现代工商业社会,占有辅助人的大量参与.商业动产流转中的指示取得,所有权保留.租赁的发达.专业仓储公司参与货物的存储等等,使交付的情形变得异常复杂,而这些情形的交付无法对外显示具体的法律变动过程,从而交付也无法承担动产移转的公示功能。
在现代的工商业社会中,占有和交付很难发挥将动产物权存在和动产物权变动“公之于众”的作用。
尽管彻底论证这一点,尚需要经验事实层面的实证研究,以确认当今现实生活中到底占有与所有分离的程度多大,以确认动产移转占有多大可能是出于动产物权的移转,但不可否认上文的论述已经展示出,占有并不意味着所有.交付并不意味着物权移转。
从而可以说,所谓占有.交付的动产物权公示功能,已然崩塌。
值得一提的是,《欧洲共同框架草案》(DCFR)的作者在设计该草案关于动产所有权的取得与丧失的第八编时,基于现代社会占有和所有大量分离的情形,明确强调DCFR并不重视动产交付的公示作用。
[[]参见ChristianvonBarandEricCliveed.,Principles,DefinitionsandModelRulesofEuropeanPrivateLaw,DraftmonFrameworkReference,FullEdition,Volume5,pp.4044-4045.这里,对于占有表征权利存在,交付表征权利变动,DCFR的作者们并没有非常明确地区分,而是以占有和所有经常分离的社会事实,来论证传统意义上的“公示”理念对于DCFR选择物权变动的交付原则,并未起到重要作用。
也就是,从占有这种静态公示手段的不适格,直接跳跃到交付作为物权变动公示手段的不适格。
尽管这里DCFR作者从静态公示手段的不适格直接跳跃到变动公示手段的不适格,似乎存在着逻辑上的断裂。
但本文作者认为,这种逻辑上的断裂并不存在,因为交付本为原占有人放弃占有,新占有人取得占有。
从而,占有与所有经常性的分离,占有作为享有物权之表征的不适格,也就意味着交付作为物权变动之表征的不适格。
]该草案虽然也规定动产所有权的移转原则上要求交付,但此规定的论证并非基于交付的对外公示作用,而是基于利益衡量的功能进路,对此详见下文。
四.对动产所有权移转交付原则的证成。
如果交付无法发挥将动产移转公之于众的功能,那么法律选择交付作为动产移转的要件之一(物权法第6条后句.第23条),是否具有正当性呢?
对于交付原则上作为动产移转的要件,如何进行理论上的证成呢?
中国学者在解释物权法第6条和第23条时,多认可该条以公示原则为基础,体现了立法者对物权公示原则的确认。
这在不动产登记中毫无疑问,因为登记用文字来体现具体权利状态和权利变动。
而在占有和交付无法作为动产物权公示(“公之于众”)手段的今天,需要对物权变动坚持交付原则进行重新论证。
[[]即便物权法立法者当时以“公示”为根据,在物权立法中规定了交付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立法者在立法之时对所立之法的教义学阐释具有约束力。
对法律进行教义学的阐释,是所有理性面对法律之人(所有以学术的视角审视法律之人)的任务。
而在此种阐释中胜出者,凭借的只应是论理的说服力。
在进行教义学阐释时,立法者的观点亦可能错误或过时。
从而,学者的任务并非对立法者的教义学阐释亦步亦趋,而是在遵从立法者所确立之规则的基础上,对此规则进行更合理的理性阐释。
在必要时,自然也可以脱离立法者的教义学阐释,而以更具有说服力的阐释取而代之。
类似观点见DieterReuter,Rechtsfä
higkeitundRechtspersö
nlichkeit,AcP207(xx),S.674.]如上文所述,DCFR不强调占有和交付的公示功能,却依然选择了交付作为动产所有权变动的原则。
也就是,DCFR不认可动产上的公示(publicity)原则,但认可动产所有权变动的交付(delivery)原则。
[[]德语中区分公示原则和交付原则。
前者被称之为Publizitä
tsprinzip,后者被称为Traditionsprinzip。
两者并不完全相同,学者一般认为,公示功能只是交付原则的功能之一,参见MichaelMartinek,TraditionsprinzipundGeheiß
erwerb,AcP(188)
1988,S.576.]DCFR在动产物权变动的模式上,选择了交付作为动产物权变动的原则,并规定了交付原则的例外。
[[]DCFRVIII.–2:
101
(1)规定:
“本章中货物所有权的移转要求:
……(e)存在针对所有权移转之时点的合意以及该合意实现的条件的约定,或者在不存在此种约定时,存在交付或存在交付的等同。
”]DCFR中交付原则的例外有:
1)单纯合意:
在当事人约定的情况下,允许通过单纯合意让与动产,如大陆法占有改定和所有权保留的情形[[]DCFRVIII.–2:
101
(1)
(e)
第一种情形。
DCFRVIII.–2:
103对以当事人合意方式决定动产物权转让时点进行了规定。
按照对该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