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陆哲学异同的几个方面Word文件下载.docx
《朱陆哲学异同的几个方面Word文件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朱陆哲学异同的几个方面Word文件下载.docx(1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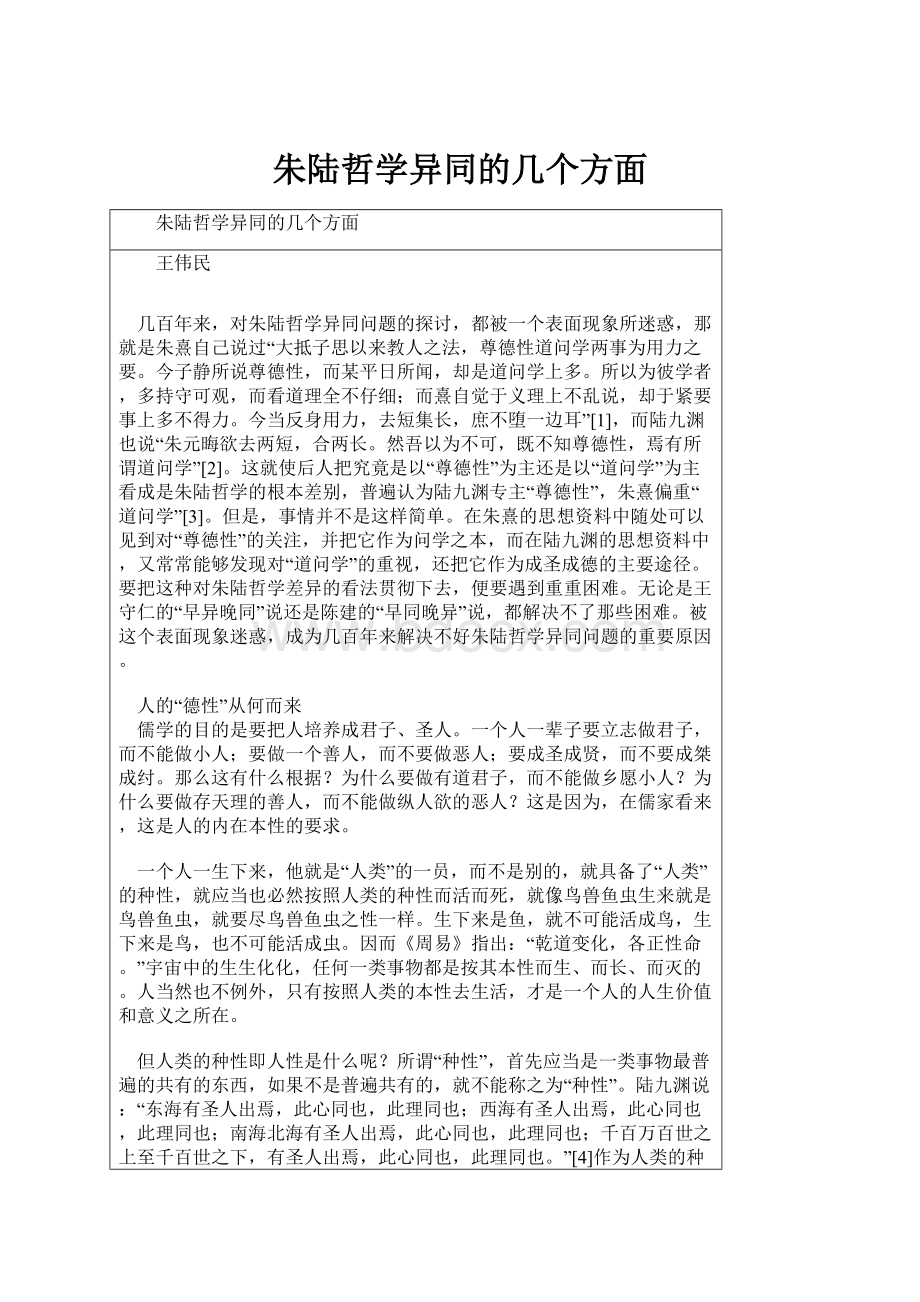
“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
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
南海北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
千百万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
”[4]作为人类的种性,就应当是人类所共有的东西,是不分地域、不分国家和民族、不分是古是今,都普遍共有的性情。
但仅仅是“普遍共有”还不够,还应当是这一类事物所特有的。
如:
饥而欲饱,寒而欲暖,趋利辟害、两性相悦等,它们是人类普遍共有的,但并非人类所特有的,动物甚至某些植物也都有这些性情。
它们就不能是人类的种性,而只是人的动物性,就应当从人性概念中剔除。
所以孟子说: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
”(《孟子·
离娄下》)那么这个“几希”是什么呢?
儒家认为主要有四点:
一是爱父母兄弟,二是好善恶恶,三是敬长慈幼,四是认同公理。
孟子把它们概括为仁义礼智。
对于上述这些观点,朱陆二人都是认同的。
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人类的这种善的本性,对于每一个具体的个人来说,到底有多大的现实性?
即这种善的本性具体到每个现实的人身上,只是潜在的还是已经实在的?
朱熹认为,它只是潜在的,必须通过不懈的学、思工夫,才能变潜在为实在。
陆九渊则坚持并发展了孟子的看法,认为是“不学而知”,“不虑而能”2的。
朱熹把世界二分为“理”的世界和“气”的世界,虽然他常讲理与气不可分,但更强调理与气不相杂。
“理”的世界空阔洁净,无限完满,永恒不变,是宇宙之本;
“气”的世界混杂不齐,良莠不均,多变易逝,是由“理”世界派生的。
“理”的世界一旦与“气”的世界结合了,就有了杂质,就变得不洁净不完满。
他把这一宇宙观贯彻到人性论上,就合乎逻辑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人性只是在“理”的世界中才是洁净完满的,才是至善的,而现实中每个具体的人的人性则各有亏欠,无善可言。
所以他说:
“吾之心即天地之心。
但天命至正,人心便邪。
天命至公,人心便私。
天命至大,人心便小。
所以与天地不相似。
而今讲学,便要去得与天地不相似处,要与天地相似。
”(《朱子语类·
36》)
《诗经》说:
“天生蒸民,有物有则。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这是儒学最基本的观念之一。
朱熹对此是认同的。
他认为万事万物各有其理,都是秉受其理而存在、发展和变化的。
人类芸芸众生,也都是秉受了人类之理才成为人类一员的。
人人共此一理,就同“月印万川”、万川共此一月一样。
他说:
“譬如一树花,皆是显诸仁处。
及至此花结实,则一花自成一实。
方众花开时,共此一树,共一个性命。
及至结实成熟后,一实又自成一个性命。
”(《语类·
74》)又说:
“天地之生万物,一个物里面便有一个天地之心。
圣人之于天下,一个人里面便有一个圣人之心。
”((《语类·
27》)但是,各人所实际秉受的人类之理、所拥有的圣人之心并不是完全一样的,有的多一些,有的少一些,有的全一些,有的偏一些。
就像到大江中去取水,有人用勺,有人用碗,有人用桶、用缸,虽然都取到水,但用勺的只得了一勺,用碗的便得了一碗,而用桶、用缸的则得了一桶、一缸。
“如一江水,你将杓去取,只得一杓;
将碗去取,只得一碗。
至于一桶一缸,各自随器量不同,故理亦随以异”(《语类·
4》),“天之生物,其理固无差别,但人物所禀于形气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异”(《朱文公文集·
卷58,答徐子融》)。
朱熹十分赞赏张载关于“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思想,并把它进一步发展。
朱熹认为,人类之理是一个全体,它完满至善,是现实世界中人性的本体,与现实中的人性是“体用”关系和“不相离”“不相杂”的关系。
而通常所说的人性,是指现实中的人性,是人类之理参杂在气质之中,受了气质的污染,已不是人类之理的本来面目。
他说,“才说性,便已涉乎有生而兼乎气质,不得为性之本体也。
然性之本休亦未尝杂。
要人就此上面见得其本体元未尝离,亦未尝杂耳”,“所谓天命之谓性者,是就人身中指出这个是天命之性不杂气禀而言尔。
若才说性时,则便是夹杂气禀而言。
所以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也”(《语类·
95》)。
因而在朱熹看来,《诗经》所说的“民彝”、孟子所说的“性善”指的只是人类之理这一“天命之性”,而各人身上所具有的只是参差不齐的“气质之性”。
所以朱熹主张,仁义礼智作为人类之理,属于“天命之性”,是本体,现实中的人并不完具此理此性,它们只是潜在于人们的“气质之性”中。
人们要通过不懈的“变化气质”的修养工夫和“格物穷理”的认知工夫,才能使它们由潜在变为实在。
也只有在它们变为实在之后,人们才能够“直道而行”,“从心所欲而不愈矩”,才能成就自己的德性人格,实现自己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因此,在人的德性从何而来的问题上,朱熹一方面承认来自于先验的天赋,以“天命之性”为基础,另一方面也强调要靠后天长期的学习、思虑和涵养,否则它就永远只是潜在的东西。
“学之久,则心与理一”(《语类·
2》)。
“学者克己复礼上做工夫,到私欲尽后,便粹然是天地生物之心”(《语类·
20》)。
而陆象山则不这样看。
象山认为,人的德性是人天生而有的,它实实在在就在人的心中,不论人生下来时禀的气是清是纯,是厚是薄,都具备了人的德性,即便是顽冥不化的人,在他身上,人的德性也是完满无缺的。
只不过有的人对这种德性觉得多,有的人觉得少,有的人甚至茫然不觉;
有的能事事照它而行,有的照它而行多,不照它而行少,有的则相反,甚至完全不能照它而行。
圣贤智愚的差别就在这里。
象山说:
“人生天地之间,禀阴阳之和,抱五行之秀,其为贵孰得而加焉。
使能因其本然,全其固有,则所谓贵者固自有之,自知之,自享之,而奚以圣人之言为?
”(《陆九渊集·
卷30·
天地之性人为贵》)又说:
“彝伦在人,维天所命。
良知之端,形于爱敬。
扩而充之,圣哲之所以为圣哲也。
先知者,知此而已;
先觉者,觉者此而已。
气有所蒙,物有所蔽,势有所迁,习有所移,往而不返,迷而不解,于是为愚不肖”(《卷19·
武陵县学记》),“良心之在人,虽或有所陷溺,亦未始泯然而尽亡也。
下愚不肖之人所以自绝于仁人君子之域者,亦特其自弃而不之求耳”(《卷32·
求则得之》)。
孟子曾说过:
“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孟子·
告子上》),“非独贤者有此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同上),“君子之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离娄下》。
象山着力发扬了孟子的这些思想,提出了“心即理”的观念:
“四端者,即此心也;
天之所与我者,即此心也。
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卷11·
与李宰》)。
他认为,德性在人身上“有何欠阙?
当恻隐时自然恻隐,当羞恶时自然羞,当宽裕温柔时自然宽裕温柔,当发强刚毅时自然发强刚毅”(《卷35·
语录下》)。
他教导学生:
“汝耳自聪,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无少缺,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卷34·
语录上》)。
他指出:
“圣贤垂教,亦是人固有,岂是外面把一件物事来赠吾友?
但能悉为发明天之所以予我者如此其厚,如此其贵,不失其所以为人者耳”(《卷35·
他揭露朱子以德性在人身上不是现实具有的,而是思而后有,虑而后能,修而后得的,实际上就是告子式的“义外”论,是“外入之学”,得人们成圣成贤失去了现实可靠的根据,而陷入“假借”、“虚饰”,疲于外役的境地之中。
朱陆在这个问题上的差异,是朱陆哲学异同之根本,其他的差异,都是这一差异的自然延伸和发展。
紧紧抓住这一根本,就抓住了朱陆哲学异同的钥匙。
圣人的标准是什么
儒学在孔子那里,是学以为己,学以成仁,而并没有要求人们学以成圣。
所以孔子讲得多的是“君子”,是“仁”,而“圣”则讲得较少。
他只有五处讲到圣人:
“子贡曰:
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
可谓仁乎?
子曰:
何事于仁?
必也圣乎!
尧舜其犹病诸!
”(《论语·
雍也》)“子曰:
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
”(《述而》)“子曰:
若圣与仁,则吾岂敢?
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
”(同上)“孔子曰:
君子有三畏:
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季氏》)“君子之道,焉可诬也?
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
子张》)从这几处对圣人的描述看,孔子认为圣人是不易做到的。
在孟子那里,“圣人”则讲得稍多些,孟子认为孔子是“圣之时者”[5],而提出“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
公孙丑上》),初步提出了学做圣人的观念。
但孟子之学主要在其“仁政”,主张通过扩充“恻隐之心”达成仁政,而扩充“恻隐之心”的过程,也就是从“可欲之谓善”,通过“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这几个阶段,达到“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6]的成仁成圣的过程。
到宋代,经过周濂溪和二程等人的宣扬,“志于圣”“学以至圣”才成为儒家对读书人的普遍要求。
但在孔子孟子那里,没有对圣人的境界和标准作出较为明确的说明,所以在“学以至圣”成为普遍要求的宋代,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做圣人,就成为必须讲明的问题。
而朱子与象山在这个问题上观念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
朱子认为,宇宙是一个“理”的宇宙,“理”是宇宙的根本,它是形而上的,是事物之所以然及其所当然。
万事万物各有其自身之理,这些理就在各个具体事物之中。
而“心”属于“气”,是形而下的形器,它与理的关系是末与本的关系,用与体的关系。
虽然他也提出“心具众理”“心包万理”,但它们是像饺子一样,是皮子包着馅子[7],两者截然不同,是“不相离”又“不相杂”的两种东西。
人生下来时,理就具在心中,但与“气质”夹杂在一起。
禀得清纯之气的,就是圣人,禀得浑浊之气的就是愚人,常人则是清纯浑浊之气皆有,有的清一些,有的浑一些。
而圣人是纯清无一毫杂染的,所以圣人的心至明至灵,其心中之万理纤毫毕察,是生而知之,天生下来就“心”与“理”一,应事接物之时,自然分厘不差。
因此在朱子那里,圣人是全知全能和无过的,能参天地之化育,成旷世之奇功。
朱子说:
“人性皆善,然而有生下来善底,有生下来便恶底。
此是气禀不同”(《语类·
4》),“精英者为人,渣滓者为物。
精英之中又精英者为圣为贤,精英之中粗渣者为愚为不肖”(《语类·
14》),“圣人之心,浑然一理。
他心里全包这万理,所以散出于万物万事,无不各当其理”(《语类·
27》),“自古无不晓事底圣贤,亦无不通变底圣贤,亦无关门独坐底圣贤。
圣贤无所不通,无所不能,哪个事理会不得?
117》)“圣人事事会”(《语类·
36》),“直有阖辟乾坤之功”(《语类·
53》)。
朱子把圣贤看成是天生的,“无所不通”,“无所不能”,这样的圣人,常人怎么做得成?
他自己也发出了圣人难做的感叹:
“某十数岁时读《孟子》,言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
以为圣人易做,今方觉得难”(《语类·
104》),又说:
“以某观之,做个圣贤千难万难”(《语类·
115》),又说:
“古时圣贤易做,后世圣贤难做。
古时只是顺那自然做将去,而今大故费手”(《语类·
90》),“后世圣贤难做,动着便恁地粘手惹脚”(同上)。
可见,朱子的圣人观,是把孔子“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尧舜其犹病诸”的观念发展到极至。
但既然成圣人是儒学的终极目的,朱子也只好免强而为,要求学者去做艰苦细致的格物穷理和修心养性的工夫了。
象山则不然。
象山虽然也同朱子一样,认为人是禀气而生,而所禀之气,也有清浊纯杂之分,如:
“气禀益下,其工益劳,此圣人、贤人、众人之辨也”(《陆九渊集·
卷13·
与郭邦逸》),“诚使圣人者并时而生,同堂而学,同朝而用,其气禀德性,所造所养,亦岂能尽同?
”(《卷22·
杂说》)但是,他决不承认圣人所禀之气,就全清无浊,至纯无杂,而是认为圣人所禀之气当中,也是有杂质的,其心并非生来就至明至灵,并非能洞悉天下一切事物之理。
圣贤也要做“学”“养”“推”“扩”的工夫,只不过他宅心仁厚,工夫做起来不必多费力气,所谓“其工益劳”,就是说圣人也要做工夫,也有劳在其中,只不过其工其劳相对众人来说,要少些,轻些而已。
所以象山认为,圣人并不是全知全能的,而也是有过的,其过人之处,只在于圣人能不断地改正过错,渐趋完美。
“过者,虽古圣贤有所不免,而圣贤之所以为圣贤者,惟其改之而已”(《卷6·
与傅全美·
2》),“过,恐非一旦所能尽知。
贤如蘧伯玉,犹欲寡其过而未能。
圣如夫子,犹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卷6·
与傅子渊》),“虽古圣贤,尚不能无过,所贵能改耳。
《易》称颜子之贤曰‘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
由是观之,则颜子亦不能无不善处。
今人便欲言行无一不善,恐无是理”(《卷7·
与张季忠》),象山甚至还说:
“以铢称寸量之法绳古圣贤,则皆有不可胜诛之罪”(《卷17·
与致政兄》)。
象山指出,天下事物之理是无穷的,而圣人之智是有限的,并不能知尽天下事。
之所以称圣人为智,不肖为愚,那主要是因为圣人明觉了其固有的本心,事事依本心而行;
不肖则泯灭了其本心,不能依本心而行。
“人情物理之变,何可胜穷?
若其标末,虽古圣人不能尽知也。
稷之不能审于八音,夔之不能详于五种,可以理揆。
夫子之圣,自以少贱而多能,然不如老农,圃不如老圃,虽其老于论道,亦曰学而不厌,启助之益,需于后学。
伏羲之时,未有尧之文章;
唐虞之时,未有成周之礼乐。
非伏羲之智不如尧,而尧舜之智不如周公,古之圣贤,更续缉熙之际,尚可考也”(《卷1·
与邵叔宜》),“圣人之智,非有乔桀卓异不可知者也,直先得人心之所同然耳”(《卷30·
智者术之原》)。
说圣人之智明切洞达,只是因为圣人应事接物之时本心充达,而“无一毫私意芥蒂于其间”,这样,圣人才能“于是非利害,不啻如权之于轻重,度之于长短,鉴之于妍丑,有不加思而得之者。
……虽酬酢万变,无非因其固然,行其所无事,有不加毫末于其间者”(同上)。
总之,象山指出:
“能涵养此心,便是圣贤”(《卷35·
语录下》),所以圣贤之学和学做圣贤,并不是高远难行之事,它易而易知,简而易能,只在于人们自己去自立、自求、自觉和自得而已。
怎样成德成圣
象山继承和发扬了孟子关于“不为”与“不能”的观点,指明成德成圣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的,是所谓“愚夫愚妇”都可以与知能行的。
人们成不了德,成不了圣,只是不明本心,就像不帮老人折根树枝做拐棍那样,不为而已,而不是像挟着泰山跨过北海那样,不能办到的事。
这是因为德和圣就在每个人的心中,只要把自己心中的德和圣发明出来,做将而去,那么你终将成圣成贤则是谁也挡不住的。
“故正理在人心,乃所谓固有。
易而易知,简而易从,初非甚高难行之事”(《卷11·
与李宰·
2》),“道理无奇特,乃人心所固有,天下所共由,岂难知哉?
但俗习谬见不能痛省勇改,则为隔碍耳”《卷14·
与严泰伯》,“天之所以予我者,非由外烁,不俟他求。
能敬保谨养,学问、思辩而笃行之,谁得而御?
”(《卷14·
与包详道》)“自有诸己至于大而化之,其宽裕温柔足以有容,发强刚毅足以有执,斋庄中正足以有敬,文理密察足以有别。
增加驯积,水渐木升,固月异而岁不同。
然由萌蘖之生而至于枝叶扶疏,由源泉混混而至于放乎四海,岂二物哉?
”(《卷1·
与邵叔宜》)所以,成德成圣根本无须到心外和身外去求。
如果信不及自己的本心,不知道自己心中就有德性,心中就有圣贤,而非要到圣贤的书册中去求,到万事万物中去找(找到事物之理,然后依事物之理去应事接物,使自己无毫厘之失),那势必要越求越远,越找越难。
“今终日营营,如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有采摘汲引之劳,而盈涸荣枯无常,岂所谓‘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者哉?
”(同上)到自身心上去求,就是做发明本心、先立其大和尊德性的工夫。
这种工夫主要是要靠自己去做,别人是帮不上多大的忙的。
“若的实自息妄见,良心善性,乃达材固有,何须他人模写?
但养之不害可也”(《卷4·
与胡达材》)。
这些工夫,实际上也是一种“减担子”的工夫,减去自己心中“内交”“要誉”“恶声”“利害”“得失”“声名”“祸福”的担子,减去自己身上要做圣贤,要知尽圣贤事、格尽天下物的担子。
这些担子减去之后,做起工夫来自然轻松活泼,本心自然可以无牵无扯,无隔无碍地发用流行。
“圣人之言自明白。
且如‘弟子入则孝,出则弟’,是分明说与你入便孝,出便弟,何须得传注?
学者疲精神于此,是以担子越重。
到某这里,只是与他减担,只此便是格物。
”(《卷35·
语录下》)
朱子所要做的恰恰相反,他是要给人加担子。
本来人们心中的私欲杂念就很多,要透过这些私念才能看到真己大我,看到本心良性,要在反观自省上下工夫,去察识,去体认,去觉悟。
他对此是认同的,常常说出要求心务本的话来。
他说“人之一心,本自光明。
常提撕他起,莫为物欲所蔽。
便将这个做本领,然后去格物致知”(《语类·
15》)“要于本领上理会”(《语类·
8》)“格物须是从切己处理会去,待自家者已定叠,然后渐渐推去,这便是能格物”(《语类·
15》)“且穷实理,令有切己工夫,若只泛穷天下万物之理,不务切己,即是《遗书》所谓游骑无所归矣”(《语类·
18》)“万理皆具于吾心,须就自家身上做工夫,方始应得万理万事”(《语类·
130》)但是,他最终却又信不及本心,以为照本心去做,并不能做到尽善尽美,即并不一定能符合事物本身的所当然。
只有广泛认识天下事物之理,应事接物时才能无差,才能开物成务,才能做成无过的圣贤。
而且也只有广泛认识了事物之理,才能豁然贯通,使心与理合而为一,才能真正求得心,明得本。
“此心此理虽本完具,却为气质之禀不能无偏,若不讲明体察,极精极密,往往随其所偏,堕于物欲之私而不自知”(《朱文公文集·
卷54·
答项平甫》),“若大人只守个赤子之心,则于穷理应理皆有所妨矣”(《文集·
卷55·
答潘谦之》),“凡一物有一理,须先明此,然后心之所发,轻重长短,如能准则。
若不于此先致其知,但见其所以为心者如此,识其所以为心者此,泛然而无所准则,则其所存所发,亦何自而中于理乎?
”(《文集·
答张敬夫》)。
所以朱子要求人们去格外物,名物度数、兵刑钱粮、草木鱼虫,都要去格它,这一物不格,就缺了对这一物道理的认识,那一物不格,又缺了对那一物道理的认识,今日格这件,明日格那件,格多了,就会有脱然贯通之时。
这就给学圣人者加上了无比沉重的担子。
因为,事物的所以然和所当然之理,并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格得清的,一辈子也格不了几件事物。
而且即使格清了几件物事,与自己的身心和德性又有什么相干呢?
正是因为朱子把格物致知作为明心见性、成德成圣的根本方法,所以他才承认自己在“道问学”上讲得多。
到这里,才形成了所谓“尊德性”和“道问学”的问题。
可见,这一问题只是“心”与“理”这一根本问题的发展与延伸,并不是朱陆哲学异同的关键和实质。
“里面出来”与“外面入去”
朱熹哲学的总体特征是格物致知,要求学者广泛认识天下事物,做既道德高尚,又能治世安民的全知、全能的无过的圣人。
在他看来,“天地阴阳事物之理、修身齐家治国以至于平治天下之道、与凡圣贤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礼乐之名数,下而至于食货之源流、兵刑之法制”等等,都是学者的分内之事,都要去认识,否则就“无以明夫明德体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极”(《朱文公文集·
卷80·
福州州学经史阁记》)。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自己身体力行,把自己的毕生精力都用于格物致知上,以建立一个大全的儒学体系。
厘清儒学概念范畴的内容和联系,为它们作出确切的定义;
为儒家经典作出清楚明白的注解;
对儒家伦理和礼仪作出细致而精确的考证。
他自信自己的学说为学者提供了一个进德入道的样板,把绣鸳鸯的金针交给了别人,让他人也可以绣出漂亮的鸳鸯来。
而陆九渊哲学的总体特征是发明本心,教导学者在自己的人生实践中体认自己的良心善性,并在实践中保任涵养,使它充实而光大,做一个迁善改过、过而能改的圣人。
只要能以自己的良心善性去应事接物,即使不能全对,也可离道不远。
这种良心善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志,是人类区别于鸡鸭牛马、鸟兽鱼虫等他类事物的种性。
它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先验的,与生俱来的。
因而君子圣贤是每个人自己心中本有的,无须到自己身外去寻求。
以这种观念为基础,九渊的全部学说和毕生精力,都集中在引导人们发明本心、自觉自得、自立自求上,极力倡导“里面出来”的治学方法,反对依葫芦画瓢的“外入之学”。
九渊说:
“孔门唯颜曾传道,他未有闻。
盖颜曾从里面出来,他人外面入去。
今所传,乃子夏子张之徒外入之学。
卷35·
语录下》)“外面入去”的“外入之学”的特点是,把儒学关于成圣成贤的观念和道理作为客观外在的知识去求习,就如同学习一加一等于二、前代君臣如何治国应事一样,而没有通过读书讲论和日用常行去印证和体悟自己身心中本有的德性良知、良心善性。
它造成的后果是:
卑下者以所学得的儒家身心性命知识资言谈、助胜心、增意见、作文饰、应科举;
高明者恪守先圣先贤之训,以儒学观念“防闲”、“检敛”、“刚制”自己的言行,以期迹同形似。
卑下者不足论,就高明者而言,其意志之坚、行道之勇让人钦佩,坚持下去,或许也能达到不动心的境界,但毕生束缚于外,终不能明道,终不能自由自觉、洒脱自然,或者只可称做“孔门别派”。
“告子之意,‘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是外面把捉的。
要之亦是孔门别派,将来也会成,只是终不自然。
”(同上)“告子不动心,是操持坚执做;
孟子不动心,是明道之力。
卷34·
语录上》)操持坚执做,是屈从于外,一时一事则易,长久则难;
而明道自适,则悠游自然,是“实有诸己”,必能“充实”而“光大”,就如同混混源泉,自可放乎四海。
有见于此,九渊的讲学,便是直指人之本心,着力于“悼时俗之通病,启人心之固有”(《陆九渊集·
卷20·
朱氏子更名字说》),揭露“外面入去”的外入之学之非,孜孜不倦地以“里面出来”的方法引导求学者体悟自己的本心,引导学者自求自立、自觉自得。
九渊教导求学者:
“‘诚者自诚而道自道也’,‘君子以自昭其明德’,‘人之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暴谓‘自暴’,弃谓‘自弃’,侮谓‘自侮’,反谓‘自反’,得谓‘自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