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是九十年代异军突起的先锋作家之一Word下载.docx
《余华是九十年代异军突起的先锋作家之一Word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余华是九十年代异军突起的先锋作家之一Word下载.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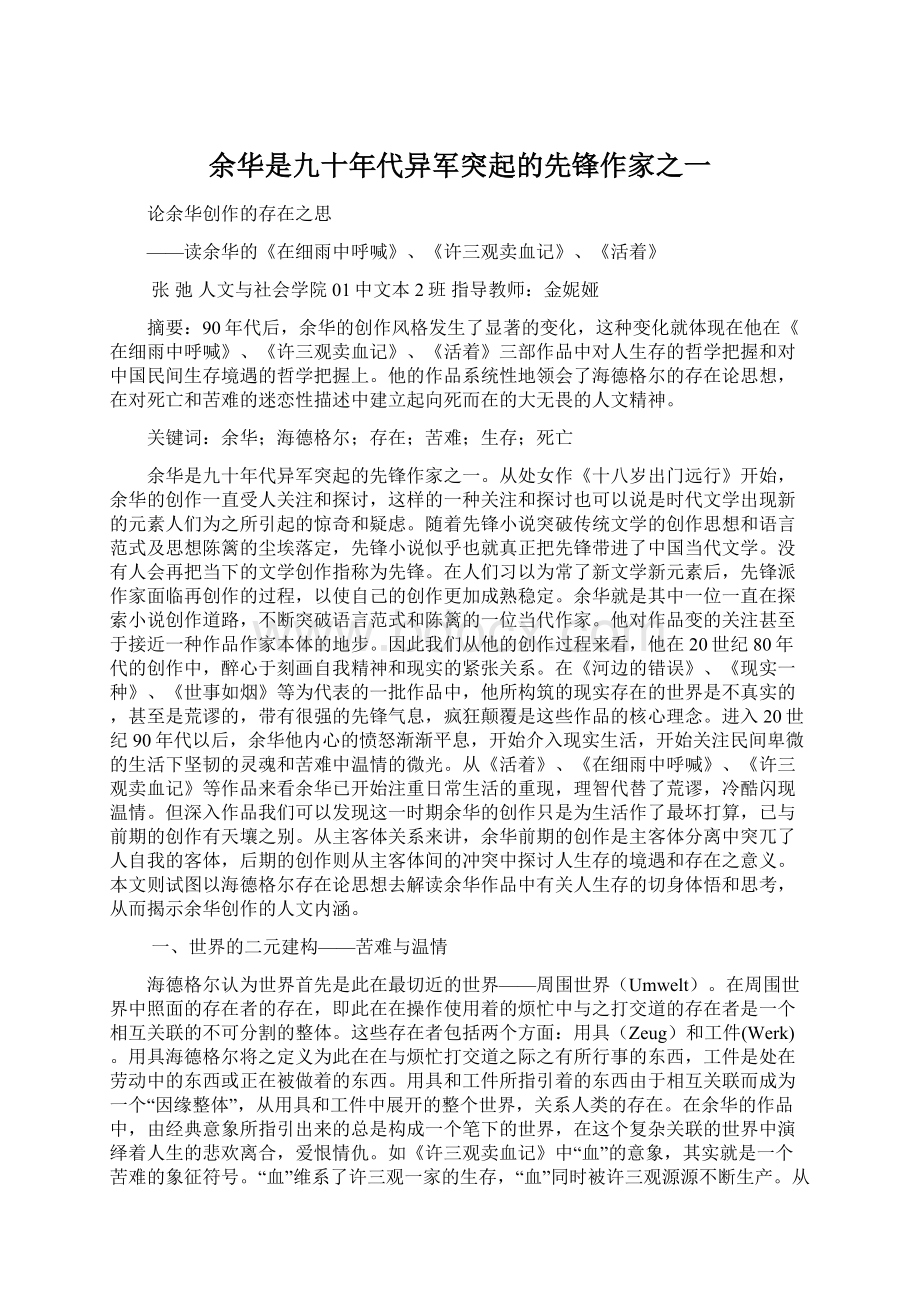
余华就是其中一位一直在探索小说创作道路,不断突破语言范式和陈篱的一位当代作家。
他对作品变的关注甚至于接近一种作品作家本体的地步。
因此我们从他的创作过程来看,他在20世纪80年代的创作中,醉心于刻画自我精神和现实的紧张关系。
在《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世事如烟》等为代表的一批作品中,他所构筑的现实存在的世界是不真实的,甚至是荒谬的,带有很强的先锋气息,疯狂颠覆是这些作品的核心理念。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余华他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开始介入现实生活,开始关注民间卑微的生活下坚韧的灵魂和苦难中温情的微光。
从《活着》、《在细雨中呼喊》、《许三观卖血记》等作品来看余华已开始注重日常生活的重现,理智代替了荒谬,冷酷闪现温情。
但深入作品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时期余华的创作只是为生活作了最坏打算,已与前期的创作有天壤之别。
从主客体关系来讲,余华前期的创作是主客体分离中突兀了人自我的客体,后期的创作则从主客体间的冲突中探讨人生存的境遇和存在之意义。
本文则试图以海德格尔存在论思想去解读余华作品中有关人生存的切身体悟和思考,从而揭示余华创作的人文内涵。
一、世界的二元建构——苦难与温情
海德格尔认为世界首先是此在最切近的世界——周围世界(Umwelt)。
在周围世界中照面的存在者的存在,即此在在操作使用着的烦忙中与之打交道的存在者是一个相互关联的不可分割的整体。
这些存在者包括两个方面:
用具(Zeug)和工件(Werk)。
用具海德格尔将之定义为此在在与烦忙打交道之际之有所行事的东西,工件是处在劳动中的东西或正在被做着的东西。
用具和工件所指引着的东西由于相互关联而成为一个“因缘整体”,从用具和工件中展开的整个世界,关系人类的存在。
在余华的作品中,由经典意象所指引出来的总是构成一个笔下的世界,在这个复杂关联的世界中演绎着人生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
如《许三观卖血记》中“血”的意象,其实就是一个苦难的象征符号。
“血”维系了许三观一家的生存,“血”同时被许三观源源不断生产。
从作品中许三观“喝水生血”的荒唐事中,我们所看到的不仅仅是在这块土地上延续了几千年的农民简陋的生产生活方式,而且可以发现民间以自己身体作为本钱来生产的“血”作为隐性工件的象征。
众所周知,“血”这一意象正是源于农民自身的身体,余华对血这一意象的运用,正是基于对人生存的体悟,也正是在排除掉工业文明污染的赤裸裸的农民身上,才能更加本真显露人生存的境遇和苦难,在这一点上余华似乎想得更远。
余华似乎想证明并不是工业时代的时代危机造成人的苦难,而是由于人本身的命运的安排要求人来接受“苦难”的洗礼。
同时“血”又浓缩了海德格尔所谓的用具与工件,使其成为一个值得玩味的意象。
由“血”展开故事,通过血把许三观的世界逐步建立起来,构成了一个血肉丰满,善与恶,好与坏,苦难与温情并存的多彩世界。
在这个世界之中,余华更多的是传达了人生存的极度苦难与恐惧,或者我们可以说余华是以渲染苦难为目的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余华也把温情作为了一个物的象征,温情成了他笔下主人公要去追求制造以求得使用的东西,在温情的追求制造和享受中展开因缘整体,构筑生存的世界,同时通过人与温情的操劳展示苦难渲染苦难。
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以人为纽带的苦难和温情在世界中的二元建构。
温情和苦难构成世界,是现实世界同时又是精神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温情与苦难同行,在温情之少和苦难之多的双重话语中体现人性的悲壮美感和世界的内在张力。
在余华九十年代的作品中我们都可以发现余华对世界的这样一种建构。
如《在细雨中呼喊》中,孙光林想融人家庭中,成为家庭中平等的一员,希望得到家庭成员的关心和呵护,但在这样一种温情的追求中,苦难把这样一种追求击得粉碎。
在孙光林和苏宇的友情中,我们不仅发现温情而且洞察了苦难。
又如在《活着》中,福贵在年轻时的一夜豪赌输光家产后幡然醒悟,想重振家业,给家人带来幸福的生活,可那体现人性之爱的死亡间歇中的滴滴温情掩盖不了死亡带来的心灵震颤。
温情之少和苦难之多对世界的二元建构使余华把读者带进了一个形而上的层面,是余华对常识世界的一种反思,是对人类文明秩序世界的一种反思。
他把秩序的世界用苦难去打乱,以求建立起余华所说的真正真实的世界——精神的世界。
余华要建立的精神世界是通过作品中人物在苦难和温情中的挣扎来建立的。
余华把现实世界苦难的不可逃离作为他对世界的感知,并以此来传达他的世界观。
我们在《在细雨中呼喊》中能发现这种逃离的寓言。
我们可以把孙光林离开南门到孙荡的生活看成一种逃离,后来上大学离开南门看成又一次逃离。
第一逃离次他感受了王立强和李秀英的温暖,但温暖却是短暂的,南门又鬼使神差地召唤他归来。
第二次孙光林以为已经逃离了南门,事实是他永远生活在南门对他的精神磨难中,正像海德格尔所说的:
“世界就是此在作为存在者向来已曾在其中的‘何所在’,此在无论怎样转身而去,但纵到天涯海角也还不过是向之归来的‘何所向’”[1],余华笔下人物的这种不由自主的归来正是由于温情和苦难对世界的二元建构。
二、共在的挟持——挣脱不了的苦难
余华对人生存方式生存境遇的描述和渲染无不在传达一种无奈的宿命观点。
在其作品中人总是被共在和他人挟持,成为悲剧苦难命运的根源。
在余华所构造的世界中,人不仅无法逃离由象征性的用具和工件所展开的“因缘整体”——现实世界,并受其制约,而且人还受与他生活在一起的他人的制约。
在海德格尔的哲学里,“他人”是指与我们本身多半无区别,我们也在其中的那些人。
由于“此在”我与“他人”共在一个因缘整体展开的世界中,此在因此具有了双重身份。
一方面“此在”区别于“他人”,独立于他人的世界。
另一方面,此在又与他人共在,是他人的一部分。
余华作品中的主人公作为此在存在也具有这双重的性质和身份,因此表现在作品的故事情节中为人物生活追求的双重对立。
首先作为此在而在的主人公,处于一种本真的自我的生存状态下。
如《在细雨中呼喊》的主人公“我”孙光林竭尽全力去融入父亲的主流话语世界,但父亲的拒绝,使其反而隐身于世界的幕后,冷静地观察这个世界发生之种种,洞察了生存的本质——苦难。
其次作为他人而在的此在,余华作品中的主人公又处于一种非本真的生存中。
如《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他的命运完全是被挟持的,许三观第一次卖血为了讨老婆,第二次卖血是为了摆平一乐砸了方铁匠儿子的头,第三次卖血所得最后大部分花在了家人的穿上面,第四次卖血是为了让家人在苦难的年代吃上一顿饱饭。
总之,许三观的一生是卖血的一生。
他在卖血中经历了酸甜苦辣。
他为了给二乐治病,一路卖血到上海,差点丢掉性命。
在余华语言的狂欢中,在余华对苦难的渲染中,我们深深的感受了许三观的坎坷命运,和许三观之于命运的无力,尽管我们无法漠视许三观身上显示出的那一份弥足珍贵的人性光辉,但这种点滴的温情依然无法掩盖的是被挟持的命运,这种无奈便是此在消融在他人中非本真生存境遇的他人因素和寓言式的命运。
此在苦难命运的另一种情况是此在在与他人的共在中,被共在所挟持又被共在所抛弃,构成了人生存境遇中的一大悖论。
如《在细雨中呼喊》中的孙光才孙光平父子。
在孙光明救人被淹死后,孙广才和孙光平非常出乎意料的放弃了被救孩子父亲所主动要求给予的赔偿,而是慷慨激昂地向被救孩子的父亲提出了一个小小要求:
你明天就去城里,让广播给播一下。
而事实上,孙广才父子俩开始沉浸于自身的幻想中,他们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将脱离卑微的生活,不仅能接到上天安门城楼的邀请,而且还能捞个一官半职。
在这种幻想中,我们看到了社会主流话语对他的影响和共在的强大力量,这种主流话语海德格尔称之为“闲言”。
后来情况变化得很戏剧,“孙家父子以无法抑制的兴奋,将他们极不可靠的设想分阶段灌输,于是有关孙家父子即将搬走的消息,在村里纷纷扬扬,最为吓人的说法是他们有可能搬到北京去住。
这样的说法来我家时,让我在某个下午听到父亲激动无比的对哥哥说:
‘无风不起浪。
村里人都说了,看来政府的人马上要来。
’……就这样我的父亲先把自己的幻想灌输给村里的人,然后再用村里的人因此而激起的流言巩固自己的幻想”。
被流言迷惑了的孙广才父子之后的一系列荒唐事叫人哭笑不得。
先是全家整容穿新衣服,之后孙广才觉得应该向政府来人显示家庭的朴素与艰苦,结果全家人都穿着打满补丁的衣服,被人嘲弄。
后来孙光平认为父亲的这种做法“是对共产党社会的污蔑”又使孙广才不停得向村里人解释这是忆苦思甜。
再后来孙广才望眼欲穿地期待穿中山装的政府代表的来到,以至成了全村人的笑柄。
在这件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孙广才作为此在的个体在共在话语旋涡中的尴尬境地。
他一方面被共在所挟持,一方面共在时不时又将此在个体不切实际超越于共在的行为予以嘲笑。
海德格尔说;
“凡是公开承担责任之处,常人都已经溜走了”[2],共在将所有的嘲笑加之于孙广才父子俩时,共在却永远不会反思自己对此在——孙广才父子的挟持。
在海德格尔看来这是人生存的被抛状态的宿命,海德格尔称其为共在的平均状态。
三、生存的领会——孤独与迷失
在余华笔下,他小说中的人物还不时流露出一种孤独意识,在卡夫卡和川端康成那里我们可以找到这种气质的原形。
因为正如余华自己所言的他是深受卡氏和川氏的影响,但作为一名中国作家,余华将中国民间因素融入进这种意识之中,使其显得更加有韵味。
余华的孤独意识在作品主人公身上的流露首先来自于余华自身对生存中此在“在”的洞察和体悟。
余华九十作品《在细雨中呼喊》《许三观卖血记》、《活着》中的人物似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总是被苦难所包围,在漫漫的人生旅途中品味着孤独或是显示出一种孤独的气质,他们像是加缪笔下的西绪弗,但他们民间的生活哲学又缺少一种主观的反抗气质。
他们的生存哲学是“为活着而活着”,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感觉到他们作为此在的被抛状态,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是生活并不如他们所愿,如他们所选择,他们“存在着且不得不存在”。
如《活着》中的福贵,《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还有孤独意识最为浓重的《在细雨中呼喊》的主人公孙光林。
这种孤独意识被海德格尔称之为此在在此的现身情态:
情绪,有情绪。
这种情绪正是缘于人“在此”的被抛状态。
《在细雨中呼喊》主人公“我”孙光林的这种意识十分明显,因为他是被共在世界排斥最为厉害的一个,这种孤立放大了他生存的被抛状态。
在这部作品中同样孤独的还有孙光林爷爷孙有元,后来的朋友苏宇,以及国庆和鲁鲁,病女人李秀英。
比如文中写苏宇“从童年起就被事实和绝望纠缠不清了”,鲁鲁的那种孤独会使孙光林觉得“两年前我在年长的苏宇那里体会的友情的温暖,两年后我和年幼的鲁鲁在一起时,常常感到自己成为了苏宇,正注视着过去的我”。
余华对孤独持有一种特殊的迷恋,但他笔下的孤独人物并不是消极对待生存的不公,在他笔下,这些人物往往具有强烈的自尊和自得的自我的人格力量。
苏宇的那种敏感,鲁鲁的那种自尊,李秀英的那种善良,国庆的纯真和勇敢都那么美好,都成了孙光林的精神寄托。
他们的生活虽然是坎坷和苦难的而且是无奈的,但他们面对生活的方式却是本真的。
那种本真的自我之爱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幅诗意的温馨的画面。
如写孙有元晚年的凄惨晚景时作者还不时写孙有元的自得和自尊,整个画面充满着暖色调:
“孙有元端坐在竹椅里,回想那个年轻漂亮而且曾经富有过的女人时,那张远离阳光的脸因为皱纹的波动,显得异常生动。
我经常偷看那脸上如青年般微微摇晃的笑容,这笑容在我现在的目光里是那么的让我感动。
”又如鲁鲁在没有父亲和哥哥的呵护,母亲为了生计被迫卖淫的环境中,却拥有强烈的自尊,他在母亲被抓后的一系列行为另人心生敬佩。
再如李秀英虽然病入膏肓,但“她骨子里却是天真和善良”,她给了孙光林以温暖和信任。
这些孤独者形象仿佛能洞察世界的秘密,他们不断地与世界照面,在此在与他在的彷徨中保持了一种善良和爱,虽然他们的人生是苦涩的,但他们有如在黑夜里点起的一盏明灯,给所有孤独之人以心灵的安慰。
《在细雨中呼喊》是对孤独情绪的写实,作者并未提出面对这种孤独怎样在心灵中找到哲学的依靠。
而余华在其后来的作品《活着》中则不仅向我们展示了福贵这个最大的孤独者形象,而且还建立了一种生存哲学。
在余华的这部作品中,福贵的这种孤独和被抛感被写得淋漓尽致,这种孤独感并不是体现在福贵家究竟死了几口人,而是体现在福贵在家庭成员一个个离去时所遭受的心灵打击和其背后的寓言般的涵义上。
福贵的一夜豪赌是作者向读者展示孤独的契机。
豪赌后的福贵被塑造成了一个勤劳淳朴的形象,我们或许还可以说这个形象是中国农民传统优点得到集中体现的典型形象。
他的乐观精神促使他一次次不由自主地相信他的付出会得到同等的回报。
他的这种价值观念在其生活中表现为他的勤劳,如果不是命运的捉弄,我们是可以想象福贵的生活虽不会重现当年良田万顷的家境,但至少可以相信他们会有尽享天伦的富足。
但余华却安排了围绕福贵一家的次次死亡,福贵身边的亲人都死于了非命,但福贵却活了下来,福贵陷入了不断遭遇死亡本身却不得死的尴尬境地中,一次次遭受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心灵的创痛。
余华的意图不着痕迹,他通过稳重似乎是真实可信的非正常死亡消解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传统价值观人生观,把福贵塑造成了一个最大的孤独者的形象。
正是由于福贵成为了一个最大的孤独者,福贵也就在余华笔下成为了一个对生存的领会者,他对生存意义生存境遇和对死亡的领会,使他真正认识了自己和世界,他秉承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道”来消解人生的孤独感和荒谬感。
福贵所唱的“皇帝抬我做女婿,路远迢迢我不去”,不禁让人想起南朝陶宏景答皇帝请他做宰相的诗句:
“山中何所有?
岭上白云多。
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
”
福贵成为一个对生存洞察深刻的隐士了。
但由于此在层面的此在总是根据他自我的现身领会即能在一道存在,因此常人作为有所领会的存在者,在日常生活中常常迷失和认错自我。
就像《在细雨中呼喊》的孙广才,他的身上则是集中了中国农民的一切劣根性,愚昧,荒唐,卑劣。
他似乎永远缺少冷静的判断和理性的思考。
由于“我”孙光林和“祖父”孙有元一起偶然遭遇了家中的火灾,从而使我得到孙广才长达一生的排斥,而孙广才的这种情感似乎显得很荒谬,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孙广才身上冲动的无理性。
孙广才父子的“英雄梦”则更显示了孙广才的迷失。
余华在这部作品中对孙光明之死的叙述则更是加入细节的描述来表达迷失的情态。
从作者描写孙光明救人动机可以看出:
“将舍己救人用在我弟弟身上,显然是夸大其词。
弟弟还没有崇高到以自己的死去换别人的生。
他在那一刻的行为,来自于他对那几个七八岁孩子的权威。
当死亡袭击孙光明手下的孩子时,他粗心大意地以为自己可以轻而易举地去拯救”,这个“一直口齿不清”说话时“鼻涕都流进了嘴巴”的孙光明自以为自己有强大的能力,他从孙光平“脸上学会了骄傲”,他要以“权威”的名义去拯救孩子时,显然他迷失在了他所领会的情绪之中,迷失了自己,在永不复生的“可能性”生存之路上越滑越远。
四、沉沦下的境遇——悖谬的承担
“领会”给生存带来了“可能性”的存在,把不同的生存道路和不同的生存境遇摆在此在面前,而在日常的此在中则表现为此在的沉沦,即包括闲言,好奇、两可,它们根植于领会的可能性。
而对此在沉沦的描述则构成了余华作品人物的基调。
余华从游离于主流话语之外的民间话语出发,要求能更加原始的展现人类生存的苦难,所以极尽了对“沉沦”的描写。
在余华的这三部作品中,主人公在民间话语中总是处于尴尬的境地,或是想进入高一级的优势话语而不得,或是被优势话语所挟持,无力主张自我,丧失了本真性,体现了“沉沦”的闲言、好奇、两可这三种形态。
《在细雨中呼喊》是余华对“沉沦”形态刻画得最为有力的一部作品,在作品中,“沉沦”无时无刻不在挟持着亲情。
例如,“我”本来想进入“父亲”和“哥哥”这一高一级的优势话语层面的,可“父亲”和“哥哥”却被“我”是灾星这一闲言所挟持不停地对我进行放逐,使我最后反而发现自己并不需要进入“父亲”和“哥哥”的话语世界。
因为“父亲”和“哥哥”的世界反而是失去自我的世界,他们一方面在他们的世界中勾心斗角,另一方面又出于对“主流话语”的“好奇”而丧失了自我。
如“父亲”孙有才在孙光明救人牺牲后,在主流话语对他的挟持中,丧失了对事情真实性的判断,耽于幻想最后成为全村人的笑柄。
而“我”孙光林则在被“父亲”和“哥哥”放逐后,反而找到了自我的本真性存在,洞察了世界的真实本质。
同样,《活着》中福贵的一生也是“沉沦”的一生,他的一夜豪赌输光了祖辈的家产后,企图重新通过“一只鸡到一只羊再到一头牛”的财富量化积累来重振家业,这样的一种从“小康”落到“困顿”的生活使他在一生中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悲欢离合,可到最后,他怎么也想不到“龙二”竟然“代替”他被枪决了,他发现了活着的重要意义。
同样,许三观用其自以为用之不竭的血液维持了一家的生存,当他血液老化没人要,需要人告诉他他这一生苦难的终结时,三个儿子的冷嘲热讽使我们看到最后许三观在酒楼里快乐的享受猪肝时的一丝苦涩。
海德格尔说“常人自以为培育着而且过着完满真实的生活”[3],三部作品中的人物就在这样一种“自以为”的“完满真实”中走过一生,最后才发现生存的真正真实,因此才有福贵平静的晚年,哥哥孙光平与“我”孙光林最后的冰释前嫌,生活开始富足起来的许三观享受希望的精神上的“猪肝”。
“沉沦”遮蔽了他们的一生,他们的一生充满着苦难,他们始终消散在“共处”之中,始终没有自我,只有苦难。
在余华这三部作品中,余华在其笔下陷入沉沦的人物身上展现出寻找希望的同时又面临着加深“沉沦”的人生悖谬。
无论在《在细雨中呼喊》还是在《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中,作品的主人公总是在遭遇困境,或是在困境中无法前行,或是走出这个困境又进入另一个困境。
命运的锁将他们紧紧锁住,但他们在困境中始终充满对幸福生活,对真善美的向往,并且在这种希望中做着最努力的反抗,但他们又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被“共处”不停地摆布,即将实现的希望又往往在轻易之间丧失。
而沉沦作为共处世界本质的生存特征,作品的主人公只要“在世”就始终无法摆脱“沉沦”,并且由于身陷“沉沦”,使此在丧失了对事情本真的认识,把可能性的生存作为一种希望去实现,他们“自以为培育着而且过着完满真实的生活;
这种自以为是把一种安定带入此在;
从这种安定来看,一切都在最好的安排之中,一切大门都敞开着。
”[4]就这样,许三观,福贵开始了他们的悲剧生活,“沉沦”的安定作用和引诱作用使他们充满了对生活的希望和激情,即使遭受命运不停的打击,他们也始终没有放弃希望,为希望而不停的战斗。
他们的“自信与坚决传播着一种日益增长的无须乎本真地现身领会的情绪”[5],富贵始终相信活着,许三观始终相信自己身上有用之不竭的血液去对抗灾祸。
但同时这种坚信作为“起引诱作用的安定加深了沉沦”[6],就这样,一方面他们在非本真的遮蔽下始终把非本真的希望作为他们努力的方向,另一方面,这种对希望的执着加深了沉沦。
“沉沦在世界起引诱作用和安定作用的,同时也就是异化着的”[7],“沉沦”在人生存中的双面作用,使他们在希望的执着中加深了“沉沦”,而加深了的“沉沦”使他们反之对希望的执着具有了更加悲壮的意味。
他们陷入了一个无法走出去的循环,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对生存境遇的承担,具有加缪笔下的西绪弗般的勇气和决心。
五、死亡的建构——向死而在
如上所述,余华作品对人生存之苦难的描述极尽了笔墨,他对孤独,原始欲望的迷恋是残酷的,但同时我们也无法规避余华对温情的迷恋。
余华作品中的温情有时像汪洋上的一片孤舟,像黑夜里的一盏豆灯,指引我们对温情的感动至于涕泪俱下时,引起我们思考的是难道余华是个残酷无情的作家,是一个迷恋残酷对温情肆意践踏的作家,是一个在黑暗中放下生存尊严的作家?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死亡就是余华要表达的尊严。
余华的作品中充斥着大量对死亡狂欢般的描写,他对死亡的描写充满着一种原始般的激情,他着墨于死亡时,总是把死亡描写得富于诗意。
《在细雨中呼喊》第一章开头第九段就先谈了“我”六岁时对死亡的感受:
“他仰躺在潮湿的泥土上,双目关闭,一副舒适安详的神态。
我注意到黑色的衣服上沾满了泥迹,斑斑驳驳就像田埂上那些灰暗的无名小花。
我第一次看到了死去的人,看上去他像是睡着了。
”在这部作品里,余华对苏宇之死也进行了描写“他正沉下无底的深渊,似乎有一些亮光模糊不清地扯住了他,减慢了他下沉。
那时候外面灿烂的阳光,被藏蓝的窗帘吸引了,使它自己闪闪发亮……苏宇听到一个强有力的声音从遥远处传来,他下沉的身体迅速上升了,似乎有一股微风托着他升起……一切都消失了,苏宇的身体复又下沉,犹如一颗在空气里跌落的石子,突然一股强烈的光芒蜂拥而来,立刻包围了他,可光芒顷刻消失,苏宇感到自己被扔了出去……苏宇的身体终于进入了不可阻挡的下沉,速度越来越快,并且开始旋转,在经历了冗长的窒息以后,突然获得了消失般的宁静,仿佛一股微风极其舒畅地吹散了身体,他感到自己化作了无数水滴,清脆悦耳地消失在空气之中”《在细雨中呼喊》还写了孙有元离奇古怪的回光返照的死,及孙广才的死,《许三观卖血记》中根龙,王小勇的死等,在《活着》中更是将死亡贯穿了整个故事。
余华在作品中的死亡各有各的特点和他的美学观念,给读者带来的更多是思考而不是恐惧。
在余华的作品中,余华不仅仅把人存在的消失作为死亡来加以表现。
在其作品中,余华有很多死亡的象征来表现其死亡的体验。
我们称这一类情绪领会叫死亡的象征。
在余华的三部作品中,有两类死亡的情绪领会的象征。
一是无名状态,二是逃跑状态。
无名状态指称“余华的小说标题‘我没有自己的名字’所显示的那种不被人关注,缺乏尊重,人格与感受俱遭忽略的真实成长状态,亦指‘在细雨中呼喊’却杳无应答,孤独无依的心灵际遇”[9],在《在细雨中呼喊》这部作品里,小说一开始便写出了这种“无名”的恐惧:
“1965年的时候,一个孩子开始了对黑夜不可名状的恐惧。
我回想起了那个细雨飘扬的夜晚,当时我已经睡了,我是那幺小巧,就像玩具似的被放在床上。
……一个女人哭泣般的呼喊声从远处传来,嘶哑的声音在当初寂静无比的夜晚突然响起,使我此刻回想中的童年颤抖不已。
……那个女人的呼喊声持续了很久,我是那么急切和害怕的期待另一个声音的来到,一个出来回答女人的呼喊,能够平息她哭泣的声音,可是没有出现。
现在我能意识到当初自己恐惧的原因。
那就是我一直没有听到一个出来回答的声音。
”接着余华又写道:
“可能几天以后我似乎听到了回答这个女人呼喊的声音。
……一个陌生男人向我走来,他穿着一件黑色的衣服……”,而这个黑衣男人后来死了。
余华在这里的描述似乎是以死亡来回答这种“无名”;
是以死亡来消解“无名”的精神焦虑。
如果说死亡是对无名的回答。
还不如说“无名”是一种死亡的“召唤”。
这种死亡的“召唤”在唤醒了存在的“在”。
孙光林这段六岁时对死亡“召唤”的无助的无名状态伴随着他后来的成长过程。
孙光林的“无名”体现为他的孤独无依,他的“无名”表现为他生存中自我存在认可的丧失,他需要友情去消解这种无名,他需要内心的平静和思考去认可自我的存在。
但他所有的朋友似乎都与他好景不长,苏宇死了,和鲁鲁与国庆的友情不知所终,真正意义上曾给予他父母之爱的王立强和李秀英则由王立强的自杀和李秀英的乘船远去而告终,亲生父母和同胞兄弟则对其采取排斥的政策。
他的无名表现为他人对他存在确认的丧失所引起的自我精神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