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分层与跨层冲突文档格式.docx
《叙述分层与跨层冲突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叙述分层与跨层冲突文档格式.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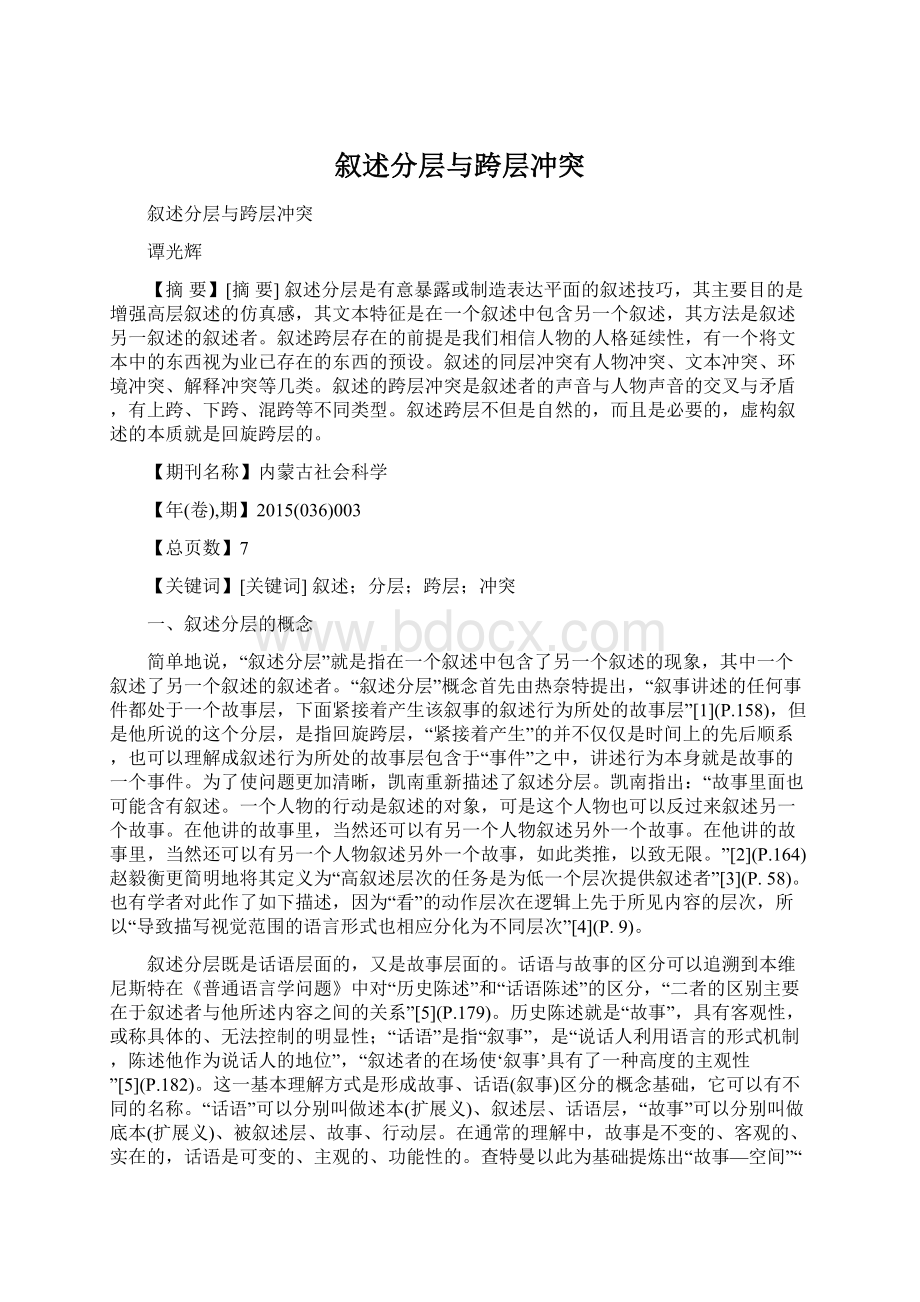
”[2](P.164)赵毅衡更简明地将其定义为“高叙述层次的任务是为低一个层次提供叙述者”[3](P.58)。
也有学者对此作了如下描述,因为“看”的动作层次在逻辑上先于所见内容的层次,所以“导致描写视觉范围的语言形式也相应分化为不同层次”[4](P.9)。
叙述分层既是话语层面的,又是故事层面的。
话语与故事的区分可以追溯到本维尼斯特在《普通语言学问题》中对“历史陈述”和“话语陈述”的区分,“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叙述者与他所述内容之间的关系”[5](P.179)。
历史陈述就是“故事”,具有客观性,或称具体的、无法控制的明显性;
“话语”是指“叙事”,是“说话人利用语言的形式机制,陈述他作为说话人的地位”,“叙述者的在场使‘叙事’具有了一种高度的主观性”[5](P.182)。
这一基本理解方式是形成故事、话语(叙事)区分的概念基础,它可以有不同的名称。
“话语”可以分别叫做述本(扩展义)、叙述层、话语层,“故事”可以分别叫做底本(扩展义)、被叙述层、故事、行动层。
在通常的理解中,故事是不变的、客观的、实在的,话语是可变的、主观的、功能性的。
查特曼以此为基础提炼出“故事—空间”“话语—空间”“故事—时间”“话语—时间”等一系列概念[6](P.81)。
故事就是“内容平面”,话语就是“表达平面”,是叙事结构中的两个部分。
[3](P.130)用一个比喻来说,话语就像一面镜子,述本中的故事就像镜子中映照出来的影像,底本中的故事就像现实世界中的实物。
镜子可能扭曲、放大、缩小、延迟、颠倒实物,所以述本可以重构、扭曲、放大、缩小底本故事的结构、因果、时间。
至少我们可以在观念中有这样一组关系,当我们只注意到镜中的影像而不知道有镜子的时候,在我们的观念中影像就是实存。
当我们注意到这面镜子的时候,就明白了在影像之外还有一个实物,述本之外还有一个底本。
对虚构叙述而言,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有镜子和影像,但是在观念中仍然可以想象出有一个实物,所以虚构故事仍然有一个底本,底本就是这个述本之所以存在的各种可能,虚构叙述的底本是想象。
底本与述本的区分前提是我们注意到了叙述者、话语、叙述层这个“表达平面”,看不见这个表达平面,镜像在观念中就是实存的。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如果只有一面镜子,我们不会认为镜像是分层的。
如果我们通过另一面镜子去看前一面镜子中的影像,而我们又注意到了这两面镜子的存在,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个镜像是分层的。
如果两面镜子互相映照对方,那么镜像就是“无限递归”[7](P.275)的嵌套。
假设把镜子放在一条莫比乌斯带上,并假设光线只能沿莫比乌斯带的曲面传播,那么镜子就可以呈现自己背面的镜像,叙述者就可以处于自己所述的故事之中,这就是回旋跨层。
高层次叙述为低层次叙述提供叙述者的说法就可以理解成“低层次的叙述者被高层次的叙述反映了出来”,因为高层次的叙述即使提供了叙述者,如果没有低层次的叙述,这个叙述者也就不成立。
恰如一个镜像中有一面镜子,而该镜子中空无一物,那么镜像中的镜子就成不了映射者。
“一个故事中的人物也可以反过来叙述另一个故事”的说法就可以理解成“镜像中的镜子分裂出两个功能,它既有一个镜子本身的影像,同时又可以映射一个影像”。
这两个功能,既是合一的,又是可以在观念中分开的。
也就是说,当高层次叙述者在叙述低层次叙述者的时候,他同时处理了该“人物—叙述者”的两个功能。
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把大部分叙述篇幅分给了人物功能,对叙述功能只作提示。
在特殊情况下,他把大部分篇幅分给了该“人物—叙述者”的叙述功能,这种叙述被称为“元叙述”或“元小说”。
恰如一个镜像可以被无数面镜子不断映照一样,任何叙述都可以被无数叙述者不断转述。
由于存在叙述者的可靠性问题,对纪实性叙述而言,被转述次数越多,真实信息丢失的就越多。
这一思维方式可能被移用到对虚构叙述的想象和理解中,因此虚构叙述也就存在叙述者的可靠性问题,而且叙述层次越多,基础层故事的可靠性就越低,虚构感就越强。
在实践中,读者会自然反推:
叙述层次越高,纪实性越强。
所以给虚构故事安排多层次叙述者,修辞效果是越高层次的叙述者越具有仿真感。
综上所述,所谓叙述分层,就是有意暴露或制造表达平面的叙述技巧,其主要目的是增强高层叙述的仿真感,其文本特征是一个叙述中包含另一个叙述,其方法是叙述另一叙述的叙述者。
二、叙述跨层的原则与内涵
不同叙述层次中的人物与事件一般不能交叉,叙述层的人物不能跨入被叙述层,“层次与层次之间,原应属不同世界互不相通,正如神界、阳界、冥界互不相通”[8](P.108),然而叙述跨层却让“属于不同层次的人物进入另一层次,从而使两个层次的叙述情节交织”[3](P.71)。
简单地说,跨层就是让处于表达平面的叙述者——人物进入故事平面的情节之中(下跨)或故事平面的人物进入表达平面(上跨)的叙述方式。
赵毅衡认为,“叙述从定义上说,就是分层的。
但是绝大多数叙述,层次间隔没有被破坏”,所以,虚构叙述“可以跨层,但不一定跨层”,纪实叙述“不太可能发生跨层”。
[7](PP.276~277)也就是说,纪实叙述的跨层从理论上讲不可能,虚构叙述的跨层却非常自然。
按照热奈特的理解,虚构都是转叙,而转叙就是跨层,“转叙就是通过嵌入式叙事、套层结构或者有意暴露自己的身份进入文本的叙事,对故事空间和话语空间进行干扰或者破坏,让读者产生模糊不清的认识,给读者阅读或者阐释叙事意义制造障碍,阻碍读者进入想象世界”[9](译序),所以虚构都是跨层。
只不过,在叙述者没有被暴露的情况下,需要通过二次叙述化才能作此理解。
从表面看,任何叙述都可以跨层。
第一人称叙述好像只能理解成跨层叙述,因为只有处于叙述层的“我”被理解为进入故事层参与情节,或者故事层的“我”参与叙述,才叫做第一人称叙述。
在纪实叙述中,跨层似乎也极其常见。
写日记的时候要先写下日期甚至时刻,还可以写下“我现在开始写日记”这件事情。
历史学家把自己写历史的事写进历史是历史叙述的常用手法,《史记》最后一章“太史公自序”记载了太史公写《史记》这件事。
如果不做一个结构分析,就是跨层叙述。
然而纪实叙述必然有一个现实存在物作为源头,现实存在物不可能真正跨入镜中,镜像不可能跨到现实世界中来。
《史记》中的太史公不可能离开文本另写一本书,因此纪实叙述的跨层是不可能的,若发生跨层也是假象。
有些假象很难判断,记者拍下的被采访者在拒绝拍摄时用手遮挡镜头,或者对记者破口大骂,人物似乎跨入叙述层;
我如实写下老师指导我写这篇作文的过程,作为人物的老师也似乎跨入叙述层。
但是纪实之所以是纪实,正是因为现实与文本之间永远是映射或记录的关系,而不是可以互为因果的关系。
“我”可以被写进文本,但是“我”一旦被写入文本,就被固定下来,被写的“我”不可能再回过头来写该文本。
被录下的采访者可以有遮镜头、骂记者的动作,但是他却不能阻止影片被播出。
若他阻止成功,记录片就没有了。
也就是说,纪实性叙述永远有个现实作为归宿,镜像永远不可真正跨入现实。
庄周梦蝶,在梦中怎么想象都没问题,一旦认为梦中之蝶真的跨入现实,或者认为现实中的庄子就是梦中之蝶的梦中人物,这个跨层就走得太远了。
为了不让虚构与现实之间互相跨层,处于现实中的人必须有一个坚定的现实信仰,不然就会犯病。
李碧华小说《霸王别姬》中的程蝶衣,就是因为没有弄清楚虚构与现实的距离,所以不能把握住现实。
虚构跨入现实让现实变成虚幻,生活可能多了一份诗意,然而会失去理性。
现实与虚构之间不能互跨的原则最难解释的是宗教信仰。
按现实为本的理解原则,神是被叙述出来的,处于被叙述层。
但是在信仰者的心中,神却叙述了现实中的一切,连叙述神的事迹的典籍也是神叙述的。
神既是叙述者,又是被叙述者,被叙述者叙述了叙述者,叙述者叙述了被叙述者,宗教典籍是回旋跨层叙述。
进入其中,现实就被剥离开了,神被视为现实,人反而成了虚构。
所以,立足于现实的叙述学必须划定现实与虚构之间的区隔界线。
虚构永远存在于镜像之中,可以作为现实的参照,但永远不能侵入现实,除非虚构侵入现实的事件本身就是虚构。
忘记这条原则,跨层将无处不在,凡是有叙述,就一定有跨层。
只有我们明白了现实是立身之所,才可以把跨层问题说清楚。
一般说来,在纪实性叙述中,上侵下是可能的,而下侵上是不可能的。
任何纪实叙述都难免带上叙述者的风格特征。
在虚构叙述中,由于并不存在一个可以用于检验的现实,所以无论怎样跨层都很容易被理解。
从本质上说,第一人称虚构叙述就是回旋跨层的,而且是自然而然的,常被忽略。
第一人称叙述相当于抹去了叙述层的标志,自己叙述自己的镜像时并不需要叙述框架,所以我们不会注意到叙述框架的存在。
但是,当第一人称叙述中再出现一个第一人称叙述的时候,框架就会被注意到。
例如博尔赫斯的小说《玫瑰色街角的人》至少有两个叙述层,第一层是“你”来向“我”打听关于雷亚尔的事,第二层是“我”讲的“我”参与了的关于雷亚尔的故事。
两层故事都是第一人称叙述,但是由于第一层叙述主要讲述了“我”作为叙述者的功能,所以“我”的叙述动作被注意到了,该叙述就被自然而然地看作两层。
由于读者相信第一个叙述层中的“我”与第二个叙述层中的“我”具有人格上的延续性,所以第一个叙述层中的人物“我”就被理解成跨层参与了第二个叙述层中的情节。
当第一人称的自然跨层叙述被移用到第三人称叙述的时候,叙述跨层就被强烈地注意到了。
例如《红楼梦》的超叙述层,石头是叙述者,然而在故事层,石头又作为人物参与了情节,由于不是用第一人称叙述,所以我们注意到了这个跨层。
上文说过,只有当我们注意到了镜子的存在,才会注意到底本、述本和叙述层次。
任何第三人称叙述也可以通过叠加一个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实现跨层。
《天方夜谭》中山鲁佐德讲述的故事中的辛巴达是一个第三人称人物—叙述者,在辛巴达叙述的故事中,由于使用了第一人称,他就自然而然地实现了跨层。
以此思路理解第二人称叙述也会发现,第二人称叙述中的受述者“你”也可以自然地进入故事层,轻松自然地实现跨层叙述。
总地来说,实现叙述跨层的前提是相信人物的人格延续性,人物的人格延续性在虚构叙述中的理解是很自然的。
在鲁迅的《祝福》中,“我”叙述了祥林嫂的部分故事,在“我”叙述的故事中又有卫老婆子叙述的关于祥林嫂的故事。
由于在“我”叙述的故事中,卫老婆子和祥林嫂处于同一层面,所以卫老婆子作为叙述者叙述的祥林嫂的故事就要低一层。
然而,由于相信“我”叙述的祥林嫂和卫老婆子叙述的祥林嫂是同一个人,在人格上具有延续性,所以祥林嫂就轻易地跨到了下一层。
用严格的眼光看,“我”眼中的祥林嫂和卫老婆子眼中的祥林嫂虽然不相同,但是这个跨层却十分自然。
结合上文镜子的比喻可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相信“我”拿的那面镜子里面照出了卫老婆子和祥林嫂,而卫老婆子拿的那面镜子中也照出了祥林嫂,我们自然地相信在底本中存在一个完整的祥林嫂。
在虚构故事中,并不存在一个真实的人物或事件来提供情节源头,所有故事和人物都是虚构的,这时我们就只能按各种扭曲变形的镜像去反推一个能够为这些镜像提供源头的“底本”,这个底本被理解成自洽的。
芥川龙之介的《筱竹丛中》,总叙述者的镜子中有数面镜子,每面镜子中照出的影像和故事都不相同,每面镜子也可以被其他镜子映射,实现跨层,似乎每面镜子都在部分撒谎。
面对这样的故事,解释意向性仍然努力重构一个说得过去的底本故事,意向努力的方向和动力,是想象这个没有现实根据性的故事的现实根据性。
跨层叙述之所以可能实现,主要原因是我们自然地把叙述理解为一个具有时间和因果延续性故事的反映。
也就是说,底本是跨层叙述存在的原因。
当述本过于混乱,我们完全没有办法重构底本的时候,跨层叙述就很难被理解。
齐泽克引用拉康的观点指出:
“拉康的观点更极端,‘我们为什么要说故事?
’答案就是:
叙述之所以会出现,其目的就是在时间顺序中重新安排冲突的条件,从而消除根本矛盾冲突。
”[10](P.12)“因此,叙述的形式也正证实了一些被压制的矛盾冲突。
”[10](P.12)“叙述悄悄把它意在再生产的东西预设为业已存在之物。
”[10](P.12)任何叙述,不论是纪实叙述还是虚构叙述,都自然地存在一个将文本中的东西视为业已存在的东西的预设。
如果没有这个“业已存在”的预设作为保证,我们不可能相信《祝福》中“我”讲的祥林嫂和卫老婆子讲的祥林嫂是同一个人,也不可能试图给《筱竹丛中》的矛盾说法一个合理的解释,当然也不可能把《红楼梦》中刻字的石头和变成贾宝玉的石头看作同一块石头,这样的话,当然就不存在“跨层”了。
三、叙述中的同层冲突
与符号的解释过程中存在同层次的元语言或元语言冲突从而形成“解释漩涡”[11](P.241)一样,叙述文本在叙述方面也可能存在叙述层或被叙述层的同层冲突。
叙述冲突和解释/评价冲突在层级上是对应的。
叙述的同层冲突有两种情况,一是叙述平面中的叙述者的自我冲突,二是故事平面中的人物的自我冲突。
关于叙述者的自我冲突,笔者在《叙述声音的源头与叙述主体冲突的类型》一文中已做详细论述,本文从略。
本文只对故事平面中的冲突略作讨论。
人物自我冲突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讨论人物的时候认为“可以将人物分为扁平的和圆形的两种”,扁平人物又可称为“性格人物”“类型人物”或“漫画人物”,“他们最单纯的形式,就是按照一个简单的意念或特性而被创造出来”,“真正的扁平人物可以用一个句子表达出来”。
[12](P.59)对于扁平人物而言,不可能产生自我冲突。
福斯特并没有给“圆形人物”一个严格的定义,但从他的描述中可以感觉出来,圆形人物“我们不能一言以蔽之地去概括”“有改变”“不易回忆”“必给人以新奇感,必须令人信服”。
[12](PP.61~68)事实上,他所说的圆形人物,就是冲突人物,不再单纯,充满矛盾性或多面性。
圆形人物的存在证明,在一个叙述中,产生冲突的不仅可能是叙述者,也可能是对同一个人物的不同解释造成的解释冲突,而且是在人物层面已经具有冲突。
林兴宅在分析阿Q的性格系统时,将其性格分成十组矛盾二十个侧面[13],不是说阿Q性格被解释成这样,而是说阿Q性格中本就存在这些相互矛盾的成分。
在现实世界中,人都不可能是单面存在的,任何人不可能没有矛盾面。
所以扁平人物只存在于虚构世界,其作用是为了表达某种观念或推进情节的发展。
虚构叙述表现圆形人物,是为了追求仿真感,也是为了接近现实的复杂性。
所以虚构叙述表现有矛盾有冲突的人物,就是为了解释现实的复杂性。
人物冲突也可理解成文本中的冲突、自相矛盾。
这种冲突在修辞学上叫做“悖论”。
按照布鲁克斯的说法,“诗的语言是悖论语言”,“诗人要表达的真理只能用悖论语言”。
[14](P.354,355)以此类推,由于文学作品或多或少具有诗性,一部小说若要具有文学性也就必然部分具有诗的特征,那么使用悖论修辞也就在所难免。
事实上,悖论在小说中很常见,例如阿来小说《尘埃落定》写了一个聪明的傻子,还写了一群愚蠢的聪明人。
小说并不避用“聪明”和“傻”这两组形容词,因而可以视为在文本层面安排了这样一组悖论。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也有一组“疯狂”与“清醒”的悖论设置。
在标题中“我”自称“狂人”,但是开篇第一章就写晚上见到月光后“精神分外爽快”,而在他疯狂之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
巴赫金讨论拉伯雷作品的时候所举的例子是13世纪古文集里评述英国的话,“英国最优秀的醉鬼”[15](P.498),由于文本层面设置了矛盾的话语,所以也可以看作文本层面的冲突。
在故事层,人物可能自我冲突,环境也可能冲突。
环境本身的冲突是生态文学的重要主题。
在常规小说中,更多的是人与环境之间的冲突。
有学者认为,“人与环境的冲突是感伤产生的必然性因素之一”[16](P.2)。
因而绝大多数悲剧的社会学根源的分析,都要落脚到人物与环境之间的冲突。
但是对哈代的“性格与环境小说”而言,可能在故事层面就已经具有了人与环境冲突的品质,“哈代以强烈的时空感来表现与人物性格相冲突的活动环境”[17](P.153)。
人物与他人、环境的不和谐和矛盾,正是小说情节的重要组织方式和推动力量。
情节在否定中展开,而一旦否定,就成了冲突,因此故事层面的各种冲突就是故事之所以成立的原因。
除了叙述层和故事层,在解释层也可能发生同层冲突。
即使在故事层面或叙述层面没有明显的冲突,持不同元语言的读者对同一个事件也可能产生两种不同的解释。
乐黛云在留学生课堂上讨论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让留学生们各抒己见。
一位美国学生说,她最喜欢的是三仙姑,最恨的是那个村干部。
这个见解让乐黛云大吃一惊,发现在不同的文化元语言中,理解差异巨大,“我深感这种看法的不同正说明了文化和社会价值观念的不同”[18](P.176)。
在小说中,三仙姑身上具有的冲突不明显,叙述者的冲突也不明显,但是在解释过程中却可能有很大的矛盾冲突。
传统批评一般认为三仙姑是农村中的坏女人,但是留学生却认为她的行为无可厚非。
四、叙述中的跨层冲突
跨层有很多类型,第一类是叙述层的声音侵入被叙述层(下跨),第二类是被叙述层的声音侵入叙述层(上跨),第三类是超出两个层次以上的叙述声音互相交织(混跨)。
自由间接引语本来就是跨层冲突型叙述。
自由间接引语相当于人物的想法或话语由叙述者讲述出来,本来就是两种声音的混合。
例如池莉小说《太阳出世》中的一段:
“这关系到他(赵胜天)的荣誉问题。
他要让街坊邻居,让肉联厂欺侮过他的狗杂种们,让曾经甩了他的那个幼师婊子看看,都看看。
”在这段叙述者话语中,“狗杂种们”“幼师婊子”是人物赵胜天的想法,其反向跨入叙述层语流。
这段话也可以这样理解,整段话都是赵胜天的想法,整段文字都是自由间接引语。
自由间接引语本来就是叙述层和故事层话语冲突的阵地,到底属于上跨还是下跨并不特别清楚,要根据上下文语流判断。
语流往往是感觉层面的。
例如一段叙述人物活动的情节,话语应该视为叙述者的话语。
但是在故事进行过程中,读者常常会忘记这是叙述者的话语而专注于故事本身,若此时在叙述语流中插入一段评论,就会让读者注意到叙述者的存在。
这种情况通常被称为“叙述者干预”[3](P.35)。
“对叙述形式的干预可以称为指点干预;
对叙述内容进行的干预可以称为评论干预。
”[3](P.29)除了这两者,叙述层的风格也可能进入故事层,让人物的话语带上叙述层话语的特点,可以称为风格干预。
中国古代文言小说,不论人物身份如何,说的都是文言,话语风格与叙述层的风格一样。
在现代小说中,叙述层的风格也可能进入人物话语,使人物成为叙述者的代言人。
简单地说,转述语带上叙述语风格可以视为风格干预。
各种叙述者干预都是上侵下的跨层,相当于叙述者下跨到故事层作为一个人物发言。
在第一人称虚构叙述中,由于作为叙述者的“我”与作为人物的“我”不仅有结构上的差异,还存在时间上的差异,即“二我差”,在故事迫近叙述时刻之前,“同一个‘我’,作为叙述者,作为人物,两者之间会争夺发言权,形成主体冲突”[7](P.158),常常出现两个“我”的声音互现的情况。
林白《一个人的战争》第三章“随意挑选的风景”中有这样一段:
“这是我此生的一次壮举。
我独自一人,自始至终。
我意识到,再也没有比一个年轻女人独自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更危险、更需要勇气的了。
”“此生”“自始至终”涉及时间是对一生的评述,所以是叙述者的声音。
“我意识到”不是现在的“我”意识到,而是“当时的我”意识到,所以是“当时的我”的声音。
当两个声音混在一起时,就产生了叙述层中的“我”和故事层中的人物“我”的冲突。
当然,由于没有明确的提示,这个理解也可能颠倒过来。
在语流中,由于此段讲述的是曾经的“我”的故事,所以可以看作上跨下。
在更多的时候,第一人称叙述经常出现两个声音交替的情况。
申丹认为,“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无论‘我’是主人公还是旁观者),通常有两种眼光在交替作用”[19],其实交替出现的不仅是眼光,还有声音。
王小波《黄金时代》的叙述视角有时是人物“我”的,例如“看了她的样子,我就开始捉摸:
她那件白大褂下是穿了点什么呢,还是什么都没穿”,因为有“捉摸”的动作,所以视角是人物的;
有时是叙述层中的“我”的,例如“倒退到二十年前,想象我和陈清扬讨论破鞋问题时的情景。
那时我面色焦黄,嘴唇干裂”,因为是“想象”,所以视角是叙述者的;
有时不清楚是哪个层次的,例如“春天里,队长说我打瞎了他家母狗的左眼,使它老是偏过头来看人”,视角既可以理解成叙述层的,也可以理解成人物层的。
也就是说,判断第一人称叙述声音来自哪里,要靠提示语,如果该叙述没有提示语,就只能靠视角方位判断,若视角方位也没有,就不知道声音来自哪里。
在有明确提示语的时候,可以认为第一人称叙述是没有主体冲突的,在没有明确的提示语的时候,叙述者和人物的声音就是冲突的,它混合了两个主体的声音。
然而,因为第一人称叙述被设想成有一个现实中的“我”作为真实性保障,所以会被自然地设想为更具真实感,因而纪实性叙述使用第一人称就非常普遍,哈特甚至认为“很难想象一篇个人散文中没有第一人称”[20](P.64)。
由于第一人称叙述具有天然的跨层性质和与纪实叙述的姻缘关系,所以常常难以分清是叙述者干预还是人物抢话。
在第三人称叙述中,叙述层和故事层争夺话语权的情形就显得更为明显。
许地山《缀网劳蛛》中,尚洁许多带有哲理的话语都不是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知识的妇女能够讲得出来的,读者能够明确地感觉到叙述者通过尚洁之口道出了宗教的说辞。
其中有一段尚洁的话:
“我很愿意你把这事的原委单说给史先生知道。
至于外间传说我和谭先生有秘密的关系,说我是淫妇,我都不介意。
连他也好几天不回来啦。
我估量他是为这事生气,可是我并不辩白。
”在尚洁的话语中,“原委”“外间”“估量”“辩白”都太书面化,是叙述者的语气,而不是人物的自然语气。
这种话语方式说明,叙述者希望读者按照人物的话语去理解叙述者的意图,或者是写小说的技巧不到位,不能使用有个性色彩的直接引语。
第二种冲突形式是故事层中人物的话语或风格进入叙述层,例如人物的话语风格侵入叙述语风格,让叙述语仿佛是人物说出来的。
如果叙述语中出现大段的人物话语,很容易辨认出来。
如果“某些个别形容词或副词,突然采用了只有人物才会用的某种语汇”,就是“抢话”。
[7](P.253)抢话可以视为“一种简短的间接自由式引语”,是典型的下跨上式冲突。
与视角人物语言比较起来,主要有一个长短、主次的区别。
例如鲁迅《药》中:
“老栓看看灯笼,已经熄了。
按一按衣袋,硬硬的还在。
仰起头两面一望,只见许多古怪的人,三三两两,鬼似的在那里徘徊;
定睛再看,却也看不出什么别的奇怪。
”整个叙述语流是叙述者的,然而有些形容词或句子也可以理解成是来自人物的视角或声音。
“已经熄了”,既可以看作是叙述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