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新吏学碰撞Word文件下载.docx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新吏学碰撞Word文件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新吏学碰撞Word文件下载.docx(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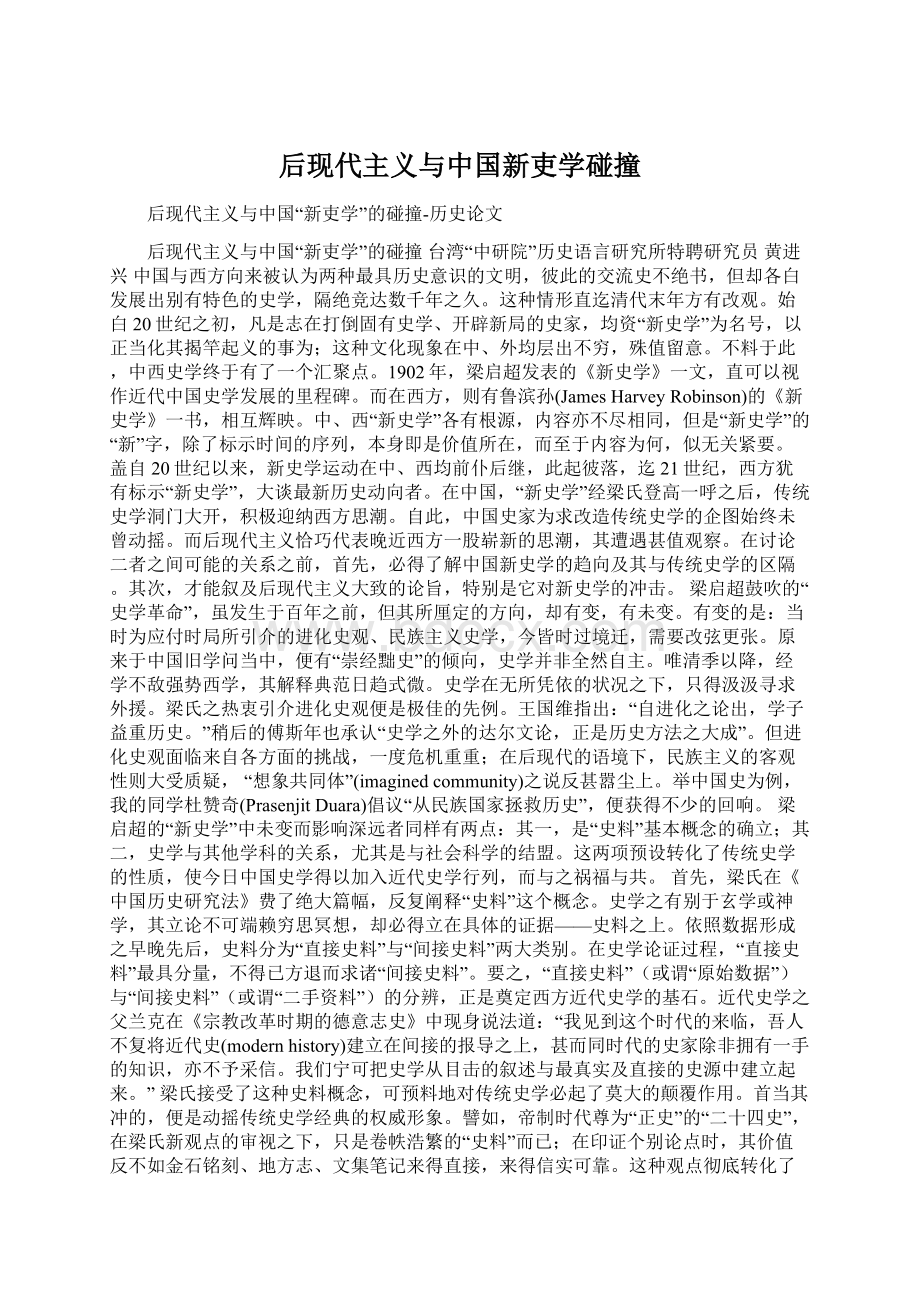
当时为应付时局所引介的进化史观、民族主义史学,今皆时过境迁,需要改弦更张。
原来于中国旧学问当中,便有“崇经黜史”的倾向,史学并非全然自主。
唯清季以降,经学不敌强势西学,其解释典范日趋式微。
史学在无所凭依的状况之下,只得汲汲寻求外援。
梁氏之热衷引介进化史观便是极佳的先例。
王国维指出:
“自进化之论出,学子益重历史。
”稍后的傅斯年也承认“史学之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
但进化史观面临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一度危机重重;
在后现代的语境下,民族主义的客观性则大受质疑,“想象共同体”(imaginedcommunity)之说反甚嚣尘上。
举中国史为例,我的同学杜赞奇(PrasenjitDuara)倡议“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便获得不少的回响。
梁启超的“新史学”中未变而影响深远者同样有两点:
其一,是“史料”基本概念的确立;
其二,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尤其是与社会科学的结盟。
这两项预设转化了传统史学的性质,使今日中国史学得以加入近代史学行列,而与之祸福与共。
首先,梁氏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费了绝大篇幅,反复阐释“史料”这个概念。
史学之有别于玄学或神学,其立论不可端赖穷思冥想,却必得立在具体的证据——史料之上。
依照数据形成之早晚先后,史料分为“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两大类别。
在史学论证过程,“直接史料”最具分量,不得已方退而求诸“间接史料”。
要之,“直接史料”(或谓“原始数据”)与“间接史料”(或谓“二手资料”)的分辨,正是奠定西方近代史学的基石。
近代史学之父兰克在《宗教改革时期的德意志史》中现身说法道:
“我见到这个时代的来临,吾人不复将近代史(modernhistory)建立在间接的报导之上,甚而同时代的史家除非拥有一手的知识,亦不予采信。
我们宁可把史学从目击的叙述与最真实及直接的史源中建立起来。
”梁氏接受了这种史料概念,可预料地对传统史学必起了莫大的颠覆作用。
首当其冲的,便是动摇传统史学经典的权威形象。
譬如,帝制时代尊为“正史”的“二十四史”,在梁氏新观点的审视之下,只是卷帙浩繁的“史料”而已;
在印证个别论点时,其价值反不如金石铭刻、地方志、文集笔记来得直接,来得信实可靠。
这种观点彻底转化了中国近代史学的评断。
柳诒征说:
“吾国诸史仅属史料,而非史书。
”便是明证。
更有甚者,梁氏将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疏通成“六经皆史料”,以方便衔接西方史学。
上述的“史料”概念实为中国新一代史家所共享。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19)中,批评“中国人作史,最不讲究史料”,职是,特别强调:
“审定史料乃是史学家第一步根本工夫。
西洋近百年来史学大进步,大半都由于审定史料的方法更严密了。
”反过来,他批评传统的中国史书:
“神话、官书都可作史料,全不问这些材料是否可靠,却不知道史料若不可靠,所作的历史,便无信史的价值。
”值得指出的是,在《中国哲学史大纲》所列“史料审定及整理之法”参考书目中,胡适建议阅读的正是同样为梁氏所取资的朗格诺瓦(CharlesVictorLanglois)与瑟诺博司(CharlesSeignobos)合著的《史学原论》英译本。
要知《史学原论》与伯伦汉(ErnstBernheim)的著作在西方史学具有同等的份量,均代表兰克史学于世纪之际的再兴。
此外,受业于胡适、复为兰克史学的践行者傅斯年,更直截了当地宣称:
“近代的史学只是史料学。
”他认为:
“史的观念之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做客观的史料学。
”换言之,“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
傅氏对“史料”极端重视,毋怪后人径以“史料学派”标示他所领导的“史语所”。
世纪之交,梁氏等诸贤敞开胸怀,迎纳西方史学,不料却让自身陷中、外史学的双重危机。
一方面,传统史学固不敷应付世变日亟的时局,而必须引进西方史学,然而后者复逢西方新兴社会科学的挑战,窘态乍露。
故梁氏乃不得已移樽就教,认为“史学,若严格的分类,应是社会科学的一种”,决心将中国史学带离传统的“四部”(经史子集)之学,正式加盟西学阵营。
早在《新史学》一文中,梁氏便批评中国史学“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他学之关系”。
他认为与史学有“直接关系”的学科,相当于今日的社会科学;
有“间接关系”的就是哲学与自然科学。
与傅斯年同为兰克史学代言人的姚从吾,也认识到其他科学对历史研究的益处,他说:
“觉Ranke及Bernheim的治史,实高出乾嘉一等。
他们有比较客观的标准,不为传统所囿。
有各种社会自然科学的启示、指导,可以推陈出新。
”这种认识在当时的历史学界相当普遍,举其例,清代的章学诚在民初获得极高评价,备受中外名家诸如日人内藤湖南、胡适等所推崇,但吕思勉于比较章学诚与今日史家的异同时如是评道:
他(指章学诚——引者注)的意见,和现代的史学家,只差得一步。
倘使再进一步,就和现在的史学家相同了。
但这一步,在章学诚是无法再进的。
这是为什么呢?
那是由于现代的史学家,有别种科学做他的助力,而章学诚时代则无有。
依吕氏之见,章学诚的史学造诣与现代史学所差无几;
唯现代史学的进步乃拜别种科学之赐。
而在诸多科学之中,社会科学尤为“史学的根基”。
简言之,踵继梁氏而起的新史学,大致遵循“史料优先”及“以客(社会科学)为尊”的两大方向发展。
前者固可强化传统学术,尚不致威胁正规的历史研究;
然而迎门接纳代表西学的社会科学,却是地道的“城下之盟”,极大斫伤了史学的自主性。
试举倡导以行为科学(behavioralsciences)治史的比克霍福为例,他便明确主张:
“人作为分析的单元,只能透过某些概念架构去研究,一旦取得了人类行为的知识,其他史学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观此,史学遂仿若失去半壁江山,只得拱手让出解释权,沦为资料整理的工具罢了。
20世纪中国“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大概只能用“夸父追日”堪以道尽其中原委。
中国史学结盟社会科学,不意令自身陷入西学的轮回而无法自拔。
鉴诸台湾六七十年代流行的行为科学,在在证明所言不差。
然而西方的社会科学在这段时间内突然弊病丛出,危机重重;
其反思的结果,竟是后现代主义的产出。
这对牺牺惶惶的中国新史学而言,不啻雪上加霜。
1980年代之后,两岸骤然必须同时面对西潮崭新一波的冲击,此无他,便是后现代主义的来临。
简言之,“后现代主义”的来源不一,最早见诸20世纪50年代西方的文学与建筑评论,60年代方在哲学与思想园地发荣滋长,70年代以降便席卷社会科学,史学则殿其后,方受波及;
而中国史学则尤在其后。
顾名思义,后现代主义旨在颠覆或取代“现代主义”(modernism),而中外“新史学”恰是“现代性”(modernity)所孕育的智识产物,遂成为其所攻讦的对象。
后现代史学的追随者动辄大放厥词:
“历史乃是西方的神话。
”或者放声喧嚷:
“历史的死亡。
”必须指出的是,他们所谓的“历史”,意指一切非经由后现代程序所制造出来的史著。
后现代史家采取的正是“彼可取而代之”的态势。
后现代史学的祭酒——福柯于1969年刊行《知识考古学》,该时的书评者立谓“敲响了历史的丧钟”,似乎语不惊人誓不休。
这对正规史家而言,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纵使他们刻意排斥或回避后现代主义的挑衅,但是后现代主义的语汇业已充斥坊间的历史写作。
举其例:
“文本”(text,巴尔特)取代了“作品”(work),“论述”(话语)(discourse.福柯)取代了“解释”(explanation),“空间”(space)取代了“时间”,“间断性”(discontinuity)取代了“连续性”(continuity),“解构”(deconstruction,德里达)取代了“结构”(structure),“修辞”(rhetoric,怀特)取代了“论证”(argument),“书写”(writing,德里达)取代了“阐释”(interpretation),诸如此类,俯拾即是。
可见后现代主义的渗透力,无远弗届。
尤有过之,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研究正面的冲击,仍然有二:
其一,解消“后设叙述”(meta-narrative);
其二,“语言的转向”。
后现代哲学家利奥塔厘定“后现代”乃是对“后设叙述”的质疑;
其界义适可运用到史学领域,“后设叙述”,在史学上又可谓之“大叙述”(grandnarrative),诸如:
民族史观、进步史观、马克思史观等等。
它们均难脱本质论(essentialism)或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的色彩,而具有线性发展与目的论的特征。
职是,受后现代主义所影响的史学,动辄推崇“小叙述”的“微观史学”(microhistory),“大叙述”则受到贬抑。
直接受冲撞的,便是法国年鉴学派所鼓吹的“整体史”(totalhistory)了。
在中国史领域,前述杜赞奇力图从民族国家的神话“拯救历史”,便与俞旦初所阐扬的爱国主义的民族史学,形成鲜明的对比。
而台湾史家沈松侨受此氛围启示,解构了“黄帝”的民族神话,则是这方面别开生面的代表作。
换言之,后现代史家强调分歧(diversity)与异质性(heterogeneity);
遂将整体的大历史(history),裂解为多元分化的小历史(histories)。
同时,“后现代史学”一反实证史学,遂行了“语言的转向”。
从史学方法的角度观察,“语言的转向”促使史学进行一系列的回归,从史实至语言、从语言至文本,最后从文本至符号,其结果则是将语言和经验完全隔绝。
巴尔特就说:
“事实无它,仅是语言性的存在,”德里达亦附和道:
“文本之外,别无它物。
”封闭的文本论,令历史不再指涉过去;
而失去对外的指涉性,历史变成自成一格的符号游戏。
从解读的角度,巴尔特“作者之死”(TheDeathoftheAuthor)的观点,迥异于往昔阅读文本的取径,令“读者”的诠释凌驾于“作者”与“作品”之上。
无独有偶,德里达的“解构”及“书写”概念,进而摧毁了“史源中心观点”,标榜独树一帜的历史进路。
上述观点如果落实至史学操作,便是测试史料与历史解释的限度。
倘纯依循读者观点,师心自用似乎难以避免。
试举近年中、西史学中喧腾一时的争论,环绕《魏玛共和国的崩溃》和《怀柔远人》(CherishingMenfromAfar,1995)两部著作的论辩,便代表“现代”与“后现代”史学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策略,而后现代的解读似逃脱不了望文生义的指控。
“望文生义”,析言之,即是符号学家艾柯(UmbertoEco)所谓的“过度诠释”(overinterpretation)。
“过度诠释”肇自解释漫无准则,以致言人人殊,背离了语言“沟通”(communication)的基本宗旨。
严格言之,上述两部著作连德里达所提示的“文本注疏”(commentary)和“批判阅读”(criticalreading)的程序,都难以通过。
推其极致,甚至有“语言决定论”(linguisticdeterminism)之虞!
举例来说,刘禾在开发“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practice)的文化现象方面甚有建树,但她把帝国的实质冲突归诸语言诠释的问题,则未免不太相称(outofproportion)!
她在解释中英《天津条约》的交涉时说道:
通过挖掘这个衍指符号诞生的轨迹,我们会看到语词的冲突绝非小事,它凝聚和反映的是两个帝国之间的生死斗争,一边是日趋衰落的大清国,另一边是蒸蒸日上的大英帝国。
谁拥有对“夷”这个汉字最后的诠释权,谁就可以踌躇满志地预言这个国家的未来。
观此,语言不止是“存有的殿堂”(thetempleofbeing),并且变成“语言的牢房”(theprison-houseoflanguage)。
攸关历史知识的性质,后现代史学系持“建构论”(constructivism)的立场。
意即:
史家旨在拟构历史,而非发现历史。
“逝者已矣!
”(Whatispastispast!
),后人已无法再知晓真实的过去。
所谓的“历史”也不过是人类心智当下意识的产物。
毋怪怀特会借道“语艺学”(poetics),抛出“历史若文学”(historyasliterature)的论点。
而历史既然允纳虚构,史实的客观性与可知的过去,遂成过眼云烟!
不止西方后现代史学有此现象,连中国史亦受到此类观点的渗透。
汉学名家史景迁(JonathanD.Spence)的《胡若望的疑问》(TheQuestionoHu,1989),固以叙事著称,驰骋于史料与想象之际,极尽文艺之能事。
然而传统史家却拒之于千里之外,视该书仅与“小说”相埒,竞未得入列“历史小说”之林。
总之,“文史不分”或者允纳“虚构性”(fictionality),皆是与历史的实在论(historicalrealism)大唱反调,更与中国传统的“秉笔直书”及西方“陈述事实”的史学精神大相径庭。
况且,后现代史学祛除历史知识的指涉作用,不啻就瓦解了自身鉴古知今的功能;
因此除了美学的意义,历史则变为无用论。
归根结蒂,后现代史学呈现有“语言迷恋”(linguisticobsession)或“文本崇拜”(thefetishismoftext)的倾向。
后现代的阅读观点只着重符号或文本的“示意作用”(signification),而鲜少措意“沟通”与“效度”(validity)的问题。
典型的示例,便是克莉斯娃(JuliaKristeva)的文本观。
他们但求其异而略其同,似乎遗忘了维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长久以来的教诲:
莫让语言对我们的智力产生迷惑。
完全自足的文本论就仿佛“缸中之脑”(brainsinavat)无所指涉(non-referentiality),因此就不具有任何经验的意义。
晚近语言哲学的探讨复指出,“语言”得以指涉实在(reality)乃吾人知晓任何语言的先决条件(precondition)。
是故,在“语言转向”后,即激起一股返归经验的浪潮,他们固然承认语言的媒介作用,但坚持“经验的不可化约性”(irreducibilityofexperience)。
毋怪晚近的“后一后现代主义”(post-postmodernism)不少人出自重视“硬事实”(hardfacts)的马克思阵营。
也因此,后现代史学只能着力于思想史与文化史的言说层面,而难以逾越雷池(若经济史)半步。
况且,后现代史学经常陷入自我矛盾,一方面他们攻讦“后设叙述”,另一方面在分期上,他们却口口声声断定当前正由“现代主义”迈入“后现代主义”,这难脱“后设叙述”之嫌。
人类学家列维一斯特劳斯说得好:
过去原为杂乱无章的数据(data),本身并无任何意义,而史书的叙述轮廓悉由史家所施加。
换言之,历史的叙述总是因时制宜的权宜之计,故只要符合实情,大、小叙述皆宜。
若由实在论出发,则叙述之大小固与实存经验攸关,非全由史家片面所能决定。
套句詹明信(FrdricJameson)的说词,后现代主义,说穿了,也只是“后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自然有其局限。
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复曾经如此开示过:
“每一种主义都是对历史的误解与死亡。
”总之,后现代主义虽有其偏颇之处,但绝非一无是处,譬如它能激发史家的省思,重新去思考文本与史实之间的关联;
再者,在开发新的史学领域尤功不可没;
例如后现代史学的祭酒福柯,其开发历史议题的能量(诸如医疗史、法政史、心理史等),无人可望其项背;
连他的敌对者都不得不称赞他乃是近三十年社会史的泰山北斗。
是故,不可一概抹煞。
至于中国新史学与后现代主义,究竟又是一次短暂的流行际遇,或则会散叶开花,留下较恒久的结果,吾人则可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