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雇工统计数据家庭农场农业企业家庭化的生产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农业雇工统计数据家庭农场农业企业家庭化的生产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农业雇工统计数据家庭农场农业企业家庭化的生产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1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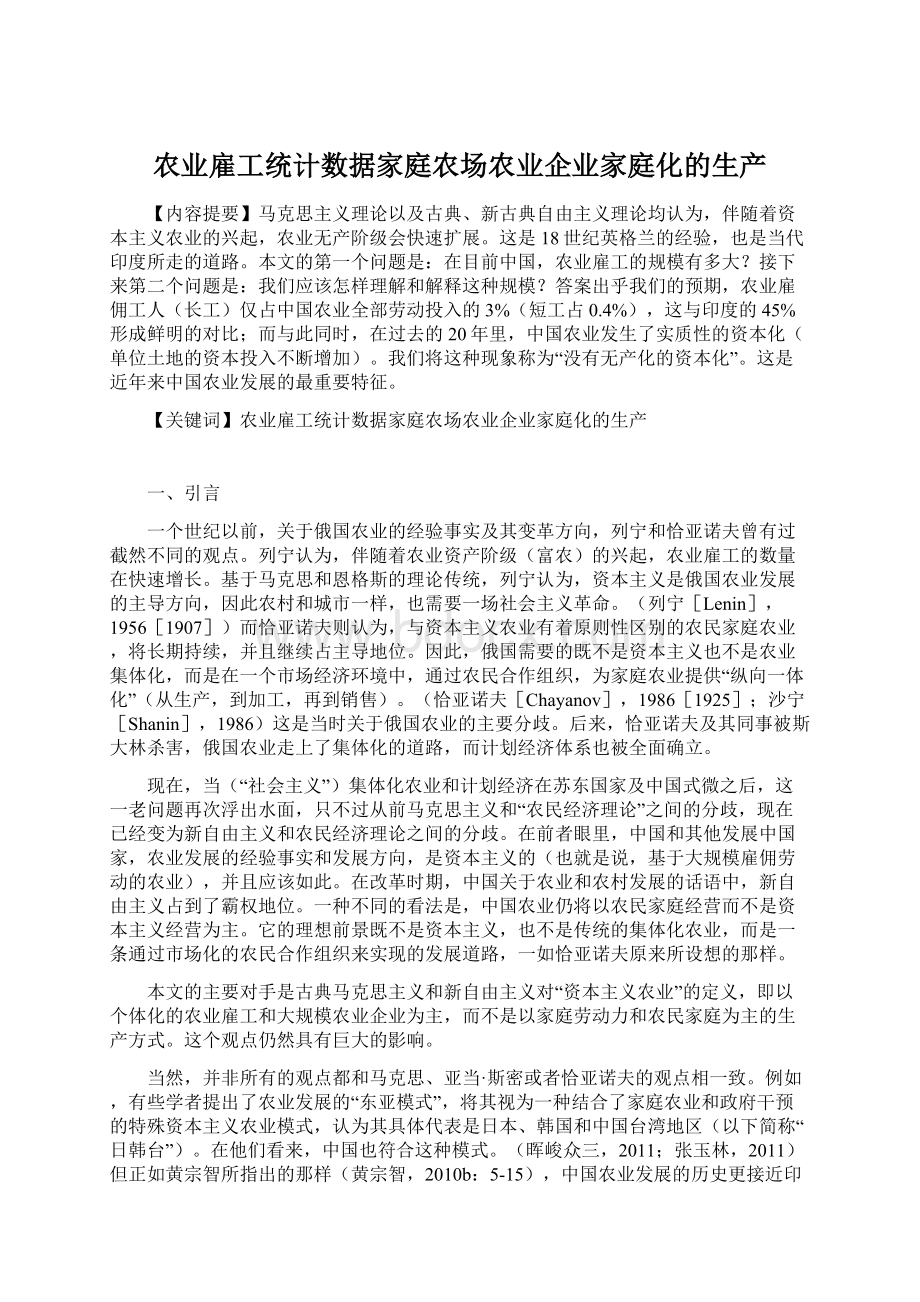
在前者眼里,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的经验事实和发展方向,是资本主义的(也就是说,基于大规模雇佣劳动的农业),并且应该如此。
在改革时期,中国关于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话语中,新自由主义占到了霸权地位。
一种不同的看法是,中国农业仍将以农民家庭经营而不是资本主义经营为主。
它的理想前景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传统的集体化农业,而是一条通过市场化的农民合作组织来实现的发展道路,一如恰亚诺夫原来所设想的那样。
本文的主要对手是古典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对“资本主义农业”的定义,即以个体化的农业雇工和大规模农业企业为主,而不是以家庭劳动力和农民家庭为主的生产方式。
这个观点仍然具有巨大的影响。
当然,并非所有的观点都和马克思、亚当·
斯密或者恰亚诺夫的观点相一致。
例如,有些学者提出了农业发展的“东亚模式”,将其视为一种结合了家庭农业和政府干预的特殊资本主义农业模式,认为其具体代表是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以下简称“日韩台”)。
在他们看来,中国也符合这种模式。
(晖峻众三,2011;
张玉林,2011)但正如黄宗智所指出的那样(黄宗智,2010b:
5-15),中国农业发展的历史更接近印度,而不是日韩台。
从1720年开始,日本已经进入了人口增长缓慢的时期(HanleyandYamamura,1977),而且,在现代化要素投入开始被引入农业的1890年~1960年间,日本强劲的工业增长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以至于这一阶段其农业人口数量基本保持不变。
这与中国有很大的不同。
至于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它们都经历了20世纪60和70年代的“绿色革命”(主要是化肥、科学选种以及机械的应用,这些现代化要素投入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并由此跃入持续的工业化。
而十分不同的是,在中国,现代化投入为农业带来的产出增长几乎都被人口的增加所蚕食掉。
(下文将进一步讨论。
)其后,在东亚模式的典范日本,农业人口缩减到总人口的10%以下。
虽然家庭农业仍然持续着,但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农业大规模扩展,远远超过了中国。
在人口压力以及农业负担问题上,中国其实更接近印度。
而且,在20世纪50年代(现代化的要素投入即将被引入农业的前夜),中国和印度的人均GDP大致相同,比同期的日韩台要低得多。
(黄宗智,2010b:
5-15)因此,本文将主要讨论中印之间的比较,但也会对中国与所谓东亚模式之间的不同做一定的讨论。
摆在我们面前的首先是一个经验的问题。
在目前中国,基于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农业到底有多大的规模?
中国农业正在向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我们如何理解和解释经验研究所得出的基本事实?
二、数据
在中国的改革“转型”期,毛时代的旧有修辞和新自由主义的实践与论述糅杂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混合。
旧有修辞中一切关于“阶级斗争”的话语都被清除出去(伴随着对“文革”的彻底否定),同时,新自由主义实践及其话语则被安置在“市场社会主义”的范畴之下。
这种混合的一个结果是,在官方统计数据中,阶级和生产关系几乎被完全忽视。
因此,农业雇工并不作为一个统计指标而存在;
庞大的、从事非农业的农民工也同样不存在。
统计意义上的工人,仅指那些(正规的)“职工”。
(“职工”这一统计范畴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个遗迹,当时认为资本主义阶级关系已经被消除,白领和蓝领工人之间的区别也不复存在。
)“劳动”和“劳动者”被限定为工业领域(即“第二产业”,以与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相区分)规范的、正式的职工(经过官方注册,并且享受法律保护和各种福利)。
因此,在关于“劳动”的统计年鉴中,没有关于“非正规”的农民工的信息(《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7》)。
但我们知道约有1.5亿户籍登记为农民身份的人远离家乡在城市工业和服务业中劳动,通常被描述为“离土又离乡”的农民。
此外,还有约1.5亿农民在家乡附近从事非农劳动,通常被描述为“离土不离乡”的农民。
这些劳动者一般承担着最重、最脏的劳动并且获得最低的报酬。
和正规职工相比,他们基本不享受法律保护,没有或者只有较低的福利。
上述的事实,不是来自官方常用指标的统计,而是来自它们之外的研究。
(《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0;
一个总结性的讨论参见黄宗智,2009;
亦见黄宗智,2010a)
今天,“农民”仍然是职工和/或劳动者之外的一个独立和分明的统计范畴。
早前,农民曾被概念化为村庄集体的成员;
现在则主要指那些被政府正式登记为农村居民的人——即使社会现实是这些人中存在巨量非农就业。
对于那些仍然留在农业中劳动的人,官方将其标示为“农业从业人员”。
农业雇工,和城市、乡镇中的农民工一样,并不作为一个统计范畴而存在。
在一定程度上,统计数据的缺失导致了农业雇工研究的匮乏。
对学术文献的搜索表明,国内基本没有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
在2011年8月下旬,我们通过中国知网(CNKI)对“农业雇工”这一关键词进行检索共得到38条项目,其中大部分是历史研究,只有6项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当代;
其中没有一项研究对某地农业雇工的规模进行数量估计,更不用说区域性或者全国性的数量估计了。
然而,通过田野研究,通过书刊文献的间接描述,以及通过个人的生活经验、观察和记录,我们知道,今天中国存在着相当数量的雇佣农业劳动。
至于准确数字,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想象,往往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
经典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支持者倾向于夸大雇佣劳动以及“资本主义农业”在目前中国的比例。
有些观点和列宁勾勒出的那幅图像非常接近;
而有些观点则甚至认为,大型的、资本主义化的农业企业(跨国公司或是本土企业),正在席卷全国。
那些质疑正统马克思主义或者新自由主义观点的人,则倾向于走向另一个极端——低估或是干脆无视资本主义农业。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得到一幅更为系统的图像呢?
通过对现有统计资料的检阅,我们认为较为可信的数据是存在的,但我们需要从中国庞大的统计机构所积累的大量统计信息中去挖掘这些有用的数据。
其中,一种较为有用的资料是一年一度的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统计,它们是基于全国1553个县的60000户农户定点调查所编汇而成的。
(《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10》:
“编者说明”第二条)该资料包含调查户的用工信息,在各类农产品的成本收益栏目中,以播种面积、产量的“平均”雇工费用(元)或劳动日投入出现,与家庭劳动投入并列。
①
利用这些数据,我们能够得出调查户在各种农产品的生产中的雇工投入占全部劳动投入的比例,进而可以估计在全部农业劳动投入中雇佣劳动可能占到的比重。
表1和图1给出了五种主要农产品的生产中雇佣劳动在总劳动投入(以天数计算)中的比重。
这五种有系统数据的农产品包括:
谷物(三种主要谷物水稻、玉米和小麦的平均,2009年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占全国农产品总播种面积的68.7%),蔬菜(占总播种面积的11.6%),花生和油菜籽(占7.4%,油料作物一共占8.6%),棉花(占3.1%),苹果(占1.5%,作为所有瓜果的一种近似)。
容易看到,对于谷物(最大的一类农作物,占总播种面积的68.7%)而言,雇佣劳动还不到总劳动投入的5%,而且在过去的10年间没有表现出任何实质性的增加。
对于蔬菜(第二大类农作物,占总播种面积的11.6%),雇佣劳动在过去10年间有明显增加(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在城市和交通线附近,“劳动—资本双密集”的“温室”(多是塑料拱棚)蔬菜种植有较大的发展(黄宗智,2010b),但其在全部劳动投入中所占比重,也仅有8.5%。
这是因为蔬菜生产仍然主要是由家庭经营实现的,这种生产需要高密度的、细腻的、不定时的劳动投入。
(黄宗智,2011b;
亦见下文)典型的使用雇佣劳动的经营模式是,夫妇二人雇佣一两个短工。
对于油料作物(第三大类农作物,占总播种面积的8.6%),雇佣劳动占总劳动投入的比例同样很低,在过去10年里维持在1%~3%的水平。
对于棉花(第四大类农作物,占总播种面积的3.1%),过去10年里雇佣劳动占比有显著上升。
调查户种植棉花所投入的雇佣劳动现已占全部劳动投入的7%。
部分原因可能是最近几年新疆新棉田的大开发——从1996年占棉花种植总面积的24%扩增到2006年的41%。
(《中国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综合提要》,2008:
7-2-8)因为在新疆土地相比人力更加富裕,所以足有1/4的农场规模在100亩以上,同时有较大数量的雇佣劳动存在(雇佣单个雇工的费用也比其他地区高)。
然而即便如此,雇佣劳动仍然多是季节性的短期雇工,其主要工作是采摘棉桃。
家庭农作仍占主导地位。
(毛树春,2010)
唯一一个雇佣劳动投入有显著增长的例子是苹果(这是唯一一种有系统数据的水果,占总播种面积的1.5%)。
2009年,雇佣劳动占全部劳动投入的比例达到了40%。
这部分是因为山区的苹果地有时候是大片承包的(但也有平均分配给所有农户的),还因为高价值品种的扩展需要较密集的劳动投入——比如为苹果套上果袋以增加质量和外观。
同时,采摘苹果也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参见韩文璞,2011)但苹果生产中雇佣劳动的大量增加不应被过于夸大,因为其播种面积仅占1.5%。
高价值蔬菜和水果种植的扩展是中国“隐性农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样一场革命,在过去30年里使农业总产值增长了将近6倍(以可比价格计算)。
它背后的动力,主要是人均收入增长带来的对高价值农产品的消费增长。
黄宗智使用“隐性农业革命”这一概念来描述上述现象,以与传统意义上基于同一种作物绝对产量的提高所呈现的“农业革命”相区别。
后者的代表有广为人知的18世纪英格兰农业革命,以及更为晚近的20世纪60和70年代的“绿色革命”(中国在60和70年代也经历了自己的“绿色革命”)。
最近的这场“隐性农业革命”并非来自于某种特定作物产量的增长,而是来自于中国居民食品消费结构的根本性重构(以及这种重构所带来的农业结构转型)——从谷物—蔬菜—肉类之比例为8:
1:
1的结构向4:
3:
3的转变。
(黄宗智、彭玉生,2007;
黄宗智,2010b:
第6章;
黄宗智,2010c;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1》:
表6-22)
日益发展的畜禽饲养是“隐性农业革命”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图2给出了几种主要畜禽产品的生产中雇工占全部劳动投入的比例。
首先考察三种主要的肉类——猪肉、家禽和牛肉(按重量计各占2009年全国肉类总产出的64%、21%、8%[亦即共93%],《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0》:
7-38,7-40)对于生猪饲养而言,在有系统的、可比较的数据的过去5年间,调查户雇工占全部劳动投入的比重,波动于6%~8%之间。
典型的生猪饲养模式是,一个小规模家庭农场以传统的方式饲养一两头猪,利用残羹剩饭作为猪只的吃食,这种饲养方式叫做“散养”。
“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中所谓的“规模生猪”(其统计标准为饲养规模在30头以上,参见《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10》:
附录一、附录三),仍然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家庭经营进行的——规模生猪饲养中家庭劳动约占全部劳动投入的2/3。
这种规模生猪饲养,如我们所见,仅将全部生猪饲养中雇佣劳动所占比例提高到了2009年的8%。
对于牛肉生产,“资料汇编”中仅有“散养肉牛”的数据,其雇佣劳动所占比例在2009年仅为5%。
(《中国畜牧年鉴2010》:
205)②对于肉鸡(禽肉中最主要的一项)而言,“资料汇编”中不存在不分规模的所有肉鸡饲养的数据,因为散养户不易统计。
③但即便是“规模肉鸡”这一项目,雇工所占比例也从2004年的22.5%下降到2009年的15%,这显示出家庭养鸡的顽强生命力。
基于一些零碎的质性资料,我们可以了解到,即使是大规模的养鸡或蛋公司,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和散养农户签订合同来进行饲养,而不是集中于大规模的农场来饲养。
(《中国农业产业化发展报告》,2008;
亦见黄宗智,2011c)总而言之,和农作物种植一样,在肉类生产中,家庭劳动同样占据主导性地位。
另外两种重要的畜禽产品奶类和蛋类(2009年总产量为6500万吨,相较于肉类的7600万吨,《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0》:
7-40,7-41),因为对标准化生产有着更加严格的要求,资本主义经营有较大的扩展。
如图2所示,奶牛饲养中,2009年,28%的劳动投入属于雇佣劳动。
蛋鸡饲养中,2005年雇工投入占到30%以上,但在2009年则下降到27%。
(这也再次说明了使用家庭劳动力的家庭农业的坚韧性。
“成本收益资料汇编”里,蛋鸡饲养也不存在散养的数据。
与肉鸡一样,成本收益调查在2006年放弃了对这一项目进行调查。
)
对于水产品,在2007年(最后一个有统计资料的年份)总产量达到4700万吨(相较于肉类的6700万吨、奶类和蛋类的6200万吨,《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8》:
7-44),资本主义经营同样有着较大的发展,这是因为水产养殖需要相对更高的资金投入。
“资料汇编”中,仅在2004年~2007年有“淡水鱼精养”这一项目。
如图2所示,在2007年,雇工占全部劳动投入的26%。
综上所述,相比于由资本主义式农业企业进行的大规模生产,中国的家庭农业经营仍占据压倒优势地位。
对于黄宗智称之为“旧农业”(主要是由家庭农户进行谷物、油料作物甚或棉花的生产)的那部分农业来说,尤其如此。
对于黄宗智称之为“新农业”的高产值农产品,尤其是蔬菜、肉蛋奶,很大程度上也如此。
后者涉及资本和劳动双密集的投入:
一个劳力可以耕种4亩旧式的露地菜,但同样一个劳力只能管理1亩新型的塑胶棚蔬菜。
类似的,一个典型的农户利用厨房的剩饭剩菜可以喂养一两头猪,而通过利用生物剂将谷物秸秆转化为饲料则可以饲养10头或更多。
(黄宗智,2010b)水果、奶类和鸡蛋生产则需使用较多的雇佣劳动。
要精确量化所有的雇工在全部劳动投入中所占的比例,目前看来还不容易实现,其实或许也并不可取。
这部分是因为各种农产品之间存在巨大差异:
像谷物、蔬菜、花生—油菜籽、棉花、生猪—禽类—肉牛这些农产品,家庭经营仍旧占主导地位;
另一方面,有少部分农产品比如水果、奶类、养殖的水产品、蛋类,基于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式农业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
然而,我们仍然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总体上看来,雇工仍然只占全部劳动投入的一个较小比重。
对于表1中的五种主要农作物(占总播种面积的93.5%)而言,只占5%;
对于肉类生产而言只占7%;
但是对于需要更密集资本投入的淡水鱼饲养和需要更高标准化操作的奶类和蛋类生产而言,雇佣劳动占比则要高些。
总体看来,根据成本收益调查得出的雇佣劳动所占比例应该在5%~8%之间,肯定要低于10%。
三、另一组不同的数据
5%~8%,或者“肯定低于10%”的估计,或许比有些人的预期要小。
但其实这很有可能是一个过高的估计。
前面我们给出的统计数据均来自针对全国范围内60000户样本农户的成本收益调查。
这60000户是个有限的样本集,我们因此不得不面对样本选择所可能带来的对真实状况的偏离。
确实,这些农户来自于全国范围内的1553个县④,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数目,但必须注意,它同时也意味着平均每个县只有38户调查户。
另外,这项调查的主要目的与其说是为了获取中国农业的基本状况,不如说是通过检测不同生产要素成本间的关系,为国家制定价格政策提供基础。
除上述主要目的以外,这项调查也明显意在为官方所期待的农业发展道路树立典型。
如发改委价格司(该司是这项调查的主导部门)司长赵小平所说:
……基层成本调查队和调查人员……注意发挥调查户的示范作用,努力寻找适应本地实际的特色产业,为农民提供看得见的致富门路,以一户带百户、一点带一片,为农民增收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受到了农民的交口称赞,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充分肯定。
“要致富,看农调户”成为农产品成本调查为农民增收服务的真实写照。
(赵小平,2004)
鉴于赵小平所说的调查户要发挥“示范作用”,我们认为,成本收益调查所选择的调查户,很有可能是那些被认作比较先进的农户。
这种具有倾向性的样本选择,很可能会使基于这些调查户的数据所得到的雇佣劳动占总劳动投入的比重,高于真实情况。
那么,怎样才能纠正这套被广泛用于学术研究的统计资料(利用这套资料进行研究的最近例子,见王美艳,2011)所可能存在的偏差呢?
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是为了克服小样本所带来的问题,中国自1996年以来开始进行每十年一度的全国农业普查。
农业普查的性质与每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类似——后者提供了关于人口的基础数据。
迄今为止,我们有两次农业普查的资料——1996年度和2006年度。
这两次普查分别以1996年和2006年的12月31日24:
00为准。
这个大型的农业普查要求每位调查员对被调查对象进行现场访谈,当面填写调查问卷。
调查采用全国统一的标准4页问卷,并且附有给调查员的详细说明。
调查问卷包含有针对农业雇工数量的项目(标准问卷中的问题10),并且对雇工有受雇时间(6个月以上和6个月以下)和性别的区分。
对于6个月以下的农业雇工,调查问卷要求填写确切的受雇天数。
第8节,第285~339页)
总的来说,十年一度的农业普查的用意和十年一度的人口普查相同。
与针对60000户样本农户的成本收益调查不同,农业普查意在尽可能精确地捕捉到社会实际,而不附带任何试图确立某些农户作为典型的意图。
实际上,农业普查被用来给中国的农业统计数据确立新的标准。
例如,它被用来纠正关于农业的旧有数据,正如人口普查数据被用来更新旧的人口与就业数据那样。
(例见《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8》,关于畜牧业情况的表7-38)
农业普查中所使用的主导范畴是“农业生产经营者”,它的主要部分是农业生产经营户,亦即我们所谓的家庭农场,在2006年总计达2.002亿户,它们拥有共3.42亿“本户劳动力”。
在这些家庭农场之外则是39.5万个“农业生产经营单位”,这一范畴包括“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以及“其它法人单位”。
“农业生产经营单位”中,具有官方注册的“农业法人单位”身份的有23.9万个,这些单位共有627.8万从业人员(平均每单位26人),其中企业共雇佣358.3万人(占“农业经营单位”雇用的全部从业人员的57%)。
也就是说,企业雇用的从业人员仅占全部农业劳动人员(包括家庭农场和农业生产经营单位的全部劳动人员)的1%。
(《中国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汇编》[农业卷],2009:
表1-5-1)那些在农业企业中的从业人员,应有相当部分可以被视为“农业雇工”,亦即被(资本主义)农业企业全职雇佣的农业工人。
如果我们假设所有没有注册的“农业生产经营单位”都是私营的、追求利润的企业(因为别的单位,诸如事业单位、机关、社会团体等,应该多是注册单位),而且进一步假设它们具有与已注册企业相同的平均雇员数量(实际上,这些没注册的单位可能规模要小),则可以得到另外405.6万雇佣从业人员。
再加上已知的企业雇员358.3万人,总计可得763.9万雇员,占全部农业从业人员的2.2%。
这一数目可作为由资本主义农业企业雇佣的农业工人的一个上限估计。
⑤
家庭农场(也就是“农业生产经营户”)的数据更精确一些。
这些家庭农场的“家庭户从业劳动力”总计3.42亿,其中3.37亿(98.5%)属于“自营”,剩余的少部分属于“雇主”、“家庭帮工”、“务工”、“公职”等范畴。
表2-1-14)
需要指出的是,农民家庭经济活动的多变性增加了这些数据本身的复杂性。
现在,大多数农户同时从事多个领域的活动。
除农业以外,还有大量的非农活动,比如商贸、运输以及其他服务业。
十年一度的农业普查依据全年从事农业的时间在6个月以上和以下对农户进行了划分。
依照这种划分,在被如此统计的3.05亿农民中,有2.14亿全年从事农业的时间在6个月以上,0.91亿在6个月以下。
在前者之中,有160万人(0.7%)被认定为“雇工”;
对于后者,没有直接给出雇工人数,但普查资料指出总计有2.75亿个工日是由雇工完成的。
按照一年300个工日计算,这些工日被折算为90万个“年雇工”。
表2-1-15)这二者相加,我们可得雇工数量为250万,这占全部3.05亿农民的0.8%。
然而还需考虑到,按照一年300个工日折算年雇工,虽然对年雇工来说是合理的,但这样的天数很有可能比2.14亿每年从业6个月以上的“自雇”农民每年的从业天数要多,也肯定比9100万每年从业6个月以下的自雇农民每年的从业天数要多。
更精确的计算雇佣劳动在全部劳动投入中所占比重的方法是,计算自雇农民和雇工的全年劳动天数。
如果我们假设从业6个月以上的自雇农民全年平均劳动250天,从业6个月以下的自雇农民平均劳动100天,则可以得到雇佣劳动占全部劳动投入的比重为1.2%,大于前面得到的0.8%。
⑥这些雇佣劳动中,64%是长期雇工(6个月以上),36%是短期雇工(6个月以下)。
短期雇工的主体应该是那些自己也有家庭农场的农民,他们只是将部分时间与人佣工。
这一类人不属于“农业无产阶级”的范畴,而是更近于“半无产阶级”。
对于在家庭经营的农场中劳动的“农业无产阶级”的规模,我们应该使用0.8%的数字。
之前我们为农业企业雇佣的农业雇工估计的上限是2.2%,那么加上刚刚估计的0.8%,得到3.0%,这就是全部农业劳动投入中,“农业无产阶级”所占的比重。
如果我们把同时自己经营家庭农场的短期雇工也计算在内,这一数字将是3.4%。
第二次农业普查的数据说明,农业雇佣劳动占全部农业劳动投入的比重要比通过60000个样本户的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调查估计的比重要低。
这进一步表明,成本收益调查的样本户很可能是“致富”的地方“示范”者——这是一种有倾向性的样本选择。
在获得更加精确的数据之前,基于60000个样本户的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调查所计算得到的5%~8%(或者“肯定低于10%”),可以作为农业雇佣劳动比重的一个上限估计;
由覆盖性更强的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计算得到的3.0%或者3.4%,可以作为一个下限估计。
鉴于成本收益调查的样本户很可能是具有“示范作用”的“先进”农户,我们更倾向于认为较低的比重更加符合实际。
四、地方和微观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