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晨民国国立大学教师兼课研究Word文档格式.docx
《梁晨民国国立大学教师兼课研究Word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梁晨民国国立大学教师兼课研究Word文档格式.docx(1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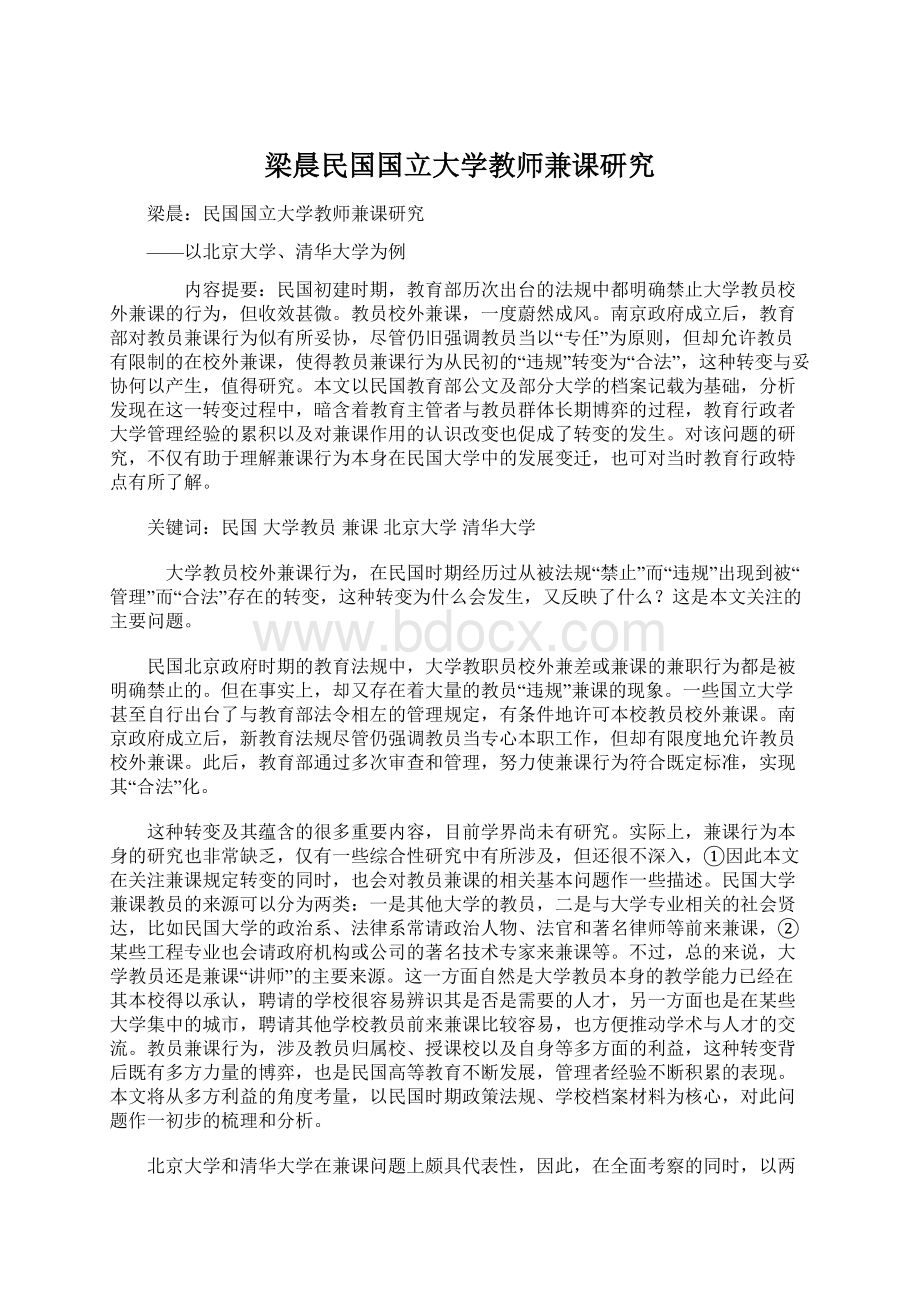
一是其他大学的教员,二是与大学专业相关的社会贤达,比如民国大学的政治系、法律系常请政治人物、法官和著名律师等前来兼课,②某些工程专业也会请政府机构或公司的著名技术专家来兼课等。
不过,总的来说,大学教员还是兼课“讲师”的主要来源。
这一方面自然是大学教员本身的教学能力已经在其本校得以承认,聘请的学校很容易辨识其是否是需要的人才,另一方面也是在某些大学集中的城市,聘请其他学校教员前来兼课比较容易,也方便推动学术与人才的交流。
教员兼课行为,涉及教员归属校、授课校以及自身等多方面的利益,这种转变背后既有多方力量的博弈,也是民国高等教育不断发展,管理者经验不断积累的表现。
本文将从多方利益的角度考量,以民国时期政策法规、学校档案材料为核心,对此问题作一初步的梳理和分析。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兼课问题上颇具代表性,因此,在全面考察的同时,以两校为中心,以作更具体和深入的讨论。
限于交通水平,民国大学教员的兼课基本都发生在同一城市的大学之间。
北京和上海是民国大学最为集中的城市,北京更被称为“大学之城”,国立大学最为集中。
官方对于教员兼课的管理,直接对象自然是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国立大学而非私立大学。
北大和清华是北京乃至全国最为著名的两所大学。
北大是最早的国立大学,校长蔡元培曾认为北大乃以一校之力,“单独担任全国教育”,③其执掌教育部后,一校之规定很可能转为学界之法则。
清华在民国则以经费充裕,教师生活水平高而著称。
两校都有众多的“良好教授”,他们恰是其他学校兼课教师的优秀人选;
另一方面,两校为推动自身的发展,也曾聘请过许多知名学者来校兼课。
因此透过这样两所在民国时期特别重要却又差异很大的学校,可以较为深入地理解民国高校关于教师兼课的面貌。
一、北京政府时期:
“禁止”与“违规”
民国成立后,教育部出台的多项规程中,虽然承认大学可以有兼任教员,但同时强调大学本身的教员不可在外兼职,要以专任为原则。
1912年,民国教育部制定的第一部大学规程《民元大学令》中就有专门条款指出,大学在有必要的时候,可以延聘兼任教员,即“讲师”。
1917年,北京政府教育部修订《大学令》时,这一条款丝毫未动,得到了继承。
④兼任教员在学校的工作基本只以授课为限,故称为“讲师”。
也正因此,他们的劳动报酬均按照所授课时钟点多少予以发放,且每年以10个月为限。
对于大学教员的校外兼职行为,政府法规则明确禁止。
民国元年7月,教育总长蔡元培给各大学下达了《凡担任校务者须开去兼差以专责成》的照会,认为“盖人才各有专长,精力不可分用,专责始克有功,兼任不免两败”,要求有兼职的大学校长们“于学校职务与官署职务之中,何去何从,择任其一”。
⑤禁止校长兼职当是为禁止教员兼职做铺垫和表率。
1914年5月教育部在《专门以上学校职员薪俸暂行规定》中第一条就规定:
“凡直辖专门以上学校职员,除特别规定外,不得兼司他项职务。
”⑥1917年民国大学令中也再次强调了这一要求,除本属兼任的讲师外,其他各类教职员都不可在校外兼职。
⑦
但与规定格格不入的是,当时专职大学教员“违规”在校外兼课的现象却较普遍,有些甚至还很夸张,而大多数教员们则认为是北京政府经常拖欠教员薪俸导致了这一现象。
⑧1920年代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李宗侗就说当时北平教育界的“兼课之风大作”,甚至“常有人兼课到五十几小时一星期”⑨。
兼课的课时如此之多,课表上的课不仅都排满,而且还可能有重复,需要轮流向各学校请假以应付。
⑩这些人也被称之为“兼课专家”。
(11)李宗侗认为“那时正好北(京)政府经济困难,公教人员的薪水全发不出来,所以总是在欠薪的状态中”。
因此,“彼时北平的教育界,皆因欠薪而难维持生活”(12)。
蒋廷黻也同意这种看法,他回忆说:
“在我返国时,大多数学校发不出薪水,老师无心上课,或者尽量兼课,因为薪水是按钟点计算的。
”(13)
北京政府教育经费常被挪用,教员薪俸不能按时发放确实存在,而且对教员生活影响颇大。
民初军阀干政,局势多变,内阁“并不比电影中的统治者具有更多的实力”,“财政总长没有钱。
交通总长无铁路可管,因为铁路全在军队指挥官手中。
教育总长总该管公立学校,但这些学校被关闭,因为不能支付公用事业的费用,教员也领不到薪金”。
(14)欠薪一度成为公立大学财政的主题。
舒新城在1925年就指出:
“自民国五年而后,教育经费逐渐被军人提用,民十以后,积欠日深,十四年中央教育经费已积欠至一年以上,经费云云自无良好消息。
”不仅中央如此,“各省亦然”。
(15)吴民祥对1920年至1930年间北京地区因欠发大学教师薪俸而引发的“索薪”运动进行过简单总结,发现除1928年未有“索薪”运动外,其余各年都有,且欠薪数量短则三五月,长的累积有两年多。
1923年情势最危急,北京《晨报》连续有诸如“京师教育势将完全停顿”、“教育部名存实亡”、“八校已陷入绝境”、“八校危在旦夕”、“国立八校已无法维持,数万青年失学”以及“国立八校已有五校关门”等报道出现。
(16)教员生活也大受影响。
一些低级教职员一面是薪俸无着,一面又是“米面价格昂贵”,导致“典当一空,告贷无路矣”(17),窘困之情形,可谓无以复加。
而即便高薪的教授如胡适者,在长期欠薪的状况中,也会出现囊中羞涩,生活困顿的情形。
(18)当时教育评论家称此时为教育的“恐慌时代”。
(19)为此,“教师的生活必须先安定,始能乐业,以求向上的发展”。
“如一校之报酬不足以维持生活,势必兼课兼差,以致体力精神两俱不足。
”(20)
在这种局面下,教育主管部门既然已是“其身不正”了,自然是“虽令不行”,禁止兼课的法规毫不起作用。
实际上,一段时间里,教育部的大小官员们自身也曾深受欠薪的困扰,甚至也组织了“索薪团”,进行罢工斗争。
(21)或许是认同教员们“兼课是迫于生计”的看法,或许是出于对欠薪痛苦的感同身受,教育部此期并未对各大学教员兼课行为有过任何检查或批评,这与南京政府时期形成鲜明对比。
但教员大肆兼课,甚至请假轮流上课,于学风和教学秩序实在大为有害,也从根本上影响了大学教员对研究的投入,这必然引起一些著名大学管理层的紧张。
为此,北大和清华这样的学校,不得不出台本校内部的管理规定,希望能控制本校教员的兼课行为。
这些规定对日后教育行政部门的法规制定有着重要的影响。
1922年时,北大评议会成为学校主要决策机构,该会明确北大教授在“不得已”时可兼职,但必须得到学校的承认。
(22)确定了兼课需得到校方认可的首要原则。
同时强调,教授如果在校外不是兼课,而是兼任其他职务,则不可以继续担任北大教授,必须改成兼任性质的讲师。
(23)这实际上规定了北大专任教员只可在外担任兼课工作。
为了限制教员兼课时间,避免北大教员成为“兼课专家”,在多个高校不停兼课,评议会还规定教授在他校兼课“每星期至多不得过六点钟”(24)。
北大对于本校教师校外兼课身份、工作内容和时间的限制在其他高校乃至后来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相关法规中都有所体现。
清华的兼课规定则另具特色。
1925年清华设立大学部和研究院国学门,专任教授开始不断增加。
尽管清华经费稳固,从未拖欠教员薪俸,但一方面,兼课在京城教坛已然成风,清华一校难以遏止。
另一方面,清华欲建大学,教授匮乏,课程开设不足,需要他校教授前来兼课。
为此清华多次与燕京大学商议合作办法。
(25)1926年,燕京大学洪煨莲欲聘清华教授朱彬元、陈达二人为燕大讲师,清华借此机会与燕大制订了两校互用教授章程五条,其内容如下:
(1)甲校聘乙校某教授兼任某功课者须由甲校与乙校直接交涉得其允许。
(2)该项兼课须不妨害某教授在乙校所应进之职务。
(3)该项兼课每星期钟点不得过四小时(某教授在甲乙两校每星期授课钟点合计不得过十五小时)。
(4)甲校致送某教授兼课薪金每小时定为五元。
(5)兼课薪金应由乙校与教授各得金额之半。
(26)
合约的达成,使清华、燕京教师兼课合法化,兼课成为校际合作的重要表现,但同时校方意志也成为兼课是否可行的关键因素。
例如清华曾想从燕京聘请教授吴文藻任社会人类学课,吕复任政治学课,但燕大以该二人校内钟点已满为由拒绝。
(27)
相对于北大的规定,清华的限制更多。
首先,只能在燕大兼课。
这样教授们就不会因为要进城兼课而影响在清华的工作。
其次,兼课钟点不得超过4小时,少于北大的6个小时。
最后,教师兼课的薪金要和学校对半分。
这种做法虽不见得具有大范围推广的可能,但却很好地协调了两校校方的利益和诉求,至少间接地为此后1932年国立专科以上学校校长开会讨论统一兼课规定提供了范本。
因此,总体来说,北京政府时期,教育部虽明确禁止教员校外兼职,但限于教育经费的困难,对此仅有规定而无落实,教员兼课之风盛行,各高校为此不得不自行制定诸多措施。
这些措施基本都试图从许可权、兼课资格、兼课时间以及兼课薪俸等角度来限制兼课行为。
一方面试图避免兼课之风影响正常的教学,另一方面也照顾了教员利益,为兼课保留一定空间。
同时,高校往往只审查自己教授外出兼课的时间、资历等,而对前来兼课的教师则基本没有审查,具有“内紧外松”的特点。
二、南京政府时期:
“限制”与“合法”
南京政府成立以后,教育得以重新调整,担任教育部长者,如蒋梦麟、朱家骅以及王世杰等都曾担任大学教授与校长,对大学管理与教员状况有实际的经验,在对待“兼课”问题上的措施也有别于北京政府时期。
一方面他们深刻地认识到北京政府时期教育界那种肆无忌惮兼课的风气对整个高等教育非常有害,“妨碍学校进步,盖无有甚于此事”,(28)必须加以管理和纠正;
另一方面从大学行政的实践中,他们也认识到“兼课”行为是大学所需要的。
当时大学人才匮乏,各类学校水平和教员素养多有差别,兼课行为有利于人才资源的共享。
此外,大学教员本身也是校园政治中的重要力量,严格禁绝大学兼课,很可能招致教员的集体反对而导致政策流产。
因此,在种种努力之后,简单“禁止”兼课转变为了“限制”兼课,兼课行为得到了规范管理,走向了“合法”化。
教育管理者们认为大学教员兼课是学风变坏,教员不思学术钻研的重要原因,必须加以管理。
国立大学的校长们对此尤其看重。
例如蔡元培一直想将北大建设成“高深研究”而不是单纯训练学生的场所,“教授及讲师不仅仅是授课,还要不放过一切有利于自己研究的机会,使自己的知识不断更新,保持活力”(29)。
教员过多兼课显然不利于达成此目的。
蒋梦麟担任北大校长后发现北大教员“纷纷兼课,越有名的教授,兼课也越多,甚或有以轮流辍课,或迟到方式以便在各处兼课者。
”(30)因此他在1931年提出的中兴北大计划的第一点就指出必须限制教员兼课行为。
(31)或许是为了配合蒋梦麟的改革计划,在该年早些时候,天津《大公报》曾发表署名“寿亭”的北大学生所撰《整顿北京大学之我见》一文,其中指出北大教授方面的弊病就是“教授晚来上课的弊病,多因在外兼课太多,甚至有一人在北平各大学身兼三个主任,五个教授的情形”。
(32)而先后担任清华大学、中央大学等校校长的罗家伦同样指出,此时大学教员腐化非常严重,教授风纪急需整治,而“第一要先实行限制兼课着手”(33)。
因此,192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就曾下文要求教授坚持以“专任为原则”,各大学对兼课行为“亟应严加整顿以绝弊端”(34)。
但这种管理并非简单的一纸“禁令”,而是有多重措施的配合。
首先,显然考虑到北京政府时期,大学教员多宣称乃因“薪俸不稳”,为“维持生计”而不得不兼课,提高教员待遇,保证薪俸稳定就成为教育主管部门解决兼课问题的第一步。
教育部在保证教育经费稳定的同时,努力提高教员待遇,使得教员不再因为生计而兼课,也让教员失去随意兼课的理由。
1929年6月,教育部给各大学去函,明确指出“大学教员,关系一校教学者至巨,待遇自应从优,以期效能增进”。
(35)到王世杰出任教育部长时,高等教育经费“由行政院责成财政部拨给教育部,再由教育部直接拨给各校”,各主要国立大学经费发放“较合理”,(36)教员欠薪现象也不再发生,教育行政也因此趋向稳定。
(37)大学校长则想办法提高教授待遇。
如蒋梦麟在北大时提出“要提高教授待遇”,然后方能“绝对限制在外校兼课,使教授有充分时间研究学问,富藏高深学问之储蓄”(38)。
为此,北大利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资助,以5年为期限,设立“研究教授”15名,其人选“以对于所治学术有所贡献,见于著述,为标准”。
“研究教授每周至少授课六小时,并担任学术研究及指导学生之研究工作,不得兼任校外教务或事务。
”(39)研究教授的薪俸远高于一般教授,禁止兼课得以接受。
此外,一般的教授,“待遇亦力求提高,使其生活有保障、家庭安定舒适而且限制校外兼职,俾能有充分的体力及愉快的精神来致力研究教学工作”(40)。
蒋梦麟在教育部长任内,还发起了大学校长不兼职运动,以便为限制教员兼课做表率。
为此,1930年他先后辞去了兼任的浙江省立高中校长和浙江大学校长职务。
(41)《时事新报》为此评论道:
“现在国府要人,如部长等遥领大学校长者,实繁有徒……近日报载教育部长蒋梦麟辞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意指蒋部长为全国教育行政机关首领,深知个中流弊,故毅然辞去兼职,而今而后,将专心为党国服务,未审其他部长次长之兼国立大学校长者,亦有动于中否耶?
”(42)而在蒋氏辞职后,相继有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辞中山大学校长兼职,孙科辞去国立交通大学兼职。
(43)1934年南京政府修正大学组织法时,明确禁止了大学校长的兼职。
此后历年大学统计表明,大学校长兼职的情况已经很少发生了。
但这番努力之后,教育部并不准备完全禁止教员兼课。
1929年教育部明确表明,尽管政府要求“自十八年度上学期起,凡国立大学教授,不得兼任他校或同校其他学院功课”,但“倘有特别情形不能不兼任时”,“每周至多以六小时为限;
其在各机关服务人员担任学校功课,每周以四小时为限,并不得聘为教授。
”(44)显然,这一规定实际上是允许教授兼课,但何谓“特别情形”当时并没说明。
之所以不是断然“禁止”而是有条件的“允许”,是教育管理者与教员群体不断博弈的结果。
结合此时的实际,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理解大学教师兼课的意义:
第一,教育部主要官员及大学校长们在此前大学实践中发现,兼课行为对大学发展有一定益处。
尽管大学校长们都同意“良好教师”是办好大学的关键,但由于教育界人才匮乏严重,优良教员非常难得。
(45)而大学的不断增长,也使这种人才缺口更加显著。
兼课,实现“借才异校”,推动了大学间的“资源共享”,对高等教育发展显然是有利的。
例如1928年罗家伦代表南京政府接办清华大学后,“增加良好教授”一直是他整顿清华的重点。
但他却不得不承认,由于“其他大学之竞争”等原因,“一时想聘到多数的良好教授,确属不易”(46)。
因此,当该年清华经过一番努力,争取到数名燕京大学教授前来兼课,罗家伦认为这是“可喜之事”。
(47)而当他从清华辞职时,曾经聘请了多名“有根底”、“有造诣”的兼课讲师,也被其看成在清华的重要成绩。
(48)1930年代的清华,兼课老师就更多了,对学校发展也裨益良多。
当时清华主要有14个学系,其中10个系有兼课教师,只有社会人类学系、物理系、化学系和数学系没有兼课教师。
兼职教师占整体教师的比例达到27%。
(49)哲学系专任教师不过3人,兼任却有4个,其中就有燕京大学哲学系主任黄子通、著名教授许地山和张崧年等,(50)他们的存在对清华哲学系之影响显而易见。
当时其他来清华兼课的著名教授还有讲授民法与公司法的北大教授何基鸿;
曾在历史系兼课的教师,朱希祖、张星烺是北大教授,瞿宣颖是南开大学的教授,刘朝阳为燕京教授,李济则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的主任。
这些兼课老师的到来,不论对学生之学习、就业,还是学校间学术的交流,都颇有益处。
因此,聘请兼职教师以保证教学与发展是民国时期很多大学的主动行为。
冯友兰也认为:
“这种学校争教授,教授选学校的情况,也促进了当时各大学的学术空气的发展。
”(51)从这个角度来说,禁绝大学教师兼课,不仅既无此可能,也似乎无此必要。
不过,尽管只是讲课,但大学对兼课教师的要求并不低。
教授这样的高级教员以及从海外归来、学有所长的教员成为各校追逐的热门,兼课教员的规模甚至可能超出了以往。
李书华就指出,民国北京大学里兼课的那些讲师并非比教授们低一级,实际上,讲师们的“资格地位本甚高”(52)。
冯友兰也说过,民国的清华大学“不大喜欢请初出茅庐的人”(53),学术成绩突出的大学教授就成为各校兼课的主力,甚至成为一种稀缺资源。
例如1930年代清华中文系主要有朱自清、陈寅恪、杨树达、刘文典、俞平伯、闻一多6位教授,至少有5人曾在校外兼课。
其中陈寅恪曾在北大兼课,讲授“佛经翻译文学”,后又改授“蒙古源流研究”一课。
(54)杨树达曾在中国大学校兼课。
朱自清1933年到1934年学年曾在师大兼课。
(55)1929年,已经在清华任教的俞平伯也同时在北京大学兼课,到1931年才辞去北大兼课。
(56)闻一多1933-1934年间在北大兼课的材料也早在十多年前就在北大档案馆被发现了。
(57)由于清华很多教授是从国外学成归来的,其研究方法与课题在国内都颇为新颖,因此他们刚回国,甚至并未取得教授资格,也会成为其他高校聘请的热门人选。
如张荫麟回国后,担任清华的专任讲师。
(58)他兼授历史和哲学两系的课程,其历史哲学课在国内更是独树一帜。
因此北大很快就请他兼授一门历史哲学的功课。
(59)顾毓琇1932年初一回国任教清华,北大就同时请他兼课。
时人郭一岑曾感慨教育部要求限制兼课的命令发布后,“兼任教授反比以前加多”。
(60)
第二,从教员角度分析,兼课实际上是名利双收的事情,多数教员都有兼课的动机。
就名来说,大学教授能到他校兼课,表示“能叫座”,因此“北京各大学的名教授以兼任功课为光荣”。
(61)从利来说,兼课获利较厚。
如吴宓在1929年上学期开始为北大上课,而这个学期他在清华每周也只有两次课,时间比较充裕。
每月他都能从北大第二院领取100元的兼课薪金。
(62)相对于他在清华每月300多元的月俸也相当可观了。
民国初期任教于清华的狄莫尔(C.G.Dittmer),1917年指导清华学生调查了北京西郊第一区195家乡民生活费,1918年调查清华校役93人的生活费,根据这些研究,他指出年收入100元足以使一个5口的劳工之家过上相对舒适的生活。
(63)王玉茹经过研究,指出若1930年的物价指数为100的话,1918年当为50。
也就是说1918年100元达到的生活标准到1930年差不多要200元。
教授兼课发薪为10个月,吴宓兼课一年收入在1000元,刚好满足5个5口劳工家庭一年舒适生活的费用。
而陶希圣通过兼课,每月可获得100元,这些钱足以支持他办理《食货》半月刊。
(64)此外,教授们上课内容也基本是本校课程的重复,可以说工作相对轻松,投入少而产出多,教授们自然乐意。
第三,除了直接的收入原因之外,兼课现象众多也应与民国时期大学教师合同期短,职位不够稳固,流动频繁有一定关系。
民国有评论者指出“教员的问题是在无恒心”,而首要原因是“任期短”,“作教员之于学校,如燕之巢于幕上,其受聘之期,短者为一学期二学期,最久者亦仅一年”。
(65)这种制度设计,一方面使得教授流动很自由,学校间争夺教授的空间较大;
另一方面,也让教授们神经有点紧张。
或是因为教学水平不够,或是因为人际关系不好,或是其他种种原因,都有可能使得教授轻易失业。
而美国大学在1915年后就有规定“大学教授、副教授以及讲师以上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任职期限超过十年以上者均应终身聘用。
”(66)因此,冯友兰就曾说:
“虽然清华的一般教授都觉得自己的地位很稳固,但有些大学,教授每到暑假都有一次惶惶不安。
”(67)有的教授每当发聘书时期,先到别的某一学校表示愿意来应聘,等到拿到此学校聘书之后,又拿这个聘书要挟原来的学校,讨价还价,在如愿以偿以后,他又把某一学校的聘书退回去。
(68)谢泳曾经统计过北大、清华、南开、北师大在1949年前的一百位教授的自由流动情况,发现他们当中平均自由流动三次,多的则达四五次。
(69)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民国教授有着较强的流动需要。
要想从一个学校流动到另一个学校,方式当然很多,比如自荐,朋友介绍等等,但兼课无疑是一种更好的方式,即可以提前相互了解,以备不时之需。
郭一岑曾在《不要忘了大学教育的另一个使命》一文中指出,教育部对兼课限制的命令实际如一纸空文,兼任教授反比以前加多。
其原因不仅是教师薪资不定,也是因为任期不稳。
(70)总之,不论出于什么目的和境遇,由于短暂的合约引发的流动性,使得教授们也有需要去他校兼职,以免在本校合约发生问题时没有去处,形成失业。
合约制度对兼课现象的影响虽不明显,但可能更深刻。
第四,教员,尤其是教授们是民国大学中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群体,对于他们的利益,教育主管者,特别是大学校长们不能不有所忌惮,因此也不会轻易禁绝教员兼课权利。
冯友兰曾回忆蒋梦麟有一个经验,即“在一个大学中,校长、教授、学生是三种势力。
如果三者之中,有两种联合起来,反对其余一种,一种必然失败。
”他还认为清华校长梅贻琦常说“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其实有讨好教授之嫌,从而“在学校有事的时候,教授会总是帮他的忙”(71)。
尽管冯氏的看法未必能真实反映两位校长的想法,但显然教授群体能量强大,大学校长对此颇为忌惮,而对兼课限制过严,可能直接影响校长地位的稳固。
1931年时,任职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就认为教员拜金现象严重,甚至有人“身兼五教授四主任,每月收入在一千五六百元以上者”,政府经费都被这些人瓜分了。
但是如果有校长想制止这种现象,严格管理教员的兼职,那么“教授联合学生以仇视校长”,“必联学生以倒之”,校长的位置就坐不稳了。
因此尽管有教育部的规定,“但各处无不阳奉阴违”,是以教育界“无正义,无是非也”。
(72)绝对禁止教员兼课对大学校长来说,也是具有一定风险的,而“管制”则似乎成为了更好的选择。
因此在此种种博弈之中,教育主管者的选择也就比较明确了,那就是对兼课进行限制与管理,这也就是1929年教育部限制兼课规定的由来。
而或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