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我为河南杀人喂狗案主角高铁钢的辩护 精品Word格式.docx
《最新我为河南杀人喂狗案主角高铁钢的辩护 精品Word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最新我为河南杀人喂狗案主角高铁钢的辩护 精品Word格式.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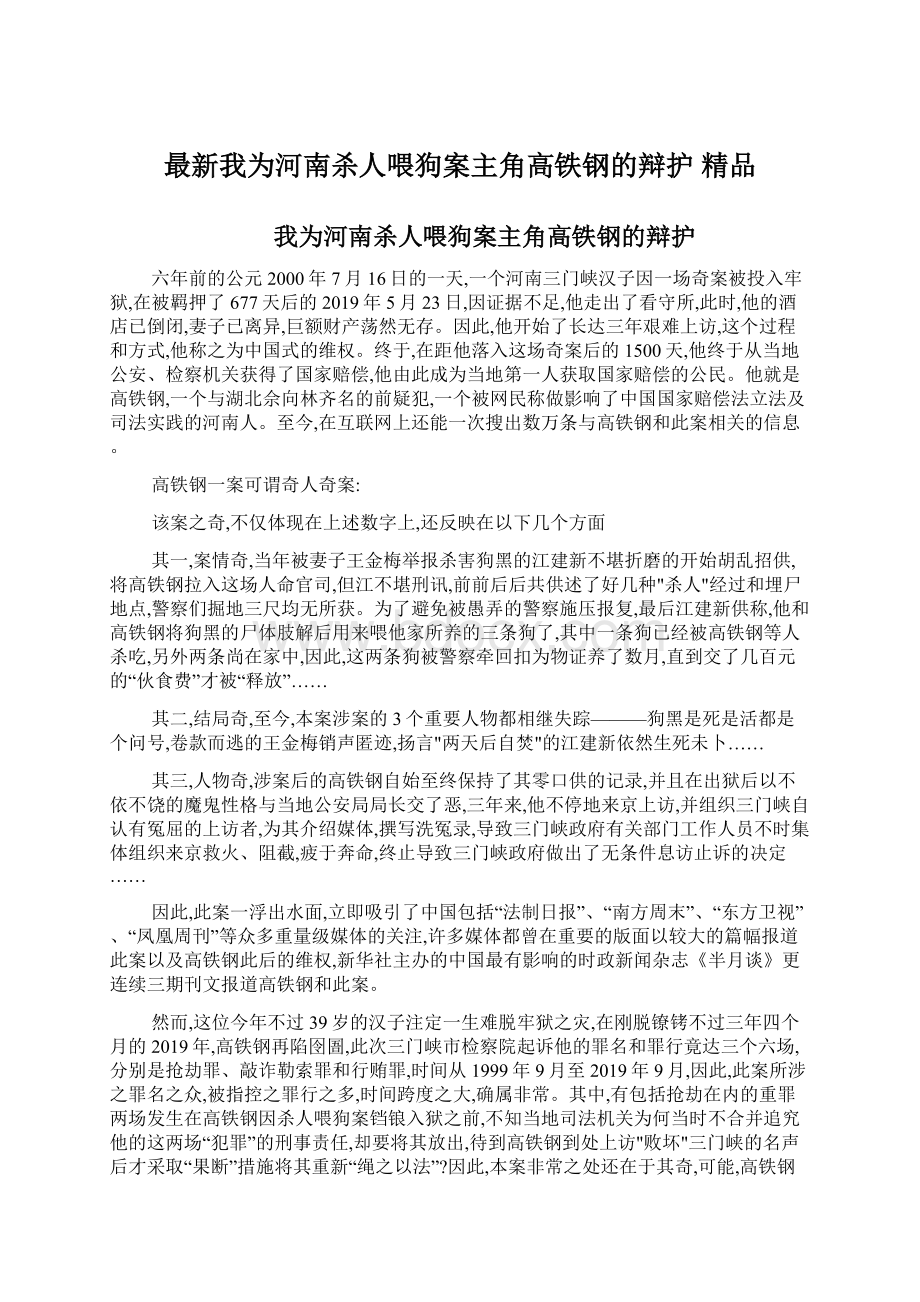
石野原是南海舰队宣传科的一名军人,退伍后在南方都市报等多家媒体从事记者工作,去年曾出版了两本畅销书,一本是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卧底调查——我的四次死里逃生》,一本是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的《卧底记者——我的正义之旅》,该二书长登搜狐、新浪两着名网站读书频道的榜首达半年之久,全国50多家地方报纸争相转载,一时间洛阳纸贵,其因此名声大噪,包括“凤凰卫视”、“北京电视台”、“东方卫视”在内地十几家电视台制作并播放了对他的专访节目,“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等十几家纸媒对其专题报道,“石野现象”因此一下子成为05年中国十大新闻现象之一。
本人系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某部曾效力二十三年的正团职中校军官,退役后又从事律师职业,因此对公平、正义有着本能的追求。
加之与石野有共同的军旅生涯背景且追求及人生价值观基本相同,因此,平日相交十分投契,因此,在其劝说下,在高铁钢的同学、好友在当地和北京找不到合适且有胆识的律师的情况下,本人毅然接受了高铁钢年近七旬的老父的委托,充当了高铁钢的辩护律师。
从此,笔者的包括情感在内的精神世界便不能平静,笔者的灵魂便不能自由,只要笔者的那位当事人还在牢笼之中。
本文就是我陷入这场恶水潜流后的事实经过的记事,我力求以平静客观的态度来记录有关过程,并附以该案包括检察机关的起诉书、我的辩护意见、会见犯罪嫌疑人笔录、公诉机关装入案卷作为证据使用的案卷资料等全部文件,以及媒体对前案的有关报道,以便让有心的读者对有关事实做出自己的道德评判。
受托
2019年初的一天,石野对我说:
“河南杀人喂狗案你听说过没有?
”作为一个律师和半个传媒人的我当然对此案不陌生,在我印象中前两年几乎所有国内主要媒体都以较大篇幅报道过此案,其影响与其后的湖北佘向林杀妻冤案几乎相同,而且其主角高铁钢04年还被网络评为影响了中国国家赔偿法修改立案进程的“年度中国式维权新闻人物”。
“怎么?
”我问石野。
“高铁钢又被抓了起来了!
”石野回答说。
“为什么?
”我问道:
“与上次的案件有关吗?
”
“说无关也无关,说有关也有关。
”石野有些诡谲地答道。
“此话怎讲?
“说无关是因为这次事由与上次杀人案确实无关。
”石野道:
“说有关是因为任何人都可以看出这是上次那个事的因产生的果。
我更是入坠云里雾中了。
“这次是因另外几个事,其中包括两场上次杀人案以前的事,1999年的事。
”石野解释道。
“那为什么不与上次的案子一起合并立案侦察起诉,反要到七年后再另案追究?
”我问道。
“这就是我说的‘说有关也有关’的含义了”石野笑道:
“如果上次出狱后高铁钢不到处告状‘败坏’三门峡的名声,不到处向媒体揭三门峡警方的短,不穷追猛打地向人家讨什么国家赔偿,或许他这次就不至于栽了。
“也是,中国人讲究恕道,有道是穷寇勿追,落水狗勿打。
高铁钢得理不让人,做得是有些过分。
”我点头称是。
“特别是把三门峡的冤主全组织起来到北京告御状,写什么‘洗冤录’!
”石野说:
“你想想,他们每年至少‘两会’时要来北京一趟信访告状,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就不得不来北京围追堵截;
这样,只要高铁钢们一来北京,当地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就得忘得不亦乐乎,这下子高铁钢把自己搞到监狱去了,当地政府部门不就消停了。
“可是你提起这事,和我有什么关系吗?
“正是,这不马上要开庭了,辩护人还没着落哩!
高铁钢的父亲虽然在当地请了一个律师,但是,人家要在三门峡地面上生存,高父考虑到人家可能心有余悸,不敢放胆辩,因此想在北京找一个大律师一起为高铁钢辩护,这也是三门峡那位律师的意思。
“有钱在哪儿请不到好律师,更何况我也不是什么大律师。
”我说道。
“这件事难就难在这儿,高家自从上次打官司后,已花去了几十万,百万家产也因高铁钢入狱而荡然无存,这次哪花得起大价钱,只能象征性付一些,权当法律援助。
“所以你就想到我了?
!
”我有些不平地说。
“可不是,在这种情况下到三门峡去办案还有些风险,没点胆量的人还真不敢去。
“你看我像个胆大的主?
”我反问道。
“但是你当过兵,有良知,也有正义感,这种情况你应当不会拒绝。
”石野正色道。
本人最怕激将,就这样,我应下了这桩业务,准备趟一趟这个案子的浑水。
探究
有关情况和材料不断从三门峡送来。
我开始深入研究案情。
我发现这桩案子确实有些奇:
第一:
明明有两件发生在上次杀人喂狗案以前的“犯罪”,在高铁钢因杀人案被拘时竟然完全没有提及,当然也就不会立案追究了。
当时不追究是因为当时确未发现还是当时认为不构成犯罪哩?
不得而知。
但是如果当时认为不构成犯罪,为何事隔六年多又重新提起哩?
第二:
一个案子里居然涉及到六场犯罪,时间跨度竟然达五年之久,为什么公安机关不在案发后立即立案追究,而要集攒起来“批量”处理哩?
难道事先案发后没有人报案吗?
问题到此我才发现这六场犯罪就是在没有受害人报案的情况下由公安机关依职权主动立案追究的。
看来公安机关惩治高铁钢刑事犯罪的热情和主动性十分之高。
第三:
虽然涉及的犯罪有六场,可是其中四场都是由两个核心的证人的作证来支撑的,这两个证人就是高铁钢的原“马仔”贺红星、高铁钢的原雇员秦凤莲。
这两个人一个作为同案犯在押,一个(秦凤莲)在给警方做完证后就仿佛人间蒸发般不知踪迹,就像我们过去常说的那样:
退出了历史舞台。
而另外两场犯罪即所谓行贿罪,都是因高铁钢为求媒体曝光他的冤案而给记者钱引起。
这点凭常识我就认定为不构成犯罪,因为高铁钢在这件事上没有“为谋取不法利益”的主观构成要件,当然谈不上行贿罪了。
关于其他四场犯罪,我凭直觉也感觉不应认定为犯罪。
但是我还是觉得没把握,于是我向所里的合伙人、经验丰富的高级律师汤炳煌先生讨教。
“当然也构不成犯罪呀!
”汤律师听完我陈述的案情后这样说:
“这其中三场都是基于合法的债权债务纠纷,纵有手段不当,也不能构成抢劫罪呀!
你想,连讨非法的债务都不构成抢劫罪,更何况合法的债务哩。
如果他造成债务人的轻伤以上的伤害,那也是伤害罪,而不是抢劫罪。
如果没有这个事实,当然就构不成犯罪了。
汤律师和我都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校友,他原是岳阳市律师协会的副主席,办过许多大案要案,前不久还因为代理《老鼠爱大米》的着作权交易纠纷而为中央电视台午间新闻报道过。
所以我对他的经验和学识十分相信。
但是,要想推翻这几场犯罪嫌疑也很困难,因为前述两个人自始至终都做出了对前老板高铁钢不利的证言。
而且我发现所有在场的人警方都取过证。
包括高铁钢
的同学和朋友王有红。
此人是高铁钢其中三场所谓犯罪的知情人和其中一场的见证人,正是她对我说高铁钢在这三场中都不存在警方所言的犯罪,她的证言如果是据实说的,当然只会对高铁钢有利而不会对高铁钢不利。
奇怪的是,警方对她的调查却是轻描淡写地问了几句与这三场犯罪关联不大的事。
核心的事实问题却没有提到。
但是,由此给我的取证造成极大的麻烦。
因为,按中国刑事法律的规定,成为控方如警方和检察官方的证人后,除非得到控方的同意,辩方律师是无法向该证人调查取证的。
虽然王有红给警方所做证言与本案核心事实无关,但是,我也不能再向她取证。
然而,她是目前唯一只反映事实真像也愿意为高铁钢做证的人!
我开始明白警方的高明之处了:
不向王有红取证,且王有红很可能成为辩方的证人而做出对控方不利的证言从而解脱高铁钢的犯罪嫌疑;
如果向王有红问及核心的事实,王有红则可能说明事实真像从而也能使高铁钢洗清罪名,唯一的办法就是询问王有红但并不问其核心或实质性问题。
这样,王有红便有了控方证人之名而却没有证人之实,便是这个控方证人之名已足已防止辩护律师接近王有红并获取有利于高铁钢的证言了。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工作者的我唯有依据法律规定行使我的申请权了,我正式向法院申请向控方证人王有红及本案几个所谓受害人调查取证,虽然我知道,申请归申请(正如司法机关工作人常说的——那是你的权力),但是,批准不批准却是法官和检察官的自由裁量度空间了。
事实与我所想完全一致,我的书面申请递交给法官后,便如石沉大海。
这就是说,我的申请未获批准。
蓄势
接受委托已好几个月了,我还一直没有去过三门峡去见我哪位委托人,因为,我知道,一旦我来到三门峡,警方立即会知道高铁钢已在北京聘请了律师,为了把这个案子做成铁案,警方便会运用一切手段把工作做得扎实一些。
按我所知,当时高铁钢还是零口供,我也是钦佩他是一条汉子才同意为其辩护的。
如果警方觉得工作应该做得更扎实一些,便会想法撬动高铁钢的铁嘴,那样,不仅可能我的当事人要受一点委屈,更重要的是我以后的辩护工作难度将更大。
如果我暂时隐身,警方只知道高铁钢在三门峡请了一位他们都了解也认识的律师,或许对高铁钢和我的工作都要好一些。
因为毕竟在检察机关那里还有两次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察的机会,每退补一次,证据都会更扎实一些。
但如果不惊动控方,或许其可能不用这两次机会,即使用也不至于很慎重地使用。
因此,我说服了当事人的亲属,暂不到三门峡来见高铁钢,因为此事来三门峡即看不到卷宗又会惊动我们的对手(只有到起诉阶段律师才能不受限制地查阅卷宗)。
我如此来计划我的行动步骤:
让控方在不受我刺激的情况下顺利地按程序要求往下走,公安机关尽快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尽快审查,若需退补早退,若认为条件已成就便尽快向法院起诉,到那时,我再来三门峡,彼时,控方已用尽一切审判前的一切权力,只能在法庭上就已有的证据与我搏弈。
我严格按计划行事,并嘱当事人家属严格保密,因为据其称他们的手机和电话都被监听着,因此,我要求他们一定不要用手机和家里的电话与我联系,而要用街上的公用电话与我通话。
果然,检察机关将案子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察了,我们依然按步不动。
果然,检察机关没有使用其第二次退补的权力,因为他们觉得起诉的条件已具备了。
2019年7月中的一天,三门峡传来该案已正式起诉到该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消息,第三天,我如约前往三门峡市。
初会
考虑到此案的前因后果,石野总觉得我办此案有一定的职业风险。
因此,他决定陪我一起去一趟三门峡。
于是,我们花了一整天时间,于当晚赶到了三门峡市。
当晚,我们见到了高铁钢的老父高义先生,这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干瘦苍老,须发皆发,其长样酷似已故的相声演员李文华。
但是我们却怎么也无法将其与李文华所给人留下的轻松愉悦的艺术形象连起来。
因为手里总是点着一支香烟的高老先生给我们留下的只有坚韧的悲苦的印象。
数十年前,高义先生作为水利专家、高级工程师从北京水电部举家迁到三门峡市,参加国家重点工程三门峡大坝的建设,在三门峡,高义作为主要的工程技术人员发挥了骨干作用,为三门峡的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
高铁钢就是在那火热的时代在三门峡出生的。
但是,作为三门峡工程的功臣的高义退休后并没能象其他老人一样安渡晚年,而是因为儿子的前一个冤案受尽了惊吓、恐慌和担忧,好不容易待到高铁钢出狱,且冤案被平反,还没有过一两年舒心日子,儿子又再陷囹圄。
从高铁钢2000年第二次入狱后,高老本不轻的烟瘾便更重了,如今的他本到了含饴弄孙的晚年却不得不再次为人打工以挣一份工资以填补儿子的官司所拉下的饥荒。
“唉!
我这个儿子太不听话,当时出来后我就劝他算了,可是他偏不见我的话,到处上访,结果又把自己给弄进去了!
”高老先生一见我们的面就一个劲地抱怨道。
看着高老那苍老干瘦的样子,我们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
当晚,我与高老在三门峡聘请的律师李朝阳见了一面。
李律师戴着一幅眼镜,一付性情温和的书生模样,他和我对此案的意见基本一致,都认为公诉机关对高铁钢的六项指控皆不能成立。
第二天一早,我在李律师的陪同下来到三门峡中院,不巧本案的承办法官、审判长任法官到郑州去了,我只好回到宾馆,先研究刚从李律师手中借到的案卷材料。
案卷材料足足了一百多页,我从上午九点一刻也没休息地一直看到下午二点半,因为我下午安排去见高铁钢,我必须在会见他之前对本案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看完案卷后我的心情不太好,石野看出来了,问我的印象如何?
我直言道,我虽然没有见到高铁钢本人,但是那些同案犯笔录和证言人证言给我留下的印象是:
高铁钢就是一个地痞无赖,一个地道的流氓!
石野笑道,不是这样,高铁钢外表十分英俊,其内心也很善良;
你过去不认识他,所以不了解他。
接着,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石野与高铁钢是高铁钢在北京上访时认识的,当时,石野的两着名自传体的书出版后在现会上引起了轰动,高铁钢慕名去找他,希望他能为自己的冤案出出力。
后来在石野的帮助下,高铁钢在北京通州住了下来,有一天,石野去看他多年来一直帮助的一个为讨薪儿子被杀而上访的四川农民幸永怀,高铁钢陪他一块去,到了幸永怀家,幸永怀的妹妹幸小芳提出要请石野和高铁钢到附近餐馆吃饭。
高铁钢看到幸家一贫如洗的样子,得知幸小芳到通州是为了做一点缝纫生意来支助哥哥上访,于是坚决拒绝下馆子。
他自己到附近的超市买了一些食物,提着来到幸家,在幸家亲自下厨做熟,大家一起吃。
石野说,他正是从这件事看出高铁钢的本质。
听了石野的故事,我更想见到高铁钢本人了。
下午三时许,我、石野、李律师一起来到了看守所,石野没有律师身份,只能在看守所外等着我们。
在看守所,由于律师会见窗口只有一个,我们办好手续后只能等待这个窗口空出。
好不容易等了近一个小时,我们才坐到了会见窗口前。
过了一会儿,只听得悉悉嗦嗦一阵镣铐响后,一个高大的汉子隔着铁栅栏坐在了我们的对面。
这就是高铁钢。
尽管剃成了光头、穿着寒骖的号衣,高铁钢依然十分英俊,只是长久不从事户外活动,皮肤变得十分白净。
他一开口便传出一种十分有磁性的男高音。
高铁钢开始向我们一一澄清被指控的事实,他澄澈的眼神让我无法怀疑他这些与控方的证据完全不同的话的真实。
虽然对有些事实我早已根据其亲属的陈述和我对案卷的研究有所了解,但他的细节的提供使我对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是非曲直有了一个完整的了解,这坚定了我对为他做无罪辩护决心。
警惕
第二天,我一早又来到法院,终于见到高铁钢案合议庭的审判长任法官,这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女士,给人以十分精干的印象,在借出了全部案卷资料并复印以后,任法官问我对此案的看法,我提出了我的观点,我认为全部指控都不能成立,任法官未置可否,只是说那你就认真辩吧。
就是在这一次,我正式向法院提出了要求向本案所有“被害人”取证以及向控方的证人调查取证的申请,任法官收下了申请,但是说这要看检察官的态度。
我问,您觉得会怎样?
任法官说我认为一般不会批准。
这就是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缺乏对律师取证保障的一个事例,但是,如果律师在取证问题上不能享有同等的权利,其如何能平等地在法庭上与控方对抗呢!
事实上,在制度设计上,律师一开始就处于不平等的弱势地位。
我只有无可奈何地问:
如果不许可,法院是否应该给我一个书面的答复。
任法官回答说:
如果许可将会有书面的答复,如果不许可,就不会给我答复了。
在离开法院的时候,由于距本案起诉和受理已有较长时间,为了不超过审限,任法官当场与我订下了开庭的时间:
2019年8月2日。
距当时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
当天下午,为告知开庭的时间,我再次前往看守所会见高铁钢。
石野不放心,决定还是与我一同去,虽然他进不了看守所的大门。
在看守所办会见手续的时候,按要求我将手机存放进了看守所的铁柜。
这一次,高铁钢与我熟悉起来,谈话也轻松许多,考虑到当晚我就要离开三门峡,我打算陪他多聊聊,因为我知道,在号子里的人多半很寂寞,特别是看高铁钢这样的未决犯,长达一年左右的时间不允许家属探视,更是希望能有机会与人多沟通沟通。
于是我在进一步了解了案情和细节之后,陪着他聊了一会儿,便更主要的是要他提供可以作证的人员姓名和联系方式。
高铁钢告诉我,关于其受骗与张某在河南办所谓“中国法制观察”河南记者站时,张某向其要钱以及其为张某垫付该站办公费用的事,当时也在该站工作的一个小女孩刘某某知情,该女子后来与已离婚的高铁钢堕入了情网,并曾准备与他结婚,只是因为双方年龄相差太大,高父没有同意。
但是作了过去的情人,刘某某应该会为高铁钢作证。
另外,关于法制日报社记者雷某向其索要发稿费的事,有很多与他同在北京的上访者可以作证,其中包括曾被超期羁押近十年被释放的杨某某。
高铁钢说,这些人或与他有情,或与他有旧,他曾在困难的时候资助过这些比他更困难的人,因此,高铁钢认为他们断不会拒绝为他作证的。
不知不觉我与高铁钢聊了近三个小时,完全忘记了石野还在门外等着,待我告别高铁钢取回手机走出看守所大门时,我才发石野已不在大门口了,我想他一定是先回宾馆了。
于是我打了一辆车往回走,打开手机,我才发现有许多个未接电话,都是石野打来的。
还有几条短信,大意是你在干什么,请速回电话!
我想他在门口蹲了几个小时可能有点着急了,于是准备给他打个电话。
正在此时,接到了他的一条短信:
“我已打电话给全国律师协会,同时给你律所的主任也打了电话,我不等你了,现在正在往郑州去的路上!
这条短信不看则已,一看我就慌了神,我的第一感觉是他可以受到什么
人的施压了,可能有人在为难他,于是我马上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他一接电话便喝道:
“你为什么打电话也不接,短信也不回!
”当得知他没有离开三门峡我才喘了一口气。
考虑到我们的电话肯定有人监听,我只是简短地说:
“见面再说”。
在招待所我们见了面,当得知没有人为难他时,我才放下了心。
接着明白了他给我发那条短信的用意:
他以为我被什么非法控制了,故发此短信告诫对方不要胡来。
于是我马上告诉他看守所的规矩是会见嫌疑犯前必须交出手机,以防嫌疑犯利用律师的手机与外界联系,发生串供、通风报信、隐匿转移赃款赃物等情况。
虽然是虚惊一场,但我明白长年作为卧底记者,警惕已成了他的职业习惯,特别是考虑到是他把我拉进这场不同寻常的官司,他自觉应对我和我的家人负责,这方面的警惕性就更高。
他甚至要求我除非必须,不出宾馆;
有人敲门不问清身份和事由,不轻易开门。
“万一你一开门,闯进来一个光身子女人,接着便有人闯进来以卖淫嫖娼为由拘你,你怎么说得清楚?
不是有几个教授因此死于非命吗!
”事后证明,他的担心不是多余的。
在我下一次单独来到三门峡时,高铁钢的朋友亲眼见到人有盯我的梢。
但是,总体上我不并担心,因为毕竟本人心底坦荡,我是一个持有执业证的律师,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专业法律工作者,我来此没有任何违法勾当,而是光明正大地行使法律赋与我的权力——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更何况我是一个部队转业的正团职干部,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预备役中校军官,在全国各地都有无数情感相连的战友;
而且,我还是一个拥有近25年党龄的中共老党员,我不相信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人敢随便侵犯我的人身权利。
但是,为以防万一,我还是将我原部队政委、我人事档案所在单位海淀区人事局主管部门主任、我所在律所的主任等电话留给了石野,以防不测。
当天晚上,在嘱高父及其朋友分别按高铁钢提供名单联系证人之后,我与石野离开了三门峡。
取证
高铁钢此案,最关键也最难办的是取证。
虽然从法理来看很明白:
高的六场犯罪指控一般都不能成立。
但如前所述,向受害人取证或向控方的证人取证的路子基本走不通,我们只能考虑向其他人取证了。
我首先拨通了一个证人的电话,却是对方的弟弟接听的,而且更出人意料的是,对方告诉我其兄半年前已出车祸身故。
“幸好接电话的不是我父母,否则你一问起我哥他们还不知道要哭多半天。
”对方如是说。
真未想到事情如此凑巧,岂非天意高铁钢命中当有此一劫?
我虽如此,但是,仍然将希望寄托到以后的取证。
但回到北京后,从三门峡传来的消息却不太好,高父说大部分人不愿作证,甚至在上一次都曾挺身而出的人这次也躲躲闪闪了。
这一结果其实早在我们的预料之中,因为上一次,江建新与高铁钢的杀人喂狗案的苦主或受害人亲属是江建新那位当过坐台小姐的第四任老婆,而就是她举报的江建新和高铁钢,因此她不是一个苦主,而是一位“大义灭亲”的人,更何况她也人间蒸发了。
因此,有心想帮一把高铁钢的人不必有任何顾虑。
但是,这一次不同,这一次虽然有“受害人”,但是,这些人并不认为自己是什么苦主,至少他们都没有报案,而是由有关部门依职权立案侦查的,在这个案子里,人们隐隐约约可以看到某些强力部门的身影,因此,绝大部分人当然不敢与其作对,所以,我们的取证难度将是空前地大。
最后,只有一个在天津的高大姐同意为高作证,但是,她在天津有工作来不了北京,而按要求到天津去取证必须要有两名律师,可是另一名律师却在三门峡。
因此,我只好请同所的律师帮忙通过电话取个证。
考虑到这种形式的取证法院往往因证人的身份无法核实而拒绝承认其证据效力,我们专门询问并记录了她详细的身份和住址、电话。
高大姐所能证明的是她与高铁钢同去法律日报,高铁钢带了两万块钱上楼去交给雷某,并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