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念刘和珍君》阅读材料鲁迅杂文四篇 无花的蔷薇之二 死地 可惨与可笑 空谈文档格式.docx
《《记念刘和珍君》阅读材料鲁迅杂文四篇 无花的蔷薇之二 死地 可惨与可笑 空谈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记念刘和珍君》阅读材料鲁迅杂文四篇 无花的蔷薇之二 死地 可惨与可笑 空谈文档格式.docx(1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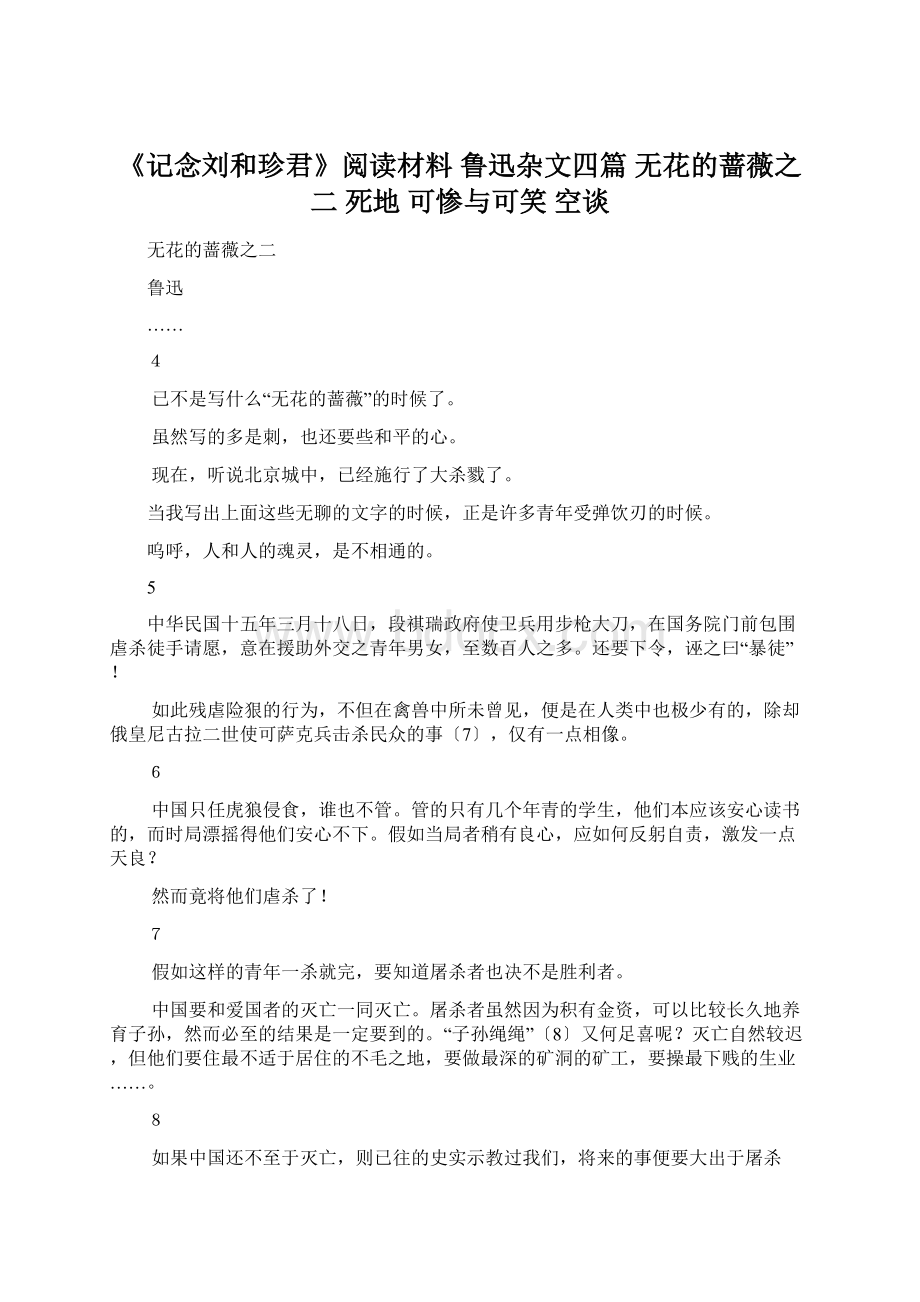
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
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9
以上都是空话。
笔写的,有什么相干?
实弹打出来的却是青年的血。
血不但不掩于墨写的谎语,不醉于墨写的挽歌;
威力也压它不住,因为它已经骗不过,打不死了。
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写。
【注释】
〔7〕一九○五年一月二十二日(俄历一月九日),彼得堡工人因反对开除工人和要求改善生活,带着眷属到冬宫请愿;
俄皇尼古拉二世却命令士兵开枪。
结果,有一千多人被击毙,两千多人受伤。
这天是星期日,史称“流血的星期日”。
〔8〕“子孙绳绳” 语见《诗经·
大雅·
抑》:
“子孙绳绳,万民靡不承。
”绳绳,相承不绝的样子
死地①
从一般人,尤其是久受异族及其奴仆鹰犬的蹂躏的中国人看来,杀人者常是胜利者,被杀者常是劣败者。
而眼前的事实也确是这样。
三月十八日段政府惨杀徒手请愿的市民和学生的事,本已言语道断②,只使我们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
但北京的所谓言论界,总算还有评论,虽然纸笔喉舌,不能使洒满府前的青年的热血逆流入体,仍复苏生转来。
无非空口的呼号,和被杀的事实一同逐渐冷落。
但各种评论中,我觉得有一些比刀枪更可以惊心动魄者在。
这就是几个论客,以为学生们本不应当自蹈死地③,前去送死的。
倘以为徒手请愿是送死,本国的政府门前是死地,那就中国人真将死无葬身之所,除非是心悦诚服地充当奴子,“没齿而无怨言”④。
不过我还不知道中国人的大多数人的意见究竟如何。
假使也这样,则岂但执政府前,便是全中国,也无一处不是死地了。
人们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
因为不易相通,杀人者便以杀人为唯一要道,甚至于还当作快乐。
然而也因为不容易相通,所以杀人者所显示的“死之恐怖”,仍然不能够儆戒后来,使人民永远变作牛马。
历史上所记的关于改革的事,总是先仆后继者,大部分自然是由于公义,但人们的未经“死之恐怖”,即不容易为“死之恐怖”所慑,我以为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但我却恳切地希望:
“请愿”的事,从此可以停止了。
倘用了这许多血,竟换得一个这样的觉悟和决心,而且永远纪念着,则似乎还不算是很大的折本。
世界的进步,当然大抵是从流血得来。
但这和血的数量,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世上也尽有流血很多,而民族反而渐就灭亡的先例。
即如这一回,以这许多生命的损失,仅博得“自蹈死地”的批判,便已将一部分人心的机微示给我们,知道在中国的死地是极其广博。
现在恰有一本罗曼罗兰的《Le-Jeu-de-L’Amour-et-de-La-Mort》(5)在我面前,其中说:
加尔是主张人类为进步计,即不妨有少许污点,万不得已,也不妨有一点罪恶的;
但他们却不愿意杀库尔跋齐,因为共和国不喜欢在臂膊上抱着他的死尸,因为这过于沉重。
会觉得死尸的沉重,不愿抱持的民族里,先烈的“死”是后人的“生”的唯一的灵药,但倘在不再觉得沉重的民族里,却不过是压得一同沦灭的东西。
中国的有志于改革的青年,是知道死尸的沉重的,所以总是“请愿”。
殊不知别有不觉得死尸的沉重的人们在,而且一并屠杀了“知道死尸的沉重”的心。
死地确乎已在前面。
为中国计,觉悟的青年应该不肯轻死了罢。
三月二十五日。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日《国民新报副刊》。
②言语道断 佛家语。
《璎珞经》:
“言语道断,心行处灭。
”“言语道断”,原意是不可言说,这里表示悲愤到无话可说。
③死地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研究系的机关报《晨报》在三月二十日的“时论”栏发表了林学衡的《为青年流血问题敬告全国国民》一文,诬蔑爱国青年“激于意气,挺(铤)而走险,乃陷入奸人居间利用之彀中”,指责徐谦等“驱千百珍贵青年为孤注一掷……必欲置千百珍贵青年于死地”,同时该文还恶毒攻击“共产派诸君故杀青年,希图利己”。
三月二十二日,《晨报》又发表陈渊泉写的题为《群众领袖安在》的社论,胡说“纯洁爱国之百数十青年即间接死于若辈(按即他所谓“群众领袖”)之手”。
④“没齿而无怨言” 语见《论语·
宪问》。
没齿,终身之意。
⑤《Le-Jeu-de-L’Amour-et-de-La-Mort》《爱与死的搏斗》,罗曼罗兰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的剧本之一,作于一九二四年。
其中有这样的情节:
国约议会议员库尔跋齐因反对罗伯斯庇尔捕杀丹东,在议会投票判决丹东死刑时,他放弃投票,并中途退出会场;
同时他的妻子又在家中接待一个被通缉的吉隆德派分子(她的情人),被人告发。
他的朋友政治委员会委员加尔来到他家,告以委员会要他公开宣布对被通缉者的态度;
在他拒绝以后,加尔便给予两张事先准备好的假名假姓的护照,劝他带着妻子一同逃走,并告诉他已得到罗伯斯庇尔的默许。
鲁迅这里所举的就是加尔在这时候对库尔跋齐所说的话。
可惨与可笑
(1)
三月十八日的惨杀事件,在事后看来,分明是政府布成的罗网,纯洁的青年们竟不幸而陷下去了,死伤至于三百多人
(2)。
这罗网之所以布成,其关键就全在于“流言”的奏了功效。
这是中国的老例,读书人的心里大抵含着杀机,对于异己者总给他安排下一点可死之道。
就我所眼见的而论,凡阴谋家攻击别一派,光绪年间用“康党”(3),宣统年间用“革党”(4),民二以后用“乱党”(5),现在自然要用“共产党”了。
其实,去年有些“正人君子”们称别人为“学棍”“学匪”的时候,就有杀机存在,因为这类诨号,和“臭绅士”“文士”之类不同,在“棍”“匪”字里,就藏着可死之道的。
但这也许是“刀笔吏”式的深文周纳(6)。
去年,为“整顿学风”计,大传播学风怎样不良的流言,学匪怎样可恶的流言,居然很奏了效。
今年,为“整顿学风”(7)计,又大传播共产党怎样活动,怎样可恶的流言,又居然很奏了效。
于是便将请愿者作共产党论,三百多人死伤了,如果有一个所谓共产党的首领死在里面,就更足以证明这请愿就是“暴动”。
可惜竟没有。
这该不是共产党了罢。
据说也还是的,但他们全都逃跑了,所以更可恶。
而这请愿也还是暴动,做证据的有一根木棍,两支手枪,三瓶煤油。
姑勿论这些是否群众所携去的东西;
即使真是,而死伤三百多人所携的武器竟不过这一点,这是怎样可怜的暴动呵!
但次日,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的通缉令(8)发表了。
因为他们“啸聚群众”,像去年女子师范大学生的“啸聚男生”(章士钊解散女子师范大学呈文语)一样,“啸聚”了带着一根木棍,两支手枪,三瓶煤油的群众。
以这样的群众来颠覆政府,当然要死伤三百多人;
而徐谦们以人命为儿戏到这地步,那当然应该负杀人之罪了;
而况自己又不到场,或者全都逃跑了呢?
以上是政治上的事,我其实不很了然。
但从别一方面看来,所谓“严拿”者,似乎倒是赶走;
所谓“严拿”暴徒者,似乎不过是赶走北京中法大学校长兼清室善后委员会(9)委员长(李),中俄大学校长(徐),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北京大学教务长(顾),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易);
其中的三个又是俄款委员会(10)委员:
一共空出九个“优美的差缺”(11)也。
同日就又有一种谣言,便是说还要通缉五十多人;
但那姓名的一部分,却至今日才见于《京报》。
(12)这种计画,在目下的段祺瑞政府的秘书长章士钊之流的脑子里,是确实会有的。
国事犯多至五十余人,也是中华民国的一个壮观;
而且大概多是教员罢,倘使一同放下五十多个“优美的差缺”,逃出北京,在别的地方开起一个学校来,倒也是中华民国的一件趣事。
那学校的名称,就应该叫作“啸聚”学校。
三月二十六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八日《京报副刊》。
(2)应为二百多人。
参看本卷第265页注(6)。
(3)“康党” 指清末参加和赞同康有为等变法维新的人。
(4)“革党” 指参加和赞同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人。
(5)“乱党” 一九一三年,孙中山领导的讨袁战争(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就把国民党作为“乱党”取缔。
(6)深文周纳 歪曲或苛刻地援用法律条文,陷人于罪。
(7)“整顿学风” 指一九二六年三月六日,西北边防督办张之江致电执政段祺瑞和总理贾德耀,侈谈“整顿学风”。
他胡说当时“学风日窳,士习日偷……现已(男女)合校,复欲共妻”,“江窃以为中国之可虑者,不在内忧,不在外患,惟此邪说诐行,甚于洪水猛兽。
”
请段祺瑞“设法抑制”。
段祺瑞接到电报后,除令秘书长章士钊复电“嘉许”外,并将原电通知国务院,责成教育部会同军警机关,切实整顿学风。
去年的“整顿学风”,参看本卷第120页注(4)。
(8)通缉令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政府下令通缉徐谦等五人,胡说他们“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
本日徐谦以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名义,散布传单,率领暴徒数百人,闯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
……徐谦等并着京内外一体严拿,尽法惩办,用儆效尤。
”徐谦(1871—1940),字季龙,安徽歙县人。
李大钊(1889—1927),参看本卷第66页注(8)。
李煜瀛,字石曾,河北高阳人。
易培基,字寅村,湖南长沙人。
顾兆熊,字孟余,河北人。
(9)清室善后委员会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冯玉祥国民军驱逐溥仪出宫后,北洋政府为办理清室善后事宜和接收故宫文物而设的机构。
(10)俄款委员会 即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
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苏俄政府宣布放弃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包括退还庚子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
一九二四年五月,两国签订《中俄协定》,其中规定退款用途,除偿付中国政府业经以俄款为抵押品的各项债务外,余数全用于中国教育事业,由中苏两国派员合组一基金委员会(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负责处理。
这里所说的三个委员,即李煜瀛、徐谦、顾兆熊。
(11)“优美的差缺” 这是引用陈西滢的话。
他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六十五期(一九二六年三月六日)的《闲话》里说:
“在北京学界一年来的几次风潮中,一部分强有力者的手段和意见,常常不为另一部分人所赞同,这一部分强有力者就加不赞成他们的人们一个‘捧章’的头衔。
然而这成了问题了。
……不‘捧章’而捧反章者,既然可以得到许多优美的差缺,而且可以受几个副刊小报的拥戴,为什么还要去‘捧章’呢?
(12)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六日《京报》登载消息说:
“该项通缉令所罗织之罪犯闻竟有五十人之多,如……周树人(原注:
即鲁迅)、许寿裳、马裕藻……等,均包括在内。
”
空谈
一
请愿的事,我一向就不以为然的,但并非因为怕有三月十八日那样的惨杀。
那样的惨杀,我实在没有梦想到,虽然我向来常以“刀笔吏”的意思来窥测我们中国人。
我只知道他们麻木,没有良心,不足与言,而况是请愿,而况又是徒手,却没有料到有这么阴毒与凶残。
能逆料的,大概只有段祺瑞,贾德耀〔2〕,章士钊和他们的同类罢。
四十七个男女青年的生命,完全是被骗去的,简直是诱杀。
有些东西——我称之为什么呢,我想不出——说:
群众领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3〕。
这些东西仿佛就承认了对徒手群众应该开枪,执政府前原是“死地”,死者就如自投罗网一般。
群众领袖本没有和段祺瑞等辈心心相印,也未曾互相钩通,怎么能够料到这阴险的辣手。
这样的辣手,只要略有人气者,是万万豫想不到的。
我以为倘要锻炼〔4〕群众领袖的错处,只有两点:
一是还以请愿为有用;
二是将对手看得太好了。
二
但以上也仍然是事后的话。
我想,当这事实没有发生以前,恐怕谁也不会料到要演这般的惨剧,至多,也不过获得照例的徒劳罢了。
只有有学问的聪明人能够先料到,承认凡请愿就是送死。
陈源教授的《闲话》说:
“我们要是劝告女志士们,以后少加入群众运动,她们一定要说我们轻视她们,所以我们也不敢来多嘴。
可是对于未成年的男女孩童,我们不能不希望他们以后不再参加任何运动。
”(《现代评论》六十八)为什么呢?
因为参加各种运动,是甚至于像这次一样,要“冒枪林弹雨的险,受践踏死伤之苦”的。
这次用了四十七条性命,只购得一种见识:
本国的执政府前是“枪林弹雨”的地方,要去送死,应该待到成年,出于自愿的才是。
我以为“女志士”和“未成年的男女孩童”,参加学校运动会,大概倒还不至于有很大的危险的。
至于“枪林弹雨”中的请愿,则虽是成年的男志士们,也应该切切记住,从此罢休!
看现在竟如何。
不过多了几篇诗文,多了若干谈助。
几个名人和什么当局者在接洽葬地,由大请愿改为小请愿了。
埋葬自然是最妥当的收场。
然而很奇怪,仿佛这四十七个死者,是因为怕老来死后无处埋葬,特来挣一点官地似的。
万生园多么近,而四烈士〔5〕坟前还有三块墓碑不镌一字,更何况僻远如圆明园。
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
三
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
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
我对于这回的牺牲者,非常觉得哀伤。
但愿这样的请愿,从此停止就好。
请愿虽然是无论那一国度里常有的事,不至于死的事,但我们已经知道中国是例外,除非你能将“枪林弹雨”消除。
正规的战法,也必须对手是英雄才适用。
汉末总算还是人心很古的时候罢,恕我引一个小说上的典故:
许褚赤体上阵,也就很中了好几箭。
而金圣叹还笑他道:
“谁叫你赤膊?
”〔6〕至于现在似的发明了许多火器的时代,交兵就都用壕堑战。
这并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虚掷生命,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
在战士不多的地方,这生命就愈宝贵。
所谓宝贵者,并非“珍藏于家”,乃是要以小本钱换得极大的利息,至少,也必须卖买相当。
以血的洪流淹死一个敌人,以同胞的尸体填满一个缺陷,已经是陈腐的话了。
从最新的战术的眼光看起来,这是多么大的损失。
这回死者的遗给后来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许多东西的人相,露出那出于意料之外的阴毒的心,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
四月二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国民新报副刊》。
〔2〕贾德耀 安徽合肥人。
曾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三一八惨案的凶手之一,当时是段祺瑞临时执政府的国务总理。
〔3〕群众领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研究系机关报《晨报》发表陈渊泉写的题为《群众领袖安在》的社论,诬蔑徐谦等“非迫群众至国务院不可,竟捏报府院卫队业已解除武装,此行绝无危险,故一群青年始相率而往”。
并公然叫嚷:
“吾人在纠弹政府之余,又不能不诘问所谓‘群众领袖’之责任。
”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六十八期(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评论三一八惨案的《闲话》中,也企图把这次惨案的责任,推到他所说的“民众领袖”身上去,说他“遇见好些人”,都说“那天在天安门开会后,他们本来不打算再到执政府。
因为他们听见主席宣布执政府的卫队已经解除了武装……所以又到执政府门前去瞧热闹。
……我们不能不相信,至少有一部分人的死,是由主席的那几句话。
要是主席明明知道卫队没有解除武装,他故意那样说,他的罪孽当然不下于开枪杀人者;
要是他误听流言,不思索调查,便信以为真,公然宣布,也未免太不负民众领袖的责任。
〔4〕锻炼 这里是罗织罪名的意思。
〔5〕四烈士 指辛亥革命时炸袁世凯的杨禹昌、张先培、黄之萌和炸良弼的彭家珍四人。
他们合葬于北京西直门外约二里的万生园(即今北京动物园),在张、黄、彭三人的墓碑上都没有镌上一个字。
圆明园在北京西直门外二十余里的海淀,是清朝皇帝避暑的地方,清咸丰十年(1860)被侵入北京的英法联军焚毁。
三一八惨案后,被难者家属和北京一些团体、学校代表四十多人,于二十七日召开联席会议,由民国大学校长雷殷报告,他认为公葬地点以圆明园为宜,并说已非正式地与内务总长屈映光商议,得到允诺等。
会议遂决定成立“三一八殉难烈士公葬筹备处”,并拟葬各烈士于圆明园。
〔6〕许褚 三国时曹操部下名将。
“赤体上阵”的故事,见小说《三国演义》第五十九回《许褚裸衣斗马超》。
清初毛宗岗《三国演义》评本,卷首有假托为金圣叹所作的序,并有“圣叹外书”字样,每回前均附加评语,通常就都把这些评语认为是金圣叹所作。
金圣叹(1608—1661),名人瑞,江苏吴县人,明末清初文人,曾批注《水浒》、《西厢记》等书,他把所加的序文、读法和评语等称为“圣叹外书”。
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
周作人
我是极缺少热狂的人,但同时也颇缺少冷静,这大约因为神经衰弱的缘故,一遇见什么刺激,便心思纷乱,不能思索,更不必说要写东西了。
三月十八日下午我往燕大上课,到了第四院时知道因外交请愿停课,正想回家,就碰见许家鹏君受了伤逃回来,听他报告执政府卫兵枪击民众的情形,自此以后,每天从记载谈话中听到的悲惨事实逐日增加,堆积在心上再也摆脱不开,简直什么事都不能做。
到了现在已是残杀后的第五日,大家切责段祺瑞贾德耀,期望国民军的话都已说尽,且已觉得都是无用的了,这倒使我能够把心思收束一下,认定这五十多个被害的人都是白死,交涉结果一定要比沪案坏得多,这在所谓国家主义流行的时代或者是当然的,所以我可以把彻底查办这句梦话抛开,单独关于这回遭难的死者说几句感想到的话。
──在首都大残杀的后五日,能够说这样平心静气的话了,可见我的冷静也还有一点哩。
我们对于死者的感想第一件自然是哀悼。
对于无论什三死者我们都应当如此,何况是无辜被戕的青年男女,有的还是我们所教过的学生。
我的哀感普通是从这三点出来,熟识与否还在其外,即一是死者之惨苦与恐怖,二是未完成的生活之破坏,三是遗族之哀痛与损失。
这回的死者在这三点上都可以说是极重的,所以我们哀悼之意也特别重于平常的吊唁。
第二件则是惋惜。
凡青年夭折无不是可惜的,不过这回特别的可惜,因为病死还是天行而现在的戕害乃是人功。
人功的毁坏青春并不一定是最可叹惜,只要是主者自己愿意抛弃,而且去用以求得更大的东西,无论是恋爱或是自由。
我前几天在茶话《心中》里说:
“中国人似未知生命之重。
故不知如何善舍其生命,而又随时随地被夺其生命而无所爱惜。
”这回的数十青年以有用可贵的生命不自主地被毁于无聊的请愿里,这是我所觉得太可惜的事。
我常常独自心里这样痴想:
“倘若他们不死……”我实在几次感到对于奇迹的希望与要求,但是不幸在这个明亮的世界里我们早知道奇迹是不会出来的了。
──我真深切地感得不能相信奇迹的不幸来了。
这回执政府的大残杀,不幸女师大的学生有两个当场被害。
一位杨女士的尸首是在医院里,所以就搬回了;
刘和珍女士是在执政府门口往外逃走的时候被卫兵从后面用枪打死的,所以尸首是在执政府,而执政府不知怎地把这二三十个亲手打死的尸体当作宝贝,轻易不肯给人拿去,女师大的职教员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到十九晚才算好容易运回校里,安放在大礼堂中。
第二天上午十时棺殓,我也去一看;
真真万幸我没有见到伤痕或血衣,我只见用衾包裹好了的两个人,只余脸上用一层薄纱蒙着,隐约可以望见面貌,似乎都很安闲而庄严地沉睡着。
刘女士是我这大半年来从宗帽胡同时代起所教的学生,所以很是面善,杨女士我是不认识的,但我见了她们俩位并排睡着,不禁觉得十分可哀,好象是看见我的妹子──不,我的妹子如活着已是四十岁了,好象是我的现在的两个女儿的姊姊死了似的,虽然她们没有真的姊姊。
当封棺的时候,在女同学出声哭泣之中,我陡然觉得空气非常沉重,使大家呼吸有点困难,我见职教员中有须发斑白的人此时也有老泪要流下来,虽然他的下颔骨乱动地想忍住也不可能了。
这是我昨天在《京副》发表的文章中之一节,但是关于刘杨二君的事我不想再写了,所以抄了这篇“刊文”。
四
二十五日女师大开追悼会,我胡乱做了一副挽联送去,文曰:
死了倒也罢了,若不想到二位有老母倚闾,亲朋盼信。
活着又怎么着,无非多经几番的枪声惊耳,弹雨淋头。
殉难者全体追悼会是在二十三日,我在傍晚才知道,也做了一联:
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
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
惭愧我总是“文字之国”的国民,只会以文字来纪念者。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之后五日
在比较中阅读《记念刘和珍君》
钱理群
《记念刘和珍君》是中学语文课本中的传统教材,有关的参考资料数不胜数,关于文章的内容、结构与语言的分析已经十分深入细致,似乎已无“文章”可做。
要想在“山穷水尽”之中发现“又一村”的新境界,恐怕得变换我们阅读、思考的思路、角度与方法。
本文即试图作一个试验:
引入鲁迅的兄弟、同为现代散文大家的周作人所写的同一题材的散文:
《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作一次“比较”阅读。
而且我们的分析重点将不放在思想内容的“比较”上——尽管此时周氏兄弟已经失和,但就思想倾向的主要方面而言,两篇文章毋宁说是“同”大于“异”的,无论是对爱国学生的同情与赞颂,对北洋军阀政府的谴责和抗争,对所谓“学界名流”“诬陷”的义愤与揭露,以及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强调,对“请愿”之举的保留……都是惊人的相似,真正的差异倒在于周氏兄弟有着不同的气质,不同的思考方式和情感表达方式,由此而产生不同的文章风格。
—我们的“比较”,就从这一角度切入。
(—)
两篇文章都从写作心境写起。
周作人在《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一文开头就以平实的语气陈述自己在事件发生过程中心绪的变化:
先是由于“逐个增加”的“悲惨人事”“堆积在心上”,既多愤激,又存“期望”,“心思纷乱”,“摆脱不开”,“什么事都不能做”,自然也无以作文。
“到了现在已是残杀后的第五日”—时间的距离,使人们从最初的愤激中冷静下来,抛却了无益的幻想,不再说“彻底查办”之类的梦话,也就将“心思收束”到对于“死者”本身的思考,终于可以执笔作文,能够说这样平心静气的“话”了。
“平心静气”自然含有某种“反语”成分,周作人其实也并不能真正“平心静气”。
但已经从事件本身“升华”、“超越”出来,进入理性思考,却也是事实。
感情经过理性的过滤,自然滤尽了其中的愤激焦躁,而变得“平静”——看起来是情感浓度的淡化,力度的减弱,其实是一种情感的深化。
周作人从原先“心思纷乱”,到现在“心思收束”,可以“平心静气”地说话、著文.是一个情感流动的自然过程。
鲁迅在《记念刘和珍君》里宣布:
“我已经出离愤怒了”,那么,他也进入了深入的理性思考(我们以后还会专门著文来讨论他的这些思考),但他的“心思”却没有这么容易“收束”。
这乃是因为作为一个本质上的“诗人”,他的“冷静”的思考总是包裹着最“热烈”的情感,“思”与“情”永远拥抱、纠结为一体。
而且,他的内心始终交织着“两种情感欲求”的搏战:
一方面是激情喷发的冲动,另一方面却是克制激情的欲求——这是真正的历史的强者所独有的情感选择.如鲁迅在下文中所说明的那样,他不愿在“非人间”的仇敌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