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疏议之不孝制度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唐律疏议之不孝制度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唐律疏议之不孝制度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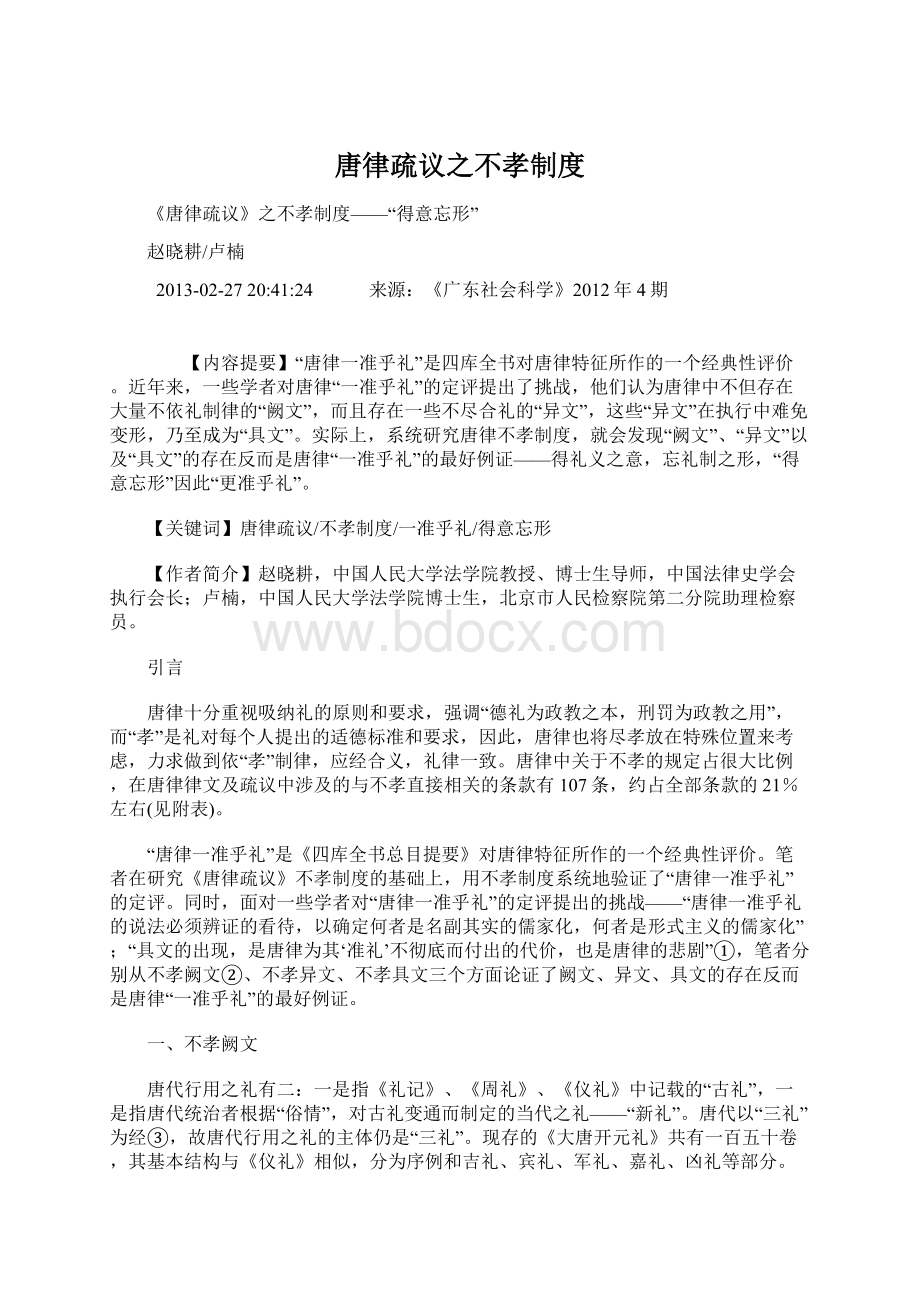
谓律、令无条,理不可为者。
事理重者,杖八十。
议曰:
杂犯轻罪,触类弘多,金科玉条,包罗难尽。
其有在律在令无有正条,若不轻重相明,无文可以比附。
临时处断,量情为罪,庶补遗阙,故立此条。
情轻者,笞四十;
”
笔者认为,本条中“理不可为者”的“理”就是指“礼”,即符合儒家伦理要求的“情理”。
郑国执政子产曾说:
“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
”④朱熹讲得更清楚“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
”管子即说:
“礼者,谓有理也”。
⑤可见,“理”与“礼”往往是相通的。
唐律中多次出现的“理”之名义也证明了这一点,如:
父母之恩,昊天罔极。
嗣续妣祖,承奉不轻。
枭镜其心,爱敬同尽,五服至亲,自相屠戮,穷恶尽逆,绝弃人理,故曰“恶逆”。
⑥
父为子天,有隐无犯。
如有违失,理须谏诤,起敬起孝,无令陷罪。
若有忘情弃礼而故告者,绞。
⑦
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殴击,子孙理合救之。
⑧
父母知女擅去,理须训以义方。
不送夫家,违法改嫁,独坐父母。
⑨
因此,唐律谓“律、令无条,理不可为者”,也即是“律、令无条‘礼’不可为者”。
这样,违礼而不违律的不孝行为自然就被纳入法典范围,要受到唐律的处罚,轻者处笞四十,重则杖打八十。
非但如此,唐律还在条文中亲自示范了这种规定的应用方法。
例一:
问曰:
闻丧不即举哀,于后择日举讫,事发合得何罪?
答曰:
依礼:
“斩衰之哭,往而不返。
齐衰之哭,若往而返。
大功之哭,三曲而依。
小功、缌麻,哀容可也。
”准斯礼制,轻重有殊,闻丧虽同,情有降杀。
期亲以上,不即举哀,后虽举讫,不可无罪,期以上从“不应得为重”;
大功,从“不应得为轻”;
小功以下,哀容可也,不合科罪。
若未举事发者,各从“不举”之坐。
关于得知期亲以上亲属死亡而不马上举哀、择日再举哀的行为。
《唐律疏议·
职制》“匿父母及夫等丧”条惩罚得知期亲以上亲属死亡而不举哀的行为,规定:
“诸闻父母若夫之丧,匿不举哀者,流二千里”;
“闻期亲尊长丧,匿不举哀者,徒一年”;
“大功以下尊长,各递减二等。
”但是,如果遇到闻亲丧不立即举哀,而于以后再择日举哀的情况又该如何惩处呢?
此条“问答”按照礼制要求认真分析情势,认为“准斯礼制,轻重有殊,闻丧虽同,情有降杀”,故最终做出了明确的指示:
“期亲以上,不即举哀,后虽举讫,不可无罪,期以上从‘不应得为重’;
大功,从‘不应得为轻’”,即分别要被杖八十,笞四十。
例二:
居父母丧,与应合嫁娶之人主婚者,杖一百;
若与不应嫁娶人主婚,得罪重于杖一百,自从重科。
若居夫丧,而与应嫁娶人主婚者,律虽无文,从“不应为重”,合杖八十。
其父母丧内,为应嫁娶人媒合,从“不应为重”,杖八十;
夫丧从轻,合笞四十。
关于在父母丧期内,为其子女做媒的行为。
户婚》“居父母丧主婚”条惩处在父母的丧期内为其子女主婚的行为,规定:
“诸居父母丧,与应嫁娶人主婚者,杖一百。
”那么,如若在父母的丧期内为其子女做媒又当如何呢?
此条“疏议”又作了补充:
“其父母丧内,为应嫁娶人媒合,从‘不应为重’,杖八十”,即仍用“不应得为”来制裁这种行为。
例三:
有人嫌恶前人,妄告父母身死,其妄告之人,合科何罪?
父母云亡,在身罔极。
忽有妄告,欲令举哀,若论告者之情,为过不浅,律、令虽无正法,宜从“不应为重”科。
关于妄告他人其父母死亡的行为。
诈伪》“父母死诈言余丧”条处罚在父母死后诈称他人死亡而不解官回家守丧的不孝官吏,规定:
“诸父母死应解官,诈言余丧不解者,徒二年半。
”然而,如果遇到某些“心怀叵测”之人,诈称他人父母死亡,又该科以何罪呢?
此条“问答”分析说:
“忽有妄告,欲令举哀,若论告者之情,为过不浅,律、令虽无正法,宜从‘不应为重’科”。
以上违反“理”或“礼”的行为都属“法无明文规定”的不孝阙文,可是,这些行为还是被纳入了唐律刑罚的处罚之中,难怪传统观点认为唐律的内容疏而不漏。
另外,又因为唐律中的“疏议”与律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因此“断狱者皆引疏(议)分析之”。
⑩唐代前期有一道判文,内容是因冯甲在亲丧期间“朝祥暮歌”,虽然律文并没涉及这种行为,但官吏仍然依礼进行了惩处,判曰:
父母之丧,三年服制;
孝子之制,万古增悲。
朝祥暮歌,是亵于礼,以哭止乐,斯慰所怀。
诉词既款服终,言讼请依科断。
(11)
此判书并没有说到具体的判决结果,但是,照以上情况分析来看,这位在父母大祥祭后之当日作歌的不孝子被杖打八十大板是在所难免了。
可见,律条有阙时,《唐律疏议》可以直接以礼释律、以礼补律;
疏议在阐释律条时,其解释也皆须“合理”以合“礼”。
因此,关于不孝之律条纵有阙文,也难逃唐律“礼法”网,《唐律疏议》之不孝制度果真“一准乎礼”。
二、不孝异文
《唐律疏议·
斗讼》“告祖父母、父母”条,疏议曰:
“子孙之于祖父母、父母,皆有祖父子孙之名,其有相犯之文,多不据服而断。
实际上,礼制规定的服制本来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和缌麻五等(12);
而唐律中的五服却变更为:
斩衰、期、大功、小功、缌麻五等。
这种改变的原因在于,齐衰三年本系子为母服,而唐律规定父母不分;
齐衰杖期本系孙为祖父母服,而唐律中祖父母例同父母;
齐衰五月本系曾孙为曾祖父母服,齐衰三月本系玄孙为高祖父母服,而唐律规定“称祖父母者,曾高同”,“称孙者,曾、玄同”(13),结果,所有的直系血亲都从齐衰中被划了出来,只剩下旁系血亲的不杖期。
上述条文中所说的“多不据服而断”指的就是这种情形。
可见,唐律虽然袭用“五服制度”作为自己定罪量刑的标准,但并没有“严格”依照五服制度断罪,即出现了与“礼制”不合的“异文”。
除上述例证外,这样的典型异文就是《唐律疏议·
户婚》“妻无七出而出之”条,其疏议曰:
七出者,依令:
“一无子,二淫泆,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
三不去者,谓:
一,经持舅姑之丧;
二,娶时贱后贵;
三,有所受无所归。
这条规定的直接依据是汉代的《大戴礼记·
本命》:
妇有七去:
不顺父母去;
无子去;
淫去;
妒去;
有恶疾去;
多言去;
窃盗去。
……妇有三不去:
有所娶无所归,不去;
与更三年丧,不去;
前贫贱后富贵,不去。
《小戴礼记·
内则》注也说:
妇有七出:
不顺父母一,无子二,淫三,妒四,有恶疾五,多言六,窃盗七。
三不去:
有所受无所归,不去;
曾经三年丧,不去;
仔细阅读、对比上述律法的规定与礼制的内容,我们会发现如下三个问题。
问题一:
为何礼称“不顺父母”而律言“不事舅姑”?
问题二:
七出入律后,“无子”出妻因何取代“不顺父母”跃居第一位?
与之自相矛盾的是,“经持姑舅丧”却成为“三不去”之首?
问题三:
既然“七出”入律时,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次序上,都对礼制规范作出了诸多的改变,那么,我们还能坚持说这一与不孝相关的制度是“一准乎礼”的吗?
首先,从内容上看,礼称“不顺父母”而律言“不事舅姑”,这二者内容虽大致相同,但却反映了礼与律这两种不同社会规范的区别:
依礼,言“顺”不言“事”,“顺”的中心是取悦舅姑,即是以舅姑的主观好恶作为评判标准;
依法,言“事”不言“顺”,“事”的中心是侍奉,即是以妻的客观行为作为判断尺度。
所以礼与法,一个强调主观修养,一个强调客观可操作性,他们担负不同的职责,发挥不同的作用。
因此,在引礼入律时,对礼制规范做出适当的调整,更有利于法律规范趋向合理化和世俗化,使之达到某种程度的统一性、确定性和可操作性,使得人们的行为可以控制在有序的和可预见的范围内。
《唐律疏议》中“居父祖丧”的规定正是贯彻了这一原则。
礼曰“丧事主哀”,而“哀”的标准是很难统一的,如哭丧的声音、憔悴的形容(14)等;
同时,礼制中的许多规定也只能靠人们自觉执行和自我监督,如丧期内不能饮酒食肉,不能与妇人同房,而且要睡草苫枕土块等(15)。
而法律规范则要求守丧制度具有可操作性,也就是说,他人可以通过守丧者的外在行为而对其进行评判与监督。
因此礼制中那些无法统一、不便监督的行为标准在法律规范中消失了;
某些礼制规范则通过变通而具备了可操作性,因而被法律所采纳,如居丧饮酒食肉转化为居丧参与吉席,居丧与妇人同房转化为居丧生子等。
综上,我们可以说“礼称‘不顺父母’而律言‘不事舅姑’”基本上是唐代立法技术进步的结果,这说明,唐代立法者已经充分注意到了礼制与法律不同的适用范围和功能。
可见,引礼入律在唐代已经相当成熟,这一时期多的是对礼制的合理吸收,少的是对礼制的盲从。
其次,从顺序上看,“不顺父母”本来是礼制中出妻罪名之首,而七出入律后,“无子”取代了“不顺父母”跃居第一位,这样的规定似乎暗示了唐代父母地位的降低。
而同时,对抗“七出”的“三不去”制度中,“经持姑舅丧”却又从原来礼制中的第二名,升为律法中“三不去”之首,这种改变显然又预示着唐代父母地位的提高,强调子妇对姑舅的孝丧可以成为对抗七出的法定理由。
关于父母地位规定的这一下一上,着实让人困惑。
瞿同祖先生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指出:
“法律上七出的秩序与礼书所载略异,秩序的先后或表示社会着重点的不同。
无子跃居第一,妒嫉及恶疾退处最后,其变动应与社会的意识形态密切相关。
”(16)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从顺序上看,七出入律后,无子、淫佚、口舌、盗窃的位次有所上升,而妒忌、恶疾的位次相对下降,这表明法律对继嗣、财产和家族伦常的重视较礼制有所上升,位次的前置与后置本身就是社会的根本要求和特征在法律上的反映。
这就不难理解“经持姑舅丧”为何在入律时跃居“三不去”之榜首,原因就是因为唐代统治者走的是“以孝治天下”的礼治路线。
至于无子跃居首位,则有着更深层次的社会经济原因。
唐初,经过隋末战乱,民间残破已极。
贞观六年,魏征谏曰:
“今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
”(17)自太宗执政后,虽君臣上下齐心望治,然而却受到劳动力匮乏的限制。
“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不及隋之十一”(18)。
这是因为,在“以农为本”的社会,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大力推行重农政策,而要推行重农政策,解决劳动力匮乏问题便成为当务之急。
为此,唐太宗先后多次采取了回赎外流人口的措施,如“武德九年九月,突厥颉利献马三千匹,羊万口;
上不受,但诏归所掠中国户口”;
贞观三年时,户部奏言:
“中国人自塞外来归及突厥前后内附、开四夷为州县者,男女一百二十余万口。
”(19)又如,贞观五年正月“以金帛购中国人因隋乱没突厥者男女八万人,尽还其家属”(20)。
但是回流人口毕竟有限,要从根本上解决劳动力缺乏的问题,还应靠人口自然繁殖。
为此唐太宗要求男女及时婚配,贞观元年,颁布《令有司劝勉民间嫁娶诏》,诏曰:
昔周公治定制礼,垂裕后昆,命媒氏之职,以会男女。
……若不中之以婚姻,明之以顾复,便恐中馈之礼斯废,绝嗣之衅方深,既生怨旷之情,或致淫奔之辱。
宪章典故,实所庶几,宜令有司,所在劝勉。
其庶人男女无室家者,并仰州县官人,以礼聘娶。
……男年二十,女年十五已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婚媾,令其好合。
……刺史县令以下官人,若能婚姻及时,鳏寡数少,量准户口增多,以进考第。
如导劝乖方,失于配偶,准户减少附殿。
(21)
在上述诏令中,太宗不但规定男子年二十以上,女子年十五以上必须及时婚配,就连战后大量丧期已过的鳏夫寡妇都“并须申以婚媾,令其好合”。
另外,唐太宗还以婚姻是否及时、鳏寡数量多少、户口是增是减,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依据,规定:
“刺史、县令以下官人,若能婚姻及时,鳏寡数少,量准户口增多,以进考第。
如劝导乖方,失于配偶,准户减少附殿。
”综上可见,阻碍人口增长的“无子”无疑是统治者当时最为重视的问题。
因此,“无子”出妻在唐代初次入律时被调至“七出”之首也是势在必行、众望所归了。
法律是一种应时性很强的统治工具,立法是一个把统治阶级的意志上升为法律的过程,高的立法技术,不但应使制订的法律准确地反映统治阶级的要求,而且应该符合时代的需求。
因此,唐代的统治者能正确地运用自己手中掌握的立法权,根据“世情”的变化,删改损益礼制的内容,改礼入律,正体现了其高超的立法技术。
最后,“七出”入律时,确实对礼制规范作出了诸多的改变,成为我们所讨论的“不孝异文”。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坚持说这一与不孝相关的制度是“一准乎礼”的。
首先我们说,何谓礼?
礼就其内容而言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一是,礼义;
二是,礼仪,也就是文中一再提到的礼制。
其中,礼义是礼的宗旨和精神,其核心内容即是伦理道德——忠、孝、节、义四字而已。
而礼制,是礼的外在表现,又称为“礼之文”、“礼之容”、“礼之貌”,即礼的制度、条文和规范。
礼义与礼制在礼治体系中显然是前者,即礼义占主导地位。
上文中所说的“七出”异文,准确地说是对礼制,即礼仪的改变。
《慎子》曰:
“礼从俗”;
《汉书》曰:
“王者必因前王之礼,而顺时施宜,有所损益,节人之心,稍稍制作。
”(22)可见,礼具有从俗、顺时,与时俱进的特点。
因此,在礼义精神的指导下,根据世情、俗情对包括律法在内的规范做出调整是礼治的应有之义。
文中唐律对礼制的变通,“无子”地位逾居“不顺父母”之上,正是生法者根据世情、民情,顺应礼治精神做出的正确抉择。
同时,它与“经持姑舅丧”地位的上升所体现出来的“以孝治国”的原则也并不矛盾,试问:
如果连子孙都没有,又何谈孝敬呢?
所谓俗语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也。
总而言之,唐律中的不孝异文真正做到了“得意忘形”——得礼义之意,忘礼制之形,因此“更准乎礼”了!
三、不孝具文
何谓具文?
具文,即空文,徒有其文而实不符。
《汉书·
宣帝纪》有云:
“上计簿,具文而已,务为欺谩,以避其课。
”按照此种解释,唐律不孝制度中确实出现了一些“徒有其文而实不符”,即有法不依的情况,下面就以备受争议的“孝子复仇”为例进行阐释。
(1)复仇具文:
斗讼》“祖父母为人殴击子孙即殴击之”条规定:
“诸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殴击,子孙即殴击之,非折伤者,勿论;
折伤者,减凡斗折伤三等;
至死者,依常律。
贼盗》“谋杀人”条规定:
“诸谋杀人者,徒二年;
已伤者,绞;
已杀者,斩。
从而加功者,绞;
不加功者,流三千里。
造意者,虽不行仍为首,即从者不行,减行者一等。
唐律中没有专门规定复仇条款,但由以上两条律文可以看出,唐律虽赋予子孙援助父祖的合法性,且在刑罚上给予减免,但其仍然是禁止私自复仇杀人的——“至死者,依常律”,即“谋杀人”条所规定的“已杀者,斩”等。
那么如果在唐代现实生活中出现复仇杀人的案件,生法者和执法者们又是怎样处断的呢?
据统计,《新唐书·
孝友传》和《新唐书·
烈女传》中较著名的复仇案件有十例(23),其中只有三例真正按律论死,其他七例的复仇者都得到了宽宥,更有甚者,卫孝女甚至因为复仇得到了太宗皇帝“赐田宅”的嘉奖,可见,上述两条律文对复仇来说确属“徒有其文而实不符”的具文。
下面再来看唐律中与复仇相关的另一个重要规定,“私和”:
贼盗》“亲属为人杀私和”条:
“诸祖父母、父母及夫为人所杀,私和者,流二千里;
期亲,徒二年半;
大功以下,递减一等。
受财重者,各准盗论。
虽不私和,知杀期以上亲,经三十日不告者,各减二等。
从律文看,唐律虽然限制复仇,但又严惩“知仇不报告”,尤其重惩父祖被人杀子孙“私下和解”的行为。
这是因为,私下和解既违反了律法之规定,又违反了“父之仇,弗与共戴天”的礼之要求。
因此若有犯者,处流二千里;
若受仇家之财物重于私和之罪的,则最多要受到处流三千里的重惩。
(24)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发生在唐代的真实案例:
穆宗即位……有前率府仓曹曲元衡者,杖杀百姓柏公成母。
法官以公成母死在辜外,元衡父任军使,使以父荫征铜。
柏公成私受元衡资货,母死不闻公府,法寺以经恩免罪。
潾议曰:
“……柏公成取货于雠,利母之死,悖逆天性,犯则必诛。
”奏下,元衡杖六十配流,公成以法论至死,公议称之。
(25)
本案中,柏公成接受了杀母仇人曲元衡的钱财,隐瞒其母亲的死讯,不向官府报告。
依律,私和者流二千里,受财重者准盗论,即不论柏公成受财多少,亦至多处流三千里。
而兵部员外郎裴潾则以柏公成收受仇家钱财,以母死谋利,违背天理为由,要求将其处死。
最终,皇帝下旨将柏公成处以死刑,而杀人者曲元衡被杖六十后配流。
这其中对柏公成的处罚显然已经超出了律文规定的“私和”罪的量刑幅度,但“公议称之”。
可见,对复仇的轻宥和对私和的严惩,确似是架空律文,以礼代律的表现。
(2)驳具文论:
试想一:
如果唐律不禁止私自复仇,甚至鼓励复仇,将会出现怎样的情况?
南齐时发生过一起令人啼笑皆非的连环报仇案:
朱谦之,字处光,吴郡钱唐人也。
父昭之,以学解称于乡里,谦之年数岁,所生母亡,昭之假葬田侧,为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
同产姊密语之,谦之虽小,便哀戚如持丧。
年长不婚娶。
永明中,手刃杀幼方,诣狱自系。
县令中灵勖表上,别驾孔稚圭、兼记室刘琎、司徒左西掾张融笺与刺史豫章王曰:
“礼开报仇之典,以申孝义之情;
法断相杀之条,以表权时之制。
谦之挥刃酬冤,既申私礼;
系颈就死,又明公法。
今仍杀之,则成当世罪人;
宥而活之,即为盛朝孝子。
杀一罪人,未足弘究;
活一孝子,实广风德。
张绪、陆澄,是其乡旧,应具来由。
融等与谦之并不相识,区区短见,深有恨然。
”豫章王言之世祖,时吴郡太守王慈、太常张绪、尚书陆澄并表论其事,世祖嘉其义,虑相复报,乃遣谦之随曹虎西行。
将发,幼方子恽于津阳门伺杀谦之,谦之之兄选之又刺杀恽,有司以闻。
世祖曰:
“此皆是义事,不可问。
”悉赦之。
(26)
本案中,先是朱幼方放火烧毁了朱谦之母亲的尸首(此尸首被谦之父临时安葬于田侧),于是朱谦之自小将仇铭记于心,后终于被他找到机会将仇人朱幼方杀死,并到官府自首。
齐武帝闻之很赞赏朱谦之的孝举,将其赦免。
同时为防朱幼方的亲属再行报复,命人陪他西去。
不料,在将行之际,朱谦之还是被埋伏已久的朱幼方之子朱恽杀死。
而朱谦之的哥哥朱选之闻听此讯,又刺杀了朱恽。
有关部门上报此案,齐武帝竟说:
“此皆义事,不可问”,最后也赦免了朱选之。
上述案例中君臣齐心置律法于不顾,放纵孝子,风德虽广,杀戮不止,正所谓“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仇,其乱谁救”?
(27)所以,唐律中“祖父母为人殴击”条承认子孙援救父祖合法性的制度合情!
“至死者,依常律”,禁止私自复仇的规定有理!
试想二:
如果唐律不设“知仇不报告”和“私下和解”之条,又当如何?
自古以来,为亲复仇就是为人子孙责无旁贷的事业,也是儒家孝道理论的内在要求,虽然自西汉初复仇行为就开始受到法律的追究(28),但千百年来屡禁不止。
《旧唐书·
刑法志》有云:
“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志;
许复仇,则人将依法专杀,无以禁止其端矣。
”因此,唐律既然关闭了子孙“私自复仇”之门,就必须再为其打开一条“成全孝心”之道,否则就难以符合礼经中“父之仇不共戴天”的孝义。
唐律中不许私和的规定,则正好完美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一方面,唐律禁止子孙私自复仇,另一方面唐律又要求子孙必须复仇,只不过其对复仇问题的处理已转变成了“国家报复主义”,即其要求子孙必须依据法律程序告官请求“报复”,私和不纠和私行擅杀都是律所不容的,此条规定之用心良苦,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试想三:
既然实践中统治者常对复仇者予以宽宥,唐律规定复仇杀人者死岂不成具文?
“在礼父仇不同天,而法杀人必死”,二者孰轻孰重,分寸很难把握,因此,负责此类案件的官员,通常不敢贸然判决,而是将案情上报宸极。
皇帝在处理复仇案件时,又多给予宽宥,这样就给人造成一种印象:
复仇杀人常能免死,“杀人者死”自成具文。
但是,这种看法忽略了一个关键的因素,唐律开宗明义曰:
“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
”(29)可见,儒家虽然重视礼的教化作用,但并没有因此忽略刑的威慑作用。
正因为律严惩复仇杀人,才没有出现“转相仇杀,随无已时”的乱世,进而因孝复仇报到宸极的案件还是“屈指可数”的。
因此对复仇杀人,必须严惩,一旦有人“视死如归”、“志在殉节”冒死复仇时,自有最高统治者结合案情、折中礼法对其做出相应判决,以求经律两不失,韩愈的设想便符合这一考虑:
复仇,据礼经则义不同天,征法令则杀人者死。
礼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异同,必资论辩,宜令都省集议闻奏者。
伏以子复父仇,见于《春秋》,见于《礼记》,又见于《周官》,又见于诸子史,不可胜数,未有非而罪之者也。
最宜详于律,而律无其条,非阙文也。
盖以为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训;
许复仇,则人将倚法专杀,无以禁止其端矣。
……宜定其制曰:
凡有复父仇者,事发,具其事由,下尚书省集议奏闻。
酌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