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达我将尽力表彰中华文明文档格式.docx
《张广达我将尽力表彰中华文明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张广达我将尽力表彰中华文明文档格式.docx(4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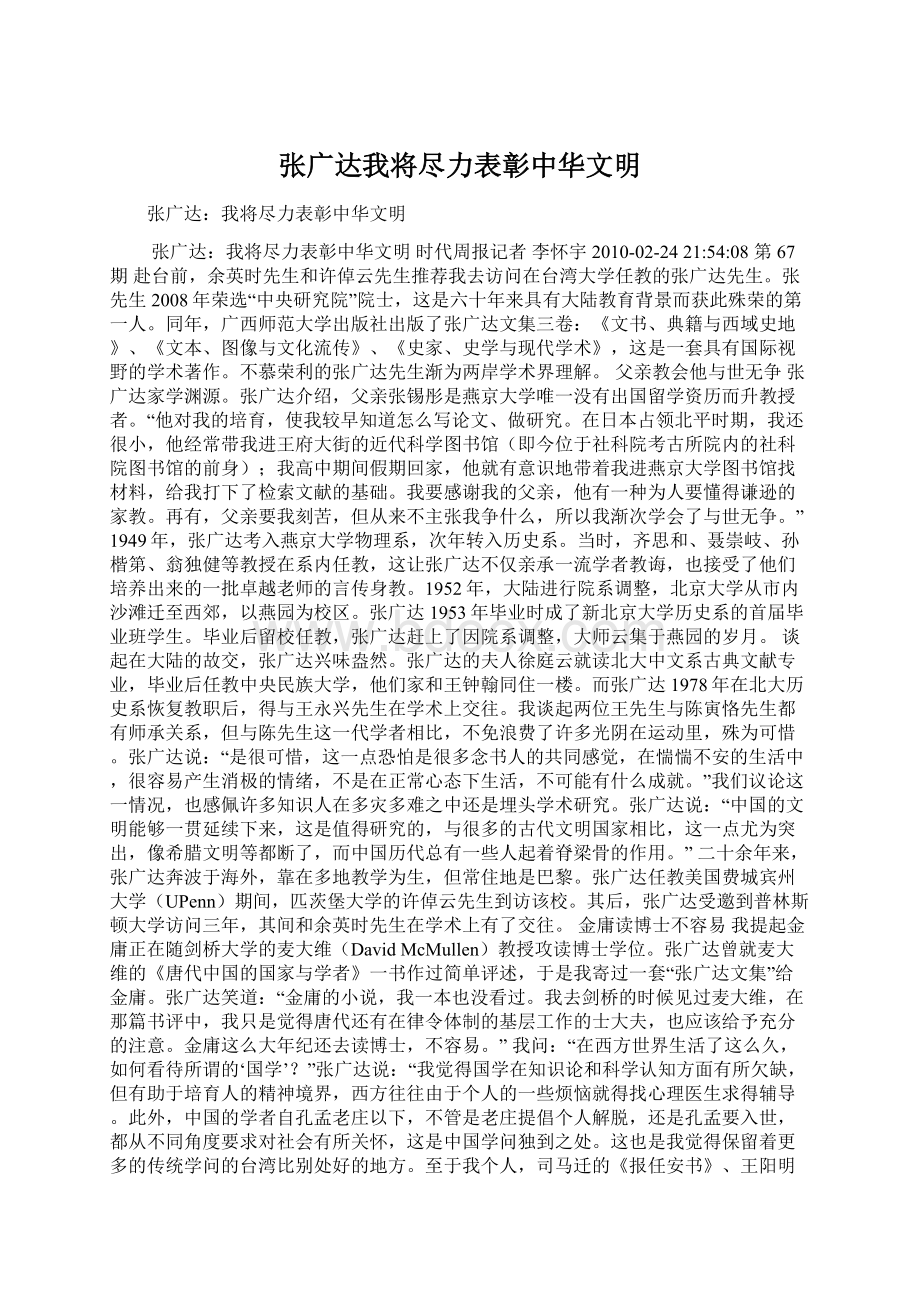
我高中期间假期回家,他就有意识地带着我进燕京大学图书馆找材料,给我打下了检索文献的基础。
我要感谢我的父亲,他有一种为人要懂得谦逊的家教。
再有,父亲要我刻苦,但从来不主张我争什么,所以我渐次学会了与世无争。
”1949年,张广达考入燕京大学物理系,次年转入历史系。
当时,齐思和、聂崇岐、孙楷第、翁独健等教授在系内任教,这让张广达不仅亲承一流学者教诲,也接受了他们培养出来的一批卓越老师的言传身教。
1952年,大陆进行院系调整,北京大学从市内沙滩迁至西郊,以燕园为校区。
张广达1953年毕业时成了新北京大学历史系的首届毕业班学生。
毕业后留校任教,张广达赶上了因院系调整,大师云集于燕园的岁月。
谈起在大陆的故交,张广达兴味盎然。
张广达的夫人徐庭云就读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毕业后任教中央民族大学,他们家和王钟翰同住一楼。
而张广达1978年在北大历史系恢复教职后,得与王永兴先生在学术上交往。
我谈起两位王先生与陈寅恪先生都有师承关系,但与陈先生这一代学者相比,不免浪费了许多光阴在运动里,殊为可惜。
张广达说:
“是很可惜,这一点恐怕是很多念书人的共同感觉,在惴惴不安的生活中,很容易产生消极的情绪,不是在正常心态下生活,不可能有什么成就。
”我们议论这一情况,也感佩许多知识人在多灾多难之中还是埋头学术研究。
“中国的文明能够一贯延续下来,这是值得研究的,与很多的古代文明国家相比,这一点尤为突出,像希腊文明等都断了,而中国历代总有一些人起着脊梁骨的作用。
”二十余年来,张广达奔波于海外,靠在多地教学为生,但常住地是巴黎。
张广达任教美国费城宾州大学(UPenn)期间,匹茨堡大学的许倬云先生到访该校。
其后,张广达受邀到普林斯顿大学访问三年,其间和余英时先生在学术上有了交往。
金庸读博士不容易我提起金庸正在随剑桥大学的麦大维(DavidMcMullen)教授攻读博士学位。
张广达曾就麦大维的《唐代中国的国家与学者》一书作过简单评述,于是我寄过一套“张广达文集”给金庸。
张广达笑道:
“金庸的小说,我一本也没看过。
我去剑桥的时候见过麦大维,在那篇书评中,我只是觉得唐代还有在律令体制的基层工作的士大夫,也应该给予充分的注意。
金庸这么大年纪还去读博士,不容易。
”我问:
“在西方世界生活了这么久,如何看待所谓的‘国学’?
”张广达说:
“我觉得国学在知识论和科学认知方面有所欠缺,但有助于培育人的精神境界,西方往往由于个人的一些烦恼就得找心理医生求得辅导。
此外,中国的学者自孔孟老庄以下,不管是老庄提倡个人解脱,还是孔孟要入世,都从不同角度要求对社会有所关怀,这是中国学问独到之处。
这也是我觉得保留着更多的传统学问的台湾比别处好的地方。
至于我个人,司马迁的《报任安书》、王阳明的《瘗旅文》曾在我跌倒后召唤我重新上路。
”我说:
“听黄进兴先生说,你非常关心台湾的时局,每天晚上都看台湾新闻。
“现在台湾表面看很乱,但是它的民主体制初步建立了起来,两党交替也粗具规模。
只要我有工夫,睡觉之前都看一眼名嘴们的讨论,因为一个念历史的人还是要关怀现实,研究过去是为了关怀未来。
”名家访谈:
“不能简单袭取大唐时代的辉煌”访问前几次电话联系,我在电话里特别说明等我到了台湾大学校门时,再请他骑单车过来见面。
张先生还是早早就在台大门口等候了。
我们沿着台大校园的椰林大道边走边聊,初次见面便有许多共同的话题。
“北大”的土与“燕京”的洋时代周报:
1949年考大学时,你怎么去读物理系呢?
那个时候凡是念书好的学生,都要报考理工,你要是第一志愿就去念文科,表示你理科不行。
那时候就是年轻不输这口气,表明我也是可以念理工的。
我学数学、物理理论不成问题,但是我动手操作能力有问题,我的物理实验的误差往往在两位数以上,一次实验不及格可以,长期的话,怎么再升级?
所以我读了一年的物理系后转到了历史系。
时代周报:
余英时先生跟你是同一年进燕京大学,但他当时进的是历史系。
是的,我们都是1949年入学,等我1950学年度转到历史系,他已经走了。
他是寒假回香港去探亲,父亲余协中先生把他留了下来,亲自带他去见钱穆的。
我和余先生要等到五十年后在普林斯顿方才结识。
你那时候已经对历史感兴趣了?
我对文科感兴趣比较早,即便念理科的话,我已经对文科不陌生了。
但是我注意的文科不是填词、作诗、音韵等。
我很早就注意念外语,注意西洋史中国史并重。
那时我虽然是个年轻的孩子,但是已经有一些史学的概念。
燕京大学历史系中,聂崇岐先生跟我父亲是好朋友,聂先生是我恩师,对我如何打好基本功有些课外指点。
我访问过王钟翰先生,他当时已经开始教你清史了?
他开始教清史,他当时在燕大的贝公楼顶层的哈佛燕京学社有一个研究室,他在那儿念《清实录》,很勤奋。
他把研究《清实录》的成果拿来给我们讲,讲清初的拜堂子等风俗习惯。
他有时也把他的老师邓之诚请来上堂课,所以我也听过邓之诚先生的几次讲课。
邓先生的儿子叫邓珂、邓瑞,是比我高两班的和低一班的同学,有时我跟邓珂、邓瑞来往的时候也跟随着他们去邓先生家,坐在客厅里面,跟着王剑英等研究院的大师兄一道听听老先生说这说那,他对掌故非常熟。
1952年的院系调整后,新北大是几个学校合在一起的?
老北大、燕京、清华,可能还有些从辅仁大学等校并过来的老师,但人数不会很多。
很有意思,那时候三个学校的校风是不一样的,燕京的人数虽然有点少,但是受洋人的影响,比较带点洋味。
北大呢,所谓的土,就是一中午就得午睡。
还是很正经地睡,脱了衣服,有时候脱了裤子背心,燕京的人看着都瞪大了眼睛。
那时候是大师云集,有很多人是真正的大师。
尤其是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老北大、燕京、清华合并到一起,各系的主力教授是名副其实的大牌教授,校园内简直抬头就是大师,哲学系、中文系、文学研究所、历史系、外语系、经济系等大师密度之大,今天颇难想象。
那时候,中文系、历史系集中在文史楼二层,西边是中文系,东边是我们系,挤在东头角落里的是图书馆系,图书馆系是小系,但那也都是刘国钧、王重民等大牌教授任教。
那时候北大拥挤着那么多大牌教授,却没什么人出来拥戴他们为大师,今天没国学了,反倒雨后春笋般地遍地冒出大师。
有意思。
学术界的浮躁与谦逊时代周报:
毕了业以后就是留校?
留校。
我在大学的最后一年也没念什么书。
共产党进城后,为接管,为南下,为抗美援朝,几度动员在校学生参军参干,同学陆续走了不少。
到我们毕业时,主要就是老北大、清华、燕京的同学,并在一起不到30人。
留校3个人,我是其中一个。
留下以后把我放到世界史教研室,原因就是我会点外文,有一个念书的名声。
等到48岁真正上了讲坛,跟邓广铭先生的提携有很大关系?
“文革”结束后他出任历史系系主任,我从世界史转到中国史,就是他认为不能让我总是做翻译、资料工作,所以我很感念他。
我能够从世界史领域转到中国史领域跟邓广铭先生很有关系。
陆扬说他上世纪80年代在北大读书时,有一次看你在图书馆借了一本余英时先生的《历史与思想》。
他大概是从那里认识余先生的名字的。
那时候你已经对前沿的学术都很感兴趣?
只要有机会我就涉猎。
这里没有什么奥妙,只要留心,只要注意积累,就会知道得早一些、多一些,尽管那时候中国门户没有开放,更没有google。
在这方面,我还是很感念我的父亲和老师们早早就让我打下了检索文献的基本功。
在当时的历史系,我还有一位大师兄陈庆华,博闻强记,我也很受他的影响。
他是邵循正先生门下的首席大弟子,邵先生写文章也常靠他搜集材料。
我常常和这位大师兄讨论海内外学术动态,比方说徐复观、牟宗三、唐君毅、张君劢这些人出去了以后又怎么样。
余英时先生成名很早,海外华人里,杨联陞之后,在哈佛最耀眼的应该就是他了,所以我知道余先生的名字较早,也注意他的著作。
余英时先生当时在台湾是很有影响的。
是啊,人们老讲国宝,余先生才是真正的国宝。
有些有成就的人是给吹捧而成大师的,还有些有成就的人无形中把自己放大,自居为大师,但是,一旦自我膨胀了,大概也就成不了真正的大师了。
王国维先生什么时候自居为大师了?
还不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我觉得余先生旧学根底深厚,那是得自钱穆先生的真传。
另外,我深感余先生不像我,我的一些认识和体验是付出了惨痛代价得来的,而余先生待人谦逊,平和理性,是自己读书真正读通了的结果。
我实际上拿余先生当作自己的一个师长看待,尽管他只比我大一岁。
余先生的成就越来越大,但在他身上看不到任何自满的影子。
许倬云先生也是如此。
你跟许倬云先生接触多吗?
有不少接触。
他是我初到美国的时候主动打电话来跟我联系的,我很感谢他,其后一直提携我。
许先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学问无比渊博,思路无比敏捷,无论提一个多么复杂的问题,他都会很快给你一个鞭辟入里的明确回答。
他和余先生一样,为人也总是那么谦逊,非常平易平和。
线性思考与多元思考时代周报:
到了海外,在学术上有什么新的收获?
初到海外,我曾想走王重民、向达先生的老路,打算也到各处去搜罗一些流落到海外的珍稀图书,看一些敦煌文书的原件。
不久,我决定将主要的精力和时间用于了解西方学者治学的路数。
现在我主要的精力是研究中西文化的对比,考察研究中国史的大家的治学路数跟中国学者治学路数的同异。
日本人方面,我以研究内藤湖南的唐宋时代观为一个例证。
法国人方面,我选择沙畹为主,看看沙畹及其门生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等研究中国的路数跟中国传统学术的区别在哪里。
你到过的国家的学术研究有什么新的方法值得借鉴?
出去以后,觉察西方学者很注意理论思维和阐释,做多角度或多面相的多元思考。
我开始意识到,我在国内教书和研究中国历史,习以为常的往往是做从古到今的线性铺叙和线性思维,在讲授和研究中外交流史的时候再加上世界史做参照系,如此而已。
现在,我处理史料,开始意识到还可以从历史的时间观对史料所反映的文化与历史再做思考。
海外研究中亚史和唐史的人多吗?
研究古代中亚操印欧语的民族的人较多,他们感兴趣的是研究印欧人的来龙去脉,探索印欧人在历史的空间和时间这两维中的分布以及发展的过程。
在历史上,中亚是游牧民族往来迁徙的通道,东西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
中亚对唐代的重要性在于,在唐代前期,西域的安西四镇是唐代京城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的安全屏障;
到唐代中期,先有751年的怛逻斯之败绩,继有粟特胡安史之叛乱,唐朝开始退出中亚,是为唐朝由盛转衰的契机;
到唐代后期,中亚地区在宗教上伊斯兰化,语言上突厥化,中亚史迈入一个新阶段。
所有这些,无不与中国史有莫大关系。
你的研究涉及到现在大陆很流行的一个学问—敦煌学,到底敦煌学成不成一个学?
不叫它敦煌学,你也没办法找一个概括性的名词称呼它,只能叫这个非常勉强的称呼,反正都是研究那批卷子。
而且敦煌的汉语卷子只是一部分,还有好多胡语卷子,中国大陆学者不大管,所以即便叫敦煌学,也没把这些研究都概括进去。
余英时先生讲到中国情怀的问题。
你有中国情怀吗?
我有我的中国情怀。
中国能够几千年延续下来,是全世界留下文献最多的国家,这个民族能够存续到今天绝非偶然,我将尽我的最大力量加以表彰。
但是,另一方面,我不能不管不顾我们传统文化中的阙失和缺点。
我的中国情怀是尊重国内各个民族群体的感受、考虑和东亚各个邻国的关系、正视世界各个地区联系日益紧密的现实的中国情怀,而不是无根据地、盲目地不管现实世界的发展、不研究境内境外的“他者”。
我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但又是生活在反思性的现代化时代的中国人,这就决定了我不能简简单单地袭取辉煌的大唐时代或大清帝国时代的中国情怀。
当美国学者罗友枝、柯娇燕、欧立德、路康乐、罗维廉等纷纷提出清史研究上一些新思考的时候,我无法闭目塞听,我的中国情怀不允许我无视“他者”提出的一些值得思考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