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课本themerelyverygood课文翻译Word文件下载.docx
《英文课本themerelyverygood课文翻译Word文件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英文课本themerelyverygood课文翻译Word文件下载.docx(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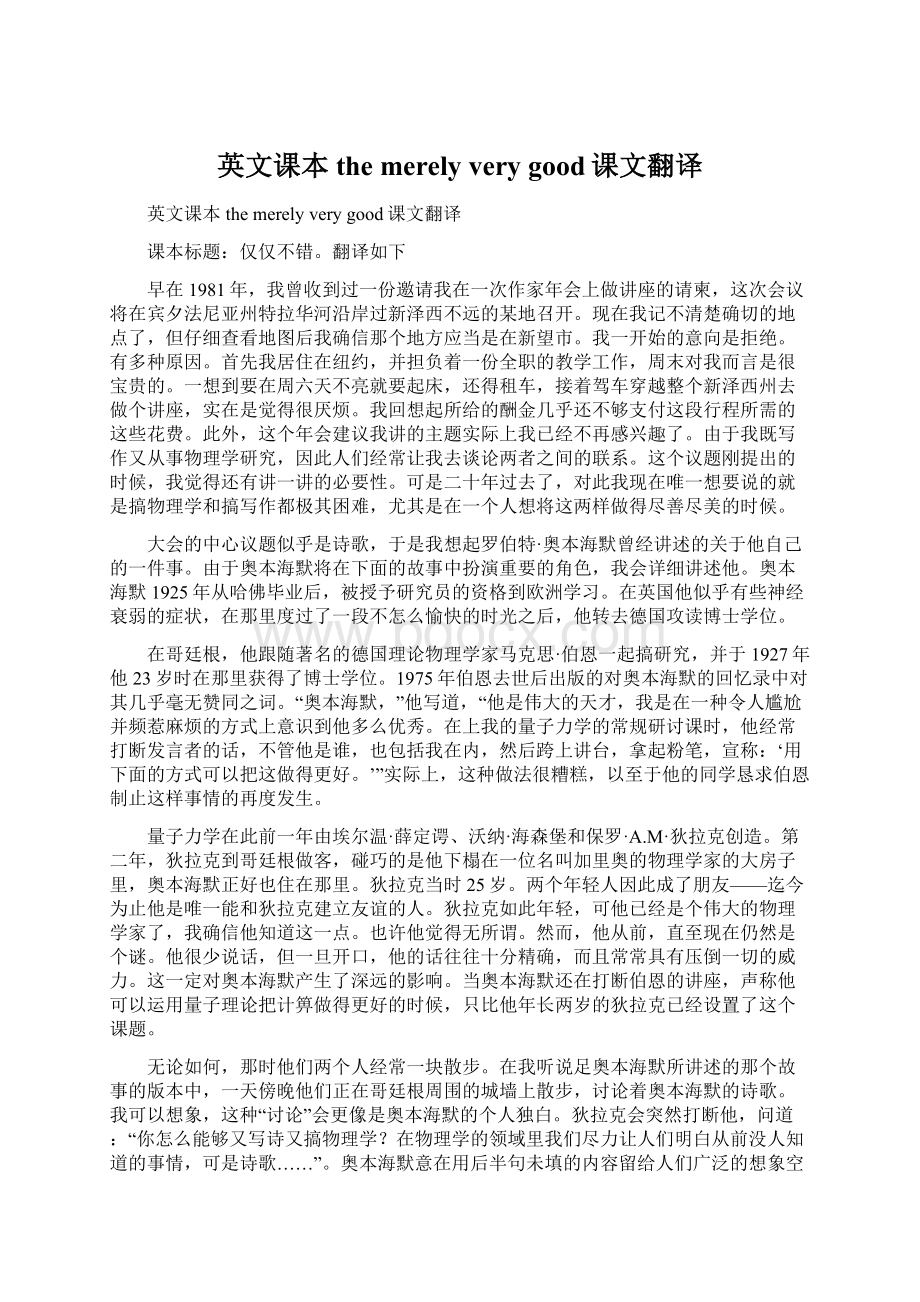
“奥本海默,”他写道,“他是伟大的天才,我是在一种令人尴尬并频惹麻烦的方式上意识到他多么优秀。
在上我的量子力学的常规研讨课时,他经常打断发言者的话,不管他是谁,也包括我在内,然后跨上讲台,拿起粉笔,宣称:
‘用下面的方式可以把这做得更好。
’”实际上,这种做法很糟糕,以至于他的同学恳求伯恩制止这样事情的再度发生。
量子力学在此前一年由埃尔温·
薛定谔、沃纳·
海森堡和保罗·
A.M·
狄拉克创造。
第二年,狄拉克到哥廷根做客,碰巧的是他下榻在一位名叫加里奥的物理学家的大房子里,奥本海默正好也住在那里。
狄拉克当时25岁。
两个年轻人因此成了朋友——迄今为止他是唯一能和狄拉克建立友谊的人。
狄拉克如此年轻,可他已经是个伟大的物理学家了,我确信他知道这一点。
也许他觉得无所谓。
然而,他从前,直至现在仍然是个谜。
他很少说话,但一旦开口,他的话往往十分精确,而且常常具有压倒一切的威力。
这一定对奥本海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奥本海默还在打断伯恩的讲座,声称他可以运用量子理论把计箅做得更好的时候,只比他年长两岁的狄拉克已经设置了这个课题。
无论如何,那时他们两个人经常一块散步。
在我听说足奥本海默所讲述的那个故事的版本中,一天傍晚他们正在哥廷根周围的城墙上散步,讨论着奥本海默的诗歌。
我可以想象,这种“讨论”会更像是奥本海默的个人独白。
狄拉克会突然打断他,问道:
“你怎么能够又写诗又搞物理学?
在物理学的领域里我们尽力让人们明白从前没人知道的事情,可是诗歌……”。
奥本海默意在用后半句未填的内容留给人们广泛的想象空间。
尽管听听人们对此的反应可能会很有趣,可这似乎并不适合在以诗歌为主题的年会上去讨论。
尽管有这么多不去参加会议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但另外两个原因最终还是占了上风。
首先,由于我刚刚同一位极其热衷于写作的年轻女士同沐爱河。
她对写作是如此热切以至于为此她甚至辞掉了一家广告公司的报酬丰取的工作,给了自己一年时间,在此期间她只靠积蓄生活,除了写作什么也不做。
这么做的确称得上勇气可嘉,可是像许多如此尝试的人一样,她逐渐觉得这事异常艰难,并且毫无进展。
事实上,她已经有些泄气了。
因此,为让她高兴,振作起来,我建议参加这个会,在会上她也许有机会同与她处于相同困境的人谈谈。
这个暂且不提,我读到会议的暂定议程,在得知其他的导师之中有斯蒂芬·
斯彭德。
这才决定了我最终确定去的行程,原因我会马上解释。
我得首先说明我并不是斯彭德诗歌的狂热崇拜者。
对我而言,他是那种关于自己作品的评论比作品本身更有趣的那类人之一。
不过我曾饶有兴趣地读过斯彭德的自传《世界中的世界》,尤其是书中谈到的一位对我很重要的诗人,即W.H.奥登。
奥登的狄拉克式的冷静清晰,对语言的十足妙用,对严肃的事情的幽默感——例如“至少我现代风格的作品会给人带来欢乐,就如英国的主教在论述量子力学。
”这样的诗句——对我来说具有非同一般的魅力。
我为斯彭德对奥登的痴迷所吸引。
奥登对于斯彭德所产生的意义一定跟狄拉克对于奥本海默一样,不断地提醒着“伟大”与“仅仅不错”之间的差别。
另外,与奥本海默一样,斯彭德看起来似乎有些“不够集中”,这也让我印象深刻。
一部分信仰犹太教,一部分有点同性恋倾向,一部分又是英国当权派中的人物,人们很奇怪他用什么时间来写诗。
不像奥登和狄拉克,也许他们极其怪异的举止很自然就把他们自己与世隔绝。
他们像激光光束一样集中。
1981年我还有所不知的是斯彭徳曾于1956年11月简短地拜访过普林斯顿的高级研究院,是在我到那里的前一年,比狄拉克常年访问中的一次还早两年。
直到1986年斯彭德的日记发表以后我才知道这些。
斯彭德在日记中对他那次访问的描述十分吸引人,包括所提到的和没有提到的事情。
在日记的开头他写逍:
“奥本海默住在一所漂亮的房子里,内部几乎彻底粉刷成白色。
”
这就是研究院主管的公寓。
斯彭德没苻注意到,由于奥本海默的西方情结,他的庭院里还有一匹古怪的马。
斯彭德接着写道:
“奥本海默有漂亮的油画。
我们刚一进来,他就说,‘现在是欣赏梵·
高的时候了。
’我们走进他的起居室,看到一幅优秀的梵·
高作品,在画上太阳髙髙地悬挂在几乎完全被阴影所笼罩的田地上空。
”在我驾着篷顶露个大洞的折篷汽车,翻山越岭从洛斯阿拉莫斯风尘仆仆赶来赴约的这次与奥本海默的首次见而结束的时候,他对我说他和他妻子有些画,也许我什么时候愿意看看。
我那时不太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样的画,几个月以后我受邀来到一个在奥本海默家里举办的晚会,才意识到他说的是一幅梵·
高的画。
几年以后,我了解到这是他从他父亲那儿继承的小规模收藏的一部分,他自己从来没有再增添过。
斯彭德在日记中对奥本海默的相貌做了描述:
“罗伯特·
奥本海默是我见过的样貌最奇特的人之一。
他的头就像一个聪明的小孩的头,后脑勺很长,让人想到被埃及人特意拉长的那些脑壳。
他的脑壳给人的感觉像脆弱易碎的鸡蛋壳,撑在一根细细的脖子上面。
他的表情看起来总是神采奕奕,但同时又像苦行僧一般。
”在我看来这个描写大部分都是准确的,只是他遗漏了这样一个事实:
奥本海默有一幅像一个大量时间在户外度过的人那样满布晒纹的相貌,而事实也是如此。
斯彭德似乎也没有对奥本海默的那双总是闪着一种谨慎的寒光的眼睛进行评论。
暹罗猫的眼睛也可以给人一种类似的感觉。
但是更更重要的是,出现在斯彭徳的日志中的奥本海默是一个游离于斯彭德本人的生活环境之外的脱离实体的人物。
日记中也没有评论这样一个事实:
三年前奥本海默曾因被疑为对国家不忠而受到“审讯”,其接触国家机密文件的权利被剥夺。
不利于他的一项指控是他的妻子凯瑟琳·
普宁·
奥本海默也是约瑟夫·
戴勒特的前妻。
约瑟夫·
戴勒特曾是一名共产党员,在1937年与西班牙共和军的战斗中牺牲。
同一年,斯彭德也是英国共产党员,当时也在西班牙。
奥本海默知道这件事吗?
他总是知道他所感兴趣的人的大多数事情。
“基蒂”·
奥本海默知道这件亊吗?
这与斯彭德来访期间她正在楼上养“病”避而不见的事实是否有关?
斯彭德在日记里没有任何评述。
他那时在想什么?
他们两人有许多可以互相倾诉的事情,却什么都没谈,谈的只是苏伊士运河的入侵。
我在研究院的第二年的秋天,狄拉克来到这里访学。
我们都知道他要来,却没有人真的遇到过他,尽管谣言有人看到他在远处的身影。
当时已经50多岁的狄拉克,在物理学界仍然占据游有点奇怪的一席之地。
与爱因斯坦不同的是,他能够紧跟研究领域的发展形势,还能不时地品头论足一番。
但是跟爱因斯坦一样,他没有建立学派,没有追随者,也没有培养出几个学生。
基本上也没有合作者。
有一次被问及此事时,他说:
“物理学上真正有价值的见地,只属于个人。
”这个说法好像对诗歌也挺合适。
他曾经在剑桥大学教授量子理论课程,在那里他坐着牛顿曾经执掌过的卢卡斯教授的席位,在教授课程时他以一种梢确的、掐头去尾的方式念着与课题有关的他本人的著作中的东西。
当有人对此质疑时,他回答说他对该课题钻研至深,但没有更好的方式演示出来。
在研究院有一个每周一次由奥本海默主持的物理学研讨会,他还是不停地打断发言者。
初秋的一天,其中一个研讨会正在进行,当时那个小房间容纳了大约有40余位与会者。
这时门开了,狄拉克走了进来。
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不过经常看到他的照片。
他本人比照片好多了。
他大致穿的是蓝色的套装——西裤、衬衫、领带,还有,我记得他还穿着一件毛衫。
但是真正给人留下刻骨难忘的印象的是他的那双过膝的、粘满污泥的橡胶靴。
后来证明他是在离研究院不远的树林里用了很长的时间手持板斧朝特顿大致的方向开辟一条小路。
几年以后,当我开始给《纽约人》杂志撰稿时,试阁要一个狄拉兑的个人简介,他建议我们可以一边淸理那条小路一边找一些时间来谈这件事。
很明显他仍然在从事着这项工作。
现在大约25年过去了。
太阳还没有升起,我正驾车和我的女友穿越新泽西州。
我们大约在早晨五点钟离开纽约,这样我才能及时到会做一个安排在上午的讲座。
我胡乱拼凑了一些关于物理学与写作之间的关系的东西。
我们俩都没好好地吃一顿早饭。
当我们穿越林肯隧道时,我想起我的同伴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讲的一件关于狄拉克的轶事。
他当时正开车穿过这座隧道送狄拉克从纽约去普林斯顿。
已经通过隧道的某个时候,狄拉克打破沉默说道:
平均起来,如果把通行费提高一倍而只把收费站建在隧道的一端,收上来的钱其实是一样多的。
几年以后,口岸管理部门似乎做了同样的分析,然后把收费站的数量减半。
我们经过了通向普林斯顿方向的岔道。
很想去拜访一下。
可是那时奥本海默已经去世,狄拉克和妻子住在佛罗里达。
他的妻子是他的物理学家同伴尤金·
维格纳的妹妹。
狄拉克过去常常把妻子以维格纳的妹妹的身份介绍给人们,比如:
“我想让你们认识一下维格纳的妹妹。
”狄拉克于1984年在佛罗里达去世。
然后我和我的女友在当地的一家咖啡馆吃了顿不人流的午餐,会议方好像没有准备正式的午餐。
此时我情绪不佳,厌烦透顶,想马上启程回纽约去,但是我的女友非常想多待一阵,至少等到看看部分斯彭德的诗歌讲习班,所以我们留了下来。
因为从前我不曾参加过这种诗歌讲习班,所以无法想象其中会有些什么内容。
我倒是去过很多物理学讲习班,因此太知道它们都可能做什么:
六个物理学家在一个带有黑板的房间里彼此叫嚷。
斯彭德要举行诗歌讲习班的房间里挤得满满当当的,容纳了大约有三十个人。
一个人也许不应该过于以貌取人,可是这些人大多数是女士——在我看来似乎过于迷恋诗歌,视它为救命稻草一般。
如果那时我能有幸接触到斯彭德的日记的话(不过这些日记几年以后才出版),我就会明白他对所有的这一切已经习以为常了。
事实上,自从十年前他从伦敦的大学学院退休以后就开始给这样的人群做讲座和开讲习班来维持生计。
我还得知,在1981年的时候他对此已经十分厌倦了,他也厌倦了去当他如今已经过世了的朋友——如奥登、C戴·
刘易斯以及其他人的替身。
他虽然比他们每个人都长寿,可是仍活在他们的阴影里,尤其是奥登,那个与他在牛津初次结识的人,刚好和奥本海默遇到狄拉克是同一年龄,也是同一时期。
斯彭德带着一叠讲习班成员写的诗走了进来。
他没做任何开场就直接开始读起学员们的诗来。
我对于那些诗竟然写得如此糟糕感到十分,他们大多数都像一串清单,诸如“天空、性爱、海洋、大地、红色、绿色、蓝色”等等。
斯彭德没有露出任何想表达对这些诗的看法的意思,只是时不时间断朗读,找到作者问类似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你选用红色而不是绿色?
红色对你意味着什么?
”他对这种流程十分熟练,如同在用自动驾驶仪一般。
很遗憾斯彭德的日记中没有记载关于这段时期的只言片语,但是很明显他当时有着一种丰富多彩的社交生活:
某日与杰奎琳·
奥纳西斯一同进餐,一星期以后在缪顿的罗氏银行——手段高明。
我感觉无论他怎么想都与这个讲习班无关。
然而不知为什么,我越来越觉得恼怒。
我猜这不关我的事。
但我耗费了一整天的时间,我觉得斯彭德欠了我们很多。
我说不出来欠的是什么——反正很多。
我的女友一定预料到了我要做些什么,因为她开始在她随身带来的一个大笔记本上狂写一通。
最终,在听完了一个尤其恶劣的“淸单”之后,我举起了手。
斯彭德看起来有点惊讶,但还是叫起了我。
“那为什么也算是一首诗?
”我问道。
几年后读了他的日记我才发现,我问的这是一个他已经被学生问过很多遍却从来没有想出一个他自己满意的答案的问题。
1935年,在一篇奥登为一本给小学生写的诗集做的序中,他对诗歌给出了“难忘的演讲”这样的定义。
这个定义听起来还不赖,直到有人问道:
对谁难忘?
这很重要吗?
如果不重要,为什么要弄讲习班?
我已经记不太清楚当时斯彭德是怎么回答我的,但是后来我告诉他,在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我听过T.S.艾略特的讲座。
讲座后听众中有一个学生问艾略特他认为最美的英文诗句是什么,一个愚蠢的问题,真的,这个问题就如同问最大的数字是什么一样。
但令我万分吃惊的是,艾略特毫不犹豫地回答了这个问题,“瞧,清晨披着金黄色的氅蓬,踏着髙山上的露珠从东方走来。
”于是我问斯彭德,他认为最美的英文诗句是哪一句。
他从椅子上站起,坚定地在黑板上写下了一行奥登的诗句。
他以一种我永难忘怀的复杂表情看着诗句——悲伤、惊叹、悔恨,或许还夹杂着妒忌。
他慢慢地背诵了一遍,然后坐了回去。
此刻房间里悄无声息。
我感谢了他,随后与我的女友离开了课堂。
之前我已经很多年没有想过这些事了,可是最近由于某种原因,我几乎又都想起来了。
我记得所有的细节,唯独忘了斯彭德写在黑板上的那行诗句。
我的的确确能够记起来的就是那句诗与月亮有关一反正就是某种关于月亮的东西。
我十五年前的那位女友如今已经不是我的女友了,所以我也没法去问她。
我一直是个收集成癖的人,热衷于收集过去的数据资料,多数资料以条款的形式列出,甚至曾经对返税起了作用。
或许我保存了那次会议的章程,上面会写着那句诗。
因此我仔细翻看了装着1981年材料的信封,但没有找到一丁点儿关于那次旅行的资料。
后来我有了个主意——十分愚蠢的(lunatic)、月亮的(lunar),也许这两个字差不多。
我要从头到尾查遍奥登所有的诗集,找出里面每一句与月亮有关的诗句,看看我是不是能够突然想起来。
这项工作一旦开始,令我惊奇的是,我才发现这些诗里与月亮有关的诗句寥寥无几!
在一本长达897页的诗集中,我怀疑可能连二十句都没有。
在《月球登陆》里有“谢天谢地,我的月亮没有受到污染,月缺又月圆,她仍后居天庭……”或者在《焦虑的时代》里,“月亮升起,温柔,安详,草在摇曳……”,还有在《夜曲》里的“月亮出现,悄然无声,避让山峦的獠牙磋齿;
悄悄然,溜进开阔的天空,豁然知所处”——都是奇妙的诗句,但这些可都不是我记得的那一句。
最接近的是“渐逝的月儿苍白地高悬,犹豫踌躇在天边……”,也是《焦虑的时代》里的。
可是这似乎也不对。
后来我又有了一个主意。
我要重读一遍斯彭德的日记,看看其中他是否提到过一句奥登的有关月亮的诗。
在1975年2月6日的那篇日记中我找到了这样的话:
“模仿晚年的奥登并不是件闲难的事。
(他于1973年去世。
)因为在他晚年的诗歌里有一种暴躁的人格面貌,一些有抱负的有聪明技巧的年轻人完全可以效仿。
但是模仿早期的奥登就很难了。
‘此月之美,无始无终,初始即已成……’”这一句,我敢肯定,正是1981年那个下午斯彭德写在黑板上的那行诗。
可怜的斯蒂芬·
斯彭德,可怜的罗伯特·
奥本海默,他们都被局限在或归类到仅仅不错之列,而他们又清楚地知道什么叫作出类拔萃,这就使他们不可避免地感到悲哀痛苦。
“做个不太著名的诗人如同做个不太重要的王族中人,”斯彭德在日记中写道,“任何人,正如玛格利特公主的侍卫女官有一次给我解释的那样,成为那种角色都不会髙兴的。
”至于奥本海默,我记得埃斯德·
拉比曾经跟我说:
“如果他研究的是犹太教法典和希伯来语,而不是梵语的话,他(奥本海默)或许会成为更伟大的物理学家。
我从未遇见过比他更聪明的人。
但要想更具独创性、更有深度,人还是要更专注于某个领域才行。
正如斯彭德所说,W.H.奥登的诗无法模仿,保罗·
狄拉克的物理学更无法模仿。
那才是伟大的诗歌与伟大的物理学的共同之处:
都是随着无法预见的天才们掀起的浪潮狂扫而来,而同时把仅仅不错的人冲刷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