遮蔽与突显农民工在大众传媒中的位置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遮蔽与突显农民工在大众传媒中的位置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遮蔽与突显农民工在大众传媒中的位置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1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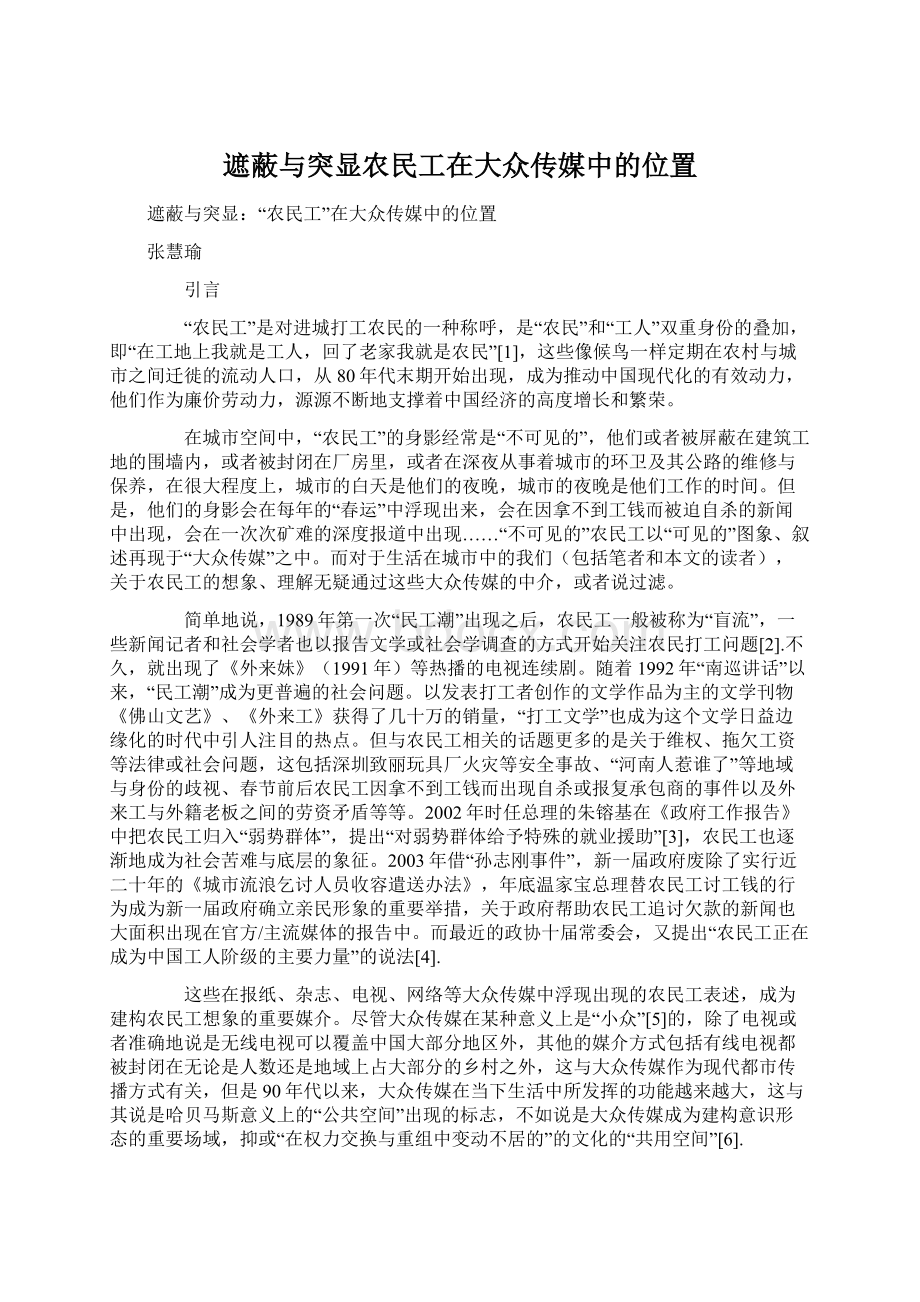
随着1992年“南巡讲话”以来,“民工潮”成为更普遍的社会问题。
以发表打工者创作的文学作品为主的文学刊物《佛山文艺》、《外来工》获得了几十万的销量,“打工文学”也成为这个文学日益边缘化的时代中引人注目的热点。
但与农民工相关的话题更多的是关于维权、拖欠工资等法律或社会问题,这包括深圳致丽玩具厂火灾等安全事故、“河南人惹谁了”等地域与身份的歧视、春节前后农民工因拿不到工钱而出现自杀或报复承包商的事件以及外来工与外籍老板之间的劳资矛盾等等。
2002年时任总理的朱镕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把农民工归入“弱势群体”,提出“对弱势群体给予特殊的就业援助”[3],农民工也逐渐地成为社会苦难与底层的象征。
2003年借“孙志刚事件”,新一届政府废除了实行近二十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年底温家宝总理替农民工讨工钱的行为成为新一届政府确立亲民形象的重要举措,关于政府帮助农民工追讨欠款的新闻也大面积出现在官方/主流媒体的报告中。
而最近的政协十届常委会,又提出“农民工正在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主要力量”的说法[4].
这些在报纸、杂志、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中浮现出现的农民工表述,成为建构农民工想象的重要媒介。
尽管大众传媒在某种意义上是“小众”[5]的,除了电视或者准确地说是无线电视可以覆盖中国大部分地区外,其他的媒介方式包括有线电视都被封闭在无论是人数还是地域上占大部分的乡村之外,这与大众传媒作为现代都市传播方式有关,但是90年代以来,大众传媒在当下生活中所发挥的功能越来越大,这与其说是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出现的标志,不如说是大众传媒成为建构意识形态的重要场域,抑或“在权力交换与重组中变动不居的”的文化的“共用空间”[6].
在这个空间中,农民工被不同的意识形态所借重,有时甚至成为支撑彼此矛盾叙述的修辞,比如“民工潮”一方面表述为中国实现非农化/城市化/工业化的标志,另一方面也被表述为“现代奴隶”、“包身工”等社会苦难与底层的象征。
而媒介自身的背景也影响到关于农民工的表述,比如下面我要分析的《三联生活周刊》使用“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来指称矿难与《真理的追求》使用“包身工”来指称农民工,虽然都借用社会主义时期的经典文本,但是其不同的选择与这些刊物自身在90年代的不同意识形态背景密切相关。
更为重要的是,关于“农民工”的叙述,并非来自于“农民工”的自我建构(当然,在“打工文学”中参杂了些许自我想象),而是“大众传媒”对“农民工”的追认、整合和命名,在这个意义上,关于“农民工”的话语可以读解为葛兰西意义上的“霸权统识”的争夺战,农民工在不同时期、不同媒介中被再现为不同的身份,是不同意识形态运作或协商的结果。
所以,本文并不是对农民工现象进行社会学、政治学或经济学方面的分析,而是把“农民工”作为不同的文化表象进行意指实践的“表征/再现”,或者说一个不断被建构为“他者”的景观,正如赛义德在《东方学》中把西方文化尤其是东方学研究领域中的关于中东或近东的文化表述作为建构西方主体身份的一部分,而关于农民工的表述,也在某种程度上,发挥着同样的功能。
这些在大众传媒中指认“农民工”的不同方式,与“农民工”在社会权力网络中的位置密切相关,因此,我的工作就是呈现这些大众传媒中关于“农民工”的表述背后所隐藏的意识形态及其权力关系。
或许,这样一篇研究报告很难被“农民工”所阅读,这依然是对“农民工”的一种再现而已,但我希望这是一种关于再现的再现。
一、“农民/工”的起源或谱系
“农民工”来自于工人与农民的组合,而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关系的产生有着密切的关系。
尽管“农民”及其所从事的生产似乎有着久远的历史,但农业生产是在与工业生产相对比的结构中才获得意义的,因此,“农民”也是在与工人的关系中获得意义的,可以说,农民的命名与工人一样,是一种现代的发明,或者说农民和工人一样都是现代性叙述的衍生物[7].而关于农民/工人以及阶级的话语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才逐渐确立起来的,或者说晚清以来的工业化进程,创造了近代的工人阶级,随之农民也获得了新的含义,这成为讨论“农民/工”问题的历史背景。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叙述中,工人阶级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出现的,正如《共产党宣言》中,资产阶级时代的特点被描述为“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个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8],可以说,工人阶级在经济上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即工业化大生产,在政治上属于革命的主体即被压迫阶级的代表,在进步论和目的论的历史叙述中被预设为人类历史的主体,而农民的位置则被排斥在历史主体之外。
一方面,农民是工人阶级的来源,因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始阶段农民被强制剥夺土地而变成除了出卖劳动力“自由到一无所有的地步”[9],支撑这种叙述的历史经验是英国的圈地运动,而与这种叙述相伴随的是用“大工业生产”取代“农业生产”,即“大工业在农业领域中引起的最有革命性的一件事,是剿灭旧社会的堡垒——‘农民’——而用工资雇佣劳动者去代替他们”[10],在这种现代化/工业化/资本主义化的叙述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前身,而工人阶级是农民转化的结果,这种叙述直到今天依然成为对“农民工”持乐观态度的依据。
另一方面,农民或者准确地说是“法国农民”在马克思的《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被比喻为“一袋马铃薯”,即“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11],这就决定农民如果作为单个的马铃薯,他们不是一个阶级,但他们被装进“袋中”又是一个阶级[12],只是他们不能自已把自己装起来,或者换作马克思的说法就是“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
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13],这种叙述是为了解释路易·
波拿巴如何获得小农支持的,但也在政治上否定了农民的自主性,当然,农民阶级更不占据历史的主体位置。
在这种以生产关系为参照标准的历史叙述中,农民阶级由于其落后的生产关系而处于低级和需要被历史“剿灭”的命运上。
如果按照经典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的理论,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体,并没有给农民阶级预留下任何位置。
在这个意义上,农民/农民阶级被排除在历史之外,但是自“十月革命”以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按葛兰西的说法是“反《资本论》的革命”[14],也就是说发生革命的区域不仅不是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地区,而是那些以农业为主体的工业化相对落后的国家,这就使得纯粹的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被历史验证,反而是像中国这样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作为同盟军而完成的革命,农民恰恰处在历史之中。
在某种程度上,毛泽东赋予了农民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主体位置,或者说把农民建构成一个“阶级”,是对第二国际时期卢森堡、葛兰西无法在西欧发达国家发动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社会主义革命所带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的克服。
进一步说,农民是被线性进步的历史观排斥在历史之外的[15],但是在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理论视野下所展开的对历史目的论、进化论、阶级还原论的批判,为反思农民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表述中的尴尬位置提供了可能。
吕新雨在《<
铁西区>
:
历史与阶级意识》一文中从第三世界/中国的资本主义化的历史出发,通过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去物化或者说符号化的分析,推论出当代工人阶级丧失历史主体性的原因是“资本离弃了工人”,而“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对传统农民主体性的否决,可以被视为当代工人主体性失落的前提”[16],并提出“不是马克思所期望和设想的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不是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条件下的反资本主义革命,而是资本主义在它所确立的过程中所激发出的旧世界的反抗,恰恰是这种革命运用了社会主义的旗帜并获得成功,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其实都不是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的结果,而是农民革命的结果”[17].这样,用农民替换工人或者说在资本主义结构中把农民与工人放置同等的历史位置上,就颠覆了经典马克思主义赋予工人阶级历史主体性的叙述。
可以说,农民阶级不但没有离开历史,反而成为推动历史的动力。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叙述也建立在以沃伦斯坦为代表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和弗兰克的依附理论对西方中心主义/普遍主义的批判之上,通过对“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划分,把东方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结构内部的因素或者说把西方/东方、中心/边缘作为共时的结构来处理,从而修正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历史叙述中以西方为中心的进步观[18].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把“农民工”看作是从农民演化为工人的过渡状态,从而预设着历史的进步与进步中的代价,就掉入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叙述的陷阱,尽管这种叙述包含了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批判,但是这种批判背后预设着乌托邦的前景,或者说用“明天更美好”的允诺来化解今天的苦难。
但是,现代化/工业化依然是当下世界或中国的宏大叙事,“现代化和工业化以对农民、农业的掠夺来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无论是资本主义的英国还是社会主义的中国、苏联,都是同一个历史动机的不同演绎”[19],在这个意义上,“农民工”的问题也不得不放置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语境中来理解,诸如社会主义革命、户籍制度等深刻影响中国当下社会生活的“历史事件”,都与这个“宏大叙事”有着密切的联系。
与其说这些“历史事件”阻碍了或逃离了“宏大叙事”,不如说它们是“宏大叙事”的一部分[20],历史也远没有终结[21].
二、“盲流”与民工潮
“民工潮”第一次出现在1989年春天,“引起了全社会的震动,也成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22],当时的媒体普遍使用“盲流”来指称“农民工”。
“盲流”是对“盲目流动”的简称,这来自于1952年中央劳动就业委员会提出要“克服农民盲目地流向城市”的政策,到1995年8月10日公安部发布《公安部关于加强盲流人员管理工作的通知》还依然使用这个名称。
当时之所以能够引起社会的震动,是因为改革开放前,农民是不能进城打工的。
乡下人/城里人作为一种不仅仅是区域分隔更是等级或阶级分化的身份标识,使农民户口/城市户口成为众多社会身份中分外重要的一个。
这种户籍制度或者说严格的城乡二元结构是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期更好地从农业生产中积累原始资金而不得不采取的制度安排[23].改革开放以后,首先启动的是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后是城市双轨制的改革。
但1984年出现卖粮难以后,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调整了农业生产的结构,当时的政策是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这种就地解决农业人口非农化的方案没有形成民工流动。
随着“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务工经商”(1986年农业一号文件),农民开始离开乡土,这样就出现了由西部向东部、乡村向城市、欠发达向发达、内陆向沿海的内部移民,当然,许多农民工不仅流向城市或大城市,也流向东部乡村经济发达的地区,或者流向劳动力缺乏的宁夏新疆等西北地区[24].
这究竟是新出现的现象,还是“重演的故事”[25]呢?
从历史上看,“民工进城”并不是80年代末期才出现的现象,按照上一节所分析的,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必然造成农民向工人的转化,因此,自晚清“洋务运动”以来的工业化运动,“民工潮”就已经出现了,在这个意义上,“民工潮”是一个重演的故事,但是,这种历史追溯固然能够把民工潮的问题引向对现代化/工业化的讨论中,但却忽略了80年代末期出现的民工潮有着更为复杂的历史动力,这种微妙的变化可以从“民工”与“农民工”的不同称呼上呈现出来。
与建国前出现的“民工”不同的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或者说作为既得利益的“工人阶级”是受到社会/国家保护的,在这个意义上,“农民工”才与晚清以来形成的“民工”具有不同的含义,如果说后者的“民工”基本上与“工人”是同义词的话,那么这里的“农民工”却不是工人阶级。
在1953年出版的《民工卫生》中可以看出这里的“民工”是指建国初期参加“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劳动人民。
这本书属于《爱国卫生丛书》,其分类为“工厂卫生、矿山卫生、农村卫生、城市卫生、部队卫生、交通卫生、个人卫生、学校卫生、民工卫生、妇女卫生、孩子的卫生……”等等,“民工”既不属于“工厂”也不属于“农村”,而是属于“大工程的工地——广大的露天工厂”,但在具体的叙述中,“民工”又与“工人”混合在一起,比如《怎样搞工人生活》一节中,“工人生活,就是民工到工地后的衣、食、住、行,也就是工地环境卫生”[26].这充分说明,“民工”从事着工业劳动,但是他们又不属于工厂里的工人。
在这里,“民工”的处境已经类似于“农民工”了。
“民工潮”引起了一些新闻记者的关注,于是,出现了一些关于“民工潮”的报告文学。
报告文学在80年代文学、文化地形图中占据着特别突出的位置,在某种程度上,报告文学充当了新闻调查的功能。
葛象贤、屈维英在对1989年春节后出现的民工潮进行三个多月的追踪寻访的基础上,于1990年出版了《中国民工潮——“盲流”真相录》(简称《真相》)的报告文学,把刚刚出现的“民工潮”比喻为“中国古老的黄土竟然流动起来了——那象黄土一样固定的中国农民开始象潮水一样流动起来,而且势头很猛”,这里的“黄土”与陈凯歌的电影《黄土地》一样是80年代以来对“中国”特有的修辞方式。
“那黄土啊,是多么的长久,多么的厚重,多么的闷寂,多么的慵懒,多么的灰面土脸,黄里巴吉。
我们亲身经历了那里‘学大寨’、战天斗地、改土造田,然而黄土依然是那样的黄土,黄土地上的农民依然象黄土那样沉郁、冷漠、恋乡、僵化……,依然是那样的穷困潦倒,不追求如何目标,生下来时老天安排他们怎样生活就一直照样生活下去,直到死了归葬黄土,而下一代也是如此。
”[27]在这种静止的、去历史化的叙述中,中国/黄土/农民变成了循环往复的、没有生机的存在,正是这种静止的状态赋予“民工潮”以流动的形象,正如作者手记所写“当脚下的黄土也流动起来的时候,中国就会真正、彻底地变”。
在《真想》一书中,作者把“民工潮”比喻为“倒插队”,把“工仔楼”、“工妹楼”命名为“知青点”,认为民工青年到城市打工是与60年代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正好相反的历史运动,“这是因为历史虽不会重演,但有时却十分相似,甚至细节”[28].“上山下乡”与“民工潮”确实是建国后发生的两次比较大的人口流动,如果说前者是为了解决城市劳动力过剩[29],那么后者则是为了解决农村中的人口剩余问题[30].暂且不谈背后的政治经济学动力,这种“相似的历史”的叙述已经抹去历史自身丰富的差异性,“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叙述与“农民工”背井离乡是不同意识形态下的结果。
在某种意义上,重提“上山下乡”的历史记忆是为了建立历史的相似性,以便在这种类比中,把“民工潮”镶嵌到已经断裂的历史之中。
在《真相》中,还把“民工潮”类比于美国19世纪的“西进运动”。
“19世纪席卷美利坚合众国的‘西部浪潮’——生气勃勃的美国人疯狂般地向西部移民,吸引他们的是土地、草原、财富和机会”[31],而在杨湛被收入“珠江三角洲启示录丛书”的《汹涌民工潮》的结语中则提到“在美国,200年来第一次出现了迁往农村的人口远远超过迁往城市的人口的现象”[32].这种把从乡村迁往城市的“民工潮”与从东部城市向西部开拓的美国人放置在一起的叙述,无非为“民工潮”预设了一个美好的前景,而这个美好的前景被进一步表述为“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因为美国西进农民“那吱吱作响的大车,把资本主义制度从大西洋岸一直推到了太平洋岸”[33],从而作为“民工潮”具有历史进步性的证明,但是美国“西进运动”与中国“民工潮”之间的历史差异在于前者不仅仅是与农民有关的运动,还是包括大地产商在内的以土地换金钱的“开发西部”,可以说,“西进运动”在土地市场化基础上形成的金融资本成为美国完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重要过程[34].
第三种关于“民工潮”的修辞方式是把“民工潮”比喻为“出国潮”。
在《真相》中“从民工潮我们联想到了这几年另一股波及全国的潮水——出国潮。
出国潮的弄潮儿多是青年学生和中青年知识分子”[35].把“出国潮”的群体指认为“知识分子”,并建立一种关于知识分子从中国的“士”阶层以来都是“在流动中谋生”的叙述,用这种叙述来参照“中国的农民,亘古以来就象胶着的黄土。
现在他们竟也流动了起来”的历史意义。
这种农民/知识分子的叙述依然延续了社会主义话语中对农民/知识分子的划分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一种“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动力”的观念,“因为这是由静到动、由僵到活的变化,而且发生在中国社会的根基部分。
从此中国社会不再是构筑于凝固的黄土之上,而是浮载于流动的黄土之上了”[36],因此,在农民/知识分子的对立中,就遮蔽了另外两种移民,一种是通过教育体制由农村转入城市的少数精英,另一种则是或合法或非法(偷渡)的跨国打工的事实。
而在《汹涌民工潮》一书中描述“民工潮”现象时也把国内移民比喻为跨国移民,比如把聚集在珠江三角洲的操持各种方言的农民工比喻为“联合国”,把农民工没有正式户口的处境比喻为没有“绿卡”,“因为她们没有一张长期留居城市的‘绿卡’——也许移居美国所需的那一张‘绿卡’,也没有在中国之内从农村移居城市的长住户口那样难搞到吧”[37],这无疑暗示着“农民工”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而无法享有合法“身份”的处境,而没有“绿卡”的非法身份却成为充当廉价劳动力的保证[38].
“民工潮”与“出国潮”之所以能够构成转喻关系是因为在“打工/出国”的背后是“黄金海岸”的诱惑,正如《汹涌民工潮》的内容提要中所说:
“20世纪80年代以来,乡土观念最强的中国农民再也抵不住南国商品经济繁荣的诱惑和吸引,纷纷背离祖先眷恋了数千年的故乡本土,从全国各省区地向珠江三角洲滚滚流动,5000万民工蜂涌南下,投奔‘黄金海岸’”[39],在这个意义上,资本/金钱成为解释“民工潮”的历史动力,诸如商品经济、竞争意识、“炒鱿鱼”“跳槽”等新词汇作为取代“铁饭碗”的标志,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人只有能自救,上帝才会拯救你——‘打工仔’们,你别无选择”[40]的逻辑,也成为对新的游戏规则进行辩护或论证的话语方式。
可以看出,关于“民工潮”的叙述是在一系列转喻性的修辞中完成的,“民工潮”被比喻为“倒插队”、“西进运动”、“出国潮”,在这些“高难度”的历史对接中,所要实现的是对“民工潮”的乐观主义叙述,诸如“在对民工潮三个月、上万里的追踪中,我们看到的并非是一股股到处横流的盲目的祸水,而是一幅离开农村、离开家乡的农民走向新的生活,追求现代文明的气壮山河的进军图”[41],或者“民工潮的出现,是历史的进步,是社会的进步”[42].而这种历史对接的实现不仅把放弃以农业生产为代表的农耕文明作为“历史的进步”,而且“民工潮”之前的中国历史被以静止化、去历史化的方式彻底否定掉,这种在分享由农业到工业的线性现代化逻辑下虚构了一个创世纪开端式的进步叙述,成为重新建立一种新的意识形态逻辑的一部分。
三、“外来妹”与跨国想象
在上一节中,我提到“民工潮”的一个修辞方式是类比于“出国潮”,如果联系到90年代初期两部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外来妹》(1991年)与《北京人在纽约》(1993年),就可以看到在“外来妹/女性”的“城市想象”与“北京人/男性”的“美国梦”之间有着更为微妙而复杂的性别逻辑和欲望逻辑。
90年代以来,电视作为强势媒体的地位凸现出来,并且从覆盖地区上说,电视成为名副其实的“大众传媒”。
《外来妹》是最早反映广东地区外来打工者生活的电视剧,1991年播出后获得极大的成功。
讲述了一群来自偏远山区的姑娘到广州打工的经历,呈现了这个群体寻找自己的身份和位置过程中的众生相,以一个成功步入管理层的形象昭示了外来妹的希望。
“从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前期,外来工尤其是外来妹作为一种‘新生事物’,作为‘社会进步’的标志”,而如《外来妹》这样的电视剧也“大都仍在‘城市/乡村’、‘文明/愚昧’的二项对立的表达中,把离乡离土的姑娘表现为勇者,一种战胜陋俗、战胜偏见的成功者”[43].为什么在“民工潮”刚刚出现的历史时刻,诸如《黄山来的姑娘》、《外来妹》等女性成为“农民工”在“大众传媒”中显影的方式呢?
这种把农民工/女性的身份叠加在一起的表述,不仅仅遮蔽了男性农民工的存在,而且是把阶级问题转移为性别问题的重要策略。
《外来妹》主题曲是《我不想说》(“我不想说,我很亲切;
我不想说,我很纯洁;
可是我不能拒绝心中的感觉,看看可爱的天,摸摸城市的脸,你的心情我能理解,许多的爱,我能拒绝,许多的梦,可以省略,可是我不能忘记你的笑脸,想想长长的路,擦擦脚下的鞋,不管明天什么季节,一样的天,一样的脸,一样的我就在你的面前,一样的路,一样的鞋,我不能没有你的世界”),这首由杨玉莹演唱的情歌,传达的是“我不能拒绝心中的感觉”、“我不能没有你的世界”、“我不能忘记你的笑脸”,而“你”与其说是某个具体的情人,不如更是“城市”、“城市的天空”,在这个意义上,这首歌表达了乡村姑娘对“城市”的向往,“不管明天什么季节”都会“擦擦脚下的鞋”,走上通往城市的“长长的路”,乡村/城市的欲望逻辑就建立在女性/男性的性别关系之上。
如果对照刘欢演唱的《北京人在纽约》的主题歌《千万次的问》(“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
你不像是在我梦里,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
Once,onceagain,Youaskme,问我到底爱不爱你,Once,onceagain,Iaskmyself,问自己是否离得开你。
我今生看来注定要独行,热情已被你耗尽。
我已经变得不再是我,可是你却依然是你。
Once,onceagain,Youaskme,问我到底爱不爱你,Once,onceagain,Iaskmyself,问自己是否离得开你,Once,onceagain,Youaskme,问我到底恨不恨你,Once,onceagain,Iaskmyself,问自己你到底好在哪里?
好在哪里?
”),在这种男性爱恋的独白中,表达的是“我/中国”对“你/美国”的一往情深,但“你却并不在意”。
在“问自己是否离得开你”、“问自己你到底好在哪里?
”的苦苦“追问”中,与其说表达了“北京人/男性”对“美国梦”的“重估”,不如说更是一种“无奈与失望”[44].在这里,北京/纽约、中国/美国的欲望关系也是放置在男性/女性的性别关系之中来完成的。
尽管“外来妹”与“北京人在纽约”使用了不同的性别策略,但个人主义式的成功故事,就成为“类似‘美国梦’式的表述,固然关乎‘个人’话语与空间的构造,但更为重要的,是它无疑会在中国的特定语境中,还原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