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命本体看中国文学的文体变迁Word文件下载.docx
《从生命本体看中国文学的文体变迁Word文件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从生命本体看中国文学的文体变迁Word文件下载.docx(1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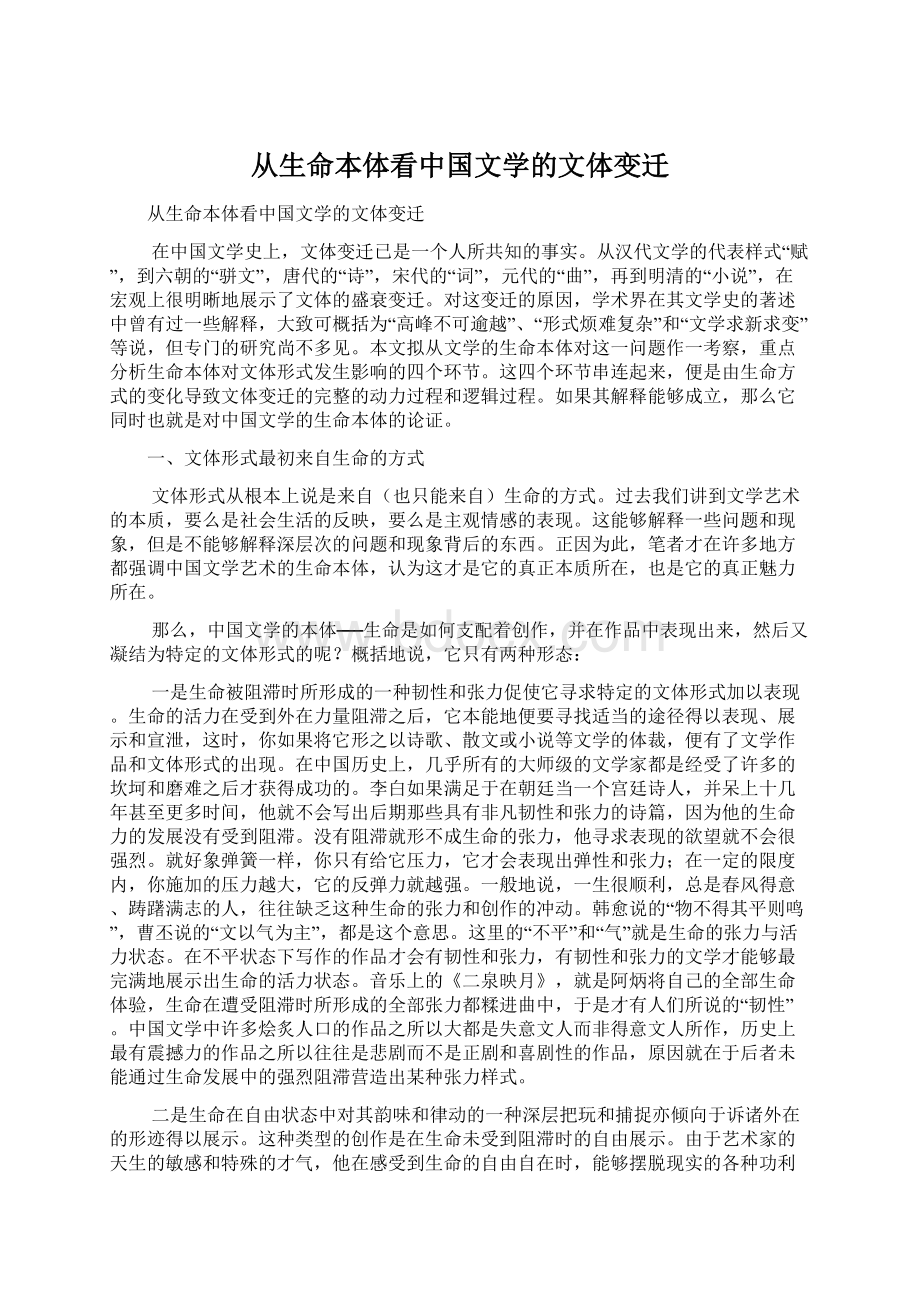
音乐上的《二泉映月》,就是阿炳将自己的全部生命体验,生命在遭受阻滞时所形成的全部张力都糅进曲中,于是才有人们所说的“韧性”。
中国文学中许多烩炙人口的作品之所以大都是失意文人而非得意文人所作,历史上最有震撼力的作品之所以往往是悲剧而不是正剧和喜剧性的作品,原因就在于后者未能通过生命发展中的强烈阻滞营造出某种张力样式。
二是生命在自由状态中对其韵味和律动的一种深层把玩和捕捉亦倾向于诉诸外在的形迹得以展示。
这种类型的创作是在生命未受到阻滞时的自由展示。
由于艺术家的天生的敏感和特殊的才气,他在感受到生命的自由自在时,能够摆脱现实的各种功利考虑和理智运作,将其精力和兴趣集中在自身生命状态的体验、捕捉和把玩上,这样就可以得到表现生命自由状态、展示生命本身的和谐与韵律的文学作品。
一般说来,那些比较清淡、宁静、柔和、飘逸、洒脱的诗人即属此类。
这样的作品,在中国文学中,从量的方面说是占了大多数,因为人不能总是处于愤激、苦闷、紧张的张力状态,它总有缓解的时候,如亲人的团聚、老友的重逢、知音的相会以及花前月下、名山胜景的观赏等,此时人的生命状态是和谐的,故而写出的作品也是和谐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个体的生命是以展示自身张力和律动的方式来营造文学世界,使作品具有活力和魅力的。
只有这样的文学作品才是真正的文学作品,才能构成真正具有永恒魅力的文学世界。
那些没有立足自己的生命状态,仅仅从形式格律着手的作品,不是真正的文学创作,因而不具有美学价值。
根据这一原理来考察中国文学中文体形式的产生,我们就会发现,中国文学的文体形式都是直接源自特定时代、特定阶层的人的生命方式,首先是由人的生命方式产生出文学作品,然后在大量文学作品的创作实践中总结出较为规范、较为固定的文体形式。
众所周知,汉代的代表文学样式是大赋。
大赋的特点是铺陈排比,气势阔大。
从内容上说,它所表现的往往是当时人的一种豪奢的、壮阔的生活场面或自然场面。
大赋的这种特质,正是由汉代人的生命方式决定的。
汉代虽是从秦代发展而来,但秦代为时太短,所以实际上它是直接承继着东周的。
从东周到秦汉,由于社会的变化使得人的生命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新的生命方式便导致新的文体形式的产生。
东周时代主要是一个以宗教为核心的贵族社会,而汉代则是以伦理为核心的世俗社会,在文化氛围中占统治地位的不是贵族文化,而是世俗文化;
东周是一个分裂的、动乱的时代,而汉代则是安定的、大一统的时代;
东周时代由于战乱频仍,所以生产萧条,生活水准低下,而汉代则由于政治安定,人民得到休养生息,经济迅速恢复,生活水准有了较大提高。
正是这些变化导致了汉代人的生命方式与东周人的生命方式的不同,这不同处在于:
因其是大一统的帝国,就需要一种很有气势的文体形式来作它的载体,大赋正好能够满足这一要求。
大赋中常常表现的人对自然、动物的征服,就正是汉帝国的大一统气概和汉代人在世俗生活中所建立的自信心的表现。
汉赋中的铺陈排比夸张和宏篇巨制的规模正是为此服务的。
又因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国家的实力强大了,人的优越地位也初步确立,故而造成一种新型的天人关系。
在东周,人对天是“敬畏”的,孔子就多次讲“畏天命”;
而到汉代,董仲舒首先改造了儒家,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
“天人合一”的实质是人向天看齐,它意味着人和天是同一的、同位的、同构的。
因此,在汉代,只能是赋,而不可能是其它文体会成为这一时代的代表文体。
从审美价值上说,汉代最有成就的并非是赋,无论是叙事的散文还是乐府民歌,都远远超出于它;
但若从最能体现汉帝国的气势和汉人的生命方式来看,就只能是赋。
再以诗歌为例。
我们不说诗经、骚体、乐府等古体诗,因为它们还没有形成一定的体式。
我们只对格律化了的近体诗为例予以分析。
格律化了的近体诗讲究平仄、押韵,讲究句式和字数的统一和固定。
这又植根于什么?
实际上仍然是特定时代的生命方式。
这里有两点我认为最重要:
一是魏晋时代生命意识的觉醒。
生命意识的觉醒强化了、激发了中国人的娱乐感或享乐感。
有了这种享乐感和娱乐感,它就不太满足于以前诗歌的那种古拙、质朴、缺少色彩和光泽的诗歌。
以前的诗歌读起来不是很美,它是以意胜,以质胜,而不是以文胜。
魏晋时代生命意识觉醒之后,人们开始认识到生命自身的价值,便自然会执着地去追求它,抓住它来细心的品玩、享受。
这表现在生活上,就有以服药来追求生命的长度(量的),以饮酒来追求生命的密度(质的)和以纵情山水来追求生命的自然(本质的);
而表现在文学上,就有对文学形式美的重视,就有骈文和近体诗的新文体、新形式的出现。
近体诗的形式特征在于对辞藻的重视和对诗的音乐感的追求。
这一追求始于南朝的宫体诗,而完成于盛唐的格律诗;
其理论上的阐述者是南朝的沈约。
另一较为重要的原因应该说是外部的,那就是安史之乱等一系列动乱的社会政治背景。
安史之乱的时代正是格律诗成型并开始为人们广泛接受的时代,所以它对格律诗起着至关重要的催化作用。
在一个动乱的年代里,人们从心底里,从生命的深处通常是渴望着一种规范,希求一种有则可循、有章可依的有序状态的,而格律诗正好能够满足此时人的这种心理企求。
所以说,格律诗是魏晋、盛唐人的生活方式和生命状态寻求展示的直接产物。
再以词为例。
词的出现最早在盛唐,但那只是个别的现象。
到晚唐五代时,词的创作便魔术般地盛行起来,并涌现了著名的词人,如温庭筠、韦庄、李煜、冯延巳等。
这也是由于唐代人的生命方式有了重大变化的缘故。
正是在中晚唐时代,中国士大夫文人的价值观念、内心情趣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即由外在功名、社会责任转到个人心灵、情感趣味,由“兼济天下”转到“独善其身”上来。
这时候,他们虽然仍旧做着长篇政论,仍然留意功名仕途,仍然思考着国家的安危、民族的兴废,但真正的兴趣却已经转到另一方面。
不是边塞军功,不是国家的安危,世间的治乱,而是闺房、心境成为这一时代人最为关心的主题;
不是豪迈的气度、宽广的胸怀、乐观的情调,而是柔美、细腻、哀婉、感伤成为人的情感的突出旋律。
与之相应,不是边塞诗的功名歌唱,不是“诗史”式的现实忧患,也不是乐府、古文的批判锋芒,而是山水诗的高远闲静、旷达超脱,爱情诗的温馨妩媚,深婉密丽,以及宋词的一唱三叹,余味深永,成了这一时代诗歌的审美方向。
词便是在这样的生命状态中形成的。
在初盛唐时,人的心情是乐观的、进取的、豪爽的、明朗的、粗犷的、开放的,与之相应,就有诗这一文学形式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律诗句式的整齐、音节的匀称,与昂扬的情绪、豪迈的气度正相吻合,而古诗格式的自由、篇幅的不限、韵脚的随便,又与乐观的情调、开放的胸襟正相吻合,使这一形式正好成为初盛唐文人心理情感趣味的完美载体。
但是,中唐以后,随着重心的转移,人的心理情感逐渐完成了由乐观到感伤、由豪迈到含蓄、由明朗到朦胧、由粗犷到细腻、由进取到颓唐、由开放到封闭的转变,使诗歌所要表达的感情内容发生了巨大变化。
同时,随着重心的内转,人们对自己的内心世界,特别是情感世界有了日益深入细致的发现和感受,使原来那个透明的、单纯的、强烈的心理世界一下子变得复杂、朦胧、含蓄、幽深起来。
这时,以前那种整齐、规范、刻板划一的律诗和无遮无拦、自由挥洒、气势磅礴的古诗就显得很不适应,而那活跃在市井民间歌女口中的词便顿然兴起,成为士大夫文人争相运用的新的诗歌形式。
词的那种长短参差不齐的句式,那一唱三叹、余味满口的音乐,那华丽、绮靡、哀婉、含蓄的风格基调,正是最能引起人的深心共鸣的完美形式。
从历史上看,词也正扮演了晚唐五代和北宋文人的双重人格中个人情趣、心灵闲适方面的表现者的角色,并因此而赢得了历代文人特别是青年的青睐,显示了独特的美学成就。
与之相似,词之后的曲也是特定生命状态的产物。
曲的生命状态主要不是以时代,而是以阶层、人群为标志。
一种文学,它的享用主体怎样,会对这种文学以直接的影响。
诗和词的享用主体是文人,但是曲的享用主体则是新兴的市民阶层。
市民阶层与士大夫阶层有很大的不同,它有自己特有的生命方式,因而需要自己的文学样式,曲正是对这一种生命方式的适应和满足。
而元代市民阶层的生命方式大致有以下特点:
首先,他们的文化修养不高,甚至大部分人不识字;
其次,他们有闲遐,又有钱,所以便需要消遣、娱乐,需要一种适合于他们的文学样式。
这便是曲得以兴盛的根本原因。
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曲才具有自己的文体特征、形式特征和审美特征。
这种特征在将它同诗、词相比时见得尤为明显。
对此,笔者曾作过比较,指出“诗常一句一境,一联一境,通篇合起来,又构成一个整体的意境,故其境多雄浑博大、旷远开阔;
而词常是一阙一境,一首一境,故其境多尖新轻巧,精工密丽;
曲虽也一首一境,但由于直接诉诸听觉,所以极自由随便,通俗直率,是喜笑怒骂皆成文章。
诗和词都讲求含蓄,讲究‘藏’,而曲则明言直说,提倡‘露’。
从辞采上讲,诗贵典雅,词主绮丽,曲贵浅显,但这个浅显不是浅陋、浮泛。
曲也追求深邃的意境,不同的是,诗寓深于庄,词寓深于媚,曲则寓深于浅。
”这些特征都直接来自元代市民阶层的特定的文化状态(低水平)、传播方式(非阅读的)和功能要求(消遣、娱乐)等生命样式。
因为是听(单向流动)的而不是读(读是可以反复咀嚼)的,又没有较好的文化修养和较高的审美要求,故只能追求直露而不是含蓄,追求浅显而不是高深,追求诙谐幽默而不是庄重严肃。
和诗、词一样,曲这一文体形式也是特定时代、特定阶层人的特定生命方式的产物。
二、形式产生后即获得“自发展”的本能
文体形式一旦产生,就会获得一种“自发展”的本能。
也就是说,这种文体一旦产生,它就具备了一种本能的冲动,尽力扩展自己,完善自己,使自己的形式体系能够趋向于完备和定型。
这在所有的文体形式的产生发展当中都可以找到例证。
我们还是先从辞赋入手进行考察。
辞赋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而形成三种赋体:
大赋、骈赋和律赋。
大赋盛行于两汉,骈赋盛行于六朝,律赋则产生于唐代,是唐宋科举中的重要文体。
从大赋到骈赋再到律赋,正可以清楚地见出赋体自发展的过程和趋向。
汉代的大赋在形式上常常使用多句排比,这就意味着在大赋中较少使用对偶,而对偶正是赋体的一个本质性的特征;
在对偶句式中不避同字相对,这也意味着对偶本身在大赋中的不成熟,因为严格意义上的对偶是不可以同字相对的;
篇幅宏大,文意比较疏放。
到六朝时代,大赋发展为骈赋(骈文亦属此类),形成了双句骈偶的格式,使赋的对偶句式正式确立;
并在对偶句式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定型,形成四、六句式,并讲究平仄;
骈赋中还大量用典,讲究辞藻,追求形式的华丽,尤其喜欢运用色彩、金玉、灵禽、奇兽、香花、异草、风情、雪月等词汇,来宣染某种情调、气氛,制造形式美的效果;
其篇幅也相应缩小,结构更加紧凑,文笔更加精致。
从汉赋到骈赋,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它的跳进过程。
再到律赋,就又跳进一步。
作为唐宋科举中的重要文体,律赋的格式更为严格。
首先是对仗更工整,其对仗几乎可以同律诗相比美,有许多严格的规定;
其次是特别注重音乐性,除了要押韵之外,还得按照指定韵字(常为八个)押韵,甚至连次序都不得变更;
而且,律赋的句子不仅要符合平仄规律,即连韵脚的平仄也很严格,大多是一平一仄相间而出;
甚至连字数也有规定,一般不得超过四百字。
可见,从大赋到骈赋再到律赋,正是赋这一文体形式不断发展、不断完备、不断定型的过程。
赋这一文体形式的自发展的趋向,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四句话:
音乐性愈加突出,对仗愈加工整,句式愈加规范,修辞愈加讲究。
与之相似,诗的发展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这从古体诗到近体诗的演变中即可看出。
诗的格律正是在这一发展的过程中一步步地严格起来、完备起来,并最终得到定型。
首先,古体诗不讲平仄,到近体诗那里就特别讲究平仄,并以对、粘的方式来组成诗的句式。
其次,古体诗的用韵极为自由,它只是根据口语读音来选择韵字,读来和谐有音乐感即可,没有韵书的限制;
用韵时可以转韵和通韵,且平韵、仄韵、平仄换韵并存。
近体诗则一律押平韵,并且一韵到底,不得通韵,其韵均需以某一部韵书为准,不得随意改变。
再就对仗来看,古体诗对仗较为自由,一般不要求合律,要求合律者仅第2字须遵守对、粘的原则。
而近体诗中的律诗则特别讲究对仗,并将对仗分成各种不同的种类,如工对、宽对、邻对、借对、流水对、扇面对等,其区分与研究已十分细致。
另就结构来看,近体诗对古体诗也有了实质性的变化。
古体诗是诗无定体,结构十分自由,全由诗人灵活妙用,没有固定的模式。
近体诗则十分讲究结构,无论是律诗还是绝句,都必须遵循起、承、转、合的规则。
正因为近体诗的格律要求十分严格,所以人们往往在写作实践中提出一系列的避忌,其中最著名的是“八病”说,即:
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和正纽。
前四病是就平仄而言,后四病是就用韵而言。
此外在平仄方面还有“三忌”,即忌失对、失粘,忌孤平孤仄,忌三平脚、三仄脚等。
用韵方面还特别忌“出韵”,近体诗格律认为邻韵、通韵、转韵、窜韵、借韵、重韵等都是出韵;
唯一例外的是只在首句可以用邻韵,而在律诗中首句原是可韵可不韵的。
另在对仗方面也有三忌:
忌合掌,忌同字相对,忌邻联雷同等。
从这些避忌上,我们也可以看出诗的格律到了近体诗时是何等地严格。
文体形式的这种自发展倾向我们还可以从其它的文体形式当中找到痕迹。
不仅在赋和诗中经历了这种自发展的过程,即在词与曲中也同样经历了这一过程。
词的发展阶段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表示,一是从配乐到不配乐,一是从谱化前与到谱化后。
词开始是配乐歌唱的,并且是为了配乐歌唱而写作的,后来随着词的发展,它逐渐地脱离了与音乐的紧密联系,虽然它仍还不时地配乐歌唱,但已不是仅仅为了配乐歌唱了,而是有了自身独立的文学意义。
同样,词在开始是没有所谓“谱”的,它只是随着音乐的需要填上歌词,只是到后来才在大量的作品实践中被固定成“谱”,进入“谱化”阶段。
词的正式确立应该从文人自觉地从事词的创作时算起,这大致在晚唐时期。
这一时期的词尚处于未定型状态。
但是,随着文人的介入,随着这一文体的正式确立,它就同时获得自发展的动力,进入自我完善的过程。
首先从平仄来看。
词是讲究音乐性的,这一点无庸置疑。
但在开始时,由于它是配乐歌唱的,所以,它的音乐性就在于它的曲调。
因此,文字上的音乐性就见得不那么重要,就好象现在歌曲中的歌词一样。
歌词中的音乐性不足,可以由曲调中的音乐性来弥补。
中国的诗在魏晋南北朝之前是不太讲究音乐性的,因为此时的诗都是配乐的。
《诗经》本来就是由民歌和其它创作歌曲组成的,乐府诗则全是各地收集来的歌曲,即如屈原等人所作的楚辞,也多是配乐的,里面的《九歌》就是从各地的祭神歌曲改写而成的。
正因为这时的诗都是配乐的,所以才不太需要在语言文字上来讲究音乐性,也就不会去注意平仄问题。
只是到后来,歌词与曲调相分离,诗脱离音乐而独立之后,人们才意识到诗必须有自身的音乐性,而魏晋南北朝正是文人摆脱音乐而写作纯文学的五言诗的时代。
所以,正是在这时,出现了专门研究文学自身音乐性的理论成果──沈约的“声律论”;
也正是从这时起,中国的诗歌走上了音乐化的道路,出现了新的诗歌形式──近体诗。
这一原理正好可以用在词的发展上面。
词最早也是歌曲,与音乐结为一体,这时它不太需要文字自身的音乐性,不需要讲究平仄。
后来,他们写出来的词虽然有时还是要让歌女歌唱的,但是已经不再将自己的写作牢牢地捆在歌唱上面,而是试图使其词作脱离音乐而获得独立存在的意义,成为独立的文学样式,这就需要在语言本身具有一定的音乐感。
所以,后来的词虽然有时也配乐,但其创作的目的却已不在配乐歌唱,而纯粹是一个案头化了的读本了。
这时的词便开始注重平仄,并吸收了近体诗中的平仄规律。
这种平仄规律后来随着词的“谱化”而更加严格,并最终定型,完成了它的自发展的过程。
再从用韵上看。
早期配乐的词用韵十分自由,它们只是根据口语,甚至根据方言押韵,只要求读来和谐上口即可。
当词被案头化,特别是谱化之后,其用韵就更加讲究了,它必须严格地按照韵书来操作。
这样一来,填词这件创作活动就同时又成为一门学问,一门技术了。
填词这件事被大大地复杂化了。
另就词的格式上说,它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
这个过程是以谱化前与谱化后来划分的。
谱化前的词在句式上比较自由,尚未形成固定的模式,就如同歌曲中的词一样,同一曲谱下的各段歌词的字数有参差是正常的,这对歌唱无关紧要。
词在谱化之前也有这种灵活度,因为这时主要是为了歌唱的。
谱化之后,词的格式便得到定型,这首先是总字数的固定,其次是每节(阙)、每句的字数也被固定下来,不可以随意增减。
所以从词本身来说,它的文体形式也经历了一个自发展过程,即不断完善、最后定型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复杂化的过程。
与之相似,曲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也有一个谱化前与谱化后的差别。
曲在谱化前基本上都是自由的,因为它也是诉诸歌唱的。
里面的歌词后来独立出来,就成为案头化的散曲作品。
在谱化之前,它的一切都是自由的,平仄是自由的,用韵是自由的,甚至它的格式也是自由的,亦即字数是自由的。
谱化之后,曲在许多方面都定型了,而且有些比诗词更加严格。
例如平仄,谱化后的曲不仅讲究平仄,而且要求“平分阴阳,仄分上去”,更加精细、复杂。
由此可见,任何一种文体形式一旦产生,它就进入一种自发展的过程,趋向于使自己走向复杂,走向规范,走向定型。
实际上,如果我们把视野扩展一下,看一看其它艺术门类,如戏曲、书法、绘画、音乐、建筑等门类的程式化过程,就会更加明白这一点。
当然,说它是“自发展”,只是一种拟人化的表述。
形式本身没有自发展的本能,只有人对形式的需要和创造才具有这种本能。
所以,形式的自发展的真正的动力仍然在人,在人所普遍具有的那种使形式趋于完备与定型的“完形”张力。
三、形式的高度发展会造成遮蔽
我们说,文体形式高度发展后便会形成遮蔽,出现误区。
这是为什么?
按理说,一种文体形式得到高度发展,应该是一件好事,怎么又会造成遮蔽?
实际上,遮蔽恰恰就是因为它有某种好处,没有好处就不会形成遮蔽。
文体形式形成遮蔽的直接原因就在于它提供了一套可以直接操作的方法和程序,使其运用更加方便,更加容易。
这种遮蔽大致有三种情况:
⑴形式的复杂性消耗了人的注意力和精力。
高度发展后的文体形式一般都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形式自发展的趋向之一就是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精密。
而它的高度复杂和精密必然会吸引和消耗我们的精力和注意力去研究这种复杂、精密的文体形式。
例如写诗,在格律尚未完备、定型时,它是比较自由的,它主要是凭自己的诗的感觉来写作,其音乐性的表现也是十分灵活的,是根据所表现的内容来确定的。
但到格律诗的体式定型之后,你要写一首近体诗,就必须研究其相关的格律问题,如平仄、用韵、句式等。
这就意味着,你要做一个诗人,你首先得做一个学问家,要懂得诗的一切形式格律要求。
这无疑会耗费掉人的许多时间和精力。
但精力应该说还不是十分重要的,更重要的还在于它能够吸引并转移人的注意力。
本来写诗是为了表达自己的生命感受的,但由于有了一种比较复杂、比较精巧、比较完美的艺术形式摆在你的面前,它就会展示其魅力,将你吸引过去。
这样你在写作时就不会再去关注自己的生命感受和生命过程,你的创作便会与生命本体相疏离和脱节。
遮蔽首先从这里产生。
⑵形式的复杂性使人们误以为形式就是艺术。
形式的复杂性很容易使人们产生一种误解,误以为形式、格律就是艺术,就是美。
这是更普遍的现象。
以为做诗只要掌握其平仄、韵脚、句式等格律规范就万事大吉了,以为这样写出来的诗就是真正的诗了。
其实,这样的诗至多只是格律上“不错”,但“不错”与真正的“好诗”还相距遥远,它们不是一回事。
把形式当作艺术本身,把文体形式的操作当作艺术的创作,这是形式高度发展后最常见的误区。
⑶生命体验不足时,只得以形式的工夫来代替它。
对于那些自己的生命体验和人生经验准备不够,但是又要进行文学创作的人,他们便会进入这个误区──以形式的功夫来代替他的生命体验。
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代替,因为一个人对自己生命的体验达到什么程度,这往往不是主观能够做到的,有些东西是要整个环境、整个机遇的提供,你才能够成就它。
如果你生活在一个事事如意的安乐的环境中,你就很难获得历史上那些饱经磨难的伟大人物所具有的那种生命张力。
客观条件就限制了你不可能具有非凡深刻的生命体验。
但没有这种体验,却又要写出作品来,其作品又要能够吸引读者,就只有从形式、技巧上下功夫。
这不仅在古代是这样,在当代尤其是这样。
文学在到了二十世纪之后,其发展几乎全都是在形式的层面上进行的,尤其是现代主义文学。
这种对形式的极端追求,就形式的探索来讲,是允许的;
但就文学的本性来讲,则是不能允许的。
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创作植根于生命状态,而是仅仅出自对形式的一味好奇和过分依赖。
这实质上是用形式来掩盖其生命体验的不足,是生命领悟上的一种苍白和空虚。
现代的职业化作家在这个方面很容易走得更远。
那么,形式高度发展后形成遮蔽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理论上说,文体形式的一切要素都有可能形成遮蔽。
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⑴以格律为诗。
格律就是指平仄、对仗、用韵、句式等方面的因素。
这几个方面的内容,在高度发展了的文体形式中,已经够有志于从事文学写作的人琢磨的了。
写出一首诗或词来,而平仄、韵脚一点不出差错,已经是相当不容易的事了。
也正因为实行起来比较困难,所以才会耗费人们大量的精力去掌握它。
而一旦人们花费了较大的精力去从事某种事情时,它就不知不觉地会使人们产生对这件事情(即研究对象)的偏爱。
每个人都会对自己倾注了大量精力的东西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珍惜和依恋的感情,作出过高的评价。
对于格律也是如此。
古人为了学习做诗,都曾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研习有关的格律,这无形中便会形成对格律的过分重视,而诗的本性倒渐渐被忽视、被遮蔽了,终至于把格律本身当成了诗。
只要一涉及古典诗词,人们首先就想到平仄、韵脚、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