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成本问题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社会成本问题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社会成本问题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24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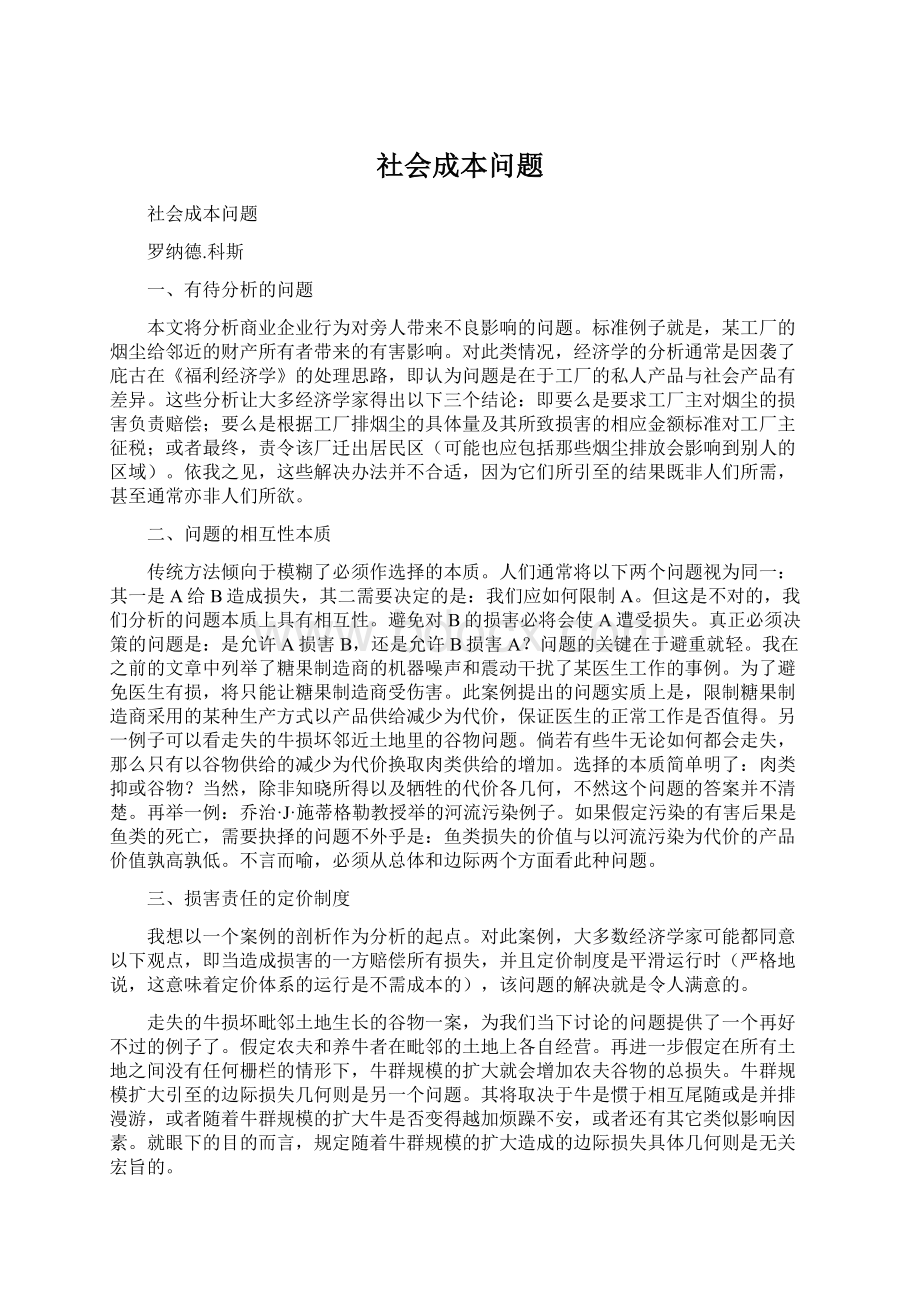
当然,除非知晓所得以及牺牲的代价各几何,不然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清楚。
再举一例:
乔治·
J·
施蒂格勒教授举的河流污染例子。
如果假定污染的有害后果是鱼类的死亡,需要抉择的问题不外乎是:
鱼类损失的价值与以河流污染为代价的产品价值孰高孰低。
不言而喻,必须从总体和边际两个方面看此种问题。
三、损害责任的定价制度
我想以一个案例的剖析作为分析的起点。
对此案例,大多数经济学家可能都同意以下观点,即当造成损害的一方赔偿所有损失,并且定价制度是平滑运行时(严格地说,这意味着定价体系的运行是不需成本的),该问题的解决就是令人满意的。
走失的牛损坏毗邻土地生长的谷物一案,为我们当下讨论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再好不过的例子了。
假定农夫和养牛者在毗邻的土地上各自经营。
再进一步假定在所有土地之间没有任何栅栏的情形下,牛群规模的扩大就会增加农夫谷物的总损失。
牛群规模扩大引至的边际损失几何则是另一个问题。
其将取决于牛是惯于相互尾随或是并排漫游,或者随着牛群规模的扩大牛是否变得越加烦躁不安,或者还有其它类似影响因素。
就眼下的目的而言,规定随着牛群规模的扩大造成的边际损失具体几何则是无关宏旨的。
为简化论述,我尝试使用一个算术例子。
假定农夫的土地的年栅栏成本为9美元,谷物价格为每吨1美元,并假定牛群数与谷物年损失之间的关系如下:
牛群的牛数
(头)
谷物年损失
(吨)
每增加一头牛所造
成的谷物损失(吨)
1
2
3
6
4
10
假定养牛者对损害负有责任。
如果他将牛群的牛从2头增加到3头,他须追加年成本3美元。
在确定牛群规模时,他就须将此3美元与其它成本一起纳入核算考虑。
也就是说,除非追加的牛肉产出(假定养牛者宰杀牛)价值大于其相应成本以及附带增加谷物的损失价值,否则他不会扩大牛群。
当然,如果利用狗、放牧人、飞机、步话机和其他办法可减少损害,也只有在其成本低于免于损失的谷物价值,这些方法才会被采用。
假定圈围土地的年成本为9美元,养牛者希望有养4头或更多的牛,假定没有其它更便宜的方法可达到同样目的时,他愿支付这笔费用。
当栅栏围起来后,损害责任的边际成本为零,除非牛群规模扩大到不得不加固并花费建造更大的栅栏,因为同一时间内可能会有更多的牛在“破坏”栅栏。
但是当然,对养牛者而言,像以上数字例子中当牛群只有3头牛或更少一些时,不设栅栏而支付谷物的损失费也许更加合算。
人们可能会想,若养牛者支付所有谷物损失,那末如果养牛者将要影响到邻近土地农夫将会增加种植量。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如果先前谷物是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出售,边际成本等于已种谷物数量的价格,生产的任何扩张都会减少农夫的利润。
因为在新的条件下,存在谷物损害意味着农夫在公开市场上出售的谷物量将减少,但既然养牛者将为破坏的谷物支付市场价,所以农夫从既定产量中得到的收入不变。
当然,如果放牛通常不可避免有谷物破坏,因此养牛业的成长将抬高谷物的价格,那时农夫就会扩大种植。
不过,我只想将注意力限于单个农夫的情况。
我说过,养牛者占据邻近土地不会促使农夫增加产量,确切地说是种植量。
实际上,若要说养牛会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它只会减少种植量。
理由是,就既定的某块土地而言,如果遭破坏的谷物价值是如此之大,以致于剩下未坏的谷物销售所得不足以弥补耕种该块地的总成本,那么对于农夫和养牛者来说,达成一笔交易即不在此块土地上开荒耕种将是有利可图。
一个算术例子就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
假定起初耕种某块土地收获谷物价值为12美元,耕种成本为10美元,净收益为2美元。
为简明起见,假设土地为农夫所有。
现在假定养牛者开始在毗邻的土地上经营,谷物损失的价值为1美元。
在此情况下,农夫在市场上销售谷物获得11美元,因蒙受损失得到养牛者赔偿1美元,纯收益仍为2美元。
现在假定养牛者发现扩大牛群规模有利可图,即使损害赔偿费增加到3美元也不在乎,这意味着追加牛肉生产的价值将大于包括2美元额外损害赔偿费在内的追加成本。
但是,现在总的损害赔偿支出是3美元。
农夫耕种土地的净收益仍是2美元。
如果农夫同意不耕种的损害赔偿不超过3美元,那末养牛者的境况就会得到改善。
而农夫只要赔偿费用超过2美元就会同意不耕种。
显然,农夫放弃耕作且双方都满意的讨价还价余地还是有的。
然而,同样的观点不仅适用于农夫耕作的整块土地,而且也适用于任何分成小块土地的情况。
举例来说,若牛有相当固定的行走路线比如通向小溪或树荫地带。
在此情形下,沿路两旁的谷物损害量也许较大。
若是如此,农夫与养牛者将发现,农夫放弃耕种此狭长土地的交易将使双方均能获利。
然而,这可能引至其它的情况。
假定牛有一条相当固定的路线,再进一步假定耕种这一狭长地带所获谷物价值为10美元,但耕种成本为1l美元。
没有养牛者的情况下,土地就会荒芜,然而,当出现养牛者之后,如果耕种这块土地,所种谷物很可能会被牛损坏。
在此情形下,养牛者将被迫支付给农夫10美元。
诚然,农夫会损失1美元,但养牛者则损失10美元。
很明显,这种情况不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因为任何一方都不愿看到这种结果。
农夫的目的是要养牛者赔付其同意不耕种。
农夫获得的赔偿不可能高于用栅栏土地的成本,同样也不可能使赔偿金高到迫使养牛者放弃使用邻近的土地。
实际赔付额取决于农夫与养牛者进行讨价还价的本领。
但是,由于赔付既不会高得使养牛者放弃这块土地,同样其也不会随牛群规模变化而改变,因而如此协议不会影响资源的配置,而仅仅改变养牛者与农夫之间的收入和财富分配。
我认为,很清楚如果养牛者对相应的损害承担责任,而且定价制度平滑运行,在计算牛群规模的附加成本时则就须考虑别处产值的减少。
该成本将与牛肉生产的增加价值相权衡,给定养牛业完全竞争,那末养牛方面的资源配置将是最佳。
需要强调的是,通常案例情况中养牛者纳入成本核算的别处产值下降,很可能低于牛对谷物的损坏。
这是因为市场交易的结果可能导致土地耕种不再延续。
任何情况下,如果牛对谷物的造成了损坏且养牛者也愿意支付赔偿费,且其金额超过农夫使用土地的费用支出,那末上述结果(即,不再延续耕种,译者)总是可能实现。
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农夫使用该土地的费用支出应等于该土地上生产要素的总产值与其在次优使用状态下的附加产值之间的差额(即农夫必须支付的要素费用)。
若损害超过农夫使用土地的支出,则要素在别处使用带来的产出增加将超过纳入损害因素后该土地的总产出。
如此人们就将会放弃耕种这块土地而将各种要素释放到别处的生产中。
程序上仅要求养牛者赔偿谷物损坏但不涉及可能的耕种停止,终将导致养牛业中生产要素雇佣过少而谷物种植业中生产要素却又过多。
但如果存在市场交易,则对谷物的损害超过土地租金的情况不会持久。
不论是养牛者支付给农夫一笔钱让他放弃土地耕种,还是养牛者支付给土地所有者一笔稍高于给农夫交付的租金(若农夫自己也正出租土地的话)租下土地,最终的结果都一样,都将会实现产出价值的最大化。
即使农夫被引诱种植谷物而其在市场上销售却又无利可图,这也纯粹是短期现象,而且可期农夫与养牛者将达成一项停止种植的协定。
养牛者仍将留在原地,肉类生产的边际成本依然如故,因此,对资源配置并无任何长期影响。
四、对损害不负责任的定价制度
现在,我转向分析此种情况,即虽然假定定价制度平滑运行(即无成本),但企业对造成的任何损坏都无须承担责任。
这些企业不必对其行为造成的损害赔付。
我旨将说明,这种情况下的资源配置结果与企业必须负损害赔付责任并无二致。
由于前例中已经证明了资源配置是最优的,因而无须再重复这部分的论述。
回到农夫与养牛者的例子。
农夫的谷物损失随着牛群规模的扩大将增加。
假设牛群内有3头牛(这也就是若不考虑谷物损失时牛群的规模)。
如果养中者将牛减为2头,农夫最多可支付3美元;
如果减为1头,则最多可支付5美元;
如果减为零,则可以是6美元。
因此,如果养牛人将牛群规模定为2头而非3头,那末他就可从农夫处得到3美元。
因而,逝去的3美元也应是增加第3头牛的部分成本。
不论养牛人为增加第3头牛而付出3美元(如果养牛人得负责赔付农夫的谷物损失),还是他选择不多养第3头牛而得到3美元(如果养牛人对无须赔付农夫谷物损失),都不会影响最终结果。
在这两种情况下,3美元都是增加第3头牛成本的一部分,将与其他成本一并纳入考虑。
假如牛群规模从2头增至3头,养牛产值的增加超过引至的成本增加(包括支付3美元谷物损失费),那末牛群规模将扩大。
反之则反是。
无论养牛者是否对谷物损失负责,牛群规模都将一样。
有人可能会争论假定出发点为3头牛未免有点武断。
确实如此。
但若养牛者无法破坏谷物,农夫也不愿花钱避损。
举例来说,农夫的最高年支付不能超过每年9美元的栅栏土地成本。
而且也只有当农夫收入不至于下降到得放弃耕种此土地的水平时,他才愿意支付这笔费用。
进而,也只有当农夫相信,若不进行支付牛群规模将维持在4头或更高的水平,他才愿支付此费用。
假定情况确实也是如此。
若养牛者将牛减至3头,农夫最多愿付3美元;
如果减至2头,则最多愿付6美元;
如果减至1头,则是8美元;
如果完全放弃养牛,则是9美元。
将会发现出发点的变化并无改变养牛者将牛群减至任何既定规模而增长的金额支付。
若养牛者同意将牛从3头减至2头,他仍旧将从农夫处获得额外的3美元,这3美元也仍旧表示增加第3头牛将造成谷物毁坏的价值。
虽然农夫认定(不论是否正确)若没有对养牛者付费,其将维持的牛群数目实际有一些差异(即农夫认为若没有对养牛者付费,后者也不会将牛群维持到最大规模或对这个最终规模有所异议,译者),也许会影响他愿意支付的总费用,但实际上,这种偏差并不会对养牛者将实际维持的牛群规模有任何影响。
如果养牛者必须赔付牛造成的谷物损失,结果仍还并无二致,因为从既定数目(牛数,译者)中失去的收入就是等于(维持到,译者)同一数目所需的支付。
人们可能会认为,一旦交易达成,为了使农夫总支付增加,养牛者就有欲于增加超出其原所欲维持的牛群规模。
这也可能是确有其事。
这与(当养牛者必须赔付谷物损害时)农夫行为的本质完全一样。
由于已与养牛者达成赔付协议,农夫还是会在此后商议放弃耕种的土地上种植(若无养牛影响本身完全不耕种的土地亦是如此)。
但这种策略调整也只是双方协定的初步情况,并不影响长期的均衡结果。
即不论养牛者是否对牛破坏谷物负责,均衡结果均是同一。
有必要知道损害方是否应对破坏负责,因为若没有权利的初始定界,就不存在权利转让和重新组合的市场交易。
但是,若假定定价制度的运行无须成本,最终的结果(产值最大化)将不受法律决定(legal
position)的影响。
五、问题的重新说明
工商业活动的有害影响可谓形形色色。
英国早期的一个案例讲述的是一幢建筑物阻碍空气流通,从而影响一座风车的运转。
最近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案例涉及一幢房子的影子影响到毗邻旅店的小屋子、游泳池和日光浴场区域。
虽然前两节详细分析的走失牛群与谷物损失的例子似乎是有些特殊,但实际上却是不失为形式多样的此类问题的一个典型例证。
为了澄清本文观点的实质以及证明其普遍适用性,我将着手分析四个实际案例以对此作出新的说明。
先看“斯特奇斯诉布里奇曼案(Sturge
v.Bridgman)”,我曾在“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中用此案例说明此类一般问题。
此案中,某糖果制造商(在辉格莫尔街(Wigmore
Street))生产中需使用到两个研钵和杵(一个在该地已使用了60多年,另一个则使用了26年)。
接着某医生迁入其邻近房屋内(在文普洱街(Wimpole
Street))。
在医生搬入新隔壁住宅的头八年,糖果制造商的机器对医生一直并无什损害,直到医生在花园尽头紧挨制造商炉炊处造了一间诊所,情况便不复如此了。
医生发现糖果制造商机器的噪声和震动使他难以再利用他的新诊所,“特别是……噪声妨碍他用听诊器检查病人的肺部疾病。
他还发现在此无法开展任何需要思考和集中精力的工作。
”医生于是便提出诉讼,要求糖果制造商停止使用机器。
法院爽快地发出了医生所要求的禁令。
“严格贯彻本判决所依据的原则会给个人带来痛苦,但是,否定该原则将导致更多的个人痛苦,同时还不利于此土地开发为住宅用途。
”
法院确立了医生有不让糖果制造商使用其机器设备的权利。
但是,当然原本也还可能可以设想通过双方当事人的讨价还价,亦实现更改法院的安排。
倘若糖果制造商愿支付给医生一笔钱,且其数目大于医生将诊所迁至成本较高或较不方便的地段所带来的损失,或超过医生仍在此地看病但收入减少的损失,另一个可能的建议或是高于建造一堵墙以隔开噪声与震动所花的成本,医生本也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让制造商生产照旧。
制造商也会愿意如此行事,倘若其对医生的付费少于改变原地的生产方式、放弃生产、或搬迁它处所需的费用。
该问题解决办法的本质在于继续使用机器给制造商带来的收入增加是否超过给医生带来的收入减少。
但现在考虑此案糖果制造商胜诉的情况。
那末他将有权继续使用有噪声和震动的机器却不必支付给医生任何赔偿费。
于是,情况就正好和原来反一反了:
医生将不得不付钱给制造商使他停止使用机器。
倘若机器继续使用,医生收入的减少要大于制造商收入的增加,那末显然双方之间还是有讨价还价余地,即便由医生向制造商付费换取其不再使用该机器。
这也就是说,原来无须对制造商继续使用机器付费,并且还得赔偿医生因此所蒙受损失的情形(如果医生有权不让糖果制造商使用机器),将就变为医生从自身利益出发付钱给制造商以促使其不再使用该机器(如果制造商有权继续使用机器)。
此案的基本情况与牛损坏谷物的例子完全相同。
若市场交易的无须成本,法院有关损害责任的判定对资源的配置并无影响。
诚然,在法官们看来,他们正在影响经济系统的运行,使之朝己所意欲的方向。
任何其它判决“都将对住宅土地的开发产生不利影响”,该论点已在荒芜土地的打铁铺(冶炼厂)的例子中详细阐述,后来该土地就开发为住宅用地。
法官们的观点认为他们正在解决土地如何利用,也只有在必要的市场交易的成本超过权利的任何重新安排所能得到的收益时,才是正确的。
而且,也只有当住宅便利的价值超过损失诸如钢铁、板砖等的价值时,保持某区域(文普洱(Wimpole
Street)或荒地)作为住宅或其它专门用途(通过禁令赋予非工业使用者以消停噪声、震动和烟尘污染等方面的权利)才是人们所意欲的。
但法官们对此似乎并不了解。
“库奇诉福布斯案(Cooke
v.
Forbes)”是进一步说明此问题的另一个例子。
在编织可可果纤维草席时,有一道工序是将草席浸在漂白剂里,然后取出晾干。
来自某制造厂的硫酸氨气体会使光洁的草席变暗变黑,原因是漂白剂含有氯化锡,当它受到硫化氢的影响时,就会变成黑色。
原告企求发布禁令让工厂停止排放硫酸氨气体。
被告律师抗辩说,“如果原告不使用……某种特定的漂白剂,他们的草席纤维就不会受到影响;
他们的生产工序是不正常的,与商业惯例不相符的,甚至会对他们自己的纤维造成损害。
”法官评论到:
“……一个人有权在自己财产上安排某一生产工序,不论使用了氯化锡或是其他金属染料在这种工序中他,这在我看来似乎是再直白不过了。
但其邻人却无权随意排放气体,以干扰他的生产。
如果可以溯源到邻人,那末我很清楚,他显然有权来此要求消除此种损害。
”但事实上,损害纯属意外或是偶发的,若采取谨慎的防范措施也无例外风险,禁令就不再需要了,最终原告只落得企盼破坏行为发生,若这即为其本所欲。
我不知道此案例后续发展如何。
但很清楚,其本质上与“斯持奇斯诉布里奇曼案”的情形相似,只不过可可果纤维草席制造商不一定能得到禁令,但却不得不受到硫酸氨制造商的损坏。
对这种情况的经济分析与牛损害谷物的情况完全无二致。
为了避免损害他人,硫酸氨制造商可以加强预防措施或搬至他处,但随便哪种方法都会增加他的成本。
他也可以选择支付赔偿费,如果赔偿费少于为避免损害他人而导致的成本的增加。
于是,他所支付的赔偿费就成了硫酸氨生产成本的一部分。
当然,也正如法律程序中提出的,倘若通过改变漂白剂(假定这将增加草席制造商的生产成本)可以消除这种损害,并且其成本的增加少于其它方面的损失,如此,两家厂商可能达成一项双方都满意的交易方案即使用新的漂白剂。
倘若法院的判决草席制造商败诉,即意味着他不得不蒙受破坏却又得不到赔偿,但最终的资源配置还是不受影响。
如果硫酸氨制造商愿意停止制造硫酸氨,那末草席制造商将愿意支付给硫酸氨制造商一笔费用,其在量上应该等于硫酸氨制造商成本的收入减少量(成本或损失的增加)。
该收入损失则仍旧是硫酸氨制造商(应该是草席制造商,译者)的生产成本。
此案例就分析意义上确实完全等同于牛的例子。
“布赖恩特诉勒菲弗案(Bryant
Lefever)”以一种新的方式提出了令人闹心的烟尘问题。
在此案例中,原告和被告的房屋紧挨着,且高度大体相同。
1876年之前,原告可以在他房子内任何一间里生火而室内都没有烟;
两幢房子维持老样大概有了三四十年。
1876年,被告拆掉了旧房重盖新屋。
他们在原告烟囱旁造了一堵墙,大大超过了原先的高度,并且在房顶堆放木材。
因此,每当原告生火,烟囱的烟就会进入室内。
当然,烟囱冒烟是竖立了剁墙和房顶堆放木材影响了空气流通所致。
陪审团初步裁定原告获得40英镑的损害赔偿费。
此案接着转到地区法院,原有判决被推翻。
布拉姆韦尔(Bramwell)法官争辩说:
……据说,陪审团已发现被告的所作所为对原告房屋的产生了侵害。
我们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一点。
毫无疑问,侵害是存在的,但这不是被告引起的,他们没有做出任何引至侵害的事,他们的房子和木材也无甚害。
恰恰是原告自己引起了破坏,因为他在烟囱里生火而烟囱又置于离被告的墙过近的地方,于是烟无法消散只有倒灌入室内了。
一旦原告不生火,一旦他将烟囱挪个地方,一旦他将烟囱造得再高些,讨厌的烟不就没了。
那么,是谁招来讨厌的烟呢?
显然是原告。
如果原告在被告堆放木材后建房,毫无疑问这是原告引起的;
而原告在被告堆放木材之前建房,实际上亦是如此。
但是(同样的回答实际上意味着),如果被告惹出讨厌的烟,他们也是有权如此的。
如果原告除了毗邻被告的房屋建房和在房上堆木材的权利之外,没有任何通气的权利,那么他的权利就从属于被告的了,而且虽然被告在行使自己的权利时造成了对原告的侵害,但他们对此并没有责任。
并且,科顿(Cotton)法官还说:
此处我们发现被告房墙的耸立确实不论理解上和现实上都干扰了原告屋内居住者的舒适感,而且据说被告得对侵害需负责。
通常情况下确实如此,但被告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将任何烟尘和有害气体送进原告屋内,而是以某种方式阻断了原告房子烟尘的出路,对此……原告并无法律权利。
烟是原告自己弄的,也真是它弄的自己不舒服。
除了他有……权以特定的方式处理这些烟而被告干涉了原告对此的处理,否则他不能起诉被告,因为烟是他自己引起的,而对此他自己却又未有任何有效的应对措施,这才让原告自己很是恼火。
这好比某人试图通过下水道将自己土地上的污水排放到邻居上地上一样,在使用者取得权利之前,邻居可以堵塞下水道而无须对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
无疑,对产生污水的土地的所有者来说,这会引起很大不便。
但是,他的邻居的行为是合法的,且他对可能引起的结果不负任何责任,因为造污水的人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手段清除污水。
我不欲再次论证不论法院如何判决,双方当事人讨价还价对当前困境的改善(以将木材置于它处的成本或增高烟囱的成本等等为评判条件),最终的结果都将完全相同,因为有关牛的例子和前两个案例的详尽讨论中已充分阐释了此点。
我所要讨论的是地区法院法官的辩论,即讨厌的烟不是由造墙者引起,而是由生火者招致的。
该情况的奇特之处在于蒙受烟尘妨害的正是生火者而非其他第三者。
因为所讨论问题的核心关键正在于此,所以并不能说此事无关痛痒。
究竟谁引起了令人不快的烟尘?
答案似乎不言而喻的,烟正是由造墙者和生火者共同引起的。
给定生火前提,若无墙壁,就不会有烟尘妨害;
而倘若有墙,则不生火也就不会有烟尘妨害。
随便拿掉墙或生火二者之一,烟尘妨害就没了。
按照边际原理,显然双方都有责任,则两者在决定是否继续会产生烟尘的行为时,都必须将烟尘妨害产生的不适纳入成本核算。
而且如有可能市场交易,实际发生的情况也正是如此。
尽管造墙者对妨害不负法律责任,但因为烟囱冒烟户将可能愿意支付给造墙的邻居一笔钱,其金额大小大体是等于消除烟尘妨害的价值,因此,这笔钱也就成了修建高墙和房顶堆放木材的成本。
法官的论点生火者自己引起烟尘,也只有在假定墙壁是既定不动要素时才正确。
法官的判决仅是确立了建造高墙人的造墙权。
倘若烟囱里冒的烟还对木材有损害,那末此案就更有趣了。
那时,造墙者就蒙受损失,此案就与“斯特奇斯诉布里奇曼案”很是相似了,且几乎毫无疑问的是,尽管事实上直到木材所有者建起高墙后损失才发生,但生火者还是需赔付后续的木材损失。
法官们断定了法律责任,但这不应使经济学家混淆其中内含经济问题的本质。
牛群与谷物的例子中,的确没有牛群就不会有谷物损失;
但同样,未有谷物也就无谓谷物损失了。
倘若糖果制造商不开动机器,医生的工作就不会受到影响;
但倘若医生不在此特定地点设立诊所,那末机器也就没有扰及任何人了。
硫酸氨制造商的排烟熏黑了草席,但倘若草席制造商不恰在该地晾草席又恰好使用此种特定漂白剂,那末也不会有任何损害了。
如果我们讨论非得探究因果,那双方当事人均是损害的始作俑者。
但若我们的目标是资源的最优配置,那末双方当事人行动时就需将可能引至的不良影响(即妨害)纳入核算。
如前所述,平滑运行的定价系统的美妙之处正是在于,不良影响导致的产值降低都将自动转为双方的成本。
“巴斯诉格里高利案(Bass
Gregory)”是最后一个阐释此问题的极佳例子。
原告系乔利·
安格勒斯(Jolly
Anglers)酒吧的所有者和承租人。
被告拥有一个小别墅附带一庭院毗邻乔利·
安格勒斯酒吧。
在酒吧下有一辟于石间的储酒地窖。
酒窖经由一个洞或斜井样的渠道通至一个位于被告庭院的旧井。
因而,此井则就成为酒窖的通风管道。
酒窖“在酿酒过程中一直有着特殊用途,若不通风则无法酿酒”。
诉讼的起因是被告将一个栅栏从旧井口移走,“以便使得酒窖中的空气无法从井口散发……”。
依照案例报告,是什么推动被告如此行事已经无从确知。
也许,“酿酒过程中会挥发出某种气味,沿井扩散至上面的空气中”,而他对这种气味却又是极其反感。
无论如何,他偏好于将庭院里的井堵上。
法院首先须确定酒吧老板是否拥有空气流通权。
若他们享有此权利,此案将明显有别于“布赖恩特诉勒菲弗案”(前已考察过)。
然而,这对分析此案也并未造成多大困难。
在此案中,空气流通仅限于“严格设定的通道”,而在“布赖恩特诉勒菲弗案”中,所涉及却是“所有人必须的正常空气流通”。
法官因此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