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金纳访谈521309685Word格式.docx
《斯金纳访谈521309685Word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斯金纳访谈521309685Word格式.docx(2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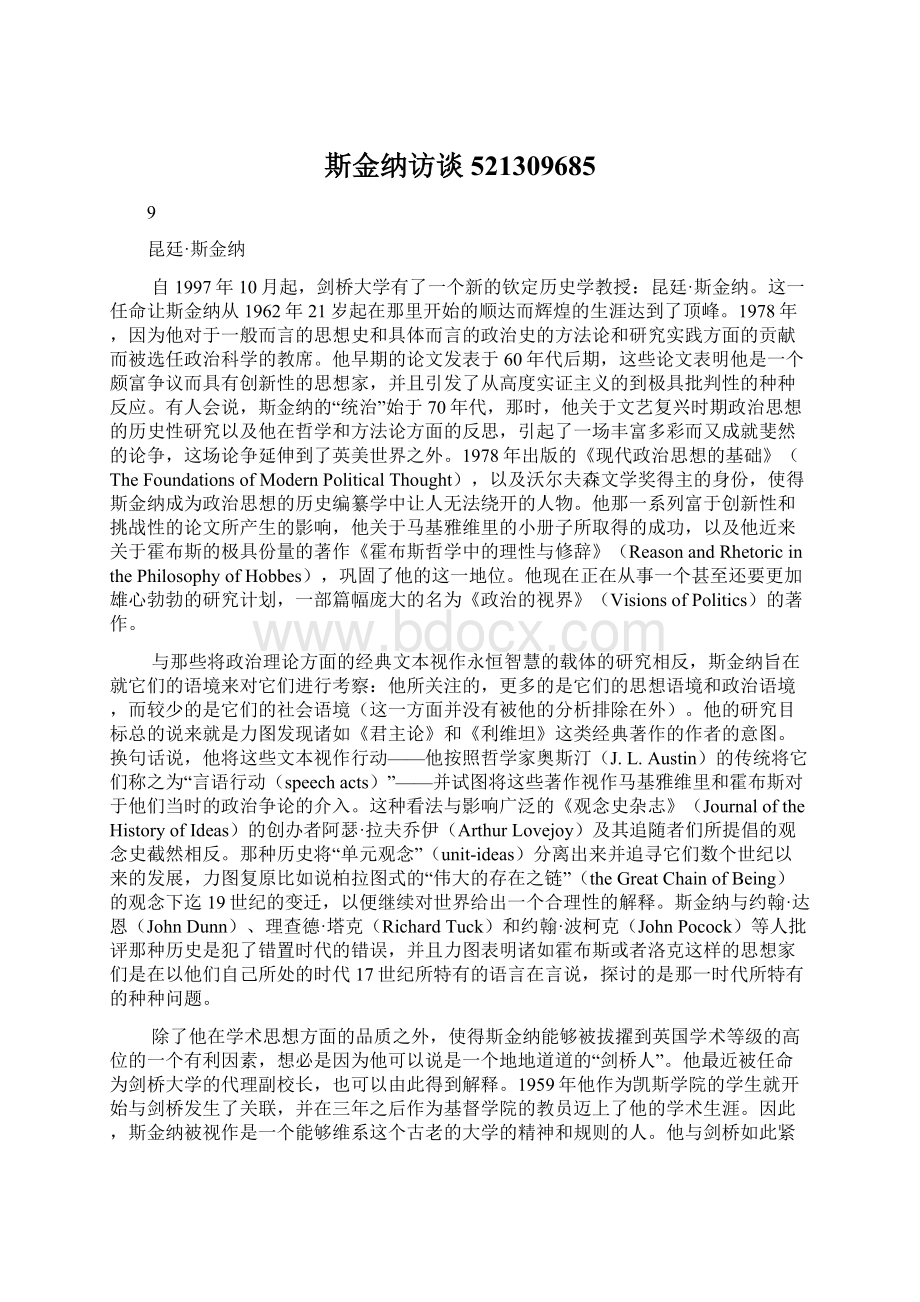
塔克(RichardTuck)和约翰·
波柯克(JohnPocock)等人批评那种历史是犯了错置时代的错误,并且力图表明诸如霍布斯或者洛克这样的思想家们是在以他们自己所处的时代17世纪所特有的语言在言说,探讨的是那一时代所特有的种种问题。
除了他在学术思想方面的品质之外,使得斯金纳能够被拔擢到英国学术等级的高位的一个有利因素,想必是因为他可以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剑桥人”。
他最近被任命为剑桥大学的代理副校长,也可以由此得到解释。
1959年他作为凯斯学院的学生就开始与剑桥发生了关联,并在三年之后作为基督学院的教员迈上了他的学术生涯。
因此,斯金纳被视作是一个能够维系这个古老的大学的精神和规则的人。
他与剑桥如此紧密相连,以至于他的某些同事认为,有一部描绘这个大学城的某些生活侧面的侦探小说(很不幸那不是一部很好的小说)中的主人公就源自于他。
尽管因为他的新职位所带来的行政事务而忙碌不堪,以及众所周知他在周围众多学生的身上花了不少功夫,斯金纳还是乐于为这次访谈安排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
在基督学院他那优雅的套间中,他用了很多时间来谈论他的研究、他的批评者、他的方法、兴趣、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自由的观念、当今史学趋势等等。
斯金纳在兴致盎然和彬彬有礼的同时,又非常郑重和认真,他给倾听者留下的印象,是他在谈到他的研究课题时那种机智、流畅而又热情饱满的风格。
他的思想的井然有序,正与他房间中各种材料、书籍和物品安放得一丝不苟相映成趣。
他那娓娓道来的言谈中没有任何的偏题、犹疑或者语法上的失误,与他的史学和哲学著作中那种优雅而清澈的文字并无二致。
他的一个同事以开玩笑的口吻,将斯金纳非凡的流畅风格用他的解释理论中一个核心概念作了这样的比附:
“斯金纳说话的时候给人的印象,就是一台装好了生产高能高效的‘言语行动’的程序的计算机!
”
玛利亚·
卢西亚·
帕拉蕾丝-伯克是什么使得你成为了一个政治思想史家?
斯金纳我上中学时有一个出色的校长,他让我阅读英国政治理论中的好几种经典文本,从而将我送上了这条道路。
他对我的青年时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且最早点燃了我对于我的专业的热情。
当我想到我在那样早的时候所研读的文本时,内心总是颇为惊异。
其中的一本是托马斯·
莫尔的《乌托邦》,我们在学校里是当作考试要考的文本来念的;
还有一本他坚持要我们全要念完的,是霍布斯的《利维坦》。
我依旧保存着我在中学时代得到的这些书,而且从那时以来我就在围绕这些文本进行写作和演讲。
在这个幸运的开端之后,我在剑桥念本科时听到的一些出色的课程加深了我的兴趣。
有两个人对我尤其有影响。
其中的一个是约翰·
布罗(JohnBurrow),他那时是基督学院一个年轻的研究员(现在是牛津的思想史教授),他上的一些课是我本科时代所听到的最激动人心的课程。
然而,从我如何试着来从事这个专业的研究的角度而言,另外一个人对我来说甚至还更为重要,那就是彼得·
拉斯莱特(PeterLaslett)。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的,是他涉猎广泛而又充满洞见卓识的授课,还有他所编定的洛克的《政府论两篇》(TwoTreatisesofGovernment),我上本科时此书就出版了,一直是我这专业内现代文本研究的最了不起的成就之一。
我记得,约翰·
布罗告诉我,我必须写一篇关于洛克的论文,因为拉斯莱特的新版本将要带来的不仅是这个领域的新标准,而且还会开启一种新的研究取径。
我记得正式阅读拉斯莱特给他那个版本所作的导论时,完全被它征服了。
我觉得它在很多方面都精采纷呈。
首先,它是一篇优美的英文,具有一种在我看来是无与伦比的优雅和明晰。
尤其是与我当时被指定阅读的那些公认的大史学家的任何文字比起来,更是如此。
其次,这个新版表明,拉斯莱特作出了许多对我来说在方法论方面很有意思的发现。
洛克的《政府论》一直以来就被视作对于1688年英国革命的辩护,以及对于均衡的议会立宪制度之建立的颂扬。
拉斯莱特证明了它其实是在付印之前10年就已经写好了,它不是对于任何革命的辩护,并且是在查理二世治下的绝对主义日甚一日的势头下写就的。
对我而言尤其重要的,就是拉斯莱特坚定地认为,我们不应该将这个文本孤立于它写作的环境来加以思考。
他揭示了了解洛克写作那个文本时所处的语境对于理解其意涵所具有的重要性。
《政府论》成为对那场革命的颂词、自由主义的伟大文本、英国立宪主义的奠基性的文本。
然而,这些名目当中没有一样是与它在历史上的身份相吻合的;
它们与洛克写作时认为他自己在做的事情毫无干系。
你的家庭和童年的经历对你选择了要做一个历史学家是否起了什么特别的作用?
还真没有。
我想过这个问题,我并不认为它们对我的学术发展有什么直接的影响。
我母亲倒的确在大学里学的是英国文学,结婚之前是一个中学教师,我早年阅读的很多东西就受到了她的影响。
然而,我青年时代的生活中有一件事情与此相关,这在英国是不大寻常的。
那就是我在长到相当大的年纪之前并没有与我的父母生活在一起,因为他们住在非洲,我父亲是尼日利亚殖民当局的官员。
我不仅不是在那里出生的,而且我从来没有踏上过非洲的土地,即便学校放假的时候也没去过。
英国殖民当局不鼓励小孩子去非洲,因为从医疗条件来说那里仍然是一个危险的地方,而且还因为那里没有学校——至少没有英国人能够认可的那种学校。
我的父母亲常常在我父亲离开那儿的时候回到英国来,但那也只是每两年才有一次。
因此我是跟我的监护人、我母亲的姐妹生活在一起的,直到我7岁时上了寄读学校——也就是贝福德学校(BedfordSchool);
在那之后我的假期照样还是跟她一起过。
我的姨母是曼彻斯特附近的一个医生,或许她对我后来的生涯产生了某些影响。
她是一个很引人注目的人,是历史书籍的热心读者,她家里堆满了历史书。
她也很有热情去参观英国著名的建筑,并且经常把我给带上。
考虑到所有那些早年被人领着的旅游经历,或许我应该成为一个社会史家的。
我还记得战后不久我们的一次游历,当时还有宵禁(作为医生,她有特别许可证),我们访问了德比郡的查特沃斯,那是德文夏尔公爵们的别墅,在曼彻斯特东南方向50英里的地方。
我一点也不知道,40年之后我会花很多时间在查特沃斯作研究,霍布斯死后他的档案文献就存放在那里。
想起我早年的生活,巨大而直接的影响来自于我刚提到过的那个人,我的校长约翰·
艾尔(JohnEyre),我们至今仍然有联系。
正是他坚持要我参加剑桥的入学奖学金考试,因为他相信我能够得到奖学金。
那些奖学金已经废止好长一段时间了,然而在当时要是得到一项的话,可是一桩光彩的事情。
在我的学校里,如果有哪位男孩子得到了这样的奖项,我们全都会额外放半天假的。
这个时候我和我父母生活在了一起,因为我父亲退休之后他们在贝福德买了房子,我不再做贝福德学校的寄宿生了,而只是白天上学。
我还记得,到了向剑桥提出申请的时候,我让我那可怜的父亲给冈维尔与凯斯学院(GonvilleandCaiusCollege)写了一封颇为莽撞的信,我哥哥就在那儿学医。
我父亲在信中说,他的长子在凯斯,因为对于学医来说,那是一个出色的学院,而他的小儿子想要读的是历史。
凯斯对于学历史来说是个不错的学院吗?
学院给他的回答让我记忆犹新,那是负责录取的老师写的一封两行字的信,里面写道:
“凯斯在所有学科上都是最好的学院”。
这听起来真不错,于是我拿到凯斯的一份奖学金,进了这个学院。
你曾经说过,听到你的批评者们把你说成是唯心主义者、唯物主义者、实证主义者、相对主义者、好古成癖的人、历史主义者以及甚至于单单就是一个方法论者,让你大惑不解。
你怎么看待你自己呢?
这可不大容易。
在这些头衔中,我最不想否认的就是相对主义者,如果那不是意味着概念上的相对主义者的话——我当然不是后者。
那就是说,我不相信,真理的概念可以径直等同于任何在某一特定时间可以合理地认其为真的东西。
然而,在我看来,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倾向于某种温和的相对主义。
我的意思是说,所有有兴趣去了解其信仰和习俗与他们自身的文化大为不同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学家,就已经是持有一种温和的相对主义了。
他们将自己的研究视作一种广义上的翻译,也即,试图深入一个不同的文化的内部,尔后在阐述那个文化的方方面面时又出之以这样的方式,使得那一文化的差异性得以忠实地反映出来。
说到别的头衔,我一直对哲学中的唯心主义传统很有兴趣,我所敬仰的很多人物也来自英国哲学中反实证主义的、唯心主义的传统。
事实上,我觉得对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实践而言产生了最为直接的理论影响的作者就是柯林武德;
如此说来,倘若他是一个唯心主义者,那么那个标签就不是我想要拒绝的了。
我想要给自己贴上的标签,是我在给剑桥大学出版社编辑的一套丛书想名字时用到的那一个,那是一个表达了我感兴趣并且努力去实践的那种类型的思想史的名称:
“语境中的思想(IdeasinContext)”。
换句话说,倘若非得让我来描述一下自己的话,那我就是在研究方法上是跨文本的、语境论的(intertextual,contextualist)一个历史学家。
罗伯特·
达恩顿自陈,他的历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走入了“历史学家的梦境”—-那就是一个等待着人们来发掘的档案的宝藏——的好运。
在他而言就是发现了18世纪瑞士最大的出版社纳沙泰尔印刷公司的档案中各种没有被人碰过的材料。
在你身上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吗?
我没有这样的运气,但我觉得,我可以准确地记得究竟是什么东西让我开始起步的。
说到这儿我又得回到彼得·
拉斯莱特(我毕业时他是我的第一个导师),还可以谈一谈在60年代早期的时候学术生涯可以以多么不同的方式起步,因为那是一个(用拉斯莱特的名作的书名来说)“我们失去了的世界”。
我属于在拿到博士学位之前以及甚至于没有博士学位还可以指望得到大学里的终身教职的那代人。
我毕业于1962年,我所在的凯斯学院在当时还可以依据本科考试的结果选择有的人来充任研究员的职位。
学院在选定我的时候并没有要求任何学术研究来证明选择我的正当性,我马上就从一个本科生变成了我那个学院的教员。
但是实际上我从来没有接受那个职位,因为那个夏天稍晚的时候,一件还要更加不同寻常的事情落在了我的身上。
基督学院主要的历史教师之一约翰·
肯扬(JohnKenyon)、一位出色的研究17世纪的史学家突然接受了赫尔大学的教授席位,转眼之间就离开了基督学院。
就在这个时候,我在凯斯学习时的导师奈尔·
麦肯德里克(NeilMcKendrick)——他现在是这个学院的院长——把我推荐给了普拉姆爵士(SirJackPlumb)、当时整个大学最成功的历史教师之一。
我于是被选任基督学院的教职,并担任了历史学科方面的主任助理,尽管我才刚21岁。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让人兴奋的开端,有一阵我陷入了繁重而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之中:
我要协助历史学科本科生的录取工作,主持学院的很多考试,每周要上15个小时的课。
另一方面,这样的情形使得我很难开始做研究。
这个时候,彼得·
拉斯莱特又一次在我的发展道路上给我了重要的帮助。
他看到我所遇到的事情看起来也许挺不错,但对于我的学术发展而言实在不是什么好事。
由于我没有一个正式的导师,也没有在做一篇博士论文,他对我的关注、我们在他学院的办公室和他家里无休无止的谈话,对那个时候的我而言,真是弥足珍贵。
我记得与他谈到他那个洛克著作的新版本,感觉到他对于他在那项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有一种奇怪的想法。
他告诉我,论者往往将霍布斯和洛克作为系统的政治理论家相提并论,而他试图将洛克从体系式的思想家的宝座上拉下来,并且表明洛克的《政府论两篇》与霍布斯的《利维坦》正好相反,不过是一部piè
ced’occasion[应时之作]。
然而,他似乎依然将霍布斯视作一个能够独立于其历史语境来加以评判的政治学体系的作者。
问题在于,拉斯莱特自己的著作让我相信,与他似乎所相信的相反,对于任何哲学文本而言都必须要进行类似的研究。
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决心为霍布斯来做拉斯莱特为洛克所做的那种工作。
当然,我没有完全做成这件事情,因为这是一个繁重的任务,然而拉斯莱特帮助我走上了这条道路。
尤其是他建议我去查特沃斯,看看是否有什么能够有助于将霍布斯与他的政治语境联系起来的手稿材料。
我最初发表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基于认真考虑彼得的忠告的结果。
让我吃惊的是,在此之前几乎没有人去过查特沃斯翻看那些材料,并且提出那样的问题。
我想,我是最早利用霍布斯未发表过的通信的学者之一,并且我最早的论文之一就是关于那一史料的重要性的。
它并没有能够使我搞清楚霍布斯思想的意识形态语境,然而它的确让我开始对于他的研究所处的各种思想传统有了某种感受。
这同一个机缘也让我碰到了霍布斯就某个特定的政治危机——也即所谓的“废黜危机”——发表评论的一份简短的手稿,那是在他辞世的那一年写下的。
这真是让我兴奋不已,因为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理论家对于当时国会所正在发生的事情作出的评论。
因此,可以说我的学术生涯开始之时有三件幸运的事情。
一是受益于拉斯莱特精辟的忠告。
另一件则是,我是在历史学而非哲学的学科体制内开始做研究的,哲学学科里面对于这类语境问题是不会有什么兴趣的,而我很快就发现,最吸引我不过的恰恰就是这类问题。
然而,我最大的幸运,也是我所乐于一再回过头来谈到的,还在于我的同辈人中间,因为我是与一群出色的年轻学者在同一时间开始研究工作的,我们都同样受益于1960年代英国高等教育的大幅度扩张。
在你看来,对于还原一个文本的“历史身份”(historicalidentity),作者的意图再重要不过。
那么,你能够谈谈你在写作看起来像是你的宣言书的1969年的那篇文章——“思想史中的意义与理解”(MeaningandUnderstandingintheHistoryofIdeas)——时内心所怀有的意图吗?
你其它所有的论著是否都是对于同一个问题的回应呢?
很大程度上是这样。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实践一直是在我早期那篇论文所指出的方向上在走。
你说得很对,那是一篇宣言书。
那篇论文写来就是为了让人们震惊和恼怒的,它成功了。
我旨在对两种盛行的思想史研究路数提出挑战,也许一点也不奇怪,这篇文章要想发表的时候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在最后被《历史与理论》(HistoryandTheory)接受之前,它被好几家杂志退了回来。
它在很大程度上属于那个年代的作品,很有争议性,我也再不会照那个样子写作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当时所论及的两种研究路数不再有那么多的人在实践了。
这些路数中的一种,是将比如说柏拉图、霍布斯、休谟或者黑格尔的哲学著作视作仿佛它们是在某种永恒的现时之中飘荡。
我的目标不仅是说我想要以不同的路数来处理这个主题,而且还想表明,单纯的文本分析是不可能指望对这些文本达到恰当的理解的。
我以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为例,试图说明许多哲学文本中有着大量的重要问题,是单单靠阅读它们所永远也无法领会的。
尤其是,你永远无法理解它们是在做什么,它们究竟是在讥讽、否定、嘲弄、忽视、还是在接受别的观点,如此等等。
在我最近关于霍布斯的书中,我依然是在同一个方向上走,力图回答那种问题。
我的宣言书的第二个靶子是思想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传统,那在当时、尤其是麦克弗森(C.B.Macpherson)对17世纪政治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ThePoliticalTheoryofPossessiveIndividualism)——于1962年出版以来很有影响。
那本书让我极为不安。
我认为那是一篇杰作,对于霍布斯和洛克的文本的思考方式富于洞见,然而,与此同时,我又觉得将他们的学说视作对于他们的社会的深层社会经济结构的某种反映,这中间有着极为错误的东西。
我一点也不喜欢那种东西,尽管如今我觉得我在宣言书中根本就没有能够成功地说清楚让我不喜欢它的是什么东西。
我想要论证的是,切入这类文本的办法,不是力图发现他们提出他们的学说时所处的社会的语境,而是要揭示其思想的语境。
你是全盘拒斥马克思主义呢,还是在马克思或者他的某些追随者那里也看到了某些有价值的东西?
简单的回答就是,我一点也不全盘拒绝马克思主义,并且我还进一步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哲学变得如此名声扫地,这是当代社会理论的不幸。
考虑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我愿意多花点功夫来谈谈。
一开始,我想说一下对我而言马克思主义具有价值和重要性的三点。
第一点是在方法论的层面上。
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假设在我们所有人这里都深入人心,那就是社会存在决定意识。
如今人们在写作历史时都会假设在某些层面和某种程度上是这样的情形。
当我们追问此种决定作用是在何种程度和何种层面上发生时,问题就出来了。
我想稍后多谈一下这个问题。
第二点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留传给我们的那种社会诊断的方式及其诊断用语。
我们显然无法否认,马克思主义给我们带来了讨论任何社会中的社会关系的一套有价值的词汇。
如今没有人会认为,他们可以不运用诸多实际上起源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性概念——比如,异化或者剥削——就可以对社会领域进行研究。
这就到了我要说的第三点,也即,颇有讽刺意义的是,就在眼前、在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哲学而四处声名扫地的时候,马克思的某些预言却前所未有地显示出了他的深邃洞见。
当然,马克思不是在全球范围上来思考的,然而资本主义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关系——第一世界变得越来越富裕的同时,第三世界却越来越穷困,那是欠了第一世界的债的结果——在我看来是将要来临的这个世纪的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
说了这些话以后,我还得澄清一点,那就是我自己的思想不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但肯定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这其中有两个主要的缘由。
我前面提到过,当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路数由于诸如麦克弗森和克里斯托弗·
希尔等人的论著而风靡一时的时候,我在1960年代引起争议的那些论文中对马克思主义是持批判态度的。
我最为反对的一个信条是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也即认为人们的信仰可以解释为不仅是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所导致的产物,而且还不过是其附带现象,。
我那时候的一个重大抱负就是要表明这种观念是错的,我觉得我以以下的方式做到了这一点。
意识形态结构的根本目的之一就是使社会安排合法化或者瓦解其合法性。
倘若情形真是如此,任何群体要想拥有这样的能力,使得他们在他们的社会安排中能够进行任何变革、并且在任何有关那些变革的道德价值的争议中吸引人们站到他们一边,就有赖于他们可以利用一套可以拿来批判那些安排的道德词汇,这样的道德词汇不是由我们给定的,而是给定了我们的;
换言之,倘若它们有着什么样的规范性力量的话,那也是因为它们置身于特定的历史处境,并且结果就成其为显而易见而又可资利用的争论武器。
情况既是如此,那么,我们可以通过革新和改变我们的社会而能够做到的事情,就有赖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将我们拟议中的变革规划适合于一套现成的道德语汇;
因为,除非人们能够认可这些改革规划乃是道义上正当的规划,他们就不会拥护这些规划。
我想强调的是,你在社会实践中能够做什么事情,取决于你能够给你所做的事情什么样的道德上的说法。
倘若如此的话,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显然错了,因为这些说法不是附带现象,不是某些其它过程所导致的产物,而是相反,必须将其列入引发社会变革的条件之一。
我成为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其他方面的主要原因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证主义有关,这是我在70年代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的它的一个缺陷。
那些年,我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于是有了与克利福德·
吉尔兹和托马斯·
库恩成为同事的幸运。
(我的办公室就紧靠着库恩的。
)他们帮助我看到了这一事实的重要性:
马克思依旧生活在一个让他觉得能够谈论真实意识与虚假意识的过于简单的世界之中。
然而,在一个更加后现代的文化中——就像是我在普林斯顿所置身其中的那一种——人们更多地从建构的特性来看待意识,马克思主义就开始像是考察社会领域的一种非常粗糙的方式。
更有意思的问题似乎是关于如何在不同的建构之间进行协调的问题,既然它们全都有着自己的话可说。
于是,历史学的或者人类学的任务,就是通过从内部来理解不同的建构来确证它们的合理性。
而马克思主义将真假截然二分,就无法将这样的取径容纳在自身之中。
但是,我还是想说,尽可能地确证我们祖先的合理性的这样一种抱负,是历史学家所必须怀有的。
最后,我想说的是,与西方世界的其他许多人一样,我还是认为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病症的诊断中依然有着某些崇高的东西。
我们确实发现资本主义是最有效率的——也许是唯一有效率的——将繁荣景气分送到为数众多的人民之中的手段。
然而没有其它的经济体制曾经获得过那样绝大的成就这一事实,也不应该让我们对于它让人类付出了巨大代价这一事实视而不见。
仅仅因为它比之别的任何体制都更有效率就装做它没有付出那些代价,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这么做。
共产主义声名扫地的事实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之中就没有声名扫地的东西。
它依旧是一个很不公平的体制,正如马克思主义仍旧是思考那些不公平的一种很有意思的方式一样。
你所实践的那种类型的思想史被说成是“政治思想的史学编纂中的一场革命”。
你认为它究竟有多大的革命性?
维特根斯坦在他的《哲学研究》的篇首引言中说,一切进步都没有它们看起来那样重要。
我认为,我同代的有些学者确实改变了思想史写作的方式,然而,你可以很容易地看到我们是从那儿得来我们的观念的。
我当然不认为我制造了一场革命。
我的确是以与通常写作思想史稍有不同的方式开始我的写作的。
可是,要让我回想起深刻地影响了我的那些人——或者是因为他们已经将我所选取的立场理论化了,或者是因为他们的实践对我来说树立了典范。
——并非难事。
平心而论,在我起步的时候这样的人没有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