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科学课程与教育形态Word下载.docx
《芬兰科学课程与教育形态Word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芬兰科学课程与教育形态Word下载.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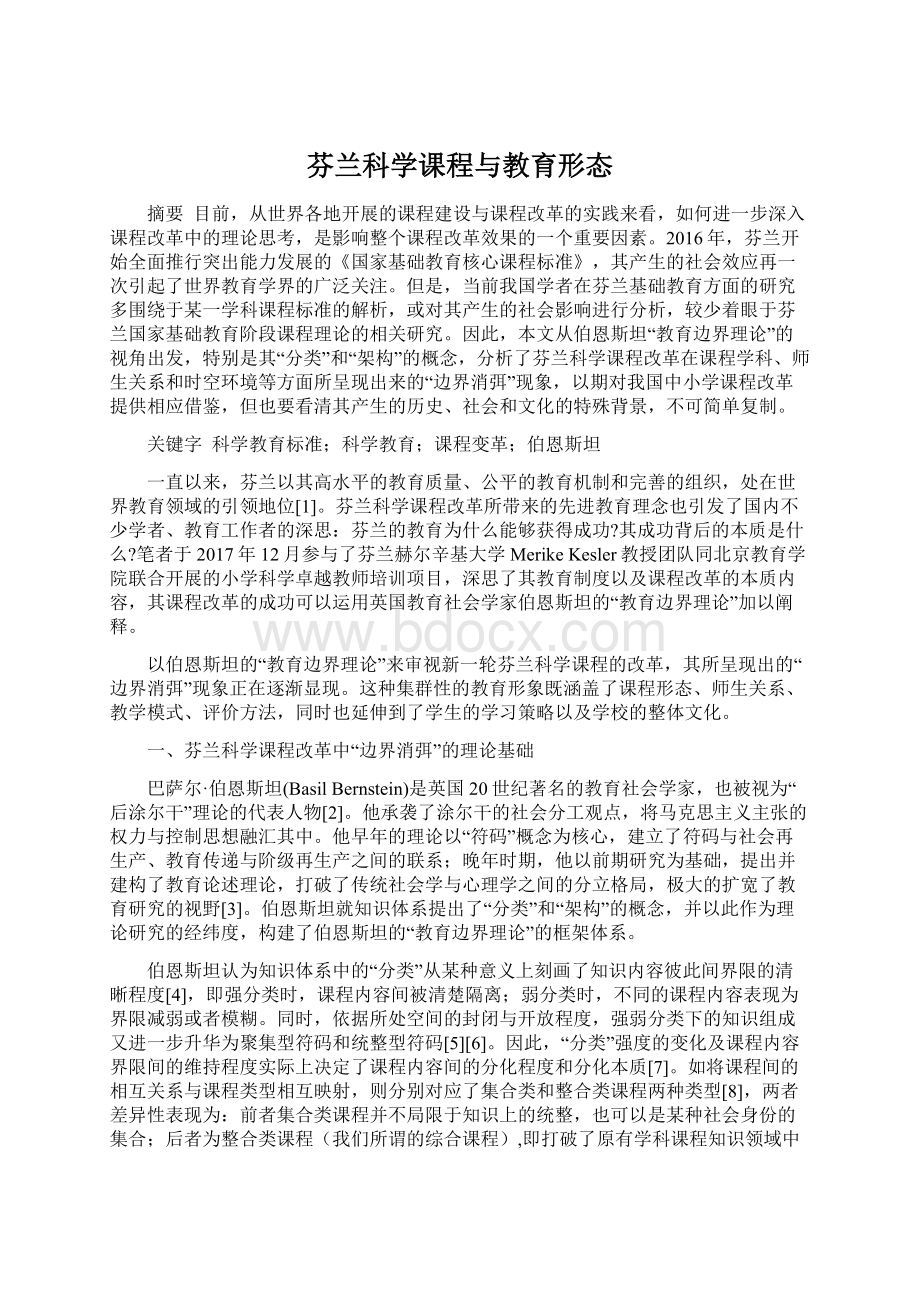
伯恩斯坦
一直以来,芬兰以其高水平的教育质量、公平的教育机制和完善的组织,处在世界教育领域的引领地位[1]。
芬兰科学课程改革所带来的先进教育理念也引发了国内不少学者、教育工作者的深思:
芬兰的教育为什么能够获得成功?
其成功背后的本质是什么?
笔者于2017年12月参与了芬兰赫尔辛基大学MerikeKesler教授团队同北京教育学院联合开展的小学科学卓越教师培训项目,深思了其教育制度以及课程改革的本质内容,其课程改革的成功可以运用英国教育社会学家伯恩斯坦的“教育边界理论”加以阐释。
以伯恩斯坦的“教育边界理论”来审视新一轮芬兰科学课程的改革,其所呈现出的“边界消弭”现象正在逐渐显现。
这种集群性的教育形象既涵盖了课程形态、师生关系、教学模式、评价方法,同时也延伸到了学生的学习策略以及学校的整体文化。
一、芬兰科学课程改革中“边界消弭”的理论基础
巴萨尔·
伯恩斯坦(BasilBernstein)是英国20世纪著名的教育社会学家,也被视为“后涂尔干”理论的代表人物[2]。
他承袭了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观点,将马克思主义主张的权力与控制思想融汇其中。
他早年的理论以“符码”概念为核心,建立了符码与社会再生产、教育传递与阶级再生产之间的联系;
晚年时期,他以前期研究为基础,提出并建构了教育论述理论,打破了传统社会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分立格局,极大的扩宽了教育研究的视野[3]。
伯恩斯坦就知识体系提出了“分类”和“架构”的概念,并以此作为理论研究的经纬度,构建了伯恩斯坦的“教育边界理论”的框架体系。
伯恩斯坦认为知识体系中的“分类”从某种意义上刻画了知识内容彼此间界限的清晰程度[4],即强分类时,课程内容间被清楚隔离;
弱分类时,不同的课程内容表现为界限减弱或者模糊。
同时,依据所处空间的封闭与开放程度,强弱分类下的知识组成又进一步升华为聚集型符码和统整型符码[5][6]。
因此,“分类”强度的变化及课程内容界限间的维持程度实际上决定了课程内容间的分化程度和分化本质[7]。
如将课程间的相互关系与课程类型相互映射,则分别对应了集合类和整合类课程两种类型[8],两者差异性表现为:
前者集合类课程并不局限于知识上的统整,也可以是某种社会身份的集合;
后者为整合类课程(我们所谓的综合课程),即打破了原有学科课程知识领域中的内容边界,组合了两个及以上的学科领域知识,构成一门综合学科[9]。
因此,“分类”这一概念实际上界定了学校教育过程中,不同类型知识范畴的学科边界[10]。
“架构”这一概念从垂直维度的层面界定了教育过程中不同参与群体在角色和地位上的博弈。
本质上,这种博弈可以理解为教师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在课堂主导权上的“重新分配”与“规则调控”[11]。
其中,“重新分配”可以理解为教师和学生在整个教学活动中的关系重组;
“规则调控”则强调了教育知识的传递方式,以及教师如何将已有知识进行转化,形成何种形式的链式结构。
两者外显为教师与学生在课堂主导权上的比例分配。
我们不难发现:
在“强构架”体系下,教师与学生的选择范围大大缩小;
反之,弱架构体系下,教师和学生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和自由发展的空间。
因此,“架构”这一概念实际上界定了学校教育过程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以及传递方式的边界。
伯恩斯坦的“教育边界理论”界定了知识领域的边界、师生关系的边界[12],并进一步衍生出虚拟与现实之间的边界。
伯恩斯坦认为,在所有的教学制度里,新旧学校时空上的差异对比已经失去了传统意义上的固定参照,其特殊的功能属性和空间的多元目的性决定了空间边界的模糊特征;
更多的空间和学校建筑开始发挥其弹性作用,并涵盖了更多潜在性的设计理念。
此外,伯恩斯坦的“教育边界理论”将时间界定为多个被正式分割的时间片段,每一个时间段被称之为一个“单位”。
从时间范畴的划分来看,课程是由时间单位和内容间特殊关系的原则所决定的[13]。
因此,其“空间”和“时间”的界定形式取决于教育符码的类别,强隔离下的“聚集型符码”通常呈现为传统意义上的有限教学时间、空间以及明确的功能区域;
弱隔离下“统整型符码”则跨越了学校、家庭和社会的时空边界,明显的边界隔离已经消失。
基于上述概念的建构,伯恩斯坦认为正规的教育知识应该包含课程、教学、评估这三个信息系统[14]:
即课程界定了什么是可迁移、具有范式效应的知识;
教学界定了有效知识的传递方式;
评估则界定了知识最终内化为能力的程度。
其三者之间并不是平行推进的关系,而是形成了具有一定层级式的递进关系,从知识的产生,到再脉络化,最终转化为知识再生产的过程[15]。
其知识的“分类”“架构”赋予了不同界线维持间的本质与强度的差异。
因此,课程、教学、评估这三者分别对应了学科、师生关系和时空边界本质的划分,三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统一,不可分割,其背后是社会关系和社会权利结构的重要显现。
二、芬兰科学课程改革中的“边界消弭”
从伯恩斯坦理论对于课程符码类型的划分来看,新一轮芬兰科学课程改革中三大边界的界定,基本上呈现了“弱分类、弱架构”的特征属性,同时也凸显了芬兰希望通过课程改革来实现培养未来学习者的长期目标。
由此可见,这种打破了时间、空间、虚拟与现实以及不同阶层间的“边界消弭”效应在芬兰的课程学科、师生关系以及时空环境等关键环节中均得以展现。
(一)课程学科边界的消弭:
跨学科教学理论模型(MLS)下的主题课程
芬兰学校对于学科边界的界定与我们传统学校教育最为显著的不同在于伯恩斯坦对于课程呈现方式的差异性分析。
一方面,芬兰的科学课程兼具知识结构“弱分类”的属性特征和科学学科的本质特征;
另一方面,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知识结构的“弱分类”还体现在芬兰科学课程的设置是遵循综合和跨学科的教学理论模型(MultidisciplinaryLearningmodules,简称MLS)(如图1所示)[16]来实现的。
从伯恩斯坦“教育边界理论”的角度来看,综合和跨学科的教学理论模型所体现的“弱分类”知识结构具有以下属性:
一方面,知识内容间的“界限模糊”使得不同学生群体间的文化差异得以保护,多种文化背景交融下的个体自我认同得以实现,新的融合模式最终建立。
另一方面,该结构打破了某一学科对本学科专门知识的独占,借鉴多学科的观点、方法进行重组和整合,为解决复杂性问题提供了创新性的可能。
在此基础上,芬兰综合和跨学科教学理论模型不仅考虑了学科融合的前期基础,同时又指向了知识内容“边界模糊”的目标所在。
改革后,其课程结构由原有的5~6年级的部分学科整合变为多学科间的统整,彻底地打破了原有学科间的界限,统整为《环境研究》一门综合学科,将学校健康教育作为环境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融汇其中;
初中阶段的科学课程设置虽然在形式上呈现出了分科的形态,但在实际教学的过程中往往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进行:
一种是教师对于学科内部不同知识模块的重新整合,另一种是基于同一主题下不同学科教师间的相互协作。
以小学科学3~6年级为例:
课程标准提供了大量核心概念下的主题内容,例如:
自然界中的人,周围环境与日常生活中的社会群体等[18]。
如下表1所示,课程作为芬兰学生横向能力发展的重要载体,其背后承载着课程需要培养的相应目标,同时课程标准提供了与学生年龄层次相匹配的应用能力和科学探究能力的水平划分。
在此基础上,不同学科的教师或同一个学科的教师群体可以根据同一个主题进行课程的二次组合与统整。
这种打破学科知识内容边界的课程改革使得科学课程的组织模式从学科走向了学习领域[19][20],实现了通过学科群及学科素养来进行学科课程的组织和实施[21]。
表1
芬兰小学科学课程内容和横向能力要求对比
(二)师生边界的消弭:
平等与自治的教学关系
伯恩斯坦“教育边界理论”的精髓在于他对于课程的分析与理解并不局限于知识内容维度上的理解,而是从课程“架构”体系中不同符码或同一种符码部间的互动关系来界定知识传递的模式,即“架构”决定了知识内容的传递方式和途径,以及符码间的强弱转换[23]。
芬兰自由的教育环境和宽松的研究气氛使得师生关系呈现出了“弱架构”下的教师角色和地位的改变,并逐渐形成了双向曲线的知识传递方式。
如下图2所示,在传递知识的过程中,教师同时承担着知识的输出者与接受者的双重角色,平等的师生关系得以确立;
在反馈知识的过程中,教师为解决或协助学生解决新的问题,需要进行多次的课程改进和设计,因此教师也是课程的具体开发者和设计者。
由此可见,教师与学生在知识内容的传递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输出—反馈—再输出—再反馈”的传递链条,即传递过程应该包括:
知识的直线输出,学生的实时反馈,新内容的产生,新内容的反馈这四个部分。
相比于传统的单向快速模式,教师的教学过程不再是单一的输出,而是在不断的修订中得以缓慢前行与折返。
表面上,这种曲线模式下的知识传递方式并没有达到快速传递的效果,但是从长期的教学成效来看,各部分之间“以始为终,循环往复”,使得学生在整个过程中的收益得以进一步的放大和辐射。
因此,在这个知识传递的过程中,“架构”的强弱程度不仅仅决定了师生间的互动关系与教育形态,同时也直接影响着信息传输的速度与学生的学习成效。
图2
伯恩斯坦视角下的师生知识传递链条示意图
伯恩斯坦的“教育边界理论”认为“架构”不仅仅涉及了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之间关系的界定,同时也涵盖了师生间知识传递与接受的选择、组织以及课堂主导权的比例分配规则[24](如图3所示)。
在课程的实践过程中,芬兰的科学教师与学生会产生不同符码间的动态强度转换,即教学过程往往会根据不同教学环节间的差异进行课堂主导权比例的重新分配。
以科学探究为例,一个完整的过程应该包括:
问题的提出,解决方法的选择,结果的分析和结论四个部分。
从问题的提出到问题的解决,课堂主导权的分配应该体现出从封闭的知识系统到开放知识系统[25]、从“强架构”到“弱架构”的变化趋势,即教师在课堂上的主导权应根据课程进程的推进而逐渐让位于学生在课堂上的主导权。
首先,教师在问题的引导环节应该具有较高的主导权,表现为教师通过问题的总体设置来把握课程的培养目标和课程内容的具体设定;
其次,学生在问题的解决及结论部分应该享有高度的主导权,以此促进学生科学思维的构建。
因此,不同课程环节中师生关系间的“边界消弭”有利于构建平等的师生关系和自治创新文化的形成。
图3芬兰科学课程中强弱架构间的转换
注:
浅灰色和深灰色分别代表了学生和教师在不同环节中的课堂主导权的比例差异
(三)时空边界的消弭:
注重视域融合和自我筹划的评估体系
用伯恩斯坦的“教育边界理论”来看国内学校与芬兰学校在学习时空上的差别,也能从中感受到明显的差异性。
芬兰的科学教育遵循学生知识、态度和行为的阶段性发展特征,从视域融合和自我筹划的角度出发[26],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教育现场,将评估体系延伸到传统的纸笔测试之外,实践社会第三方参与融入教育评价的新模式[27],最终构建了芬兰科学教育中的双维度、四象限的学习环境[28](如下图4所示)。
图4
芬兰科学学习环境范围示意图[29]
(1)正式与非正式学习环境的跨界组合
芬兰的科学教育将正式的科学课程同非正式的科学课程进行跨界组合,通过非正式的科学课程形式对正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