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特劳斯论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解读Word文档格式.docx
《施特劳斯论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解读Word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施特劳斯论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解读Word文档格式.docx(3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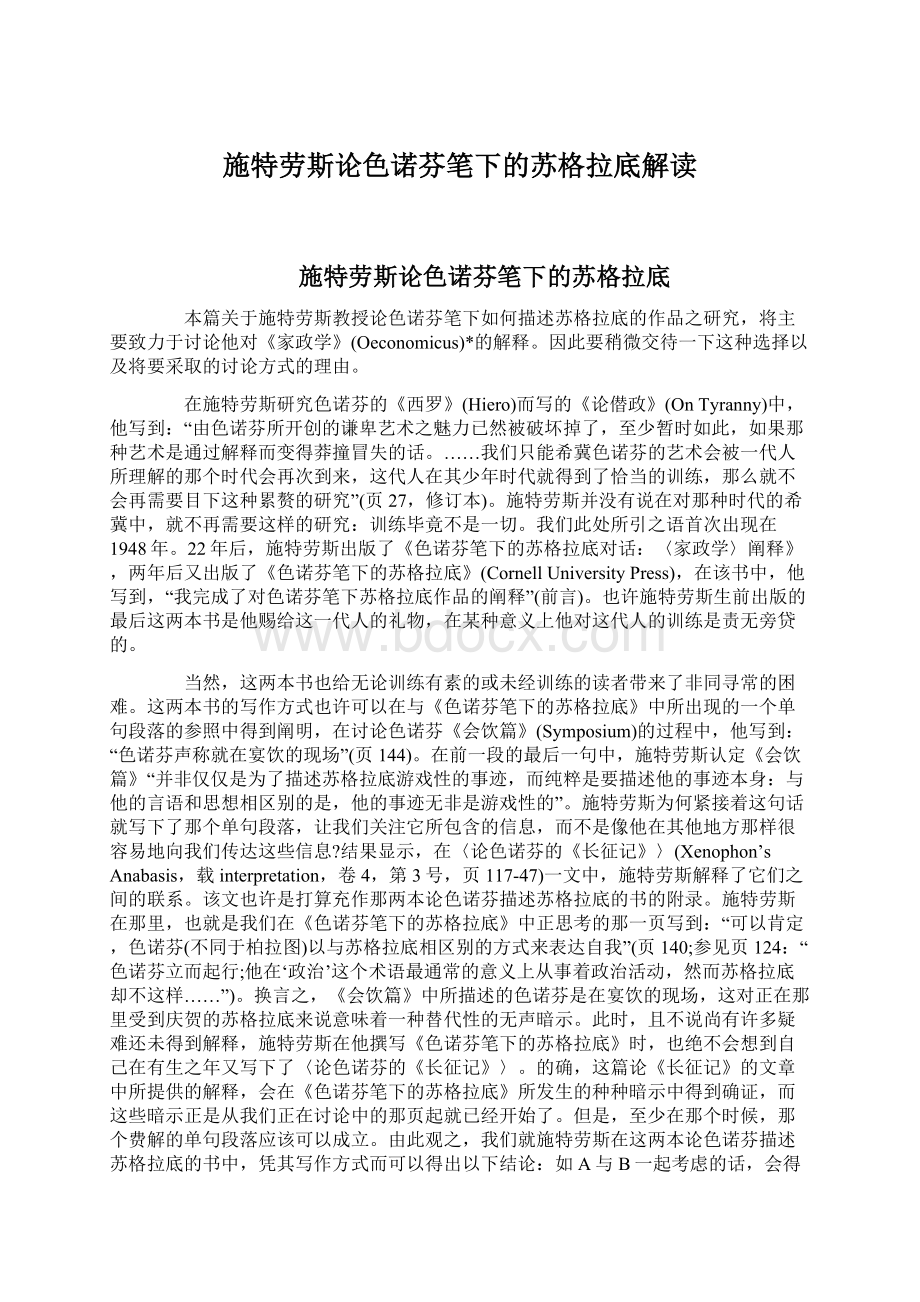
我们此处所引之语首次出现在1948年。
22年后,施特劳斯出版了《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对话:
〈家政学〉阐释》,两年后又出版了《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CornellUniversityPress),在该书中,他写到,“我完成了对色诺芬笔下苏格拉底作品的阐释”(前言)。
也许施特劳斯生前出版的最后这两本书是他赐给这一代人的礼物,在某种意义上他对这代人的训练是责无旁贷的。
当然,这两本书也给无论训练有素的或未经训练的读者带来了非同寻常的困难。
这两本书的写作方式也许可以在与《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中所出现的一个单句段落的参照中得到阐明,在讨论色诺芬《会饮篇》(Symposium)的过程中,他写到:
“色诺芬声称就在宴饮的现场”(页144)。
在前一段的最后一句中,施特劳斯认定《会饮篇》“并非仅仅是为了描述苏格拉底游戏性的事迹,而纯粹是要描述他的事迹本身:
与他的言语和思想相区别的是,他的事迹无非是游戏性的”。
施特劳斯为何紧接着这句话就写下了那个单句段落,让我们关注它所包含的信息,而不是像他在其他地方那样很容易地向我们传达这些信息?
结果显示,在〈论色诺芬的《长征记》〉(Xenophon’sAnabasis,载interpretation,卷4,第3号,页117-47)一文中,施特劳斯解释了它们之间的联系。
该文也许是打算充作那两本论色诺芬描述苏格拉底的书的附录。
施特劳斯在那里,也就是我们在《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中正思考的那一页写到:
“可以肯定,色诺芬(不同于柏拉图)以与苏格拉底相区别的方式来表达自我”(页140;
参见页124:
“色诺芬立而起行;
他在‘政治’这个术语最通常的意义上从事着政治活动,然而苏格拉底却不这样……”)。
换言之,《会饮篇》中所描述的色诺芬是在宴饮的现场,这对正在那里受到庆贺的苏格拉底来说意味着一种替代性的无声暗示。
此时,且不说尚有许多疑难还未得到解释,施特劳斯在他撰写《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时,也绝不会想到自己在有生之年又写下了〈论色诺芬的《长征记》〉。
的确,这篇论《长征记》的文章中所提供的解释,会在《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所发生的种种暗示中得到确证,而这些暗示正是从我们正在讨论中的那页起就已经开始了。
但是,至少在那个时候,那个费解的单句段落应该可以成立。
由此观之,我们就施特劳斯在这两本论色诺芬描述苏格拉底的书中,凭其写作方式而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如A与B一起考虑的话,会得出结论C,但施特劳斯自己总不把对结论C的证明看作自己必要的或适当的工作,他甚至不承认A与B相关;
他把这些情况摆在那里,只提到A和B具有同样密切的关系,而全赖读者去做余下的推理。
这当然给施特劳斯的读者或阐释者带来极大负担,而且,除非搞清楚了他的文章所因循的脉络,任何阐释都不可能令人信服或有太大用处。
比如,在目前这种审视方法限度内,我们不可能弄清楚这两本书的脉络。
并且,就算有必要挑一本书来集中讨论,也很容易证明第一部书,即讨论《家政学》的那本书,是更为根本的著作。
这不仅在第二本书的前言里得到了承认,而且第二本书(以及那篇论《长征记》的文章)预先就暗含了在城邦面前为苏格拉底辩护的主题,以及苏格拉底身上那些使得辩护如此艰难的种种特性和局限性,并且从《家政学》自身的观点来看,该主题只是从属性的(《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对话》,页176-77)。
[1]
我们也许造成了一种印象,即施特劳斯的阐释基本上是一种技术性玩意。
阐释的技术性无非是从属于该项任务,即发现那个(或那些)打动施特劳斯的问题,通过这些问题他找寻到那条能够回归久已忘怀的世界之路,并且还表明这个世界依然是一个适当的住所。
当然,在施特劳斯此前论古代、中世纪和现代政治哲学的等身的鸿篇巨制中,那个问题很可能就已揭示了出来。
但是,即便他的主要关切点在那本书里已经充分地揭示出来,我们领悟到了吗?
此外,施特劳斯最后这两本论色诺芬的书是他对苏格拉底最终论述的组成部分,[2]并在该题目范围内堪称其毕生的顶峰之作。
这两本书难道不是形成了比他早期著作更全面和深刻的指导性问题或关切点?
这也许就是施特劳斯在书中愈加明显地保持习惯性缄默的又一原因,正是这种缄默使这两本论色诺芬的著作如此难以理解。
关于导论
在《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对话》的导论中,施特劳斯说“伟大的政治哲学传统肇始于苏格拉底”(页83);
他解释了为何色诺芬应被看作“我们关于苏格拉底思想确切理解”的卓越源泉(页83-84);
还讨论了色诺芬论述苏格拉底作品的不同目的和主题(页84-86)。
施特劳斯并未追问我们为何要与政治哲学相关,即便相关,他也没有问我们为何要与其源头相关。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施特劳斯也许在一次有关苏格拉底所谓全盘弃绝“整个自然界……以便自己能完全献身于伦理事物的研究”的评论中指出了答案,该答案正是他希望通过暗示而让读者自行提供、并为之所左右的。
该评论指出:
“苏格拉底的理由似乎就在于,如果人们并不必然需要所有事物本性的知识,就必然会关心应该如何独处和群居”(页83)。
至于施特劳斯为什么在苏格拉底的研究中采用了人们所说的以往那种方向,施特劳斯本人并没有保证这一说法的真理性,也丝毫没有表示说自己是否满意于自己的研究所引领的方向,以及这种方向是否准确。
换句话说,我们无法认定施特劳斯是否对这里所提出的苏格拉底在伦理-政治问题方面的真正性质和目的感到满意。
如果他不满意,那么,这就如他最初所预料的那样(即便他未曾注意到——参页94),直接表示在他和读者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就上述原因而言,就算我们与政治哲学相关,我们为何还要与它的源头和苏格拉底相关?
施特劳斯早期著作的读者,尤其《自然权利与历史》的读者,会发现上述问题的原因,与(或应该与)我们今天仍然强劲有力的观点(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所引发的政治哲学危机大有干系,这些观点怀疑是否存在自然权利,或是否存在一种能回答“我们应该如何独处和群居”问题的理性和客观的答案。
然而,施特劳斯现在丝毫没有提及那种危机。
他在这里主要关心,不管对与否,读者们不会如此被这些观点所困扰,以致害怕在追寻人们应如何生活问题的答案时会徒然无功。
因而这样的读者会唯苏格拉底是视,会简单地把他当作一个已经找到答案的人,而且该答案今天仍然有效,因为它现在就是如此这般对人类起着作用的。
因此,这样的读者很可能要困扰于施特劳斯在论苏格拉底著作的不同目的和主题时表面低调的讨论所发出的暗示(由此,施特劳斯的直接努力假如是半心半意的话,就是要贬低那种暗示的意义)。
按照施特劳斯的观点,《回忆录》*“整个儿地……致力于证明苏格拉底的正义”(页85)。
但他又接着说,这也意味着“其他三本有关苏格拉底的著作不是维护苏格拉底的正义”,而是颂扬“他甚至超越了正义”(页86)。
那种懂得人们“应该如何独处和群居”的关切,以及鼓动读者感兴趣于苏格拉底的关切,最低限度而言,很难与对正义的关切相区别:
如果不是正义地,我们又该如何独处和群居?
不管苏格拉底多正义,他“超越正义”又意味着什么?
论标题与开头
读者诸君已然看到,在施特劳斯的观点中,《家政学》是“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精妙绝伦的logos或话语”(页86)。
施特劳斯现在断定,“《家政学》传授家政(oikonomos)管理的艺术”(页87)。
色诺芬为什么要把苏格拉底精妙绝伦的话语搞成“苏格拉底对家政管理艺术的教导”?
施特劳斯对于他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只是说给出了一个“暂时性的答案”(页89)。
照这个答案看来,其原因必得追溯至苏格拉底所赋予家政管理艺术的崇高地位(它与“政治或王道的艺术”几无二致,且“并不次于将兵之道”,参页87)。
但也许更出自色诺芬愿望的是,苏格拉底宁可传授这种和平的艺术,也不愿教授好战的将兵之道,尽管他本来也可以教授它。
这就与色诺芬贬低苏格拉底的军功相一致,也与他无言地否定苏格拉底具有硬汉气质之说相一致(页88-89)。
在色诺芬的描述中,如果苏格拉底超越了正义,那既非出于他的正义,更不是由于他的男人气概。
即便这个“暂时性的答案”可以解释苏格拉底为何宁可传授家政管理也不传授将兵之道,那也根本不能解释苏格拉底为何要传授这种或任何一种艺术。
人们会轻易发现该问题的答案在施特劳斯论述该书的开头时就已给出来了。
在对《回忆录》相关内容稍微一瞥的基础上,施特劳斯敦请我们“要牢记‘家政管理’与‘友谊’的主题之间是否存在着联系这一问题”(页91)。
在其他事情上,原来在《家政学》中苏格拉底向之传授家政管理艺术的克里托布洛斯(Kritoboulos)**就是苏格拉底的朋友克力同(Kriton)的儿子。
这里,苏格拉底传授那种艺术,这同时也是一种出自友谊的行动(参阅页101)。
此外,这也解决了我们先前更大的难题,因为一种出自友谊的行动,就会像这样通过超越苏格拉底兴许所欠克里托布洛斯及其乃父的人情,而达到“超越正义”。
施特劳斯在此处的语境中谈到“在《回忆录》这本宣扬苏格拉底正义的书”与《家政学》(页90)这本书之间的“深刻的区别”。
如同我们在施特劳斯早期评述中所看到的,即据他看来,这种区别意味着苏格拉底“超越了正义”。
但如果苏格拉底只是因为友谊的因素而“超越了正义”,那么就如施特劳斯这里也强调了的,为什么色诺芬要如此处心积虑“掩藏”这两本书深刻的区别(并且由之而来的是,这种区别意味着什么)?
无论情况会怎样,就苏格拉底为何要传授艺术之解释来说,要弄明白他“超越正义”的方式这一根本困难依然未得解决。
这兴许牵涉到如下的事实,即施特劳斯在这一点上千方百计说明,色诺芬已意识到阿里斯多芬在《云》中对苏格拉底的处理:
那种处理也建立在苏格拉底“超越了正义”的前提上(参看关于“正义的说法”〔JustSpeech〕与“不义的说法”〔UnjustSpeech〕的争论)。
论第一章
在展开第一章的讨论前,施特劳斯提起了那个仍未回答的问题,即“为何色诺芬在描写苏格拉底对话的著作中,选择了克里托布洛斯作苏格拉底的谈话对象”。
(页92)而克里托布洛斯之为友人之子却还不足以回答这个问题。
也许在苏格拉底为何要教导或试图教导他这一相关问题上,根本就没有任何简单意义上的答案。
事实证实了这种怀疑,即如施特劳斯所强调指出的,在第一章中,正是苏格拉底本人把讨论引向了这样的结论:
“如果一个人懂得怎样利用朋友并能从他们身上得到好处,朋友就是金钱……”(页95)。
当我们不为诱惑所扰,而不妄下结论说苏格拉底在友谊的取向上自认为超越了正义时,我们似乎就对了。
但如此一来,他又如何超越正义,以及如何能将“朋友就是金钱”这样的想法理解为一种苏格拉底式的想法,理解为一种属于或符合于苏格拉底生活的思想?
当然,这并不是说,对财富的过分关注是哲学人生的特质:
是克里托布洛斯而不是苏格拉底这样认为,家政管理的目的应是增加财富(页93);
“照苏格拉底看来,聪明人自身所需很少”(页97),这是苏格拉底整个一生印证的观点。
当然,它的涵义倒是必须通过反思其题中之义来予以阐明,这种反思(即反思知识与财产之间的关系),以施特劳斯所认为的苏格拉底在合法性的意义上超越了正义为基础。
苏格拉底在理论上——如果不是在实践上的话——尤其忽视财产在法律上的定义,抑或忽视法律所确认的我的(东西)和你的(东西)之间的差别:
在此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