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判牍中的情理Word格式.docx
《明清判牍中的情理Word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明清判牍中的情理Word格式.docx(1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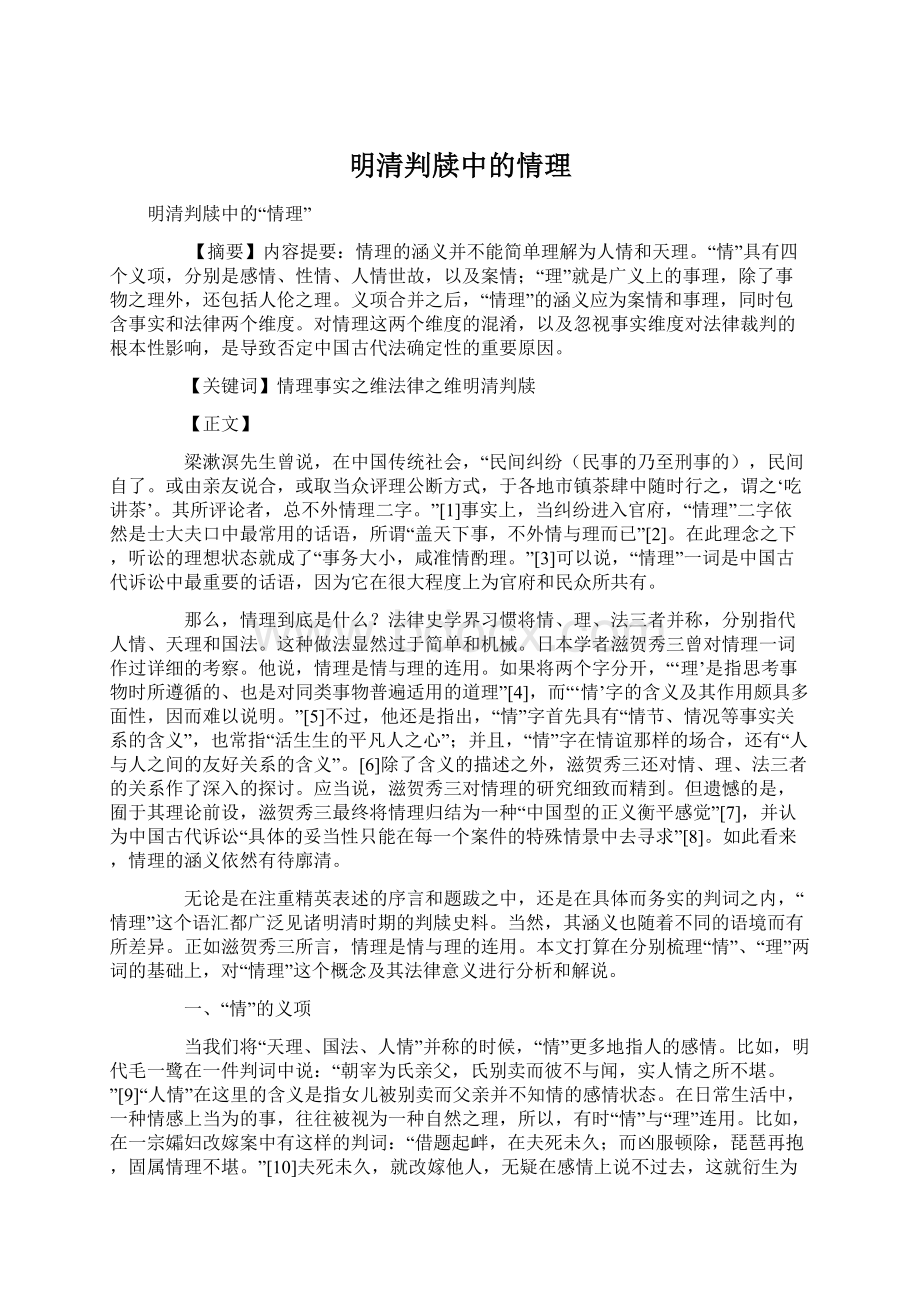
在此理念之下,听讼的理想状态就成了“事务大小,咸准情酌理。
”[3]可以说,“情理”一词是中国古代诉讼中最重要的话语,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为官府和民众所共有。
那么,情理到底是什么?
法律史学界习惯将情、理、法三者并称,分别指代人情、天理和国法。
这种做法显然过于简单和机械。
日本学者滋贺秀三曾对情理一词作过详细的考察。
他说,情理是情与理的连用。
如果将两个字分开,“‘理’是指思考事物时所遵循的、也是对同类事物普遍适用的道理”[4],而“‘情’字的含义及其作用颇具多面性,因而难以说明。
”[5]不过,他还是指出,“情”字首先具有“情节、情况等事实关系的含义”,也常指“活生生的平凡人之心”;
并且,“情”字在情谊那样的场合,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关系的含义”。
[6]除了含义的描述之外,滋贺秀三还对情、理、法三者的关系作了深入的探讨。
应当说,滋贺秀三对情理的研究细致而精到。
但遗憾的是,囿于其理论前设,滋贺秀三最终将情理归结为一种“中国型的正义衡平感觉”[7],并认为中国古代诉讼“具体的妥当性只能在每一个案件的特殊情景中去寻求”[8]。
如此看来,情理的涵义依然有待廓清。
无论是在注重精英表述的序言和题跋之中,还是在具体而务实的判词之内,“情理”这个语汇都广泛见诸明清时期的判牍史料。
当然,其涵义也随着不同的语境而有所差异。
正如滋贺秀三所言,情理是情与理的连用。
本文打算在分别梳理“情”、“理”两词的基础上,对“情理”这个概念及其法律意义进行分析和解说。
一、“情”的义项
当我们将“天理、国法、人情”并称的时候,“情”更多地指人的感情。
比如,明代毛一鹭在一件判词中说:
“朝宰为氏亲父,氏别卖而彼不与闻,实人情之所不堪。
”[9]“人情”在这里的含义是指女儿被别卖而父亲并不知情的感情状态。
在日常生活中,一种情感上当为的事,往往被视为一种自然之理,所以,有时“情”与“理”连用。
比如,在一宗孀妇改嫁案中有这样的判词:
“借题起衅,在夫死未久;
而凶服顿除,琵琶再抱,固属情理不堪。
”[10]夫死未久,就改嫁他人,无疑在感情上说不过去,这就衍生为一种处事和辨别是非的“理”。
明代的张九德在《云间谳略》的序言中谈到听讼时曾说:
“设以身处其地,务使彼情不隔于己情,又使己心可喻于彼心。
”[11]就是说,听讼过程中的“情”与“心”都不具有个体的意义,而是彼此共通的感情状态,正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这样一种由“情”产生的“理”,有时在听讼中被用来判断具体行为的合理性。
比如,在一件匿告事中,“徐光悦亲弟出外樵渔,而弟妇陈氏寄暇佣人周邦圣者。
光悦不忿而告鸣,自是闺门之义气。
光悦不能自告,而翁思禺为代告,亦是周亲之情。
”[12]明清时期为防止民众滥讼,一般禁止与讼情无关的人代告。
此案中,判官认为徐光悦因为有“闺门之义气”不方便自告,翁思禺出于“周亲之情”而为之代告,于理无碍。
另外,普遍的情感有时候也被用作裁决案件的依据。
比如,明代有一悍妇,“其人如虎,其舌若雕”,所以先逐于叔,再逐于婿,以致年老无依,于是诉至官府。
判官断令叔出谷米,在女家供养。
究其所由,是因为“生养死葬,亦乌鸟至情,所难置为道墐之弗顾者也”。
[13]由此看来,感情是“情”的一个基本义项,但并非指个体的特殊感受,而是具有普遍性的情感。
在社会生活中,这种感情上当为的事往往被视为自然之“理”。
情与理由此沟通。
再来看另一种“情”的用法。
明代的张肯堂曾在一则判牍中说,“人情利来未必交让,而利尽必至互推。
”[14]这种趋利避害的描述显然是对人性所作的一种假设。
在此理解之下,人的功利性时常被表达为“人情”。
比如,在一宗买卖纠纷中有这样的判词:
“议价之始,稍有低昂,得价之后,更生变态,亦人情之常也。
”[15]明人苏茂相所辑的《新镌官版律例临民宝镜》也有类似的用法:
在一宗入赘案中,判官说,“吴天因乏嗣而赘婿,周常因乘产而送终,亦人情也。
”[16]意思是,吴天因为没有子嗣养老而招婿,周常为了得到财产而为其送终。
此一“人情”也是对功利心态的一种表达。
基于对功利人性的普遍假定,“人情”不时被用来作为判断事实的依据。
比如,明代有这样一起案件:
曾氏之夫郑中翰亡故后,其向亲家游若林讨取亡夫所寄之银,因而发生争执。
判官说,“郑中翰积金四千,而不为家营寸产,以四千金寄若林,而不以数金留曾氏,此人情所必无者。
”[17]在判官看来,人性是自私的,决不会以数千金存寄他人之处,而不为家人存留数金,此一讦告有悖常理。
有时,对人情的功利假设也被用作法律上的判断。
在一起清代的踩踏青苗案中,有这样的判词:
“查种田之人,以青苗为性命,如有损坏,即拼命阻止,乃人情之常。
”[18]以功利的人性而论,在阻止损坏青苗的过程中,往往不顾性命,稍有损伤亦可以原谅,因而无需追究。
所以,“情”的另外一个重要义项,是基于功利假定的性情或者人性,它往往被判官视为当然之“理”。
“情”的第三个义项是人情世故,即日常所见的事情或事理。
先来看这样一起奸局案:
宋玉借蔡承祖本银些微,负而不偿,捏控蔡承祖与其妻通奸,但并无确证。
判官说:
“宋玉妻吴氏与蔡承祖对门而居,蔡之寡嫂及氏,茶话往来,妇人常情耳。
”[19]对门而居的妇人茶话往来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仅仅据此而怀疑通奸显然理由并不充足。
再来看一件清代的判词:
“周道成被盗之时,当遗有周道远帕子、鞋子等件,遂至误会周道远知情。
细查周维贤诉词,据称帕子、鞋子,系伊子周道远晒在窗下,夜间未收。
揣度其情,想系贼先将帕子等物窃去,欲偷周维贤屋,尚未得手,因转向周道成房内,被人惊醒,致将此帕子失去,是乃人情之常。
”[20]周道远的鞋袜晒在窗外未收,被盗贼趁机盗走而遗失他处,并不稀奇,所以不能仅凭遗失之物就据以为盗。
以上两例中的“常情”皆是指具体的事情,但是正因为其平常发生,所以就成了普遍之理。
还有的“情”直接就是指事理。
比如,有一宗明代的人命案:
群殴中,陈三将在光踢死,被在光之妻黄氏所亲见。
公堂之上,陈三父陈良“始称三到之时,在光已死,继称打抢之时,黄氏有虔布一疋,因三抢夺付收敛,怪恨执此报仇。
夫抢布之仇与杀夫之仇孰重?
不仇杀夫而仇抢布,决非人情。
”[21]无论从感情还是从价值上看,夫仇都远胜过抢布之仇。
所以,在光之妻仅为了抢布之仇而诬陷陈三,从而放过杀夫的真正仇人,在常理上说不过去。
作为日常所见事情或事理的“情”,其实蕴含着普遍的事理和逻辑,在事实判断的过程中,这种平常之理妥贴而必要。
实情和情节是“情”的最后一个义项,也是最重要和最常用的一个义项,却总是被忽视。
事实上,它频繁出现在各类法律文献之中。
比如,在官方正式用语中,“情”时常指案情:
源于明代朝审的清代秋审制[22],最后将案件分为情实、缓决、可矜和留养承嗣四种处理,“情实”的“情”就是指的案件事实。
另外,这样的用法在明清判牍的序和跋中也很常见。
比如,在《棘听草》的“叙”中,李之芳谈到听讼时就说,“要使讷者尽言,诪者献诈,而悬河辩者缩其舌,反覆推勘,务求得情而止。
”[23]“情”在此处就是案情和实情的意思。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张五纬在《未能信集》中说:
“民间讼事不一,讼情不齐。
其事不外乎户婚、田土、命盗争斗,其情不外乎负屈含冤,图谋诈骗。
听讼者即其事察其情,度之以理,而后决之以法。
”[24]此处的“情”明显指案件事实,虽然情、理、法并用,但是与“天理、国法、人情”中“情”所指称的并不一样。
在实际的判词中,也经常在案件事实的层面上使用“情”字。
比如《云间谳略》中,有这样的判词:
“朱宗政侵盗仓粮一事,浪费有据,借贷有主,情最真,罪最确。
”[25]《莆阳谳牍》中也有相同的用法:
“陈朝宁与翁在缙以灌水相争。
朝宁之女适死,与本事无干。
盖在缙何憾于幼女而击之致死耶?
况乡众公呈亦无一语及死女,其情已显然矣。
”[26]这些判词中的“情”都指的是案情。
类似的判词还有:
“吴正险如墉隼,奸似城狐。
预报睚眦之仇,则匿名而告罪……非张保证明,定成滥狱。
不设计赚出,谁得真情。
”[27]作为“案情”的“情”字,除了与具体情节连用之外,还时常被用作判词的起始语、过渡语和修饰语。
以清代李钧的《判语录存》为例,判词一般以“审得……等情”开头,在叙述案情的过程中偶尔会用到“情势”、“情由”[28]这样的词汇来表示事实,有时也会以“别有阴情”[29]、“真情吐露”[30]、“昧情饰控”[31]、“装点情节”[32]以及“供情如绘”[33]这些词句作为案情叙述的过渡,还会出现“情同略卖”[34]以及“虽无惨杀之据,却有虐遇之情”[35]之类的修饰性用法。
总之,在明清时期的判牍中,以“情”来指代案件事实相当普遍。
以笔者浏览数千件判词的经验来看,判词中使用“情”字的场合,“实情和情节”这一义项超过半数。
综而言之,“情”共有四个义项,分别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感情、(功利假定的)性情、(作为日常所见的事情或者事理的)人情世故,以及(包括实情和情节的)案情。
除了“案情”这一义项之外,其余的“情”都无一例外地指向事理——自然感情上当为的事是一种当然之理,趋利避害的人性是一种普遍之理,日常所见的事情所蕴含的是一种平常之理。
二、“理”的义项
相较“情”字含义的复杂多变而言,“理”的义项要简单明晰许多。
首先来看“天理”这个词。
在一宗明代的人命案中[36],水手葛某与稍人艾某,在船行僻处时,操刀杀死客商主仆二人,抛尸灭迹于江湖,判词说“不思天理难欺,自度奸谋叵测”。
此案中凶徒自以为僻处杀人,无人知晓,但是终被查究,这里“天理”应该是指“杀人偿命”之理。
如果凶徒未获,那无疑是没有“天理”;
最后凶徒伏法,也就“天理”得彰了。
再来看一件钱债案的判词:
“山有定主,谋者妄焉。
债有定额,负者非矣。
王某只可据理取债,不可执典契而妄葬李某之山;
李某合认还父债,不可昧天理而负王之银。
”[37]此处“欠债还钱”也成了“天理”。
由以上两例可知,“天理”之“理”无非是一种事理而已,“天”字之加,只是增添了此种事理的神圣性和恒久性,仅为一种修辞,并非特别的义项。
除去“天”字,作为事理的“理”在判词中被广泛使用。
先来看一件明代的判词:
“杨云顶王义所赁房,将营酒腐之业。
乃王义在房之日,以车碇为生,有半间稍空,借与张懋新收布。
盖松俗,布市唯在平旦,故彼此贸易两不相妨耳。
及转赁与杨云,云所业酒腐,与义不同,自不得以其余及懋新,此亦情理之常。
”[38]这里的情理之“理”意为:
基于营业时间的不同,车碇可与收布共赁一屋,而酒腐之业则不能与收布同用。
这是显而易见的日常事理,从具体的行为派生出来,反过来也成为诉讼中具体行为合理与否的标准。
再来看一个例子:
戴士琦有房五间,典与林正学之父林人文,回赎之时戴士琦称原典价为五十两,而林正学称典价为一百两。
判官认为,“无一间房而二十两典价之理,士琦五十两之说为是。
”[39]一间房的典价属于具体问题,但在特定时间特定地域,其并非毫无标准可循,应该有一个大致的价格,与此价格相隔玄远的——比如此案中多出一倍——无疑是不合“情理”了。
从以上两件判词我们可以看出,布市的营业时间与“松俗”有关,而一间房的典价更是特定时空背景的产物,这正是张五纬所言的“民间之各有其情、各有其理”[40],这类情理虽然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