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从儒家的当前使命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docx
《牟宗三从儒家的当前使命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牟宗三从儒家的当前使命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docx(2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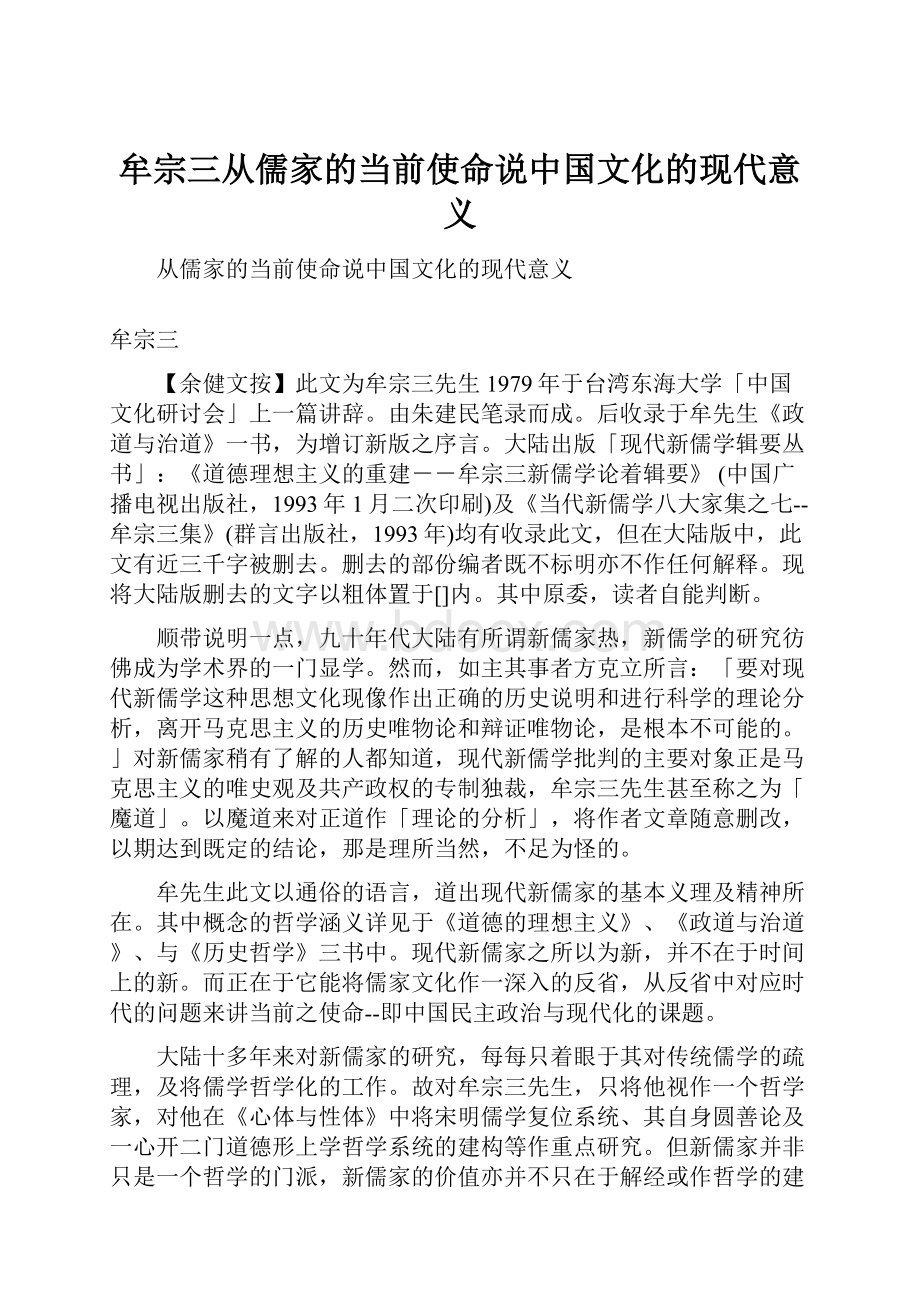
牟宗三从儒家的当前使命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
从儒家的当前使命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
牟宗三
【余健文按】此文为牟宗三先生1979年于台湾东海大学「中国文化研讨会」上一篇讲辞。
由朱建民笔录而成。
后收录于牟先生《政道与治道》一书,为增订新版之序言。
大陆出版「现代新儒学辑要丛书」:
《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牟宗三新儒学论着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1月二次印刷)及《当代新儒学八大家集之七--牟宗三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均有收录此文,但在大陆版中,此文有近三千字被删去。
删去的部份编者既不标明亦不作任何解释。
现将大陆版删去的文字以粗体置于[]内。
其中原委,读者自能判断。
顺带说明一点,九十年代大陆有所谓新儒家热,新儒学的研究彷佛成为学术界的一门显学。
然而,如主其事者方克立所言:
「要对现代新儒学这种思想文化现像作出正确的历史说明和进行科学的理论分析,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是根本不可能的。
」对新儒家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现代新儒学批判的主要对象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唯史观及共产政权的专制独裁,牟宗三先生甚至称之为「魔道」。
以魔道来对正道作「理论的分析」,将作者文章随意删改,以期达到既定的结论,那是理所当然,不足为怪的。
牟先生此文以通俗的语言,道出现代新儒家的基本义理及精神所在。
其中概念的哲学涵义详见于《道德的理想主义》、《政道与治道》、与《历史哲学》三书中。
现代新儒家之所以为新,并不在于时间上的新。
而正在于它能将儒家文化作一深入的反省,从反省中对应时代的问题来讲当前之使命--即中国民主政治与现代化的课题。
大陆十多年来对新儒家的研究,每每只着眼于其对传统儒学的疏理,及将儒学哲学化的工作。
故对牟宗三先生,只将他视作一个哲学家,对他在《心体与性体》中将宋明儒学复位系统、其自身圆善论及一心开二门道德形上学哲学系统的建构等作重点研究。
但新儒家并非只是一个哲学的门派,新儒家的价值亦并不只在于解经或作哲学的建构。
如此研究新儒家,正如民初学者的「整理国故」,与西方历史学者的「埃及学」研究一般,将它作为一种已死的学问来作「科学的分析」,绝不能理解新儒家的义理与真精神。
一些浅簿的自由主义者见到一个「儒」字就不问因由的跟着乱起哄,甚而将它打成「新权威主义」。
然而,新儒家所标示的正是人的价值与尊严,其批判的对象正是一切压制个人自由的专制政权,这与新权威主义有何相干?
故大陆新儒学的研究,绝不能把握到新儒家的真精神。
只读几篇大陆学者的新儒家论文,而对新儒家大加批判,则只能是武断之论。
我以为要能真切体认到新儒家的精神,必须以敬畏之心认识牟宗三、唐君毅等大师的圣贤人格。
因为他们以生命向人们显示了儒家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生命方向的光明面。
各位先生,我们原先订的题目是「儒家学术的发展及其使命」,这是个大题目,而限于时间,只能长话短讲,综括地集中于几点上,来谈这个问题。
1.儒家的常道性格
首先,我们要表明儒家这个学问具有「常道」的性格。
儒家这个学问,从古至今,发展了几千年,它代表一个「常道」——恒常不变的道理。
中国人常说「常道」,它有两层意义:
一是恒常不变,这是纵贯地讲它的不变性;一是普遍于每一个人都能适应的,这是横地讲、广扩地讲它的普遍性,即说明这个道理是普遍于全人类的。
「常道」没有什么特别的颜色,就如同我们平常所说的「家常便饭」;它不是一个特殊的理论、学说,儒家的学问不可视为一套学说、一套理论,也不是时下一般人所说的某某主义、某某「ism」,这些都是西方人喜欢用的方式。
凡是理论、学说,都是相对地就某一特点而说话;局限于某一特点,就不能成为恒常不变的、普遍的道理。
儒家的学问更不可视为教条(Dogma),西方的宗教有这种教条主义的倾向,可是儒家的「家常便饭」绝不可视为独断的教条。
又有一些人讲孔子,常为了要显示孔子的伟大,而称孔子是个伟大的教育家、政治家、外交加、哲学家、科学家、………,把所有的「家」都堆在孔夫子身上。
依这种方式来了解孔子、了解圣人,是拿斗富的心态来了解圣人。
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在推尊孔子,实际上是在糟蹋孔子。
事实上,没有一个人能成为那么多专家。
凡是拿这种心理来了解孔子,都是不善于体会圣人的生命,不能体会圣人之所以为圣人的道理安在。
常道不可舍弃
我们今天把儒家的「发展」与「使命」连在一起讲,而讲的重点则在使命上。
使命是就着眼前说,在这个时代中,儒家担负什么样的使命、责任。
然而儒家并非今天才有,因此在谈它的使命之前,我们亦当该照察它过去的发展。
在过去两千多年历史中的发展,儒家这个学问既然是个常道,则在每一个时代中,当该有其表现;发展到今天,儒家这个学问又有负有什么责任呢?
这是个严重问题,在今天问这个问题,要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来得严重。
何以会如此呢?
因为我们今天谈儒家的使命,似乎还可再反问一下:
儒家本身今天是否还能存在呢?
能存在,才能谈使命,若自身都不能存在,还谈什么使命呢?
若是儒家本身都若有若无,几乎不能自保,所谓「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还谈什么当前使命、责任呢?
在以往的时代中,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在今天这个时代,就有这个问题。
以往一般人,不论是士、农、工、商,提起圣人,没有不尊重的,提到圣人之道,每个人都能表现相当的敬意,没有不肃然起敬的。
不但整天捧着圣贤之书的读书人是如此表现,即使是农、工、商,亦莫不如此。
但是在今天讲圣人之道,就没有这个便利。
今天这个时代,先不讲农、工、商,即使是读书人亦很少有尊重圣人之道的,亦很少有了解圣人之道的。
在以往,从小即读四书五经,今天的读书人却是愈往上读,离开四书五经愈远。
知识分子把儒家这个常道忘掉了,很难再接上去。
事实上,也许农、工、商对于圣人之道还客气些,还保留一些尊重,知识分子反而不见得有此「雅量」。
因此,在今天讲儒家在当前的使命,尤其成了个严重问题。
要是大家都把圣人之道忘掉了,认为它是不适应时代的落伍之学,那么这种被时代抛弃的学问还谈什么当前的时代使命呢?
我认为这只是这个时代所表现的一个不正常的变态现象;落实地看,并不如此,所以我们仍可讲儒家在当前的使命。
我之所以要指出这些不正常的现象,乃是要大家正视、严重考虑「儒家本身存亡」的问题。
儒家这个常道落到今天这种若有若无的地步,几乎被世人忘却、抛弃,这是不合理的。
既然是常道,怎能被忘掉!
怎能若有若无!
常道而被埋没,这是任何人良心上过不去的。
假若良心上过得去,这就不是常道。
既然是常道,我们就不能让它被埋没下去。
这是就儒家本身存在的问题而言,另外就是牵涉到外界的作用、使命来讲儒家当前的使命,也是比其它任何一个时代都难讲。
因为现在来说儒家的使命,不只涉及它本身存亡的问题,还得涉及到其它的一些特殊问题,才能显出「使命」的意义。
尤其是牵涉到现代化的问题。
中国从清末民初即要求现代化,而有人以为传统儒家的学问对现代化是个绊脚石。
因此,似乎一讲现代化,就得反传统文化,就得打倒孔家店。
事实上,儒家与现代化并不冲突,儒家亦不只是消极地去「适应」、「凑合」现代化,它更要在此中积极地尽它的责任。
我们说儒家这个学问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积极地负起它的责任,即是表明从儒家内部的生命中即积极地要求这个东西,而且能促进、实现这个东西,亦即从儒家的「内在目的」就要发出这个东西、要求这个东西。
所以儒家之于现代化,不能看成个「适应」的问题,而应看成「实现」的问题,唯有如此,方能讲「使命」。
2.儒家第一阶段的发展
我们在此先照察一下儒家在过去两千多年中的「发展」。
大体说来,可分成两个阶段,今天则属儒家学术的第三阶段。
这是个大分类的说法。
儒家学术的第一阶段,是由先秦儒家开始,发展到东汉末年。
两汉的经学是继承先秦儒家的学术而往前进的表现,而且在两汉四百年中,经学尽了它的责任,尽了它那个时代的使命。
从汉武帝复古更化说起,建造汉代大帝国的一般趋势,大体是「以学术指导政治,以政治指导经济」,经学处于其中,发挥了它的作用。
因此,不能轻视汉代的经学,它在那个时代,尽了它的责任、使命;尽得好不好,是否能完全合乎理想,则是另外的问题,至少在汉朝那种局面下,儒家以经学的姿态出现,而尽了它的使命。
先秦儒家与先秦诸子齐头并列,至汉朝,以经学的姿态表现,一直发展到东汉末年,即不能再往前进了。
汉朝大帝国亦不能再往前发展了。
这已是绝路,任何人出来也没办法;照前人的说法,即是「气数」尽了。
当时郭林宗即谓:
大厦将倾,非一木之所能支也。
此即表示那个时代要「峰回路转」了;顺着以前所定的那个模型,己走到尽头了。
「气数」不是可以随便说的,一个力量兴起,必得维持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说气数。
在东汉末年那个关节上,说「气数」才有意义,说「峰回路转」也才有意义,在此方显出无限的苍凉之感、沈穆的悲剧意味。
若只是一些小弯曲,亦用不上「峰回路转」这种形容,必在看着就是死路,然而却绝处逢生,在绝望至死之际,忽有一线生机开出,这才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这种情形好比修道人所说的大死大生。
这个「峰回路转」,开了另一个时代,即是魏晋南北朝隋唐这一个长时期。
照中国文化的主流、照儒家的学术而言,这一大段时间算是歧出了,岔出去了、绕出去了。
儒家的学术在这个时代中,暗淡无光彩。
魏晋盛行玄学,乃依先秦原有的道家而来;尽管道家是中国原有的,但不是中国文化生命的主流,因此仍属中国文化之「旁支」。
玄学虽属歧出者,但仍是继承中国原有的道家,至于东晋以下,历经南北朝、隋、以至唐朝前半段,这一个长期的工作则在于吸收佛教、消化佛教,佛教则纯属外来者,当时即初以道家为桥梁来吸收佛教。
南北朝两百多年,中国未得统一。
南朝宋齐梁陈,北朝则是五胡乱华,在这两百多年的混乱中,处在当时人,不是很好受的。
我们今天处在这个动乱的时代中,由民国以来,至今不过六十多年,这六十几年的不上轨道、种种不正常的现象,在历史上看来,并不算一回事。
所以大家处在这个时代中,应该有绝对地贞定的信念,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总是会过去的。
从南北朝到隋唐,佛教不但被吸收进来,而且被中国人消化了,这等于消化另一个文化系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在长期的吸收、消化中,佛教几乎成了中国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份,充实了我们文化生命的内容。
佛教在中国文化中发生了很大的作用,这是事实;至于进一步衡量这个作用的价值、利弊,则属另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暂不讨论。
文化生命不可摧残
从魏晋开始,乃中国文化的歧出。
所谓「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又一村」即指的是此一歧出的阶段——魏晋,南北朝到隋唐。
到了唐末五代,这也是中国历史中最黑暗的一个时期。
五代不过占五十多年,却有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每个做皇帝的,原先都想万世一系地往下传,而今每个朝代却至多不过十几年,可见五代这段时期是个差劲的时代,更重要的是这个时代的人丧尽了廉耻。
所以,一个民族糟蹋文化生命,同时就牵连着糟蹋民族生命。
什么叫做糟蹋文化生命呢?
在这里所表现的即是人无廉耻。
五代人无廉耻,代表人物即是冯道,[亦如今日大陆上有所谓的「四大不要脸」,其中领衔的即是郭沫若与冯友兰。
]你想,谁愿意不要脸呢?
谁能没有一点廉耻之心呢?
唐末五代的人难道就自甘下贱吗?
但是,五代这个局面就把人糟蹋得无廉耻。
[大陆上,黄帝的子孙,那能没有廉耻之心呢?
为什么能够出现「四大不要脸」呢?
难道说郭沫若、冯友兰就愿意不要脸吗?
这都是毛泽东糟蹋的!
这都是共产主义糟蹋的!
才使得人无廉耻。
这「四大不要脸」不过是因为他们较有名气,易受注意,而特别举出来。
事实上,岂止这四个人而已,一般人谁敢有廉耻之心呢?
共党在内部批斗时,常以「风派」抨击他人;其实,那一个人不是风派呢?
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今天邓小平要现代化,谁敢说不现代化?
以前毛泽东要文化大革命,谁又敢说不文革?
谁敢出来说句反面的话呢?
他们还对那些投机的人名之曰风派,事实上,那个不投机呢?
这句话在自由世界说,是有意义的,在那个极权的世界说,是没有意义的。
有的人听了这些话,还以为共产党在讲气节、讲廉耻。
「气节」、「廉耻」,在自由世界的人才有资格说,这些名词也才有意义,在那个专制暴虐的政权下,说这些话都是没有意义的,完全不能表意的。
又如说共产党以前在海外宣传大陆没有失业,而谓在共产主义统治下没有失业,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中则到处有失业问题。
头脑简单的人听了,还误生幻想,以为不错。
其实,这只是耍文字语言的魔术,专门骗那些头脑简单的人。
试问,你有不失业的自由吗?
你有不工作的自由吗?
在自由世界,才有失业、不失业的分别,才可说有气节、讲廉耻。
因为人们有自由,法律上保障人的独立人格,承认人的尊严。
有了自由,人即须负责任。
再深一层说,人有道德意志、自由意志,才能谈有气节、有廉耻的问题。
在大陆上,谁敢说我有自由意志呢?
所以,共产党耍的那些文字魔术,都是没有意义的话,你听他那些话干什么呢?
偏偏有些人利用这个机会,去捧叶剑英、邓小平,你捧他作什么呢?
其实,说穿了,还不是一丘之貉。
当年邓小平作副总理的时候,还不是顺着毛泽东的话转,还不是一样地拍马屁。
根本的关键在于共产党的本质即是彻头彻尾地摧残、斲丧人的廉耻。
孟子说的好:
「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然而,说是这样说,现实上人到了生死关头,谁不害怕呢?
要承认人有自由意志,才能表现「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假定人没有自由意志,连这句话都不能表现。
你想死,我还不让你死呢!
以前的人可以出家,今天在大陆上,往那里出家呢?
以前的人可以不作官,今天连不作官的自由也没有了。
你没有不参加政治的自由,你没有不参加人民公社的自由,你也没有不接受政治洗脑的自由。
在那种统治下,人丧失了自由,想要「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你都做不到。
中华民族发展到今天,大陆的同胞被共产党圈在人民公社,不能讲廉耻,不能讲气节。
这个就是作贱人的生命,作贱文化生命,同时亦即作贱我们这个民族生命。
这个生命被继续作贱下去,是个很可悲的现象。
问题即在于共产党能够作贱到什么一个程度?
人性究竟还有没有苏醒的一天?
人性能否觉悟,而发出力量把共产主义冲垮?
有没有这么一天呢?
我个人对此一问题,不表悲观,但也不表乐观,我希望大家注意到这是一个很艰难的问题,需要随时警觉。
说起来,「人之初,性本善」,在太平年间这样说是很容易的,若是现实上没有表现出善,我就通过教育等方法使你容易表现;但是这句话在今天这个时代,就不那么容易。
不过,我相信人性总有复苏的一天,至于拉到多么长的一段时间才能表现,就很难说。
]我说这个意思,就是要加重这个观念——文化生命不能随意摧残,摧残文化生命,同时就影响民族生命。
文化生命不能摧残太甚,一个民族是经不起这样摧残的。
就好象一个人得些小病是无所谓的,生长中的痛苦是不可免的,但是大病就不能多患。
又如一个人的命运不能太苦,人受点挫折、受点艰难困苦,是好的,但是挫折太多、苦太重,就会影响人的生命。
3.儒家第二阶段的发展
上面说到唐末五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暗的一个时期,其黑暗之所以为黑暗的原因,即在于无廉耻。
说这层意思,也是要大家了解下一个阶段——宋明理学。
宋明理学是儒家学术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就是对着前一个时期的歧出而转回到儒家的主流。
理学本质的意义即在唤醒人的道德意识。
何以宋人出来讲学,特别重道德意识这个观念呢?
自清朝以后,以至于民国以来,提到理学家,一般人就头疼,如同孙悟空听到金箍咒一样。
谁敢做理学家呢?
可是只因为自己做不到,就用种种讥讽的字眼来丑诋、笑骂,这是清末以至于今的一个可怪的风气。
其实,道德意识有什么毛病呢?
宋明理学家主要就是要唤醒道德意识,这又有什么不对呢?
有什么可以讥笑的呢?
宋明理学家之所以重视道德意识,主要即因他那个社会背景、时代背景就是唐末五代的那个「无廉耻」。
人到了无廉耻的地步,人的尊严亦复丧尽,这就成了个严重问题。
亦即所谓文化生命没有了,就影响到你的自然生命。
这句话,大家听起来似乎觉得有些因果颠倒。
其实不然。
一般人说民族生命、自然生命没有了,就影响文化生命;我现在倒过来说,文化生命摧残得太厉害,你的自然生命也没有了,一样的受影响。
[抗战以前,共产党在江西盘据了一段时间,等到剿共把他们驱逐出去以后,这些地区好几年不能复兴,即是被共匪摧残得太惨。
所以,]一个地方穷,不要紧,只要有人去努力开垦,明天就富了;若是把人的生命糟蹋了,没有人种田,则成了严重问题。
我举这个例子,即说明文化生命摧残太甚,自然生命也不会健康旺盛。
[所以今天大陆上,共产党摧残文化生命,使人成为白痴、成为无廉耻,究竟将来影响到什么程度,就很难说。
想起来,这是个很可怕的现象。
一个不正常、变态的暴力,若想把它恢复过来,并不容易。
甚至到最后,他们本身亦不会觉悟,有个结果,就是发疯。
在过去也有这种经验,老辈的人说过,当年太平天国洪秀全、杨秀清等人打到南京,本来就已不正常了,但他还有战斗力,还是不好对付,残暴地用儿童做冲锋队,这和共产党用人海战术一样地可恶。
到了太平天国覆亡后,转成捻匪,结果那些残众都发疯。
当年听老辈谈这些事,心中就有非常多的感触。
一个太平天国闹了一下,就糟蹋中华民族如此之甚,而今共产党统治大陆同胞、黄帝的子孙,以那种方式来统治,统治那么久,对中华民族生命的摧残当然更甚。
这不是个大悲剧吗?
圣人说要悲天悯人,这才是可悲可悯的事。
]所以,廉耻不可丧尽,不可任意地斲丧。
人的生命不可完全感性化、完全形躯化、完全躯壳化。
完全感性化、完全躯壳化,就是老子所说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
人的生命不能完全感性化,即表示随时需要文化生命来提住。
代表文化生命的廉耻、道德意识,更不可一笔抹煞,不可过于轻忽。
所以理学家出来,尽量弘扬儒家,对治唐末五代无廉耻而讲儒家的学问。
至此,经过魏晋南北朝隋唐这一长时期的歧出,中国文化再回到它本身,归其本位;而转回来的重点则落在道德意识上。
儒家的学问原来讲的是「内圣外王」,宋明儒则特重「内圣」这一面,亦即强调道德意识,讲求道德意识、自我意识的自我体现。
「内圣」是个老名词,用现代的话说,即是内在于每一个人都要通过道德的实践做圣贤的功夫。
说到圣贤,一般人感觉高不可攀,甚至心生畏惧;实则道德实践的目标即是要挺立自己的道德人格,做圣贤的功夫实即挺立自己的道德人格、道德人品,这是很平易近人的,没有什么可怕。
我们对「内圣」一词作一确定的了解,即是落在个人身上,每一个人都要通过道德的实践,建立自己的道德人格、挺立自己的道德人品。
这一方面就是理学家讲学的重心。
可是儒家原先还有「外王」的一面,这是落在政治上行王道之事。
内圣、外王原是儒家的全体大用、全幅规模,《大学》中的「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即同时包括了内圣外王;理学家偏重于内圣一面,故外王一面就不很够,至少弘扬不够。
这并不是说理学家根本没有外王、或根本不重视外王,实则他们亦照顾到外王,只是不够罢了。
我们今天说宋明儒虽亦照顾到外王而不够,这个「不够」,是我们在这个时代「事后诸葛亮」的说法。
在当时,理学家那个时代背景下,他们是否一定觉得不够呢?
这就很难说。
固然理学家特别重视内圣的一面,然他特别重视于此,总有其道理;在他们那个时代中,或许他们亦不以为这种偏重是不够的。
外王方面,在那种社会状况、政治形态下,也只好如此,不能再过份的要求。
我们得反省一下,外王方面开不出来,是否属于理学家的责任呢?
事实上,政权并不在理学家的手中,他如何能负这个责任呢?
政权是皇帝打来的,这个地方是不能动的,等到昏庸的皇帝把国家弄亡了,却把这个责任推给朱夫子,朱夫子那能承受得起呢?
去埋怨王阳明,王阳明那能担当得起呢?
所以,批评理学家外王面不够,这个够不够的批评是否有意义,也得考虑一下。
在那个时代,那种政治形态下,也只好这样往前进了。
外王方面够不够,不是理学家所能完全决定的;不是他能完全决定的,也就表示不是他能完全负这个责任的。
我们把这个责任推到理学家的身上,这是「君子责贤者备」的批评,这是高看、高抬知识分子,这也就是唐君毅先生所说的:
只有知识分子才有资格责备知识分子,只有王船山、顾亭林才有资格责备王阳明。
只有在这层意义下,我们才能责备理学家,谓之讲学偏重之过,不应只空谈心性,仍应注重外王、事功。
这还是在讲学问之风向的问题上说的。
4.儒家的当前使命——开新外王
以现在的观点衡之,中国文化整个看起来,外王面皆不够。
就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来看,以今日的眼光衡之,确实在外面不够,顾亭林那些人的要求外王、事功,也是对的。
今天仍然有这个要求。
可叹的是,今天不仅外王面不够,内圣面亦不够,儒家本身若有若无。
但是儒家若为常道,则人类的良心不能让这个常道永远埋没下去,这得诉诸每个人的一念自觉。
儒家学术第三期的发展,所应负的责任即是要开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外王,亦即开新的外王。
「新外王」是什么意义呢?
外王即是外而在政治上行王道,王道则以夏商周三代的王为标准。
照儒家说来,三代的王道并非最高的理想,最高的境界乃是尧舜二帝禅让、不家天下的大同政治。
儒家的政治理想乃以帝、王、霸为次序。
帝指尧、舜,尧舜是否真如儒家所言,吾人不必论之,但此代表了儒家的理想则无疑,以尧舜表现、寄托大同理想。
三代则属小康之王道。
春秋时代的五霸则属霸道,以齐桓公、晋文公为代表。
从前论政治,即言皇王帝霸之学。
齐桓、晋文的境界虽然不高,但比得秦汉以后的君主专制要好;君主专制以打天下为取得政权的方法,在层次上是很低的。
当初商鞅见秦孝公,先论三皇五帝之学,孝公不能入耳;而后言王道,仍嫌迂阔;最后言霸道,乃大喜。
可见前人对于政治理想是有一定的次序。
秦孝公之喜霸道,乃因它能立竿见影,马上见效,而儒家的学问往往不能满足这一方面外王、事功的要求。
早在春秋战国,即有墨家因此而批评儒家,只承认儒家维持教化的责任。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亦批评儒家云:
「博而寡要,劳而少功」。
后来南宋陈同甫与朱子争辩,亦是基于要求外王、要求事功的精神。
而实际上,要求外王中,就涵着要求事功的精神。
陈同甫以为事功须赖英雄,而讲英雄主义,重视英雄生命,推崇汉高祖、唐太宗。
到了明末,顾亭林责备王学无用,亦是秉持事功的观念而发。
而后有颜李学派的彻底实用主义。
一般人斥儒家之无用、迂阔,评之曰:
「无事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以为不究事功者最高境界亦不过是此一无奈的结局。
这些都是同一个要求事功的意识贯穿下来的,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老传统,在中国文化中是一条与儒家平行的暗流,从墨子开始,一直批评儒家的不足。
这个要求事功的传统再转而为清朝干嘉年间的考据之学,则属要求事功观念的「转型」。
干嘉年间的考据之学以汉学为号召,自居为「朴学」,以此为实用之学,以理学为空谈、无用,骨子里还是以有用、无用的事功观念为背景。
何以谓「朴学」为要求事功观念的「转型」呢?
因为他们虽然批理学无用,而其本身实际上开不出事功来,这些考据书生没有一个能比得上陆象山、朱夫子、王阳明;这些理学家都有才干,都会做事,只是不掌权而已。
然而考据家假「朴学」之名,批评理学无用,背后的意识仍是有用、无用,即可谓之乃事功观念的转型。
事实上,这种转型更是无用,故实非事功精神之本义。
由此转而到民国以来,胡适之先生所谈的实用主义,以科学的方法讲新考据,实仍属此一传统,背后仍是要求有用、斥责无用。
我们可以看出,儒家这条主流,旁边有条暗流,这条暗流一直批评儒家无用而正面要求事功,这个传统从墨子说起,一直说到胡适之所倡的新考据的学风,可谓源远流长。
但是这里面有个根本的错解,若是真想要求事功、要求外王,唯有根据内圣之学往前进,才有可能;只有根据墨子,实讲不出事功,依陈同甫的英雄主义亦开不出真事功。
希望大家在这里要分辨清楚。
中国人传统的风气,尤其是知识分子,不欣赏事功的精神,乃是反映中华民族的浪漫性格太强,而事功的精神不够。
事功的精神是个散文的精神,平庸、老实,无甚精彩出奇。
萧何即属事功的精神,刘邦、张良皆非事功的精神,可是中国人欣赏的就是后者。
萧何的功劳很大,所谓「关中事业萧承相」,但因其属事功精神,显得平庸,故不使人欣赏。
汉朝的桑弘羊、唐朝的刘晏皆为财政专家,属事功精神,然而中国人对这一类人,在人格的品鉴上总不觉有趣味。
事功的精神在中国一直没有被正视,也没有从学问的立场上予以正视、证成。
中国人喜欢英雄,打天下、纵横捭阖,皆能使人击节称赏。
[由于中国人在性格上有这种倾向,所以毛泽东才能投这个机,就是因为他不守规矩、乱七八糟,而带有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