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第二梯次提升大学基础教育计画.docx
《教育部第二梯次提升大学基础教育计画.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教育部第二梯次提升大学基础教育计画.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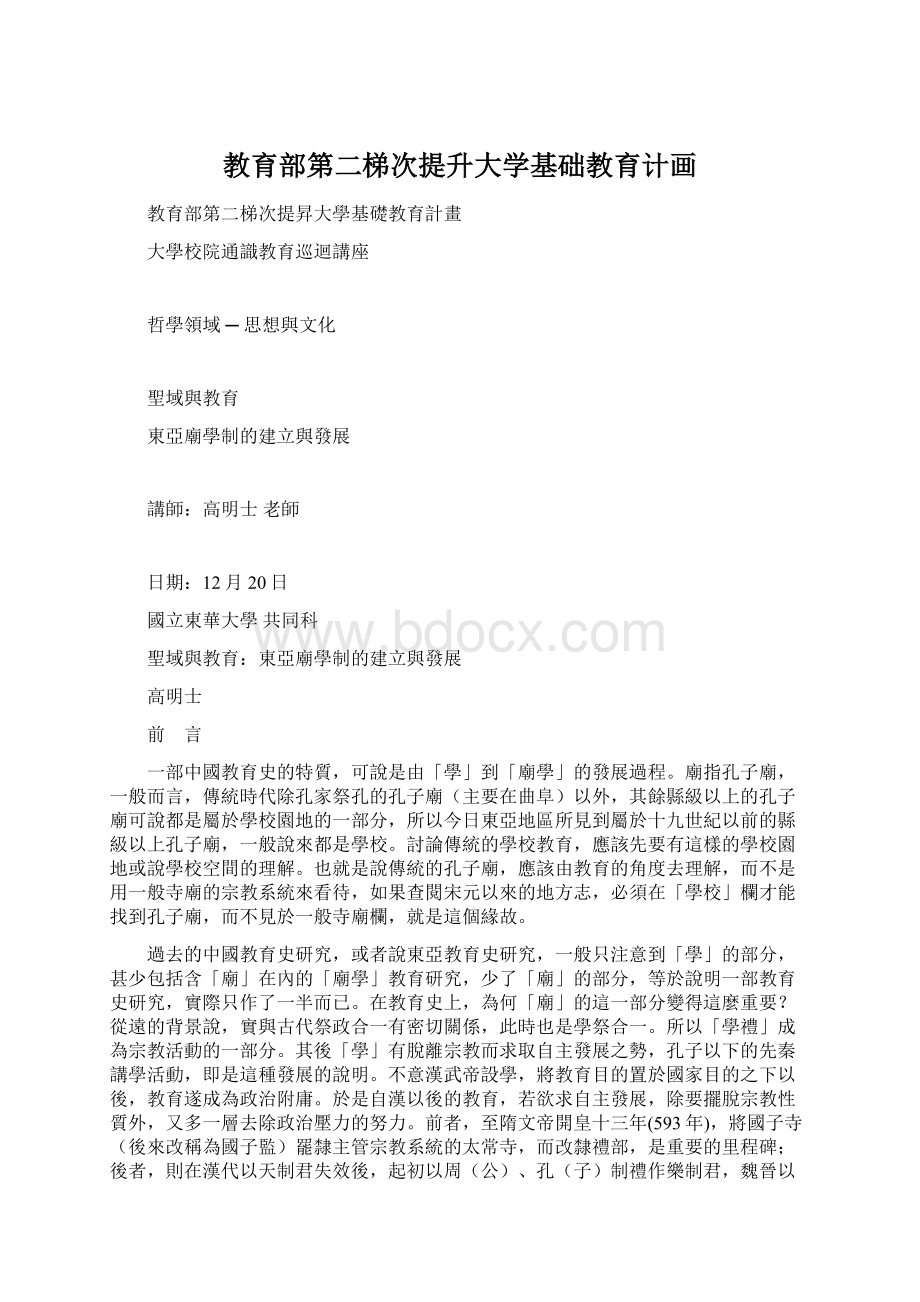
教育部第二梯次提升大学基础教育计画
教育部第二梯次提昇大學基礎教育計畫
大學校院通識教育巡迴講座
哲學領域─思想與文化
聖域與教育
東亞廟學制的建立與發展
講師:
高明士老師
日期:
12月20日
國立東華大學共同科
聖域與教育:
東亞廟學制的建立與發展
高明士
前 言
一部中國教育史的特質,可說是由「學」到「廟學」的發展過程。
廟指孔子廟,一般而言,傳統時代除孔家祭孔的孔子廟(主要在曲阜)以外,其餘縣級以上的孔子廟可說都是屬於學校園地的一部分,所以今日東亞地區所見到屬於十九世紀以前的縣級以上孔子廟,一般說來都是學校。
討論傳統的學校教育,應該先要有這樣的學校園地或說學校空間的理解。
也就是說傳統的孔子廟,應該由教育的角度去理解,而不是用一般寺廟的宗教系統來看待,如果查閱宋元以來的地方志,必須在「學校」欄才能找到孔子廟,而不見於一般寺廟欄,就是這個緣故。
過去的中國教育史研究,或者說東亞教育史研究,一般只注意到「學」的部分,甚少包括含「廟」在內的「廟學」教育研究,少了「廟」的部分,等於說明一部教育史研究,實際只作了一半而已。
在教育史上,為何「廟」的這一部分變得這麼重要?
從遠的背景說,實與古代祭政合一有密切關係,此時也是學祭合一。
所以「學禮」成為宗教活動的一部分。
其後「學」有脫離宗教而求取自主發展之勢,孔子以下的先秦講學活動,即是這種發展的說明。
不意漢武帝設學,將教育目的置於國家目的之下以後,教育遂成為政治附庸。
於是自漢以後的教育,若欲求自主發展,除要擺脫宗教性質外,又多一層去除政治壓力的努力。
前者,至隋文帝開皇十三年(593年),將國子寺(後來改稱為國子監)罷隸主管宗教系統的太常寺,而改隸禮部,是重要的里程碑;後者,則在漢代以天制君失效後,起初以周(公)、孔(子)制禮作樂制君,魏晉以後改為以孔、顏(回)等儒門系統之教育力量制君,孔子進而以「百世帝王之師」作為制君的代表,這個時候的孔子已經不是先秦的孔子,而是學問之神,所謂道統的代表,或者說是文化傳統的代言人。
於是藉由教育力量以制君,求取政治合理性的努力,乃成為一千數百年所追尋的目標。
其具體成果,就是在學校建置孔廟,以及隨著廟制而建立的祭祀制度(如配享、從祀等),使學校在王域之內,另外成立「聖域」,雖然,這種聖域的建立,也來自皇權的恩許,但是聖域一旦建立,便成為神聖不可侵犯,也是傳統讀書人的庇護所。
由於中國皇權自秦漢以後日益專制化,在以天制君失效後,設若無設計以孔子為代表的教育力量出來,則中國的專制統治,除非被推翻,否則將是暗無天日。
基於這樣的理解,拙稿擬先探討「廟學」教育制度的由來,以及透過「廟學」教育制度在東亞的普遍化。
一、「廟學」的出現
學校園地中,具體建置廟宇,而成為「廟學」的制度,其事可考者,當始於東晉孝武太元十(385)年,就學制而言,實是自古以來的一大變化,其議可能出自謝石。
孝武帝太元九(384)年,尚書謝石上書曰:
立人之道,曰仁興義,翼善輔性,唯禮興學。
……今皇威遐震,……豈可不弘敷禮樂,使煥乎可觀。
請興國學,以訓胄子,班下州郡,普修鄉校。
帝納其言。
於是「選公卿、二千石子弟爲生,增造廟屋一百五十五間。
」(《宋書》卷十四禮志)此處的「廟屋」,當指孔子廟、國子學與諸生省(即博士省)。
《晉書》卷九孝武紀載太元十(385)年二月,立國子學。
所以此等廟屋當在太元十年二月完成。
問題是:
太元十年為何會在國子學出現「廟屋」而成為「廟學」教育制度?
筆者認為此事在中國教育史上,實是非常重大的一件事。
過去在學校所舉行的釋奠祭禮,只是掃壇為殿,現在有了具體的廟屋建築,其作用為何?
值得檢討。
關於這問題,可惜無直接的資料可作說明,此處只能由謝石的上書推測。
謝石說:
「今皇威遐震……豈可不弘敷禮樂,使煥乎可觀。
」顯然在肥水之戰勝利之後,欲藉由振興教育,提倡禮樂,以強化東晉在文化上的正統性,進而對北方作有力的號召。
在謝石上書中(太元九年),見不到在國學中建置孔廟之議,但由翌(太元十)年完成「廟屋」一事看來,自謝石上書後到建築廟屋之前,君臣之間,顯然有一番討論,其結論即在國學中建置孔廟。
這一段討論過程,已不見於今存文獻了。
目前只能由謝石上書的文詞分析與推測,這種顧左右言他的情況,在中國歷史上,經常可見到。
也是專制王權下,為維護道統而有其不得不的苦衷。
如上所述,自東晉孝武帝太元十(385)年,創建「廟學」制後,翌年,即太元十一(386)年,又追謚孔子後裔,另建孔子廟(宣尼廟),以比擬曲阜孔廟,使東晉雖處偏安之地,猶可宣示文化傳承之正統性。
其後南朝各朝相沿如是,而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三(489)年,也在中書學(原稱國子學)建置了孔子廟。
從此以後,中國南北兩朝在中央官學都設有孔子廟。
到了北齊,文宣帝天保元(550)年,更令郡學立孔顏廟,這是地方官學立聖廟之始。
隋朝建立,據《隋書》卷九〈禮儀志〉的記載,說:
隋制,國子寺每歲以四仲月上丁,釋奠於先聖先師……州郡學則以春秋仲月釋奠。
此處雖無提及孔廟,但北齊國子寺有孔顏廟(《隋書.禮儀志》),隋承襲北齊之制,理應也有孔顏廟,例如隋代的相州州學建有孔子廟,就是明證。
(《隋書》卷73〈梁彥光傳〉)
二、「廟學」的制度化
所謂「廟學」的制度化,主要有兩項特徵:
一是全國學校園地到縣學為止,規定必須建置孔子廟;一是「學」制與「廟」制的完備。
前者,即中央到地方縣學普遍完成廟學制,是在唐太宗貞觀四(630)年。
是年,太宗詔令全國縣學皆建置孔子廟(《新唐書.禮樂志》),在此之前,只有京師及各州(郡)學完成「廟學」制;從此以後直到清代為止,自中央國子監到地方縣學,皆須具備「廟學」制;即連後來出現的書院制度,也是屬於廟學制的形式。
本世紀在敦煌所發現的《沙州圖經》,其載沙州州學、縣學之制,實為唐代廟學制提供最具體的例子。
其卷三云:
州學
右在城內,在州西三百步。
其學院內,東廂有 先
聖太師(廟)堂,(堂)內有素(塑) 先聖及先師顏子
之像。
春秋二時奠祭。
縣學
右在州學西連院。
其院中,東廂有 先聖太
師(廟)堂,(堂)內有素(塑) 先聖及先師顏子之像。
春秋二時奠祭。
醫學
右在州學院內。
於北墻別構房宇安置。
卷五記載壽昌縣之縣學云:
一所縣學
右在縣城內,在西南五十步。
其〔(院中,東廂有先聖太師廟)〕
堂,堂內有素(塑) 先聖及先師〔(顏子之像)〕。
〔春秋二時奠祭〕
(標點及括弧內文字為筆者所加)
《沙州圖經》所載的內容,代表唐朝前期的制度。
其州縣學在東廂均建有奉祀聖師廟堂,也就是採用「左廟右學」制度。
孔聖顏師為塑像,每年春秋二仲月舉行釋奠之禮,此制完全符合唐初以來所建立的廟學制度。
《唐六典》卷4「祠部郎中員外郎」條規定:
凡州縣皆置孔宣父廟,以顏回祀焉。
仲春上丁,州縣官行釋奠之禮,仲秋上丁亦如之。
這是唐朝前期對於廟學制的規定。
其次,關於「學」制與「廟」制的完備。
從今日的觀點看來,「學」是教學空間,「廟」是祭祀空間,在校園設計上,則以「廟」為軸心而展開。
正常的情況下,均各有其圍牆,但彼此可相通。
教學空間的「學」,主要指講堂,宋末以後,逐漸改稱「明倫堂」。
此外還有特定學習場所、藏經閣如奎(魁)星閣(樓)以及師生住宿的齋舍等。
「廟」常以孔子封號或尊號稱之,如謂宣尼廟、宣父廟、宣聖廟、先聖廟、先師廟、聖廟、文廟等。
「廟」之附屬建築物,從唐朝以後的發展,可知包括照壁、泮池、櫺星門、大成門、大成殿、崇聖祠等,儼然成為一座宮殿,所以又稱「學宮」。
分別而言,可分為前導、主體、後部等三部分。
前導部分包括照壁、泮池、櫺星門等;主體部分包括大成門、大成殿以及兩廡等;後部主要有崇聖祠(啟聖祠)。
整個廟學的附屬建築,尚有鄉賢祠、名宦祠、鐘鼓亭、碑亭等,隨時代不同或地方特性而有差別。
「廟」的祭祀制度,有主神、配享、從祀等制度的建立,以及每年春秋二仲丁的大典(含樂、舞等)與每月朔望的祭禮等。
簡單說,所謂「廟學」教育制度,指學校以文廟為主軸而展開的儒教主義教育。
三、「廟學」制度的發展
1、官學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43〈學校考.祠祭褒贈先聖先師〉條末按曰:
自唐以來,州縣莫不有學,則凡學莫不有先聖之廟矣。
然之前賢文集,……皆言廟而不及學,蓋衰亂之後,荒陋之邦,往往庠序頹圯,教養廢弛,而文廟獨存。
從馬端臨一段話,可知自唐到宋的州縣學(含中央的國子監),均已完成「廟學」體制;但遇衰亂而無法正常實施教學時,則常存廟而廢學。
南宋寧宗嘉泰(1201年)《會稽志》卷1〈學校〉云:
宋興,學校之制皆因前代。
惟州郡自唐末五代喪亂,學官盡廢,有司廟祭先聖而已,猶有廢而不舉者。
這段話可印證馬氏說,以為唐末五代衰亂之際,地方學校常獨存文廟而已。
再如宋朝尹洙「鞏縣孔子廟記」云:
宋興,八十載。
……郡府立學校尊先聖廟十六七。
(《河南先生文集卷4》,收入《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這是自北宋以來,從中央到地方縣學為止,多建有孔子廟的旁證。
元朝順帝至元《嘉禾志》卷7〈學校〉云:
廟以崇先聖,學以明人倫。
郡邑廟學,大備于唐,中廢於五代。
宋(仁宗)慶曆中始議州縣皆立學;(徽宗)崇寧間著為令,此州縣學廢興之由也。
此處除說明「廟學」之意義及其緣由而外,亦述及宋以來的發展。
文中對宋代雖只曰州縣學,其實當含廟制。
其下接著敘述嘉興路學,並兼及廟制之修建,最後曰:
「丙子兵火,廟學幸存。
」丙子即元順帝至元二(1336)年。
以上是簡單說明「廟學」制在宋代的發展情形。
遼、金、元時代的情形如何?
遼朝的上京、中京、西京,都設有國子監,其旁建有孔子廟,按時祭祀先聖先師。
監與廟的關係位置,不甚清楚。
其各州、縣學也都有孔子廟。
金朝沿襲前朝,除上京國子監有孔子廟而外,州縣學也是建有廟學。
章宗泰和四(1204)年二月,詔刺史曰:
「州郡無宣聖廟學者,並增修之。
」(《金史.章宗本紀》)這是進一步推廣廟學制的措施。
段成己〈河中府重修廟學碑〉云:
隋唐以來,學遍天下。
雖荒服郡縣皆有學,學必立廟,以禮孔先聖先師。
……至於近代,廟學制益備。
此處再度說明自隋唐以來的所謂「廟學制」,指「學必立廟,以祀孔先聖先師。
」,到宋、金時代已達普遍化。
元朝太宗六(1234)年,在打敗金國,取得金朝中都燕京之後,改其樞密院為宣聖廟。
(《元史.選舉志》)同時在廟旁設立國子學,令侍臣子弟入學。
(《新元史.太宗本紀》)一般認為這是元朝國子廟學最早的紀錄。
世祖至元四(1267)年五月,敕上都重建孔子廟。
(《元史.世祖本紀》)到成宗即位,詔中外崇奉孔子。
(《元史.成宗本紀》)又詔:
曲阜林廟、上都、大都、諸路、府、州、縣、邑廟學、書院,贍學土地及貢士莊田,以供春秋二丁、朔望祭祀,修完廟宇。
自是天下郡邑廟學無不完葺,釋奠悉如舊儀。
(《元史.祭祀志》)
此事說明元朝建立之初,也致力於廟學制的推廣。
甚至邊區如雲南、福建、兩廣,特殊地區如軍隊駐地、轉運司治所、鹽場等也都有廟學的建置,民間在鄉村里社也有自發創建,其普及程度,超越唐宋。
明太祖洪武十五(1382)年四月,詔天下通祀孔子。
五月,南京新建國子監孔子廟完成,帝親詣釋奠,並頒釋奠儀注於府州縣學。
其國子監孔子廟的建制,是以廟在學東,中間為大成殿,左右為兩廡,其前為大成門,此亦即「左廟右學」之制。
(明朝黃佐《南雍志》卷7載洪武十五年六月「敕建太學之碑」、《明史》卷3〈太祖本紀〉、《明史》卷50〈禮志〉)
成祖遷都北京後,將北平府學改為國子監,並重建孔子廟。
明末清初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卷21「文廟」條云:
文廟在城東北,國學之左。
元太祖置宣聖廟於燕京,以舊樞密院為之。
成宗大德十年,京師廟成。
明太祖改為北平府學,廟制如故。
永樂元年八月,遣官釋奠,仍改稱國子監孔子廟。
尋建新廟於故址,中為廟,南向,東西兩廡,……正殿初名大成殿。
嘉靖九年,改稱先師廟,殿門為廟門。
萬歷二十八年,廟宇易以琉璃。
明朝郭磐《皇明太學志》(嘉靖三十六年刊,崇禎間增刊本)卷1〈典制上.建學〉,即以「廟學」說明太學之建制,並附以「廟學圖」。
這就是今日北京國子監與孔子廟的由來。
其廟學建制,仍然採用「左廟右學」之制。
王陽明〈萬松書院記〉(《王陽明全集》卷7〈文錄四〉)云:
惟我皇明,自國都至於郡邑,咸建廟學,群士之秀,專官列職而教育之。
其於學校之制,可謂詳且備矣。
而名區勝地,往往復有書院之設,何哉?
所以匡翼夫學校之不逮也。
夫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今之學宮皆以「明倫」名堂,則其所以立學者固未嘗非三代意也。
據此,可知明代全國的學校(自中央到郡邑)均建有「廟學」,廟學之外,又有書院,以輔助官學的不足。
到清代,北京國子監的廟學制仍沿襲明朝之舊,「為廟於城東北隅,太學之東;殿曰大成。
……廟後建祠曰崇聖。
」(《欽定大清會典》卷45〈禮部.先師之禮〉)此處的太學是通稱,實即國子監,廟當然是孔子廟,或曰文廟,仍為「左廟右學」建制。
雍正二(1724)年六月,世宗以平定青海,而遣官恭詣太學、闕里,告祭孔子;同時又令:
「各省修理文廟、學宮」。
(《清朝文獻通考》卷74〈學校考.祠祭褒贈錄後〉)乾隆(1738)三年二月,高宗至國子監文廟親行三獻禮,同時下諭禮部曰:
朕祗承丕緒,嚮慕心殷,國學文廟特命易蓋黃瓦,以展崇敬。
(清.龐鍾璐《文廟祀典考》卷1〈祀典紀盛〉)
這是今日北京所見文廟為黃瓦之由來,但在此處也是以「國學文廟」並稱,實是「廟學」的具體說明,此處的國學是通稱,仍指國子監。
清代對廟學及曲阜孔廟之尊崇,不遜前朝。
其於地方之直、省、府、州、縣學,除文廟之外,又規定在文廟左右並建置忠孝、節孝、名宦、鄉賢四祠。
(同前引《欽定大清會典》、《欽定大清通禮》卷11〈吉禮.先師春秋釋奠〉)這是清代對前代規制的修正,此即明確將治統要素(前列四祠)加入道統區域,導致道統、治統廟制產生混淆現象,有利於滿清政府的統治。
以上簡單的敘述,可知自唐以後至清代為止,中央的國子監到地方的州縣學,也就是全國的官學,均以「廟學」作為普遍的學制形態。
這樣的學校制度,指校園由「廟」的祭祀空間與「學」的教學空間兩個共同構成,而成為傳統學制非常重要的特徵。
2、聖域的界定──下馬碑的出現
金朝在「廟學制」的發展過程中有一重要突破,就是金章宗明昌二(1191)年在曲阜孔子廟欞星門左右各設置一個下馬碑,其歷史意義重大。
(明朝陳鎬《闕里誌》卷11〈林廟誌〉)此制有無適用於轄區內的學校孔廟,不得而知,但章宗尊孔,重視學校教育,則為事實。
如同年四月,以孔子五十一代孫孔元措襲封為衍聖公。
(《闕里誌》卷14〈詔誥〉)同年五月戊辰,詔:
「諸郡邑文宣王廟隳廢者,復之。
」(清朝孔繼汾《闕里文獻考》卷14〈祀典〉);四年,親臨釋奠於先聖(《闕里誌》卷6〈祀典〉);至泰和四(1204)年二月,如前所述,下詔州郡無宣聖廟者,增修之。
這些措施中,均無明言各地文廟亦須建置下馬碑之事,可能一時尚無推廣到各地。
但《(陜西省)定遠廳志》(光緒五年刊本,收入《中國方志叢書》第270號),卷9〈學校志〉在敘述「歷代尊崇典禮」時,亦記述:
「金章宗明昌二年詔廟門置下馬牌」。
此處無詳細說「廟門」是指曲阜孔廟或包含全國各地孔廟,而此節所敘述的內容是包括全國的郡縣學,依此看來似乎可適用於全國。
實際如何,有待查考。
明憲宗成化十六(1480)年春二月辛酉,「命所在過孔門者皆下馬。
」(《闕里文獻考》卷14〈祀典〉)既然過孔門者皆須下馬,則孔門之前必須豎有下馬碑。
此處所謂的「孔門」,當不只是指曲阜孔門而已,應當包括全國各地的孔門,也就是全國所有的「廟學」。
所以至遲到此時,已將廟門前建置下馬碑的規定,推行到全國廟學之地。
今日吾人在曲阜孔子廟前仍可見左右兩個下馬碑曰:
「官員人等至此下馬」,北京國子監孔子廟前可見到下馬碑曰:
「大小官員過此皆下馬」,在台灣台南台灣府學孔子廟前的下馬碑曰:
「文武官員軍民人等至此下馬」,韓國漢城成均館孔子廟前的下馬碑曰:
「大小官員過此皆下馬」(按,此碑文與北京同),日本東京湯島聖堂不見下馬碑,但仍宜有其制,詳細待查。
因為筆者於2001年10月到水戶德川家的西山莊,發現其入口右前方即立有「下乘」兩大字之石碑,此即下馬碑。
筆者於2002年12月赴越南順化、河內、北寧參觀孔廟,雖不見有下馬碑,但在順化阮朝皇宮前則有下馬碑的建置曰:
「傾蓋下馬」,相信孔廟也應有其制。
傳統東亞教育文化中,具有獨特的普遍性,於此可見知一斑。
3、書院
宋初的書院教育,恐怕一開始就受到唐五代以來「廟學」制的影響,而具備廟(祠)學之制。
其開風氣之先者,正是嶽麓、白鹿洞兩書院。
若取較明確的時間,宜設定在開寶五(976)年。
真宗咸平五(1002)年,敕有司重脩繕,又塑宣聖、十哲像的措施,可視為宋代全面性實施「廟學」制(含官學與書院)的開始。
宋代的書院,因接受政府贈書或學田等益處,導致走向半官方化,也逐漸成為廟學制的形態,只是書院教育本為私學教育形態,其與官學相較,乃呈現多樣化,尤其在奉祀對象方面。
過去討論書院教育,一般是偏重藏書與教學兩項功能的說明,對於書院供祀問題較少著墨。
最近出版的楊慎初、朱漢民、鄧洪波等著《岳麓書院史略》(1986)、李才棟《白鹿洞書院史略》(1989)、同氏著《江西古代書院研究》(1993),以及毛禮銳.沈灌群主編《中國教育通史》第三卷《宋元明清時期的教育》(1987)、李國鈞主編《中國書院史》(1994),均已注意到供祀問題的重要性,這是非常可喜的現象。
前者主張供祀的目的在於「突出其道統源流和建院功績,以進行傳統和典型模範教育。
」李才棟氏則認為供祀是「展禮」的一種表現,「包含著尊師、重道、崇賢等含義,是一種生動的教育過程,也是朱熹所謂『格物窮理』的重要方面。
」此外,王炳照氏也以為書院祭祀活動的目的主要有二:
一是樹立楷模,感發志向和信念,使學者「入其堂儼然若見其人」。
二是標榜學派學風特點和旨趣,激勵後學繼承發揚學派特色。
是一種形象化的教育手段。
此等主張,大致可歸納為以下三點:
第一,進行模範教育;第二,提示學術源流;第三,提倡尊師重道,可謂對盛氏說的進一步發揮,均有見地,值得重視。
惟筆者以為供祀的教育作用,主要有以下三點:
第一,提示聖賢可學而至,也就是教育理想的具象化。
第二,供祀之祠宇,除儒門之統而外,亦有其他祠宇,提示人生價值的多元化,並非侷限儒者一途。
第三,透過供祀禮儀,進行人格教育與文化傳承教育。
四、東亞教育圈的成立及其特質
自從唐朝普遍推廣廟學制以後,廟學之制遂成為此後傳統學制的基本型態。
不但此後宋、元、明、清諸朝的學制是如此,即連鄰近之韓國、越南以及日本的傳統學制也是如此。
因此,廟學制的成立,可以說是東亞諸國傳統的共通基本要素之一,在我國以及東亞教育史上實是一項重要的發展。
筆者將這種文化的共通現象,稱之為「東亞教育圈」。
其形成的時機,與「中國文化圈」(或謂東亞文化圈)一樣,是在七、八世紀的隋唐時代。
以下對新羅、日本、越南等地創建廟學制略作說明。
新羅方面,六八二年創建國學制度,其國學有無建置孔廟,史籍無明確記載,但八世紀以後從唐朝攜回「文宣王、十哲、七十二弟子圖,即置於大學」;惠恭王以後又常幸學(當含釋奠),聽學官講經,因此,頗疑景德王六年(747年)實施國學經學教育前後,當亦已建置孔廟。
《三國史記》卷四十雜誌職官下收錄「其官銜見於雜傳記,而未詳其設官之始及位之高下者」,其中有「孔子廟堂大舍」之職,足證新羅已建置孔廟,而此孔廟當如唐制建置於國學之內。
唐制孔廟,在國子監設有「廟幹」二人,其編制列于國子學之內。
(參看《唐六典》卷21國子監條目錄)地方官學之孔廟,如國子監制一樣,設有「廟幹」,員額不明,或只一人。
劉禹錫:
「許州文宣王新廟碑」(撰于開成元年,西元836年)(見《文苑英華》卷846)云:
「指蹤有役夫,灑掃有廟幹」。
則廟幹之職責在灑掃,或含看守等雜務。
無論如何,孔子廟本身是設有專人管理,唐制如此,新羅亦然;唐曰廟幹,新羅曰大舍。
高麗朝以後,直至李朝,廟學教育制度是共同的特色,歷代提倡儒教的學校教育以及定期在學校舉行釋奠之禮,可謂不遺餘力。
日本方面,其古代學校的創建,亦取法唐代廟學制的形式,所以大寶、養老〈官(職)員令〉規定大學頭的職掌,是「掌試學生及釋奠。
」(《令集解》卷3)〈學令〉也規定:
凡大學、國學每年春秋二仲之月上丁,釋奠于先聖孔宣父。
(《令集解》卷15)
於是大寶元年(701年)二月十四日丁巳有釋奠之禮的舉行,此爲釋奠之始。
(《續日本紀》卷2)至於聖廟的建立,史無明文,但《延喜式》(927年制定,967年公布)的大學寮式,規定釋奠儀式中,有「庿」、「庿司」、「庿戶」、「庿庭」、「庿室」、「庿門」、「庿堂」等場所(同書卷50雜式所載之〈諸國釋奠式〉略同);《本朝文粹》卷九、十收錄有關九、十世紀在孔廟(聖廟)釋奠後講經之詩序文多篇,可見聖廟在古代日本是存在的。
頗疑廟學制的建立,在大寶元年(701年)之前,既已出現。
神護景雲二年(七六八年)七月三十日,大學助教膳大丘自唐歸國後,建議仿唐新制,對孔子的尊稱,將孔宣父改爲文宣王。
(《續日本紀》卷29)《延喜式》卷二十〈大學寮式〉記載釋奠十一座,其中規定:
二座先聖文宣王先師顏子
從祀九座
這是有廟、有學與祭禮的具體說明。
越南方面,在北屬中國時期之實施情形,多無可考。
漢末之際,士燮出任交州太守,越南史臣吳士連以爲越南「通詩書,習禮樂,爲文獻之邦,自士王始。
」(《大越史記全書.外紀全書》卷3〈士紀〉)屬於吉禮之一的釋奠之禮,或於此時開始實施於交州。
但西漢末、東漢初,錫光任交阯、任延長九真太守時已創立學校,論釋奠之禮之起始,自然也可追溯至此,只是均無直接證據而已。
其明確而可靠之記載,當在李朝聖宗神武二年(1070年)八月之「修文廟,塑孔子、周公及四配像,畫七十二賢像,四時享祀。
皇太子臨學。
」的記載。
(《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全書》卷3〈李紀〉)「皇太子臨學」,當含主持釋奠之禮在內,而此時既已「修文廟,塑孔子、周公及四配像,畫七十二賢像」,則一O七O年之際,當已建置國子監及文廟。
易言之,此時當已完成了廟學制(含從祀制)。
廟學制是「東亞教育圈」的基本特徵;而「東亞教育圈」的存在,又是推動「中國文化圈」成長的基本動力。
這個文化圈的推動力與政治秩序的推動力是有別,後者是以中國為主動,他國為被動,而教育事業則由各國主動推展。
往後中國國力時有消長,東亞政治秩序也時有調整,但無礙於中國文化圈歷久不墜,究其原因,當是「東亞教育圈」繼續存在的緣故。
東亞教育圈在共通的廟學制建構下,其教育發展的特質,可有如下幾項:
1.漢字教育、2.儒學教育、3.養士教育、4.成聖教育。
後三項的成立,也還是以公、私或僧、俗方面實施漢字、漢文教育為前提,所以中國文化圈或東亞教育圈也可稱為漢字文化圈。
至於「儒學教育」,指教育內容以儒家經典為主;「養士教育」,指教育目的在於培養吏才;「成聖教育」,指教育理想在於成聖成賢。
所以東亞教育圈的教育特質,簡單說就是實施儒教主義教育。
學校以文廟為主軸而展開儒教主義教育的作用為何?
此即學校教育透過「廟學」形制的規範,使為師者身兼經師與人師,可視為聖賢的化身,學生學習的榜樣;而學子平時與廟中聖賢為鄰,又瞻仰為師之人格、學問,乃體會步登聖賢堂奧之境是有可能的,這也是東亞傳統共通的成聖教育特質。
以下擬就成聖教育再作進一步說明。
宋朝周敦頤所云: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又云: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周子全書》卷2〈志學章〉)
周子的希聖希賢說,影響日後教育理念甚大。
例如宋代四大書院之一的湖南嶽麓書院,除建有文廟以外,並有崇道祠,以供奉朱熹(晦菴)、張栻(南軒)兩先生,六君子堂以供奉地方良吏。
明末黃衷的〈嶽麓書院祠祀記〉說:
院舊有祠,以祀晦翁、南軒。
……文公(張栻)集諸儒大之成,以明聖賢之道,講學于茲,吾師焉;安撫(朱熹)于茲,吾師焉。
……夫所謂過化者存焉,吾祀之。
(《萬曆.重脩嶽書院圖志》卷8)
此處是說明書院建置祠宇,專祀先賢,以作為士子學習之典範,萬古流芳。
足見在教育園地裏,祭與學是分不開關係的,兩者皆成為「學禮」的主要內涵。
清.龐鍾璐《文廟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