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影视改编的话语分析.docx
《《三国演义》影视改编的话语分析.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三国演义》影视改编的话语分析.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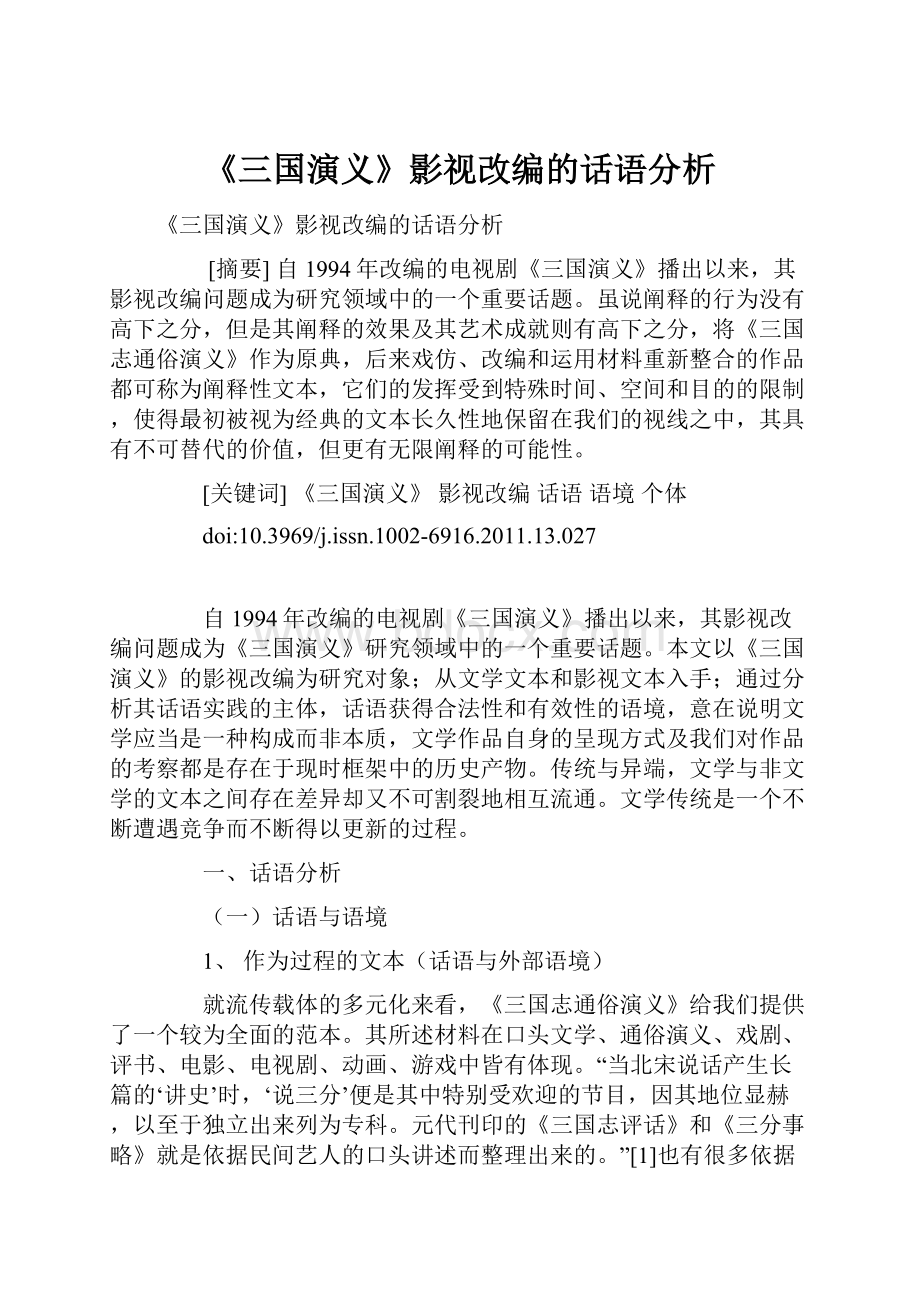
《三国演义》影视改编的话语分析
《三国演义》影视改编的话语分析
[摘要]自1994年改编的电视剧《三国演义》播出以来,其影视改编问题成为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话题。
虽说阐释的行为没有高下之分,但是其阐释的效果及其艺术成就则有高下之分,将《三国志通俗演义》作为原典,后来戏仿、改编和运用材料重新整合的作品都可称为阐释性文本,它们的发挥受到特殊时间、空间和目的的限制,使得最初被视为经典的文本长久性地保留在我们的视线之中,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但更有无限阐释的可能性。
[关键词]《三国演义》影视改编话语语境个体
doi:
10.3969/j.issn.1002-6916.2011.13.027
自1994年改编的电视剧《三国演义》播出以来,其影视改编问题成为《三国演义》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话题。
本文以《三国演义》的影视改编为研究对象;从文学文本和影视文本入手;通过分析其话语实践的主体,话语获得合法性和有效性的语境,意在说明文学应当是一种构成而非本质,文学作品自身的呈现方式及我们对作品的考察都是存在于现时框架中的历史产物。
传统与异端,文学与非文学的文本之间存在差异却又不可割裂地相互流通。
文学传统是一个不断遭遇竞争而不断得以更新的过程。
一、话语分析
(一)话语与语境
1、作为过程的文本(话语与外部语境)
就流传载体的多元化来看,《三国志通俗演义》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范本。
其所述材料在口头文学、通俗演义、戏剧、评书、电影、电视剧、动画、游戏中皆有体现。
“当北宋说话产生长篇的‘讲史’时,‘说三分’便是其中特别受欢迎的节目,因其地位显赫,以至于独立出来列为专科。
元代刊印的《三国志评话》和《三分事略》就是依据民间艺人的口头讲述而整理出来的。
”[1]也有很多依据三国故事改编的戏剧被搬上舞台,袁阔成、单田芳、姜存瑞等评书表演艺术家都先后演义过评书《三国演义》。
随着二十世纪初电影和电视技术的发展,传统的古典小说也相应地被搬上了银幕或屏幕。
聚焦小说《三国演义》全本的作品都在其推出后引起了“三国热”,如1979年袁阔成的评书《三国演义》、1994年王扶林导演的电视剧《三国演义》和2010年高希希导演的电视剧《三国演义》。
影视剧导致的“三国热”一方面是由于作为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广为流传,其中的故事和情节为诸多读者耳熟能详,人们被新的艺术形式吸引的同时,也在寻求一种与旧有认知对应的认同感;另一方面,在94版《三国演义》播出的时候,电视已进入越来越多的家庭,影响面日益扩大,互联网普及之后,传播与讨论平台变得更为开放。
由于《三国志通俗演义》小说在文学史上树立了经典的地位,接受者便习惯与以其为标准来评判其它形式的作品。
所以他们在最开始接触改编作品时,总会带着审视和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它。
但是我们眼中的经典不是定格的,一成不变的,经典之永恒不代表其媒介的永恒,在媒介更替的过程中,它在每个阶段的存在形式既是对作品本身存在的强化,又促进了文本的生成和发展。
在视觉媒介兴起,印刷媒介式微的背景下,改编行为本身与改编作品的存在即具有其对文学名著进行解读和完形构建的合法性。
2、从有机统一的情节到碎片化情节(话语与内部语境)
我们所讨论的语境除了文本在不同传播媒介中的存在与变化的外部语境外,还包括文本自身的内部语境,其中人物、故事等构成因素都融合统一到了情节的结构安排中。
小说和影视剧大都属于叙事艺术,所以情节结构起到统摄全篇的重要作用。
纵观小说名著电影改编的历史,前人对于情节、结构改编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简单说来就是神圣化不可随意改动情节→可根据具体需要适当修改→相对自由开放的情节观(如可不改动,亦可少改动,甚至可以解构、戏拟)从1994版《三国演义》到2010版,我们也可以看到改编观念从不可随意改动到逐渐多元化的发展倾向,但由于《三国演义》是历史性的小说,有其依据可考,故而改编是否忠实于原著或历史事实引起的争议自然比一般小说更大。
传统意义上的“情节”有两种倾向:
其一情节是一个有时间顺序、因果联系的故事展开,与人物无多大关联,人物性格在其中只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如侦探小说骑士小说;其二是以人物塑造、性格刻画为重,情节只是人物性格的发展史,要在人物性格的展开图中才能得以形成。
《三国演义》的小说即属前者,而影视改编作品倾向于后者。
影视媒介的视觉性特征决定了人物塑造对剧情的演进与整体刻画的重要性。
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将人物分为扁平和圆形两种,前者为类型人物,特征明显,容易辨认,后者则较为复杂。
在小说和戏剧中,人物形象大都被脸谱化、类型化了,看到“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的必然是关云长,白脸奸雄则非曹孟德莫属。
而在电视剧中,脸谱化、类型化的人物已经不能满足形象刻画和情节发展的需要,观众希望看到的是有血有肉的人物而不是机械出现的脸谱,故而电视剧人物性格的塑造更为复杂丰满,力图将人物的忠奸善恶都呈现出来,留待观众评判。
但比较来看,1994版电视剧仍然延续了毛评本小说尊刘抑曹的思想,每个人物都是贴好标签出场的,曹操就是奸雄,刘备就是忠诚,张飞就是莽夫,人物都随着既定情节的发展而完成自己的使命;相比之下,2010版电视剧中的人物则较为立体,每个人都是矛盾的统一体,没有绝对的忠奸之分。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情节的发展就是人物性格塑造的历史。
此外,影视剧不能如小说般依靠文字叙述线性表达构成的有机统一文本使接受者实现不同程度的理解,而是将人物、情节打碎到镜头的拼接和剪辑中进而完成情节的构建。
在这里,情节并不必然承担连缀全篇的责任,其因果链条作用的是各种因素打碎而重组的画面。
影像和文字的蒙太奇不必要是叙事性的,它只对我们看世界的方式负责。
如果在观看中存在理解事物本质的可能,那就必须借助于揭示事物和现象之间内在联系的感性表象,即银幕呈现给我们的场景。
小说和电视剧毕竟不同,如在改编处理上苛求一板一眼的真实则会损伤电视剧的连贯性。
1994版电视剧《三国演义》从小说中取材,情感基调、人物性格、细节构成、故事框架等都与小说基本一致。
不同的是,电视剧无法依靠任何有助于澄清情节的叙述性语言,而只能将叙述性作品中的各种要素打碎重组,以人物形象及其行动呈现在观众面前,以此连缀全篇。
2010版则更好地将这种碎片化体现出来,它几乎抛弃了小说“抛物线”的情节构造,情节总体上按诸葛亮之欲成大业之三步进行铺排,其中对人物、战场、事件的构造都有其目的性,主题意识淡化,而博弈、造势的情况随处可见。
(二)话语与个体
1、改编者
每一次改编都是一次话语实践,是建立话语的关系序列或关系网络的实践活动,改编者要考虑的不只是对文本的处理这一问题,还要关注所选名著作为一个特定话题在社会生活或社会制度中的存在情境,关注与其相关的知识、行为的各种形式,从而确定如何做是恰当的,如何做又是不恰当的,什么材料是相关的、可用的,还得考虑所针对的受众及何谓“真实”,何谓“忠实”等问题。
而每个人的知识水平和个人能力是不同的,所以在构成性的活动中,任何一个人都有权对经典作出阐释,但又要对这种阐释作出限制。
1994版《三国演义》处于崇尚改编尽量忠实原著的阶段,而2010改编从较单一的尊刘抑曹,忠义主打的价值观走向了多元化的价值选择,选择权掌握在编剧、导演、演员手里,同时也掌握在观众手中,其不以表达一种既定历史观为目的,其中充满造势、博弈等铺排。
与名著全本的电视剧改编相比,一些以三国为题材的电影价值多元化取向更为明显,如刘德华、洪金宝主演的《见龙卸甲》以赵云为叙述主体诉说了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感慨,从重视个体价值的角度出发解构了宏大的历史叙事。
而吴宇森导演的电影《赤壁》则完全只是挂三国的“羊头”卖娱乐的“狗肉”。
2、观看者
关于改编作品的受众,前人有专门撰文或在专著中花较大篇幅进行分析的,多从接受美学和心理学方面入手进行审美经验、期待视野等方面的分析。
而在网络时代,观看者已经不是单纯的接受者,而很多时候是以观看者、阐释者、谈判者甚至也可以是改编者的角色出现的。
斯蒂芬•葛林伯雷在《通向一种文化诗学》一文中说:
“艺术作品本身并不是位于我们所猜想的源头的纯清火焰。
相反,艺术作品本身是一系列人为操纵的产物,其中有一些是我们自己的操纵,许多则是原作形成过程中受到的操纵。
这就是说,艺术作品是一番谈判以后的产物,谈判的一方是一个或一群创作者,他们掌握了一套复杂的、人所公认的创作成规,另一方则是社会机制和实践。
为使谈判达成协议,艺术家需要创造出一种在有意义的、互利的交易中得到承认的通货。
”[2]评判者衡量这种产物的标准是多样的,可以是理性和学识,也可以是快感和兴趣,在操纵和调节的过程中,话语得到动态生成。
观看者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取决于其存在于怎样的话语关系网络中。
1994版《三国演义》推出时,正处于电视媒介的繁荣发展时期,且电视剧的创作态度是基本忠实于毛评本《三国演义》,创作态度也是相对严谨的,故而虽然在一些细节上有争议,但观众的评价还是整体趋于肯定。
而由于改编尺度较大,对原著研究不够,融入更多电视剧商业元素(如植入较卖座的英雄美人模式而将连环计一节修改较大)等原因,2010版《三国演义》一问世便受到了较大争议,但事实上其技术上的进步和一些新的价值观念的表现还是值得肯定的。
在这里,改编作品的优劣不是笔者想着重探讨的问题,毕竟欣赏和评价都是主观性很强的行为,而在评价时的思维方式是值得思考的。
观者通常的批评标准是将《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小说文本看作原典,甚至是正典,1993年电视剧版《三国演义》上演时便招来过质问与不满之声,而2010年版《三国演义》登场时,老版则被和小说放到了一边,作为评价的标准存在,这样一来新版就遭受更多质疑。
这是一种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势,与既定知识和期待视野出入较大的事物很容易先受到否定的对待,然后再从对比中确定是非。
笔者认为,在无法做到完全客观理性地对待批评对象的时候,这种“问题先行”的做法是可行的,我们宁愿相信真理是被保存在错误概念的残余形式中,从而以否定态度的力量为起点打破肯定的态势,探求不同于现实的另一种秩序。
但问题在于在所有传统和既定标准都不具有绝对的(或超越时空的)合法性的情况下,我们是否能追寻到无限可能的对比阅读呢?
所谓的正统与异端、经典与非经典只是个相对性概念,其与时空、审美、经济和政治等语境密切相关。
3、建构主义的文本观念VS解构主义的文本观念
无论是从改编者还是观看者身上都体现着建构和解构两种文本建构的观念,二者既对立又统一。
建构主义的文本观念将作品视为一个有机统一体,即一个相对封闭和相对自足的整体,在逻辑上文本所有内部构成要素间互相关联。
具体到小说《三国演义》来说,故事、情节、人物等要素之间并不存在从属关系,而是相互并列、相互包含的关系,这就意味着其为接受者创造了多个欣赏点和较广的阐释角度。
尽管如此,小说还是被当作一个整体来欣赏的。
而解构主义的文本观念对有机统一性没有这么严肃的要求,不强调各个组成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如二十世纪以来淡化情节、模糊人物性格的西方现代派小说,创作者可以更为自由地根据目的来进行操作和抒发情感,在这里读者也能发挥更大的能动性,创造空间更大。
二、对经典作品影视改编的态度
我们所接受的“文学传统”是由经典构成的。
经典“是‘永恒的’,但也是历史的。
它有一个可以描述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不是别的,而是一件特定的艺术品在历史上一系列的具体化”。
[3]经典不仅是作为图式的传统上的一个坐标点,其更应“包含一种可以超越它的具体时代背景而覆盖到后代的超越性,也一定会有超越它的具体描写内容和主题的,可涵盖到更广泛社会生活的普遍意义。
”[4]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意识形态的自觉主导下,各种传统中经典的组合序列都只是文学传统诸多外延的一种,而不直接指涉内涵。
面对新的视觉生存环境,每一次戏仿、改编和运用材料重新整合的作品都是一次阐释,虽说阐释的行为没有高下之分,但是这种由文本形式展示出来并公开发行、产生公众效应的阐释的效果及其艺术成就都是有高下之分,所以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无可厚非。
笔者认为可将业已成为经典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作为原典,后来戏仿、改编和运用材料重新整合的作品都可称为阐释性文本,它们的发挥受到特殊时间、空间和目的的限制,使得最初被视为经典的文本长久性地保留在我们的视线之中,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但更有无限阐释的可能性。
注释
[1]罗贯中.三国演义(嘉靖本)[M].长沙:
岳麓书社,2008:
2.
[2]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4.
[3]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M].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165.
[4]张荣翼.文学经典的类型及其意义[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
1.
作者简介
袁晶,武汉大学文学院文艺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