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苦短幸福绵长.docx
《人生苦短幸福绵长.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人生苦短幸福绵长.docx(1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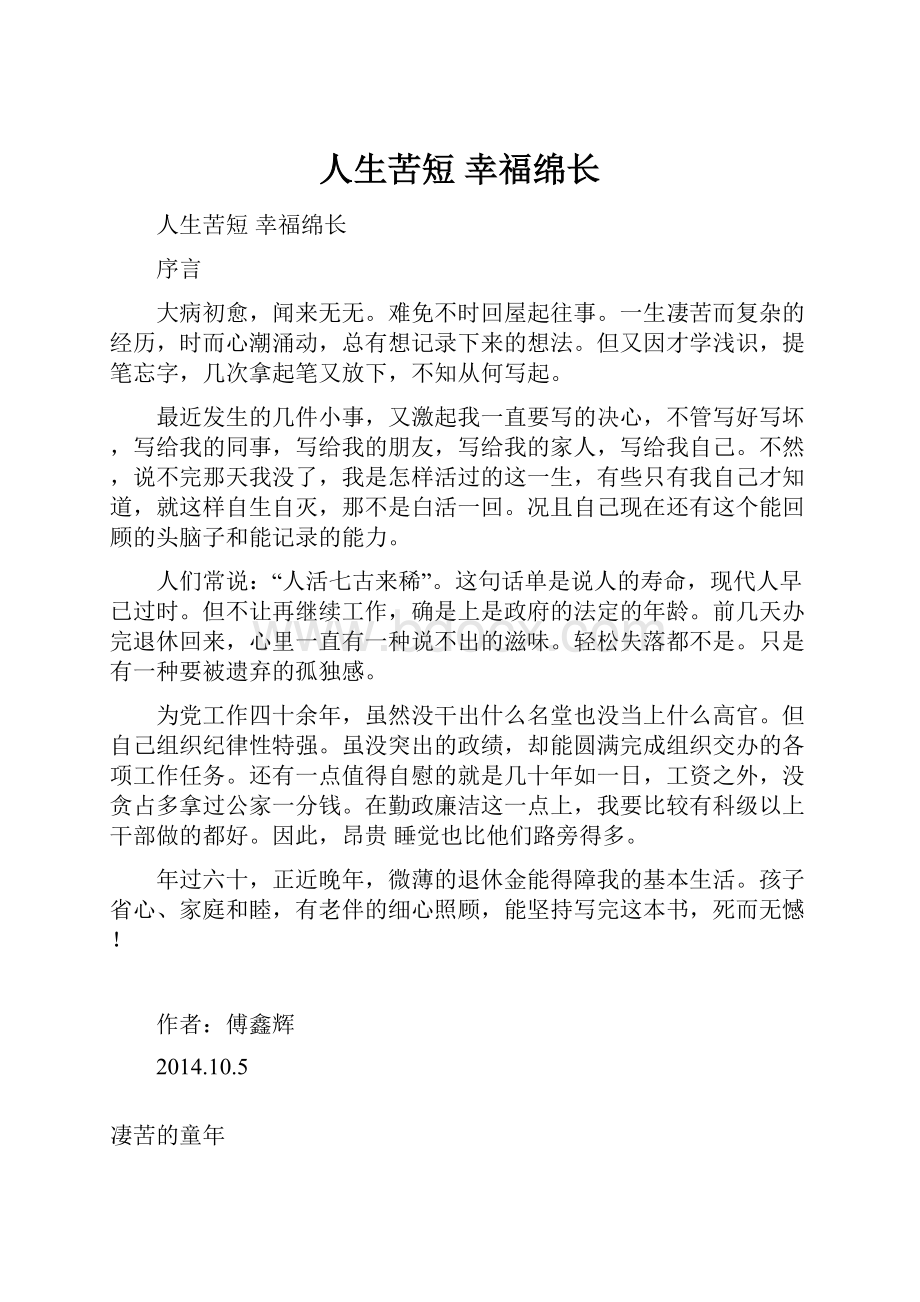
人生苦短幸福绵长
人生苦短幸福绵长
序言
大病初愈,闻来无无。
难免不时回屋起往事。
一生凄苦而复杂的经历,时而心潮涌动,总有想记录下来的想法。
但又因才学浅识,提笔忘字,几次拿起笔又放下,不知从何写起。
最近发生的几件小事,又激起我一直要写的决心,不管写好写坏,写给我的同事,写给我的朋友,写给我的家人,写给我自己。
不然,说不完那天我没了,我是怎样活过的这一生,有些只有我自己才知道,就这样自生自灭,那不是白活一回。
况且自己现在还有这个能回顾的头脑子和能记录的能力。
人们常说:
“人活七古来稀”。
这句话单是说人的寿命,现代人早已过时。
但不让再继续工作,确是上是政府的法定的年龄。
前几天办完退休回来,心里一直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轻松失落都不是。
只是有一种要被遗弃的孤独感。
为党工作四十余年,虽然没干出什么名堂也没当上什么高官。
但自己组织纪律性特强。
虽没突出的政绩,却能圆满完成组织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
还有一点值得自慰的就是几十年如一日,工资之外,没贪占多拿过公家一分钱。
在勤政廉洁这一点上,我要比较有科级以上干部做的都好。
因此,昂贵睡觉也比他们路旁得多。
年过六十,正近晚年,微薄的退休金能得障我的基本生活。
孩子省心、家庭和睦,有老伴的细心照顾,能坚持写完这本书,死而无憾!
作者:
傅鑫辉
2014.10.5
凄苦的童年
一九五四年八十二八日,在一个雾雨懞懞的早上,山东省元城县城南四十里鹿官屯傅家大院四爷傅登科的第五个呱呱堕地,取名京辉。
当时正值新中国刚成立不久。
往过十几年战争的洗礼,到处还是伤痕累累。
一切都在恢复之中。
开国际风云变幻,我们的苏联关系一度紧张,还要勒紧腰带还债。
同时党内还利起各种妖风。
让国家决策的领导人得不到真实的下情。
什么虚报,浮夸风,坑苦了不少的老百姓。
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三面红旗的照耀下,全国人民正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很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
还有部分地区要踏步进入共产主义。
老百姓称之为公社社员。
公社以下的树屯为生产大队和生产队。
一九五七年,上级命令,以生产队的单位成主食堂,社员集体用餐,日用口按需分配,一家发牙膏一盒,每人发牙刷一枚。
领时一家一户到食堂窗口打饭,盛菜。
蹲在生产队院子里,一围就是一顿饭。
晚上是前街搬到后街后街再串到前街住,谁也不甭想回自己家,主要是怕农民家里藏粮食。
各家各户做饭的铁锅都拿走砸碎,名曰:
大炼钢铁。
一年到头社员起早贪黑,辛勤劳作。
生产队长喊着空口号,会计打着假算盘,工作队员写着假材料,工作队队长向上级做着假汇报。
欠收说成丰产,丰收吹得甚是没边。
他们的口号是: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本来只能产300厅,你敢说超千,就有人敢说超万。
尽管是丰收年,但农民生产的粮食,却大车小辆地运往了站台。
经过仔细地筛选,优质饱满地装进标准袋,运往了苏联抵债。
给农民留下的,仅是些劣质的稗谷和微少的高粱。
从此地瓜也就成了各地农民的主食。
并一直维持了足有十五年。
从我记事开始,农民就一年到头,上顿下顿全是吃地瓜,早晨煮地瓜块粥,中午是地瓜干窝头,晚上是地瓜石糊糊,吃得我们这些还不太懂事的孩子,到吃饭时直身条,但肚子饿得叫唤时还得硬着头皮去吃。
别看现在人偶尔吃一次地瓜还觉得挺新鲜,挺香满好。
但常年累月的吃一种食品,谁都会吃弱的。
可以说在我们那地方象我这年龄的都是靠吃地瓜长大的。
因此大部分人体较弱。
但毕竟地瓜还是养活了不少人。
这里还得说一说,屯子北边一块胡萝卜地救的人故事。
一九五八年晚秋,随着社会主义大食堂的倒闭,社员们扎脖啦。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当时的清除一切姓公的障碍,老百姓住了几辈子的房子不是自己家的啦,前街人要搬到后街去住。
只带行李和衣物,锅灶早已拆掉,做饭用的锅都拿去砸碎炼起钢铁。
听老人说当时的五大妈把一眯粮食藏在了枕头里,半夜时分、孩子饿得直器,大妈用茶缸给孩子煮了点饭,不知怎么被队长知道啦,第二天一早、队长就带人来搜查,野外都翻了遍,没招聘后把院子挖地一尺。
那阵势,不亚于当年小鬼子搜查地下党。
从此以后,只要发现谁冒烟,队长就带人去搜查,再也没人敢在家里藏粮食。
所以生产队食堂从不定量到定量,从定量到关闭,社员家里又什么吃的都没有。
人们常说“人是铁、饭是钢,一天不吃饿得慌”。
于是,人们想起了屯北的一块萝卜地。
因当年霜冻来得早,胡萝卜长的虽好还没来得及刨就冻在了地里。
社员们使不约页同地来到这地方,因都饿着肚子没力气、只能用小锹、板角之类的工具,今天挖出一小块,明天再按下一截,一根胡萝卜分几次才能挖到根底。
每天这块地里黑压压的全是人,不到十亩地里挤满了足有几百人,每家刨回半筐回家用,洗脸盆一煮,全家人各吃几块这半生不熟的胡萝卜,一天就算挺过去啦,第二天早起又去刨。
一次只能刨出一小块,就这样人们一直刨到第二年开春冻化才刨出根。
没有了胡萝卜,人们开始吃树皮、草根,一夜之间村里的树干由皴绿变成黄白,有人想起曾在吃食堂时扔进烘池里的地瓜皮,也想法翻出来,不管酸、梁、苦、臭,凡能填肚的都吃啦。
但可怕的死亡还是陆续降临。
大命的奄奄一息,因严重的缺乏营养,勉强活着的得了两种病。
一种是水肿病,身上大腿肿得象汽吹的一样,严重的张裂着淌着水。
另一各是瘦铁病,黢黑的皮紧紧地包着骨头,一点点脂肪没有,骨瘦如紫,两眼垢直,象猴子,又象枯髅。
短命的经常起折腾将一个接一个地死去。
今天张家老太太死啦,明天王家老头咽了气。
后天老李家的侈和守灵的儿子死在了一张床上,真是命苦啊。
老百姓没死的只能扶着墙走道,大部分竣躺在家中,无力帮忙的死者处理后事,每个村只能由生产队长和会计等几个人用席筒卷着尸体一个又一个拉往村头,扔在乱死岗子上,任凭乌鸦、小鸟、餐食和烂掉。
过后,曾有人统计过,就从食堂倒闭到第二年定量供应,中间八十多天,人们就没见到过粮食全靠野草、树皮,艰难度日而真没挺过去饿死的三百伍拾柒人。
第二年春天,国家开始拨发返销粮。
每人每天按四两供应。
虽吃不饱但饿不死,勉强维持能保住性命。
为恢复生产,青年成立了突击队,吃住干活在一起,姐姐当年十七岁,是一名突击队员。
记得姐姐有一天自然到家告诉我晚饭时到她们食堂栅栏外边拿小罐等她又勿勿返队。
天还没黑我提着小罐便来到了栅栏旁。
开饭时,我看姐姐从食堂出来端着盛满汤的碗直奔我藏身的地方,我背过小罐,她把汤倒进去,又示意让我再等一会,姐姐又返回食堂去,不一会又端来第二碗小罐装满啦,让我赶快回家。
姐姐却没再进食堂,拿着空碗直奔了宿舍。
我跌跌撞撞地回到家妈妈把姐姐省下来的汤分给在家所有的人,每人都喝上几口算是晚饭,肚子热乎乎的,但姐姐却干了一天的活为了爸妈和弟兄自己饿着肚子。
姐姐长得不算十分漂亮,也不算丑,中等个头,大大的眼睛,乌黑的短发,得理不让人。
是个性格倔强,干什么都不服输的人。
早早地加入了共青团,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后因家庭出身中农,在入党的问题上受到了挫折,因孩子多再加上父亲重男轻女也没让读书,虽没成就大学业、但懂得早,能操心,帮父母照顾弟弟,维护家庭,功不可没。
还记得一天中午,姐姐回到家看妈妈躺在病床上上,搂着刚刚出生不久的小羊,因妈妈舍不得吃东西,当然也没有奶水,饿得弟弟嗷嗷直哭。
大一些的爬在床边,爸爸去外地买粮去啦,家里什么都没有。
姐姐看看粮囤是空的,揭开锅盖是凉,急啦!
随即叫着我二哥、三哥,拉着我说,满地黄橙的麦子就要成熟,不能眼睁睁的让饿死,走;都跟我下地支。
因为把守森严,所有的路口都有民兵和护炫粮员把持,出去容易,但要想带回东西就难上加难。
老百姓回来不管是筐、篓、布袋都要仔细检查一遍。
姐姐念头我们来到麦地,往里走别人几乎看不到的地方,捋下麦穗让我们边搓边吃,哥几个边带面,狼吞虎咽一个时辰就吃了半饱,怎么能带回一些呢?
于是姐姐开始给我往衣袖里、裤兜里,前后身上,塞个圆满满圆。
因为小麦有麦网,一走顺刺上下左右走动,于是刚走不远、麦穗头就溢满全身,指导在身上、脖子上、腿变部,也不说痛、不嫌痒。
姐姐、哥在能藏的地方也者放了一些到了卡口,姐姐提前就把门的打热乎,没细松查便马马虎虎地过了关。
到家后,我一下就躺在地下累的已没有一点力气。
任凭妈妈把身上的麦穗都掏出来。
搓粒上磨、推奞、点火煮了满满一锅麦仁粥,全家都吃了一顿饱餐。
记得我当时才3岁,吃喝了四小碗,肚子撑得圆圆的好像要爆炸、还想喝怕撑坏,被妈妈劝住啦,请备、明天回来一定能带回好。
我才不要、走出厨房、到院理粪坑边尿泡尿,回屋就睡着啦。
那在夜里我帮了一个梦。
爸爸回来啦,带回那么多好吃的,我还把从来没见过的饼干分给别人家的小朋友,十分满足。
昨天被麦网刺伤了大腿里子,又被憋不住尿湿的裤子,泣得直痛,勉强忍着、不敢说、也不想哭。
只是尽量避开别人的目光,不让他们看出一为,不到半天暖干啦,一切正常,才舒了一口气。
第二天,爸爸走了一夜的路,一早就到了家。
背着他排了数次才排除买回的半袋饼干和姑姑帮助买到的两瓶奶粉,救活了我们和弟弟。
几天后,爸爸又得离开家到四百里远的省城济南去排除啦。
每次往回近干里都是步行。
真了不起!
爸爸走路是高手。
为了超近、专走小路,遇山爬山,遇河趟河。
爸爸过河,顺热抓两捆高粱秆往前一扔,一个箭步十几米水中间,稍赶上,轻轻一点,象青蜒点水,飞一样就过去啦。
爸爸虽然个子不高,但有一个强健的体魄,平时很少说话,量一个极严以律已也亚以待人的将军范,虽然并没有打过我们,可我们都怕他,他在家时谁也不敢大声说话,更别说打闹啦。
但他除了吃饭又很少在家,从我记事起,春、夏、秋三季都是穿着白、黑裤子,干层底的圆口黑布鞋、出门戴一顶草帽,走路快而轻,走去象一阵风。
街坊邻居都管他叫四爷,男女老幼都非常尊重他。
解放前当过邨子的保长,又曾以伪保长的名誉为共产党卖过命。
我家杂货店是共产党人地下联络点、曾和解放后成为地区专员的郑鲁民被国民党抓去戴过一付脚镣子。
大军南下时因奶奶有病没随军页去。
土改时被列为中农成份。
以致后来文化大革命时被当成保皇派去揪斗,被我们哥几个强行阻拦。
因此哥几个的政治命运也都不同程度的受到影响。
大哥京华、中等个儿,一双黑又亮的眼睛显得格外精神,乳名黑孩子,其实长的很白静。
因天资聪慧,父亲因忙于外边的事。
十四岁地就让他当了杂货店的掌柜的。
后因染上赌博的恶习,三年不到就把杂货店输个净光。
后来被父亲送到天津一个远门的叔叔家,在一家被板厂当学徒,虽然仅干了三年又改了行,也为他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石。
二哥京宪,长得英俊潇洒,四方大脸上一双大大的眼睛忽煽忽煽地相个武官,因安份听话,爸爸培养他一直念书,是我们屯子少有的中学生。
在最困难时期,为把在学校省下的干部送回家给弟弟们吃,怕被发现都是在晚自习息灯后以上厕所的名意往返16华里,把半块半块的干粮交给母亲,简单说两句话,歇都不能歇一会,转身又消逝在夜色里。
三哥京玉比我大三岁,从不眩光傻乎乎的,但有力气。
没念几年书就下来帮家里干活,小时候我俩在一起的时候最多,他打我疼我的也最多。
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这三是要命的坏年头。
天不是旱得冒烟,就是阴雨连绵,自然灾害造成如之人为的饥饿病变,我们屯子走的走、逃的逃、死的死、仅剩的还不到一半。
近两千人的大屯子白日里已看不到有几个人在晃动。
五家胡同的七户人家已死绝五户,仅剩下两户三口。
活着的人只能扶着墙跟走,站不起来的只能爬行。
为要一口吃的,记得屈街上的东泰老哥爬了将近两个小时,到我家其实不到半里路,呼喊着我妈、嬸子给口吃的吧,我母亲赶快拿出那筐地瓜干,让其吃饱再拿点回去,可怜那,天灾人祸,人们活得是真难啊!
一天晚上,我还同睡着就听爸爸和妈妈商量说:
“卖柏林的钱眼看也花光啦,剩下的几个钱也根本买不到东西地瓜叶子已涨到八毛,杂粮五块钱一斤,黄豆按粒查着卖,咱这一大家人家,小的太小,走也走不动,往后日子可怎么办哪?
特别小五、小六,一个刚过两岁,一个还不到一生。
妈妈舍不得吃饭,那来的奶法,小六往常是嗷嗷待哺。
妈妈只能给熬点衡粥式喂点清水,爸爸沉默了半天,说把小六送人吧,所赛诗的五叔说,他有个表倒夫妇是一对老师,不会生养,想要个孩子,把孩子送给他们不能遭罪。
“妈妈不吱声,爸爸又说了不少的话,怎么也比在家饿死强吧。
”妈妈还是不说话。
是妈妈不通怀理还是母子连心、弃子心痛啊!
看着妈妈满脸的泪水,爸爸也没再说话。
又过两天,爸爸让妈妈多做几个窝头,当盘缠背起弟弟邻居着三哥和我上路啦,把我们哥俩要安排回老家鱼名瞳里去,看是否能维持一下。
我当时年仅五岁,又是头一次出门走远路。
走了不远脚上就磨起泡,不到半天就肿起老高。
刚过巨野就走不动啦,歇一会吃点东西,一步三拐的再往前挪。
已低头走,招眼往前一看。
东边半天黑云密布、高低处齐边齐沿,波浪起伏,我惊叫起来,和爸爸说:
爸爸,是不是要来雨啦!
咱也没带雨伞,赶快找个地方避雨吧。
“爸爸却笑着说傻孩子,那不是雨,是山”。
出生在平原,没见过山。
错把青山当作乌云。
着实吓了一跳。
爸爸又说“那是大山头,今晚咱们就住在那里。
快些走,早些到回许能喝上店里的勿拉汤。
”我长这么大,也没喝过,心里想着勿拉汤的味道,脚步不由自主地加快啦。
带着两脚的血泡,过到大山头山脚下的店铺里,已是晚上七、八点钟,汤是没喝着,我也没闹,一头扎进草铺上,忽悠一下就睡着啦。
爸爸给我脱鞋洗脚,我全然不知中。
第二天,天刚放亮。
爸爸就把我俩叫醒,说起来又要上路啦。
头一天仅走了六十里,还有一百多里的路程要走。
可是我起来穿上鞋,脚刚一着地,脚疼的就受不了啦,我咬牙又强走了几步,疼地就中跪倒在地,我正要爬起,爸爸顺势把我抱进怀里。
把所有和干粮交给三哥,把我背起来继续赶路。
又不知走了多远,三哥看爸爸累得也是满头的大汗,想试着替爸爸背我,但一个七岁的孩子即使再有力气背一个五岁的能走多远。
……。
这一天,当我们走到离老家还有二十里的鱼台县城,天就大黑啦,虽然三大爷在县医院里当大夫,我们却没去找他。
爸爸给我俩商量是住县走,我却高声说,咱们走马。
三哥有点饿啦要吃的,爸爸主我们在路边等着,不在会弄过两碗丸子汤,泡上自带的干粮吃饱喝足又上了路。
当我们到达老屯子集时,天已快半夜时分,爸爸敲开我大娘家的门,傻哥哥给开门我们都进了屋,爸爸让大娘给两个孩子安排睡下,自己却又不知走了何处。
大伯早已去逝,扔下大娘和傻哥哥,孤儿寡母基本是没有生活能力,她娘俩成了生产队的无保户,说五保就是每年能给些吃的送点紫草,远一些的叔叔大爷,谁家也不宽裕,那家的粮食都不弱吃,那有我们的份,只是能帮助给照顾一下。
第二天,我们小哥俩就开始了自谋生路,邻居这家借给把锹,那家借给了筐,跟着大伙下地刨尊根去啦。
这里有刨不尽的算尊根,将一下泥土放进嘴里能嚼出甜味,但不能咽下,顶不了饿。
还有一种牵牛花粮,虽然很难刨多少,但洗净煮熟的象地瓜,甜而有点面,吃多了能当饭,刨起来费劲还刨不多少。
浅处的早已让人刨走,必须在一尺以下部位才能刨到。
第一天我们没刨到多少,尽管三哥还算有点力气,但找不到长根的地方。
刨累了就回到家,回到大娘已给安排好的小屋住下。
我煮熟了刨回来的牵牛花根和三哥俩连根带水都喝下、便睡在了地铺上。
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清晨,不知爸爸几时回来的也睡在我们身旁边。
并带回不多的粮食。
早饭后爸爸说还要去什么屯子要一要过去他们曾欠我们的钱,没钱能多少给点粮食也好。
爸爸走啦,我俩也各自拿着工具下地,重复着等明天的生活,三哥刨,我跟着检。
这一天我俩走的特别远,在一个小土坎边上看到上边有几根牵牛花秧,三哥就起动地刨起来,深处也没刨到多少,但在半米的下却刨出了白花花的横七竖八的花根,三哥热的满头是汗,我也捡得分外高兴。
这一天我俩大半筐,回到家煮熟后还给大娘和傻哥哥送去一碗。
开不过,象这天能刨到吃的心情并不多,有时为了先地方,小哥俩发生争执,三哥理改不过我有一次还狠狠地打了我,我嚎淘大哭起来,周时又想妈妈、弟弟、爸爸也不知道,哭到伤心处,怎么也控制不住,三哥以为把我给打疼啦,又过来抱着我的头,也失声痛哭起来。
并劝我“小弟、不哭,以后哥再也不打你”,回家见到爸爸我并没有告三哥的状。
以后,三哥再也没打过我,爸爸不在时,很多事情他总是听我的。
当时我才只有五岁。
也是在这一年,我学会了游泳。
论学,其实谁也没有交过我。
是有一次,我和三哥有两天没看着爸爸啦,听大娘说可能是在后屯等着欠账的人家在凑粮食。
我想爸爸等不了啦。
长时已近中乖,骄阳直晒大地,晒得大地都滚烫的,没林荫处,然车人们身上,脸上,火辣辣的地疼。
但我还是不大孩子他们的劝阻径直奔爸爸去的方向跑去,走着走着,大约起八七里路的光景,前石横着一条河,大约有十几米宽。
我东西看看,没有尽头,也没有桥梁。
怎么办?
恩父心坎,加上生死不怕的性格,索性脱下衣服和鞋子,用一只小手托举着就下了水。
趟了还不到两米,脚就不着地啦,水已过腰齐脖人就要倒时,我不顾衣眼的干湿,两只手和两条小腿都动起来,紧着往前扑腾,决不回头。
从水温感觉到河中间部位是有两人深。
我奋力前游,很快就游到了对岸。
穿上湿露露的裤叉,手拿着上衣和鞋子,踏着横垄地,向着那隐约可见了的屯子奔去。
屯虽然不大,也有几十户人家,爸爸在哪里?
我进屯就哭喊起来“爸爸、爸爸!
”有人听到哭喊声,出来问“谁是你爸爸”?
“付登科”。
这人挺好的,进我家先吃口饭,然后我帮你找,虽饭时已过,我并没感到饥饿,那人家饭桌上也只有一个树叶团子和半块棉籽饼,还有一个在车喂牛的老人没吃,所以我只喝了他家中碗开水,等这位叔叔念头我在屯里找我爸爸时,有人告诉爸爸早已回家啦。
叔叔告诉我怎么绕有桥能过河,我都没听进去。
在村头,我告别叔叔,还是我来时的路,趟河回家。
回去过河时,心里有了底。
自认为自己已会游泳。
多深多远的水也不怕,并用一只手拿着衣服和鞋子,高高地举过头顶;用另一只手和两只脚慢慢趟水过了河。
到家时,天色已晚,不管爸爸和哥哥怎么责怪我,我都没感到委屈。
因迷次去找爸爸,学会了游泳,换批评是值得的。
爸爸要回了半袋粮食。
用不磨破碎后,给我俩蒸了一锅干粮,让我们阴天下雨蚀草根时充饥用。
其余的要送回家。
因为妈妈及弟弟还不知怎样度日,后来听说爸爸回家后还是把三岁的五弟送了人。
表叔本还是抱六弟的,但因五弟总跟人家套近科、闲搭话。
另外比小的要好伺养,说话间就把五弟给领走啦。
爸爸送到村头,说五弟坐上爸新爸爸的自行车,头也没回就让人家给拖走啦。
五弟被送走后,妈妈成天以泪洗面。
两天没吃一点东西,总说“死也要死在一起”。
第三天,爸爸不得已又去把五弟接回来。
其实我也曾送过人。
只不过是自己偷跑回来的。
也是在那一年,爸爸带着要回的粮食回了家。
把我和三哥留在了疃黑。
可能是爸爸走前曾给本家亲属留过话,说:
这年头孩子多,连口吃的都很难弄到。
有今天、没明天,总不能把孩子活活给饿死吧,如果谁能遇到要孩子的好人家就把民小四送出去,逃个活命吧。
所以爸爸不久,有一天、有一个叫“大蝴”的叔叔过来领人啦。
说根据登科哥的意思,我给小四找了个好人家。
是谷亭东南牛寨大队支书牛万金家有一个女儿,缺个儿子。
生活能不错。
我找人说好啦,让赶快送过去。
就这样,在爸妈都不知情的情况下,我大娘当家把我送到了远离老家四十五里选的牛家。
当时我懵懵懂懂,直听大人说送人是好事。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跟这们胡口中听到牛寨。
过到大队部,说支书在车开会。
我们在门口小房等着。
看屋的还给我们倒了碗水。
晚饭时,我跟这位牛爸爸回到了他家。
牛爸牛妈已年近五十有五,有一个女儿二十大多还没出嫁。
一面青的砖房,摆满古老的桌椅的橱柜,屋子不大,收拾得倒也干净。
牛妈和姐姐好象并不欢迎我的到来。
总偷偷打量我这个远道而来的孩子。
我虽然已快六岁,但长的瘦小,眼睛不大,眨巴眨巴的象个精灵。
邻居都说过:
小四不长个,是让心眼给附住了吧。
我也细细地观察着她人。
偷听着他们的对话。
牛妈曾说“这孩子太精,怕养不住。
”牛爸说“不诽个儿子,将来谁咱摔分子打帆”。
姐姐说“这孩子长的太干瘪,一点都不水灵。
养些日子看吧”。
总之,他产对收养儿子有不同的意见,我的自尊也受到了伤害。
心想,走着瞧吧,晚饭后,牛爸爸从里屋里走出,喊着给我起的名字“牛福,走,去队部睡去”。
当晚,在大队部好大的一个土炕上。
我紧挨着牛爸,睡在了炕头。
炕中和炕尾睡着值班干部和打更老头。
刚一吹天油灯,就听见牛爸打起喷嚏。
紧接着是值班民兵连长叔叔,你哼他哈你吹他喝,最后上炕的是打更尧头,但最后睡着的是我——这个方居异乡想心及的孩子。
第二天早上回到家时,饭妈妈已做好。
姐姐正洗脸化妆。
我和牛爸坐车饭桌前,我什么也不敢动,牛爸给我什么就吃什么,好不自然。
其实他们家吃的也是粗粮并带着糠菜,只不过能吃饱罢啦。
吃过早饭,爸去公社开会啦。
牛妈让我去搂柴和我扛着爬子和竹筐出门不知往好走、顺着一条沟沟沿是一排排杨树,我搂了大半天的树叶,吃力地从老远的地方扛到家,摆放在院子的角落里。
下午还要去搂,倒也可以。
让我生气的是,中午吃的是我在家时就吃弱了的棉籽饼。
因为棉花籽的皮和棉花吃进肚里、干燥。
大全里一个蛋一个蛋、稀稀拉拉,拉也拉不尽,憋着实在难受。
我最愿意吃的是石条。
在家时,有时自己躺在床上两三天,妈妈不给做一碗石总是不会好。
只要吃上那碗点了点油的石条,立马就能起来唱歌,在牛家,我多想能吃上一碗热腾腾的石条啊。
但是已经三天啦、上顿下顿基本上总是一样的饭菜,再馋那也不能说要石条吃吧,真没耐力!
更让我生气的是,无意中发现小猫正在吃奶奶吃剩下的三条盒包蛋,我搂回那么多柴禾,还不如一只猫。
已是来牛家的第四天。
下午,我扛着笊子拉着筐,又出了家门。
漫不精心地往前走着,想着走的很远、很远。
想着这里没有我的亲人、牛爸对我还好,但他总不在家。
牛妈和姐姐并没有把我当做他们的家人。
同时我又想起了我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和弟弟,我要回家!
一个念头,就是一个决定,把笊子往沟里一扔、罗筐一甩,朝着来时的方向,直奔老家的路。
从牛寨到县集,没啥途老寨、谷亭、闫集三个乡镇,十多个村屯。
四十五里路。
那时我那知足。
只记得大致是从东南往西北的方向。
跑一阵,走一阵,已走过不少村庄。
道上路过的不少的妇女和老人,人出人意料以为我是追逐大人的孩子,谁也不问,我感觉应走了一大半路,天渐渐黑下来,我虽然累啦也不敢停歇,坚持向前,向前走着……,走到离家还有十五里的谷亭镇,天真的黑下来啦,星星点点的路灯已亮起,我又累又饿,一步三倒地来到一个饭店门口,隔窗看出有一伙人吃完饭往外走,我便挤进了去,在服务员没弄清我是走还是来的那伙人的领来的孩子时,我马立地端起桌上剩下的菜汤和扔在旧相的半块馒头,狼吞虎咽,两三口吃下,又一溜烟似的跑出来,向东缕缕走我回家的路。
一出谷亭镇,天真的黑啦,黑的伸手不见五指。
在那黑的森人而又无声的临时,我疾步,走在田间小道上。
根本遇不到行人。
有时看这到处象萤火虫似的几处昏暗的灯光,知道又快到了一个屯子。
再走过一个村庄时,竟连一点光亮都没有,因为人们都已经入睡。
穿过屯子不远处顺路就来到了河边。
哦,我忽然感觉不同,水都是那样亲切。
对面就是我要回的老家。
这是一条很宽的河,风一吹水波荡漾。
绕屯流得很远,有一眼看不到边的感觉。
白天只能隐约看到对岩的村庄和树。
在这有唯一的一个渡口,每天接送着老家出来进去的人。
摆渡的是我本家的叔叔付登云,在我到这时,早已没有了行人。
叔叔能否在对岸,我抱着希望大声喊起来“登云叔叔、登云叔叔”,“我是京辉,我回来啦!
”叔叔还真的没回家,隐约能听到对岸一个小孩子的喊声,再仔细听,听出是我的声音,便回了音“稍等一会,我马上就过去”。
听我叔叔的声音,我感觉真的到家啦,激动得快要哭出来。
等一会上了叔叔的船,上岸后又把我送回家。
到大娘家的下屋里,三哥蜷缩在地铺的一角早已睡着啦,听到我拽窗子门三哥忽地坐起来。
听到是我的声音,三哥说是弟回来啦,真想死你啦。
“我说”我也想您“。
于是,小哥俩又抱头痛器起来……。
我回来后,牛家也没有找,老家也没有人细问原由,一切就象没有发生一样。
但在我的心灵等处,却留下了一道永远也抹不去的阴影。
没过几天,爸爸捎信来,说让我们跟大山头姓氏的哥俩搭伴回家去,我高兴极啦。
一天早晨,天还没亮,我们就动身啦。
拿着头天上大娘帮蒸的几个菜团子作为路上的给养,开始了回家的行程。
在家兄弟都膀大腰圆的大小伙子,用木制的手推车,一边装着行里和给养,一边空着老大的小姑娘,看样子比我要小一两岁,起初大家走得都挺起动。
我什么也没拿,紧跟在大家车子后面。
三哥背着行里和干粮袋,大步推车在后,小的在前拉车。
谁也不说话,一直往前走。
只听到木轮车吱吱扭的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