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以撒散文精选.docx
《朱以撒散文精选.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朱以撒散文精选.docx(2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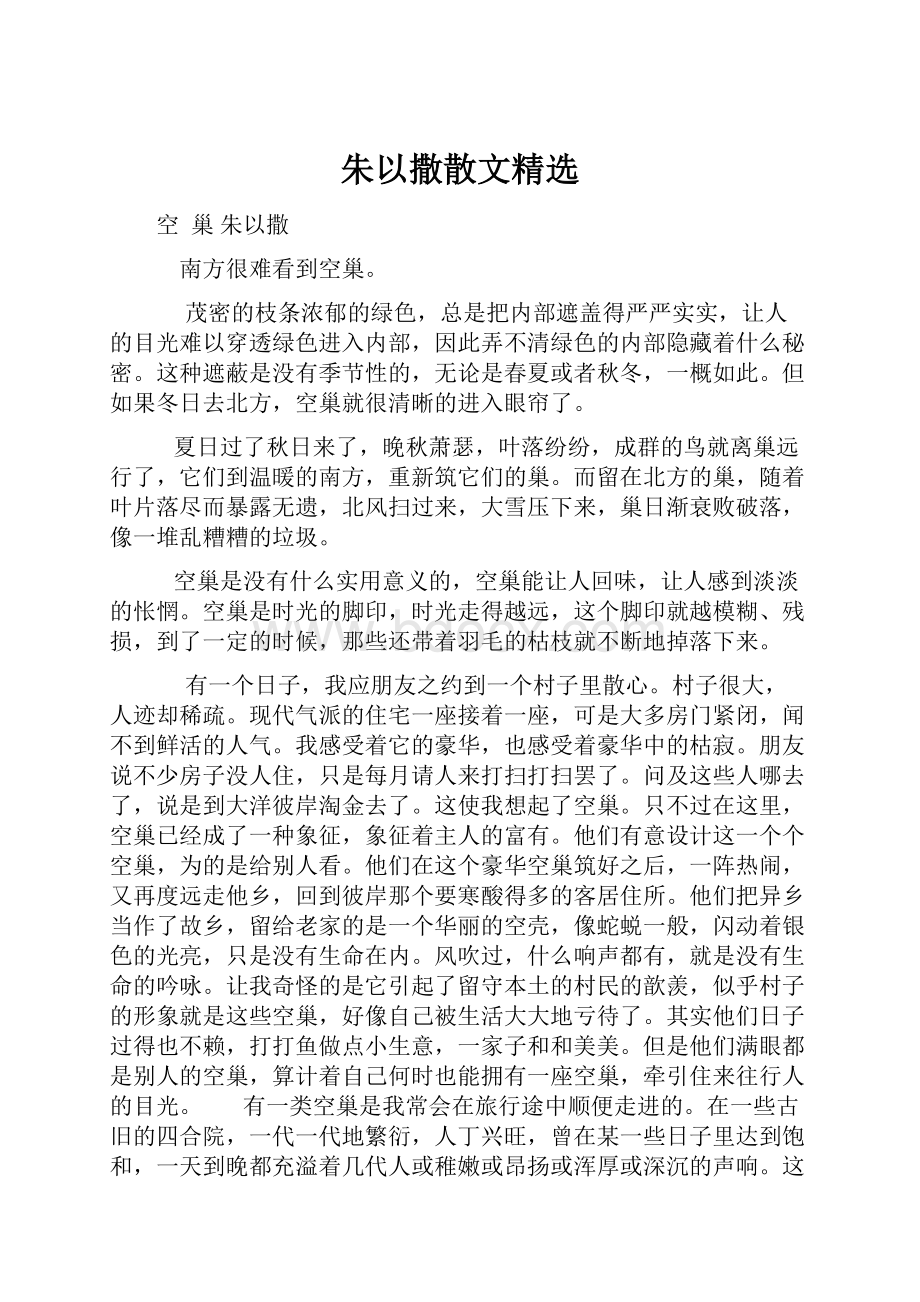
朱以撒散文精选
空 巢朱以撒
南方很难看到空巢。
茂密的枝条浓郁的绿色,总是把内部遮盖得严严实实,让人的目光难以穿透绿色进入内部,因此弄不清绿色的内部隐藏着什么秘密。
这种遮蔽是没有季节性的,无论是春夏或者秋冬,一概如此。
但如果冬日去北方,空巢就很清晰的进入眼帘了。
夏日过了秋日来了,晚秋萧瑟,叶落纷纷,成群的鸟就离巢远行了,它们到温暖的南方,重新筑它们的巢。
而留在北方的巢,随着叶片落尽而暴露无遗,北风扫过来,大雪压下来,巢日渐衰败破落,像一堆乱糟糟的垃圾。
空巢是没有什么实用意义的,空巢能让人回味,让人感到淡淡的怅惘。
空巢是时光的脚印,时光走得越远,这个脚印就越模糊、残损,到了一定的时候,那些还带着羽毛的枯枝就不断地掉落下来。
有一个日子,我应朋友之约到一个村子里散心。
村子很大,人迹却稀疏。
现代气派的住宅一座接着一座,可是大多房门紧闭,闻不到鲜活的人气。
我感受着它的豪华,也感受着豪华中的枯寂。
朋友说不少房子没人住,只是每月请人来打扫打扫罢了。
问及这些人哪去了,说是到大洋彼岸淘金去了。
这使我想起了空巢。
只不过在这里,空巢已经成了一种象征,象征着主人的富有。
他们有意设计这一个个空巢,为的是给别人看。
他们在这个豪华空巢筑好之后,一阵热闹,又再度远走他乡,回到彼岸那个要寒酸得多的客居住所。
他们把异乡当作了故乡,留给老家的是一个华丽的空壳,像蛇蜕一般,闪动着银色的光亮,只是没有生命在内。
风吹过,什么响声都有,就是没有生命的吟咏。
让我奇怪的是它引起了留守本土的村民的歆羡,似乎村子的形象就是这些空巢,好像自己被生活大大地亏待了。
其实他们日子过得也不赖,打打鱼做点小生意,一家子和和美美。
但是他们满眼都是别人的空巢,算计着自己何时也能拥有一座空巢,牵引住来往行人的目光。
有一类空巢是我常会在旅行途中顺便走进的。
在一些古旧的四合院,一代一代地繁衍,人丁兴旺,曾在某一些日子里达到饱和,一天到晚都充溢着几代人或稚嫩或昂扬或浑厚或深沉的声响。
这样的家族给人的感觉就是旺盛,尽管屋瓦上长出衰草,天井的缝罅漫上青苔,外人还是羡慕这种大家族的团圆、集合,有时就爱上门说说话儿,沾点旺气回去。
人们乐于与这种人家接近,缘于这类宅院的欢笑、和睦和协调气息,让人觉得这里盛满了寻常人家生活的全部内容。
十年、二十年过去,这些宅院明显萧条和空旷了,年轻人都走远了,去追求他们的梦。
外边世界要比老宅广大得多,使他们的才情得以无限量地扩张。
只有年关将近,他们才像候鸟般返回,使老宅重新焕发生气。
只是新春末了,他们又离巢远行,继续新的里程,老宅又一度归于岑寂。
越往后,他们返回的次数越少,一次又一次难以聚齐,不是少了这个就是少了那个,而老宅也有不少地方颓了倾了。
前尘梦影交迭,旧时月色重来。
有的老宅因着这些远行者的声名,贴上了名人故居的标签,引得四面八方的人来参观。
但岁月的风雨已把老宅摧残成千疮百孔的空巢,在飘摇中任人指认、品评。
有些人记住了,有些人以为和自己无关,看过以后也就淡忘了。
时光越往后移,这类空巢越多。
人们寄寓的心愿,似乎教化的一部分内容,就由空巢来承担。
譬如我们会说,某位名人就是从这里走向世界的,提示人们不要忘记了这个起点。
南方是游移的放纵的不安分的,这使得许多人居无定所,没有固定的温馨的巢。
他们的巢总在路上,是背上那个移动的壳子。
没有固定居所的日子就是漂泊的日子,漂泊的日子更多一分风险和一大串求知数,匆忙仓皇,在急切中穿行。
可是有些人恰恰适应这种节奏,这大致可以追溯到古人游历的风尚、杖剑而行四海为家、天当被地当床的浪漫主义情怀。
现在年轻的漂泊者正在重温这一壮举。
只是日子变得越发实际,其中滋味若何,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了。
每次冬天我到北方,都要目击空巢,这是北方空间中最能吸引我仰望的目标。
空巢在瑟瑟寒风中发抖,谁也不知道它们的主人是鸟类中的哪一种,更没人关注它们年复一年的变化,我只是在目击时荡起淡淡的思想上的涟漪。
但愿来年春天,里面能传出雏鸟们参差不齐的欢叫。
上天坠落的一枚钉子
在一些富有古典气息的城市里,不难看到塔的高耸。
倘若是名塔,甚至就成了这座城市的象征。
当你不知道城市的方位、渊源时,往往会有这么一个经验,有人提到了里边的一座古塔,于是眼前一亮,这座城市蓦然变得可亲起来。
的确有过几次,有人问我故乡,和他们说是唐宋时帆樯如云的港湾、海上丝绸之路,皆一脸茫然,后来只好把东西二塔搬出来,听者便觉得立体极了、感性极了,还想起李贽、郑成功、李叔同这拨人来。
古塔是天上宫阙脱落的一枚钉子。
城市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渐渐遮掩了古塔,可遮掩不住的是古塔浑然一身的典雅气息。
它汲历史之风霜、融人间之智慧、渗入前朝工匠好手的精湛技艺,使它在堂皇富丽的大厦群里毫不猥琐。
它所散发出的气息,甚至使遥远前来的人们流连忘返。
但在夜间登临塔楼高处,风,依稀掀动古塔的影子,安然地飘浮在明月之夜的水面。
看着城市中心那些大厦总是灯火通明,如此多的人,他们在温暖的灯光下做着什么呢?
古塔是如此地孤独无群,昏暗无光,被清冷紧紧包裹。
古塔的沉沦,缘于审美趣味的沉沦。
这一点,似乎不须费太多的口舌了。
古塔的兴盛与佛教的兴盛相连。
脂粉的南朝和血腥的北朝,应是塔的生发最普及和迅速的时间段。
云来云往里,风起风止时,有不少古塔就坍塌在烟雨中了。
尽管后人群策群力再起楼台,毕竟塔是越来越少。
今人不再造塔,而塔却敌不过风雨,于是由崭新而陈旧、完美而残缺。
但我们喜爱古塔,也就是喜爱这种没有掩饰的本真。
虽然说当初的造塔者,在建造过程中都心地虔诚,可几百年之后矗立在我们面前的,无论是形或质,都有了相当的差异。
土塔石塔也罢,木塔陶塔也罢,每一座古塔,总是渗透了当时的趣味,独拔于世。
不过,我最心动的还是土塔。
土塔是最能映现沧桑之变的,它对风雨的感受的敏感,远远超过了陶塔、石塔和金属塔。
雨水滴落的痕迹,长风刮过的痕迹、雷电击打的痕迹,都穿透厚重的时光,历历在目。
有意思的是,我常常发现围绕古塔的古寺院被修缮一新,金碧辉煌,好像未经历史风雨一般。
古塔和古寺,倘翻到初始这一页,它们是一致的,而愈往后,古塔这枚巨大的钉子,却是浑身锈迹,没有人来把它擦拭得铮亮。
不过,我对古塔的看重,还是它生命在整个流程中的真实体验。
生命的状态曾盛开过,也就有闭合,这是不需要粉饰的。
塔是长久木讷的,倘若没有塔铃的话。
只有那些檐角悬挂了铃的古塔,才能借助高天长风,发出自己深沉的声响。
如果有距离不远的两座塔,那么它们的相应,会长久地洋溢着古朴的生气,融雪一般地融入高远的夜空里。
这时路过的人们,必定要举头眺望夜幕中高耸的轮廓,心弦动弹。
这些声响携带着霜雪的浸润,有一缕月光的清冷,从老远就让人闻到前朝的气味。
长风总是把这种声音推到一个很开阔的空间里,让现代的格局飘落古雅。
古塔依旧可以提供登高的条件,从光亮的外界进入塔的内部,就变得十分深邃和黑暗了。
塔梯的陡峭逼仄,使人难以透气。
抚摸古塔内壁,有一种很单调冰冷的时间感,时光一寸寸地穿透手掌,沁入心扉,在幽暗中感悟凋零。
古塔就是时间的华表,在塔顶嗅得出时间的奥秘,让人冥思多于赞美。
现在的登临者大多没有登高作赋的雅兴了,除了文才不继,也由于缺乏壮怀浪漫的情调。
但是在苍茫的西部登塔遥望,高迥的意象逼入心胸。
看黄沙随风漫起,看黄叶随风飘舞,看嫣红的夕阳沉重地落下,暮色升腾。
我固执地认为,这种体验多了,走笔一定携有苍凉的大气。
用现在实用的眼光看,塔真是百无一用的东西。
但古塔是古人憧憬、梦幻的储存器。
撩开时光的窗幔,这个储存器的每一个角度、每一个层面,都有智慧的留痕。
构想者总是将广大的世间之物,浓缩在一座塔里,让人触目绝伦的工艺、斑斓的雕绘,不禁心神迷乱。
确切地说,蜂拥而来的是一种无序的领悟,对每一块浮雕,每一方藻井,想弄清楚缘由极为困难。
智慧太密集的地方,游人只有赞叹。
这样一本厚重的书,在当时已经把精神和物质拉开了距离,尤其在澄澈明净的星光下,它的神秘,使手中的旅游指南黯然失色。
古塔的盛期已经流逝,和古塔争相轩邈的建筑群越来越密。
古塔走向清寂,失去了人气。
它们的身边,经常走动的是一些青衣布衲的僧人,他们生活在塔的范围里,他们的精神从未远离出游。
在他们眼里,塔就是一种标志,一种可以让心灵安定的标志;塔又是一种界定,界定着心灵向往的方位。
他们每一日对塔遥望,聆听塔铃清音,正是缘于一种需要。
这样的人毕竟无多,正如同古塔只会减少不会增加一样。
千百年弹指一挥间,许多倾国倾城的记忆都已飘散无存,忙碌紧张的日子,又使人缺乏了拨开线装书的黄页细细找寻的耐心。
只是在奔走的旅程里,一旦遭遇古塔、仰望古塔,静对塔尖上的悠悠白云。
这时便寓目崇高,感叹流逝:
不知能否倚仗这枚进入我们视界的坚硬钉子,扌契入古典长廊的幽深?
!
底层的微粒
从这里的任何一条小巷露出头来,可以很快地接入另一条小巷。
有时看到一个人一闪不见了,那肯定是一条巷子接纳了他。
对小巷走惯的人驾轻就熟,很简化地就到达了目的地,并且一身的灵巧。
总是在上午,会有人挑着担子在巷里走,一边用悠长的调子吆喝着。
都是一些女声,那略带夸张、延展的调子,可以从巷口一直传到巷尾。
竹篓里边摆着罐子、盆子,里边是一些小家碧玉般的糕点,或者蒸熟捣烂的、弥漫着五香粉味道的豌豆。
它们被朴素的餐巾盖着,生怕高悬在巷子上方的枝叶、飞虫落下。
家乡的韵味越来越寡淡,却因为这些残存的巷,这些大街上所没有的挑担、吆喝,复活了一些往日的少年痕迹。
如今———说来可怜,这些只是巨大变化中微弱的不变罢了。
有人开了门,端着瓷碗出来,买一些踅回去品尝,这是很实在的生活趣味。
“明朝深巷卖杏花”,读来不能不承认它的空灵超脱,还有一些湿漉漉的气味。
时间过去那么久了,杏花每年依旧,卖花的人消失了,对于越发匆忙和实在过日子的人,我们相应需要一些实在之物。
挑担吆喝的小本生意,我向来相信。
这些在巷中穿行的货郎担,家庭作坊那么小,甚至还称不上作坊,只是日常生活的增生。
他们的家中多了些石磨、石臼,还有如塔一般垒起的蒸笼、以大套小的系列笸箩,这些器物陈设在房舍里,就很有一些旧日农家气味———不是非常遥远的,已经消失的,而是晚近的,可以感受正在日渐消遁的一类。
这一类器物在我少年时期的家中,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今不知所终,就是十分沉重的石臼也无处寻觅。
我格外倾心这些手工食品,它们的确是用手的某些动作来完成的。
一个常年使用手制作同一种食品的人,手就是一杆秤,或者一架敏感的仪器,一帖恰到好处的配方。
每一天生产的量很有限,更无意张扬或者扩大规模,总是处在初始阶段的那几屉蒸笼上。
在这个世界上商家纷纷抢注商标、攻掠商机重地时,它们的主人无动于衷———没有牌号、没有出品单位和时间标志,却日复一日地生产着,执拗地对抗着机器制造的力量。
小巷里生存的人,从来没有怀疑过食品的质量,朴素地吆喝声和同样朴素的品咂,年复一年,如同签下了一纸契约,挽留下不可脱离的味觉。
没有谁会花上脚力,去窥探一下这个家庭作坊的卫生状况或者材料的真伪。
与之相投合的是这些挑担吆喝者,也从不向老主顾夸耀自己的手艺以及产品的正宗,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相互间的默认,闻到熟悉的香味、齿舌间同样熟悉的咀嚼,语言的表现显出多余,他们早交融在一起了。
木楼上的百页窗打开了,有一个竹篮从上边缓缓垂下,一个少女正在放纵着绳索,长发从肩上滑落。
竹篮边上别着几枚纸币,货郎心领神会,取下纸币,依次将糕点夹起包好放入,末了,还添了一块。
他扬扬手,笑笑,竹篮悬过头顶,随着少女捉拿的动作缓缓上升,最后落实在窗台上。
关了窗,可以想见阁楼中等候的少男少女,此时一定是忽喇喇围了上来。
我一直迷恋这样的动作,我以为它只有依傍这些破旧的木屋、红砖楼,依托这几条僻静、有些昏暗的小巷,才显出如此绵长的回味。
量不多的手工作坊,一天所生产的就只够上一天的吆喝,甚至供不应求。
积压是从未有过的,但是主人始终不愿扩大生产,觉得已能保证老小温饱,业余依旧找人聊天,或者下棋,他心里头有着绝不招摇的固执———不引人注意,尤其不要把工商还有税务的招引过来。
真让我品尝,他们用手工一下一下做成的糕点,的确比工厂产出的受用。
工厂用大机器制造出来,满足了城市人口大量地购买、储存,像秋日的松鼠一样,为冬日不挨饿而积累,忽略了舌尖上敏感的个体的探讨———便利,城里的人购买的原则。
永远是一个模子诞生的,规则、理性,可以经得起测量、观赏;手工制作则相对粗朴了一些,尤其对于圆形的糕点边缘,像阿Q画圆那般,难以圆满,再熟练的手工师傅,还是输给机器的一成不变。
不同的是机器缺乏情绪,或者说只有一种冰冷的情绪,手工业者,他在擀、揉、捏、摆、蒸的整个过程,都充满了对于生活复杂的想法———没有背景的升斗小民,都有一点居安思危的淡淡愁绪,想得多了,手的动作更加细腻,也更到位。
情绪每一日都在浮沉,实在的日子,多变的世界,动作起落中,有着微妙的变数,连同巷进巷出的步履,夸张了的悠长调子,在时光的漫长中,并不漫长的人生被动作的反复充满着。
小本生产的、家庭作坊的,产品中有一种异于大机器生产的隐蔽。
来自家族的、祖上的私秘的遗传,我是非常相信任何一种手艺都存在秘方这一说法的。
谋生过程中,自己的一点小感受就是秘方,时日长久,秘方就异于常人常态,越发具有自己的特性。
最后走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我们所说的老字号招牌,就是秘方在背后支撑着。
为了防止外泄,不靠文字立,熟记于心,成为精神上的一个部分。
秘方的传递有着严密的规矩和诡秘的仪式,寻找和考验着家族中可以信赖的后人。
有时子孙不肖,持秘方者宁肯烂在肚里,这也是秘方最好的去处。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公私合营,即便是那么难熬的时段,有一些独到的经营者还是不愿把秘方献给政府。
实在无奈,有的被迫献出秘方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则沉入记忆的海底以示抗议。
对此我是完全同情和理解的。
少年时期的幼稚,对秘方充满了神奇的联想,却对秘方的形成艰辛没有太多的认识。
赢者通吃似乎是社会生存的一个规律,公共的氛围使人对于不献出秘方的行为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直到后来,我越来越注重自己内心的需要,才算理解了一个家族为了不泄露祖传的心血进行的默默抗争———祖上智慧的结晶,对于任何一个后人,都有权力持抱不放,它们是不可奉献之物。
有的秘方最终成了公物,它的结局令奉献者十分不快:
缺乏虔诚和敬畏,在大集体的不经意甚至戏慢的操作中,秘方失去了灵验。
这使得献出秘方的这一代人,特别是执掌秘方的当家人,内心长久地持有负罪感。
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许多私秘的财物、精神都不得已地充公了,隐私亮在众人面前践踏。
一个时代没有私秘的藏身之处,肯定是苦痛和荒唐的,应该有一些昏暗的角落,让私秘安全地放置,不受风雨的碰触。
现在回忆起来,还是像这些吆喝于小巷的长调还有小食品更能让人品出日子的朴素和平安,它们很细腻地沁入,直抵内心深处,直到老大仍勾连不放。
连作梦我都作一些小的、琐碎的、普通得不得了的。
我对大的不感兴趣,大的可以联系到许多政治运动、政治事件。
公共记忆的力量十分强大,有一些人也专门着眼于这些大的方向,试图在最广泛的程度上再一次提醒人们强化那些暴风骤雨般的经历。
奇怪的是,像我这样曾经亲历过的人,对于这些大的范畴毫无兴趣,即便有人谈起,我也会把话题掐断,论说其他———这些公共记忆除了让人精神抑郁,就是滋蔓无聊。
那些生动的、还带着晨露清流的晶莹,显示出私有记忆的单独占有。
还有一些小得不能再小的物品———一枝可以对称叠起的含羞草、一把带着牙印的长命锁、一枚带着斑点的麻雀卵,它们都是针对一个具体的人产生意义的,是这个具体的人生活板块上的颗粒和碎屑,如水滴在宣纸上晕化,越发洇润,人陷了进去,被旧日潮水淹没。
想想自己的少年时代,所接收的道理都大到没有边际,那么小的年龄就知道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在受苦……在一个缺乏阅历、眼界局限在教科书上的少年来说,只能相信。
可是,只有那些切身体验的细小琐碎,才真正附着在他渐渐扩大的年轮上,构成自己精神库存中的财物。
那些重大的道理,随着后来的形势进展,还有自身眼界的开阔,不是被推翻了,就是在自己的怀疑下荡然不存。
我坚信是那些小的、琐屑的、没有什么意义可言的,倒可以追随一生。
许多小作坊停了下来,还有一些走到了小的反面,学会了包装和扩大,在一个城市里有了几个连锁店,原本的朴素或者寒俭,已被洋气替代。
过程中极其微妙的细节,由于机器无法传达手工的感受,产品的口味就弱了一些。
又过了一些时候,一些细节又略去不计,口味也越发没有个性。
老主顾是冲着纯正的口感而品之不厌的,逐渐地削弱的细节,像一个很有弹性的茧,被悄悄地抽走了一大节,抽走了停留在舌尖的余味,有一种陌生的刺痛———原以为能够守住这辈子的口福,却一家又一家地消失了。
我尊敬那些能够坚守下来的小作坊,我觉得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从小学会捉笔写字的手,于今仍是这个姿势。
不愿交与机器,缘于机器无法在笔迹中储满感情。
其实,我还得继续走研墨的老路,这和手工研磨豆浆是一个道理,都是乳白色,散发着田畦间的芳香,每一家的口味各具特色。
当我在这个城市里,有幸品尝到不失汁味的食品,看到舍弃机器的诱惑而不吝手工的劳作,会当街站了下来。
我承认,这一小部分人是我亲密的伙伴,我说:
“兄弟,歇会儿。
”
我在拥挤的人流中
回顾往昔,山村的生活里,对于拥挤的印象,只余留一旬一次的赶集了。
总是这一天,在墟场上见到四面八方前来交易的农家男女,牛哞、狗吠、果香、汗臭,加上讨价还价的鼎沸人声,赤足而行铲起的尘土,真是热气腾腾。
未及傍晚,拥挤的人群四散,人行于长长山道,犹如上天洒下的几粒豆了,很隐入绿色的山林之中。
永远不会拥挤的山村和越发拥挤的城市,是一个时代背景下的两个画面。
许多年前,它们的差别,据我的观察,密集相差不大。
那时节走在城市的大街上,也常有过于宽阔之感,甚至怀疑设计者是不是犯浪费的毛病。
几十年后,大街在感觉上有如水巷,即便拓宽了两三次,仍然满足不了人流的汹涌。
为此,修了立交桥,让一些人在另一些人头上走动。
山村依旧辽阔,尽管人的生殖力很强,要使山村空间拥挤,却不是一件易事。
城市里的每一个人都要对拥挤负责任,自已就是造成拥挤的成分之一。
从这一点出发,城里人是没有理由责怪拥挤的。
而且,从一个角度讲,拥挤好啊!
拥挤意味着人口众多,就有可能升格为市,不再称县。
拥挤的原因,从大处讲是当年不听马寅初的劝告,多生快生所致。
从细处讲,是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共同遵守某一种时间的要求造成的。
譬如全市的统一的上班时间,统一的下班时间。
这时候,人流如开闸之洪水,倾泄于街面。
加上那些汽车、摩托车和通俗工具自行车,顿时道路充塞,举步维艰。
你不可能为了摆脱拥挤,擅自推迟上班提前下班——那会造成比拥挤更可怕的后果。
因此,城市中只有足不出户的人,才可免除拥挤的不快。
拥挤使素不相识的人相互靠紧。
有时,路面狭窄,紧密程度骤然升高,像一滴水落入大海,顷刻分辨不出你我。
这个时候,个人似乎不须用力,把持住重心,就能稳稳当当地被移动,让人流的力量送抵目的地。
当然,这里说的是顺势,势不可逆——倘若途中才发现重要文件忘在家中,务必回去,逆势就出现了。
这时必须左右闪动,躲避?
面而来的人流冲撞和责骂的眼神——谁叫你反潮流呢?
城市十字路口的红绿灯,旱地上的闸门,总是拦下一批,放走一批,降低流动的凶猛气势和连绵不绝。
长龙一般的人流,被一道又一道的红灯切割之后。
顿成块状。
这对于急着到公司签到或急着回家的人来说,被拦载的短暂停滞里,时光已变得无比漫长。
这时,他们会艳羡那些拉着警笛闪烁红光的警车——他们是没有红绿灯观念的。
在这密如蛛网的路线上,不受约束尽管狂驰。
它不免让人狐疑,是不是又有人作案了?
对于特殊的体会,在红绿灯下可以辨别出来,尽管就这么几分钟的等待。
在小的时候,我贪恋人流的涌动,尤其是夜色来临,在人流的中间推推搡搡,颇有一种安全感。
拥挤,意味着单个的人数量的密集,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
的确,我们倚靠着许多个人的集中曾经干过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中国人的生殖崇拜和生殖信念比欧美人强大得多,很快就如水蔓延,流到哪里是哪里了。
城市就是这样建造起来的。
不少文章把人形容成蚂蚁,把许多的人形容成蚂蚁的集合。
这种形容的准确,就在于人对于试谋生的描绘——在我们眼里,蚂蚁无疑是终年辛劳觅食的典范,一刻不停地动弹,使世界充满了不安。
有好几次,我站在高楼顶端,鸟瞰川流不息的人——世界没有瞬间的安宁,任何一个秒数里,都甩动着无数同样的人,匆忙地筑他的巢。
东京,拥挤的都市,毫无舛误的步距,频率高扬的步滑坡,滤去了形式上的花招,直抵目标。
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固有的步法,不适应很轻易地被人判断出没是同族。
我们这个重视感性的民族,斯文是主要的特征。
许多温馨旖旎的往事,就涵纳在这种斯文的举动里。
曾经有一个古名人的故事,情节简单而有寓意,说的是大雨来临,人流躁动起来,大多数人撒腿就跑,步履仓皇、踉呛,惟有几位文人,依旧不改舒缓安然,雨中谈笑吟咏,无不自如。
端的闲云野鹤,这也许就可称为境界了。
境界是装扮不出来的,“不能安土,不能乐天;不能乐天,不能成其身”,其中就包含了泰然处之。
一个狂奔者的模样一定比闲庭漫步更直露和强大,如果十人、百人狂奔起来,一定不会有什么好兆头。
由于平时在这方面观察的细致,每逢我给学生上课时,总是特别早起,走在拥挤之势形成之前。
对于一个站在讲台上说话的人,千万不要自毁形象。
人生的体验,通常借助他人的行为,从比自已年少的人身上,看到自已的苍老;从比自已苍老的人身上,听到即将响起的晚钟.生命被时日淡淡地消融和稀释,逝去着的和诞生着的,在拥挤中表现为眼熟的少了,眼生的多了起来.一些统计,似乎对热爱宽松的生存中人提供安慰:
在整个世界大环境里,臂如每分钟里某些疾病患者若干人故去,臂如每分钟里,车祸使多少人丧生;臂如每分钟里,某个战争使多少人魂魄无归.允许我发表意见的话,如果这种情形是持续化.那么地球上已经寥廓苍凉了.让人百思不解的是,人口正在走向密化,许多远古的的不毛之地,已经响起了婴儿的哭声.真实的恍惚被隔在遥远的别一边,连同往昔的清静和安宁。
以为暮色深浓时登高望远,会更贴近自然的门径,谁能想到满目的万家灯火,横扫着低垂的眼帘。
如此地光柱相击、交错,编织成网。
视线的极限处仍然是灯光的诱惑,可以想见,每一盏灯底下,有多少人才正在继续着白昼的忙碌。
灯光,对于忙碌的人才起作用,倘若一个人静态地怡养身心,就不需要辅助的、附加的、装饰的条件,漆黑理应成为空间的惟一内容。
许多的建筑形态发生了巨变,土地在拥挤中悄悄地增值。
有一些很雅致的小别墅,曾经相互拉开距离,由翠绿的草坪充当天使。
矮墙上爬满了令人怀念的曼陀罗花,这是五四时期文人笔下经常出现的一种花。
后来,别墅和草坪相继不见了,连同风情万种的曼佗罗。
那一年非常巧,我一直走在这条路上,所有变化都在我的眼底。
尽管总是处于准备状态,我这个不学建筑学的人,也看得出,有几幢高大建筑将拔地而起。
夏多布里昂在十九世纪初就讽刺过:
“今天,人们希望一切建筑物都有明确的用途,而不考虑对人们来说存在一种更为崇高的精神用途。
”是的,我进一步判断是实用的高层住宅——这说明原先别墅里那种清幽的生活早已结束,还表明再也看不到那些精美的雕花廊柱、婉约的红砖院墙和昂扬的檐角,听不到在夜间飘逸出来的悦耳琴声,而那弹奏的女子更是让人遐想不已。
立体——当代对于建筑的基本要求,就在于它能在同样方寸的土地上,最大地解决拥挤中人们的栖止。
典雅而略带冷清的别墅啊,你的优点成为致命的弱点,只能远离我们的视界了。
有人问过我,什么样的空间最能体验人流的密集和平民气息呢?
我认为是南下的火车。
无数的北方人流,拎着无数的鼓鼓囊囊的蛇皮袋,涌向这列在南北两端奔驰的钢铁长虫,希望随着它的奔驰给自己的生存带来福音。
他们绝没有享受卧铺的念头,行程中以简便为主,很快就把硬座车厢填满。
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善于忍受煎熬。
车厢内烟雾弥漫,垃圾扔满过道,几天几夜的无从漱洗,每个人身上散发出的怪味交织混合,连资深的列车员也难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