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风荷举选.docx
《一一风荷举选.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一一风荷举选.docx(1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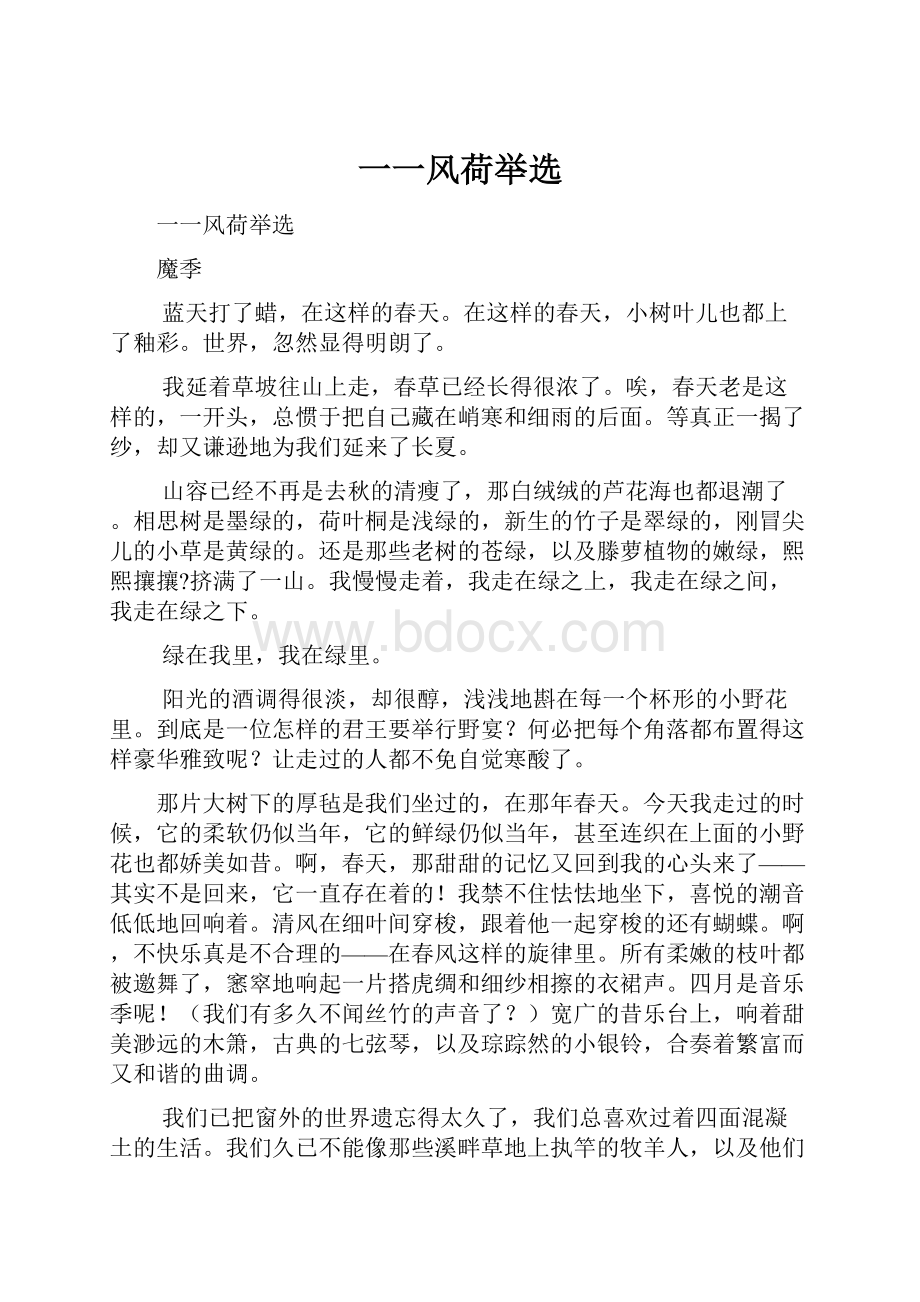
一一风荷举选
一一风荷举选
魔季
蓝天打了蜡,在这样的春天。
在这样的春天,小树叶儿也都上了釉彩。
世界,忽然显得明朗了。
我延着草坡往山上走,春草已经长得很浓了。
唉,春天老是这样的,一开头,总惯于把自己藏在峭寒和细雨的后面。
等真正一揭了纱,却又谦逊地为我们延来了长夏。
山容已经不再是去秋的清瘦了,那白绒绒的芦花海也都退潮了。
相思树是墨绿的,荷叶桐是浅绿的,新生的竹子是翠绿的,刚冒尖儿的小草是黄绿的。
还是那些老树的苍绿,以及滕萝植物的嫩绿,熙熙攘攘?
挤满了一山。
我慢慢走着,我走在绿之上,我走在绿之间,我走在绿之下。
绿在我里,我在绿里。
阳光的酒调得很淡,却很醇,浅浅地斟在每一个杯形的小野花里。
到底是一位怎样的君王要举行野宴?
何必把每个角落都布置得这样豪华雅致呢?
让走过的人都不免自觉寒酸了。
那片大树下的厚毡是我们坐过的,在那年春天。
今天我走过的时候,它的柔软仍似当年,它的鲜绿仍似当年,甚至连织在上面的小野花也都娇美如昔。
啊,春天,那甜甜的记忆又回到我的心头来了——其实不是回来,它一直存在着的!
我禁不住怯怯地坐下,喜悦的潮音低低地回响着。
清风在细叶间穿梭,跟着他一起穿梭的还有蝴蝶。
啊,不快乐真是不合理的——在春风这样的旋律里。
所有柔嫩的枝叶都被邀舞了,窸窣地响起一片搭虎绸和细纱相擦的衣裙声。
四月是音乐季呢!
(我们有多久不闻丝竹的声音了?
)宽广的昔乐台上,响着甜美渺远的木箫,古典的七弦琴,以及琮踪然的小银铃,合奏着繁富而又和谐的曲调。
我们已把窗外的世界遗忘得太久了,我们总喜欢过着四面混凝土的生活。
我们久已不能像那些溪畔草地上执竿的牧羊人,以及他们仅避风雨的帐棚。
我们同样也久已不能想像那些在陇亩间荷锄的庄稼人,以及他们?
足容膝的茅屋。
我们不知道脚心触到青草时的恬适,我们不晓得鼻腔遇到花香时的兴奋。
真的,我们是怎么会痴得那么厉害的!
那边,清澈的山涧流着,许多浅紫、嫩黄的花瓣上下飘浮,像什么呢?
我似乎曾经想画过这样张画——只是,我为什么如此想画呢?
是不是因为我的心底也正流着这样一带涧水呢?
是不是申于那其中也正轻搅着一些美丽虚幻的往事和梦境呢?
啊,我是怎样珍惜着这些花瓣啊,我是多么想掬起一把来作为今早的晨餐啊!
忽然,走来一个小女孩。
如果不是我看过她,在这样薄雾未散尽,阳光诡谲闪烁的时分,我真要把她当作一个?
精灵呢!
她慢慢地走着,好一个小山居者,连步履也都出奇地舒缓了。
她有一种天生的属于山野的纯朴气质,使人不自已地想逗她说几句话。
“你怎么不上学呢?
凯凯。
”
“老师说,今天不上学,”她慢条斯理地说:
“老师说,今天是春天,不用上学。
”
啊,春天!
噢!
我想她说的该是春假,但这又是多么美的语误啊!
春天我们该到另一所学校去念书的。
去念一册册的山,一行行的水。
去速记风的演讲,又计数骤云的变化。
真的,我们的学校少开了许多的学分,少聘了许多的教授。
我们还有许多值得学习的,我们还有太多应该效法的。
真的呢,春天绝不该想鸡兔同笼,春天也不该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土语,春天更不该收集越南情势的资料卡。
春天春天,春天来的时候我们真该学一学鸟儿,站在最高的枝柯上,抖开翅膀来,晒晒我们潮湿已久的羽毛。
那小小的红衣山居者很好奇地望着我,稍微带着一些打趣的神情。
我想跟她说些话,却又不知道谈讲些什么。
终于没有说——我想听有我能教她的,大概春天都已经教过她了。
慢慢地。
她俯下身去,探手入溪。
花瓣便从她的指间闲散地流开去。
她的颊边忽然漾开一种奇异的微笑,简单的、欢欣的、却又是不可捉摸的笑。
我又忍不住叫了她一声——我实在仍然怀疑她是笔记小说里的青衣小童。
(也许她穿旧了那袭青衣,偶然换上这件红的吧!
)我轻轻地摸着她头上?
蝴蝶结。
“凯凯。
”“嗯?
?
”
“你在干什么?
”
“我,”她踌躇了一下,茫然地说:
“我没干什么呀!
”
多色的花瓣仍然在多声的涧水中淌过,在她肥肥白白的小手旁边乱旋。
忽然,她把手一握,小拳头里握着几片花瓣。
她高兴地站起身来,将花瓣小小红裙里一兜,便哼着不成腔的调儿走开了。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击了一下,她是谁呢?
是小凯凯吗?
还是春花的精灵呢?
抑或,是多年前那个我自己的重现呢?
在江南的那个环山的小城里,不也住过一个穿红衣服的小女孩吗?
在春天的时候她不是也爱坐在矮矮的断墙上,望着远远的蓝天而沉思吗?
她不是也爱去*吗?
爬在树上,弄得满头满脸的都是乱扑扑的桃花瓣儿。
等回到家,又总被母亲从衣领里抖出一大把柔柔嫩嫩的粉红。
她不是也爱水吗?
她不是一直梦想着要钓一尾金色的鱼吗?
(可是从来不晓得要用钓钩和钓饵。
)每次从学校回来,就到池边去张望那根细细的竹竿。
俯下身去,什么也没有——除了那张又圆又憨的小脸。
啊,那个孩子呢?
那个躺在小溪边打滚,直揉得小裙子上全是草汁的孩子呢?
她隐藏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在那边,那一带疏疏的树荫里,几只毛茸茸的小羊在啮草,较大的那只母羊很安详地躺着。
我站得很远,心里想着如果能摸摸那羊毛诙多么好。
它们吃着、嬉戏着、笨拙的上下跳跃着。
啊,春天,什么都是活泼地,都是喜洋洋的,都是嫩嫩的,都是茸茸的,都是叫人喜欢得不知怎么是好的。
稍往前走几步,慢慢进入一带浓烈的花香。
暖融融的空气里加调上这样的花香真是很醉人的。
我走过去,在那很陡的斜坡上,不知什么人种了一株栀子花。
树很矮,花却开得极璀璨,白莹莹的一片,连树叶都几乎被遮光了。
像一列可以采摘的六角形星子,闪烁着清浅的眼波。
这样小小的一棵树,我想,她是拼却了怎样的气力才绽出这样的一树春华呢?
四下里很静,连春风都被?
得腻住了——我忽然发现自己已经站了很久,哦,我莫不是也被腻住了吧!
乍酱草软软的在地上摊开、浑朴、茂盛,那气势竟把整个山顶压住了。
那种愉快的水红色,映得我的脸都不自觉地热起来了!
山下、小溪蜿蜒。
从高处俯视下去,阳光的小镜子在溪面上打着明晃晃的信号。
啊,春天多叫人迷惘啊!
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是谁负责管理这最初的一季呢?
他想来应该是一个神奇的魔术师了,当他的魔术棒一招,整个地球便美妙地缩小了,缩成一束花球,缩成一方小小的音乐匣子。
他把色与光给了世界,把爱与笑给了人类。
啊,春天,这样的魔术季?
小溪比冬天涨高了,远远看去,那个负薪者正慢慢地涉溪而过。
啊,走在春水里又是怎样的滋味呢?
或许那时候会恍然以为自己是一条鱼吧?
想来做一个樵夫真是很幸福的,肩上挑着的是松香,(或许还夹杂着些山花野草吧!
)脚下踏的是碧色玻璃,(并且是最温软的,最明媚的一种。
)身上的灰布衣任山风去刺绣,脚下的破草鞋任野花去穿缀。
嗯,做一个樵夫真是很叫人嫉妒的。
而我,我没有溪水可涉,只有大片大片的绿罗裙一般的芳草,横生在我面前。
我雀跃着,跳过青色的席梦思。
山下阳光如潮,整个城市都沉浸在春里了。
我遂想起我自己的那扇红门,在四月的阳光里,想必正焕发着红玛瑙的色彩吧!
他在窗前坐着,膝上放着一本布瑞克的国际法案,看见我便迎了过来。
我几乎不能相信,我们已在一个屋顶下生活了一百多个日子。
恍惚之间,我只觉得这儿仍是我们共同读书的校园。
而此刻,正是含着惊喜在楼梯转角处偶然相逢的一刹那。
不是吗?
他的目光如昔,他的声音如昔,我怎能不误认呢?
尤其在这样熟悉的春天,这样富于传奇气氛的魔术季。
前庭里,榕树抽着纤细的小芽儿。
许多不知名的小黄花正摇曳着,像一串晶莹透明的梦。
还有古雅的蕨草,也善意地延着墙角滚着花边。
啊,什么时候我们的前庭竟变成一列窄窄的画廊了。
我走进屋里,扭亮台灯,四下便烘起一片熟杏的颜色。
夜已微凉,空气中沁着一些凄迷的幽香。
我从书里翻出那朵栀子花,是早晨自山间采来的,我小心地把它夹入厚厚的大字典里。
“是什么?
好香,一朵花吗?
”
“可以说是一朵花吧,”我迟疑了一下:
“而事实上是一九六五年的春天——我们所共同盼来的第一个春天。
”
我感到我的手被一只大而温热的手握住,我知道,他要对我讲什么话了。
远处的鸟啼错杂地传过来,那音昔纷落在我们的小屋襄,四下遂幻出一种林野的幽深——春天该?
很浓了,我想。
(一九六五、五、二)
秋天秋天
满山的牵牛滕起伏,紫色的小浪花一直冲击到我的窗前才猛然收势。
阳光是耀眼的白,像鍚,像许多发光的金属。
是那个聪明的古人想起来以木象春而以金象秋的?
我们喜欢木的青绿,但我们怎能不钦仰金属的灿白。
对了,就是这灿白,闭着眼睛也能感到的。
在云里,在芦苇上,在满山的翠竹上,在满谷的长风里,这样乱扑扑地压了下来。
在我们的城市里,夏季上演得太长,秋色就不免出场得晚些。
但秋是永远不会被混淆的——这坚硬明朗的金属季。
让我们从微凉的松风中去认取,让我们从新刈的草香中去认取。
已经是生命中第二十五个秋天了,却依然这样容易激动。
正如一个诗人说的:
“依然迷信着美。
”是的,到第五十个秋天来的时候,对于美,我怕是还要这样执迷的。
那时候,在南京,刚刚开始记得一些零碎的事,画面里常常出现一片美丽的郊野,我悄悄地从大人身边走开,独自坐在草地上。
梧桐叶子开始簌簌地落着,簌簌地落着,把许多神秘的美感一起落进我的心里来了。
我忽然迷乱起来,小小的心灵简直不能承受这种兴奋。
我就那样迷乱地捡起一片?
叶。
叶子是黄褐色的,弯曲的,像一只载着梦的小船,而且在船舷上又长着两粒美丽的梧桐子。
每起一阵风我就在落叶的雨中穿梭,拾起一地的梧桐子。
必有一两颗我所末拾起的梧桐子在那草地上发了芽吧?
二十年了,我似乎又能听到遥远的西风,以及风里簌簌的落叶。
我仍然能看见那载着梦的船,航行在草原里,航行在一粒种子的希望里。
又记得小阳台上的黄昏,视线的尽处是一列古老的城墙。
在暮色和秋色的双重苍凉里,往往不知什么人又加上!
阵笛音的苍凉。
我喜欢这种凄清时美,莫明所以地喜欢。
小舅舅曾经带我一直走到城墙的旁边,那些?
驳的石头,蔓生的乱草,使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
长大了读辛稼轩的词,对于那种沉郁悲凉的意境总觉得那样熟悉,其实我何尝熟悉什么词呢?
我所熟悉的只是古老南京城的秋色罢了。
后来,到了柳州,一城都是山,都是树。
走在街上,两旁总夹着橘柚的芬芳,学校前面就是一座山,我总觉得那是就地理课本上的十万大山。
秋天的时候,山容澄清而微黄,蓝天显得更高了。
“媛媛,”我怀着十分的敬畏问我的同伴,“你说,教我们美术的龚老师能不能画下这个
山?
”
“能,他能。
”
“能吗?
我是说这座山全部。
”
“当然能,当然,”他热切地喊着,“可惜他最近打篮球把手摔坏了,要不然,全柳州、全世界他都能画呢?
”
沉默了好一会。
“是真的吗?
”
“真的,当然真的。
”
我望着她,然后又望着那座山,那神圣的、美丽的、深沉的秋山。
“不,不可能。
”我忽然肯定地说,“他不会画,一定不会。
”
那天的辩论后来怎样结束,我已不记得了。
而那个叫媛媛的女孩子和我已经阔别了十几年。
如果我能重见她,我仍会那样坚持的。
没有人会画那样的山,没有人能。
媛媛,你呢?
你现在承认了吗?
前年我碰到一个叫嫒媛的女孩子,就急急地问她,她却笑着说已经记不得住过柳州没有了。
那么,她不会是你了。
没有人能忘记柳州的,没有人能忘记那苍郁的、沉雄的、微带金色的、不可描摹的山。
而日子被西风刮尽了,那一串金属性的、有着欢乐叮声的日子。
终于,人长大了,会念秋声赋了,也会骑在自行车上,想像着陆放翁“饱将两耳听秋风”的情怀了。
秋季旅行,相片册里照例有发光的记忆,还记得那次倦游回来,坐在游览车上。
“你最喜欢那一季呢?
”我问芷。
“秋天,”他简单地回答,眼睛里凝聚了所有美丽的秋光。
我忽然欢欣起来。
“我也是,啊,我们都是。
”
她说了许多秋天的故事给我听,那些山野和乡村里的故事。
她又向我形容那个她常在它旁边睡觉的小池塘,以及林间说不完的果实。
车子一路走着,同学沿站下车,车厢里越来越空虚了。
“芷,”我忽然垂下头来,“当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生命的同伴一个个下车了,座位慢慢地稀松了,你会怎样呢?
”
“我会很难过。
”她黯然地说。
我们在做什么呢?
芷,我们只不过说了些小女孩的傻话罢了,那种深沉的、无可如何的摇落之悲,又岂是我们所能了解的。
但,不管怎样,我们一起躲在小树丛中念书,一起说梦话的那段日子是美的。
而现在,你在中部的深山里工作,像传教士一样地工作着,从心里爱那些朴实的山地灵魂。
今年初秋我们又见了一次面,兴致仍然那样好,坐在小渡船里,早晨的淡水河还没有揭开薄薄的蓝雾,橹声琅然,你又继续你的山林故事了。
“有时候,我向高山上走去,一个人,慢慢地翻越过许多山岭。
”你说,“忽然,我停住
了,发现四壁都是山!
都是雄伟的、插天的青色!
我吃惊地站着,啊,怎么会那样美!
”
我望着你,芷,我的心里充满了幸福。
分别这样多年了,我们都无恙,我们的梦也都无恙
——那些高高的、不属于地平线上的梦。
而现在,秋在我们这里的山中已经很浓很白了。
偶然落一阵秋雨,薄寒袭人,雨后常常又现出冷冷的月光,不由人不生出一种悲秋的情怀。
你那儿呢?
窗外也该换上淡淡的秋景了吧?
秋天是怎样地适合故人之情,又怎样地适合银银亮亮的梦啊!
随着风,紫色的浪花翻腾,把一山的秋凉都翻到我的心上来了。
我爱这样的季候,只是我感到我爱得这样孤独。
我并非不醉心春天的温柔,我并非不向往夏天的炽热,只是生命应该严肃、应该成熟、应该神圣,就像秋天所给我们的一举样——然而,谁懂呢?
谁知道呢?
谁去欣赏深度呢?
远山在退,遥遥地盘结着平静的黛蓝。
而近处的木本珠兰仍香着,(香气真是一种权力,可以统辖很大片的土地。
)溪水从小夹缝里奔窜出来,在原野里写着没有人了解的行书,它是一首小令,曲折而明快,用以描绘纯净的秋光的。
而我的扉页空着,我没有小令,只是我爱秋天,以我全部的虔诚与敬畏。
愿我的生命也是这样的,没有太多绚丽的春花、没有太多飘浮的夏云、没有喧哗、没有旋转着的五彩,只有一片安静纯朴的白色,只有成熟生命的深沉与严肃,只有梦,像一树红枫那样热切殷实的梦。
秋天,这坚硬而明亮的金属季,是我深深爱着的。
(一九六五、十、十七)
初绽的诗篇
白莲花二月的冷雨浇湿了一街的路灯,诗诗。
生与死,光和暗,爱和苦,原来都这般接近。
而诗诗,这一刻,在待产室里,我感到孤独,我和你,在我们各人的世界里孤独,并且受苦。
诗诗,所有的安慰,所有怜惜的目光为什么都那么不切实际?
谁会了解那种疼痛,那种曲扭了我的身体,击碎了我的灵魂的疼痛,我挣扎,徒然无益的哭泣,诗诗,生命是什么呢?
是崩裂自伤痕的一种再生吗?
雨在窗外,沉沉的冬夜在窗外,古老的炮仗在窗外,世界又宁谧又美丽,而我,诗诗,何处是我的方向?
如果我死,这将是我躺过的最后一张床,洁白的,隔在待产室幔后的床。
我留我的爱给你,爱是我的名字,爱是我的。
有一天,当你走过蔓草荒烟,我便在那里向你轻声呼喊——以风声,以水响。
诗诗,黎明为什这样遥远,我的骨骼在山崩,我的血液在倒流,我的筋络像被灼般地纠起,而诗诗,你在哪里?
他们推我入产房,诗诗,人间有比这更孤绝的地方吗?
那只手被隔在门外——那终夜握着我的手,那多年前在月光下握着我的手。
他的目光,他的祈祷,他的爱,都被关在外面,而我,独自步向不可测的命运。
所有的脸退去,所有的往事像一只弃置的牧笛。
室中间,一盏大灯俯向我仰起的脸,像一朵倒生的莲花,在虚无中燃烧着千层洁白。
花是真,花是幻,花是一切,诗诗。
今夜太长,我已疲倦,疲于挣扎,我只想嗅嗅那朵白莲花,嗅嗅那亘古不散的幽香。
花是你,花是我,花是我们永恒的爱情,诗诗。
四月的迷迭香,似乎是四月,似乎是原野,似乎是蝶翅乱扑的花之谷。
“呼吸,深深的呼吸吧!
”从遥远的地方,有那样温柔的声音传来。
我在何处?
诗诗,疼痛渐远,我听见金属的碰撞声,我闻着那样沁人的香息。
你在何处,诗诗。
“用力!
已经看见头了!
用力!
”诗诗,我是星辰,在崩裂中涣散。
而你,诗诗,你是一颗全新的星,新而亮,你的光将照彻今夜。
诗诗,我望着自己,因汗和血而潮湿的自己,忽然感到十字架并不可怕,髑髅地并不可怕,荆棘冠冕并不可怕,孤绝并不可怕——如果有对象可以爱,如果有生命可为之奉献,如果有理想可前去流血。
“呼吸,深深的呼吸。
”何等的迷迭香,诗诗,我就浮在那样的花香里,浮在那样无所惧的?
里。
早晨已经来,万象寂然,宇宙重新回到太古,混涸而空虚,只有迷迭香,沁人如醉的迷迭香,诗诗,你在那里?
我仍清楚地感到手术刀的宰割,我仍能感到温热的血在流,血,以及泪。
我仍感觉到我苦苦的等待。
歌手像高悬的瀑布,你猝然离开了我。
“恭喜啊,是男孩。
”“谢谢。
”我小声的说,安慰,而又悲哀。
我几乎可以听到他们剪断脐带的声音,我们的生命就此分割了,分割了,以一把利剪。
诗诗,而今而后,虽然表面上我们将住在一个屋子里,我将乳养你,抱你,亲吻你,用歌声送你去每晚的梦中,但无论如何,你将是你自己了。
你的眼泪,你的欢笑,都将与我无份,你将搧动你自己的羽翼,飞向你自己的晴空。
诗诗,可是我为什么哭泣,为什么我老想着要挽回什么。
世上有什么角色比母亲更孤单,诗诗,她们是注定要哭泣的,诗诗,容我牵你的手,让我们尽可能地接近。
而当你飞翔时,容我站在较高的山头上,去为你担心每一片过往的云。
他们为什么不给我看你的脸,我疲惫地沉默着。
但忽然,我听见你的哭。
那是一首诗,诗诗。
这是一种怎样的和谐呢?
啼哭,却充满欢欣,你像你的父亲,有着美好的tenor嗓子,我一听就知道。
而诗诗,我的年幼的歌手,什么是你的主题呢?
一些赞美?
一些感谢?
一些敬畏?
一些迷惘?
但不管如何,它们感动了我,那样简单的旋律。
诗诗,让你的歌持续,持续在生命的死寂中。
诗诗,我们不常听到流泉,我们不常听到松风,我们不常有伯牙,不常有华格纳,但我们永远有婴孩。
有婴孩的地方便有音乐,神秘而美丽,像传抄自重重叠叠的天外。
诗诗,歌手,愿你的生命是一只庄严的歌,有声,或者无声,去充满人心的溪谷。
丁大夫和画
丁大夫来自很远的地方,诗诗,很远很远的爱尔兰,你不曾知道他,他不曾知道你。
当他还是一个吹着风笛的小男孩,他何尝知道半个世纪以后,他将为一个黑发黑睛的孩子引渡?
诗诗,是一双怎样的手安排他成为你所见到的第一张脸孔?
他有多么好看的金发和金眉,他和善的眼神和红扑扑的婴儿般的脸颊使人觉得他永远都在笑。
当去年初夏,他从化验室中走出来,对我说“恭喜你”的时候,我真想吻他的手。
他明亮的
浅棕色的眼睛里充满了了解和美善,诗诗,让我们爱他。
而今天早晨,他以箝子箝你巨大的头颅,诗诗,于是你就被带进世界。
当一切结束,终夜不曾好睡的他舒了一口气。
有人在为我换干净的褥单,他忽然说:
“看啊,我可以到巴黎去,我画得比他们好。
”满室的护士都笑了,我也笑,忽然,我才发现我疲倦得有多么厉害。
他们把那幅画拿走了,那幅以我的血我的爱绘成的画,诗诗,那是你所见的第一幅画,生和
死都在其上,诗诗,此外不复有画。
推车,甜蜜的推车,产房外有忙碌的长廊,长廊外有既忧苦又欢悦的世界,诗诗。
丁大夫来到我的床边,和你愣然的父亲握手。
“让我们来祈祷。
”他说,合上他厚而大的巴掌——那是医治者的掌,也是祈祷者的掌,我不知道我更爱他的那一种掌。
“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地上造了一个新的人,保守他,使他正直,帮助他,使他有用。
”诗诗,那时,我哭了。
诗诗,廿七年过去,直到今晨,我才忽然发现,什么是人,我才了解,什么是生存,我才彻悟,什么是上帝。
诗诗,让我们爱他,爱你生命中第一张脸,爱所有的脸——可爱的,以及不可爱的,圣洁的,以及有罪的,欢愉的,以及悲哀的。
直受到生命的末端,爱你黑瞳中最后的脸。
诗诗。
红樱无端的,我梦见夹道的红樱。
梦中的樱树多么高,多么艳,我的梦遂像史诗中的特洛城,整个地被燃着了,我几乎可以听见火焰的劈啪声。
而诗诗,我骑一辆跑车,在山路上曲折而前。
我觉得我在飞。
于是,我醒来,我仍躺在医院白得出奇的被褥上。
那些樱花呢?
那些整个春季里真正只能红上三、五天的樱瓣呢?
因此就想起那些山水,那些花鸟,那些隔在病室之外世界。
诗诗,我曾狂热地爱过那一切,但现在,我却被禁锢,每天等待四小时一次的会面,等待你红于樱的小脸。
当你偶然微笑,我的心竟觉得容不下那么多的喜悦,所谓母亲,竟是那么卑微的一个角色。
但为什么,当我自一个奇特的梦中醒来,我竟感到悲哀。
春花的世界似乎离我渐远了,那种悠然的岁月也向我挥手作别。
而今而后,我只能生活在你的世界里,守着你的摇篮,等待你的学步,直到你走出我的视线。
我闭上眼睛,想再梦一次樱树——那些长在野外,临水自红的樱树,但它们竟不肯再来了。
想起十六岁那年,站在女子中学的花园里所感到的眩晕。
那年春天,波斯菊开得特别放浪,我站在花园中间,四望皆花,真怕自己会被那些美所击昏。
而今,诗诗,青春的梦幻渐渺,余下唯一比真实更真实,此美善更美善的,那就是你。
但诗诗,你是什么呢?
是我多梦的生命中最后的一梦吗?
祝福那些仍眩晕在花海中的少年,我也许并不羡慕他们。
但为什么?
诗诗,我感到悲哀,在白贝壳般的病房中,在红樱亮得人眼花的梦后。
在静夜里,你洞悉一切,诗诗,虽然言语于你仍陌生。
而此刻,当你熟睡如谷中无风处的小松,让我的声晋轻掠过你的梦。
如果有人授我以国君之荣,诗诗,我会退避,我自知并非治世之才。
如果有人加我以学者之尊,我会拒绝,诗诗,我自知并非渊博之士。
但有一天,我被封为母亲,那荣于国君尊于学者的地位,而我竟接受。
诗诗。
因此当你的生命在我的腹中被证实,我便惶然,如同我所孕育的不止是一个婴儿,而是一个宇宙。
世上有何其多的女子,敢于自卑一个母亲的位分,这令我惊奇。
诗诗,我曾努力于做一个好的孩子,一个好的学生,一个好的教师,一个好的人。
但此刻,我知道,我最大的荣誉将是一个好的母亲。
当你的笑意,在深夜秘密的梦中展现,我就感到自己被加冕。
而当你哭,闪闪的泪光竟使东方神话中的珠宝全为之失色。
当你的小膀臂如萝藤般缠绕着我,每一个日子都是神圣的母亲节。
当你晶然的小眼望着我,遍地都开着五月的康乃馨。
因此,如果我曾给你什么,我并不知道。
我只知道,你给我的令我惊奇,令我欢悦,令我感戴。
想像中,如果有一天你已长大,大到我们必须陌生,必须误解,那将是怎样的悲哀。
故此,我们将尽力去了解你,认识你,如同岩滩之于大海。
我愿长年地守望你,熟悉你的潮汐变幻,了解你的每一拍波涛。
我将尝试着同时去爱你那忧郁沉静的蓝和纯洁明亮的白——甚至风雨之夕的灰浊。
如果我的爱于你成为一种压力,如果我的态度过于笨拙,那么,请你原谅我,诗诗,我曾诚实地期望为你作最大的给付,我曾幻想你是世间最幸福的孩童。
如果我没有成功,你也足以自豪。
我从不认为“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如果让全能者来裁判,婴儿永远纯洁于成人。
如果我们之间有一人应向另一人学习,那便是我。
帮助我,孩子,让我自你学习人间的至善。
我永不会要求你顺承我,或者顺承传统,除了造物者自己,大地上并没有值得你顶礼膜拜的金科玉律。
世间如果有真理,那真理自在你的心中。
若我有所祈求,若我有所渴望,那便是愿你容许我更多爱你,并容许我向你支取更多的爱。
在这无风的静夜里,愿?
的语言环绕你,如同远远近近的小山。
如果你是天使
如果你是天使,诗诗,我怎能想像如果你是天使。
若是那样,你便不会在夜静时啼哭,用那样无助的声音向我说明你的需要,我便不会在寒冷的冬夜里披衣而起,我便无法享受拥你在我的双臂中,眼见你满足地重新进入酣睡的快乐。
如果你是天使,诗诗,你便不会在饥饿时转动你的颈子,噘着小嘴急急地四下索乳。
诗诗,你永不知道你那小小的动作怎样感动着我的心。
如果你是天使,在每个宁馨的午觉后,你便不会悄无声息地爬上我的大床,攀着我的脖子,吻我的两颊,并且咬我的鼻子,弄得我满脸唾津,而诗诗,我是爱这一切的。
如果你是天使,你不会钻在桌子底下,你便不会弄得满手污黑,你便不会把墨水涂得一脸,你便不会神通广大的把不知何处弄到的油漆抹得一身,但,诗诗,每当你这样做时,你就此平常可爱一千倍。
如果你是天使,你便不会扶着墙跌跌撞撞地学走路,我便无缘欣赏倒退着逗你前行的乐趣。
而你,诗诗,每当你能够多走几步,你便笑倒在地,你那毫无顾忌的大笑,震得人耳
麻,天使不会这些,不是吗?
并且,诗诗,天使怎会有属于你的好奇,天使怎会蹾在地下看一只细小的黑蚁,天使怎会在春天的夜晚讶然地用白胖的小手,指着满天的星月,天使又怎会没头没脑地去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