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起源及其宗教哲学思想.docx
《佛教的起源及其宗教哲学思想.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佛教的起源及其宗教哲学思想.docx(2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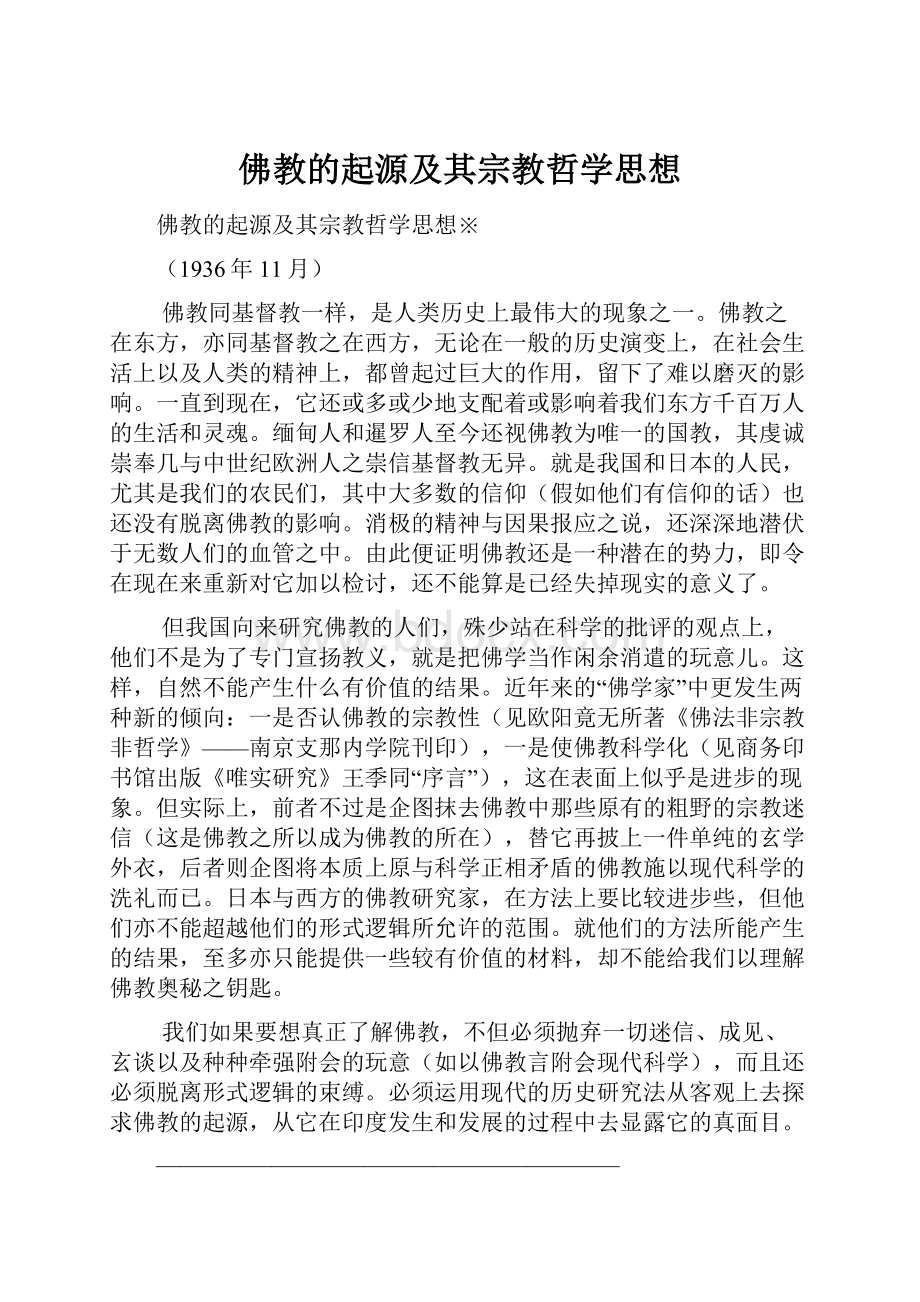
佛教的起源及其宗教哲学思想
佛教的起源及其宗教哲学思想※
(1936年11月)
佛教同基督教一样,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现象之一。
佛教之在东方,亦同基督教之在西方,无论在一般的历史演变上,在社会生活上以及人类的精神上,都曾起过巨大的作用,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影响。
一直到现在,它还或多或少地支配着或影响着我们东方千百万人的生活和灵魂。
缅甸人和暹罗人至今还视佛教为唯一的国教,其虔诚崇奉几与中世纪欧洲人之崇信基督教无异。
就是我国和日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农民们,其中大多数的信仰(假如他们有信仰的话)也还没有脱离佛教的影响。
消极的精神与因果报应之说,还深深地潜伏于无数人们的血管之中。
由此便证明佛教还是一种潜在的势力,即令在现在来重新对它加以检讨,还不能算是已经失掉现实的意义了。
但我国向来研究佛教的人们,殊少站在科学的批评的观点上,他们不是为了专门宣扬教义,就是把佛学当作闲余消遣的玩意儿。
这样,自然不能产生什么有价值的结果。
近年来的“佛学家”中更发生两种新的倾向:
一是否认佛教的宗教性(见欧阳竟无所著《佛法非宗教非哲学》——南京支那内学院刊印),一是使佛教科学化(见商务印书馆出版《唯实研究》王季同“序言”),这在表面上似乎是进步的现象。
但实际上,前者不过是企图抹去佛教中那些原有的粗野的宗教迷信(这是佛教之所以成为佛教的所在),替它再披上一件单纯的玄学外衣,后者则企图将本质上原与科学正相矛盾的佛教施以现代科学的洗礼而已。
日本与西方的佛教研究家,在方法上要比较进步些,但他们亦不能超越他们的形式逻辑所允许的范围。
就他们的方法所能产生的结果,至多亦只能提供一些较有价值的材料,却不能给我们以理解佛教奥秘之钥匙。
我们如果要想真正了解佛教,不但必须抛弃一切迷信、成见、玄谈以及种种牵强附会的玩意(如以佛教言附会现代科学),而且还必须脱离形式逻辑的束缚。
必须运用现代的历史研究法从客观上去探求佛教的起源,从它在印度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去显露它的真面目。
————————————————————
※原刊于《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三卷第四期(1936年冬季号),发表时用“欧伯”笔名。
————————————————————
教陀时代的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
佛教的创立者大家都公认是佛陀(Buddho)。
佛陀的生存年代虽至今尚无一致的确定见解,但东西学者,大概都认定他是纪元前六世纪至五世纪间人(纪元前565——486年)。
这恰当古代印度的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发生剧烈变化的时代。
在佛陀出世之前,印度的雅利安族(Arya——原为白种,与欧洲希腊人,罗马人等出于同一祖先)社会已经过了长期的发展,已经由原始的氏族共产制度进到封建王国的边界上了。
大约在纪元前千五百年顷,雅利安人以游牧民族由波斯侵入印度的五河流域(即今般遮布一带),征服原有的土著民族(Dravida和Kalaria族等),才开始从事农业的定居生活。
随后更逐渐向东方的恒河流域进展。
到佛陀降生时已经占领整个的恒河流域,而开始向德干高原及南印度开拓了。
自雅利安族开始进展五河流域至佛生,这一千年间,史家通称之为“吠陀时代”。
因为反映这一整个时期的史实遗留有最古的典籍四吠陀(Veda,为赞美神祗的颂歌)及其后来附加之《梵书》(Brahmana)和《奥义书》(Upanisad)等。
四吠陀中以《梨俱吠陀》(Rgveda)为最古,其代表的时代约与雅利安族停居五河流域的时期相当(约在纪元前1500——1000年)。
《梵书》和《奥义书》则约可代表开拓恒河流域的时期(约当纪元前1000——500年)。
《梵书》又可代表这时期中的前半期,《奥义书》可代表后半期。
《沙磨吠陀》(Samaveda)。
《夜尤吠陀》(Yajurveda)和《阿达婆吠陀》(Atharvaveda)等大约为从五河到恒河之过渡期间的产品,故可代表着过渡的时代。
依据《梨俱吠陀》,雅利安族在五河流域时代虽以开始经营农业,但还十分幼稚,牧业似乎还占主要的地位,至少在初期是如此。
那时的社会组织完全以氏族血统关系为基础。
最初共有五个氏族,每个氏族分为几个VIS,每个VIS,又分为几个Grama——这便是当时氏族社会之最基本的公社组织。
一切土地、牧场、森林、房屋、工具乃至生产品等,均归公有,由公社会议公举的族长管理和分配。
保护牧场修理水道以及祭神和对外战争等亦由族长指挥。
那时除被征服的土著民族被降为奴隶(称之为首陀罗Sudra——这个字含有被压迫民族和被剥削阶级两种意思)外,雅利安族内部尚无阶级存在。
此种情形,差不多通过五河流域时代数百年间,没有什么根本的变化——就是说,原始的氏族共产制在基本结构上一直维持下来。
但雅利安族既经占领恒河流域之后,甚至在占领的过程中,情形就起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因为恒河流域是雨水丰富而土壤肥沃的大平原,最宜于农业耕种;同时又因为征服该区域中之众多的土著民族,获得了广大的奴隶劳动,于是农业生产便大大地增加起来了。
并且开始运用了大群的奴隶劳动以经营大规模的田庄。
在另一方面就是商业经济之迅速的发展。
在五河流域时代虽早已开始了商品的交换,但还只限于少数特殊的生产品(如工具等),并且大半是在氏族与氏族团体之间,还带着偶然的物与物交换的性质。
这由于那时代的末期尚不知使用金银为货币,而仅以牦牛为交换的标准可以看出来。
但到此时期,尤其到了此期之后半期的《奥义书》时代,商品交换已经成了在经济上最重要的因素,不但超越了氏族团体的狭小范围,而且已然集中到许多巨大的商业城市之中了。
当佛陀出世之时,恒河流域中已有许多著名的新兴城市兴起,如摩辿陀(Magadha)之王舍城(Rajagrha),桥萨罗(Kassala)之舍卫城(Savatthi),弥嗟(Vamsa)之桥萨弥(Kasambi),迦尸(Kassa)之罗奈城以及其他许多城市,均为人口密集,商业繁盛之中心。
而且那时印度的商品已经超越了印度的范围,经过波斯,巴比仑或阿拉伯而达到地中海沿岸各国去了※。
随着商业范围的推广和商品需要的刺激,于是手工业也就自然发达起来。
王舍城,舍卫城,罗奈城及其他城市,不但是新起的广大的商品市场,而且同时也是手工业者集中的所在地。
绢织物,棉布,象牙及宝石等,均为当时印度输出西方的重要商品。
此外,还有高利贷资本也跟着商业的足迹在城乡各方面展布了起来。
————————————————————
※黑尔茨费德(Herzfeld)在其所著《古代犹太贸易史》(CommercialHistoryOfJewsInAntiquity)中叙述纪元前六七世纪以前从东方到西方的商业道路时,曾有这样的一段说:
“……还有别的一条路线,从波斯到格尔拉(Gerrha)收集巴比仑及印度的货物,横贯阿拉伯而达到彼德拉(Petra)。
再由彼德拉分为三条路线:
一条到埃及。
”这便显然证明古代的印度已经加入古代中亚细亚,小亚细亚和地中海诸国的国际贸易圈中了。
————————————————————
新的经济的发展自然要形成新的阶级,促进新的阶级的对立。
我们前面说过,在五河流域时代,只有征服民族(雅利安族)与被征服民族(首陀罗)的区分,尚无阶级的存在。
但在这时,阶级的对立便已十分明显而且很尖锐化了。
自然这种形势是经过长期间的逐渐发展所形成的。
最初是由那些氏族的族长队伍中发生两种拥有专门技能的分子:
即祈祷神灵的祭司和指导战争的军事领袖。
但在起初,这两种分子除分任祭神和指挥战争外,尚无何种特权。
随后因占领的土地日广,经济日见发达,财富日见增加,于是祭司们和军事领袖们便逐渐攫取了各种剩余产品归为己有,并替自己规定种种特权了。
其中最重要的是废除原有公社选举制(原来的祭司和军事领袖均由公社全体会议选举和罢免),把他们的职位改为终身制和世袭制。
这样,便产生了婆罗门(Brahman——祭司)和刹帝利(Ksatriya——贵族)两个特权等级。
当时商业发达,新的商业城市兴起时,又产生了商人,手工业者和游民无产者的新阶级成分。
另一方面,商品和货币乃至高利贷资本跟着商业的触须伸入农村,刺激了私有制度的发展,同时又因有奴隶大农场的设立,于是公社的土地公有制度发生动摇,土地变成可买卖的商品了。
这样,在乡村中又产生了无土地的农民和拥有大宗土地的地主,这恰同城市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互相对立——这便是在古代印度氏族共产社会的废墟上所展开来的一副新的阶级画图。
新的阶级的产生,自然要威胁到旧特权阶级的地位和利益。
首先感觉到这种威胁的是聪明的婆罗门——垄断当时一切指挥的知识分子。
因此婆罗门便想尽种种方法,利用当时人民对于神的迷信,把自己高高地举起在一切人民的头上,攫取了一切特权。
它擅自将人民分成婆罗门,刹帝利,吠舍(Vaisya,包括工商农等)和首陀罗四姓(即四个等级)。
它并援引《梨俱吠陀》中的“原人歌”(PurusaSukta,此歌定非《梨俱吠陀》所原有,大概为婆罗门得势后所伪造附加于其上者),谓由原人之头生婆罗门,由其肩生刹帝利,由其腿生吠舍,而首陀罗则由其足所生。
企图以此证明“四姓间有先天的差异”,为神所命定,绝对不能更改。
依据这种伪造的原理,于是婆罗门便将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权利都重新加以分配。
它说(又是一种伪造)婆罗门的保护神为祈祷主(Brhaspati——所谓梵神宇宙之主宰神中之王),刹帝利的保护神为恩陀罗瓦奴那(Indra-Varuna),吠舍的为一切神(Visvedeveh),至于首陀罗则连保护神都没有(见Pancavimsa《梵书》)。
其次,它声称自己是“人神”,应当受人民的“布施”(婆罗门所收受的布施,等于欧洲中世纪基督教会所受之“什一税”),就是说,它如天神一样,应当领受人民的供物。
这种为婆罗门至上主义。
它按四姓的阶位规定各自的终身职务。
它把自己放在神与人的中间地位,一方面代表神对人民表示神的意志,另方面又替人民向神求福免祸。
所以祭神便成为它唯一的职务,也就是它唯一的能够操纵人民生死祸福的特权;因为人民只有经过它这个经纪人才能接近神,向神办交涉。
正因为这点,它把祭神的颂歌书《吠陀》经抬高到与神同等的地位,凡《吠陀》中所言者均认为是神的意见,是神圣的法律,绝对不能移易,人民只有遵守的义务(谁要是违反了《吠陀》的教言,就是表示对于神的反叛)。
这叫做《吠陀》神圣主义。
因此,婆罗门后来又制造了各种《梵书》、《奥义书》(有一部分《奥义书》为刹帝利所作)和《经书》(Sutra)等,依照自己的意见以解释和发挥《吠陀》,使《吠陀》中的教言更能有利于它这个阶级的地位。
婆罗门不仅垄断了祭神的特权,而且垄断了一切知识,它视自己为《吠陀》或其他传说的唯一保有者。
不论是刹帝利或吠舍,要想学习《吠陀》或其他知识,都必须从师于它。
它给刹帝利规定的任务是:
执干戈以御外敌,保护宗教(即婆罗门教),保护有情的(婆罗门和吠舍的)财产,维持境内的安宁秩序。
并规定刹帝利必须以婆罗门为帝师,不但不得向婆罗门收租税,还必须纳款于婆罗门,名之为“布施”。
刹帝利向人民所收之租税数额,每由它代表确定(以上这些规定,均见载于Baudhayana和Apastambiya法典之中)。
吠舍(农工商等)的任务是:
终生经营各自的职业,虔祭神灵,供奉婆罗门,献纳租税于刹帝利等。
至于首陀罗,既沦为奴隶,除以劳动服事上面所叙之三姓外,当然不能有任何权利。
不许经营独立的生活,不许祈祷神灵。
因此婆罗门称自己与刹帝利和吠舍为再生族(Dvija意即除父母所生之第一生外,尚能从宗教方面获得第二生命),称首陀罗为一生族(Ekojati)为宗教所不屑救之贱民。
甚至连听唱《吠陀》赞歌也不许,而加以恐吓说:
“如果首陀罗故意听闻《吠陀》之诵声,则其耳聋,口诵《吠陀》则舌烂,心念《吠陀》则心坏等等”(Kautbuma法典)。
由此可见婆罗门代表当时上层阶级对于首陀罗之压迫和键视达到何等的程度了!
此外,婆罗门更进而严厉地规定着四姓不得互通婚姻,企图以此种人为的方法去永远隔离四姓,使不致混乱血统,因而得以保持那种“神圣”的等级制度(关于四姓的权利义务备载于《梵书》和《法经》DharmaSutra中)。
当婆罗门这一姓的人口日见增加,日趋于奢侈纵欲的时候,它便巧妙地想出了开辟财源的方法,那就是增立各种各样的祭祀名目,或将久已废弃的祭祀重新提出加以确定,迫令其他等级的人们按期举行。
这种倾向在《梵书》中已很明显地表示出来了。
迄到后来的《天启经》(SrautaSutra)和《家庭经》(GrhyaSutra)中更有详细的规定。
在《家庭经》中所规定的祭典有二类,其名目繁多,难以尽举。
即家庭中定期的主要祭祀必须举行者亦有七种之多。
甚至一个人由托胎出胎以至结婚期间所必须举行的重要祭祀亦有十二次(如受胎礼,成男礼,分发礼,出胎礼,命名礼……)。
《天启经》中所规定之祭典名目亦是同样地不可胜数。
其中有所谓供养祭(Haviryajna)一类,包括最重要的祭典有七种。
有苏摩祭(Somayjna)一类,亦包括有必须举行的八种祭祀。
以上这两类祭典都必须敦请婆罗门代为举行。
不用说,每举行一次必须有一定的报酬(所谓“供物”)。
并且连报酬的物品数额亦有明确的规定呢(如在国王举行的“力饮祭”中,便规定国王须布施婆罗门牛百七十头,衣服十七,车十七,黄金十七,即是一例)。
所以祭祀举行得愈多,婆罗门的收入也就愈富。
正因为如此,婆罗门也就愈加多多地规定祭祀的数目,愈加提高祭典的尊严与重要,愈加注重祭祀的仪式制度。
这叫做祭祀万能主义与上叙的《吠陀》神圣主义和婆罗门至上主义,统称为婆罗门教的三大纲,其被重视,恰等于后来佛教中的所谓三宝——佛法僧。
次于婆罗门的是刹帝利。
如果婆罗门是靠同神办理交涉起家,它的权威和权利是建立在神权的增长和祭典制度的发达之上,那末,刹帝利的兴起是靠着和敌人战争,而其权威与权利之扩大更是靠在战争之不断的发生和胜利上面了。
很显然地,雅利安族之占领恒河流域那样广大的区域,征服那样众多的土地,必曾经过长期的无数的凶猛战争,才能达到成功。
而这种长期的无数的战争之胜利,正是刹帝利实力之不断地膨胀。
雅利安势力向前推进一步,刹帝利的势力也就跟着前进一步。
尤其当商工发展至一定程度,城市制度发生的时候,刹帝利的高级领袖们(诸王们)便凭籍着城市的优越地位,利用城市的财富,训练较大的常备军,以从事于侵吞兼并的战争。
这种刹帝利内部的互相兼并的战争,从大叙事诗《摩诃波罗多诗篇》(Mahabharata)中明显地反映了出来。
该诗篇所描叙的是以般多国(Pandu)五王子枸罗国(Kuru)王子互相战争为中心的故事,其时间约当纪元前六七世纪,史家通称之为古代印度大战乱的时代。
实际上,这并不是刹帝利内部简单地互相残杀,而是反映了整个刹帝利势力之膨胀,要求由那些鸡零狗碎的小国兼并为大国的一种倾向。
自然,此种倾向又恰是反映了当时商业经济的要求。
因为那些族长式的无数小国的互相对立,互相仇视,对于新兴的商业经济实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障碍物了。
事实上,当佛陀出世前,在恒河流域中已经产生了几个强大的新兴国家。
如摩迦陀(Magadha),乔萨罗(Kasala),迦尸(Kase)和弥嗟(Vamsa)等。
而这几个国又恰是依靠在几个新兴的商业城市基础上(如摩迦罗之王舍城,乔萨罗之舍卫城,迦尸之罗奈城,弥嗟之乔萨迷等)。
这就够说明刹帝利发展之客观的新趋势了。
拥有广大土地和以新兴的富足的商业城市为基础的刹帝利,此时不能不感到自己手中已具有强大的物质力量。
另一方面,刹帝利在以前完全忙于军事,忙于战争,在知识上是十分幼稚的,差不多一切重大的问题都要依靠它的“国师”婆罗门来解决。
但到了这时候,刹帝利亦极力从事于知识的争取,研究《吠陀》,并参与《奥义书》的著作,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婆罗门。
“据圣德格耶云,昔有婆罗门五人,以‘普遍我’问于吠陀学者阿尔尼(UddalolahaAruni),阿尔尼不能答,于是六人至卡义凯尔王(AsavapatiKaikeya)处而受其教。
又据《布利哈德奥义书》云,吠陀学者巴那格(GagyaBalaki)访问卡西国王阿阇士问梵之教义,王曰,‘婆罗门乞教于刹帝利,虽反于古昔,特余欲教汝’,乃授之教义”(高楠顺次等著《印度宗教哲学史》商务版242页)。
由此便足以证明刹帝利在知识上之进步,为不可否认的事实了。
刹帝利的物质实力即经如彼膨胀,而知识又如此增进,自然会发生一种提高自己权威和权利的要求。
这首先就要对于婆罗门从前替它所规定的阶位(在四姓的第二位),所规定的权利,感到不满。
而对于婆罗门之无餍足地以祭祀为名强令它和吠舍“布施”,尤难忍受。
于是刹帝利与婆罗门的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吠舍中的商人是一个完全新兴的阶级。
它随着商业范围的扩大与城市势力的增长而发达起来。
它挟着商品和借贷资本深入穷乡僻壤之中,搜刮农民的剩余产品,甚至农民必需的生活费亦走入它的腰包了。
并且收买了农民的土地。
城市的手工业者更不用说要完全依靠它,因为它是他们的生产品和原料以及借贷资本的主要供给者。
就城市的实际经济生活说,商人是城市的主人。
而且这个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因为经营商业于海外,往来各国,不但获得了大宗的财富,并且扩大了眼界,获得了许多新奇的知识。
因此,这个阶级对于婆罗门的那种妄自尊大,及婆罗门对于它的地位及权利的限制,(与农民及手工业者同一看待),尤其是那种繁多的祭祀和带强迫性的布施,都感觉得不满,渐渐地不能忍受了。
农民和手工业者,在当时社会中是一个最广大的生产群众,是最感受压迫,剥削和痛苦的群众。
但他们所受的压迫,和剥削,不只是婆罗门,还有刹帝利的贵族和商人。
不过婆罗门当时所采取的压迫和剥削形式是比较地明显和露骨。
因为一切祭祀,法律和种种社会规程,大都由婆罗门所规定。
譬如对于四姓的权利义务之种种限制,就是最显眼的例子。
这样,农民和手工业者对于婆罗门之怀抱不满,甚至愤恨,那是很自然的了。
但这些群众有一弱点,尤其是农民们,既无知识,又特别富于保守性,所以他们对于婆罗门的压迫和剥削(如强索供物)虽深怀不满,而对于婆罗门的宗教大致还是信仰的——这便是婆罗门教在当时及以后尚能保持其相当地位之唯一基础。
至于首陀罗,这个被征服的奴隶阶级,其所受之压迫、剥削、贱视、虐待及种种痛苦,自然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因为商业的发达,生产品的增加,同时就要刺激统治阶级和剥削者的奢侈欲的发展和谋利心之亢进。
但要无限制地满足他们的奢侈欲和谋利心,就只有无限制地剥削奴隶。
这是在古代的希腊和罗马的奴隶社会中所证明过的,古代的印度事实亦完全如此。
所以首陀罗由于它的特殊的奴隶地位和所受之特殊的虐待,对于整个的雅利安族的统治者和剥削者,不论是婆罗门,刹帝利或吠舍(主要是吠舍中的商人)都是怀着敌视与痛恨的。
但它必然特别痛恨婆罗门,因为婆罗门是四姓制度的首倡者,立法者。
婆罗门不仅剥夺了它一切物质上的权利,而且剥夺了它一切精神上的权利,剥夺了它的灵魂(如禁止它信仰宗教,祭祀神灵,以及学习《吠陀》和听唱颂歌等)。
由上叙的情形看来,古代印度的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明显地发生了空前的剧烈的变化:
私有制度的发生,商业的发达,土地公有制的破坏,新兴城市的兴起,贵族势力的膨胀,商人阶级的出现,农民的破产,手工业者的贫穷,以及奴隶之遭受极端虐待——这一切都证明不但原始氏族的共有制度久已甭解,即后来婆罗门所创建的“四姓”制度亦已根本动摇,“婆罗门至上主义”已成为众矢之的,尤其是刹帝利对它表示不能忍受,大有取而代之之野心,于是酝酿已久的古代印度的阶级斗争的戏剧便从此正式开幕了。
反婆罗门运动与佛教的产生
这种斗争的表演,自然要带着宗教的面具,从宗教改革思想和创立新教运动中表现出来。
这差不多是一切古代社会运动的公律。
即欧洲中古时代的一切斗争亦多是如此。
这恰如恩格斯(E.Engels)所说:
“……中世纪的一切群众运动,必然都带上一种宗教的面具……但是,在宗教的兴奋背后,却经常地隐藏着切实的人世间的利益”(《原始基督教史》)。
不过欧洲中世纪末期反基督的运动大都为当时的资产阶级领导,而在古代印度的反婆罗门教运动,则全为刹帝利(贵族)所主动指使而已。
在起初,刹帝利尚不敢公然站在反婆罗门教的地位,它只是在婆罗门教的范围内表示一些异议,运用自己的观点去解释《吠陀经》,暗暗地反对婆罗门的教义——这从《奥义书》中明显地反映了出来(《奥义书》为婆罗门和刹帝利共同的产品,已为东西古代印度研究家所共认)。
例如婆罗门所极力鼓吹的祭祀万能主义和四姓制度,《奥义书》中便隐含有排斥和轻视之倾向;婆罗门在《梵书》(这是纯粹婆罗门主义的作品)中所极力宣扬之梵神,在某些《奥义书》中则把它变为一种纯粹抽象的宇宙原理,并力言“梵即我(Atman),我即梵”,以此灭去婆罗门对于梵所赋予之神圣性,此种反婆罗门的倾向,同样表现于《摩诃波罗多诗篇》中。
“据多依森(Deussen)的意见,谓由文体上观之,《摩诃波罗多》,在《吠陀》文体(包含古《奥义书》)与华文体之间;由宗教的观点观之,一方认《吠陀》之神权,重四姓之阶级,他一方面又渐有表示非吠陀主义四姓平等主义之倾向”(《印度哲学宗教史》——388页)并且依多依森的研究,在《奥义书》和《摩诃波罗多》中已含有数论派(Samkhya)和瑜珈派(Yoga)之基本思想。
虽然,这里所谓的数论派和瑜珈派与后来《僧法经》(SankhyaSutra)所代表之数论派和跋陀阇利(Patanjali)所代表之瑜珈派,其思想主张大有差异。
但他们大体上都带有反婆罗门主峄的倾向,至少是对于婆罗门之对于《吠陀》教义的解释及其祭祀万能主义,怀抱不满,而企图进行改革者。
这种对婆罗门教怀抱不满,企图有所改革的思想运动,在起初虽然是隐藏地,温和地,缓慢地进行;但一经发动便不能停止;并且愈往前进必然愈加激烈,愈加显露其独立的面貌;最后则走到公开地明目张胆地反对婆罗门教的斗争,甚至根本反对吠陀主义,乃至根本否认宗教之存在——这也是历史上一切伟大的社会运动的发展过程之自然的逻辑。
当佛陀出世时,古代印度的社会宗教改革运动,已达到了最高点。
那时反婆罗门教的党派团体,有如雨后春笋,到处发生。
通例称此等团体为沙门(Samana),以示与婆罗门区别。
最有趣的是:
这些沙门团的绝大多数均散布于恒河流域的新兴诸国中,并以这些国家为其根据地,为其活动的舞台。
其中尤以摩迦陀国为其中心。
例如佛陀最初所师事之阿罗逻迦罗摩(Alalakalama)为郁那迦罗摩子(UddakaramaUtta)均居愈摩迦陀的吠舍利(Vissali)城和王舍城附近。
他们都是沙门团的领袖。
后来归依佛陀之三迦叶所代表的罗底迦团(Latilika)亦为摩迦陀大沙门团之一。
所谓有名的六师所代表的团体及佛陀本人所率领的沙门团,虽散布于新兴各国,但亦多以王舍城为活动的中心地。
《五分律》中曾载有摩迦陀王频毗沙罗之弟迦留常设一大齐,会集九十六种外道互相讨论的纪事。
这些情形充分证明了:
这些新兴国家因为刹帝利在实际上已占着优势,它需要打击婆罗门,夺取在四姓中的第一席地,于是它便提倡并保护一切反婆罗门的团体和运动。
因此,这些新兴的国家便成了当时一切反婆罗门团体之自由生长的绝好园地,它们可以在这里自由发表反婆罗门的或其他的任何意见,它们各派间可以自由地相互讨论并向民众宣传,而不致受到婆罗门的无礼干涉。
于是关于宗教上,哲学上以及一般的人生问题上之一切新鲜活泼的见解,像潮水一般地涌现出来了。
这样便形成了古代印度文化史上之最光辉的一页。
在当时各种派别,各种沙门团中,其影响比较大而其思想又略可考证者(依据《沙门果经》所载),是所谓著名的六师。
六师在大体上都是非难吠陀神圣主义,反对祭祀万能主义和婆罗门至上主义的。
然而他们反对的出发点及其论调殊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
例如富兰那迦叶(PurunaKassapa)是由伦理的观点出发。
在他看来,世界无所谓善与恶,更无善恶报应之说。
所谓善与恶都依习惯而定。
由这一见解推论下去,则婆罗门所谓凡遵从《吠陀》教言者为善,反之便是恶,祀神者能得善根,反之,必得恶报以及轮回因果报应说——这一切都变成毫无根据了。
末迦黎拘舍罗(MakkhaliGosala)则主张极端的“定命论”(Fatalism)。
他以为一切皆由自然运行的规律所决定,人为的任何努力都无用处。
人的行为与命运,只有听其自然,前后经过数百劫,自然会达到解脱之境。
由这种观点看来,婆罗门的祀神求福与